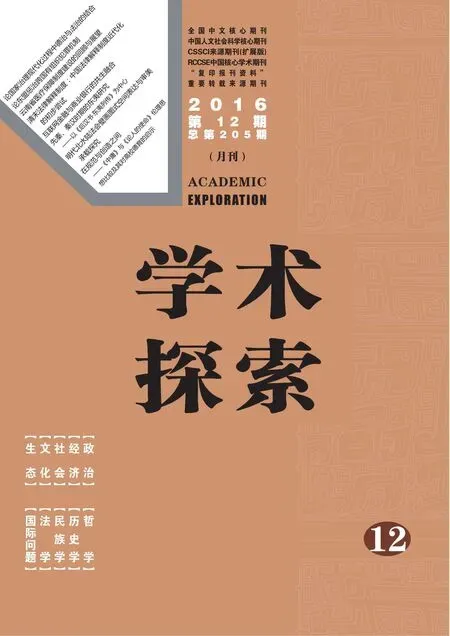清末法律解释制度: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近代化的初步尝试
李相森
(南京审计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清末法律解释制度: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近代化的初步尝试
李相森
(南京审计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清末变法改制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主管机关解答下级机关法律疑问的问答式法律解释制度。此种制度具有解释权力集中而解释主体多元、行政指示色彩浓厚、倾向于立法以及实用主义等特征,适应了当时法制变革的需要,有其独特性及现实合理性,但也存在以解释代行立法、指挥行政及审判活动、解释前后不一等种种问题。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承上启下,既带有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实践的影子,又为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确立及发达做了准备,是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近代化的初步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法律解释制度;宪政编查馆;问答式解释;统一法令解释;案件请示
法律解释与法律的诞生同其久远,可谓有法律即有对法律的解释活动。传统中国成文法典发达,并有注释律法的法律解释传统,但始终没有建构起系统完善的法律解释制度。直至清末,统治者为适应法制变革的现实需要,才初步构建了中国本土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制度。在近代以来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既受西方法律解释理论和制度的影响,又带有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实践的基因,具有独特的制度样态及运行逻辑。作为中国近代法律解释制度的源头,清末法律解释制度及其实践为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确立及发达做了准备,奠定了中国本土法律解释制度的基本形态,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我国当前法律解释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仍能从清末法律解释制度那里发现其最早的影子。然而,直至今天,我们对20世纪以来建立现代法律体制过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仍不甚了解。[1](P7)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忽视,更是发展完善我国当前法律解释制度的损失。因此,寻找中国近代法律解释制度的源头,探讨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具体样态及利弊得失,仍有其必要与意义。
一、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形成
清末变法改制过程中,地方各级官署在遵照全新的法律章程办理具体事务时,遇有疑问,不能自决,遂请求上级主管机关予以指示。中央各部、衙门对下级所提的疑问进行解答,涉及对相关法律章程的解释。各下级机关则遵照中央主管机关的解释适用法律,处理行政、司法事务。于是便形成了该管中央机关解答下级机关所提请的法律疑问,并对下级机关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解释制度。追根溯源,清末法律解释的制度化实践肇始于1908年宪政编查馆对《谘议局章程》及《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的解释。
(一)宪政编查馆法律解释权的获得
1905年11月25日,为配合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清廷谕令建立考察政治馆。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由考察政治馆主持设立谘议局、资政院等立宪预备活动。1907年8月,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直属军机处。宪政编查馆继承了考察政治馆办理宪政的职能,“从前设立考察政治馆,原为办理宪政,一切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自应派员专司其事,以重责成。”[2](P45~46)此处所谓的“编制法规”主要是指宪政编查馆有权对各种法典、单行法规草案进行考核。《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1907年8月24日颁行)第11条规定:“本馆有统一全国法制之责,除法典草案应由法律馆奏交本馆考核外,如各部院、各省法制有应修改及增订者,得随时咨明该管衙门办理,或会同起草,或由该管衙门起草咨送本馆考核,临时酌定。”[3]从《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对宪政编查馆职能的规定,并不能看出宪政编查馆具有法律解释权。但作为钦定的皇家服务机构以及预备立宪的核心机关,宪政编查馆统一全国法制之责实际上包含了对法律解释的统一。
1908年7月,《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颁布施行。宪政编查馆要求各省在筹办谘议局、选举议员的过程中,如果遇有法律疑义,“随时咨询本馆,以便详为解释”。[4]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具有议会性质的谘议局实属新鲜事物,创办之初无所参照。加之章程的有关规定又过于原则与抽象,而各省区的具体情况不一。故各省在适用章程之时,确实遇到了种种疑问。于是,各省衙门遂电咨宪政编查馆请求解答。宪政编查馆则针对这些疑义,条分缕析,明晰律意,解答疑问,并将相关的问答往来电文登载于当时的中央政府机关报——《政治官报》之上。宪政编查馆对《谘议局章程》及《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疑义的解释开启了清末法律解释制度化实践的序幕。
宪政编查馆不仅通过自我授权,获得了法律解释权,而且还试图使其解释获得“官定解释”的权威和效力,并将自身解释活动正当化、制度化。在实际行使法律解释权一年之后的1909年8月31日,宪政编查馆上奏《奏定章程应以官定解释为据片》。其文曰:
历来法律章程内笺注解释,皆系由在事臣工纂辑,奏请钦定,方准颁行。其私家撰著律例注解之类,未经呈进者,一概不得援用。诚以立法之权统之君上,断不容人自为说,致淆观听,而紊政纲。自上年《谘议局章程》通行后,各省遇有疑义皆电咨臣馆,随答随复,或推广待申之意,或驳正质难之词,皆期得所折中,俾免阻碍。已由臣馆将节次答复电稿、咨稿汇印成册,先后通咨各省,一示奉行者以率循,一资讲习者之研究。嗣后京外各衙门于奏定章程有疑义者,应以官定解释之说为据。其各处坊间所刻之私家笺注解释均不得援以为据,以免辗转相承,致滋谬误。臣等为慎重立法起见,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5]
在该奏文中,宪政编查馆对官定解释与私家解释做出了区分。首先,两种解释的主体不同,一为由有法律解释权的官方做出;一为由无法律解释权的私人做出。其次,两种解释的效力迥异,一可被援以为据,具有法律效力;一则不得被援以为据,不具法律效力。之所以要以官定解释为准据,是因为“立法之权统之君上,断不容人自为说,致淆观听,而紊政纲”。在宪政编查馆看来,其对法律疑义的解答显然属于官定解释,其法律解释权是君主立法权的自然延伸,或者说是来自君主之授权。该奏文上呈之后,奉旨依议,获得了君主的许可。由此,宪政编查馆的法律解释活动获得了正当的权力依据。这标志着传统中国与立法活动或行政指令混为一体的法律解释开始成为一项独立的制度。
(二)其他中央机关的法律解释权
清末法律解释权大致按照“谁主管,谁解释”的原则在各中央机关间进行分配,各该管中央机关皆有权解释与本部事务有关的法令法规。实践中,除宪政编查馆外,民政部、法部、大理院、陆军部、资政院等中央机关都曾解答下级衙门提出的与自身主管事务相关的法律疑问,进行法律解释。
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十一日,热河都统致电宪政编查馆请求解释《城镇乡自治章程》的相关条文。宪政编查馆则回复称:“地方自治为民政部本管事务,各省订该章程如有疑义,应随时咨询民政部决定。”[6]热河都统遂致电民政部请求解释。可见,民政部享有对地方自治相关法律章程的解释权。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宪政编查馆会同法部上奏的《司法行政分权遇有疑义咨询馆部核定办法片》称,为配合各省审判厅筹备设立工作,“嗣后各省凡属司法、行政分权诸大端遇有疑义之处,咨询馆、部,拟即由臣馆会同臣部随时核定,咨行办理。其咨行事项但系合于现行司法制度及与新颁法令并历次奏案不相抵触者,应以馆、部咨行办法为准,以为提纲挈领之计,而收整齐划一之功。”[7]由宪政编查馆会同法部对于司法、行政分权的相关疑义进行解答,可见法部亦享有法律解释权。
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10年2月7日),清廷颁布的《法院编制法》第35条规定:“大理院卿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明确赋予大理院以统一解释法令权,由大理院对法令做出最终的、权威的解释。清末大理院亦曾实际行使统一解释法令权。近人笔记中记载:“外省审检厅有疑义,电院请示解释者,向由毕业生出身之推事,或小京官拟答复稿。”[8](P556)由此可知,各级审判厅、检察厅遇有事关法律适用的疑问会提交大理院请求解释;大理院在接到法律解释请求后,则由推事(即审判人员)拟具解答稿予以解释。
同样,根据“谁主管,谁解释”的原则,与军事事务有关的法令疑问应提请陆军部解释;而资政院则有权对与议会筹备事务有关的法令疑问进行解答。例如,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陆军部应江宁第九镇徐统制的提请对《补官任职考绩章程》“统带所属各军职系由统带考绩,其上官附记格内”之规定中的“上官”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解释;[9]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署山东巡抚宝琦就《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第10条、第12条所规定的议员额数及监督员的复选权限等与议会事务相关的问题请求资政院解释。[10]
二、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运行
(一)“提问—解答”的解释程式
在清末法律解释制度中,法律解释程序的启动首先需要有请求者提请解释。具有法律解释权的机关在收到解释请求后,针对提请者的法律疑问,做出明确的解释答复。此种法律解释的运行遵循“提问—解答”的程式,可称之为“问答式解释”。兹举宪政编查馆解释《谘议局选举章程》之一例以示此种问答式解释的具体运行程序。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初二日云贵总督致电宪政编查馆:
宪政编查馆钧鉴:《选举章程》第九十八条所谓选举关系人者指何种人而言?一百一条二项云其所漏泄非事实者,应作何解?又五十四条所谓姓名是否指被选人言?查被选人资格宽于选举人,被选之人似不以选举人名册为限。姓名之符否,如何对照?又本章投票采无名单记法,若此姓名指选举人言,更无从对照。敬请钧示,以免误解。锡良叩。东。[11]
十月初五日宪政编查馆复电云贵总督:
……至《选举章程》第九十八条所载选举关系人指为游扬被选举人者而言。又一百一条第二项所载其所漏泄非事实一语,谓漏泄之姓名系属捏造,以其足以淆惑听闻,故并处罚。又五十四条所谓姓名不符,此姓名二字应作名数解,谓对照票数与名数多寡是否相符,非指被选举人而言。此复。宪政编查馆。微。[12]
由上列往来电文可以明晰宪政编查馆解释法律活动的大体步骤。请求解答者在电文中明确“乞请”宪政编查馆对法律条文用语、律意进行“解释”“钧示”。宪政编查馆则对法律用语及条文之意义予以界定、阐明。至于宪政编查馆接到解释请求后的处理,包括解答案的拟稿、商讨、确定、刊发等的具体操作程序,因笔者尚未见及相关史料,尚不明确,但必定有一套固定的惯行程式。*汪荣宝曾任宪政编查馆编制局正科员,在其日记中留有宪政编查馆解释法令活动的记载。如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日(1909年6月26日)日记载:“饭后到宪政馆,拟覆湘抚询谘议局选举疑义电稿一件。”可见,解答法令疑义可由编制局科员拟稿答复。同年五月十四日(1909年7月1日)日记载:“江督电询馆定《各省调查局章程》‘掌调查督抚权限内之单行法及行政规章之异同’一语应如何解释,当经电复,以法律与命令之区别解释单行法及行政规章之异同。旋又咨询‘以旧制言之,何者为法,何者为令,请比附示遵’。本日与仲和、伯平、绶金、子东诸君拟一复文,议论数刻,属稿未成而散。”其中,仲和即章宗祥,为编制局副局长;伯平即胡礽泰、绶金即董康,二人皆为编制局副科员;子东即邹嘉来,时任外务部右侍郎,似与宪政编查馆事务无关。由此可推知,在遇有法令解释上的疑难问题时,可由科员会同拟稿答复。参见汪荣宝.汪荣宝日记[M].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30,31.宪政编查馆若认为来电所请求解答的疑问是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则会将解答案通电各省知悉遵行,以免各地重复提请解释。比如1909年12月18日,宪政编查馆就寄居人选举资格问题统一致电各省督抚。[13]宪政编查馆还将其历次答复电稿与下级机关的咨请稿汇印成册,编为《谘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解释会钞》,*据学者研究,《谘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解释会钞》共出11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宣统三年二月《谘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解释会钞》第10册通行各省。宣统三年六月《政治官报》所刊售书广告中,有《谘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解释会钞》,并注明“已出十一册,每册大洋一角”。参见彭剑.宪政编查馆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7.通咨各省,以为遵循。
若所请求解答的事项系与两个以上部门相关,提请主体往往请求多个部门联合进行解释。各省请求解释的电稿中,常有“宪政编查馆、民政部钧鉴”“宪政编查馆、法部钧鉴”“法部、大理院钧鉴”“宪政编查馆、法部、大理院钧鉴”等语词出现,即是同时请求多个中央机关解释。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二十八日《政治官报》载有“川督致宪政编查馆、民政部电”。四川总督认为《自治章程》第17条第1、2款与《选举章程》第5章第77条之规定有抵触,请求宪政编查馆、民政部予以解释。[14]地方自治事务为民政部主管,有关《自治章程》的疑问自归民政部解释;而谘议局筹办事务由宪政编查馆主持,《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的解释归宪政编查馆。故四川总督将疑问同时提交两机关请求解答。结果,宪政编查馆、民政部分别做出了解释。
(二)法令解释异议的解决
如果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已经做出的法令解释仍有异议,可以重新提请解释。再次提请解释时,既可以提请原来的解释主体重新解释,也可以选择向其他有权机关提起。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省某初级审判厅审理了一起违反《报律》第11条规定的案件,因情节较重应处以该条所规定之最高罚金二百元。《审判管辖章程》第5条规定:“刑事及他法令罪该罚金二百元以下归初级,二百元以上归地方”,但所谓“以下”“以上”是否包含本数并不明确。于是,对于该案的管辖问题发生疑问:如果“以下”包含本数,则该案应归初级审判厅管辖;如果“以上”包含本数,则该案应该由地方审判厅管辖。当地谘议局呈请四川总督发电文给法部、大理院,请求解释:
法部、大理院钧鉴,顷据谘议局呈,京师直隶罚金满二百元之案,向以地方审判厅为第一审。川省或有解归初级厅,亦有权宣告者。按《审判厅章程》所列刑事案件、依其他法令应该罚金二百元以上者,属地方审判管辖,则如满二百元罚金案件是否照该章程民事案例以满二百元及二百元以上者,均属地方审判,俾归一律,呈请电咨贵部院解释示复为盼。人文叩。虞。[15]
法部旋即复电称:“满二百元罚金案件应照民事案例属地方审判。”照此,“二百元以上归地方”之“以上”包含本数,本案即应归地方审判厅管辖。于是,地方审判厅受理了该案,并判决结案。
但四川高等审判厅对此却有不同意见,认为“各例章,凡称以下、以上均连本数计算”,不能“二百元以上”包含本数,而“二百元以下”却不包含本数。至于归何级审判厅管辖应根据原法令的规定判断:“如原法以二百元为终数,自归初级;原法以二百元为起数或非终数,即归地方。”而且,案件发生之时,罚金数额本难以预定,“若一达终数即不归管辖,办理殊觉不便。”[16]因此,四川高等审判厅将该法律疑问呈由四川总督,请其重新提请有权机关解答。
此次四川总督将请求解释电文的起首改为“宪政编查馆、法部、大理院钧鉴”,而不再是前次的“法部、大理院”,将宪政编查馆列为被请求解释的机关之一。最终,宪政编查馆做出了不同于法部的解释:“《审判管辖章程》以二百元上下为初级及地方审判厅管辖之区别,定章本意,称二百元以下者,指至本数而言;称以上者,指逾本数而言。”[17]据此,该违反《报律》的案件应由初级审判厅管辖。至于该案件已经由地方审判厅判结,可查照《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9条第2项办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9条第2项规定:“管辖错误发见在判决后,应将本案供招、判词抄送该管审判厅详核存案,其原判有出入时,另行提案复审。”政学社印行.大清法规大全[M].台北:考正出版社,1972:1858.
如果下级衙门认为有关法令解释不当或错误,则可提请资政院进行公议。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天谘议局曾电呈资政院,认为宪政编查馆对某单行章则的解释与章则原意不符,请求资政院予以公议。[18]资政院是正式议会成立之前的预备机关,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国会性质的机构”,[19](P3)掌有制定、修改法律的立法权。将宪政编查馆做出的法律解释提交资政院公议,由资政院做出最终、权威的解释,其背后隐含着将资政院这一“最高立法机关”视为具有审查其他主体法律解释正当与否权力的统一法律解释机关的逻辑和认识。
三、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独特性
在中西法律文化碰撞、新法旧典交替的过渡阶段中发展起来的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既受西方法律解释理论及制度的影响,也与传统中国的法律解释实践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同时在制度设置、运行、功能等方面又具有其独特之处。这些制度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法律解释权力的集中及法律解释主体的多元。宪政编查馆在《奏定章程应以官定解释为据片》中,充分显示了其统一法律解释的自觉和意愿。宪政编查馆认为立法之权统于君上,则法律解释断不容各机关及私人自为其说、自行其是,奏定章程之解释应由获得君主许可和授权的官方机构进行。从而将法律解释权限定为官方机构的专属权力。而且有权解释的官方机构主要是层级较高的中央主管机关。这表现出集中法律解释权的趋向。此种趋向在宣统元年《法院编制法》有关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权的规定中得到充分表现。而在法律解释权的具体分配上,则按照各法律章程所涉及事务的不同,分别将相关法令的解释权授予对应的中央主管部门。同时,宪政编查馆作为立宪核心机关,在整个法律解释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宪政编查馆的法律解释权范围广大,其解释对象并不限于自身所拟定的《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还包括《城镇乡自治章程》《会议厅规则》《审判厅章程》《审判管辖章程》《司法区域划分章程》等其他机关拟定的法律章则。在疑问涉及多个法律法规,需要请求宪政编查馆以及其他机关共同解答时,下级衙门往往将宪政编查馆列于首位,甚至将与宪政编查馆主管事务无关的法令疑义亦请求其解答。可见宪政编查馆在当时法律解释体制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便形成了以宪政编查馆为核心、多中央部门共同解释法律的独特法律解释体制。
第二,问答式的解释法律方式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传统中国,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并未有明确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的权力划分。各种国家机构作为君权的延伸,具体承担着国家治理及社会控制功能。因而,专制时代的中国,行政力量强大,行政机关发达,整个国家机器遵循着严格的上级指挥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则运行。清末的官制改革仿照西方三权分立模式进行,试图突破传统单一行政机关的国家机构设置状态。但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一时难以成立;司法权专属法部,但法部又是传统的行政机关;大理院虽任审判之职,却远未实现独立,在整个政治制度运行中缺少实质的影响力。因而,即使在官制改革之后,实际上有效运行的仍只是各种行政性质的机关。而且传统行政机关及其运作模式以强大的惯性继续推动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可以说,清末改革官制后的各机关衙门仍是按传统的“请示—指示”行政逻辑运行着。在各级衙门看来,请求中央主管部门对法律疑问进行解答与请求对其他行政事务进行指示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清末问答式法律解释深受传统行政运行方式影响,具有浓烈的行政色彩。
第三,法律解释具有鲜明的立法倾向。从宪政编查馆上奏的文字表述“立法之权统之君上”“为慎重立法起见”可知,宪政编查馆自认其所做的法律解释可以维护立法权威。理论上,宪政编查馆并非法定的立法机关,当时的立法大权依然掌之于君上。宪政编查馆也并未将其做出的相关解答奏请钦定,因而宪政编查馆的法令解释应无立法效力。但实际上,宪政编查馆“以政府委员之地位,权代立法者,并自立法而自解释之”。[20](P445)宪政编查馆是钦定的皇家服务机构,承担着起草、审核法律法规的准立法职能。《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即均出自宪政编查馆馆员之手。宪政编查馆的准立法机关地位,使其所做的法律解释近乎立法。而宪政编查馆将其法律解释编为《解释会钞》,通行各省,以资遵行,更是赋予自身解释以如同法律般的强大效力。民政部、法部、大理院、军政部等其他的官定解释机关做出的解释直接对下级机关产生实际拘束力,亦形同法律。各中央机关以法律解释代行立法,承担起规范创制功能,也是转型时期立法机关缺位、法典不备、法律粗糙这一特殊法制条件的现实需要。
第四,法律解释的实用主义考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仿行西方先进的宪政体制,移植全新的法律体系,上层法制变革似乎可以一蹴而就。但下级衙门在具体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则面临种种困难:一是新定之法律章程本即不完善,颇多疑义;二是将全新的法律适用于旧有的政治、社会秩序,窒碍难行;三是陌生的法律名词术语、理论观念,一时难以准确掌握,运用自如。为推行新政,强行改革,采取此种下级遇有疑问,上级予以解答指示的法令解释方式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毕竟立法者不可能预见法律实施过程中遭遇的所有特别情形以及可能产生的疑义,而执行者领会、贯彻法律的能力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具备。因而,由各中央主管机关对于各省提请解释的电文,随收随复,实用高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特殊历史社会条件下政治变革的需要。但在法律解释的权力依据、解释方式、解释程序、解释规则等问题上,清末法律解释制度及其实践却未予充分注意,有所欠缺。
四、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由于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制度设置的自发性、实用性,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有其不成熟之处,存在种种问题及不合理。在当时,宪政编查馆的法律解释即招致许多批评。《东方杂志》甚至说这些解释是“草菅人命”“弁髦奏案”。[21]而宪政编查馆作为接受委任、代行起草法律的受委托机关,却以自身解释代行立法之权,实非正当。“若以少数之政府委员,本系起草之任,遂握解释之权,则是上移专制时代君主定法之权,下夺立宪时代国民立法之权”,“迨其解释时,则直以政府委员为法之所从出,此必非预备立宪之本意也。”[20](P445)即使宪政编查馆为合格的法定的立法者,这种由立法者以解答法律疑义的方式进行法律解释的做法在当时其他法制先进国家已经式微,逐渐遭到废弃。而宪政编查馆依旧采取此种方式进行广泛的法律解释。如果说宪政编查馆以行政机关的身份指示下级行政机关,尚有可说。但宪政编查馆甚至以此指导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无疑有损于司法独立。至于法令解释过程中对同一问题重复解释,前后不一,视情而变,更是所在多有。另外,宪政编查馆将自身所作解释视为官定解释,具有强制拘束力,而排斥私家之解释,亦颇遭非议,“以少数人之私见,专挟一官字名义,与私字对举,反谓人民之解释为私家之解释,而一切抹杀之”,“政府委员既起草而取决于谕旨,则不奉谕旨之解释,安足生坚强之效力乎?”[20](P445)
与此同时,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既是对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实践的继承,更是中国现代意义上法律解释制度的初步尝试,奠定了中国本土近代法律解释制度的雏形,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地位。它为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确立做了准备,直接影响了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制度内容和形态,而且今天我国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仍能从它那里找到历史的源头。
首先,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实践向近现代法律解释制度转型的过渡者。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承续了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实践,带有传统法律解释权力集中、由官方垄断法律解释权的影子,强调官方法律解释的权威性和强制效力。同时,清末法律解释制度也受西方法律解释理论及制度的影响,如有权解释与无权解释的区分、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权的设置,开始向近代法律解释制度转型过渡。另外,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是当时特殊社会条件下法制变革的产物,首先是为满足当时政治变革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可以说,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是传统法律解释实践、西方法律解释制度及理论以及当时社会现实需要共同催生的独特产物。这也使得清末法律解释制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制度弹性,为此后相关制度的形成、完善及演化提供了空间与可能。
其次,清末法律解释制度为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确立、发达做了前期准备。民国初年因法令不备而全面继受清末所修订的法律(包括未经公布的法律草案)。清末初步建立的法律制度也得以在民国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完善。换言之,民国法律解释制度就是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延续和改进。民国最高司法机关(大理院、最高法院、司法院)统一解释法令制度的规范依据直接来源于清末《法院编制法》关于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权的规定。清末法律解释制度“问答式解释”的运行模式也被民国法律解释制度所继承。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解释例皆是对各适格主体所提起的法律疑问的解答。民国时期,解释例具有普遍的拘束力,与立法无异,承担起规范创制功能。这也与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立法倾向相关。可以说,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法律解释权的配置、解释制度的具体运行、解释的效力等全面影响了民国法律解释制度。
最后,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影响波及当下。清末法律解释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带有的一些“恶”的基因,直接影响了此后我国司法制度的健康发展。清末法律解释具有立法倾向,各中央主管机关的解释实质上即是法令,对下级法律适用、执行机关具有强制约束力。在清末法律体系不完备的历史情势下,由相关机关以法律解释的方式进行规范补充尚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我国当前的司法解释制度仍存在以解释进行抽象立法的现象,模糊了立法、司法的界限。同时,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下级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案件实体及程序问题请示上级司法机而由上级司法机关予以答复的案件请示制度。而“案件请示制度并非今时所独有,其滥觞可以溯源至清末,是清末变法的附产品”[22]。确切地说,案件请示制度的源头是清末的问答式法律解释制度。问答式法律解释遵循“提问—解答”“请示—指示”的步骤进行,下级司法或行政机关在审理案件、执行法律的过程中,遇有不能自决之事件,便请示于上级机关予以指示。这种问答式解释往往成为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司法审判或行政执法的指挥和干涉。在清末司法人员素质不高、适用全新法律确有困难的情形下,案件请示制度尚有其必要性。但在根本上,案件请示制度是与司法独立原则相悖的,应正视其消极负面的影响及危害,予以彻底废弃。
结 语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与西方先进的现代法制及法学理论遭遇。在西方法制文明的强势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法制文明逐步退场,曾经辉煌的中华法系轰然崩塌。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及制度随着西方法制文明的洪流涌入中国。受西方法律解释理论和制度的导引,近代中国的法律解释制度开始萌芽。为筹备宪政,推行新法,以宪政编查馆为代表的中央机关以解答下级机关法律疑问的方式解释法律,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法律解释制度。近百年的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一整个的系统,尽管其中存在断裂,但新时期的法制仍能从旧制度那里寻找到最初的源头和影像。清末法律解释制度为此后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确立及发达做了准备,其独特的制度运行逻辑和特性影响了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样态及走向,同时,为我们理解、完善当下法律解释制度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本土样本,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当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来龙去脉,并启发我们探索解决问题的可能之道。
[1]梁治平.法律解释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宪政编查馆奏拟办事章程折[J].政治官报,1907,(1).
[4] 宪政编查馆通咨各省设谘议局筹办处文[J].政治官报,1908,(277).
[5] 宪政编查馆奏奏定章程应以官定解释为据片[J].政治官报,1909,(663).
[6] 闰二月十七日热河都统致民政部电[J].政治官报,1909,(523).
[7] 又奏司法行政分权遇有疑义咨询馆部核定办法片[J].政治官报,1911,(1256).
[8] 陈灨一.睇向斋秘录[M].近代稗海(第十三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9] 陆军部复江宁第九镇徐统制电[J].政治官报,1910,(1177).
[10]署鲁抚致资政院电[J].政治官报,1909,(750).
[11] 十月初二日又电[J].政治官报,1908,(373).
[12] 十月初五日宪政编查馆复云贵总督电[J].政治官报,1908,(373).
[13] 十二月十八日宪政编查馆发各省督抚电[J].政治官报,1909,(439).
[14] 川督致宪政编查馆、民政部电[J].政治官报,1909,(733).
[15] 法部收复川督电[J].政治官报,1911,(1303).
[16] 收川督电[J].政治官报,1911,(1308).
[17] 复川督电[J].政治官报,1911,(1308).
[18] 资政院接收各省来电·又收奉天谘议局电[J].政治官报,1910,(1136).
[19] 李启成.近代中国立宪的高潮与悲歌——《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导读[A].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辩论实录[M].上海:三联书店,2011.
[20] 孟森.新编法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1] 记载[J].东方杂志,1908,(12).
[22] 万毅.历史与现实交困中的案件请示制度[J].法学,2005,(2).
〔责任编辑:黎 玫〕
The Law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itial Modernization of Law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China
LI Xiang-sen
(School of Law,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211815, Jiangsu, China)
In the legal reform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the law interpret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initiall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explained law by way of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of law asked by the subordinate organs. The power of law interpretation was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used like the power of administrative, and had the function of legislation to adapt to the need of the legal reformation. Also,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with it, like the interpretation organs legislation by way of interpretation, commanding the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actions of the subordinate organs, and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interpretations. As the initial modernization of law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China, the law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Late Qing Dynasty was very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for it inherited the law interpretation tradition and prepar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the Republic China.
the law interpretation system; the Constitutional Compilation Bureau; question-answer interpretation type; the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law; case requesting system
李相森(1984— ),男,山东昌乐人,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近代法制史研究。
D903
A
1006-723X(2016)12-00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