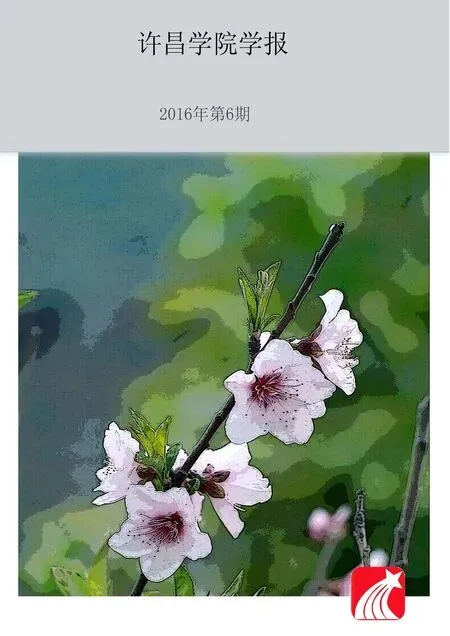元明时期《文选》的版刻与校勘
刘 锋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元明时期《文选》的版刻与校勘
刘 锋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元明时期影响最大的《文选》版本有茶陵本、张伯颜本和汲古阁本等,茶陵本出自宋建本,张伯颜本出自尤刻本,而汲古阁本来源较为复杂。这些版本在刊刻时都作了一些勘改,各具特色。由于明清以来流通的《文选》多来自这几种版本,故元明版本直接影响到清代学者对《文选》的校雠工作。
文选;校勘;元明
今知元代只有两种《文选》刊本,一为茶陵本,一为张伯颜本,两本皆出自宋刻本,又是明代大部分版本的祖本,故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明清《文选》的传承影响很大。明代中前期刻书尚严谨,此时的唐藩本、汪谅本、袁本、吴勉学本等较为精善,后期的汲古阁本亦较重要。由于宋版乃至元版《文选》在清代已为学者所希见,当时学者校雠《文选》多是据明版为底本,故明版《文选》的校雠版刻直接影响到清代学者的校雠实践。
一、茶陵本及其翻刻本
元大德(1297—1307)年间,茶陵陈仁子刻《增补六臣注文选》六十卷,世称茶陵本。记载陈仁子生平的资料不多,《四库全书》存目有陈仁子《牧莱脞语》,《提要》称仁子字同俌,号古迂,茶陵人,咸淳十年漕试第一,宋亡不仕*另明廖道南《楚纪》卷四三、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八引《茶陵州志》有简略记载,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一八记仁子祖父陈天福事,误将仁子之事迹属于其父,《天禄琳琅书目》卷十于《文选补遗》下引《万姓统谱》而沿其误。。据陈仁子文集《牧莱脞语》可以对其生平有所了解。卷七《牧莱少年稿自序》称作序时“年几二十四矣”,而此序作于宋德佑乙亥(1275年),则陈氏当生于1252年。据此则陈仁子大半生皆生活在元代,而前人多因其宋亡不仕而题其为宋人。傅增湘《牧莱脞语跋》曰:
按集中之文字多署纪元年号,于宋则有咸淳、德佑,于元则有至元、元贞、大德。其于至元辛卯诛桑哥也,则撰《诛大奸颂》;于至元庚寅诏免儒人差役也,则上《儒户免役颂》。是仁子入元代已三十余年矣,虽未入仕于朝,然已歌颂功德,不在遗逸之列,应改入元代。《提要》题作宋人,殆未及详考耶![1]774
故无论是据名分还是实际情况,陈仁子当题为元人为宜。文集卷一八又有《古迂翁传》一篇,可略见陈氏家世与志趣。其余还有不少文章亦可考其行迹交往。陈氏入元不仕,从事讲学,文集收有各书院、郡学讲义多篇。陈氏并营建东山书院,是元代著名书院之一。讲学著述外,陈氏并于书院刻印书籍,据历代书目记载其刻书有十余种*参刘志盛:《元代湖南的雕板刻书》,《图书馆》1987年第6期。。因其距宋不远,又刻印精善,故后世多误以陈氏刊本为宋刻本。
茶陵本《文选》书前有陈氏识语曰:“《文选》一编,皆纂辑秦汉魏晋文墨,中间去取,或不免涉诸君子议论,谨录卷首,因广其意。收拾遗漏者,亦起秦汉,迄昭明所选之时,得四十卷刊行,名曰《文选补遗》云。大德己亥冬茶陵古迂陈仁子书。”其后有“茶陵东山陈氏古迂书院刊行”木记。可知陈氏《文选》与《文选补遗》并刊于大德年间。
斯波六郎曾据明翻茶陵本考察,指出此本与《四部丛刊》所收宋建本《文选》行款全同,并具备《四部丛刊》本的特征,其李善注引文复出几同,故茶陵本似承《丛刊》本系统*参斯波六郎:《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见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14页。。后世目录著录茶陵本者不甚多,且诸家所记款式有所差异,主要有两种:其一为半叶十行,行大字十八,小字二十三,黑口;其一为半叶十行,行大字十八,小字则十八九,白口。故范志新推测茶陵本在元有两刻*关于茶陵本的版本以及诸家目录著录可参考斯波六郎《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论茶陵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今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其款式为第一种,但仅残存九卷。将此本与建本比对,行款全同,字体亦酷肖,且字句起讫亦同,当是初刻本,斯波六郎所据明翻本亦出自此本。而另一种款式者则恐非原本。总之,陈氏刻六臣本出自建本无疑,但与建本也有一些差异。斯波六郎据明翻茶陵本与《丛刊》本比对指出其差异多是此本校者以意改之,或删或脱误所致,其校改往往正确少而错误多,而《丛刊》本的一些讹误亦沿袭不改,甚至增加新的讹误。
茶陵本的校改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对其底本建本的注文多有删减,如斯波六郎所据例证:“《方言》曰”删去“曰”字,“某与某古字通”径删为“某与某通”,“《左氏传》然明曰”径删为“《左传》”。今就国图藏本比对,此类删减确实很多,如“《尚书》云”删去“云”字,“翰同善注”径删为“翰同”,还有一些句尾虚字如“也”字也被删去,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可知茶陵本此种校改是一通例,其删减似乎是为了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节省一点刻工,或是使注文更加清省。因其每页文字起讫仍袭建本,故删减处有空格,还算是留下了删减之迹。而后世一些六臣注《文选》版本多空格,大概即源出于此。
总之,就此本的校雠看,其基本依据建本,作了较多注文删省,纠正了一些建本的明显讹误,也沿袭并新增了一些讹误*可参斯波六郎所举例。又如卷三七孔文举《荐祢衡表》“平原祢衡”,“平”字误作“干”。,但大体上保存了建本的面貌,尚不失为较好的版本,对后世的六臣本影响很大。顾广圻、彭兆荪为胡克家校刊尤刻本,即以茶陵本为两部参校本之一*据范志新研究,其所据茶陵本当为明翻本。参《文选版本论稿》第71页。。彭兆荪《小谟觞馆文集》续集卷一《与刘芙初书》曰:“北宋单行善本未之获觏,吴门袁褧以家藏崇宁旧籍影写刊行,虽并五臣,要为近古。茶陵陈仁子亦当宋末,其所据依足资考镜。可证尤刻,惟此二书。馀如元张伯颜以后,递有摹雕,要皆宋本之重儓,遂初之别子也。”[2]
明代的多种六臣本皆出自茶陵本,除了明翻本外,尚有洪楩清平山堂本、潘惟时潘惟德本、吴勉学本、项笃寿万卷堂本、崔孔昕本、徐成位本等*对这些版本的研究可参考斯波六郎《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的相关论述。,这些版本大多自诩校勘精善,如洪楩本田汝成序曰:“钱唐洪君子美,得宋本而重锓之,校雠精致,逾于他刻。”此序被项氏万卷堂本移用,唯将上语改为“今观项氏所刻,校雠精致”云云,可见其语不实。又如徐成位本有识语曰:“郡斋旧有六臣《文选》刻,久而残失,山东崔大夫领郡,重为剞劂。但校雠者卤莽,中多舛讹,甚以俗字窜古文,观者病之。余暇日属二三文学详校,凡正一万五千余字,庶几复见古文之旧。”各本虽皆经校雠,但其质量反不及祖本。
二、张伯颜本及其翻刻本
稍后于茶陵本,元延祐(1314—1320)年间,池州路同知张伯颜刊李善注《文选》,世称张伯颜本。元郑元佑《侨吴集》卷一二有代伯颜子都中所作《平江路总管致仕张公圹志》一篇,记张氏生平较详,据《圹志》张氏至元二年(1336年)六十五岁,至元三年卒,则生卒为1272—1337年。张伯颜本前有余琏序一篇,据此序知大德间池州曾刻《文选》,但毁于火,后张伯颜于延祐七年任池州同知,再次主持刊刻。池州在萧梁时为昭明太子封邑,境内有不少关涉萧统的古迹,其中文选阁尤著。宋淳熙间尤袤曾在池州郡斋刻李善注本,是为著名的尤刻本,而张伯颜重刻,其事与尤袤颇为相似,其刻本亦出自尤刻本。
清人目录对张本及其翻刻本著录相当多,但详略不同,其中或不免疏舛,也不排除后人以明翻本充元本的可能,故关于张本系统仍有不少疑点*对张本及其明翻本较有研究的当推斯波六郎与范志新,但两家所述亦有所不同。。今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张伯颜本,仅存十一至六十卷*范志新谓此本是张氏原本,但国图著录称是重修本。。张本出自尤刻本,其行款及每页文字起讫全同,字体亦肖,基本保存尤刻本的原貌。大概张本即据尤刻本翻刻,虽然余琏序称“俾邑学吴梓校补遗谬”,但恐并未做多少校改,如《思玄赋》“幽兰之秋华兮”,李善注:“《楚辞》曰:结深兰之亭亭。”张本同尤刻本皆脱一“亭”字。“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后已”,张本同尤刻本皆误“要”为“恶”。“嘉群臣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李善注“善曰:《国语》曰:吴伐越,隳会稽,获骨节专车。吴子使来问之,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乃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张本同尤本误李注“群神”为“群臣”,《国语·鲁语下》即作“群神”。
张伯颜本在细微处也略有改动,如《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曰:“其橅刻此书,颇得宋椠模范,第书中只收李善一人之注,而又录吕延祚《进五臣注表》,未免自淆其例矣”[3]201。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一三《元张伯颜椠本文选跋》曰:“其行款起讫皆与尤延之本同,惟尤本《两都赋序》注‘亦皆依违尊者都举明廷以言之’,六臣本‘都’上有‘所’字、‘举’上有‘连’字,此本有此二字,与尤本不同,私意既刻成而挖改者,当是伯颜据六臣本所改,以掩其袭取尤本之迹耳。”[4]
总之,张伯颜本大体保存尤刻本原貌,一方面使宋本得到传承,一方面在宋本难得的情况下,大致可以代替宋本使用。故彭兆荪曰:“《文选》只要李善注,五臣竟不必看。鄱阳胡果泉漕督在苏藩任时,重刊淳熙本为第一,此我所手校,幸得顾君千里助我者。元张伯颜本次之。若无二书,则何校汲古阁本尚可。”[5]
与茶陵本相似,张本在明代翻刻甚多,明代的李善单注本大略皆出自此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明唐藩本、明晋藩本等*关于明代属张本系统的版本可参考斯波六郎与范志新的研究,二人所述稍有差别。。这些版本有的保持原貌,有的改易款式,阮元《揅经室三集》卷四《南宋淳熙贵池尤氏本〈文选〉序》曰:“元人张正卿翻刻是书,行款一切颇得其模范,第书中字句同异未能及此。若翻张本及晋府诸刻,改其行款,更同自郐矣。”[6]666
三、汲古阁本
明末,常熟汲古阁毛氏刊李善注《文选》,世称汲古阁本。此本在清中期胡刻本出现之前影响极大,前后翻刻凡十余家。盖清代学者尊李善贬五臣,当时流行李善单注本,又加汲古阁之盛名,故其刻本独盛行于世,学者囿于闻见,或目之为善本。但汲古阁本实非精良,其中讹脱甚众,清人因多研读之,故每有所论,如孙志祖《文选考异序》曰:“毛氏汲古阁所刻《文选》,世称善本,然李善与五臣所据本各不同。今注既载李善一家,而本文又间从五臣,未免踳驳,且字句讹误脱衍不可枚举。”[7]陈鳣《简庄文钞》卷三《元本李善注〈文选〉跋》曰:“余十二岁时诵《文选》,乃汲古阁所刊李善注本,在近时读本中为最善,犹恨其脱误良多,即何义门学士评校,尚有未尽,疑莫能明。”[8]朱锡庚《李善注文选诸家刊本源流考》曰:“今之所行,明毛晋汲古阁本,章句多脱落,注且不全。如枚乘《七发》遗‘太子有悦色也’、‘然而有起色矣’一节,司马长卿《上林赋》不标郭注,《宣德皇后令》失载任彦升,至一篇中脱遗数句,不可殚述。”[9]
汲古阁本虽不佳,但较之一般坊本为优,故余萧客《文选音义序》曰:“前辈何侍读义门先生当士大夫尚韩愈文章,不尚《文选》学,而独加赏好,博考众本,以汲古为善。晚年评定,多所折衷,士论服其该洽。”[10]故汲古阁本是当时学者校勘的主要《文选》版本,如何焯、陈景云、孙志祖、许巽行等校勘对象皆是此本,尤以何焯批校本最为盛行,学者移录传抄不绝,何氏批校于汲古阁本,抄录者亦多择汲古阁本为底本,故进一步加重其影响。《四库全书》所收李善注《文选》即汲古阁本,《提要》指出此本舛互甚多,但称唯是此本之外,更无别本,故仍而录之,亦可见当时汲古阁本之盛行。
汲古阁本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本子,此本来源不明,并无序跋有所交代,唯书中卷首多有“琴川毛凤苞氏审定宋本”篆印,其所谓宋本颇可疑。从其版式上亦看不出与之前版本的承袭痕迹,而其为李善单注本,扉页却题“梁昭明文选六臣全注”,不知何故,恐宋本无此体式*对此余萧客在《文选音义自叙》中推测说:“然汲古阁本独存善注,而总题‘六臣’,又误入向曰、铣曰注十数条。盖为考六臣、五臣之别,漫承旧刻伪杂,未必汲古主人有意欺世,乃以所刻数条五臣注为善也。”。汲古阁本有重刻本以及诸多翻刻本,清人往往泛称之为汲古阁本,但彼此差异也很多,各就所见而论,不免互相矛盾。如针对同一处脱误,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三曰:“抑有异者,近见坊刻《文选》,于此篇游猎一则,自‘客见太子有悦色也’至‘然而有喜色矣’,删去几二百字,其书袭毛氏汲古阁字样,然实于毛本大异。今乡塾盛行皆此本,误人甚矣,诬古人甚矣。”[11]而朱锡庚曰:“今之所行,明毛晋汲古阁本,章句多脱落,注且不全。如枚乘《七发》遗‘太子有悦色也’‘然而有起色矣’一节。”[9]又,汲古阁本混有少数五臣注,故《四库提要》谓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云《赠兄机》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赠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济曰”、“向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未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
斯波六郎复举多条混入的五臣注,但指出这些注文亦存于明翻张伯颜本中,故汲古阁本当出自明翻张本*参斯波六郎《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881页。。范志新也进一步论证汲古阁本出自明唐藩本*参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汲古阁毛本散论》。。实际上,清代一些学者已通过比对脱误与混淆,大致确定汲古阁本当属张伯颜本系统,如陈鳣《简庄文钞》卷三《元本李善注文选跋》曰:“惟司马长卿《封禅文》脱‘上帝垂恩,储祉将以庆成’二句,元刊已脱,又如《西都赋》注引‘三仓’之作‘王仓’,《闲居赋》注引‘韦孟诗’之作‘安革猛诗’,元刊亦然,汲古本盖仍其误,而义门亦未之校正也。”[8]曾钊《面城楼集钞》卷三《延祐本文选跋》曰:“《文选》李善注单行本宋有尤氏本,元有此本而已,国初毛氏本称从宋本校刊,而二十五卷陆士龙《答兄机》诗注有向曰、翰曰之文,与此本正同,殆即据此本耶?”[12]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二:“元时张伯颜刊善注,则更多增入五臣注本,明代弘治间唐藩刊本、嘉靖间汪谅刊本、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刊本,又皆以张本为原,而递多谬误,各本余皆有之。”[13]198
但傅刚则不同意汲古阁本出尤、张版本系统,认为汲古阁本是一个杂糅的版本*参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156页。。屈敬慈亦通过比对异文指出毛氏本所据底本确出宋刻,而且是早于尤本的宋刻。斯波氏以来的研究较清人的略论细密许多,但结论仍如此歧异,亦可见汲古阁本的复杂。诸家立说皆有理据,但或是限于版本闻见不足,或是仅抽样调查,结论都还不是十分确定,总体上仍以斯波六郎之说较为可信。
汲古阁本与尤、张系统版本的差异很可能是校改的结果,如屈敬慈指出:“毛氏本与尤刻本、胡刻本相歧异的文句,毛氏本十之八九同于天圣国子监本残卷及《六臣注》本的韩国奎章阁本、袁氏嘉趣堂本、明州本”[14]。这种情形恐怕并非如屈先生认为的,是汲古阁本所据乃早于尤刻本的宋本,而是汲古阁参考六臣本做了校改。又如李善注本及六臣注本皆无“移”、“难”两个类目,诗类下又没有“临终”这一次类目,而汲古阁本同五臣本皆存这三个类目,这大概是汲古阁本参据五臣本校改的痕迹。又如此本卷中的标目,不同于之前李善本与六臣本各卷标目,而是合两卷子目于奇数卷,偶数卷不标,故其子目似乎恢复了三十卷本的原貌,大概也是据五臣本而改,但亦保留有六十卷本的特征,如乐府类三十卷本在卷十四,只标“乐府”,六十卷本分置二七、二八两卷,故分标“乐府上”、“乐府下”,汲古阁本将二八卷子目合并在二七卷,但仍保留“乐府上”、“乐府下”,显然是杂糅了三十卷本和六十卷本。又五臣本卷目有“策秀才文”,李善本与六臣本皆误脱为“文”,汲古阁本亦同,则是未据五臣本改。
当然,若谓汲古阁本据其他版本做了校改,似乎也有点疑问,因为汲古阁本中脱误情况实在太多。阮元在《南宋淳熙贵池尤氏本文选序》中就有所质疑,有曰:“此册在明曾藏吴县王氏、长洲文氏、常熟毛氏。……独怪册中皆有汲古阁印,而毛板讹脱甚多,岂刊板后始获此本,未及校改耶?”[6]666实际上汲古阁不仅藏有尤刻本,又有赣州本、明州本、广都裴氏本、陈八郎本等,若据以参校,不当有很多讹误,如斯波六郎指出其较翻张本脱误更多。抑或是汲古阁本校雠过于粗疏,难以得知。
另外,汲古阁毛氏似曾修订重刻过《文选》,故汲古阁本《文选》当有初刻、修订之别。《读书敏求记》卷四“李善注《文选》六十卷”下,章钰引黄丕烈云:“此宋刻,毛氏曾以勘家刻本,秉笔者陆敕先也。”[15]431黄氏所称毛氏家刻本即汲古阁本,据黄氏所云则陆贻典据宋本校汲古阁本似是为毛氏刻书之用。许巽行《文选笔记》前《随录》曰:“乙酉官浙东,复得新刻汲古阁本,校阅再三。”[16]亦可为证。阮元《南宋淳熙贵池尤氏本文选序》指出汲古阁本脱文甚多,序中有注曰:“以上毛初刻本脱,后得宋本改。”*但如前所述,阮氏所云亦不见得十分可靠。若阮氏所云不误,则汲古阁确有《文选》修订本,而陆贻典所校盖为毛氏重刻之用*关于汲古阁本的重刊本可参考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第89-90页。。又汲古阁毛扆为陆贻典之婿,可作进一步证明。笔者所见汲古阁本扉页右上题“汲古阁新镌”,左下题“本衙藏板”,似即是修订本,而清代一些重刻本如怀德堂本、儒缨堂本、光霁堂本等,扉页右上皆题“汲古阁校订”字样,其所据底本或是汲古阁初刻本*阮元曾在一儒缨堂重刊汲古阁本上过录陆贻典、冯武、顾广圻的批校,阮氏在书前题曰:“今所用乃翻刻汲古阁初印本。”亦可为证。。又依汲古阁修订本为底本的钱士谧本,正题“汲古阁新镌”字样,则是初刻本题“汲古阁校订”,而修订本题“汲古阁新镌”。惜初刻本至今未见,是否属实仍需实物凭证。一般目录著录汲古阁本并未区别有初刻本、修订本,又因翻刻本甚多,清人泛论汲古阁本,实际上彼此有差异,故各家所述歧异颇多,莫衷一是。
除以上三种版本及其翻刻本外,元明时期比较重要的《文选》版本,尚有明嘉靖袁褧覆刊宋广都裴氏六家注《文选》,此本完善保存了宋本原貌,几乎未作改动,版本价值较高,在广都本罕见的情况下,大体可以此本替代。另外,明中后期还出现了很多《文选》的改编本,有的图清省删去注文成白文本,有的以己意删减原文,或变换次序,有的改窜原注而增入补注评点,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清代。改窜原书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与校雠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但一方面这些删节版本流行颇广,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删节者偶或也作了一定校勘,故在此亦略述之。较早对《文选》注释作删减的当属张凤翼《文选纂注》,《纂注》编纂之力多,发明较少,作一般的简明读本较为适宜,学术价值不高,且有不少舛误,故明时已有批评,但《纂注》出,几欲掩五臣而凌李善,可见其符合一般读书人之口味,故在刻书甚为发达的明代,翻刻、改编《纂注》者一时蜂起,然多为一般书商取利行径,校勘愈趋鲁莽,每况愈下矣。自《纂注》盛行,嗣后又有《文选章句》《文选尤》《文选瀹注》等改编本出现,其中陈与郊《文选章句》较有学术价值。陈与郊已注意到五臣、李善注的窜乱,并有意择取善本。同时陈氏又加以考韵、释名等,间附己说,又能参据前人,偶有考证。故《四库提要》谓较闵齐华、张凤翼诸本差为胜之。
[1]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 彭兆荪.小谟觞馆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嘉庆十一年刻二十二年增修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 陆心源.仪顾堂书跋[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 彭兆荪.忏摩录[M].《丛书集成续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6] 阮元.揅经室集[M].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7] 孙志祖.文选考异[M].《文选研究文献辑刊》影印清嘉庆间刻《读画斋丛书甲集》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8] 陈鳣.简庄文钞[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 朱锡庚.朱少河先生杂著[M].国图藏清抄本.
[10]余萧客.文选音义[M].清乾隆间静胜堂刻本.
[11] 黄承吉.梦陔堂文集[M].咸丰元年黄必庆汇印本.
[12] 曾钊.面城楼集钞[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二年刻《学海堂丛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4] 屈敬慈.校《文选李善注》应当重视汲古阁毛氏刻本[J].中华文化论坛,2000(4):120-122.
[15] 钱曾.读书敏求记校证[M].管庭芬,章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6] 许巽行.文选笔记[M].《丛书集成续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责任编辑:罗 操
Edition and Collation ofSelectedWorks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LIU 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 Law,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nxiang 453003, China)
The important editions ofSelectedWorksare Chaling, Zhang Boyan and Jiguge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edition of Chaling came from the Jianyang’s edi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while Zhang Boyan came from the edition of You Mao and Jiguge was of a complex origin. All these editions were collated when they were printed, so each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editions ofSelectedWorks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me from editions mentioned above, the editions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directly affected the collation work of the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SelectedWorks; collatio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2016-05-10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选》李善注校理”(14AZd07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文选》校雠史研究”(2016-GH-024)。
刘锋(1977—),男,河南南召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选学”与唐前文学和文献。
G256
A
1671-9824(2016)06-008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