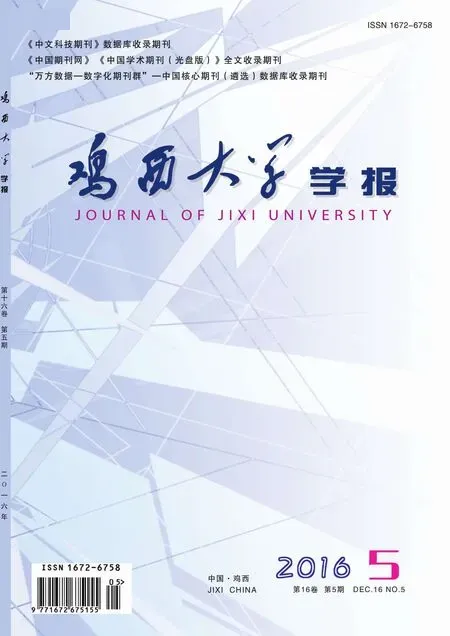追寻失落的家园
——《熊》与《红高粱家族》的比较研究
赵 鑫
(兰州文理学院 外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追寻失落的家园
——《熊》与《红高粱家族》的比较研究
赵鑫
(兰州文理学院 外语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摘要:福克纳的小说《熊》中的荒野与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高粱地都因为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感到迷惘和焦虑。在寻找失去的家园的同时,作家通过艺术与行动赋予荒野与高粱地新的意象。荒野是意志和力量的结合,是智慧与野蛮的统一。高粱地则构建起一个以生命意志和酒神精神所组成的生气勃勃的民间世界。
关键词:荒野;高粱地;家园;民间世界
福克纳和莫言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福克纳虚构了“约克纳帕塔法县”,构建了一个美国南方神话,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书写了中国百年变迁的历史沧桑。在这个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艺术王国中,杰弗逊镇就是福克纳的家乡奥克斯富,而奥克斯富所属的拉法叶特县就是约克纳帕塔法县。由此,家乡的小镇就融入了小说构建的艺术世界中。在《熊》的故事中,福克纳描述了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艾萨克·麦卡斯琳的诞生,在荒野中成长追猎一头大熊的故事。很多欧洲评论家认为“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自1940年的《村子》以来就有一种同《旧约全书》所描写的最悲惨最令人沮丧的时刻颇为类似的气氛。果真如此,我们也许可以把《熊》看成是福克纳进入光明世界的第一次尝试。”①虽然作者不遗余力地批判美国南方腐朽的守旧势力,但同时也在探索转型时期美国南方的构建。《熊》是一个转折,也是一种尝试。
在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一个红高粱的世界。《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家族小说,记叙了集土匪与英雄于一身的余占鳌司令在高密东北乡抗击日军的故事。作品热情地歌颂了红高粱以及余占鳌与戴凤莲无视世俗,纵享生命的爱情,张扬生命活力与精神状态,同时反映作家对现实的反叛欲望。对于《红高粱家族》,他说,“这是我的想象,我的家乡有红高粱但却没有血一般的浸染。但我要她有血一般的浸染,要她淹没在血一般茫茫的大水中。”②红高粱的世界是作者心灵中的幻想世界,它神奇与激越,令人向往。
在艺术想象世界中,《熊》中的荒野与《红高粱家族》中的红高粱地都是作者魂牵梦绕,渴望回归的伊甸园。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一切又是作家真实感受的人生,沉重与凄凉。
一失落的家园
1. 环境与时代的变迁。
莫言曾说:“小说就是带着淡淡的忧愁寻找自己失落的家园。”③寻找缘于失落,莫言失落了什么?他寻找的家园又是什么?《红高粱家族》里爷爷奶奶那一代敢爱敢恨,能生能死,杀人放火,扯旗造反,男的彪悍女的风流,到了“我”这一代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悲。奶奶可以大声地呼喊她高粱般充实的生活,而“我”在现实生活中,“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④不但人在退化,连自然界也在蜕变和萎缩。河枯了,狗老了,血海般的高粱地被丑陋的杂种高粱(杂交高粱)替代了。“杂种高粱好像永远不会成熟,它永远半闭着那些灰绿色的眼睛。我站在二奶奶的坟墓前,看着这些丑陋的杂种,七长八短地占据了红高粱的地盘。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辉煌的颜色。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它们用它们灰暗不清、模棱两可的狭长脸庞污染着高密东北乡纯净的空气。”同样的变化,同样的失落在《熊》中也是一样,艾萨克·麦卡斯琳在内战之后的年代里长大,成长于密西西比州。十岁起,他随表兄年年到镇北未开发的荒野去猎熊。艾萨克在狩猎中学会了打猎的本领,并且锻炼出“勇敢、荣誉、骄傲、怜悯、爱正义、爱自由”这些福克纳所崇尚的英雄品质。在狩猎中,他们的对手是一头巨大而年老的熊,名叫老班,它的身上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英雄品质,由此为人们崇拜和敬仰。艾萨克十六岁那一年,老班终于被布恩·霍根贝克和一条名叫狮子的杂种狗杀死了。两年后,当他十八岁回到荒野,发现这里已不再是一片荒芜。以前打猎时居住的小屋已经夷为平地,打猎的人销声匿迹。伐木公司开始入侵树林,改变树林的面貌。在新的文明的时代里,他感到茫然困惑,无所适从,甚至有些神经错乱。《熊》所体现的是时代的变化,是美国南方进行经济与社会历史变革的时期,是新旧时期交替中所带来的矛盾。南北战争前,南方大部分地区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密西西比州,大量种植棉花,雇佣黑奴劳作,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力的大庄园农业体系。南北战争之后,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方成为美国最穷的地方,而密西西比州又是南方最穷的州。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形势大好,北方商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经济模式正一步一步摧毁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在新旧制度的碰撞下,尽管作者理智上认同旧制度的腐朽及旧社会注定灭亡的命运,但是在情感上同旧的传统,旧的社会秩序存在着感情依恋。尽管后代们很努力地想要适应新的时代,但挽救不了传统南方社会衰亡的历史命运。《红高粱家族》里,对于莫言和他们的乡亲们来说,余占鳌和戴凤莲那样亦民亦匪的生活,占山为王,行为放纵是他们世代已经熟悉的生活方式,还有不管时事变化,安稳地做顺民,种田纳粮,苦熬苦忍,也是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但是到了父辈和我这一辈,新中国建立后的农村的变化是空前,不论是当年的“穷过渡”,还是“一大二公”的商品经济,开放搞活,对于人们都是陌生的,在陌生的环境中,人不能不感到慌乱,感到手足无措。生活变了,但人的情感却难以认同。然后就怀旧,怀恋人类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对往事的迷恋导致对新事物的排斥。
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交错中,在社会转型阶段的人们普遍感到迷惘和焦虑。人们企图在过去和现在的感觉交错中寻觅一份心理的稳妥和栖居。
2. 没落的文化。
福克纳和莫言都是在较稳定的乡土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但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并没有促使他们写出田园牧歌式的作品,相反,他们热衷于书写巨变时期下的乡土社会和生活。福克纳最为反感的就是蓄奴制和种族歧视,他不能忍受与自由、平等观念相冲突的蓄奴制和种族主义。他的作品无情地批判蓄奴制,谴责加尔文主义对人性的摧残,撕开了那层温文尔雅的面具,让南方的罪恶原形毕露。在《熊》中,艾萨克二十一岁时,他继承父亲的土地与金钱,而他父亲又是从祖父,卡罗瑟斯·麦卡斯琳处继承得来的。他祖父曾经诱奸一个名叫托马西那的黑女奴,并且同她生了一个孩子,而托马西那很可能就是他祖父的亲生女儿。艾萨克认为乱伦以及人种血缘混杂的结合反映了南方的罪恶现实。这种罪恶发源于奴隶制度对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的腐蚀影响。当艾萨克发现这是他祖父的不义之财,拒绝接受这笔遗产,继续在树林里或树林附近过着简朴的猎人生活。
《红高粱家族》中,戴凤莲在出嫁的路上,还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假如她真的遇上一位如意郎君,她大约终身是一位贤惠的农妇罢了。但是,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风病人。现实粉粹了她的梦幻,把她置于丑陋污秽中。一个陷入绝境而又不甘心毁灭的力量促使她觉醒,反抗非人的境遇,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经历了生与死,爱与恨的狂澜洗礼后,经过单家父子被杀后短暂的迷茫和恐惧,她变得泼辣强悍,思想前卫,情感放纵,“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莫言说:“山东是孔孟故乡,是封建思想深厚博大源远流长的地方;尤其是在爷爷奶奶的年代,封建礼教是所有下层人,尤其是下层妇女的铁的囚笼。小说中奶奶和爷爷的‘野合’在当时是弥天的罪孽,我之所以用不无赞美的笔调渲染了这次‘野合’,并不是我在鼓吹这种方式,而是基于我对封建主义的痛恨。我觉得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的‘白昼宣淫’是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和报复。极度的禁欲往往导致极度的纵欲,这也是辩证法吧!”⑤莫言痛恨封建礼教,高粱地里的爱情彰显了原始的生命力,是对奔放的生命力的希望与呼唤。
不论是蓄奴制,种族歧视对人性的压抑,还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伦理道德对妇女灵魂的扭曲,在压迫中,终有一种力量不畏困难努力冲破一切束缚。
二追寻与求索
“寻根溯源也许是人类最重要而最不受到重视的需要。”⑥圣经故事中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就是人类丧失精神故园的表述,并诱惑着人民去寻找失落的家园。寻找失去的家园,寻找遭受惩罚的原因同时也寻找超越 。
《熊》,艾萨克十六岁,老班死了,山姆·法泽斯(艾萨克的养父及导师)死了,杂种狗狮子死了,友情的死亡是整个世界的死亡。而艾萨克是那些死去灵魂的孤独的化身,是那个世界及其真理的孤单的见证人。十六岁是他进入成人的标志。在这一年,最后一次猎熊后的一个十二月的晚上,他解开了家族之谜,使他下定决心坚决拒绝继承他父亲的遗产。老班之死,对麦卡斯琳家族混血与乱伦的发现,似乎是同时发生的。这里隐含着人生的开始的力量使得获得再生的个人有能力抵制他遇到的罪恶。他的放弃继承权是由这些经历促成的。艾萨克成年后决定回到以前的生活,回到打猎世界的气氛和节奏中。这里又隐喻着作者希望回到故事中所描写的国家和地方传统。“如果说《熊》是一篇描写死亡的作品,那么它是描写边疆世界及其可能性的死亡;它还描写了新的尚未受到破坏的地区的死亡,在那里一种真正的和根本的道德自由—— 一种原始的纯真——又可能得以实现。”⑦
文明与荒野是对立的,在社会的文明进程中,人性却出现了背离初衷的严重异化,福克纳深刻地反醒种族歧视给人类带来的悲痛。在荒野中,一切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都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荒野之中,生存法则是意志和力量的结合,是智慧与野蛮的统一。福克纳的荒野的意象与莫言的高粱地的意象异曲同工。高粱地也在荒郊野外,“我”爷爷既不道德也不光彩的抢掠方式得到了“我”奶奶,也播种了“我”爸爸这个野种,这里成为“我”祖先的诞生之地,红高粱变成了“我”祖先的生命食粮。他们徜徉在高粱地,吃着红高粱,喝着高粱酒,脱离社会融入自然,获得一种自由。作者借助高粱地这一荒原形象寻找灵魂家园。高粱地脱离社会制约,所以“我”爷爷奶奶精神自由,行为放纵。在这个边缘状态中,没有法律,没有道德,没有党派,没有权力意志。莫言以民间文化为中心,构建起一个以生命意志和酒神精神所组成的生气勃勃的民间世界。
寻找精神家园也不仅指摆脱人性的压抑和生命的痛苦的意思。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表现为民族的觉醒,以及民族文化的重构。
艾萨克又回到了荒野,试图发现“我们来自何处,又在何处走上歧途”。 他想要追根溯源了解到他们的时代令人迷惑的灾祸。他的结论是:新世界从建立之时从未短缺过罪恶。奴隶制的罪恶扎根于精神上的骄傲和占有欲的罪恶之中。因而,《熊》创造了纯真和道德自由的更为持久的形象。 “有两头野兽,连大熊老班在内,还有两个人,包括布恩·霍根贝克。他的体内流的血液同山姆·法泽斯的完全一样,尽管布恩属于卑贱平民的血统。只有山姆,老班和杂种狗狮子是纯洁的,不可败坏的。”⑧山姆,他也是一个混血儿,是黑奴同契卡索族印地安人混血的后代,杂种狗具有 “纯洁的,不可败坏”的品质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说明作者通过艺术和行动赋予了新的纯洁,用纯真与道德的自由取代了血缘问题和形体纯洁。
在《红高粱家族》中,纯种的好汉比如“任副官八成是共产党,除了共产党,很难找到这样的纯种好汉”, “只可惜任副官英雄短命,他在昂首阔步,走出了英雄八面威风之后的三个月,竟在擦洗那支勃朗宁手枪时,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了。”这样的纯种好汉很难同高粱地的土匪共生共存。在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上,他们不是真正的主角,更不是理想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是代表民间人物,民间精神的“爷爷”“奶奶”“罗汉爷”等人物。土匪泛指缺少规范的行为方式,英雄泛指超凡脱俗的内在气质,“我”爷爷虽然是个土匪,但他更是个英雄,两者合二为一的完美结合,表达了作者对于重建完美人格的丰富联想。高粱地的命运主宰就是那些大小土匪,他们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精神自由,行为放纵。无论历史的恩怨纠结怎样的沧桑反复,最终都汇聚并消逝于民间。在一场风雨中雷电劈开了千人坟墓,坟里的那些骨架骷髅重见天日,不论他们是谁,共产党、国民党、伪军只怕都辨不清了,一切的历史与民间都被消解了。荒野更似真实地存在,不论是“纯种狗”还是“杂种狗”,“纯种高粱”还是“杂种高粱”,不论是进化还是退化,都是作者对当代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看似异端与另类,却焕发着破坏与创造力,如同西风摧毁一切,却又是一切生命原初的活力的爆发。
灵魂家园赋予作品以崇高的人文精神,叔本华曾呼吁道:“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改变环境吧!”⑨不论是《熊》中的荒野,还是高粱地世界,都是作者以自己的意志去改变人类生存环境的一种大胆尝试。历史的演化中,环境改变了,家族溃败与离散,但是作者并不是书写生命的毁灭,而是书写生命的生长。历史的终结,英雄的没落,不论是荒野还是红高粱地,自然生命力的蓬勃张扬是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灵魂。由此,失去家园的种种创伤和悲痛升华为关爱,敬畏和自由。
注释
①R·W·B· 路易斯:《<熊>:超越美国》, (陶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②赵玫:《淹没在水中的红高粱——莫言印象》,载《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第53页。
③张志忠:《莫言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④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⑤莫言:《<奇死>之后的信笔涂鸦》,载《昆仑》1986年第6期。
⑥法国作家兼哲学家西摩尼·威尔转引自《福克纳中短篇小说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⑦李文俊:《福克纳神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⑧威廉·福克纳:《熊》,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
⑨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2页。
参考文献
[1]R·W·B· 路易斯.《熊》:超越美国[M]. 陶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李文俊.福克纳神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4]叔本华. 叔本华论说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威廉·福克纳.熊[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
[6]张志忠.莫言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Class No.:I0-03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郑英玲)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ear and Red Sorghum Clan
Zhao 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Lanzhou, Gansu 730000,China)
Abstract:The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novels The Bear written by William Faulkner and Red Sorghum Clan by MoYan. Because of the changing time and environment, the wildness in The Bear and the sorghum land in Red Sorghum Clan has changed as well. People feel perplexed and worried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In pursuit of the lost homeland, the writers endow the wildness and sorghum land with the new image by means of art activities. The wildness is united with the will and power, wisdom and barbarism. The sorghum land establishes vital folk society united with willpower and dionysian spirit.
Key words:wildness; sorghum land; homeland; folk society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758(2016)05-0128-4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厅课题“福克纳与莫言家族叙事艺术比较研究”(编号2013B-105)。
作者简介:赵鑫,硕士,副教授,兰州文理学院。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