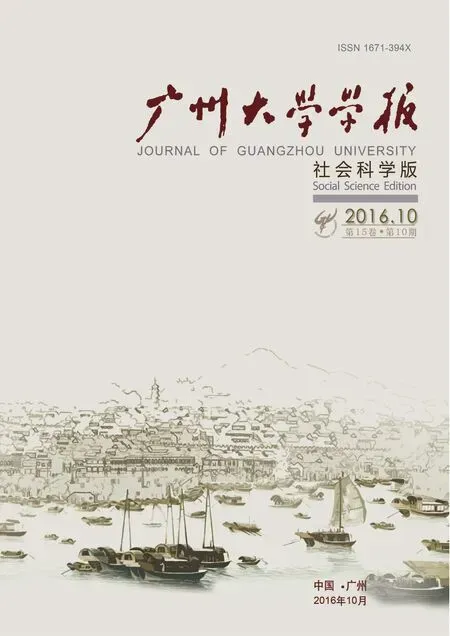与大同思想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
高 尚 , 董四代
(1.华侨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2.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公共基础部,福建 泉州 362000)
与大同思想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
高 尚1, 董四代2
(1.华侨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2.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公共基础部,福建 泉州 362000)
大同思想是中囯文化原创期的社会理想,其批判性和超越性使之形成了历史的生命力,因而它与乌托邦有异曲同工之处,并成为中国人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撞击中,大同思想终于演变为康有为的世界大同理想,并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
大同; “轴心期”; 乌托邦; 社会主义
出自《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它是如何被历史赋予生命力的,怎样认识它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这是一个关涉着理想主义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命题。只有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并从中西理想主义的比较中,才能对大同思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进而阐释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意义。
一、 大同思想溯源
理想主义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大同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主义最早出现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因此人们认为它是儒家对理想主义的表达。但是近代以来又有人对此表示疑问,吴虞是五四时期批判传统思想的领军式人物。他认为:“《礼运》‘大同’之说,乃窃道家之绪余,不足翘以有异。”[1]39也就是说,大同思想并非儒家理想主义,而是体现着道家以大道之行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因此它“讥‘小康’之世”“孔子盖闻老聃‘大同’‘小康’之绪论,故虽揭‘大同’之旨,而仍注重于‘小康’。《礼运》所举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皆家天下之君臣;其所标举为仁义礼乐,而谓礼为君之大柄。盖孔门虽慕古之志切,终不敌其用世之情深,故略举‘大同’而详述‘小康’,以迎合时君,期于得位乘时”[1]41他认为大同之论虽出自儒家经典,但它却是道家的思想,孔子关注的是小康,他对大同只是在论述小康时有简要的涉及,因而不能认为大同是儒家的理想主义。
蔡尚思认为,大同思想既不是出自儒家也并非出于道家,而是出于墨家。他说:“认《礼运》里的‘大同说’是出于道家,故极不合”,“直认大同说是儒家孔子之言,亦属非是”,“其最和大同说相合者莫如墨家”[2]83他不仅认同俞樾所言:“《礼运》曰:‘大道之行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此非圣人之言也。”而且引证王祖畬的《读礼运篇》中所说的,“大同说‘即墨子兼爱之说’,盖‘由汉儒穿凿附会而托于圣人之言者’”[2]84-85作为论据。他还特别指出:“先秦诸子最反对大同说者,莫如提倡无知识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家。”[2]83
认定大同思想出于儒家,并且以儒家正统论述大同思想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以正本清源的方式,一方面认为自东汉以来被统治者奉为治国之经的古文经学并非孔子学说之真传;另一方面又以恢复先秦儒学真面目为手段阐发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并对大同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大同是孔子依托“三代”而提出的社会理想。他在《礼运注》中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其志焉。’”“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常在太平世,必进化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3]139并且认为大同思想是“孔子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3]236后来,他又以《礼运》为宗,结合现代文明发展写了气势恢宏的《大同书》。梁启超则是在肯定康有为的这些思想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了康有为的这一思想,他说:“先生(康有为)乃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孔子之真义。”[4]747
其实,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大同思想,它既包含了道家追寻人间大道的精神、墨家的民众关怀,也有儒家的仁爱思想,是集先秦各家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为一体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理想。虽然在以后的历史变迁中,各家都根据新的社会条件对它加以阐释和发挥,但它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目标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图景;以对现实的批判超越精神点燃了中国理想主义之灯,为黑暗中行进的人们确立了前进的目标;以鲜明的民生关怀表达了对剥削制度的不满和抗议,从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认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
二、 大同思想的历史生命力
有人认为大同思想是建立在自然经济之上的、代表小生产者摆脱现实剥削和压迫的理想主义。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如果从历史发展及大同思想的生命力来分析,就会看到正是由于它的批判超越性、“大道之行”的求索精神和“天下为公”的境界追求,使之形成了持久的生命力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体现出了越来越丰富的内容。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500年是人类的轴心时期。在这个时期,一些文明古国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命题。他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5]8-9他还认为,在这个时代,人感觉到了世界的完整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感觉到了世界的可怕和自己的渺小,在面临深渊时寻求解放,为自己提出最高目标,寻求一种澄明的超越。他还认为在轴心时代,人形成了自我意识的“精神化”,诞生了“真正的人”,这就开始了“真正的历史”[6]194。这种人并不是当时特定的人,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有了对现实的批判和理想追求的人,真正的历史也是人在追求自身解放中所书写的历史。
《礼记·礼运》中关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描述,是中华文化原创期的“轴心期”命题。这种大同是与“天下为私”的小康社会相对照而提出,小康社会虽然是秩序化了的现实,大同则是对小康的超越中提出的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这是一种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精神化”了的人,面对现实困境对实现彻底解放的追求。
德国学者伽达默尔认为在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发展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实证主义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他说:“如果我们是以对规律性不断深化的认识为标准去衡量精神科学,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把握精神科学的本质。社会—历史的世界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7]12-13他主张在历史研究中采取一种阐释学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历代对有关人类彻底自由和普遍幸福命题的阐释揭示其中的真理和规律,即“只有在对传承物的‘无休止的’探索中,在对愈来愈新的原始资料的开启中,以及在对这些原始资料所做的愈来愈新的解释中,历史研究才不断向‘理念’迈进。”[7]297。
伽达默尔认为,传统中的某些经典命题往往构成人们解释的对象。但是,每个时代的人们又是根据各自时代的特点和以前人们的“前解释”,去发挥这些传统经典的。这就构成了一种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带着自己所处的时代的问题去解释历史传承下来的文本,因为这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个时代则是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当初,这些文本的作者“并不需要知道他所写的东西的真实意义,因而解释者常常能够而且必须比作者理解的更多些。……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7]403这就是说,各个时代对传统命题的解释都不是回复它的本来面目,而是在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中,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对它的再创造,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使之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并在对它的丰富和发展中保持了传统命题的生命力。因此,传统就是在这种不断解释中保存和发展起来的。对这种传统文本一代又一代的解释,使之体现出了自身的真理性,并构筑起了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家园。
大同思想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使之不能与传统社会的秩序相融,因此也就必然地被边缘化了。但在明末清初出现的早期启蒙中,人们又以歌颂古代的方式批判和反对现实,大同思想及其包含的“天下为公”、民生诉求和社会理想又一次燃起了人们心中的火焰,并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对它进行阐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对中国强烈冲击的背景下,康有为根据历史进化论,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并在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中重新阐释大同思想,提出了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使之成为影响几代中国人的鸿篇巨著。
三、 大同思想与乌托邦
“乌托邦”是由莫尔的同名小说演化而来的一个术语。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岛屿上的没有囯家、没有剥削、自由幸福、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景象。由于它是以对话的方式,在对资本早期积累的批判中展开故事叙述的,也就在一种浪漫的描述中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后来,乌托邦又转化为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形成的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这个术语是首先由严复介绍到中国的,他在《天演论》中说:“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设想所存而已。然使后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非将由任天之自然,而由尽力于人治,则断然可识也。”[8]36
现在,乌托邦已经超出了它的原意,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它作为远景,表达着一种与现实不同的美好的未来社会图景;二是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体现为人们在对现实的超越性批判中形成的追求精神。从笫一种含义讲,这种未来的图景如同黑夜中的北斗星,为人们指示方向;从第二种含义上讲,它可以使人们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弊端、丑恶和黑暗,进而寻找从现实走向理想的道路。
自从人们把乌托邦与空想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以后,往往强调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一方面在突出革命、专政和讲求实际的过程中,淡化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又把合作、改良、人道主义统统归于乌托邦的名下,强调它的作用与历史发展成反比。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评价乌托邦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因为大同思想与乌托邦有很多相似性,所以也就不能充分揭示大同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理论取向。
大同是中国思想史上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它与乌托邦还是有一些差别的:首先,产生的时代不同,大同思想产生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期”,这时人类开始觉醒,即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企图超越现实,寻求彻底解放的时期,因此它对理想的论述就显得宏大且朦胧;《乌托邦》产生于16世纪初期,这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它在对乌托邦新岛的理想社会描述中,以对照的方式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次,大同思想在中囯长期的传统社会里被边缘化了,在明朝末年出现的变革思潮中才又一次被人们提起,它在一种理想主义中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并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撞击中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乌托邦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它作为一种理想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社会思潮的变化而不断变换着形式,与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到现在仍然体现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再次,大同思想虽然与自强不息、民生关怀、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社会远景,在文字表达上也高度凝炼;乌托邦则蕴含着一种比较强烈的批判精神,并有一种开启人们想像力的浪漫主义特色,因而可以从哲学、文学、艺术等多种视角上对它进行阐释,也就比大同思想形成了更大的影响力。
尽管二者有一些不同,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大同思想也可以视为中国的乌托邦。美国学者赫茨勒说:“指南星并不因永远不能达到而失去其指南的作用。理想是目标,也是向导。”[9]因此,现实和理想虽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知道,除非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树立在它的面前,现实是不会有长足进步的。在谈到乌托邦理想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时,另一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10]也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 “如果摈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10]2如果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讲,大同思想就是中国的乌托邦。它既表达着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大同理想主义并没有隨着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失去自己的意义,它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又使中囯人民在对现实的批判中不断寻求通向理想的实践道路。
四、 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
如果把社会主义视为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理想,那么《乌托邦》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山之作。大同思想是什么时候与资本主义际遇,它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没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前提呢?这是大同思想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在很长时间里,我国理论界是以教条主义的方式认识社会主义问题的。人们往往根据前苏联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进行抽象,再据此对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主义进行定性分析。这样,就不能对五四以前的理想主义进行正确评价,甚至认为此前中国不存在社会主义思想。或者是把中国近代以来的理想主义纳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进行分析。
西方学者还从大同思想出发认识“社会主义何以在中国会这么成功”,因此,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对于东方说来,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么‘外来’。”[11]193也就是说,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就要从大同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嬗变中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
源远流长的大同思想是中国理想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面临着危机,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又为追求光明的中国人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在这种背景下,康有为反思传统、判断现实、追求未来,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剥削制度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大同思想,写出了《大同书》。书中描绘了一幅超越于资本主义的,建立在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上,消灭了私有制和国家的,人人自由幸福的世界大同美好蓝图。在大同社会里,劳动“不过等于逸士之灌花,英雄之种菜,隐者之渔钓,豪杰之弋猎而己”[12]294,人们成为“极乐天中之仙人”。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构想已经突破了传统大同思想,使之体现出了新的时代气息:它把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从歌颂过去转向了追求未来;它把批判的对象,从中国的传统专制社会转向了资本主义;把美好社会的基础,从封闭的自然经济转向了开放的现代物质文明;它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开始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考虑自己国家的前途问题。虽然康有为没有把这种理想定义为社会主义,但正如恩格斯在评价席勒的小说《阴谋与爱情》时说的:“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了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3]231-232
最先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是梁启超,他说: “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4]750梁启超不仅沿着康有为的思路从中国传统中寻求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而且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论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李大钊、吴玉章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从大同思想出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的。如果把大同视为一种理想,它是中国人接受和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精神,它又是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探寻从现在走向未来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是从现实走向理想的过程,因而在实践中也必须坚持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维度。在这个充满荆棘和岐路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有面对现实的态度,更需要有一种理想主义精神。
[1] 吴虞文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8.
[2] 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附补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 康有为.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梁启超选集[M].北京:中囯文联出版社,2006.
[5] 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 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哲学与信仰:雅斯贝尔斯哲学研究[M].鲁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8] 刘梦溪.严复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9] 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M].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0]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1]约恩·吕森.思考乌托邦[M].张文涛,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12]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肖 湘]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Idea of Datong
GAO Shang1, DONG Sidai2
(1.School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HuaqiaoUniversity,Quanzhou,Fujian362021,China; 2.QuanzhouInformationEngineeringCollege,Quanzhou,Fujian362000,China)
The Datong thought was a social ideal in the original period of the Chinese culture,that its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made it the vitality of history. Therefore, it coincided with Utopia, and became the na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ccepted the socialism. In the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modern times, the thought of Datong evolved into the ideal of Kang Youwei’s world harmony, and became the ideological premise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ccepted Marxism.
Datong; “axial period”; Utopia; socialism
2016- 05- 0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XKS010)
高尚,华侨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董四代,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研究。
B22;D616
A
1671-394X(2016)10- 0034-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