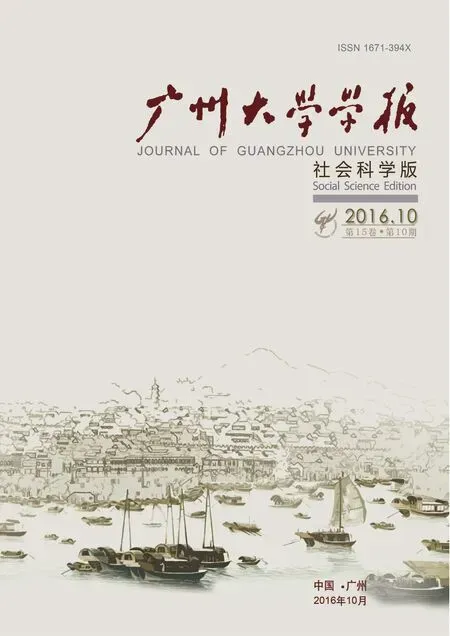“梁氏宪草”对西方宪法理论的引进与改造
王 军
(广州市监察局 第二监察室, 广东 广州 510046)
“梁氏宪草”对西方宪法理论的引进与改造
王 军
(广州市监察局 第二监察室, 广东 广州 510046)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不仅应当是审慎制定的良善之法,更不可朝令夕改。1913年,梁启超以《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作为进步党参与立宪的政治主张。缘何梁氏在宪法草案中放弃君主立宪制而采纳民主共和制,由对美国联邦制之偏好转向了单一制国家结构,不采用责任内阁制而提倡总统制?这当中体现了立宪中各派政治角力相互妥协、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过程。也启发了当今开展法治建设不可仅移植国外法律,吸收国外法治思想,更为必要的是须建立起超越政治与党派权力的宪法权威,实现对宪法理念的本土化改造。
宪法草案; 权力制衡理论; 梁启超
一、时代背景
“梁氏宪草”是梁启超于1913年以中华民国进步党名义拟定的宪法草案,旨在提出梁启超及其进步党对当时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政治主张,体现国家权力制衡的思想。研究这份宪法草案,需要熟悉当时立宪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一)梁启超立宪救国的思想
在1898年以君主立宪制为主要内容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作为改良派代表的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他仍然坚定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民主共和成为社会现实,梁启超随之放弃君主立宪制,主张民主共和制。1912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15年后,回到中国,随之加入共和党,合并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成立进步党。进步党作为中间势力跻身中华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梁启超希望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将其所考察的国外立宪成果以及自己的宪政主张形成宪法草案,并希望付诸实施。
(二)民初宪政具体制度的争议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应当如何实施宪政,各政治党派均提出自身的主张。但是在关键的政权组织形式方面,主要存在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的争论。总统制主要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派,仍然保守中国三千年的封建思想,企图总统一权独大,限制议会的弹劾权和不信任票投票权,这也为袁世凯后来的独裁统治埋下伏笔。责任内阁制的主张以革命党人即后期的国民党人为代表。因为当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希望借助袁世凯这个政治强人稳定政局,故主张建立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人员担任国务员,并对议会负责,建立虚位的总统。但是政治本身需要妥协,没有绝对的赢和绝对的输,这时候就迫切需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进行宪政方案的调和。梁启超的宪政草案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三)民初宪政的法律文化基础
中国具有三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和闭关锁国的历史,中国人对宪法、宪政知之甚少,已经习惯于中央集权和独裁专制的统治模式,导致中国清朝末年在欧美舰船利炮之前,极为孱弱。中国迫切需要通过欧美宪法学说的传播,立宪思想的争论,唤起国人对宪政这个事物的关注和拥护。在介绍西方宪法制度及学说方面,梁启超的《各国宪法异同论》《论立法权》《宪法之三大精神》《法理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系统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宪政学说。这一切都为梁启超宪法草案的出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舆论基础和法律文化基础。
二、宪法观念的“引”与“立”
(一)从无到有的“一纸宪法”
梁氏首倡“立宪”可追溯到他在1898年末逃亡日本之后,在所撰写的长文《戊戌政变记》中,建议借鉴日本的维新变法,并制定宪法。而后在《立宪法议》一文,梁启超系统阐明宪法的概念、涵义、价值和意义,并第一次提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由此,中国立宪的思潮开始兴起。
梁启超引入立宪政体的概念,也被称为“有限权之政体”,用以与专制政体比较。“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故各国宪法,皆首言君主通知之大权及皇位继袭之典例,明君之权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职分,明官之权限也;次言议会职分及人民自由也”。[1]
此后,梁氏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各国宪法异同论》和《立宪法议》等大量法学文章。在梁启超所有的法学著说中,尤以宪法学著述为甚。在民国初期,梁启超提出“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发表宪法论著,大力推行立宪,并于1913年代表进步党草拟宪法草案,投身于组建政党传播立宪理念的政治活动中。
(二)权力危机中的宪法存续问题
梁启超一直认为,国家政局要走上正确的道路,必须首先颁布宪法。在辛亥革命当时,革命党人是创造民国的主要力量,军阀官僚附和共和,立宪党人积极鼓动赞助,构成中华民国速成的主要动力。中华民国成立后,政治势力主要体现为此三大派。在中国帝制废除的时代,政治势力的发展和巩固,不仅需要党派权柄在握,也需要以宪法对权力的正统性进行确认。
然而梁启超想凭借他一己之力在民国初年推行国民制宪,尚难以实现。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三千年时势的大变——不仅是统治者权力的更迭,更是宪法权威的新塑。革命后的中国本也可以参考美国式的以制宪为中心的共和之路,遗憾的是各派政治势力定国安邦并不以立宪为路径,而是开展了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相互争夺。无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议,其本质都是围绕国家权力进行的争斗。
在尚未立宪之前,袁世凯要求国会两党先选举总统,立宪党人竟然舍弃临时约法精神,为将袁世凯推上总统宝座,提前通过总统选举法,议会民主制苦心建立起来的法治基础损失殆尽。进步党人唯恐国家会被革命后高涨的民主浪潮和地方自治弄得四分五裂,竟也妥协认为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只有袁世凯。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将最紧要的宪法的至高性地位置于次位。以为巩固了权力,天下便可稳定,却以牺牲宪法权威用以缓解权力危机。
即使在袁世凯倒台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都未能把心思放在重塑法统,订立新宪法上。而是忙于两党争权,互相抢夺地盘。同盟会派的人希望内阁落入本党手中,大力扩张本党势力。其他党派的人,也担心内阁被操之于同盟会派手中[2]。梁启超在制定“梁氏宪草”时也变得热衷于组织政党,以争取国会议员多数,这样便可由进步党组阁,执掌全国统治权,遏制地方各省的自治倾向。梁启超等人抱着入主内阁的目的,先“投靠”袁世凯,后“力挺”段祺瑞,委曲求全,却反被军阀政治力量所利用。“梁氏宪草”的草拟和制定反映了宪法观念及意识在民国初年中国有所高涨的事实,也体现出宪法理念因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妥协性,梁氏等立宪党人对权力的迷信使宪法实质上沦为权力的附庸。
(三)工具理性主导下宪法理念的流变
早年梁启超担忧以流血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度会效仿法国革命走上专政的暴虐之路。梁启超认为暴力革命“决非能得共和,反得专制”。德国政治家波伦哈克认为:“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3]但是,适逢革命思潮迭起,邹容《革命军》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4]。此时梁启超开始对温和改良的立场感到犹豫,或迫于时局压力转向革命派的阵营,以立宪的行为冠以革命之实。
而到了民国初年,梁启超推行立宪体制的道路较为曲折。他曾经轻视立宪,转而拥护袁世凯,大力主张建立坚强有力的政府。立宪派纵容袁世凯的野心,却忘记早先所坚持的权力制衡的理念,推波助澜地促成袁世凯称帝。直到此时,梁启超彻悟未能坚持立宪:“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5]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重返国民立宪改造中国的路径,遇到民国九年吴佩孚7月直皖之战,吴佩孚召集国会,希望梁启超拟定宪法,梁启超仍然坚持不立宪不能定国平内乱的工具理性主义观点。[6]他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在没有宪法,有了宪法,便可以根绝军阀的斗争,结束内乱。[7]可惜其立宪的主张在民国初年影响力非常微弱,在争民权与兴民权、内阁制与总统制、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等权力困局中淹没。
这并不能归结为梁启超一人的过错,没有坚守他的立宪理念,而是全然依赖自认为足以安定政局的权力中枢。从民初社会舆论看来,中国各派势力对法治并未引起重视,更别说立宪。其一是民众未尝认识到宪法权威;其二立宪派和革命派对待宪法的态度具有工具理性特点,即宪法只是为政治权力服务的。民初政治的最高原则依然是传统的“有道”还是“无道”,而非“合法”或“违法”。民初的中国不是没有法统,但是无论约法或是法律最后都成为党派军阀夺取权力的工具。中国关心政治的人从向往法治,转而怀疑法治、轻视法治。
三、为改而改的“改造”
(一)梁氏对自己历来权力制衡理论之偏离
梁启超所引入的西方权力制衡思想,竭力介绍卢梭“天赋人权”——“人生而有平等之权,即生而当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与我,无贵贱一也”。[8]271当时梁启超宣扬的天赋人权论,传播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但同时也对传统的“皇权至上”旧说产生有力的冲击。梁启超认为孟德斯鸠的国家学说是“实政法学之天使也”[8]270-271。梁启超据此严厉批判数千年来的中国专制政体,认为专制是亡国之总根源。他提出中国政治转型的最佳方案,应当是君主立宪制下的三权分立。“凡所谓国家者,必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具备。”[9]也即所谓“真国家”,应当实行三权分立,使权力互相制衡,表明当时的梁启超摒弃君主专制政体,将西方近代三权分立学说视为良药。但随着伯伦知理提出的“强政府”思想对梁启超宪法观念的影响,他又提出国家观念应当是国民所应该具备的素质,“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直到拟定“梁氏宪草”时他力倡“国家主义”。
(二)政治谋略左右宪法理念
梁启超对西方政府权力制衡理论改造历程被认为是流质多变,这也说明梁氏注重对他国学说与本土资源的融合,力图针对中国立宪实况提出有创建性的法律思想。只是梁氏在对现实的估计和时局的把握上判断有失误,这也显示出梁氏在乱世中易向强权意见妥协,使得其主张不得一以贯之。例如,对于立法与行政的关系,梁启超曾在《责任内阁释义》撰文,主张国务大臣应当对国家负责,而不主张国务大臣对君主负责,也不主张国务大臣对议会负责。他继而认为,国家并非议会所有,国事也不是议会私事,因此,议会不能让政府对它负责。但“梁氏宪草”第66条却规定国务大臣对众议院担负责任。对此,梁启超没有作出解释,有可能最终的立法设计是吸取进步党大部分意见的结果,导致梁启超变更早先对国家权力结构的设想。
梁启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支持袁世凯加强政治权力的控制,即便当时国民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梁启超也不愿让国民党组阁。这导致1914年袁世凯所立《中华民国约法》昭然若揭地扩张总统权力,缩小议会立法权和行政监督权,废除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仿效美国在总统之下设立“国务卿”。事实上意味着独裁性元首制的形成。1915年1月,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的颁布实施,在立法上确定袁世凯成为终身独裁元首。
(三)权力改造受制于时政变革
1. 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关系
“梁氏宪草”订立时,“国家主义”大倡其道,中央集权思想正成为立宪的主流导向,“梁氏宪草”第一章“国家结构形式”中,梁启超主张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断然否定联邦制。在“梁氏宪草”第1条的“立法说明”里,梁启超提出:“共和国加统一两字者,示别于联邦制也”,这表明宪草的指导思想是以国家之大一统为核心。甚至于,在宪草中根本没有地方制度章节,在当时的梁启超看来“地方制度以法律定之而已足,不必以入宪法也”。但是梁启超的中央集权、国家主义主张又并不反对仿照美国强中央政府的掌权之路。早在《新大陆游记》一书中,梁启超就对美国“日趋于中央集权是也”的政治现状赞誉有加,隐含了梁氏中央集权思想的倾向。
“梁氏宪草”体现出的“国家主义”态度,适当限制国会权力,建设“强善政府”的制宪理念,客观上也比较符合当时袁世凯的制宪愿望,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意志,迎合北洋军阀的要求和愿望。但出乎意料的是,1912年袁世凯宣任临时大总统后不断加剧个人独裁统治,此时联邦制又被用以牵制袁世凯滥施权力的工具。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地方制度(即省宪)是否入宪旋即成为国民续议宪法草案的话题,赞成与反对之声均有。在两派阵营中梁启超作为赞成“联省自治”的一方,反对中央干涉各省事务。
2. 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之关系
“梁氏宪草”效法1875年法国宪法,规定总统为法律上的国家元首,而政治责任由国务员承担的责任内阁制。法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总统在征得参议院同意后,有权提前解散众议院,但总统签署每项命令,必须由部长一人副署,部长就政府的政策对两院承担连带责任。梁启超宪草“第4章国会”“第5章总统”“第6章国务员”分别规定国会、总统和国务员。例如第5章规定:大总统对外代表国家,“提出议案于国会”“公布法律”“牒集临时国会”、掌握军权以及“经国家顾问院之同意,得解散国会两院或一院”等权力。第6章又规定“国务员赞襄总统,对于众议院担负责任”“大总统所发关于国务之文书,须经国务员一人之上副署”。因此,政府实质上是由国务员负政治责任的责任内阁制。但是,法国在历史演变中,总统的权力逐渐减少,成为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而“梁氏宪草”对于总统权力的态度,却又多少受到美国总统制的影响。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总统行使行政权,在宪法所定的范围内自由行使权力,不必顾及议会赞同或反对的意见,国务员只对总统负政治责任,总统和国务员都不能担任国会议员。梁启超之“国家主义”体现出“政府主义”色彩,其目的是扩大政府权力,从而实现强盛国家,对于总统权力梁氏始终抱以希望和期许。
“梁氏宪草”规定总统有解散国会两院的权力。宪草第50条规定:“大总统经国家顾问院之同意,得解散国会两院或一院。但自解散之日起,须于一个月内行总选举,于五个月内牒集新国会。”梁启超提出效法比利时宪法体制,规定总统有权解散两院。换言之,在不需要获得参议院同意的前提下,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假如两院党派状态相同,政府所坚持的政策,或许的确有理由,但两院都持反对意见,政府欲诉诸于民意,则必须解散众议院,而根本不可能得到参议院的同意。如果这样,总统有解散权也相当于没有解散权。按照梁启超力主的“国家主义”思想,要建设强善政府,政府必须强大有力。如果不赋予政府解散权,则政府难以将强善政策贯彻始终。[10]因此,“梁氏宪草”并未对解散权作过多的限制,只要经国家顾问院同意就可以行使。
3. 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关系
在“梁氏宪草”中,梁启超认为人身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固然应当列入宪法,除了第9条为规定政府有保障人民平等权利及诉讼权利,但是宪草其余各条所规定的都是国家所不得干涉的权利,比如公民的请愿、集会、结社、言论、著述、居住等权利。不过“梁氏宪草”里并未规定参政权。其次,在宪草中将纳租税、服兵役两项义务性规定放在基本权利条款之前,将“从事一切公职之权利”规定为义务。最后,规定必要时对人民权利可以因法律而限制。宪草中经常有见如“非依法律,不得”“于法律范围内”“依法律所定”“于法律所定”等措辞,强调对权利的限制。在私拟宪草中,人民权利得到的关注普遍远比国家权力少,这似乎成为当时的共识。换言之,也是默认了政府依据法令便可对诸如请愿权、公职权等人民权利进行限制。
四、树立宪法权威乃立宪之本
(一)先立宪法之“最高权威”尔后始能“限权”
宪政首要解决的是制定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因此,参与制宪的政治党派虽然有各自的政党利益,但政党在参与制定宪法过程不能以权力争夺为立宪的评价坐标。否则对权力的限制很可能顾此失彼。梁氏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就可以按照宪法制的规定制衡国家权力,避免封建专制的复辟,但却忽略在政治秩序的构建过程树立宪法的权威,并且宪法的权威应当高于中央权威与党派权威,而不应为两者所钳制、驾空。换言之,一国宪法要得到各政治党派普遍接受,制定出来的规则并不是仅仅用于对权力进行制度安排,当然也不是因人或因党立宪,而是要维护一种超越权力与党派利益,并能牢牢驾驭国家权力的制度性权威。
“梁氏宪草”也不可避免地周旋于权力轴心,难以顶住政治权力斗争的驱使,忽视建国立宪首当其冲的是要维护中立性的制度权威。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政府组织大纲》中首次规定总统制,但因为孙中山将总统让给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目的在于通过责任内阁制制衡总统权力,并通过国民党在议会的多数席位确保国民党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当时舆论激烈地批评,所谓“约法”是因党因人立法。[11]国民党以“宪法至上、天下为公”的名义牵制袁世凯的权力,讨伐政治异己。进步党则积极借用袁世凯的势力削弱国民党的政治势力,致使袁世凯逾越法治的底线,并进行封建复辟。美国革命通过制定宪法达到“天下为公”的目的,但民国初期的中国并不是以宪法所确立的制度性安排进行国家权力的制衡,而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攫取达到限制、排斥政治对手权力的目的。
(二)在宪法框架内巩固“中央权威”
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的制宪理想是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适当限制国会权力。梁氏“国家主义”救国方案的核心便是强调国家是一元的、绝对的和有效的权威,并以此为基础推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这种国家权威的一元化反映在国家机构的整体设置上就是中央集权,宪法限制国家权力的初衷在于维护中央权威。在此之外宪法权威没有实质的意义,也就是说,在中央而言,集中权力的主体是权威的中心,地方要服从中央的绝对权威。体现在国家和国民的关系上,国家意志当然在国民意志之上,国民意志要坚决服从国家意志,中央集权或者说是国家权威一元化的伦理基础是国民个体对自由与权利的自我克制乃至自我牺牲。“梁氏宪草”中所提倡的“国家主义”也是梁启超拥护袁世凯的理论依据,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在于建立强固统一的集权国家,加强政府权力以保证政治秩序;主张国权高于民权,为维护国权的必要可以牺牲民权。[12]梁启超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中讨论国权与民权的关系时说过:“我中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阙,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倚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此宪法所宜采之精神也。”[13]在当时看来,宪法扩大总统的权力,限制国会权力和人民的权利,这刚好可以实现袁世凯总统专制独裁的美梦,事实上也间接促成袁世凯独揽中华民国总统大权,成为民初立宪史上的一场难以避免的浩劫。
立宪的精神在于,近代法治国家最高权威的转移是从人治型统治转向法理型的依宪法而治,在中央权威之上还应有更高的法律规则,那便是宪法。也即在宪法的框架之内,任何权力都必定受到制度性地制约。梁氏“强有力政府”的思想确实寄托民初中华儿女强国统一的期盼,作为一种“治国之术”“强善政府”的理念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然而,一旦逾越宪法的规制,力图偏离“政治轨道”,那么都很可能将国家权力带入万劫不复的误区,甚至为人治打开权力的篱笆,让专制独裁之治大行其道。
(三)政党依宪执政维护“党的权威”
梁启超积极助推政党政治实践以启动立宪实施宪政之路,但梁氏组建政党在于与国民党实现两党政治。进步党成立后,并没有对国民党抱以和平协商政治的诚意,而是在国会中同国民党围绕大多数重大问题展开斗争。例如,在制宪问题上,国民党主张总统解散众议院应当事先征得参议院的许可,进步党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总统解散众议院不需要经过参议院同意;在内阁制上,国民党主张组织单纯的政党内阁,只有众议院议员才能成为内阁的阁员。进步党则主张内阁阁员应由总统任命,不限于政党。[14]总之,几乎在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进步党都会与国民党相争,而且立场基本上都是为袒护袁世凯的总统权威。与1913年进步党成立时所提纲领确实有较大的距离:“(1)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2)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3)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此时的政党竞争比较像古代的朋党之争,政党政治竞争仅仅是为了个别集团或者个人的政治利益。
五、结 语
民初各派立宪人士私拟宪法之风盛行,但宪法权威的意识在士绅、军阀、各党各派的权力博弈中并未能真正树立起来,皆将立宪视同国家统治工具。在中国封建立法的传统中,即便有法律之实,但统治者可以恣意逾越法律的规定,并按照人治的权力随意制定、修改、废除法律,将人治的威严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民初立宪过程的各种争斗无一例外都是以权力相互制衡展开。然而,无论何种权力,如何在宪法的框架内加强宪法的制度性权威,却被放于次要位置,甚至于为倡言立宪救国的政党和个人所忽视。任何权力都要尊重宪法,遵守宪法,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政的制度框架中得以制衡。在宪政的体制下,国家最高权威的转移,应以宪法为核心建立最高法律效力层级的统治秩序。诚如梁启超所言,制度的选择应该“惟适是求”而不是“惟优是求”,不论一种制度在理论设计上有多么完美,如果它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那么这种制度的移植,必然是不可取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循着“权力”二字,梁启超对西方权力制衡思想的引进和反复改造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宪政理论和制度输入到中国后,与中国几千年本土法治文化所发生的剧烈碰撞。
[1] 梁启超.立宪法议[M]∥饮冰室合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1.
[2] 张耀曾.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6.
[3]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M]∥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073-1074.
[4] 邹容.革命军[M]∥张枬,王忍.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78:.651.
[5]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902.
[6]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0:583.
[7] 梁启超.军阀私斗和国民自卫[M]∥饮冰室合集:第3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36-40.
[8]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M]∥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9] 梁启超.《斯巴达小志》按语[M]∥饮冰室合集: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307.
[10]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J].现代法学,2001(6):27-32.
[11]荆知仁.中国立宪史[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185-186.
[12]李育民.进步党述论[J].近代史研究,1986(2):159-160.
[1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407.
[14]胡绳武.梁启超与民初政治[J].近代史研究,1991(6):98-100.
[责任编辑 吴震华]
On Introducing and Localizing of Western Constitutional Theories in Liang Qichao's Private Draft Constitution
WAN Jun
(2ndSupervisionOffice,BureauofSupervisionofGuangzhouMunicipality,Guangzhou,Guangdong510046,China)
As the fundamental law of the country, the Constitution functions should not only function as a good law enacted with great deliberation, which must not be constantly changing. In 1913, Liang Qichao put forwarded the private draft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set forth political view of the Progressive Party. Liang Qichao abandone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urned to democratic republic, and preferred the unitary system to the federalism practiced in US, and chose presidential system rather than responsibility cabinet. It indicates the compromise among the political powers and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of the state power.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draft constitutions shows that the current legal construction may not only be based on the transplantation of the foreign law, that the foreign legal thoughts should be absorbed, that the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which will surpass the parties and the party power, so as to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cept suitable for its implementation in China.
draft constitution; theory of checks and balances; Liang Qichao
2016- 04- 27
王军,广州市监察局第二监察室副主任,中山大学法学院在职博士生,从事中国法律思想研究。
D092
A
1671-394X(2016)10- 0056-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