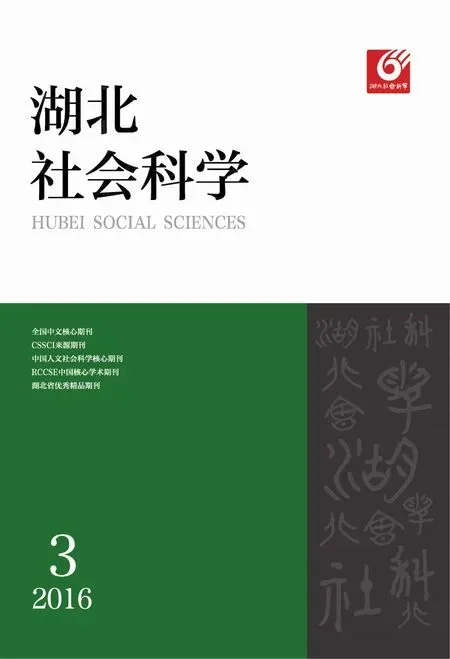摩尔“自然主义的谬误”观批判
侯忠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摩尔“自然主义的谬误”观批判
侯忠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摩尔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利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根据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对自然主义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自然主义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伦理学根据事实与价值的联系,用“自然事物及性质”以及“形而上学的实在及性质”给“善性质”下定义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说,摩尔的元伦理学所强调的只是传统伦理学的形式方面,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在社会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建立起真正合理的关于“善性质”的定义。
关键词:摩尔;自然主义的谬误;善
长期以来,实践主要指道德实践,关于实践的“科学”主要是关于行为规范的理论,因此,传统伦理学主要是规范伦理学。英国新实在论者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发表,将伦理学分成理论伦理学(元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两大类型,标志着西方元伦理学的兴起。元伦理学不是从社会道德状况的事实出发制定行为规范,而是把语言分析、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引入伦理学,理解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寻找道德判断的根据,分析道德推理的逻辑。摩尔认为:“伦理学的直接目的是知识,而不是实践;而且,任何一个利用自然主义的谬误的人,无论他的一些实践原则多么正确,肯定没有达到这一首要的目的。”[1](p30)摩尔指责实践伦理学不论是自然主义伦理学还是形而上学伦理学都犯有“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因而是不“科学”的。要想建立起“科学”的伦理学,首先要避免“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
一、“自然主义谬误确是一种谬误”[1](p53)
摩尔认为伦理学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善是什么?”的问题。摩尔说:“一切伦理学问题都可以归于三类之中的某一类。第一类只包含一个问题:……‘善’是什么意思?……还剩下关于这个属性对其他各事物的关系的两类问题。我们或者可以探问(1)这个属性在什么程度上直接属于哪些事物?哪些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或者可以探问(2)用什么手段我们将能使世界上实存的事物尽可能好一些?本身最好的事物与其他各事物之间存在什么因果关系?”[1](p52)简言之,“善是什么?”这一问题在摩尔那里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善的”或“善性质”是什么?第二,哪些事物是目的善?第三,哪些事物同目的善有因果关系即哪些事物是手段善?“自然主义的谬误”观与“善是什么?”的第一层意思相关,即与“善的或善性质是什么”相关。由于摩尔认为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绝对相同,所以在摩尔那里,“善的”或“善性质”是不可定义的。如果用“自然事物或自然事物的性质”或者“形而上学实在或形而上学实在的性质”给“善的”或“善性质”下定义就会犯“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如摩尔所说:“当他们说出这些别的性质(属于一切善的事物的其他各个性质)时,他们实际就是在给‘善’定义,并且认为这些性质事实上并不真正是‘别的’,而是跟善性绝对完全相同的东西。我们打算把这种见解叫做‘自然主义的谬误’。”[1](p19)摩尔认为传统规范伦理学分为两类:自然主义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并认为传统规范伦理学都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
首先,对自然主义伦理学所犯“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进行批判。摩尔说:“那些宣称惟一善的东西就是事物在时间上实存的某一性质之理论,是‘自然主义的’理论。”[1](p58)自然主义伦理学包括斯多葛派的伦理学、进化论的伦理学、快乐主义的伦理学(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摩尔认为自然主义伦理学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就是用一个自然客体的或者自然客体集团的某一种性质来代替‘善’;于是,就用某种自然科学来代替伦理学。”[1](p55)摩尔认为科学和伦理学应区分开来,不应相互混淆。摩尔对各种自然主义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古希腊斯多葛派提出的典型的自然主义伦理学命题是“依照自然而生活”,“依照自然而生活”意味着用“自然”给“善的”下定义。如果所有的自然事物都是善的,那就无法区分善恶,因此也就否定了伦理学的研究。如果自然规定“正常”是善的,事实上并不是一切正常的都是善的,有些情况下异常的比正常的更善。如果自然规定“必需”是善的,但形而上学对人来说不是必需的,却不能说形而上学不是善的。无论怎样理解自然,然后把自然定义为善的,都会导致矛盾,从而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经验的事实与“善的”(“善性质”)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更不可能等同。
进化论伦理学认为进化是“善的”。进化只表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完全可能的是无比低劣的物种会比我们生存得更长久。进化也不表明一定进化出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并不与“善的”相等同。进化只是一条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与价值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进化的事实推不出“善的”结论。
快乐主义伦理学认为只有快乐作为目的是“善的”。快乐主义伦理学认为快乐是值得向往的惟一的目的善,其他一切事物只是作为手段才是“善的”,原因是快乐是人们实际向往的。实际向往的既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既可能是手段善也可能是目的善,因此实际向往的不一定是值得向往的或应该向往的,因此不能证明快乐是“善的”。摩尔用“未决问题论证法”、“绝对孤立法”和“有机统一原理”反驳了“惟有快乐作为目的是善的”。根据“未决问题论证法”,如果用快乐定义“善”,只要反问“快乐是善的吗”有意义,就证明用快乐定义善不成立。根据“绝对孤立法”(“绝对孤立法”是通过除去事物的通常伴随者,让它绝对孤立存在,然后确定它的价值),只有快乐是善的,快乐意识等是没有价值的。但根据“有机统一原理”(整体的价值不与各部分的价值成比例,也不等于各部分的价值之和),作为整体的某部分虽然可能不具有内在价值,但却是整体具有内在价值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快乐并不是惟一的目的善,快乐意识也是这一目的善的真实部分。快乐不是惟一的目的善,快乐只是目的善之一,快乐是复合的,因此快乐是可定义的。“善的”、“善性质”是单纯的,不可用复合的快乐定义善,只能用善定义快乐。
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快乐主义的两种形式)也犯有“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作为手段的利己主义与作为目的的快乐主义是不同的,利己只是达到快乐的手段,一己的快乐不是惟一善的。因为利己主义主张每个人的快乐都是惟一善的,也就是主张存在很多惟一的绝对的善,这是明显自相矛盾的。“利己主义主张每个人的幸福都是惟一的善,也就是主张在许多不同事物当中,每一件都是可能的惟一善的事物。这是一绝对的矛盾!”[1](p129)利己主义不能解决每个人为追求快乐所引发的冲突。功利主义根据结果来判断善恶是合理的,但功利主义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无法确定什么是最好的结果。其次,倾向于把每一事物仅仅看成是手段,因而永远达不到目的善。再次,“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明显与快乐主义的基本原理“快乐是惟一的目的善”相矛盾。最后,功利主义不能解决个人快乐与普遍快乐的矛盾等等。
自然主义伦理学是用自然事物或自然性质给善下定义的伦理学。摩尔认为自然主义伦理学是把单纯的“善性质”混同于自然事物或自然性质,因此犯有“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其实是把事实混同于价值。因此摩尔认为事实与价值是有根本区别的,从事实不能推导出价值,从是然推不出应然,从存在求不出应该。
其次,对形而上学伦理学所犯“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进行批判。斯宾诺莎、康德以及新黑格尔主义者的伦理学说是形而上学伦理学的典型代表。斯宾诺莎认为对神的理智的爱是善的,康德认为“目的国”是善的,新黑格尔主义者认为“真正的自我”是善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把“善”归结为某些超时空的永恒实在,那些永恒实在的事物不可能受我们行为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我们也不可能造成任何“善”。形而上学伦理学之所以犯“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是因为形而上学伦理学认为“善的”必定具有超自然的性质,于是就通过形而上学的方法找出某些形而上学的实在或形而上学实在的性质来定义“善的”或“善性质”,这是从错误的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善的”是单纯的超自然的性质,本身不具有其他超自然的性质,因此,“善的”不能归结为任何其他超自然的实在或超自然的实在的性质。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断言,思索认识的内容就能把握世界的真理;而思索意志和感觉的内容,就能发现世界的善和美。然而,如同“是真实的”与“被思维”是两回事一样,“是善的”与“被矢志”也不相同。最多只是说明了“被矢志”是“善的”信念的原因,“被矢志”与“认为善”相伴随。这一切说明,形而上学伦理学对善的定义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
摩尔所谓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是指以某种形而上学的命题为基础来推导伦理学的基本命题,用形而上学的实在或形而上学实在的性质来定义善的伦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者以某种超经验、超自然的性质(善良意志、纯粹实践理性)来定义“善性质”,或者以某种先验绝对的实在(上帝)来定义“善性质”,或者以“绝对自我”来定义“善性质”,这些定义都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因为形而上学的实在或形而上学实在的性质与价值(“善性质”)是有根本区别的,价值与事实是有根本区别的,因而从形而上学的实在或形而上学实在的性质推不出价值(“善性质”),从价值推不出事实(存在),从应然推不出是然,从应该求不出存在。形而上学伦理学首先把“善性质”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实在或形而上学实在的性质,即把“善性质”与其他伦理概念相混同,其次把事实与价值相等同,从而犯了双重的错误。
摩尔对传统规范伦理学所犯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批判的合理性在伦理学上根源于他对“什么是善?”这一问题的三个层次的划分。而对“什么是善?”这一问题三个层次的划分其实是英国哲学家休谟早就提出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全面化和彻底化。把“善”严格区分为三层意思:“善性质”或“善的”、目的善和手段善。把“善性质”或“善的”和目的善归为价值,把手段善归为事实。把价值与事实,把主观与客观绝对区分开来,同时,把“善性质”或“善的”与其他伦理概念绝对区分开来,是摩尔对传统规范伦理学“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进行批判的主要根据。
摩尔对传统规范伦理学在善的定义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判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把伦理概念归结为自然事物及性质、个人的心理状态、超自然的实在及性质,不可能区分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善性质”或“善的”与其他伦理概念。善、恶等伦理概念不是代表任何孤立事物及性质的描述词,善、恶等伦理概念不能等同于评价对象。善、恶等伦理概念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事实的评价。把“善性质”或“善的”与其他伦理概念绝对区分开来,把“善性质”或“善的”作为伦理学体系的惟一的标准,从而保证了伦理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因而把事实与价值绝对区别开来,同时,把“善性质”或“善的”与其他伦理概念绝对区分开来,是有极大的理论价值的。
二、“自然主义的谬误”观的谬误
摩尔的第一部分是对传统伦理学(自然主义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伦理学)在“善的”定义问题上的理论的批判。在伦理学上的根据是事实与价值绝对二分,以及,“善性质”或“善的”与其他伦理概念绝对二分,并对自然主义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伦理学所犯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作了具体的批判。第二部分也就是这一部分是对传统伦理学在“善的”定义问题上的理论的积极意义的论证,即对“自然主义的谬误”观的批判。在伦理学上的根据是事实与价值的联系,以及,“善性质”或“善的”与其他伦理概念的联系。在这第二部分里,对自然主义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伦理学在“善的”定义问题上的理论的积极意义不作具体的论证,只作一般的论证,论证如下。
摩尔认为单纯的概念不能下定义,只有复合的事物才能下定义,摩尔说:“‘黄’和‘善’并不是复合的:它们是那种单纯的概念,由其构成诸定义,而进一步对其下定义的能力就不再存在了。”[1](p15-16)摩尔同柏拉图一样把单纯概念本体化了,但没有脱离感性事物的单纯性质。“黄”不能与黄事物分离开来,“善性质”也不能与善事物分离开来,在这一点上“黄”与“善性质”是一样的,个别与一般是不能分离的。“黄”与“善性质”虽然是单纯的,但黄的事物和善的事物都是复合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复合的黄的事物和善的事物来定义“黄”和“善性质”等等。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科学地定义善事物,但通过善事物可在历史的过程中建构起越来越深入的关于“善性质”的定义。在这一点上传统规范伦理学通过对善事物的定义来定义“善性质”是合理的。
“善性质”与自然性质根本不同,但离开自然事物、自然性质,“善性质”怎么存在呢?孤立的“善性质”如何与经验行为、感性事物发生关系呢?“善的(善性质)”、值得追求的首先应是符合规律的。虽然事实与价值有根本的区别,但价值一定包含事实,而且,应然是从是然来的,应该是从存在来的。关键是应然怎样从是然来,应该怎样从存在来。价值与事实之间是可以通约的,从存在中可以求善,善可以用自然事物或自然性质来定义。
摩尔认为“形而上学的实在及性质”无法与善事物发生联系,而摩尔又认为作为本体的“善性质”可以与善事物发生联系,这是自相矛盾的。摩尔又认为只能从“善性质”推出正义、义务、应该等伦理概念,不能从其他伦理概念推出“善性质”,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其实,“形而上学的实在及性质”、“善性质”、正义、义务、应该等概念都是从经验来,又都存在于经验之中,因此,它们是相互通约的。也就是说,可以用“形而上学的实在及性质”来定义“善性质”,也可以用其他伦理概念来定义“善性质”。
摩尔的“自然主义的谬误”观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但是,有绝对客观的事实吗?有不含有价值的事实吗?江畅教授说:“对于同一价值关系,人们可以作出两种不同的判断,对于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主体来说,作出的是价值判断;而对于这种关系之外的判断来说,作出的是事实判断。”[2](p361-362)同一价值关系中有事实关系,这说明价值中是蕴涵事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脱离人的自然事实对人来说就是无。事实都是与人相关的事实,“事实是我们人类眼中的事实,是包含了人类主观性的事实;价值是蕴涵着人类实践客观性的价值。”[3](p83)在人类产生以后,自然、“神”、人、社会都处于与人的关系之中,都是一种价值关系,因此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实不蕴含着价值。价值与事实二分,善与其他价值也是二分的,因此才需要对善下定义。又因为价值与事实、善与其他价值是相互联系的,并且价值与事实二分与善与其他价值二分只是价值与事实、善与其他价值相互联系之中的形式方面,所以,传统伦理学通过事实以及除善以外的价值给善下定义是合理的,也就是说,通过自然事物及性质或形而上学的实在及性质是可以给善下定义的。
三、“自然主义的谬误”观及“自然主义的谬误”的根据的根据
上述第一部分摩尔批判了传统伦理学所犯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认为单纯的善是不可定义的,相反,只能用善定义善以外的伦理概念以及用善评价事实,其伦理学上的根据是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以及善与其他价值的二分。上述第二部分摩尔对“自然主义的谬误”观进行了批判,也就是对传统伦理学在善的定义问题上的理论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认为善不仅可以用其他伦理概念来定义,而且可以用自然事物以及自然事物的性质来定义,其伦理学上的根据是事实与价值的联系以及善与其他价值的联系。上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在论证过程中所用的伦理学上的根据在哲学上的根据表现在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等方面。
从本体论方面看。在摩尔的元伦理学中,也就是在对传统伦理学在善的定义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判中,“善的”或“善性质”是宇宙之中不依赖于客观事物、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不依赖于社会历史的独立自在的性质。“善的”或“善性质”与自然事物或超自然的实在都没有关系。“善的”或“善性质”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非自然的性质。“善的”或“善性质”不能从别的事物中推导出来,相反,其他的伦理概念都要从“善的”或“善性质”推导出来。摩尔的元伦理学把“善的”或“善性质”完全本体化了。把“善的”或“善性质”本体化的观点导致了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善与其他价值的彻底二分。
从逻辑学方面看。“善的”或“善性质”的本体论化也导致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二分和对立。因为事实与价值不能互相推导,“善的”或“善性质”与其他伦理概念也不能互相推导,完全割裂了“善的”或“善性质”与其他任何事物的联系,把伦理学完全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了。这表现在摩尔在论证中所使用的方法(未决问题论证法、绝对孤立法、有机统一原理)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之中。未决问题论证法的本质即认为定义项与被定义项静止地同一。绝对孤立法的本质是把某部分与整体中其余部分绝对割裂开来作为孤立对象考察,部分也有其绝对的价值,部分也是绝对的目的而绝不是手段。有机统一的原理是指整体价值不与各部分价值成比例,也不等于各部分价值之和。有机统一原理的实质是虽然在形式上承认了整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在内容上,整体中的各部分却是相分离的,因此,根本上还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从认识论方面看。“善性质”的本体化,论证的形式逻辑化,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善性质”与其他伦理概念的二分,也导致了主观与客观的二分。“善性质”和目的善是纯客观的,不能通过经验和理性来认识,只能通过直觉。摩尔说:“我把这样的诸命题称为‘直觉’,我的意思仅仅是断言它们是不能证明的;我根本不是指我们对它们的认识的方法或来源”[1](p4)这无异于说,直觉是纯主观的,不能认识纯客观的“善性质”和目的善,但又要假定直觉能认识“善性质”和目的善。
从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方面看。孤立的本体论既无法表达,也无法认识。孤立的逻辑学一定是形式逻辑。孤立的认识论就只能是直觉,既无法表达也不可能逐步深入的直觉。
在本体论方面,传统伦理学并不把“善性质”作为本体,但认为“善性质”有与其他性质相区别的独特含义。在逻辑学方面,传统伦理学不仅运用形式逻辑,而且运用辩证逻辑。在认识论方面,传统伦理学不仅运用直觉的方法,还运用经验和理性的方法。总之,摩尔的元伦理学只是传统伦理学的形式方面。摩尔的元伦理学只是说明了“善性质”与其他的概念和事物不同,但没有回答“善性质”的定义是什么。传统伦理学不仅认为“善性质”与其他的概念和事物不同,而且认为“善性质”可以通过自然事物及性质或形而上学的实在及性质来下定义,但传统伦理学对善下定义的理论没有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
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才能合理地说明“善性质”可以通过自然事物及性质或形而上学的实在及性质来下定义。“事实与价值均是与人相关、基于人的实践主体性的一种客观存在,在人的实践基础上,它们具有统一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不相关联的事实与价值。”[3](p349)在实践的基础上,自然不断地人化,同时人不断地对象化。对传统伦理学在善的定义问题上的理论得失的论证和批判在伦理学上的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分与事实与价值相联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同一理论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事实与价值二分是事实与价值相联系的形式方面。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产生着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另一方面又产生着事实与价值的联系。在实践的基础上,从事实可以推出价值,从价值也可推出事实。从事实到价值、从价值到事实的过程,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伦理学上的根据从理论上说在哲学里,但无论伦理学上的根据和哲学上的根据最终都在实践之中。“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4](p78)哲学也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哲学也只有成为实践的一个方面才能起作用。实践才是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对立统一的根据,因而也是事实与价值二分和事实与价值对立统一的根据。因此,与“自然主义的谬误”观所认为的善不可定义相反,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自然事物及性质或形而上学的实在及性质是可以给善下定义的。
四、“自然主义的谬误”是走向善的定义的道路上的路标
摩尔的元伦理学为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变的“善性质”作为科学的、形式的标准,而犯有“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的传统伦理学则为伦理学提供了善事物作为研究的内容。摩尔的元伦理学及传统的规范伦理学都缺少社会实践的内容。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传统伦理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历史过程中建构起善的定义。
自然主义伦理学从感性事物出发不断超越到善本身,这是一条从个别到一般的上升的路。这条道路上的路标就是善本身的一个一个的必然的环节。自然主义伦理学在犯“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的同时是对善本身的认识的深化。
形而上学伦理学及摩尔的元伦理学从超感觉的实在及性质出发不断深入到感性事物。这是一条从一般到个别的下降的路。这条道路上的路标也是善本身的一个一个的必然环节。形而上学伦理学在犯“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的时候,既是对善本身认识的深化,同时是对事物本身的深入。虽然总不能用善本身达到对具体事物的彻底把握,也不能找到善本身内部完整的内容,但总在不断展示善本身和深入事物本身。
自然主义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伦理学在关于善的定义问题上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上升的过程其实是下降的过程,超越的过程其实是深入的过程。“事实和价值仅仅代表着同一自然秩序的不同方向。‘经验向下看,规范向上看。规范考虑总是与更广泛的语境有关,但不存在特别的(与特别的规范对立的)经验主题。’”[5](p114)自然主义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伦理学探索到哪里,人类自由的范围的边界就到哪里,人类对善的定义的边界就到哪里。而推进理论研究的终究是社会历史实践,使得人类逐步获得自由的终究是社会历史实践。人类自由以及作为自由的结果的善、恶等的最终起点和终点都是社会历史实践。
摩尔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进行的批判,创立了元伦理学。摩尔的特别贡献在于为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起点,即“善性质(善的、善本身)”,摩尔的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与形而上学伦理学相类似,且有合理之处。摩尔与传统伦理学不同的是:摩尔把对“善性质”的研究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只是建立了一个形式的、外在的标准;突出了伦理学要“科学化”的要求并形成了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从静止不变的“善性质”出发,从而走向了形式主义。要建立真正“科学”的伦理学,就要把“善性质”这个外在的标准建立为伦理学的内在的标准,那就是要把在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建立起的“善性质”的定义作为伦理学的标准。只有把摩尔开创的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的方法内化到规范伦理学的研究中去,把不可定义的“善性质”说清楚,才能使伦理学的研究走向真正“科学”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摩尔.伦理学原理[M].长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2]江畅.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聂文军.元伦理学的开路人[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向敬德.西方元伦理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高思新
·人文视野·文学·语言
作者简介:侯忠海(1964—),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3-01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