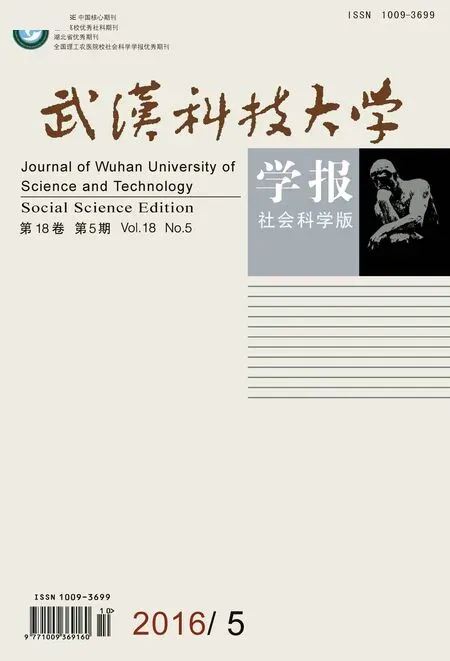“自由”不能止于“解放”:论阿伦特的自由观
杨明佳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自由”不能止于“解放”:论阿伦特的自由观
杨明佳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理念,集中体现在她与众不同的自由观上。在对18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进行政治哲学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阿伦特所推崇的美国式的以强调公民参与的自主性的自由理念,以别于法国式的将自由与解放混同的被动式的自由理念。
阿伦特;解放;自由;共和主义
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构成了现代性的根本价值,康德就宣称,“人类理性的立法(哲学)有两大目标,即自然和自由”[1]。但自由之重要不代表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没有分歧,正如美国学者方纳所指出的,“自由从来就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战场,众多的定义在这里竞争交锋,自由的定义因而不断得以创造和再创造”[2]。习惯上,人们多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和界定自由,但是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所诱发的近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种种危机,促成有着悠久传统的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在战后的复兴。犹太裔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从其行动理论出发,通过对18世纪末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政治哲学反思,系统地诠释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本文将以阿伦特的《论革命》为文本,从“解放”与“自由”两个政治概念的关联与差异的比较分析着手,对阿伦特为代表的共和主义的自由理念作一个初步分析。
一、“解放”与“自由”的语义溯源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所提出的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分,有着特殊的重要价值,它不仅为后来以赛亚·伯林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概念提供了直接思想源头,而且也为当代的共和主义者重新发现古代自由观念中的共和价值提供了思想的素材。但事实上,从自由在英语中的两种表达(liberty与freedom),就可以发现自由的历史文化起源的多样性,也就是说,贡斯当笼统地谈论的古代自由,从一开始就存在多样的内涵,因此,在分析阿伦特的自由思想之前,先就解放与自由两个词作语义学的追溯。对此,美国政治文化学者大卫·费舍尔已经有比较深入研究[]。
在西方语言中,英语的解放(liber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Livertas,意思是指不受限制和约束,或者说就是免于限制。同义字是solutus,源于动词solve,意思是去掉约束。解放(liberation)一词又与自由(liberty)一词同源。按照美国学者费舍尔的解释,与“解放”相联系的自由(liberty),是所谓典型的地中海式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是在特定社会共同体中,一部分人依据法律获得的不从属于任何人的独立性,一种与奴隶状态对立的自主性的存在状态。由此,此种自由在费舍尔那里被定义为Liberty as separation。显然,在希腊罗马拉丁语世界中,此种自由是特定社会主体的特殊权利身份,并且与另一部分人的奴隶状态相联系。但是,一旦奴隶获得主人许可,也可以通过某种法律形式的认可,成为法律上的自由人。
但是北欧世界的自由(freedom),则起源于北欧语言的大家族中,英语中的free一词,与挪威语中的fri,德语中的frei,荷兰语中的vrij,芬兰语中的vrig,凯尔特语中的rheidd和威尔士语中的rhydd有关,有一个共同的词根,都源于印欧语系的priya或friya以及riya,意思是亲爱的、可爱的。在北欧人的理解中,freedom的意思是某个人通过血缘联系和享有的共同体的权利成为自由部落的一个成员。可见,与Liberty所强调的独立性不同,在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联系,费舍尔将其命名为Freedom-as-be-long,也就是说,在古代北欧日耳曼人的世界中,自由是个人作为一个部落成员与生俱来的不可剥脱的权利,并不需要特别的法律认可,与此同时,作为共同体之一分子,这种自由更多是一种义务,每个成员为了维护共同体的自由特质,而必须有所作为。
简言之,如果说地中海式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不受他人隶属的独立状态,那么北欧的自由则以共同体成员的持续广泛地参与共同体公共事务为特征。这样,liberty与freedom的区别,似乎接近于伯林所定义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抽象理论分野。
作为共和主义信徒的阿伦特,其主要思想渊源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政治传统,因此在她眼里,美国独立革命所承载的价值,既不同于作为文化渊源的英国革命,也截然有别于法国大革命,而是遥远的希腊罗马的古代共和主义在新形式下的复活。从这个意义上说,阿伦特并不认同对美国革命的自由主义的解释,而是将其视为悠久的共和主义传统在近现代社会的复兴。正是建立在这一基本理论预设基础上,阿伦特对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发生的两场革命,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比较与反思,从而集中地表达了她的自由价值观以及彰显这一价值的政治制度设想。
二、“解放”与法国革命的自由主义政治叙事
何谓革命,阿伦特接受了法国思想家孔多塞的解释,认为革命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既然自由世界通常的观念是,判断政治实体宪法的最高标准既非正义,也非伟大,而是自由,那么我们打算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或拒绝这种一致性,就不仅取决于我们对革命的理解,而且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概念。须知,自由本源上显然是革命性的”[4]18。这样,阿伦特就将革命与自由之间建立起了直接联系。既然如此,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应该导向启蒙运动确立起来的核心价值,即通过革命摧毁旧的不利于个人自由度社会制度安排,并最终依据理性原则建立起一个保护自由的基本制度框架。革命的“核心理念就是以自由立国,也就是建立一个政治体,保护自由得以实现的空间”[4]108。因此,一个社会的政治知识精英与大众认同何种自由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影响到现代革命的进程与结局。
从社会结构上看,革命前的法国具有前述的所谓地中海式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社会内部少数人的自由以特权的方式呈现,处于社会等级结构底层的所谓第三等级承担着大量义务,却无法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因此,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比较同时代的英国思想家而言,除了孟德斯鸠等少数人具有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外,从共和民主主义的卢梭到自由主义的伏尔泰到社会主义的马布里、巴贝夫等,都将消灭等级特权、实现社会平等作为他们最为重要的价值诉求。因此,尽管法国革命起初也以自由为旗帜,但是,不平等社会结构下底层社会对平等的强烈政治要求,改变了法国革命后期的政治走向。自由的价值让位于社会幸福或社会平等,结果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超越了权力的边界,企图直接用公权力也就是雅各宾派的专政来兑现社会平等。问题在于,当权力肆无忌惮时,不仅个人自由将因为权力失控而荡然无存,而且在后革命社会中阶级清算泛滥时,不同阶级的政治平等也将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一意孤行的极端革命,将催生社会内部的反对革命的力量的政治联合,从而难以形成各种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政治权威,国家必将在左右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法国革命后也因此形成了长期动荡的政治格局,“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从根本上,就是因为它偏离了现代革命的自由立国政治旨趣。对这样一种结果,阿伦特曾经对现代社会的革命历史之吊诡发出这样的感慨:“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也知道,在未曾爆发革命的国家中,自由维护得更好,无论那儿的权力环境有多么残暴不仁,而且革命失败的国家甚至比革命胜利的国家还存在更多的公民自由。”[4]99
法国革命的结局之所以如此,固然与上述的法国等级对立的社会阶级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与法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有一定的关系。阿伦特认为,法国人的自由观,是一种解放式的自由观,解放与自由虽然存有密切联系,但是二者却不能等同。阿伦特解释说,“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观念只能是消极的,因此,即便是解放的动机也不能与对自由的渴望等而视之。”[4]18也就是说,解放所蕴含的自由,被表示为某种特定的解除束缚状态的一次性政治事件,自由似乎可以通过推翻束缚性的专制体制而唾手可得,只要革命后能建立起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那么自由就是真实的,革命的核心价值就可得以实现。按照此种自由观,当法国人民摧毁了巴士底狱,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并颁布了《人权宣言》后,自由之光就自然降临到了法国,于是自由似乎在革命后不久就成为已经完成了的政治使命,革命后的重心转移到谋求社会平等也就顺理成章。阿伦特就此评论道:“革命的角色不再是将人从其同胞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更不用说可以自由立国了,而是使社会的生命过程摆脱匮乏的锁链,从而可以不断高涨,达到极大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是自由,而是富足,现在成了革命的新目标。”[4]52而在阿伦特看来,法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在近现代世界的重大政治革命中并非一种特例。
另一方面,个人自由的获得不仅需要“解放”这一前提,而且还必须有赖于个人主体性的确立,但是“解放”本身并不一定包涵主体性的确立。在专制等级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的社会等级,有两种途径可以获得解放,其一是自我解放,也就是通过参与革命解除对上层阶级的依附与从属关系,获得独立;其二是个人并没有参与革命,但是在他人革命的条件下,由于摧毁了旧的社会统治结构,从而被动获得解放。前一种解放,常常伴随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此种自下而上的造反式的革命,却又常常因为革命中阶级意识的对立化,而有可能将从前的主奴关系颠倒过来,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个人常常在革命后成为政治上的贱民,所谓给人民自由、对敌人专政是阶级革命的逻辑,但往往却是自由与人权的灾难,最终人们将意识到,在这种解放话语背后,任何人,即便是革命阵营中的人乃至于革命精英,都极有可能成为这种革命逻辑的牺牲品,从法国革命的罗伯斯庇尔到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莫不如此。而后一种解放,则因为自由是他人政治成功的恩赐品,因此并不利于真正建立起某种自我解放的主体性意识。尤其是在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家,在自由价值还未充分启蒙的社会里,普罗大众更容易将自由看成是一种可以由他人恩赐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需要建立在主体性意识之上的并透过不断政治参与来加以维护和充实的行动过程。他们只有在自身的权利受到严重伤害时才意识到自由的重要,同样他们依旧可能祈求那些强势社会集团回应他们的要求,再解放他们一次,再多给他们点自由。
因此,革命尽管伴随着解放,并且为自由之确立提供了某种前提性条件。但是,从阿伦特的分析中,还是可以比较清晰地注意到她对革命与解放的某种审慎态度,她意识到如果革命者将自由等同于解放,那么革命的自由立国宗旨并不一定能顺利实现。显然,阿伦特对法国革命的反思既不同于保守主义者,也不同于多数自由主义者,而是从共和主义的角度,关注了这一革命事件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念及其后果。在她看来,理性与必然性支配下的法国大革命,将自由替换为解放,将自由的希望寄予一部宪法和强势的革命党人,必将导致革命的扭曲,从而结出暴政和动荡的政治恶果,这样,法国大革命既昭示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活力,也隐含了以消极自由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政治的固有弊端。
三、“自由”与美国革命的共和主义解读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美国革命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的成功典范,美国宪法被看成是自由的法,美国革命之所以没有重蹈法国革命的覆辙,在于他们继承英国宪政传统,并创立联邦体制,解决了个人自由与国家主权的平衡问题,从而实现了联邦党人的设想,摆脱了政治中的偶然性与机遇,人类第一次按照理性原则,建立起了一个促进和保护个人自由的政治体系。但是阿伦特显然对美国立宪建国的自由主义叙事持保留态度,她将美国革命视为共和主义政治的成功实践。阿伦特认为,美国革命最为宝贵的遗产,在于它践行了共和主义的政治理念,在联邦共和体制下,建立了一个保障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公共空间。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推崇的消极自由观念源自如下基本逻辑: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理性的个体在合理地追求私利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市场体制,实现私利与公益的自动平衡。因此,社会让渡给政府的公共权力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个人自由竞争创造一个基本制度框架,国家与社会存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因此自由主义的自由,主要指个人在私域中不受公权力和他人干涉,免于外在专断权力的压制,这是从洛克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而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之所以成为一个时期的主流观点,多少也切合了近代民族国家崛起、市场经济兴起、市民社会发育之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格局,对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而言,不受外在压制的追逐个人利益成为多数人生活的重心,国家被视为必要的恶,于是建立一个限权的政府就成为个人获得这种消极自由的关键,个人所要做的不过是依据掌权者的执政业绩定期通过选票来决定是否更换政府官员。多数时候,个人可以不必参与公共事务,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私事。理性的自私的个人的逻辑,划定了自由主义推崇的自由理念。
不同于自由主义者通常将自由定义为一种消极自由,一种免于暴政的权利,阿伦特从共和主义的角度这样定义自由:“自由的实质内容是参与公共事务,获准进入公共领域。如果革命仅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唯一目标,那它的目的就不是自由,而是解放,也就是从滥用权力,对历史悠久而且根深蒂固地权利肆意践踏的政府手中解放出来”。“解放是免于压制,自由则是一种生活方式”[4]21。阿伦特虽然不反对个人追逐私利,也主张建立限权政府,但是她认为,如果现代人对政治和自由的理解仅仅停留于此,就难以避免独裁与专断的复活,尤其是西方的多数民主体制极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演变为多数暴政,而这也正是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主旨。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政治实践的屡遭挫折,给予了阿伦特共和自由观以历史经验的支持。
阿伦特之所以将自由理解为一种公民不断参与公共事务的生活方式,在于她对人的生命之价值有着独特的理解。阿伦特认为人之价值只有在行动中得以彰显,但是这种个体特质的自我彰显离不开一个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缺乏了表现之空间,同时言行之互动不再被视之为人类共同生活的模式,那么个人之自我与认同的实在性,以及环境世界的现实性就无法确立”[5]208。这样,是否存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就成为人之生命意义能否得以彰显的必要条件。有学者这样概括阿伦特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唯有在这一空间出现的地方才能存在,在这个空间上,人彼此承认公民的身份,在其间,人彼此处在一有限之架构的共同世界,透过秀异的言行而彰显其个体性,去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另一方面,经由谈论与说服,表现合作共事的心志、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体认共和政治传统所强调的‘公共欢愉与福衹’。”[6]受古典城邦政治实践的影响与启发,阿伦特认为政治之真谛在于个人在公共领域里透过持续性的参与行动来彰显公民个体的特殊性与不可替代性,进而获得真正的共同体身份与共同体其他成员的承认与尊重。阿伦特明确指出:“公共领域是充满激烈之‘求秀异之表现精神’,在公共领域中,每一个人不断地以他的言行跟其他的人区别,透过他的独特的言行与成就表现他个人的优越性。换言之,公共领域是保留人的个体性,也只有在公共领域内,人才可能表现他真正的、无可替代的身份。”[5]41可见,基于行动理论和古典城邦政治的经验,阿伦特认同的自由截然不同于局限于解放的那种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自由在她看来仅仅表示以行动开启新端的局面,把新事物带给我们生活的共同体,以及持续不断的行动时间中完成一件事业。菲利普·汉森精辟地指出,与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论说不同,“阿伦特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与共同体及确立共同契约的各种历史可能性分不开的,阿伦特捍卫的是政治共同体里的自由,不是个体反抗共同体的那种自由——自由是一种政治的或公有社会的现象,而行动则是真正政治的核心”[7]。阿伦特以人的生生不息为立论基础的自由观,赋予公共领域或参与公共事务特殊的重要性。与传统共和主义一样,既然公共领域的生活如此重要,因此,不仅需要在革命后创建一个制度化的公共空间,为个人频繁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便捷条件,而且也需要参与共同体生活的公民都是有能力履行勇气、尊重、友谊、善尽责任等美德的公民。
阿伦特认为,美国革命正是共和主义自由观指导下的政治实践,一种开启新端的政治创新,她注意到了美国政治精英对革命的体验,“他们在所肩负的事业的性质中,发现了自身的能力,而唯有在解放的行动中,他们才发现了自己对‘自由之魅’的意欲——解放要求他们有所作为,他们便投身于公共事业之中,在此,不管是有意或更经常是不经意地,他们开始建构呈现的空间了,于是自由得以展现它的魅力,得以成为眼见为实的东西”[4]22。而这种特征,也使得美国革命截然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和叛乱,因为这些政治事件至多只是政权或王朝的更替,因此,革命这个源于天文学的现代政治观念,最初的意思是恢复到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但是后来革命者意识到,复辟是不可能的,于是革命获得了新的意义,创立全新的政治体系以自由立国成为革命的主要意涵。与法国革命重心迅即转向平等与幸福不同,“美国革命的方向始终是致力于以自由立国和建立持久制度,对于为此而行动的人来说,民法范围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许的”[4]78。不仅如此,美国人逐渐形成中的多元社会格局,使他们不会接受打着人民旗号而抹杀多样性的卢梭式的“公意”概念,“他们知道,共和国的公共领域是由平等者之间的意见交流所建构的,一旦所有平等者正好持相同的意见,从而使意见交流成为多余,公共领域就将彻底消失”。“这一核心理念就是以自由立国,也就是建立一个政治体,保护自由得以呈现的空间”[4]124。若公共领域不复存在,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也就缩水为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
这样,美国革命可以被看成从解放到自由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独立战争为标志,主要是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权,为自由创造前提条件;第二阶段,则是以费城制宪为标志,建立一个宪政架构,为自由提供制度保障。但是,阿伦特对宪政的理解显然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在她看来,美国革命给后人的独特的意义就在于它在制宪建国时期摒弃了传统的有关革命的专断与暴力的观念,“这场革命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经过共同协商、依靠相互誓愿的力量而缔造的。奠基不是靠建筑师一人之力,而是多数之合力”[4]200。阿伦特尤其看重美国革命第二阶段中所承袭的罗马时代的共和政治传统。罗马的丰功伟业给予美国建国者以巨大启示,“他们将自己想成是立国者,因为他们有意模仿罗马的榜样,效仿罗马的精神”[4]188。而罗马传统给美国建国者的深刻影响,不仅体现在美国首都恢弘的罗马式的政治建筑物,而且更体现在美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创新性的政治行动,从大陆会议到制宪会议,从《独立宣言》到《联邦宪法》,其中所呈现的革命特质都最大程度地彰显了阿伦特所理解的共和主义的政治理念。尤其是费城制宪进程中,即围绕政体安排进行的广泛性的政治辩论而非暴力的专断,既体现了公民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而且也展现了罗马式的共和政治的本质。
不过,阿伦特对美国革命也并非完全的溢美之词,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制宪进程尽管有广泛的政治参与,但是主导这一进程实质上是思想保守的汉密尔顿等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眼里,最要紧的是结束独立后的主权困局,建立一个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亦即消极自由的宪政体制,而并非公民广泛的政治自由。主张扩大政治参与的杰弗逊在法国出任大使,而反联邦党人其他领袖又缺乏足够的政治影响力,于是作为共和国单元的为公民参与政治事务提供公共空间的地方性的市镇会议并未纳入到联邦宪法的政治体系中。虽然代议制与分权的政府机器将美国从杰弗逊担心的危险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一机器无法将人们从公共事务的麻木和冷漠中解脱出来,因为联邦宪法本身只为人民代表提供公共空间,而并未为人民提供一个这样的空间”[4]224。尽管后来联邦宪法通过了权利法案,作为对反联邦党人政治主张的某种回应,但是权利法案本质上与法国革命中的人权法案一样,都是着眼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其重心并不在保护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自由,在阿伦特看来,尽管有限政府和权利法案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必须牢记,暴政和有限政府之间的距离,就像有限政府与自由的距离一样大,也许还要大些。但是,这些顾虑不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我们都没有理由将公民的权利误当作政治自由,将文明政府的前奏等同于自由共和国的实质。因为,政治自由一般而言,意味着成为一名政府参与者的权利,否则什么也不是”[4]218。阿伦特不无遗憾地指出,“正是联邦宪法本身这一美国人民的最伟大的成就,最终骗走了他们最骄傲的财产”[4]224。因此,美国革命虽然未吞噬自己的孩子,但是革命后的宪法,却在一定意义上为将广泛的公共参与这一美国革命最为重要的珍宝给失落了。美国的庆幸之处在于,尽管联邦宪法未明确将基层地方的市镇会议等纳入其中予以考虑,但是自五月花号缔约以来所形成的悠久的地方自治和结社传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美国地方政治、公共政治生活的活跃,从而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忧的民主的蜕变。
20世纪90年代初当冷战戛然而止时,以福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曾经乐观地宣布,历史行将终结于自由主义的市场民主体制。但是,当我们进入新世纪时却突然发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对于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而言依旧遥远,即便在有着悠久自由传统的西方也是如此。自由既未实现,那么革命就难以彻底告别。阿伦特的共和主义自由观,承袭了古典希腊罗马的政治传统,将人的价值彰显与公共领域的生活联系起来,从而使其自由观超越了自由主义推崇的消极自由,自由不再仅仅是与解放相联系的特定的法律和政治事件,也不仅仅是被有限政府保护由人权法案所规范的个人权利,而且还应该是公民在公共领域中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自由还应该是公民的积极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来理解自由,革命才不会偏离其宗旨,才能避免革命后的民主体制堕落为多数暴政。在贡斯当、伯林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那里,个人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而在阿伦特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这里,政治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政治自由的实现程度,不仅直接关系者个人自由的实现程度,而且也事关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生命意义的实现与否,自由不能止于解放。阿伦特的自由观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她奠定了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而且为我们重新透视近现代革命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叙事。对于缺乏自由传统的中国而言,20世纪的政治史更是动辄以解放替代自由,由此留下的教训也如法国大革命一样深刻,人类若要走出革命越来越激烈、自由越来越稀少的政治怪圈,阿伦特的共和主义自由观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政治反思的理论视角。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70.
[2]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M].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
[3] David Hackett Fisher.Liberity and freedom[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7-9.
[4]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5]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6] 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92.
[7] 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M].刘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65.
[责任编辑 勇 慧]
D02
A
1009-3699(2016)05-0472-06
2016-05-16
杨明佳,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