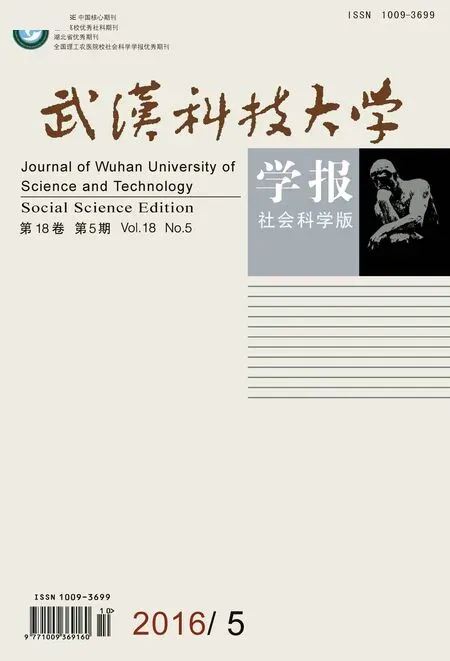民主转型中族际冲突的政治制度原因探析
丁岭杰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贵州贵阳550028)
民主转型中族际冲突的政治制度原因探析
丁岭杰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贵州贵阳550028)
很多多民族国家在经历民主转型后不但没有迎来民族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国家主权的稳固,反而承受长期的族际冲突和政治体系动荡。有三大政治制度原因值得关注:一是投票竞选导向的转型模式易带来族际政治不公,二是民主转型中不平衡的权利配置恶化民族矛盾,三是民主转型中权利(力)规制机制缺陷干扰权利保障,因此,新兴民主国家需要促成政治参与自由化、议会构成公平化、多元权利(力)协调体系权威化以及民族冲突治理机制高效化,最后实现政治发展沿着民族的国家认同强化、民主法治发展和主权稳固的方向进行,而不是向威权政体倒退,以不公正的民族压制来解决民族冲突。
民主转型;族际冲突;族际政治;政治制度;民族矛盾;权利保障;权利协调
20世纪70年代“康乃馨革命”终结了葡萄牙的威权政体,此后,各国民主转型加速并汇合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进而剧烈而深远地影响着世界政治制度地图的变化和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近年来,中东阿拉伯地区的威权体制分崩离析或虚弱不堪,这种政治转型趋势似乎为民主化浪潮注入了新的动力和发展前景。自信满满的民主转型支持者更加乐观地盼望托克维尔两百多年前作出的民主转型预言的实现:即便是阻挠民主实现的力量也在推动民主的前进,在日渐孱弱的敌人面前民主正在大步向前,势不可挡[1]。然而,这次民主转型却面临着巨大的险滩暗流,戴尔蒙德认为在第三波的后期,民主转型和新兴民主制度变得日益空虚[2]403-407,特别是在族际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多民族国家中,旧体制解体和新制度的建立过程不但没有改善族际政治关系和巩固主权完整,反而导致民族冲突数量的激增和类型的升级,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和其中的政治制度原因便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
一、投票竞选导向的转型模式易带来族际政治不公
不同于城邦和城市中的古典民主,现代民主基本是在国土广阔、民族众多和文化多元的主权国家中构建、运行和发展,因此,在全国性立法决策和官员产生的政治领域内,公民基本无法通过轮流执政和随机抽签来直接地产生和执掌公共权力,而是主要通过举行投票竞选组织政治代理人、成立代议机构和进行政治表达等,定期和间接地影响全国政治体系的价值选择、政治结构的功能发挥、政治过程的运行和发展,从而实现主权被民众所拥有、公权力被官代理和公领域向公民开发等现代民主程序和过程。
从萨托利的自由宪政主义民主到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政体民主,再到亨廷顿的民主转型过程理论,代议制和自由竞选都是制度转型和民主建构的基本指标。虽然选举制和代议制是现代民主运行的必要制度和程序安排,然而它们并非现代民主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Terry L Karl等民主理论学者不断提醒理论家和政治家,单单以选举投票为根本导向的民主理论和政治转型策略很有可能偏离政治发展的自由、公平和安全等基本价值①,然而在不少的多民族国家中,掌控政治转型过程的政治精英仍将选举投票作为构建新兴民主制和政治参与路径的关键内容,这极有可能为少数的民族精英集权和多数民族的专断打开制度大门[3]。
首先,在强势民族具备人数优势的情形下助长多数人的政治专断。如若根据选票中简单多数的政治偏好来分配政治权力和政治产品,那么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且组织整合程度低的弱势民族则会在政治过程中被长期地边缘化,甚至是面临边缘地位制度化的风险,进而他们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议会和政府组建、立法和公共决策等政治过程中,难以通过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来合理有效地主张、整合和保护本民族的多元权利。如果依据不同民族的选票在总选票数中的比例来决定和协调政治资源分配,弱势的少数民族及其政党能获得进入全国性政治机构的更宽阔路径以及在立法决策上的更大政治权重,然而仍无法摆脱在全国性政治机构和政治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政治命运。
在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之前,1956~1989年苏丹曾建立起3次议会政体,然而被竞选和代议制所包装的拟态民主[2]407却未实现族际政治公正。阿拉伯民族主要聚居在苏丹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其民族精英惯常依托民族人口数量优势和经济政治资源优势,通过竞选投票把控全国性的政治权力,进而在将本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轨道上制定、调整和执行法律和公共政策[4]。
其次,在人口主要分布于两大民族且两大民族的政治经济权能大致相同的情形下恶化族际政治的周期性波动。当国民和选民基本被民族界限所分割时,政治精英联盟、政治性社会组织和政党等都具有显著的族际对立性并且主要通过明确族际界限、强化民族政治效忠和动员民族政治参与等来调动竞选资源以获取与分配政治权力。两大民族的政治精英借助民族性政党和投票竞选轮流执掌政权并在掌权时推行民族自利导向的利益整合和资源分配过程,进而在周期性的竞选和执政政党进退中导致与恶化族际政治的周期性波动。
乌克兰的政治体系和过程就具有明显的两大民族对立和族际政治周期波动特征。俄国在1667年控制乌克兰东部,并于1795和1920年扩张了俄国所掌控的乌克兰领土,但未全部控制乌克兰的西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才占领不含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国土的主体部分[5]。东西乌克兰在民族结构和社会文化上差别较大,西部乌克兰的主要民族是乌克兰族,且在长期受西欧自由文明和天主教的影响,而东部主要被东方专制传统和东正教文化塑造,此外,旨在消除乌克兰的离心力和巩固苏维埃联盟制度,前苏联当局还有计划地和长期地将俄罗斯族人移民入东部乌克兰并对乌克兰西部的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加以压制,这些无不导致和恶化乌克兰东西两大区域和俄乌民族的对立。国家重获独立后,乌克兰推行民主转型并构建起投票竞选和代议制度,但又步入周期性政治波动。库奇马以后的总统在执政上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地区和民族偏向,尤先科通过动员乌克兰族选民而在大选中获胜,执政后又以总统身份公开赞扬备受争议的民族历史人物,并积极谋划全国文化和官方语言的乌克兰民族化[6]。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将政治运行过程偏向于实现东部地区和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这一沿着两大民族政治断层而形成的周期性政治波动为当今乌克兰的族际对抗、地区对立和国家分裂蓄积起政治动力。
最后,在多元民族高度分化态势下导致少数者的专权。在民族和宗教种类多且分化程度高的国家中,政党和压力集团也在民族和宗教的多元断层上高度分化,它们主要基于民族身份和民族内的群体界限来动员相应选民和结成政治联盟,并且借助变动和微弱的民族选票优势来谋取议会席位和组阁权重。在某次大选中获胜的政党(或政党联盟)通常只赢得微弱多于其他民族党派的选票,而且获胜党派的选票数只占总选票数的很小比例,获胜的政党联盟也会因为联盟内部某些派别的分裂和退出而失去议会中多数议席并面临政治信任和公共决策的僵局。在多民族联邦制国家中,占议会多数席位的邦(州)民族政党或政治派别可能只获得选民众多州的相对多数选票,而该州和其他州的没投给获胜党(派别)的票数之总数大于获胜党(派别)的总得票数,这种竞选结果与民主的多数表决原则相龃龉,更有可能导致数量少而权能强的民族和地区的专权,此外,在这类国家中能超越族际界限和实现多元政治整合的全国性政党基本缺失并且发展缓慢,这一政治结构特征进一步阻碍族际关系和党政关系之间的边界维护和恶化两种关系的相互渗透干扰[7]。
萨达姆政权解构后,伊拉克逐步建立并运行区别于传统西方民主模式的“协和式民主”[8],以此保障阿拉伯民族中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以及库尔德民族能在全国性立法和行政机构中按照民族与国民人数比例公平地获得席位和职位并获得对重大公共决议的否决权[9]。协和式民主还基于民族联邦制保护各民族(特别是弱势民族)的民族自治权,然而,一方面伊拉克缺少超越民族界限的全国性强力政党和公民个体权利意识与体系,另一方面有实力的民族政党(联盟)都有明确的族际政治界线,而且其内部派别利益关系极为复杂,因此,在全国性议会和政府中民族党派对立严重并且阻碍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运行。从宏观政治过程和民族政治关系来看,只分散掌握少数选票和代表个别民族利益的政治势力,在议会和政府运行中利用手中制度化的否决权阻碍了多数选民的政治权益的保障和实现。
二、民主转型中不平衡的权利配置恶化民族矛盾
族际政治对抗治理和民族政治整合的关键在于民主转型过程和制度构建结果能保障和协调公民权利和民族权利。在政治认同和政治象征维度,个体化公民权超越民族认同的限制,在平等国民和主权国家之间构筑起直接的政治契约,培育和巩固各民族的个体成员对统一主权和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在政治生产维度,各民族的个体成员能依据公民权体系,自由地影响政治产品生产和公平地分配政治产品,最大限度地防范全国性和民族内部政治权力对基本人权的侵害。
公民权在横向的公共政治多领域交往中保障全体公民(包括民族个体成员)的个体权利,民族权利则是在纵向的公共政治历史性发展中维护各民族的集体权利。正视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族际政治不公,民族权利基于“矫正正义”原理,保证弱势民族在政治参与、传统保留和福利分配上能获得制度性优待,并通过赋予弱势民族更多的地区自治权和更高的议会决策(否决)权重,来防止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对弱势民族自主权的侵害,最终将族际关系公平化②。然而,由于超越民族属性的国家认同和权利意识的衡薄、民主转型中多元权利平衡制度的缺失以及族际历史政治问题等复杂原因,民族权和公民权以及不同主体的民族权之间就必然存有明显的张力。
明德学校以校费支绌,乃集该校职员,组织剧部,于孟冬下旬,假座画锦牌坊陈宅举行。但以前所演,皆国耻纪念、社会现行等事,处处以惊心动魄出之。此次竟拦入《化子拾金》一剧,徒沾沾于声调,无裨益于风化,致见轻识者,售券之数顿减。而后此新剧之杂然并奏者,实自此始。[2]51
一方面,民族权利行使侵害公民权保障。在族际互信资本稀薄和妥协意识淡薄的政治情境下,某些昔日弱势民族的议会代表,不顾全国性利益和公共德性滥用“自卫性”的议会否决权,通过制造政治僵局来抵制国家或其他民族对自己资源的合理开发,这一过程直接阻碍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能力对公共问题的处置,最终对普通的个体公民的权利构成普遍的侵害。此外,在民族权利范围模糊和多元权利协调机制不健全的政治环境中,自治权也会被特定的强势民族利用来限制和侵害自治地区内弱势个体的权利。
在伊拉克民主转型后,昔日遭受欺凌的库尔德民族在协和民主制下获得巨大的议会立法决策否决权和民族地区自治权。在议会决策的过程中,库尔德政治联盟多次否决可能会影响自己利益的全国石油发展计划,而且多个民族党派对否决权的普遍依赖也导致全国议会难以高效地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蔓延。在自治权的行使上,库尔德人在自己的自治地区内拥有独立于全国政治体系的军事和政治机构。库尔德民族自治权的民族政治独立化倾向大大增加了自治区内弱势的个体公民权利被库尔德民族政权侵害的风险,妨害全国性政治机构在自治区内救济人权和培育个体公民的国家认同,此外也增加了伊拉克新兴民主政体退化为国家整合效力和体系稳定性低下的民族寡头体系的可能。
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权之间存在冲突。当各个党派和政治联盟的边界同民族或民族分支的界线相重叠,竞选又成为影响公共权力的主要路径,而且多元权利平衡机制缺失时,全国性政治体系和族际政治互动过程就成为一种带有民族属性的“庇护政治”[10]。在民族性的“庇护政治”中,民族和政治精英基于民族身份标签组建政党和谋取政治结盟,在关键性的竞选中通过鼓动民族感情和操作民族政治议题来获取重要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并在民族断层上制定和执行法律与政策,不公正地袒护本民族的民族权和限制其他民族的民族权。在两个或多个民族势力均衡的国家中,民族之间的政治强弱之分是相对的,并且随着全国性竞选的波动而变动。当全国性政治沦为庇护政治时,在国家层面上民族权利受庇护关系侵害的民族会在下次全国性竞选获胜后调整全国性庇护政治关系以报复其他民族和维护本民族特权,或者会退回到自己的自治区以地区庇护政治维护自身特权和侵害自治区内相对弱小民族的民族权,并且以自治权来屏蔽全国性政治机构和外部力量对自治区内民族权利问题的治理。
在前南斯拉夫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克罗地亚逐步解构威权政体并有计划地积极争取民族独立。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民族,一方面公开支持克罗地亚的民主转型和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也明确要求作为多数民族的克罗地亚民族要公正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公民权和民族权利,然而,强势民族控制了新宪法的制定过程并将克罗地亚民族的多项特权写入新宪法,此外,在全国大选中获胜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政治精英还通过立法对塞尔维亚人的自治权加以剥夺,并利用行政手段来侵害他们公平地获得社会福利、自由地参与公共政治、平等地享有就业机会、充分地获得治安保障的各项权利。制度化的民族权利分配失衡和持续的民族权利冲突最终导致克罗地亚境内族际暴力对抗的扩大和升级[11]。
在民族冲突显著的乌克兰,持狭隘民族主义政治立场的尤先科借助“橙色革命”(选举体制外民族主义政治抗争)成为乌克兰总统,此后通过提倡国家语言的乌克兰语化、本国东正教的自主化、国家历史叙事对俄罗斯族的矮化等举措来主张保护乌克兰族的集体文化权和救济乌克兰族在历史上受到俄罗斯民族推行的文化和政治“迫害”,然而这些民族权保障举措却难免走向伤害国内俄罗斯族的集体感情和侵害相关文化政治权利的极端。尤先科的继任者亚努科维奇制定出一系列利好于俄罗斯民族的经济文化政策,这些政策名义上是谋求乌克兰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福利进步,然而在客观上却明显倾向于保护俄罗斯族的民族利益,侵害乌克兰族保留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保持自主政治地位的民族权利。民族权利边界的模糊化和权利冲突随竞选换届而变化的问题,导致两大民族在民族权保障上的负和博弈和族际政治互信与文化互容的流失,并成为民族对抗与民族分离的政治根源,最终削弱国家维护主权完整的能力。族际权利冲突也为俄罗斯利用政治军事手段干涉乌克兰内政提供民族主义借口——俄罗斯有义务保护乌克兰国内权利被当局侵害的俄罗斯民族同胞。
为了获得对石油资源更多的控制权,库尔德民族当局擅自将包括基尔库克在内的多个石油产地纳入自己的民族自治区域,而后有计划地将库尔德人移入这些地区,并逐步推行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同化政策[12]。迁徙的自由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保留本是重要的民族集体权利,然而在公共政治空间狭小和民族权益界限多变不定的环境下,库尔德当局利用地区性强权来挤占多民族共有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并限制其他民族的权利保障,则违背族际权利关系中的主体资格平等和利益分配公平的原则,直接导致库尔德控制地内弱势民族对库尔德人的所谓自治权、文化权以及资源控制权的反对。
三、民主转型中权利(力)规制机制缺陷干扰权利保障
乔万尼·萨托利依据权利(力)的行使路径将民主划分为横向民主和纵向民主[13]149-150。纵向民主的核心内涵是自下而上地产生公共权力和自上而下地实行权力,横向民主则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对权利的规范与协调。在横向民主框架下,宪法体系有效且公正地运行、多元政治社会主体平等自由地参与政治,能有效规范与制约公共权力和多元权利产生、运行和调整的价值、边界、机构和过程,保障政治产品供给对权利协调和救济的有效关切。发达的西方多民族国家大多能公正和平地治理民族冲突并维护主权完整,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它们构建起制度化水平高的权利(力)规制机制,以此来限制民族权的过度扩张和协调多元权利(力)的冲突。
然而其他的多民族国家在谋划和推进民主转型时,主要关注民主纵向维度的政治授权功能以及相关的投票竞选制度,而忽视民主横向维度上权利(力)规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这种政治转型策略往往产生一个功能残缺和体系脆弱的族性民主样态,其类似于奥唐奈阐发的委任制民主[2]53。在民族性委任制民主中,国家领导人(主要是总统)产生于较为自由但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的投票竞选,并借助自身非正式的政治势力和正式的制度获取集中且影响面广的权力。虽然宪法体系、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社会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约领导人权力,然而后者基本能在法律和制度的漏洞中通过修改宪法的授权条款和操纵议会中的重要政党(政治联盟)等,来扩张自己领导权边界、延长职位任期,进而制定强化与扩充特定民族群体权利(力)的法律和政策。民族性的委任制民主还具有寡头化的特征,某些较为强势的民族借助宪法规定的地区自治权将全国政治体系分解为多个自己控制的带有独立性的政治共同体,通过使用全国性议会中的否决权来保护自治区域在法理和现实中的独立性。自治领域的扩展、自治权造成的权利侵害、否决权的滥用难以被全国性立法和司法机构所制约。
为了扭转竞选的不利局面,尤先科动员起选举体制外民族主义政治抗争,以此改变亚努科维奇的选举结果,并且在执政后以带有民族利益偏向性的法律和政策来获取乌克兰民族选民对自己的支持。此外,很多届的乌克兰总统都企图借助修改不完备的宪法来扩张和强化自己总统职权,在2003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库奇马为了能获得总统连任就主张修改宪法,进而为自己能绕过全国普选并借助议会内的选举当选总统而构建法律基础和制度路径[15],此后,尤先科、亚努科维奇等总统都借助修改宪法中的总统任职条款或宪法法院的非公正的宪法审查裁决来削弱立法机关对总统职权的监督制约[16]。
伊拉克的协和民主呈现出民族主义寡头化的特征。宪法体系明确了各民族和民族的宗教分支在全国议会中的议席保留权、在全国性重大立法决策上的否决权以及民族聚居地中的自主权,然而宪法体系未能区别这些民族权同个体权利和国家政治体系统一性之间界限,也没能有效构建民族政治冲突治理体系和提升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因此,伊拉克难以在为多元民族权利(力)提供自由的制度空间的同时,进一步塑造和强化族际政治互信与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具体表现为,伊拉克高度多极分化的民族主义民主,不但难以治理库尔德人和阿拉伯民族各宗教分支的集体权利(力)行使过程导致的立法机关僵持、个体人权侵害和国家治理能力虚弱等问题,也难以通过全国性立法(包括修宪)、宪法的司法审查和全国性公投等民主法治手段来制约库尔德人谋求民族独立的政治行动,这一系列政治运行过程又进一步削弱民族、宗教派别和普通公民对国家主权和基本政治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认同。
四、结语
民主转型砸碎了禁锢各民族的政治牢笼并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天平,而此后民主巩固和发展要面临的最关键任务是基于多元权利(力)保障协调体系、族际冲突治理机制和族际信任协作机制等的构建,建立和维护民族团结、和谐统一的国家。面对政治转型释放出来的民族政治动员能量和初创民主制度的缺陷导致的族际冲突,新兴民主国家需要完成政治参与自由化、议会构成公平化、多元权利(力)协调体系权威化、民族冲突治理机制高效化,最后实现政治发展沿着民族的国家认同强化、民主法治发展和主权稳固的方向进行。总之,民主转型中的民族政治病变还需要以民主法治来医治,而新兴民主制在权利(力)协调上的虚弱无能和恶化族际不公,甚至向权威政体的倒退,这些都会加剧族际冲突并提升民族冲突转化为民族分离主义的风险。
注释:
①参见Terry Lynn Karl:Imposing Consent?Electoralism versus Democratization in El Salvador.in W.Paul Drake,Eduardo Silva:Elec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1980-1985(University of Califonia at SanDiego,1986,pp.9-36);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3页)。
②民族群体权利参见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个体人权和民族权利的冲突参见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
[2] 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3] Horowitz D L.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J]. Journal of Democracy,1993,4(4):18-38.
[4] Warburg Gabriel R.The Sharia in Sudan implementation and repercussions 1983-1989[J].Middle East Journal,1990,44(4):624-637.
[5] 金雁.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与独立后的转轨危机[J].浙江学刊,2005(6):64-70.
[6] 张弘.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6):1-9.
[7]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卢西恩·W·派伊,迈伦·韦纳,等.发展中地区的政治[M].任晓晋,储建国,宋腊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1-35.
[8] 阿伦·李帕特.多元社会的民主[M].张慧芝,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29-59.
[9] Brooking Institution.Iraq index:tracking reconstruction and security in post-Saddam Iraq[EB/OL].[2016-03-01]http://www.brookings.edu/iraqindex.
[10]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等译.北京:东方出版集团,2007:180-182,213-215.
[11]Rothstein B.Creating political legitimacy:electoral democracy versus quality of government[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9,53(3):311-330.
[12]Fainaru S,Shadid A.Kurdish officials sanction abductions in Kirkuk[EB/OL].[2015-04-05].http://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 2005/06/14/AR2005061401828.html.
[13]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9-150.
[14]孙卫华,刘彦龙.加拿大魁北克问题论析[J].世界民族,2004(1):9-21.
[15]姜长斌.化解危机:期待乌克兰民族政治智慧[EB/ OL].[2015-07-05].http://www.china.com.cn/ chinese/zhuanti/xxsb/721865.htm.
[16]乌总统尤先科提议进行宪法改革设立两院制议会[EB/OL].[2015-06-06].http://news.qq.com/a/ 20070628/003051.htm.
[责任编辑 周 莉]
D082
A
1009-3699(2016)05-0493-06
2016-06-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6XZZ009).
丁岭杰,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权保障与民主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