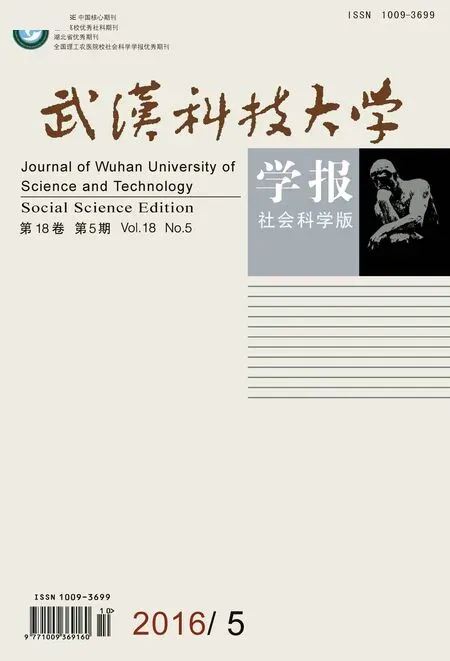企业为何需要责任型领导?——关于责任型领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周 勇
(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81)
企业为何需要责任型领导?——关于责任型领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周 勇
(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81)
责任型领导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型领导,为组织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相对于其他领导理论而言,目前国内关于责任型领导的研究及相关成果的介绍还不多,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对责任型领导的概念与测量、责任型领导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以及责任型领导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等方面进行了疏理和分析,最后,对责任型领导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责任型领导;利益相关者;伦理型领导;企业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众多类似于安然公司商业丑闻的出现,领导理论和实践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企业日益感受到履行社会责任的重大压力,企业领导者也逐渐认识到,要想获得企业的持续发展需要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处理好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1];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变革型领导等已经难以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责任型领导理论研究应运而生。责任型领导不仅将诚信道德作为其重要的领导品质,而且还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其重要的领导理论,这就弥补了传统领导理论的不足[3];责任型领导的研究能够使领导者的个人素养得到提高,从而更好地指导领导实践[4];同时,责任型领导的深入探索可以将企业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有效地融入到组织的良性发展中,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5]。本文在回顾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介绍了责任型领导概念的内涵、维度、测量方法、影响因素等,最后,在分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二、责任型领导的概念与测量
(一)责任型领导的概念
心理学最早将责任型领导解释为各种情商的结合,这就意味着责任型领导要用情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来指导他们的领导实践[6]。针对安然、美国世界通信公司丑闻事件的发生,Seeger M W等从良好的道德氛围、有效的沟通、开放的问题三个角度分析了领导者应具备的责任原则,指明了责任型领导的三个基本维度[7]。在第65届世界管理学年会上,Pless N M等首次正式提出了责任型领导的概念,他们认为责任型领导要规避各种丑闻,重塑商业信任,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可持续的信任关系[1]。随后,Maak T等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将责任型领导定义为一种发生在社会交互过程中的与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领导关系,这就将责任型领导的研究从传统的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二元关系转向了领导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元关系,他们指出责任型领导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为了更进一步深入理解责任型领导的概念,Maak T等引入了一个“责任型领导的角色模型”,帮助理解责任型领导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领导行为,该模型表明责任型领导应嵌入到利益相关者视角中,直接对客户、供应商、社区、政府等不同利益相关者负责[8]。在此基础上,2007年Pless N M重新定义了责任型领导的概念,他指出责任型领导是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并通过伦理原则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连接,旨在通过一个具有共享意义的目标来实现组织承诺创造社会的可持续价值[9]。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责任型领导的概念还未达成共识,但Pless N M的这个定义已被公众广泛认可。此外,中国学者宋继文等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将责任型领导的概念具体运用于领导实践中,指出责任型领导就是通过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与组织内外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达成互信、合作和稳定的互惠关系网,通过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建立社会资本,以共享的愿景和协调各方的责任型行为来实现商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各方的共同利益[10]。
(二)责任型领导的测量
迄今为止,由于学术界对责任型领导的概念和维度没有形成共识,所以有关责任型领导的测量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总体来看,有两种最主要的形式:一种是单一角度的测量,另一种是多元化角度的测量。
1.单一角度的测量
所谓单一角度是指测量者仅仅从责任型领导的概念出发,并未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早期对责任型领导测量的研究是从社会变革模型开始的,Dugan J P将社会变革模型运用于责任型领导量表的开发,他根据社会变革模型提出了一致性、忠诚性、目的性、合作性、竞争性、意识性、角色性和变化性等八个特征,将责任型领导的测量分为八个维度,并确定了68个题项。在美国西部的一所大学抽取100名本科生进行了相关测量,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结果显示这些题项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0.8~0.9之间[11]。陆扬华沿用Dugan J P等人的成果,从概念出发,将责任型领导划分为诚信道德、开放沟通、关怀指导、积极公民行为四个维度,形成了20个题项的量表。并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发放问卷166份,收回有效问卷128份,结果表明,量表的信度系数在0.85~0.95之间,完全符合测量的要求[12]。
2.多元化角度的测量
所谓多元化角度是指测量者不再局限于责任型领导概念本身,而是将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融入其中。Voegtlin C等将责任型领导的概念分化为几个部分,然后分别测量各个部分对整体概念的影响。具体来说,他们将责任型领导维度划分为三个部分:责任型领导的内涵,责任型领导与相关概念的区别,责任型领导与领导层次、不道德的行为以及员工满意度的关系。根据这三个部分,他们最先提出了21个题项,并在每个部分中都筛选出3~4个具有较强因子载荷的项目并将其表述规范化,同时,为了丰富测量的内容,还增加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题项,如“我的上级主管试图与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并对它的相关性和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研究还选取了瑞士公立大学139名学生进行测试,经过一系列的修改,最终形成了包含概念、区别、关系三个部分共14个题项的责任型领导量表(效度平均系数在0.8以上)[13-14]。验证结果表明责任型领导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与相关概念——变革型领导和伦理型领导也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总之,责任型领导的测量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外学者就责任型领导的维度尚未达成共识。量表数据来源并不具有普遍性,样本范围需要扩大,测量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科学地规范,这些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宽广的领域。
三、责任型领导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为了更深层次地理解责任型领导的概念,我们的视野要拓展到领导理论中其他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诸如伦理型领导、服务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变革型领导等,通过比较帮助我们多方位多角度地认识和理解责任型领导。
(一)伦理型领导
伦理型领导被认为是一个个体层面的领导现象[15],它通过双向沟通、强化、决策等一系列方法来促使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行为合乎道德规范[16],伦理型领导的目的就是通过伦理行为来影响追随者的行为。责任型领导的概念延续了伦理型领导概念中的道德标准,并强调领导者要作为一个积极的榜样用道德原则来作出领导决策[17],亦即高标准的道德要求被应用到领导者的决策实践中。但是,伦理型领导不等同于责任型领导,首先,伦理型领导仅局限于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二元关系,而责任型领导的研究视角超越了伦理型领导,强调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其次,伦理型领导试图预测单一结果,如领导效率、员工工作满意度、忠诚度,而责任型领导从微观视角出发专注于多层次的结果,旨在动员组织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责任型领导的实践,推动社会的可持续性变化,并将愿景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导因素[15];再次,伦理型领导关注的是文化因素,比如道德文化等,而责任型领导关注的是人文因素,比如人的价值取向等[18]。
(二)服务型领导
服务型领导也是一个个体层面的现象,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服务者或者领导者的追随者。因此,服务型领导是受他人支配的,而不是受控于领导者自身[19]。服务型领导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个性化的、以自我为中心形式的领导是相对的,它与那些只关注自身利益忽视追随者利益的领导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责任型领导和服务型领导都关注追随者的利益,它们都认为领导者和追随者在实现组织目标时都应该有一个更高水平的动机和道德标准。尽管责任型领导和服务型领导都超越了自身的利益,但责任型领导并不提倡牺牲自我的利益,它主张追随者的利益和自我利益的保护要齐头并进,服务是实现组织目标和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纽带,因此,责任型领导关心的是把别人的服务有效地运用到组织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去,这个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帮助他人成为有效的领导,更要满足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此外,责任型领导对利益相关者的追随者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服务型领导中所指的工作场所的追随者,还包括组织外部的追随者。责任型领导的内在驱动力是通过精神、人文、道德或其他植根于宗教、家庭、传统、教育等因素表现出来的,而这些因素是被服务型领导忽略的,这也是责任型领导与服务型领导的最大区别。
(三)真实型领导
早期对真实型领导的研究更多关注不真实的领导,缺乏对真实型领导的探索,目前的研究则更关注积极的结果和真实性的角色在真实型领导中的作用[20]。Bruce J Avolio将真实型领导定义为“一个来自于积极的心理能力和高度发达的组织环境的真实领导过程”[21]。尽管真实型领导的概念是一个多级构造,但它主要集中在个体水平过程上,个体的自我意识、自我调节过程对形成积极的心理状态有重要的作用,并能够促使真实型领导激发、影响其追随者,这是基于真实型领导将获得下属的信任、忠诚从而提高领导有效性的假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文因素(如文化、氛围等)都被认为是真实型领导作用的结果。Cooper C D等认为要将道德品质这一元素融入真实型领导中,并把道德作为真实领导力的一部分[22]。在他们看来,道德品质比如道德能力、勇气等都可以作为积极的心理资源,以提高领导效率。责任型领导与真实型领导在自我意识、自我调节的过程上是相似的,但责任型领导更强调领导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开发他人的情感和价值观,并规范他们的价值观评价标准。此外,责任型领导也要求用道德来规范领导行为,与真实型领导不同的是,责任型领导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品质的开发,它还将道德反思、用道德想象力应对困境作出决策的能力作为责任型领导的重要特征[23]。虽然真实型领导和责任型领导都会影响组织发展,但结果却大不相同,Bruce J Avolio等认为真实型领导可以通过积极的影响帮助人们找到工作的意义,促使企业持续发展,进而创造股东的长期价值[24];责任型领导虽然也重视积极的结果,但它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变量,把领导的作用范围扩展到了创造社会资本价值、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最终引起社会变革[5]。
(四)变革型领导
变革型领导概念最早被引入政治学领域,随后被进一步发展和概念化。作为一个个体层面的现象,变革型领导需要一个过程来构建组织承诺,赋予追随者一定的权力来完成组织目标。从激励、人文关怀等角度来看,责任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具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第一,在对追随者的定义上,变革型领导的追随者不涉及利益相关者,而责任型领导将追随者的定义扩展到组织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第二,关于领导的重点方面,变革型领导旨在通过影响追随者、改善领导力来实现组织目标,而责任型领导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定位于一个更高的组织目标,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组织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即责任型领导将变革型领导关注的股东利益转向公众的利益;第三,变革型领导强调具有领袖魅力,属于领袖魅力型领导,而责任型领导是根据包容、协作的原则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的关系型领导,它更加注重领导者在处理不同利益关系时的责任和角色,较少关注个人特征,不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主义;第四,变革型领导认为领导者的道德行为取决于他们的动机,只有真实、变革型的领导才有资格作为道德领袖[25],责任型领导构成一种固有的伦理现象,它侧重于强调责任型领导必须是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使用道德和原则决策时顾及他人的利益,同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追求道德和合法的目的;第五,变革型领导和责任型领导都包括观念的转化,但是责任型领导强调通过观念的变化来实现更高的社会目标[26]。
四、责任型领导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
(一)影响因素
关于责任型领导的影响因素,即责任型领导的前因变量,现有文献缺乏深入的探索,少数文献从领导者的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领导者个人因素
现有研究中涉及到的领导者个人因素包括性别、个性特征以及价值观,其中性别对责任型领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领导风格上,但是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并未达成一致。Eagly A H通过研究发现女性在领导过程中更加注重民主,更倾向于建立强大的关系网络,更容易表现出责任型领导的行为;而男性则更加偏向于任务导向型的领导风格[27]。但Dugan J P研究发现,对于责任型领导来说,男女领导者在领导风格上并无显著差异,个性特征的影响表现在道德层面的责任心上[11]。Annebel H B De Hoogh研究发现,责任心对责任型领导的影响是呈正相关的,责任心越强的领导者表现出更多的责任行为[28]。Ketola T研究表明,价值观也会对责任型领导产生影响,价值观主要强调领导者要以身作则,为企业和社会树立良好的榜样,正确的价值观会促使责任型领导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为企业和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2.情境因素
领导权变理论指出领导者所处的情境对其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组织文化氛围与区域文化方面。组织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责任型领导的行为,良好的组织氛围更有利于领导者作出正确的决策。具体而言,组织氛围的营造主要包括沟通和公民行为两个方面。沟通可以使领导者及时了解下属的动态,听取不同的意见,减少冲突,作出符合员工需求的决策;公民行为则表现为“我可以为他人做什么”“哪些行为对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些都有利于组织形成良好的氛围,促使领导者表现出责任型领导行为[11]。地域文化的差异是影响责任型领导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Dugan J P等从文化的可复制性角度出发,探索了美国和墨西哥文化差异对领导者需求的差异[30]。具体来说,墨西哥的本土文化强调高度集体主义、团队精神、人文关怀等,它要求领导者建立互惠的公共关系、关心公共利益;而美国文化则表现出激烈的竞争、注重个人成就和自我价值观,个人主义比较明显,忽视了人际关系和公共利益。墨西哥的文化偏好更符合责任型领导的特征,更能促使责任型领导的产生。
总之,领导者个人因素中的价值观对责任型领导的形成具有较为突出的影响,性别和个性特征的影响并不明显。组织氛围成为影响责任型领导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与此同时,地域文化在责任型领导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关于责任型领导形成因素的研究还不多,研究的范围也不够集中,大多是描述性研究,实证研究还不够丰富,而且现有研究只是对某些因素进行了论证,大多数研究只是从个人、组织、社会等单一角度出发来探索责任型领导的形成,并未深入验证多个层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二)影响效应
责任型领导的影响效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探讨责任型领导对组织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探讨责任型领导对员工的影响。
1.组织层面的影响效应
组织层面的影响效应,一是通过与企业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体现出来,二是通过企业的组织文化和绩效表现出来。
从与企业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来说,责任型领导通过维护组织的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积极的关系来巩固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而提高组织的经济效益[13]。首先,责任型领导可以作为组织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石,通过沟通参与帮助组织解决商业冲突,使组织作出合理的决策,从而有利于维护组织的安全性与合法性[31]。其次,责任型领导通过正确决策的影响力,与利益相关者积极开展对话,营造开放的沟通氛围,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组织的决策,使决策更加透明化,平衡各方的利益,从而使他们接受互惠互利的解决方案,最终可以促使责任型领导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持久的信任关系[32]。第三,责任型领导注重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有助于组织社会资本的构建,促进组织正式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的构建,帮助组织不断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组织效益[5]。宋继文等通过案例研究表明,责任型领导可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积极主动地履行各种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互惠、互信的关系网络,形成社会资本,以促进企业利润的提高[10]。
从企业的组织文化和绩效表现来说,责任型领导通过影响企业的伦理道德文化,让企业感知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提高组织绩效。首先,伦理道德文化是指可以引导和塑造人们行为的一种组织文化[33]。陆扬华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责任型领导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道德文化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12]。责任型领导将道德作为衡量领导者素养的一个重要标准,有助于企业的行为符合道德要求,可以逐渐影响组织的道德文化,帮助企业建立共享的价值观。其次,责任型伦理文化的形成可以使企业员工认识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积极地参与其中。再次,责任型领导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后会促使更多的公益行为出现,从而在社会上涌现出更多的社会型企业家,为社会做出有利的贡献,进而推动社会变革[34]。最后,责任型领导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促进组织绩效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责任型领导被看作是一个带动员工共同完成组织目标提高组织绩效的过程。Szekely F等对德国20家大型公司的研究证实,责任型领导可以有效地平衡社会、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进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35]。
2.员工层面的影响效应
责任型领导会影响追随者的态度和认知,主要包括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和动机等。领导者在组织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他们的行为往往会成为追随者的榜样,因此,角色模型在帮助追随着学习和加强他们的学习中显得尤为重要[16]。责任型领导对追随者的态度和认知具有双重影响:首先是对态度的影响,责任型领导通过榜样作用积极地影响追随者的态度,进而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如果追随者看到他们的领导者在经营过程中寻求平衡的理想的决策,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领导是一个具有积极处事态度的责任型领导,他们就会不断地学习领导者的态度和行为[36]。其次,责任型领导在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时也会鼓励追随者积极参与,其参与的程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同时,如果他们提供的建议被采纳,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重视了,进而增强其工作动机,进一步提高对工作和企业的认知与认同。Doh J P等对印度28家大型公司中的4325名员工的研究显示,责任型领导可以增强员工的自豪感和工作满意度,责任型领导的行为会成为员工的榜样,会增加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从而降低员工的离职率[37]。
综上所述,责任型领导影响效应的研究主要以案例和描述性的研究为主,也有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主要集中于责任型领导对组织和个人的直接影响方面。由于责任型领导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较为复杂,其影响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引入一些中间变量(如组织认同、组织承诺)来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五、责任型领导未来研究展望
责任型领导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主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责任型领导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基于对前述国内外文献的回顾,未来该领域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规范的角度看,责任型领导的概念需要统一。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关于责任型领导的概念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统一责任型领导的概念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要找到多个相关理论的结合点(比如利益相关者理论、股东理论等);二是要意识到价值观的强大推动作用;三是要与其他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区别(比如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伦理型领导等)[38]。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综合考虑以上三点,厘清责任型领导的概念,使其既完整又能被公众普遍认可。
第二,责任型领导的负面影响研究。关于责任型领导对企业的影响,现有的研究结果大多都是对企业绩效、个人的正面影响。一般的研究都认为,一方面,责任型领导可以正确处理社会、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另一方面,责任型领导也会通过自己的行为为其追随者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促使更多的责任行为产生。然而,责任型领导并不一定是有效的领导,其对企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35],它在提高领导者个人素质、促进更多社会责任行为、提高企业绩效的同时也会产生其他的负面影响,如过度强调领导者的作用可能会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导致下属对领导者的严重依赖,进而可能诱发下属对领导者的盲目崇拜,这都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探索责任型领导的负面影响,并提出积极的改进措施,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人力资源与责任型领导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利益相关者对责任型领导的影响,忽视了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及实践对责任型领导的贡献,忽视了人力资源管理及实践在责任型领导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39]。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积极配合责任型领导部署工作,可以帮助责任型领导处理好与下属的关系。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可以通过积极的社会责任实践来提高员工的社会责任感,产生更多的责任行为。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对责任型领导的贡献通过何种形式表现出来,人力资源管理及实践如何支持员工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协调员工与责任型领导之间的关系,责任型领导应如何充分利用本组织的人力资源优势巩固社会资本等,这些都是企业发展的困惑,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该加强对人力资源与责任型领导之间关系的探索。
第四,从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探讨责任型领导的效能机制方面较充分,但是对责任型领导形成的前因及形成机制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对责任型领导前因变量的深入探索,有利于提高企业领导者的领导素养,形成企业的责任型领导力,对企业的相关实践形成有效指导,从而推动企业组织的持续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同级领导者与下属是否在责任型领导形成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同级领导者的行为是否会影响责任型领导的领导行为,下属的人格类型和情绪是否会影响对责任型领导的认知,上下属关系、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责任型领导的形成等。同时,还可以探索文化差异中的权力距离是否会影响责任型领导的形成,如果权力距离会影响责任型领导的形成,那么该如何抵消这种权力距离的影响[30]。
第五,如何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多层面责任型领导模型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责任型领导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多角化视角,这里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还包括外部利益相关者。但是多层面的责任型领导模型所包括的多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它们之间是如何交互影响的,其影响机制如何也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此外,以往有关责任型领导的研究主要探索的是责任型领导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并未涉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多少的重要标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领导者的责任行为,责任型领导者的责任意识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进而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40]。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责任型领导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还可以通过引入一些中间变量(如组织文化、组织学习)来更深层次地探索责任型领导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机制。
致谢:感谢湖北广电网络武汉公司的陈柳青先生在资料查阅与整理方面的支持。
[1] Pless Nicola,Maak Thomas.Rel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leading responsibility in a connected world[C]∥K M Weaver.Best Paper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Honolulu Hi,2005:11-16.
[2] Waldman D A,Siegel D.Defining the socially responsible leader[J].Leadership Quarterly,2008,19(1):117-131.
[3] Karp T.Socially responsible leadership[J].Foresight,2013,5(2):15-23.
[4] Waldman D A,Galvin B M.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J].Organizational Dynamics,2008,37(4):327-341.
[5] Maak T.Responsible leadership,stakeholder engagement,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7,74(4):329-343.
[6] Mayer J D,Dipaolo M,Salovey P.Perceiving affective content in ambiguous visual stimuli:a componen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90,54(3-4):772-781.
[7] Seeger M W,Ulmer R R.Explaining Enron:communication and responsible leadership[J].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3,17(1):58-84.
[8] Maak T,Pless N M.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 a stakeholder society:A rela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6,66(1):99-115.
[9] Pless N M.Understanding responsible leadership:Role identity and motivational driver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7,74(4):437-456.
[10]宋继文,孙志强,蔚剑枫.责任型领导与企业社会资本建立:怡海公司案例研究[J].管理学报,2009,6(7):988-994.
[11]Dugan J P.Involvement and leadership: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leadership[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2006,47(3):335-343.
[12]陆扬华.责任型领导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D].杭州:浙江大学,2012.
[13]Voegtlin C,Patzer M,Scherer A G.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 global business:a new approach to leadership and its multi-level outcome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105(1):1-16.
[14]Voegtlin C.Development of a scale measuring discursive responsible leadership[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98(1):57-73.
[15]Brown M E,Trevio L K.Ethical leadership: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J].Leadership Quarterly,2006,17(6):595-616.
[16]Brown M E,Trevio L K,Harrison D A.Ethical leadership:a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5,97(2):117-134.
[18]Maak T,Pless N M.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 a globlized world:a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C]// Andreas Georg Scherer,Guido palazzo.Handbook of Research on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ship. 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8:430-453.
[19]Russell R F,Patterson K,Stone A G.Transformational versus servant leadership:a difference in leader focus[J].Leadership&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2004,25(4):349-361.
[20]Kim SCameron,Jane Dutton,Robert E Quinn.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foundations of a new discipline[M].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2003:3-13.
[21]Bruce J Avolio.Examining the full range model of leadership:looking back to transform forward[C]// David V Day,Stephen J Zaccaro,Stanley M Halpin.Leadership development for transforming organizations:Grow leaders for tomorrow.Mahwah:Psychology Press,2003:71-98.
[22]Cooper C D,Scandura T A,Schriesheim C A.Looking forward but learning from our past:potential challenges to developing authentic leadership theory and authentic leaders[J].Leadership Quarterly, 2005,16(3):475-493.
[23]Donaldson T,Dunfee T W.When ethics travel: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global business ethic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9,41(4):45-63.
[24]Bruce J Avolio,Francis J Yammaarino.Transformational and charismatic leadership:the road ahead[M].Format Print:Hardback,2013:449.
[25]Bass B M.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s[M].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5:231-245.
[26]魏祥迁,马红宇,闫丽萍.责任型领导:全球化时代的新型领导理论[J].东岳论坛,2012,33(11),97-100.
[27]Eagly A H.On comparing women and men[J]. Feminism&Psychology,1994,4(4):513-522.
[28]Annebel H B De Hoogh,Deanne N Den Hartog. Ethical and despotic leadership,relationships with lead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top management team effectiveness and subordinates’optimism:a multimethod study[J].Leadership Quarterly,2008,19(3):297-311.
[29]Ketola T.Responsible leadership:building blocks of individual,organizational and societal behavior[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0,17(3):173-184.
[30]Dugan J P,Morosini A M R,Beazley M R.Cultural transferability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leadership: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2011,52(4):456-474.
[31]Palazzo G,Scherer A G.Corporate legitimacy as deliberation:a communicative framework[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6,66(1):71-88.
[32]Burke C S,Sims D E,Lazzara E H,Salas E.Trust in leadership:a multi-level review and integration[J].Leadership Quarterly,2007,18(6),606-632.[33]Schein E H.Culture:the missing concept in organization studi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2):229-240.
[34]Nicholls A,Cho A H.Social entrepreneurship:the structuration of a field[M]//Alex Nicholls.Social entrepreneurship:New Models of Sustainable Social Chan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99-118.
[35]Székely F,Knirsch M.Responsible leadership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metrics for sustainable performance[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5,23(6):628-647.
[36]Konovsky M A,Pugh S D.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social exchan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37(3):656-669.
[37]Doh J P,Stumpf S A,Tymon W G.Responsible leadership helps retain talent in India[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98(1):85-100.
[38]Waldman D A.Moving forward with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three caveats to guide theory and research[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 98(1Supplement):75-83.
[39]Gond J P,Igalens J,Swaen V,et al.The human resources contribution to responsible leadership:an exploration of the CSR-HR interfac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98(1):115-132.
[40]Waldman D A,Siegel D S,Javidan M.Components of CEO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6,43(8):1703-1725
[责任编辑 彭国庆]
C933
A
1009-3699(2016)05-0534-07
2016-04-2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4YJC630217).
周 勇,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和责任型领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