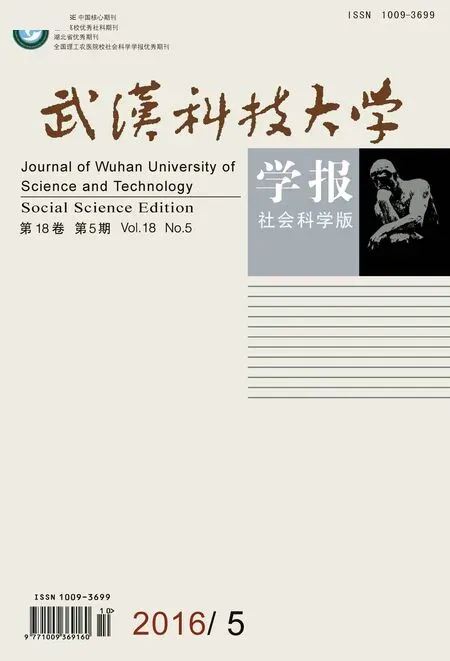中国通俗小说发生论
王齐洲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中国通俗小说发生论
王齐洲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中国通俗小说发生甚早,其成长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一现象不难理解,通俗小说属于民间文化系统,它从发生之始就受到限制,其成长空间被挤压,正统文人不予重视,相关记录少之又少,以至后人无法准确勾勒出它的完整面貌。从现存历史文献分析,我们大体可以确定,通俗小说滥觞于先秦的“稗官”,适应着当时的文化环境和言论制度,瞽矇、俳优是其主要作者,其基本语言形态是民间的偶语、谤言、谣谚、赋诵,或称“偶俗语”,主要供统治者调笑娱乐,也兼以了解民意民情,经过汉魏六朝的艰难成长,直到宋以后才形成一种成熟的文学文体。
中国通俗小说;发生;稗官;俳优;偶俗语
中国古代小说大体而言有两类,一类是著录于历代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子部古体小说①古体小说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鲁迅称之为“古小说”,著有《古小说钩沉》,今人程毅中著有《古小说简目》。此外,“子部小说”、“文言小说”、“笔记小说”等等,也是学人常用的称谓。中华书局则以“古体小说丛刊”出版这类小说的整理本,以与近体小说(白话通俗小说)相区别。本文即在此意义上采用古体小说的概念。,一类是不被正史所著录而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小说。前者在正统文化中地位虽然不高,却仍然是可以被接纳的对象;后者为正统文化所排斥,从来不入正统文人的法眼。尽管这两类小说互有影响,但它们的作者队伍、文本形态、读者对象、社会功用、文化地位、审美风格多有不同,需要分别加以探讨,不能混为一谈。然而,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有着共同的源头。本文探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生,便遵循着发生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妥之处,恳望批评。
一
提到中国通俗小说的发生,人们自然会想起鲁迅的名言:“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1]鲁迅所说的小说自然是包括通俗小说的,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通俗小说发生于先民休息时的讲故事。其实,这一说法只有理论意义并无实际意义。道理很简单,中国先民休息时会讲故事,西方先民休息时也会讲故事,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小说与西方的古代小说有很不相同的面貌呢?是二者先民所讲故事的方式不同造成的吗?然而,谁也没有听过他们所讲的故事,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讲故事,凭什么说小说是起于先民的讲故事呢?这种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的说法至多只是一种“假说”,存而不论可也。
正如人的童年对人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一样,中国通俗小说的发生对通俗小说后来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我们可以从成人的回忆中去了解他的童年,自然也可以从通俗小说发展成熟后人们对它的追溯中去了解中国通俗小说的发生。这也许是更为科学可靠的方法,探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关于通俗小说的发生,明、清学者一般都认为始于宋人的“说话”,有的明确指出应从南宋高宗做太上皇或从北宋仁宗时期算起。如署名绿天馆主人的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云: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翫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2]
冯氏在序言中明确区分了两类小说:一类是承诸子、史传而来的古体小说,起源甚早,《韩非子》、《列子》中有其最早的文本;一类是承说话艺术而来的通俗演义,起源于南宋初年的话本,其后发展成熟,《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平妖传》是其杰出代表。郎瑛则将通俗小说的起点定在了北宋仁宗朝,其《七修类稿》云:
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闾阎陶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过汴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时苏刻几十家小说者,乃文章家之一体,诗话、传记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说。[3]
而笑花主人(真实姓名不详)《今古奇观序》则云:
小说者,正史之馀也。《庄》、《列》所载化人、伛偻丈人等(原作昔,误)事,不列于史。《穆天子》、《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开元遗事》、《红线》、《无双》、《香丸》、《隐娘》诸传,《睽车》、《夷坚》各志,名为小说,而其文雅驯,闾阎罕能道之。优人黄繙绰、敬新磨等,搬演杂剧,隐讽时事,事属乌有。虽通于俗,其本不传。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4]
序言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小说:一类是文人之作,“其文雅驯,闾阎罕能道之”;一类是“说话人”所述,用白话讲“民间奇事”。这一区分是完全正确的,也与当时人看法一致。同时,序言还指出这两类小说有同一来源,所谓“小说者,正史之馀也”。认为小说为史之支流馀裔,这也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杨尔曾《东西两晋演义序》说:“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5]罗懋登《序西洋记通俗演义》称:“稗官野史谓何?此《西洋记》所由作。布帛菽粟谓何?此《西洋记》所由通俗演义。”[6]当时人不仅把文人创作的古体小说称为“稗官野史”,同样也把民间流行的通俗小说称为“稗官野史”,说明二者有更早的源头。即使从“说话人”的角度探讨通俗小说,也非起源于而是“盛行”于南宋高宗时期,因为“优人黄繙绰、敬新磨等”五代优伶也是其来源之一。这说明,明清学者已有人将通俗小说与优伶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即使是冯梦龙、郎瑛他们所说的小说起源于“说话”,其“说话人”的来源依然离不开优伶。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优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优伶的传统是十分深厚的,其源头远在先秦时期,并非始于五代。
其实,通俗小说一向被称为“稗官野史”,正透露出它与优伶的历史联系。探讨通俗小说的发生,正可以从讨论“稗官”和“优伶”开始。
二
“稗官”之称,始于秦汉,与小说有不解之缘。《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7]531,明确将“稗官”作为小说家之所从出。关于“稗官”,汉魏之际的如淳释云:“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唐颜师古则释云:“稗音稊稗之稗,不与锻排同也。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7]531如淳、颜师古均是著名学者,他们对“稗官”的解释,应该是有事实依据或文献依据的。然而,从先秦和两汉传世典籍中人们未能发现“稗官”一职,而《汉名臣奏》也已亡佚,颜师古引唐林语成为一条孤证,故有人断定所谓“稗官”只是刘、班等人受“学必出于王官”思想影响而作的附会,不可信从。近人余嘉锡“尝以经传所言官之职掌,考之九流所出之官而皆合”,于是明确提出:“如淳以‘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细碎之言’释稗官,是谓因其职在称说细碎之言,遂以名其官,不知唐林所言都官稗官,并是通称,实无此专官也。师古以稗官为小官,深合训诂。案《周礼》:‘宰夫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小官,士也。’此稗官即士之确证也。”[8]248余氏还将《左传》所云“士传言”和《周官》所载诵训、训方氏之职掌结合起来,并对《汉志》著录的小说家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稗官者天子之士也”;士的职责是“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也”[8]245-258。
“小说家出于稗官”说牵涉到对中国早期小说发生的认识,不可不细加辨明。音韵学家们早已指出,上古音同者义相通。如淳所云“稗音锻家排”,即是说“稗”读如“排”。“锻家排”指锻铁工匠的排风箱①《三国志·韩暨传》“冶作马排”裴松之注:“(排)蒲拜反,为排以吹炭”,可以为证。,如淳释“稗”音“排”,是汉魏读音,实兼释义。而颜师古则释云:“稗音稊稗之稗,不与锻排同也。”[7]531他认为“稗”不应该读如“排”(音pái);而应该读如“稗”(音bài)。其实,颜师古所读为隋唐音,而如淳所读为汉魏音。隋唐音是今音,汉魏音则是古音。颜氏以隋唐音否定汉魏音不仅违背了语音发展的历史实际,而且造成了后人理解上的障碍。今人的许多困惑,正是源于此。“稗”音“排”,“稗语”即“排语”,亦即“偶语”,所以如淳谓“今世亦谓偶语为稗”。何谓“偶语”?“偶”有对偶、排偶义,故偶语可释为对语或排语。不过,如淳所云“偶语”却并非此意,而是别有所指。《后汉书·蔡邕列传》载蔡邕上灵帝十事,中有“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9]977,如淳所云“偶语”即此“偶俗语”。梁钟嵘论魏文帝曹丕诗云:“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翫,始见其工矣。”[10]唐朱敬则《隋高祖论》亦云:“是以称刘季之灵怪者,不谋同词;说中兴之应谶者,往往偶语。”[11]均是此义。依此,则古人所谓“偶语”多指鄙俗怪异排偶之语,亦即蔡邕所云“有类俳优”的“偶俗语”。如淳云“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即是说,“稗”即“偶语”,亦即“排语”。至于“今世亦谓”云云,更是告诉我们,汉魏以前也将“偶语”叫做“稗语”,也可写做“排语”。
“稗语”、“排语”还可写作“俳语”、“诽语”,它们在上古音同义通。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指出:“古无轻唇音”,“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后世读轻唇音的非、敷、奉、微四母,在汉魏以前都读重唇音,轻唇音产生于六朝以后[12]。例如,古读“弗”如“不”、读“敷”如“布”或“铺”、读“方”如“旁”或“谤”、读“封”如“邦”,如此等等。“伏羲”亦作“庖牺”,“阿房宫”读如“阿旁宫”,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排”“诽”古音同声证据充分,而同韵也有迹可寻。从今音韵部的分合可逆推古音韵部分类的大致情况。在《广韵》206韵中,“灰”“咍”同用、“贿”“海”同用、“队”“代”同用,足以证明古韵“诽”“排”同韵。例如,南朝宋袁淑的《诽谐文》,在《隋书·经籍志》中著录为《诽谐文》,《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俳谐文》,《艺文类聚》卷91引作《徘谐记》、卷92引作《排谐集》。显然,“诽”与“排”“俳”“徘”均通。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云:“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范文澜注:“俳当作诽。放言曰谤,微言曰诽。内怨,即腹诽也。”[13]俳谐文本当作诽谐文,诽通俳、排,故“俳谐”“排谐”皆为“诽谐”,“排调”“俳调”亦即“诽调”。“诽语”“俳语”“排语”与“稗语”古音音同义通,毫无疑义。
“稗官”可释为“小官”,但并非指某一实际官职,而是指卿士之属官,或指县乡一级官员之属官。如秦简有“官啬夫免,效其官而有不备者,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14],“取传书乡部稗官”[15];汉简有“告官及归任行县道官者,若稗官有印者,听”,“都官之稗官及马苑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有秩毋乘车者,各百廿石”[16]。根据简书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得知,秦汉时期确有称为稗官者,而稗官并非指某一实际官职,而是指县乡一级官员的属官。稗官的职掌多为辅助性的,管理文书和收集闾巷传言是其职责的一部分[17]。简书所谓“乡部稗官”以及与“啬夫”并称之“稗官”,均指令、长和长吏以下之“小官”②《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至于“都官之稗官”,则指都官之属官,也称都官吏。《后汉书·符融列传》载:“符融字伟明,陈留浚仪人也。少为都官吏,耻之,委去。”[9]997此“都官吏”即简书所云“都官之稗官”,秩仅“百六十石”或“百石以下”,自是“小官”,符融耻做“都官之稗官”而离去,证明“稗官”在官场的地位确实很低。
按照如淳的理解,稗官就是向王者称说“街谈巷说”、“闾巷风俗”等“细碎之言”的官。这一解释显然符合《汉志》所云“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之义。当然也是符合西周传流下来的“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18]387-388的政治传统的。关于这一传统,还有类似的说法,如《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谏厉王云: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8]11-12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语与此略同。按照这些说法,古之王者为了政治的需要,曾实行过一套言论管理制度——“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除了听取公卿大夫对朝政的意见外,还安排一些官员收集“庶人传语”以体察民情,这些官员属于“士”这一阶层,亦即所谓“稗官”。
需要指出的是,今人多将“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理解为民间的一些琐屑的言论,而这一理解其实是不够准确的。王者所立稗官,不是为了让他们转述一些民间的琐屑言论,而是要他们收集民间对社会政治的反映,作为其了解民意民情的渠道。这里的关键是要对“街谈巷语,道听涂说”有正确的理解。那么,“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又何所指呢?《史记·周本纪》载邵公云“百工谏,庶人传语”,《集解》引韦昭曰:“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言,传以语士。”《正义》曰:“庶人微贱,见时得失,不得上言,乃在街巷相传语。”[19]19可见“街谈巷语”是指与朝政得失相关的庶人言论,非指一般的闲言碎语。《国语·晋语六》有“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战国策·齐策一》有“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诗经·大雅·板》有“先民有言,询于刍荛”,等等,依此,“道听涂说”也是指庶人的与朝政相关的谤誉之言。如淳所释“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显然并非凭空捏造,其实是指周代“士传言”制度在秦汉的延续。因此,余嘉锡所云“稗官者天子之士也”,是很有道理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士传言”之言论形态多为民间的偶语、谤言、谣谚、赋诵,因为这样的言论既便于口口相传,形成社会影响,也便于上达给统治者,好让史官记录。下举数例以明之:
(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20]2014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20]2063
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曰:“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国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既里、丕死,祸,公陨于韩。……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达於外。国人诵之曰:“贞之无报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贞为不听,信为不诚。国斯无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贞,大命其倾。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岁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18]303-305
以上事例都发生在春秋时期,著名的还有“宋城者讴”、“宋筑者讴”、“宋野人歌”、“鲁国人诵”、“洞庭童谣”、“汶山谣”以及“莱人歌”、“齐人歌”、“秦人谚”、“楚人谚”等,这些歌、诵、言、讴、谣、谚都是韵语,且多为排偶语。史官们记下这些排偶语,恐怕不是他们亲临现场采集所得,而是由生活在基层的“稗官”负责收集并报告而获得,这与传说的“春秋①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春秋”一作“暮春”、“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7]476的周代采诗、献诗制度有异曲同工之义。只是诗要配上音乐演奏,以便统治者“听政”即了解礼乐教化在各地实行的情况,往往在庄重场合使用,而这些排偶语只是随时赋诵,供王者“补察其政”而已,王者身边的“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正是这种制度安排。而“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诸侯、卿大夫们大概都有人为他们提供这些言论信息服务,他们也许不是这些歌、诵、言、讴、谣、谚的最初作者,但却是这些言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管理者和实际提供者,即由他们提供给王者“补察其政”。
唐人魏征显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他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以知地俗。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21]把小说与“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联系在一起,在制度上和采诗献诗等量齐观,确有历史眼光。而以小说内容即《周官》诵训、职方氏所掌的四方风俗、政事等,也不为无见。
然而,根据如淳注释和出土文献,我们的认识似还可深入。既然小说家所从出之“稗官”与其所用之“偶语”“排语”“诽语”有关,而“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的“箴、赋、诵、谏”又多是“偶语”“排语”“诽语”,那么,《汉志》所云稗官除包括《周官》诵训、职方氏等外,还应该包括“师、瞍、矇、百工”等,他们都是“圣人”(统治者)身边的乐官,也负有谏箴君王的责任。而进谏的“百工”中最为活跃的则是俳优。《国语·晋语》所载优施、《史记·滑稽列传》所载优孟、优旃等影响君主决策的故事,便是极好的例证。王国维的《优语录》、任二北的《优语集》便收集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冯沅君的《古优解》和《古优解补正》更有深入的讨论,证明古代俳优常常使用“偶语”(也称“排语”或“俳语”)“谐语”(也称“俳谐”)进谏君王。那么,俳优是否可以称为“稗官”呢?笔者以为完全可以。许慎《说文解字》曰:“官,史事君也。从宀从。犹众也。此与师同意。”[22]《国语·晋语八》云“固医官也”,韦昭注:“官,犹职也。”[18]435《周礼·掌讶》云“则戒官修委积”,郑玄注:“官,谓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属。”[23]《荀子·荣辱》云“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王先谦集解:“荀书每以官人百吏并言,犹《周官》所云府史胥徒之属耳。”[24]《周礼·天官》中便有膳夫、庖人、酒人、浆人等,《周礼·地官》中有牧人、牛人、舍人、仓人等,《周礼·春官》中有磬师、钟师、笙师、镈师等,《周礼·夏官》中有戎仆、齐仆、道仆、田仆等。一句话,在西周,凡服侍天子之人皆可以名官。因此,以俳语谀王谏王的俳优自然是可以称官的,只不过他们不是后代管理百姓的官。
这样看来,以“偶语”“排语”服侍君主的职官包括诵训、职方氏、师、瞍、矇、百工等,而俳优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各有分工,职责不同,官职不高,称名不一,故总称之为“稗官”。“稗官”之称可能与他们为王者提供排语、偶语服务有关。因为“偶语为稗”,“稗”音“排”,提供“排语”“偶语”服务的小官自然可以叫做“排官”,亦即“稗官”。而“俳优”之“俳”也与他们喜欢或善于使用“排语”有关,而“俳”与“排”上古本来音同义通。并且,这些“排语”与“诽语”“谤言”也有关联。《吕氏春秋·自知》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25]《史记·孝文本纪》云:“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19]47-48唐独孤及谓:“昔尧设谤木于五达之衢。”[26]诽谤之木的树立,无非是鼓励那些不能向统治者直接反映意见的庶人们可以通过一定渠道来道朝政之失、称执政之恶。《左传·襄公十四年》“庶人谤”杜预注:“庶人不与政,闻君过则诽谤。”孔颖达疏:“庶人卑贱,不与政教,闻君过失不得谏争,得在外诽谤之。谤,谓言其过失,使在上闻之而自改,亦是谏之类也。《昭四年传》‘郑人谤子产’,《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皆是言其实事,谓之为谤。但传闻之事,有实有虚,或有妄谤人者,今世遂以谤为诬类,是俗易而意异也。《周语》云‘庶人传语’,是庶人亦得传言以谏上也。此有‘士传言’,故别云‘庶人谤’为等差耳。”[20]1958由此看来,“谤”也是一种政治“谏”言,是庶人对统治者过失进行的公开批评。由于庶人的意见不能直陈统治者,故要通过“士传言”来实现。既称之为“诽谤”(注意:古语诽谤并非贬义词,孔颖达已经说明),其语言大概也是“排语”“偶语”,即所谓“偶俗语”,与上引郑国舆人在子产执政一年后的诵言相类似,而这些庶人所说的“偶俗语”正是这些“稗官”所管理的范围。当然,“稗官”的言论管理与服务既是一种政治服务、文化服务,也是一种生活服务,而这种服务是很容易转化为一种娱乐性服务的,这只要看看春秋、战国时期那些俳优们或类似俳优的滑稽家们在君王身边的所作所为,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奥秘了。
三
如果以上对“稗官”的探讨可以成立,那么,出于“稗官”的小说就十分丰富了。因为他们的身份和职掌是参差不齐的,提供给王者的“排语”“俳语”“偶语”“诽语”或称“偶俗语”也是各式各样的。史官有记载之责,其所述除朝政君国大事外,与政教相关的“街谈巷语”也在其记载的职责之内,成为官方文化的一部分。诵训、职方氏掌四方之遗事、古迹、方言、风俗等,必然采集有大量的神话、传说、逸闻、异事,《山海经》和《淮南子》中所记载的大量神话传说,恐怕都是他们所传留的文化成果,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黄帝战蚩尤”“刑天舞干戚”之类。到了汉代武帝时,方术大兴,许多逸闻异事、民间传说以及地理博物之知、巫医厌祝之术被方士们掌握,成为“秘书”,作为方士们干禄的工具。这些“秘书”后来多被《汉志》作为小说家的小说予以著录。其实,方士们的“秘书”尤其是其中的民间逸闻和神话传说是可以看作中国早期通俗小说的滥觞的。
先秦俳优们所演说的“俳语”“偶语”“偶俗语”被零星地记录下来,史书中也能发现他们的某些踪迹,虽然大都不被重视。真正受到关注的,往往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谏君主的那些俳语。如楚优孟谏楚王以大夫之礼葬马、谏楚王优待孙叔敖后代以及秦优旃谏秦始皇扩修苑囿、谏秦二世油漆长城之类。至于那些提供给王公贵族娱乐的“俳语”“偶语”“偶俗语”,史书一般不予记载,除非这些“俳语”“偶语”“偶俗语”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的确发挥了作用和影响,而且,即使发挥了作用和影响,其记载也语焉不详。当然,只要我们留心,仍然可以发现其蛛丝马迹。例如,《管子·四称》云:“昔者无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良臣不使,谗贼是舍……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於博塞,戏其工瞽,诛其良臣,敖其妇女,撩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无度,戏谑笑语……”[27]即使是有道之君,恐怕也免不了要以俳优为戏谑的。《韩非子·难三》载:“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对,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或曰:‘管仲之射隐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远,而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非其难者也。”[28]283-284《韩非子·难二》又载:“齐桓公之时,晋客至,有司请礼。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优笑曰:‘易哉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佚于使人。吾得仲父已难矣,得仲父之后,何为不易乎哉!’”[28]276-277看来,齐桓公身边的俳优确实不少,当然,俳优中也有不少人并不进行优谏,而是以俳谐取悦君王。《史记·滑稽列传》便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任二北在解释管仲对齐桓公问时指出:“优分谏、谀,所近者为谏优,与士同用,为治更非其难。”[29]这说明齐桓公身边有谏优和谀优两类俳优,当然也不排除一优而兼有两类角色。俳优虽有不同类型,但因其在帝王身边,都是有“官”的某些身份的,他们是“百工”之一,也可以说是“诸侯之士”。管仲所云“进其谀优”的“无道之君”在当时应该为数不少,像齐桓公这样的春秋霸主恐怕也难幸免。“近优而远士”也许是当时君王们的常态,不然,管仲也不会提出来讨论了。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先秦的一些俳优或类似于俳优的弄臣们的滑稽故事,为我们保存了中国早期通俗小说的重要资料。优孟、优旃是大家都熟悉的,这里不再赘述。而齐威王时期的淳于髡虽非俳优,却有类于俳优。请看下面的记载: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鞲鞠跽,待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19]348
这里记载的淳于髡的语言,多是“俳语”,或“偶俗语”,有优谏之风,其语言和行为确实“有类俳优”。齐王每次都问淳于髡是否“有说”,说明淳于髡所讲都是可以称为“说”的,当然只是“小说”。这些供君主开心娱乐的“戏谑笑语”或“小说”,连带这些引起人们阅读快感的故事,应该就是上古通俗小说的滥觞。
需要指出的是,俳优通过其特殊的语言和滑稽表演,进行讽谏或提供娱乐,丰富了统治者的文化生活。由于其“俳语”多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本质上带有民间文化的色彩,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源头。中国通俗小说和戏曲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滥觞。事实上,通俗小说和戏曲在中国古代长期被看作是一家,并不强行作出分别。宋、元“说话”中虽然有“小说”一家,但宋、元以后,以说唱艺术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小说”并非专指“说话”,它其实也可泛指一切说唱艺术。如明新安刻本《水浒传》所谓天都外臣序称:“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①所谓“天都外臣序”的题署其实并不可靠,此序落款因破损严重已无法识读,是由吴晓铃、戴望舒“籀读”(猜读)出来的。参见马幼垣《水浒二论》专论《问题重重的所谓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和简研《所谓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尚未发现第二套存本》,三联书店, 2007年版。明末通俗文学家凌濛初也说:“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30]他们所说的小说,其实就包括了所有说唱艺术,一直到20世纪初期,这一认识仍未改变。郑振铎曾不无感慨地说:“商务版的《小说丛考》和《小说考证》为最早的两部专著。但其中材料甚为凌杂。名为‘小说’,而所著录者乃大半为戏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出,方才廓清了一切谬误的见解,为中国小说的研究打定了最稳固的基础。”[31]尽管今人已经将二者作了区分,但探讨中国早期通俗小说的发生,却不能不指出小说和戏曲其实同出一源。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俳优的活动及其影响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渗透到民间,俳优们能够不断地从民间吸取营养。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晋杜预注:“优为俳优。”唐孔颖达疏:“优者,戏名也。《晋语》有优施,《史记·滑稽列传》有优孟、优旃,皆善为优戏,而以‘优’著名。史游《急就篇》云:‘倡优俳笑。’是‘优’‘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乐,戏为可笑之语,而令人之笑,是也。”[20]2000陈氏、鲍氏的圉人以装扮俳优取乐,说明当时俳优的“戏谑笑语”已经民间化。这些民间俳优的“戏谑笑语”虽然很少保存下来,但可以根据史书所记载的帝王们身边俳优的活动来推测这些“俳语”“偶俗语”的内容与形式。毫无疑问,无论是帝王身边的俳优,还是民间的俳优,他们的活动及其“作品”是先秦通俗小说的滥觞,这是可以肯定的。
这样看来,由作为“稗官”之一的俳优的说唱伎艺发展演变而来的“通俗小说”,是与“王官之学”发展演变而来的经纬之学、史传之学、诸子之学不同的文化形态,它来源于民间,使用“偶俗语”,主要供统治者调笑娱乐,也兼以了解民意民情。唐宋以后,这种“小说”发展成为民间“说话”,成为一种有着新的小说观念、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表达方式的新文体。它的主要阅读对象不是士大夫,而是市井细民,正如说唱艺术主要面向市井细民一样,其文字也主要不用文言,而用白话或浅近文言,与正统古体小说在形式上迥然有别,其作品并不用来说理,而是用来娱情,与古体小说追求学术价值也大不相同。总之,它是服务于普通民众的以通俗和娱情作为艺术追求的一种新兴文体,当然,那已经是它的成熟形态了。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270.
[2] 冯梦龙.古今小说:卷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
[3] 郎瑛.七修类稿:卷22[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229.
[4]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M]//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792-793.
[5] 杨尔曾.东西两晋演义序[M]//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939.
[6] 罗懋登.序西洋记通俗演义[M]//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009.
[7] 班固.汉书:卷30[M].《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8] 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M].长沙:岳麓书社, 1997.
[9] 范晔.后汉书:卷90下[M].《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10]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卷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1-32.
[11]李昉,徐铉,宋白,等.文苑英华:卷753[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6:3941.
[12]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25.
[1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72.
[1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1.
[15]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23.
[1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66.
[17]王齐洲,屈红梅.汉人小说观念探赜[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4):109-120.
[18]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9]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张守节正义.史记[M].《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0]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21]魏征.隋书:卷33[M].北京:中华书局,1997:3373.[22]许慎.说文解字[M].长沙:岳麓书社,2006:304.
[23]郑玄注,孔颖达疏.周礼注疏:卷38[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902.
[24]王先谦.荀子集解: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88:37.
[25]吕不韦著,高诱注.吕氏春秋:卷24[M].《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310.
[26]宋祁,欧阳修,范镇,等.新唐书:卷162[M].《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4652.
[27]戴望.管子校正:卷11[M].《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8:183.
[2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16[M].《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
[29]任二北.优语集·总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3.
[30]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M]//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785.
[31]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34-435.
[责任编辑 彭国庆]
I207.41
A
1009-3699(2016)05-0568-08
2016-06-1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1AZD062).
王齐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