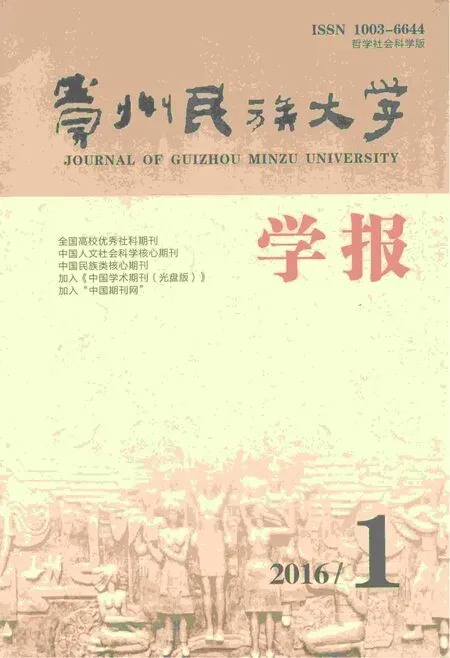东部方言苗族之巫分类说明
麻 勇 斌
东部方言苗族之巫分类说明
麻 勇 斌
苗族之巫是最具神圣性的古老文化之一,对其进行分类说明,是对其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工作。民间和专家学者已然形成的分类,均存在缺陷与不足。本文依据民间形成的关于苗族之巫的内涵最大的概念和苗巫知识体系构造,按照七种分类方法将其进行逐一分类说明。同时,对苗族之巫的核心内容:“巴狄”,进行分类说明。
苗族之巫;“巴狄”;知识体系;分类;说明
作者麻勇斌,男,苗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贵州省黔学研究院执行院长、贵州三线建设研究院执行院长、贵州省苗学会副会长(贵州 贵阳 550002)。
一、引言
苗族之巫是最具神圣性的古老文化之一。近十年来,对其进行调查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相应著述越来越多。但是,对这种文化进行符合其内在构造的分类说明,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尚未完成。已然形成的分类说明,不是从苗族之巫的知识体系出发,概括性与条理性均不够。比如,多数调查研究者认为,苗族之巫就是苗语称作“bad deib”、音译成“巴狄”的所谓“巴狄文化”,并将其分为“苗教”与“客教”,或“苗巴代”与“汉巴代”两种。这是很不全面的归纳和明显存在不足的分类。本文试图从苗族之巫的知识体系出发,对其进行分类说明,以便分享其神秘与奇妙,藉此进行条理化的记忆和读解。
二、对此前的分类述评
本文对此前关于苗族之巫的分类述评,拟从两个维度进行:第一个维度,是民间已然形成的分类;第二个维度,是专家学者的分类。
(一)民间分类述评
1.民间的分类
对于苗族之巫,民间存在的具有分类意义的概念,共有以下七个:
(1)“bad deib”,汉字拟音:“巴狄”,含义大概是:主持祭祀典礼的祭司或法师。习惯分为:“bad deib xiongb”(汉字拟音:巴狄熊)、“bad deib zhal”(汉字拟音:巴狄扎)、“bad deib lel”(汉字拟音:巴狄莱)三种。其中的“巴狄”,民俗层面的语义就是“法师”;“熊”的语义是“苗族”;“扎”的语义是“汉族”;“莱”的语义有两种:“官吏”和“田、雷、冉、赖”等姓氏苗人。“巴狄熊”的语义是:用苗语唱经主持祭祀典礼的祭司;“巴狄扎”的语义是:用汉语唱经主持祭祀典礼的祭司。“巴狄莱”的语义是:lel氏的祭司,专门负责歃血盟誓、仲裁、神判、解咒等巫事,唱诵的多是苗汉语夹杂的神辞。三种“祭司”,都是苗人,日常都说苗语。
(2)“goud niangx”,汉字拟音:“勾娘”,语义是:女师傅。民间又称:xiand niangx,音义与“仙娘”相同,汉语称之为“杠香婆”。此种法事操作者,专门负责到神域鬼界打探情况,了解人鬼之间的纠葛,堪称人鬼两界的使者,或通过“end nzot”即“看米”巫事,探问神灵作祟的理由,需要以何种法事解厄消灾。
(3)“qid”,汉字拟音:祈,语义是:“蛊”,一种邪恶的法术。日常用语又称之为“ghob gheub ghob qid”或“chud gheub chud qid”。有此法术之人,被视为邪恶术士。民间认为,这是女人掌握的法术。
(4)“dob sid”,是汉语“道士”的苗语转述,负责打绕棺、下葬、谢坟、谢土、堪舆等巫事。
(5)“nianl fax nianl sheit”,汉字拟音:“念法念水”,语义是:会法术、会化水。显然,是用汉语“法”、“水”作为中心词的苗汉语夹杂的概念。
(6)“wenx giob wus giob”,音义同于“文教武教”,是汉语“文教”、“武教”的苗语转述。大体而言,苗语称作“巴狄熊”的术类,属于“文教”;苗语称作“巴狄扎”的术类,属于“武教”。民间认为,“文教”比“武教”古老,其法术也要高明一些。
(7)“大牛角派”、“小牛角派”,完全用汉语进行分类。其中,“大牛角派”指的是操办大型而复杂仪式的正教术类,“小牛角派”指的是操作小型仪式的或正或邪的术类。
2.民间分类的概念简析
虽然民间对苗族之巫的分类很凌乱,甚至算不上分类。但是,这些概念却给出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一是对“巴狄”的内部分类非常清楚;二是对“勾娘”的职能赋予非常清楚;三是对“蛊”有专门的术语,而且认定是女性巫者掌握的邪恶之术;四是包括“道士”和“会法术”两类,并没有进入苗族之巫最初的术类概念范围。换言之,只有“巴狄”、“祈”、“勾娘”三种术类在苗族之巫本原的概念范围,其余术类是在苗族之巫的概念形成并稳定之后附加或接入的。
民间形成的关于苗族之巫的分类概念,相互之间有交叉或冲突。具体问题有四个:
一是“巴狄扎”和“道士”没有区别的标识,因为二者都是用汉语唱诵经文。实际上,此二者完全属于不同的术类。
二是除了“蛊”以外,其余术类都是“正教”,而实际上在“蛊”之外还有邪恶的法术。比如,“游坛老司”的法术,人贩子迷惑女子、孩子的法术,匠人对事主使坏的法术等等。
三是女性能够学习和运用的术类,只有“勾娘”和“蛊”两种,其余都是男性专有术类。事实并非如此费,在“勾娘”行当里面有男性,在“会法术”的行当里面也有女性。
四是把用苗语唱经的“巴狄熊”定为“文教”,汉语唱经的“巴狄扎”定为“武教”,严格地说没有合理性。虽然用苗语唱经的“巴狄熊”的法术,重在达成人神和解,其巫事进行过程中,也有很多涉及抓捕、征伐、审判、囚禁、斩杀等“动武”的仪式,比如苗语称之为“tead lis hmangt”的“退讼”,称之为“beux bleat”的“抢魂”,都不是单纯的用“文”的方式解决问题;使用汉语唱经的“巴狄扎”,也有不少根本不属于“动武”的巫事和相关仪式。比如,“朝傩”、“祭祀公安三宝”、“谢坟”、“谢土”等,并不是用“武”的方式解决问题。
尽管如此,在苗族民间,任何一个巫者,只要他施法行巫,民众马上就能识别他所传习的术类是什么种类。因此,民间形成的具有分类意义的概念,在实际生活中仍是适用的;其对巫者所持术类的判别即使不够正确,巫者也不会计较。
(二)专家学者的分类
苗族之巫是最具神圣性或神秘性的文化现象之一,内容庞大而复杂。文献表明,自清中叶至今200年左右,有不少人对其进行记述和研究。在这些人里面,有在苗族地区任职的政府官员,有专家学者,还有苗族之巫的传承人。
1.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著作
专家学者对苗族之巫的分类,最具代表性的表述,体现在以下五个著作中。
(1)凌纯生、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分类
该书以“宗教”与“巫术”为经纬划分苗族之巫。认为苗族之巫的“宗教”部分包含两种:“一为苗教,二为客教。两教各有分野,势力亦不相上下。”[1]P89其中,苗教的巫事有十五堂;客教的巫事有二十四堂。“苗人现在所保持的巫术有两种:一为‘化水’,他的用处是为人治病,是一种白巫术;二为‘放蛊’,用处是害人生病,是一种黑巫术。”[2]P143
(2)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的分类
该书对苗族之巫的记述,主要在“第十章 宗教信仰”,说“苗乡鬼神类多,有谓三十六神、七十二鬼。此系约数,实尚不止矣,殊非编者所能尽述”。因此,用十个小节内容进行分述。其在“第一节 祈禳鬼神”中,列举了“椎牛”、“椎猪”等26堂巫事,“第二节 苗覡神辞”中列举了“吴龙廖石麻等姓椎牛神辞”、“杨家椎牛神辞”、“椎猪神辞”、“接龙辞”、“通呈神辞”、“收邪勒水咒”、“符箓”7种神辞,“第三节 盟誓洗心”中列举了“囓血”、“诅咒”、“摸油锅”、“当坊土地祠”4种决疑法子,“第四节 旱魃求雨”列举了“迎天王神求雨法”、“茶枯毒捞求语法”、“设坛建蘸求雨法”、“拿龙求雨法”、“祭雷求雨法”、“抬狗求雨法”6种求雨法门,“第五节 择日秘术”中列举了“逐日择诀”、“论月建法”、“十二月月建所属十二地支总诀”、“论时择诀”、“六壬秘术掌诀”、“九刀八斫煞”、“八抵图诀”、“失物所到之处高低法”、“六壬掌诀”、“育儿男女定时法”10种秘诀,“第八节 占卜命相”列举了9种占卦法,“第九节 仙姑走阴”列举了“仙姑走阴”和“切七姊妹(qed qix zit meib)”2种法式,“第十节 巫蛊辟谬”列举了民间“归咎于蛊”的15种情形。在该书中,凡是苗人掌握和使用的术类,都归于苗覡之术。
(3)石启贵《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的分类
该书认为,“湘西苗族民间宗教有两种:一为巴代雄(bad deib xongb),俗称苗教;二为巴代扎(bad deib zhal),俗称客教。苗教和客教各设各的教坛,各有各的巴代祭司。‘巴代雄’是苗族世代相传的固有信仰,在祭祀仪式演教时,巴代祭司咏诵苗族世代口传秘诀神辞‘都肱’(dut ghunb),是苗族独有的原生型民间巴代宗教文化;客教‘巴代扎’是苗、汉杂居之后,由于文化交融产生的苗族宗教,成为苗族巴代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3]P1
(4)吴荣臻、杨章柏、罗晓宁《古苗疆绥宁》中的分类
该书说,苗族之巫“鬼的种类很多,名称不一,在苗民日常生活中简直有‘草木皆鬼’之观念。”“祭鬼以求消灾避祸,是苗民原始宗教活动的中心内容,从祭鬼活动的性质来分”,可分为三类巫事:“第一,敬奉性,就是敬奉善鬼的活动。此类活动一般规模较大,集中地表现在祖先崇拜的活动中,对善鬼人们十分崇敬,不惜杀牛宰羊以慰善鬼。”“第二,敬畏性,祭祀规模也比较大,敲锣鼓放鞭炮,一般是敬那些容易动怒,又不常作祟的鬼神,如天王、雷王、龙王、五谷神等。”“第三,贿赂驱赶式,这种形式用来祭祀恶鬼。祭恶鬼的活动主要有‘招魂’、‘隔鬼’、‘打灯’、‘收瘟’、‘打井’、‘放犁头火’、‘放桐子’等等。”[4]P257-258“其主要巫术有以下几种”:“1.‘过阴’或‘放阴’术”,“2.驱鬼术”,“3.占卜术”,“4.神明裁判”,“5.喝血酒”[5]P272-274。
(5)吴晓东《苗族祭仪“送猪”神辞》中的分类
该书说,“笔者在深入到苗族东部方言区即湖南湘西与贵州东北地区调查苗族这些祭祀仪式的时候,感到这一地区的仪式比较繁杂,这种繁杂主要表现在仪式种类比较多,而且各种仪式在各地有一些变异,名称又极不统一,稍不注意,会弄不清楚到底是同一仪式还是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仪式。另外,就是这一地区的祭祀仪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体系,即苗巴岱(bax deib xongb)体系与汉巴岱(bax deib zhal)体系,两者杂糅并存于苗族地区,都有苗民信奉。两者又有一些相互影响,让人难于区分。”[6]P1
2.上述分类存在的不足
上述专家学者及其著作对苗族之巫的分类,实际上代表了学人对苗族之巫内在结构的认识和判断。其中,关于苗族之巫分成“苗教”与“客教”的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广泛引用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些分类或判断,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是错误的归纳,后世学人务必慎用。其显见的不足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归纳的对象认识不清
上述关于苗族之巫的分类归纳表述,在研究对象上,有两种情形:
一是把苗族之巫的全部作为其归纳的对象。凌纯生、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吴荣臻、杨章柏、罗晓宁的《古苗疆绥宁》,属于此情形。在这三个著作中,数石启贵的著作罗列的对象最为全面;凌纯生、芮逸夫的著作认为苗族“宗教信仰”分为“苗教”与“客教”,并按照“苗教”与“客教”罗列“宗教”部分的内容,但没有按照“苗教”与“客教”罗列“巫术”;石启贵的著述和吴荣臻、杨章柏、罗晓宁的著述,都没有“苗教”与“客教”的概念。
二是仅把苗族之巫的“bad deib”作为其归纳的对象。石启贵编著,麻树兰、石建中整理译注,王明珂协编的《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吴晓东的《苗族祭仪“送猪”神辞》,属于此情形。他们认为,苗族之巫等于“bad deib(巴代)”,并将这种文化分为“苗巴代”和“汉巴代”。但在《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所记述的苗族之巫资料中,有很多东西超越了其所谓“巴代”的范畴。比如,“化水神咒”,“苗医口诀”、“各种武术神咒”、“安葬及撒米口诀”等。
(2)“二分法”的缺陷
所谓“二分法”,是把苗族之巫划分为“宗教”与“巫术”两个层次,把“苗族宗教”或“bad deib(巴代)”又划分为“苗教”与“客教”两种。
把苗族之巫划分为“宗教”与“巫术”两个层次,属于缺乏对苗族之巫知识体系深入了解的“硬划分”。苗族之巫并不是按照这两个层次进行构造的。如果以所祭神灵有无明确的“司职”为边界进行划分,的确可以划分出两个层次,但并不是祭祀有专门“司职”神灵的巫事就等于宗教。同时,这样划分,还会把本来在实际存在时乃是一体的巫事,被截然分开,传承者和苗族民众都不会认可。比如,苗语称作“liot guib”的“赎魂”巫事,是“苗教”巫者和“客教”巫者都会操办也都操办的巫事,这堂巫事没有固定的“司职神灵”或“当事神灵”,但它有完整而规范的仪式,将其划入“巫术”层次,肯定不当。同样的道理,“仙姑走阴”,有固定的“司职神灵”——“七仙女”等,在凌纯生、芮逸夫的著作和石启贵的著作里面,都划入了“巫术”的层次,显然不合实际。
把苗族之巫划分为“苗教”与“客教”,属于“错划分”。这种划分,源于苗族民间对“bad deib”的认识。苗族民间确实有“巴狄熊”与“巴狄扎”之分,但研究苗族之巫的学人应当知道,这是以巫者行巫时使用的语言为特征的划分,不是从苗族之巫的知识体系进行划分。以“苗教”与“客教”为范畴的划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一是无法概括实际存在的苗族之巫的所有事象。“bad deib(巴狄)”不等于“苗族之巫”。“bad deib(巴狄)”只是实际存在的“苗族之巫”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核心部分。这是认识和研究苗族之巫必须具备的基础观念。
二是“bad deib(巴狄)”,作为苗族的原生信仰文化,不止苗语称作“bad deib xiongb”的“苗教”和称作“bad deib zhal”的“客教”,至少还有苗语称作“bad deib lel”(汉字拟音:巴狄莱)的一种“巴代”。这种名叫“bad deib lel”的“巴代”,无法找到对应的汉语词进行翻译。假如必须翻译成汉语,其语义接近于“lel姓巴代”或“官吏巴代”,因为在当今苗语中,“lel”的语义有两种:“田、雷、冉、赖”等姓氏苗人;掌管律例的官吏。在民国以前的古代,“巴狄莱”主要负责的巫事是“jid nchot denb(立法合款)”、“lanb sead(论理仲裁)”、“jid dongx jid det(歃血盟誓)”、“退讼解咒(bud qiod tead lis)”等巫事。这些巫事,随着统治苗族地区的土司、土官的衰微而逐渐变成由“苗巴狄”、“汉巴狄”替代。至今苗族民间仍有广泛流行的古老歌谣,可作印证:
Chud lanl lis nhangs bad deib xiongb,
结亲要与“巴狄熊”结,
Jid nghot nkind mel dot nieax nongx;
(他)摇动铜铃就有肉吃;
Chud qiub lis nhangs bad deib lel,
联姻要与“巴狄莱”连,
Jid jiangt njiout xinb jix dot nbed。
(他)敲响“信咚”就有米粑。
三是若以唱经使用的语言为边界划分“苗教”与“客教”,即以苗语唱经的“巴狄熊”为“苗教”,以汉语唱经的“巴狄扎”为“客教”,那么,那些用苗汉语夹杂唱经的术类,应当属于哪一派系?谁都没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事实上,使用苗汉语夹杂唱经的术类,在苗族之巫里面并不是少数。如,石启贵记录的《杨家椎牛的神辞》,苗语称作“nbeud bab”、石启贵记作“报粽报新”的巫事神辞《卜粽》,苗语称作“renx rongx”、汉语译成“接龙”的神辞《接龙辞》,特别是其中的《安龙辞》等,都是苗汉语夹杂的,这些巫事应当属于“苗巴代”还是“汉巴代”?根本没有办法给出确界,并得到民间的认可。更为诡异的是,那些以“字徽”或“符箓”为特征的术类,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占卜术”,通常是苗汉语夹杂或将苗语翻译成汉语诵读,也不知道应当划归“苗教”还是“客教”。
因此,对苗族之巫的内部结构的划分,既不宜套用“宗教”与“巫术”的划分法,也不能采用“苗教”与“客教”的划分方式,要从苗族之巫的知识体系出发,找出它的本原结构和内部肌理。
三、本文提出的苗族之巫分类
以上分析已然说明,民间和专家学者此前对苗族之巫的分类,不够合理,应当寻找新的正确分类方法,以便建立逼近其本真的说明框架。
(一)寻找分类依据和分类方法
1.苗族之巫的定义
苗族民间存在的关于苗族之巫的内涵最大的概念有两个:一是“chud rongx chud ghunb”,汉字拟音为“处戎处滚”,大体语义是“办理与神鬼及龙灵的事情”;二是“chud gheub chud qid”,汉字拟音为“处告处祈”,大体语义是“办理弄蛊与弄巧的事情”。其中,前者属于好的术类,即正教巫者所掌握和运用的术类;后者属于不好的术类,即邪恶巫者所掌握和运用的术类。这两个概念所指的术类,加在一起就是汉语表述的苗族之巫。
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苗族之巫做如下定义:苗人创造和利用神性的方式与活动的总称。
2.分类依据
笔者认为,对苗族之巫进行分类说明,需要两个依据:一是苗族民间已然形成的分类;二是苗巫知识的内在肌理。
(1)民间已然形成的分类
苗族民间对苗族之巫已然形成的分类,是苗族之巫分类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必须遵循。一方面,民间已然形成的分类,在苗族民众和巫者群体里面已形成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它是从“做”或“办理”的角度进行的分类说明,不是从内涵赋予和外延界定的角度进行的分类说明,概括的准确性和边界的清晰性不足,存在一些空白处和交叉部分。
(2)苗巫知识的内在肌理
苗族之巫是一个类似于具有生命的文化活体,它具有实际存在的整体性和内部构造的系统性。对其进行分类说明,一定要在把握整体性的条件下,依据它的内在构造,找出结构方面的逻辑关系和累积方面的叠层关系。
(二)七种分类方法
分类的关键是找到分类的边界。
笔者认为,要用以下七种分类边界对苗族之巫进行分类,才能建立完全呈现和正确理解的通道,使得读者能够对苗族之巫进行全域环视和通透详读。
1.以生成神性的方式为分类边界
千百年来,苗族之巫在苗族民间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在于它充满神性,是由神性构成的和具有神性的文化现象。以神性生成的方式为边界分类,苗族之巫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1)治权神化类
此等术类,其神性生成于欲成巫者之人,通过严格的仪轨学习,熟知通往神域鬼界的所有路径,通晓解决人神争讼的礼制律例,养成高洁的品德,拥有足够的胆识和能力,而后得到前辈师尊和域内族亲的郑重赋权,统率万千“阴兵阴将”。其所履行的职责,是依照律例解决人与世间万类生命的争讼,为人谋取福祉,保证世间的公平与安宁。苗语称作“bad deib xiongb”的这类苗巫,就属于此种。
(2)学成得道类
此等术类,其神性生成于欲成巫者之人,经过投师学习或修行,由于智慧和勤奋,或得到尊师秘授,或是顿悟、渐悟,达到高于常人的境界,懂得很多知识,掌握奇妙法门,熟悉鬼界的各种关系,得到师门的颁证,因而拥有异能。苗语称作“bad deib zhal”和“bad deib lel”的这两类苗巫,属于此种;“勒咒化水”、“占卜择吉”等术类,亦属于此种。
(3)病变得法类
此等术类,其神性生成于欲成巫者之人的奇异经历或身体病变。病愈之后,或重返病发状态时,患者获得了能够与神灵沟通交流的能力。“仙姑走阴”和“发猖兵”等,属于此种。此等术类,苗族民间借用汉语表述为“阴传阴教”。那些需要通过向师傅学习才能掌握的术类,为“阳传阳教”。
2.以唱经使用的语言为边界分类
以巫者在行巫过程中使用的唱经语言为边界,苗族之巫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1)使用苗语经文的,苗语称作“ghunb xiongb”,即“苗巫事”。
(2)使用汉语经文的,苗语称作“ghunb zhal”,即“汉巫事”。
(3)使用苗汉语夹杂经文的,苗语没有明确概念,笔者且将其归为“别类巫事”。
3.以从业范围为边界分类
在苗族民间,巫者有“职业”与“非职业”两种。“职业”与“非职业”,不是巫者自己确定的,乃是其所掌握的术类决定的。
(1)职业之巫
苗语称作“巴狄”的一类巫者,属于“职业巫者”。其余都是“非职业巫者”。
“职业巫者”的显著特征有以下两点:
一是以行巫为主业。也就是说,在苗族传统观念中,这样的巫者,是拥有众多“阴兵阴将”的“大官”,其职责是管理“阴阳两界”。其“辖区”内发生了需要他解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人神纠纷”,请他解决,无论与之是否友好,他都得帮助,消灾解难。这是礼制规定的义务。
二是当今的“职业巫者”虽然也照样参加劳动,但在民国及以前,他们是不参加种植等劳动的,他们只负责操办“祭祀活动”和与“祭祀”有关的重大活动。例如,决定结盟与开战、制定律例并主持依律处罚的仪式等。他们参加劳作仅是一种自觉,而不是必须。有的劳动项目,比如播种、伐木、采果等,即使他们愿意做,民众不会让他们做,因为他们手握“重兵”、杀气过重,会吓倒种子、树木等一类生命,造成庄稼歉收或果树来年不结果实的现象。
(2)寓巫于业之巫
寓巫于业之巫,严格地说,属于“半职业”之巫。从事者虽然可以以其掌握的术类为业,但他们不是解决“人神官司”的官吏,而是为人们了解“人神官司”的程序、找出解决“人神官司”的途径提供服务。也就是说,有人需要提供服务,他们就帮助,没有人需要服务,他们就选择恰当的事情谋生。如果求者众多,他们也就以巫为业了,不必再做其他。一旦“生意”不好,他们又可以兼作别样,没有忌讳。大体上说,有以下四种:
一是占卜预测,包括读解异象。此等术类最为多样。
二是跳仙走阴,包括苗语称作“切七姊妹”的神游式娱乐活动。其法术范式,是通过呼唤神灵附体或相助而具有神性,以神游的方式探知神域鬼界拟降给人间的祸福之事。此等术类本来可以归属于占卜预测类,但它凭借的是固定的“经文”和巫者的“魂身”,与那些利用不同物类神性的做法,有明显的不同,故而可以归为一种独立的术类。
三是涉及人神关系的事生、事死活动,包括为产妇接生,为新生儿取名、赐福、办成人礼,为新婚夫妇主持婚礼,为老人祝寿,为病人送药(苗语:songt nggab),为亡人洗尸、入殓、守孝等,带有巫术内容的事宜。
四是神判决疑,包括组织立法、结盟、依照律例仲裁等。掌握和使用此等术类的巫者,民国及其以前,苗语称之为“巴狄莱”。随着土司、土官的消亡,其所负责的巫事,已逐渐被“巴狄熊”、“巴狄扎”和其他门类的“非职业”之巫替代了。
(3)寓业于巫之巫
寓业于巫的巫者,主要是有法术的艺人、匠人,以巫术为其匠艺服务,是真正的“非职业”之巫。大体上有以下六种小类:
一是亦巫亦医,包括兽医和树木作物医。这是十分常见之巫。术类掌握者在施法时,有的用苗语念咒,有的用汉语念咒。咒语的体例是篇幅较短的诗歌。念咒时还要佐以指诀和字徽。
二是亦巫亦匠,主要是木匠、石匠、瓦匠、铁匠、篾匠、补锅匠、油匠、银匠,以及牛客、鸭客等。在民间,但凡能够行走江湖,以匠谋生的匠人,都有一套属于本门匠师掌握的法术。例如,木匠掌握的法术叫做“鲁班经”。传说,这些法术既可以使人得福,也可以使人遭灾。
三是亦巫亦猎,包括亦巫亦渔。此类巫者,或是猎户,或是渔夫。在有的苗族村寨,人们将其称为“bad deib nieax”,汉字拟音:“巴狄年”。他们掌握的是与山神、水神交好,保证狩猎、打鱼时安全,并获得好收益的法术,通常是为自己护身,也可以为不掌握此类法术的猎人、渔夫提供保障。
四是亦巫亦武,即有法术的武师。这是苗族习武者能够成为师傅的重要标志。苗族传统武功的修行,有三个层次:初级习武;中级学药;高级习巫。只有到了第三个层次的武师,才能算是真正的大师傅,堪为宗师。
五是亦巫亦艺,包括杂技班子的掌坛师、舞龙灯的掌坛师、舞狮子的掌坛师等,都属于此类。
六是亦巫亦贼,包括会作法使人放松警惕或是害怕的老贼,会制作和施放迷魂药(苗语称作为:nkiob)引诱异性、拐卖人口的人贩子等。
4.以性别为边界分类
在苗族之巫里面,明显存在性别方面的观念和相应事象。按照既定的观念,男性掌握的术类与女性掌握的术类,有一个大致的分界。
从其所掌握的术类来看,以上所述的“职业”和“非职业”之巫,男性巫者都可以涉足,而且都占主导地位。女性巫者能够涉足的术类,只有以下四种:
(1)“仙姑走阴”。
(2)男性“职业”之巫中的一些小巫事。如,“ghunb wub gil”,汉字拟音:“滚务机”;语义是:“祭茶神”;“ghunb deb npad”,汉字拟音:“滚带葩”语义是:“祭蚕桑神”。
(3)亦巫亦医或亦巫亦匠掌握的一些防身法术。比如,对付放蛊、破解迷魂药的咒语和方法。
(4)蛊。在苗族民间有一种观念,认为男性拥有法术,是正道法术;女性拥有法术,则是蛊,是邪恶之术。因此,敢于声称自己掌握法术的女性较少。
5.以法术的作用为边界分类
若以其法术的作用为边界,苗族之巫可以划分为以下三大类:
(1)交神鬼以消灾祈福
凡是所祭祀的当事神灵有专门的司职,需要繁复仪式交涉才能达成和解的巫事,都属于此类。其最大特点是,当事神灵都有自己的领地和“办公场所”,巫者必须熟知从阳世前往其“衙门”的路径,以及“办事规矩和程序”。此类巫事及其相应的祭祀仪式,是兑现诺言、酬谢供奉,遵循的是人神共同遵从的道理和律例。因此,它们几乎都可以称为“还愿”,苗语叫做:“ghob jianx sot nghat”(语义:奉送钱财),或“nbad niel liot kangt”(语义:弥孽赎过)。操办此等巫事的巫者,身份是最高裁决者,不是神灵的密友或弟子。其依律作出的判决,当事神灵和事主都必须服从。如果当事神灵执意不从,操作巫事的巫者经再三规劝无效,可以对其动武,或发兵讨伐,或依律重处,使之无容身之地。所以,此类巫事及其相应的法术,是“治理”之法,安宁人神两界的大法。
(2)用神性以探测侦知
此种术类,属于解惑之术。
此种术类,“各师各教”,法门万千。有的用时间的神性来推算,有的用各种具有神性的物类作为法器侦测,有的用巫者自己的“魂身”去探问或观察。无论使用何种方法,目的任务就一个:刺探神鬼的心思,为求助者消解迷茫、慰藉惶恐、憧憬未来,给生活以方向和勇气。
(3)挟神异以增长技能
此种术类,属于通过依附、取悦神灵,或是高人,或是负有特殊本领的神性物类,习得奇妙技能,或是能够驾驭某种神异力量,成为超过常人的人。如,被人击打不痛、止血、化解惊骇、使人惧怕等等。寓巫于业的各种匠人艺人所掌握的法术,皆属此类。
6. 以巫事的功能为边界分类
按照功能划分,即按照事主举办某堂巫事的用意,也即事主出于何种事由和巫事要达成什么目的,巫事大体上可以分成10个小类别。
(1)感恩戴德类
举办此类巫事的事由,通常是事主好运迭来、人丁兴旺、发富发贵,在这种运势下,或经巫者探知,或事主自己感到,这是祖先神灵或是其他别的神灵庇佑恩赐的结果,于是就按照祭祀各种不同神灵的巫事及其规格要求,择定吉日,请巫者操办。假如事主得知所来富贵是祖先赐予,就会举行苗语叫做“pot ghot”(汉字拟音:“颇果”)的巫事。这堂巫事用的牺牲若是猪,苗语叫做“pot ghot nbeat”(汉字拟音:“颇果把”),规格一般,是普通、常见的巫事;用的牺牲若是水牛,苗语叫做“pot ghot niex”(汉字拟音:“颇果捏”),是高规格的巫事,花费很大,须是富贵人家才能举办。
(2)和神消灾类
举办此类巫事的事由,通常是事主遇到灾厄凶险,或是大病缠身、久治不愈,或人丁消亡、富贵顿失,请求巫者探问鬼神,得知是得罪了祖先神灵或是其他别的神灵,受到其降灾施祸,不及时解除必定祸不单行,于是就按照作祟神灵的要求,许下大愿(苗语叫做:“jid beal”,汉字拟音:“及巴”),答应只要神灵消解怨恨、撤除枷锁,使事主及家人恢复如初,必定按照神灵的要求,择定吉日,请巫者操办巫事,奉送牺牲、钱米,与神灵和解。例如说,假如事主得知作祟的是祖先神灵,同样会举行苗语叫做“pot ghot(颇果)”的巫事,巫事的具体的规格,根据神灵的要求来定。假如事主得知作祟的是雷神,则择日举行苗语称作“xid sob”(汉字拟音:“西索”)的巫事。巫事的具体规格,根据占卜时巫者转述出来的神灵的要求来定。
(3)赎买求恕类
举办此类巫事的事由,存在两种情形:一是粮食歉收,请巫者帮忙探问鬼神,得知是因为事主不慎,得罪了粮食的灵魂,或是别的神灵把粮食的灵魂弄走了,须及时救赎才能重新赢得丰收;二是事主或家人失落魂魄,或是被别的神灵摄走了,须及时救赎才能转危为安。赎买求恕的巫事,事主就按照作祟神灵的要求,择定吉日,请来巫者操办巫事,奉送牺牲、钱米,赎回失掉的魂魄。
主要的巫事有两堂。一是苗语叫做“liot nongt”(汉字拟音:“料农”)的巫事。在民国及其以前,苗族人遇到稻谷、小米等粮食作物突然遇到虫灾或蹊跷歉收等,通常会举办这堂巫事。二是苗语叫做“liot guib”(汉字拟音:“料鬼”)的巫事。针对的事象是,事主外出受到惊吓,出现不思饮食、身体困顿、夜来恶梦不断等现象,有经验的长者或巫者据此断定是失落魂魄,民间叫做“失落伴”,才请巫者举办此种巫事。
(4)寻找招引类
举办此类巫事的事由,存在如下三种情形:一是家中老人亡故;二是房前屋后山体垮塌,巨树折断,常年清澈的泉水浑浊不清,蛇群或鸟群等蹊跷迁徙走出房屋或聚落所依靠的山林等“异象”,请求巫者探问鬼神,得知是因为事主平日事奉不周,龙神心生厌倦,负气出走,事主就按照作祟神灵的要求,择定吉日,请来巫者操办巫事,挽留龙神;三是事主遇到家人失踪,或是遗失贵重物品,不知道落在哪里,或是知道了失踪者的落脚点与窃贼,但无法确认,因而举办巫事,请求巫者的阴兵阴将帮助找寻。
针对老人亡故的巫事,苗语叫做:“chat ngas”,汉字拟音:“查阿”,意思是“招亡”。日常用语称为“xid xiangb tud ngas”,汉字拟音:“西相秃阿”。一般在亡人下葬当晚举办,事主家人及至亲好友都要参加。
针对龙神负气出走的巫事,苗语叫做:“reax rongx”,汉字拟音:“然融”,意思是“挽留龙神”,故而这堂巫事被翻译成:“接龙”、“迎龙”、“招龙”等,日常用语称为:“jiongb rongx reax nceut”,汉字拟音:“炯融然策”。这堂巫事,有两种规格:一是单家独户举办的小型巫事,苗语叫做:“reax rongx bloud”,汉字拟音:“然融标”,意思是:“家庭挽留龙”。二是整个聚落若干家庭联合举办,甚至几个聚落联合举办的大型巫事,苗语叫做:“reax rongx gheul”,汉字拟音:“然融高”,意思是:“全寨挽留龙”。
针对遗失贵重物品和有人失踪的巫事,苗语叫做:“nbud gheud”,汉字拟音:“卜钩”,意思是:“请钩神找寻”。这堂巫事,是有权势的人家才敢举办的重大巫事。因为在巫事举行时,“持钩人”会在巫者法术作用下进入迷幻状态,被犹如富有神性的“木钩”牵引,沿着人们未知的方向一路狂奔,无论奔向哪里,事主的兵将必须追随到哪里。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找到了失物,无论对方如何强大,都必须抢回失物,彼此难免要刀兵相见。所以,举办这种巫事,事主必须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合约盟誓类
举办此类巫事的事由,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家族或宗支中出现背约现象,危及家族或宗支间的和睦关系与地方长治久安;二是鉴于共同应对危机的需要,必须以约法的形式强化团体的凝聚力。
此类巫事,是苗语叫做:“fub gheul fub rangl”,汉字拟音:“伏高伏壤”,是民间所谓“喝血酒”中较为温和的巫事,日常用语称之为叫做:“jid nchot”,汉字拟音:“机绰”,实质上是请鬼神来当中人,见证和维护起誓活动的严肃性。
这种巫事使用的牺牲,要么是鸡,要么是猫。苗族传统观念认为,鸡是凤鸟,猫是猛虎的师尊,其血充满神性,是歃血起誓最为灵验的血。巫事在距离聚落不远的某个固定场地进行。仪式结束后,参加巫事的所有人要聚餐共饮。
(6)神判决疑类
此类巫事,苗语叫做:“fud nqind ghox zhangs”,汉字拟音:“夫清郭长”,日常用语称之为叫做:“fud ghud nongx nqind”,汉字拟音:“夫孤农清”,通常翻译成:“神判”。实质上是请鬼神来当判官,判决是非曲直的官司。古时,操办这种巫事的巫者,须是“巴狄莱”主持。举办巫事时,要立法坛,供奉“法王”的大神偶。
举办此类巫事的事由分为如下两种事情:一是家族或宗支中出现叛贼,危及家族或宗支间的和睦关系与地方长治久安,需要决定处置方式;二是事主遗失贵重物品,或是受了歹人陷害、告密而遭到官司冤枉,无力昭雪冤屈,只得向神灵求助。
巫事的规格,即巫事的大小,由事主根据举办本堂巫事要达到的目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态来定。事态可能很大的,事主须集结足够的武装力量,一方面保证巫者出入安全,同时保护法场,避免冤家捣鬼使坏。另一方面,假如需要对质的,还需将拒不认罪的当事者带到巫事现场,当着神鬼的面,歃血起誓,答应接受神鬼所有惩处;或捞取油锅之物,确认是否有罪,若罪名成立,要当场执法。势单力薄的事主,往往做不到强迫肇事者到场参加歃血,其办巫事,仅是向神鬼控诉,请求神鬼做主。这种情况的巫事,巫者代表神鬼,进行缺席判决,并将结果告诉事主,让事主和参与巫事的人记住,事主的冤家将会遭到的报应方式,以便事后检验。
(7)驱逐赶杀类
此类巫事,苗语称为:“choud mangx jiad”,汉字拟音:“抽忙加”;也可以称为:“jit mangx jiad”,汉字拟音:“挤忙加”。是一种以武力驱逐和杀伐鬼魅的巫事。
举办此类巫事的事由,存在如下三种情形:
一是事主或家人失落魂魄,举办赎买求恕之类巫事,向鬼魅上供酒食钱米,祈求释放所摄之魂魄,没有奏效,患者病情日益加重,经巫者施术探知,作祟之鬼魅巢穴何方高崖洞天,事主就请巫者举办向鬼魅进攻的巫事。例如,苗语称作“beux bleat”,汉字拟音:“搏扁”,汉语翻译成“抢魂”的巫事。
二是久旱不雨,经巫者施术探知,是不良龙神无端生事,祸害地方,受害人群便推举德高望重者为事主,组织举办苗语称作“ntongt rongx”,汉字拟音:“捅融”,可以翻译成“擒龙屠龙”的巫事。巫事举行过程中,事主要按照巫者的号令,发兵进攻恶龙栖居的山洞,捉拿大蛇、大鲵、蛤蟆等爬行动物,逮到法场进行囚禁、审判或斩杀,勒令龙神下雨。
三是事主家有人非正常死亡,死者阴魂不散,时时作祟,造成阴森恐怖,事主才请巫者帮助举办这种巫事。这种巫事,苗语称作:“choud mangx zanl”,汉字拟音:“抽忙簪”。
此类巫事,巫者均是动用武力驱赶神鬼,迫使其害怕、投降、远遁,来达到事主期望安宁之目的。
(8)扫除隐患类
此类巫事,苗语没有统称,是一种预防灾祸发生的巫事。
主要有四堂巫事:一是用来防止火灾的巫事,苗语称作:“bot dongd nzeab”,汉字拟音:“保冬咋”。通常在冬季举行,是以寨子为事主举办。二是用来消灭杂草虫灾的巫事,苗语叫做:“ob mod ob nid”,汉字拟音:“喔陌喔尼”。通常在冬季举行,是以单家独户为事主举办。三是祛除不详之兆的巫事。比如,事主家及家人做了预示凶灾降临的恶梦,或是遇到在苗族民间看来预示着有灾祸发生的怪事,苗语叫做:“ghans gheix ghans gueab”,汉字拟音:“感厄感怪”,请巫者提前举行苗语称作“nzead gheix”的巫事,进行禳解祛除。四是洗刷罪名的巫事。例如,事主因不了解详情,参与了“喝血酒”发毒誓的巫事,受到了神灵的惩罚,需要忏悔解罪,请巫者提前举行苗语称作“nzead nqind”,汉字拟音为“攒清”的巫事。苗语称作“kob xid tead lis”,汉字拟音为“阔西它理”的巫事,就是此类巫事的典型。
(9)卜问前途类
此类巫事,乃是在重大关头举办的一种旨在占卜前途吉凶的巫事,苗语虽然没有统称,但其中的巫事非常繁多,需要分作两个小类进行介绍。
第一,是以家庭或个人为事主的苗语称作“shad ghunb”,汉字拟音为“沙滚”的巫事。这种巫事十分常见。例如,苗语称作“nbud goud niangx”,汉字拟音为“卜勾娘”的巫事,和苗语称作“jix beal”,汉字拟音为“及巴”,语义是“许诺”的巫事,都属于这一类巫事。在古代,苗族家庭、家族遇到重大事件,比如有人突然遭到官司冤枉,或是意外失踪、丧亡等,毫无头绪和线索,事主都会去请巫者查看和问计,巫者不论是采用“米卜”问事,还是采用“跳仙”问祖,亦或采用“掐失”判断,这些巫事都可以称作“shad ghunb”。
第二,是以家族、宗支或区域的所有人组成的团体为事主的苗语称作“nes goud”,汉字拟音为“乃勾”,语义是“问路”的巫事。其中,有两堂巫事最具典型意义。一是苗语称作“zeib gix zhangs”,汉字拟音为“镇及长”,语义是“祭战旗”的巫事。这是在作战之前进行的巫事。主要作用是卜问战事,卜问每一位参战人员的吉凶情况。二是苗语称作“dal pul dal denb”,汉字拟音为“答步答等”,意思是“确定领地疆域”的巫事。这是地界相邻的家族、宗支、部族或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确定领地疆界,确保边界安宁的巫事,主要作用是请神鬼参与见证划界活动,或埋石立碑锁定约法,或歃血盟誓折箭合符。同时,这也是苗族在战争失败之前决定迁徙路线、探问未来落脚地点的重大巫事。
(10)巫者修为类
这些巫事是以巫者为事主的巫事,有巫者自为的巫事,巫者的师尊、师兄弟代为的巫事。大概有以下四堂巫事:
一是苗语称作“jianx jiangs”(汉字拟音:“间将”)或“qiand nggied”(汉字拟音:“迁阶”)的巫事。这是巫者学成,创立门户的重大巫事,由巫者的师傅主持。
二是苗语称作“bad deib jianx xiangb”,汉字拟音“巴狄间相”的巫者丧礼的巫事,即巫者的葬礼,由巫者的大弟子主持,巫者的所有弟子参与。
三是除夕夜巫者发兵马的巫事,苗语称作“bad deib jiangt ginb”。这是巫者自为的巫事,旁人不能参与。
四是巫者出于拯救世人的责任心而进行的战凶斗恶之类巫事。例如,在遇丧人家出殡时,巫者要在丧家举行苗语称作“geud zhux”,汉字拟音为“钩筑”的巫事。届时,巫者要开启透视阴阳两界的法眼,观看是否有活人灵魂悬在棺椁下面,如有,则预示着将有人随亡人而亡,须用法力将这些灵魂打下来。
7.按照苗巫“专业术语”的称谓分类
苗巫对各种巫事有专门称谓。但是,通常情况下,苗巫大师和调查研究者,并不注意到这些称谓的含义,以及它们具有分类方面的含义。例如说,从古老时代因袭下来的巫事名称,有的用“xid”作为关键词,有的用“reax”作为关键词,还有的用“liot”作为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毫无疑问具有区分的含义,否则,古代巫者不会如此定义巫事的名称。笔者经过分析这些巫事之间的差别,发现名称中使用相同关键词的巫事,有某种共性;使用不同关键词的巫事,有显著的差异性。因此,梳理出苗巫基于名称关键词的分类,有如下14种。
(1)“xid”(汉字拟音:“西”)类
以“xid”为名称关键词的巫事,有“xid xiangb”,汉字拟音:“西相”,意思是:“祭祀祖先”;“xid sob”,汉字拟音:“西索”,意思是:“祭祀雷神”;“xid rongb”,汉字拟音:“西融”,意思是:“祭祀龙神”;“xid ndut”,汉字拟音:“西杜”,意思是:“祭祀树神”。
在苗族民间日常用语中,也有些地方把“xid”说成“xioud”(汉字拟音:修)。“xid”是一种祭祀方式的专称,具有显著的表达爱戴、崇拜之义,巫事的功能是召集、安抚、安置和取悦、稳定神灵之心,以保富贵吉祥。
“xid”类巫事,祭祀过程庄严而不乏嬉戏娱乐的内容。例如,“xid sob”,即祭祀雷神活动,祭祀过程禁忌很多很严,但在代表事主巫者与代表雷神“说雷”时,充满调侃取笑的色彩。
(2)“pot”(汉字拟音:“颇”)类
以“pot”为名称关键词的巫事,只有苗巫记作“pot ghot”,汉字拟音为“颇果”,意思是“祭祀祖先”这一堂。有两个规格的巫事,区别主要在于,所使用的牺牲是“猪”还是“水牛”。
由于“pot ghot”与“xid xiangb”都是祭祀祖先,民间将其偶联统称为“xid xiangb pot ghot”或“pot ghot xid xiangb ”。但是,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堂巫事,而且,在举办“pot ghot”巫事时,须将“xid xiangb”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放在最后。
“pot”的语义主要是崇拜、敬畏、供奉;“pot ghot”这堂巫事主要表达事主对祖先的遵从、忠心和恪守祖德。
“pot”类巫事,不论规格大小,祭祀过程始终庄严肃穆,处处体现虔诚与谨慎。例如,陪神的“舅家”要一直坐着,纹丝不动;扮作“blab menldeb qiub goud goud”的五位盛装男女,手持五柄梭镖,也要在中堂的神位静静地坐着,不能走动;制作献给祖先的肉食时,刀俎手舀汤须用两个瓢瓜,一个在上,一个在下,防止汤汁漏落在地;享用食物时不能说话,剔下的骨头必须放在桌上,活动结束时,巫者要捉人全部收拾起来,埋在事主屋外不常有人们走到的地方。整堂巫事进行过程,祖先神灵都充满威严感,事主和所有参与者都十分小心,不敢有丝毫大意。
(3)“reax”(汉字拟音:“然”)类
以“reax”为名称关键词的巫事是“reax rongb”,汉字拟音:“然融”,意思是:“祭祀龙神”。如前所述,在民间,这堂巫事又可以称为“xid rongb”,汉字拟音:“西融”。
在苗族日常用语中,“reax”的语义是呼唤、挽留、迎接等;“rongx”的语义是龙,即龙代表的富贵吉祥。通常,龙在苗语中可以用“rongx”与“nceut”偶联表达。所以,“reax rongb”这堂巫事,民间诗化表述成“jiongb rongb reax nceut”。
“reax”类巫事的祭祀活动,主要是通过美好的东西,将神灵引导或引诱回归、前来、定心住下,以保富贵安康。所以,这堂巫事中,着重于营造打动龙神的美丽房屋、美味食物、华贵的服饰,祭祀的重要环节是美丽的青年男女在美妙的节律中舞蹈,让龙神心灵动荡,回心转意,回归故里,永佑事主。
(4)“songt”(汉字拟音:“送”)类
以“songt”为名称关键词的巫事是:“songt hliet”,汉字拟音:“送里”,意思是:“送饭”;“songt nbeat”,汉字拟音:“送罢”,意思是:“送猪”。
“songt hliet”是小巫事,通常在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举行,由苗语称作“goud niangx”的女性巫者主持。主要作用是表达事主对祖先的时刻敬仰,祈求祖先不断关爱。平常,如果事主得到老人托梦或是其他方式的提示,也可能请巫者举办这堂巫事。“songt nbeat”是大巫事,以猪为牺牲。事由通常是,作祟神灵开出的条件是用猪作牺牲才能了断恩怨,才举行之。例如,假设事主家有人失踪,通过巫者“探问”得知,是虎豹之类神性动物引走的,事主就会按照虎豹喜欢吃猪的特点,举办“songt nbeat”巫事,为虎豹送猪,以赎回失踪者。
(5)“liot”(汉字拟音:“料”)类
以“liot”为名称关键词的主要巫事是以下两堂:
一是“liot nongt”,汉字拟音:“料农”,语义是:“赎小米魂”,巫事的功能是:赎粮食之魂。
二是“liot guib”,汉字拟音:“料鬼”,意思是:“赎魂”。
在巫经里面,“liot”与“nbad”互为偶联。在日常用语中,“nbad”的语义是“弥补、补偿”。因此,“liot”类巫事,就是巫者帮助事主,把走失的魂魄,或是被某种神灵摄走的魂魄,通过赎买交换的方式弄回来,使之恢复如初。
(6)“qiox”(汉字拟音:“桥”)类
“qiox”类巫事,往往是事主家中出现“异象,”或是人丁不旺,或是子息常遭飞来横祸,有人患上怪病,根据巫者的指点许愿,苗语叫做“jid beal”,之后“异象”消失,事主得偿如愿,而后择期请巫者主持巫事。
以“qiox”为名称关键词的巫事主要是以下三堂:
一是“qiox nux”,汉字拟音:“桥努”,意思是:“朝傩”。这堂巫事,是祭祀“傩公傩母”。是苗汉语夹杂使用的巫事,有戏剧部分和了断人神恩怨的部分。了愿的巫事犹似判官在衙门断案。
二是“qiox ghunb zeab nongx nggod”,汉字拟音:“桥滚咋农糕”,意思是:“朝佛”。
三是由于遭到奇遇而成巫者的人的病变过程。这样的巫者,在病变时,多数表现为成为巫者的倾向,有经验的长者会暗示事主,请个巫者来为他或她“安坛”,意思是正式封他或她为巫者,如此之后,病患顿消、恢复如初,并有了神性。
(7)“lot”(汉字拟音:“咯”或“勒”)类
“lot”,在日常用语中的语义是:“咒骂”。
“lot”类巫事,就是以咒骂的方式,将咒语中各种恶毒与污秽附着在某种物质上,让它作为武器,施加出去时充满神惧和法力。代表性的巫事是:“lot nqind”,汉字拟音:“咯清”,意思是:“血咒”,即民间所说的“喝血酒”。事主请求巫者通过咒骂将各种剧痛惨死施加给牺牲的血,让这种被施加了万般恶毒与污秽的神性之物,充当照妖镜似的角色,查证每个参与者的内心深处,并将隐瞒真相者处以咒语中的极刑。
“lot”类小巫事非常多,有的由“专职巫者”操持,有的则由那些有点所谓“法术”的匠人操持。比如,“lot ghos”,汉字拟音:“咯果”,意思是:“咒骂淋巴结块肿痛”,基本上就由一些会点所谓法术的匠人操持。具体做法是,在太阳即将落山时,让患者站在门槛里面,面朝外,巫者站在门槛外侧。巫者用手指指着患处咒骂,咒词就是:“ghos xied,ghos das”,汉字拟音:“果修,果打!”反复叨念七遍或九遍即可,然后嘱咐患者一夜之内不能触摸冷水。
实际上,民间术士“化水”治病,用针刺稻草人、木头人或泥人诅咒所恨之人等等,都属于“lot”类巫事。
(8)“nbud”(汉字拟音:“卜”)类
“nbud”,在苗族日常用语中的语义是:“发作”、“萌生”等。
“nbud”类巫事,就是巫者通过唱诵巫经和实施相应的仪式,使自己魂身或是替身的魂身,进入鬼域,以完成巫事的功能。比如,探视被鬼怪掳走的魂魄关押何处,或了解作祟神鬼的心思,弄清楚事主的诸多不顺源自何种差错,要如何解除等等。上文说及的“nbud goud niangx”,翻译成:“跳仙”、“走阴”、“跳七仙姑”等;“nbud gheud”,翻译成:“卜钩”,都属于这一类。
(9)“nbeud”(汉字拟音:“卜”)类
以“nbeud”为名称关键词的主要巫事有以下两堂:
一是“nbeud bab”,汉字拟音:“卜罢”,意思是:“卜粽子”。有的地方说,这堂巫事是祭祀毒蛇之类神灵,避免其祸害;又有的地方说,这堂巫事是祭祀屈原。巫事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巫经苗汉语夹杂。
二是“nbeud xid nux khead”,汉字拟音:“卜西努喀”,意思是:“祭祀一种栖息在森林里的雷神”。民间又将这堂巫事称作“nggud peat ndut”,汉字拟音:“孤怕堵”。
“nbeud”在苗族日常用语中的语义是:“轻轻地敲打”。在巫事话语环境里,语义是:“探问、占卦”。在巫事中,巫者的做法,是用其重要法器,苗语称作“ghob zeud”,汉字拟音:“果遭”,或“ghob kangt”,汉字拟音:“果抗”。进行时,巫者将其置于簸箕或地面上,以一仰一仆为“顺卦”,两仰为“阳卦”,两仆为“阴卦”。根据卦象断事。在操作巫事的过程中,巫者要多次进行占卜问卦。
实际上,所有的巫事都有“nbeud”这一内容。但是,以“nbeud”为名称关键词的巫事,有其特点,这就是事主与神鬼之间没有什么过节或冲突,举行巫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预测吉凶,及早安排迎福避祸的策略与方法。
(10)“zeib”(汉字拟音:“则”)类
这是一种通过献给神灵祭品,求得其保佑庇护、增添福禄的巫事,主要巫事有以下四堂:
一是“zeib gix zhangs”,汉字拟音:“则及长”,语义是:“祭战旗”。
二是“zeib jiul denb”,汉字拟音:“则就等”,语义是:“祭土地神”。
三是“zeib rud zeib bleat”,汉字拟音:“则入则扁”,语义是:“祭山崖森林之神”。
四是“zeib ghob jiangs”,汉字拟音:“则过将”,语义是:“祭师傅”。如,建造房屋时的“祭鲁班”等。
(11)“fux”(汉字拟音:“福”)类
“fux”在苗族日常用语中不太常见,多数用于庄严和睦的巫事语境,其语义是:“和”。
没有以“fux”为名称关键词的巫事,只有功能在于“fux”的巫事。例如,上文述及的“bot dongd nzeab”,汉字拟音:“保冬寨”;宗支之间进行的旨在缔结和强化盟约关系的苗语叫做“fud nqind”的巫事,都属于此类。
(12)“tead”(汉字拟音:“他”)类
“tead”在苗族日常用语中不太常见,多数用在诉讼断理的场景,其语义是:“退出”、“解除”。
以“tead”为名称关键词的巫事,事由都跟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神灵之间的官司有关。有三堂巫事:
一是“tead lis hneb”,音译:“它理内”,语义是:“白天举行的断理”。
二是“tead lis hmangt”,音译:“它理忙”,语音是:“夜晚举行的断理”,又称作“kob xid”,音译:“阔西”。
三是“tead lis qiub”,音译:“它理求”。语义是:“断姻亲之理”。
(13)“choud”(汉字拟音:“抽”)类
以“choud”为名称关键词的主要巫事是:“choud mangx jiad”,汉字拟音:“抽忙加”,语义是:“赶走不吉的鬼”。民间也称此类巫事为:“jit ghunb jiad”,汉字拟音:“挤滚加”,语义是:“驱逐不祥的鬼”。但这类巫事所针对的“不吉”是很多的。比如说,有人暴亡,造成阴森恐怖,得举办这一巫事;有鬼魅入侵,造成阴森恐怖,得举办这一巫事。
(14)“ntongt”(汉字拟音:“捅”)类
以“ntongt”为名称关键词的主要巫事是:“ntongt rongx”,汉字拟音:“捅融”,意思是:“讨伐龙”。实际上,上文述及的苗语叫做“beux bleat”(汉字拟音:“搏扁”)的通常翻译成“抢魂”的巫事,也属于这一类巫事。这是由巫者的“阴兵阴将”和事主的“阳兵阳将”组成联军,向龙神鬼魅发动进攻,将其打怕迫使其释放“人质”的巫事。
“ntongt”在苗族日常用语中的语义是:“讨伐”、“进攻”。
四、“巴狄”分类说明
如上所述“巴狄”是苗语“bad deib”的音译,其语义有三层:一是祭司;二是祭司主持的祭祀仪式;三是祭司在祭祀仪式上唱诵的经文。由于从业者唱经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须进行分类说明。
(一)称谓
1.自称
(1)用单音节词自称
“巴狄”用作自称的单音节词有两个:“deib”和“sheub”。在苗巫语境中,这是两个互为偶联的单音节语词。
“deib”,笔者用“狄”拟音;石启贵、麻树兰、石建中、吴晓东、陆群等专家学者,用“岱”或“代”拟音;在无名氏用汉字记录的苗族巫经《家先一宗》*该书的1984年抄本,由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苗族干部石化黔收藏。内容是苗语称作“tud ngas”的“招亡”,和称作“xid xiangb”的“安家先”。里面,用“悳”拟音。
“sheub”,笔者用“示”或“仕”拟音;石启贵在其《湘西文书》中用“叔”、“受”、“寿”等拟音;在无名氏的《家先一宗》里面,用“受”、“世”等拟音。
(2)用双音节词自称
苗族“职业巫者”用作自称的双音节的词有四个:“ghob deib”、“ghob sheub”;“bad deib”;“deib sheub”。
“ghob deib”和“ghob sheub”,是为了口语表述的顺畅,单音词“双音节化”,而在“deib”、“sheub”的前面附加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前缀“ghob”形成的。未见有前人对其进行拟音。如果要拟音,只要在“deib”、“sheub”的拟音之前加上拟写“ghob”的汉字即可。笔者通常用“果”、“仡”等拟写“ghob”。
“bad deib”,笔者用“巴狄”拟音;石启贵、麻树兰、石建中、吴晓东等用“巴岱”或“巴代”拟音。
“deib sheub”,是将两个互为偶联的单音词自称叠加在一起形成的。在《家先一宗》里面,用“悳受”拟音;在石启贵记录的苗巫资料里面,用“代寿”、“督叔”等拟音。
(3)用三音节词自称
“巴狄”用作自称的三个音节语词有三个:“bad deib xiongb”、“bad deib zhal”、“bad deib lel”。在民间用语中,还有“bad deib nieax”这一专指有法术的猎户渔夫,“bad deib nux,bad deib ncoud”这一专指占卜法祖,但这些称谓的巫者负责的巫事,截至目前的资料没有记述。
“bad deib xiongb”,这一自称只有用苗语唱经的巫者才能使用,笔者用“巴狄熊”拟音;湖南苗族学者用“巴代雄”或“巴岱雄”拟音。
“bad deib zhal”,这一自称只有用汉语唱经的巫者才能使用。笔者用“巴狄扎”拟音;湖南苗族学者用“巴代扎”或“巴岱扎”拟音。
“bad deib lel”,这一自称只有苗语称之为“lel”的田氏的巫者才能使用。笔者用“巴狄莱”拟音;其他研究苗巫的专家学者未见对这个自称的表述。
很显然,自称以“deib”为中心词。“deib”是苗巫文化最为重要的基础概念。
2.他称
他称有两种:
(1)以自称作为他称
有两种情形。一是双音节词的自称作为他称,只能用以上自称中的一个:“bad deib”。二是用三音节词的自称作为他称。以上三个自称都可以用。
(2)以汉语词进行他称
有两种情形。一是民间使用的他称:“苗老师”或“苗老司”;二是专家学者使用的他称:“祭司”、“巫师”、“巫者”。
3.尊称
(1)巫者对其师尊的尊称
“巴狄熊”对师尊的尊称,以一个专用的词:“goud”为核心,加上师尊与巫者的亲缘辈分称谓,以及师尊的名字,共三个语词组合而成。例如,按照亲缘辈分,师尊若是属于巫者的“叔伯”一辈,名字叫做“老元”,那么,巫者在叙述时是师承关系,对其尊称就是:“goud mat leud yanx”,汉字拟音:“勾玛老元”。
(2)民间对苗族巫者的尊称
有两种情形:一是在神圣的苗语巫事环境中,通常称作:“minl jiangs”,汉字拟音:“名将”,语义是:“大师”、“总司”。二是在一般对话语境中,通常称作:“sid fud”,音义与“师傅”相同。这可能是汉语借词。
(二)师傅及阴兵阴将
1.“巴狄熊”
(1)师尊
所有师尊没有固定法号,也没有师门字辈;一个具体巫者的师傅体系,排列以巫者为中心,大体按照直接授法在前、间接授法在后的方式进行;具体称谓组成模式是:尊称词“goud”+“师徒在亲缘上的辈分关系”+“师者名字”。譬如说,巫者麻道的直接授法师傅的名字叫做“龙正德”,按照姻亲关系,麻道应该称呼他“外公”,那么,麻道在叙述自己的师傅体系时,就要将“龙正德”放在前面,称之为:“goud dab leud dex”,汉字拟音:“勾大老德”。
(2)阴兵阴将
苗语称之为:“kob”或“ghunb kob ghunb deib”,大体上有六个兵种,分别负责不同的事务,建制单位是“三千,三百”,在经文中表述为“bub canb ghunb kob,bub beat ghunb deib”。
一是负责礼待祖先和征伐的,叫做“kob youd kob ncheat”,汉字拟音:“课尤课蚩”。
二是负责抓捕缉拿的,叫做“kob noul kob dat”,汉字拟音:“课耨课打”。
三是负责占卜探问的,叫做“kob shad kob nes”,汉字拟音:“课沙课乃”。
四是负责探查寻找的,叫做“kob tud kob chat”,汉字拟音:“课图课查”。
五是负责招龙迎凤的,叫做“kob rongx kob nceut”,汉字拟音:“课戎课草”。
六是负责护法断理的,叫做“kob qiod kob lis”,汉字拟音:“课敲课理”。
(3)本命元神
苗语称作“guib xiand guib deb,guib mos guib gied”,汉字拟音:“鬼仙鬼代,鬼末鬼家”。本命元神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巫者周身器官,如脚板、脚趾、小腿、大腿、阳具、小腹、心脏,甚至头发、指甲等等,本命元神都是独立存在的,是巫者本命元神群体中的个体。
(4)占卜法祖
占卜时必须迎请的“巴狄熊”法祖:
Jiul bul bad deib nux,
大山之巅的“巴狄傩”
Jiul denb bad deib ncoud;
大地边缘的“巴狄蚩”
Deb longb dongs bul,
“代弄董布”
Deb ghueas dongs denb;
“代歡董邓”
Deb nqianb bad nux,
“代箭巴傩”
Beb xid bad reas。
“代西巴冉”
2.“巴狄扎”
(1)师尊
有两大部分:祖师;本师。
祖师又分两种:一是权力体系的祖师,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王母、佛祖、三元将军等凶猛战将、三山五岳神圣、天地精灵等神话人物;二是法术体系的祖师,有“天传天教祖师,地传地教祖师。阴传阴教祖师,阳传阳教祖师。茶中茶教祖师,酒中酒教祖师。香中香教祖师,梦传梦教祖师。自传自教祖师,三十六教祖师。”[7]P140
本师。巫者称本师为“师父”。称谓有固定格式:师父的“汉姓”+“法名”。如“烧香奉请传度师父吴法德、师父吴法旺、师父吴法清、师父吴法桢、师父无法高、师父吴法得、师父吴法雷、师父吴法灵、师父吴法贞、师父龙法兵、师父廖法通、师父石法桢、罡曹师父人等。”[8]P140
(2)身份与自称
巫者在本门“巴狄”中的身份是玉皇门下的“臣子”,具体官职是“元帅”或“将军”;在法事语境中,巫者自称“弟子”或“小臣弟子”。
(3)阴兵阴将
巫者似乎没有自己掌管的成建制的“阴兵阴将”。行巫时,巫者是借用“黄帝”第九个儿子统领的“九州”兵马,即东南西北中五方兵马,以及“三元将军兵”[9]P119-120
3.使用苗汉语夹杂经文的“别类巴狄”
这些巫者,包括“巴狄莱”,操办“杨家吃牛”、苗语称作“nbeud bad”的“报粽报新”的“巴狄”。
(1)师尊
此类巫者的师承体系,虽有“巴狄熊”影子,但更多的是“巴狄扎”的特点,间或还有佛的神祗在里面。
(2)阴兵阴将
此类巫者几乎没有自己统率的成建制的阴兵阴将。他们是通过依附并请来“太上老君”、“如来佛祖”、“凶猛鬼魂”、“有术本师”等,站在“身前身后”,支持自己,而获得法力。
(3)经文
使用的多数是篇幅较大的口传经文。经文采用“巴狄熊”的基础架构和经文格式;很多经句是从将“巴狄熊”的苗语经句翻译成汉语。
(4)法式
所使用的法式,有些是“巴狄熊”的,有些是“巴狄扎”的。
[1][2]凌纯生,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3][7][8][9]石启贵.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5]吴荣臻,杨章柏,罗晓宁.古苗疆绥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6]吴晓东.苗族祭仪“送猪”神辞[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杨正万
NotesontheWitchcraftClassificationoftheMiaoPeopleoftheEastDialect
MA Yongbin
The Miao people’s witchcraft is the most sacred ancient culture, whose classification is a fundamental job for survey and research. The folk and expert classifications have their own shortcomings. Based on seven typ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notes on the classification by means of the most extensive folk concept and the Miao witchcraft knowledge system. Meanwhile, Badi, the core content of Miao witchcraft, is illustrated by types.
Miao witchcraft; Badi; knowledge system; classification; illustration
B99
A
1003-6644(2016)01-0001-22
——以凯里地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