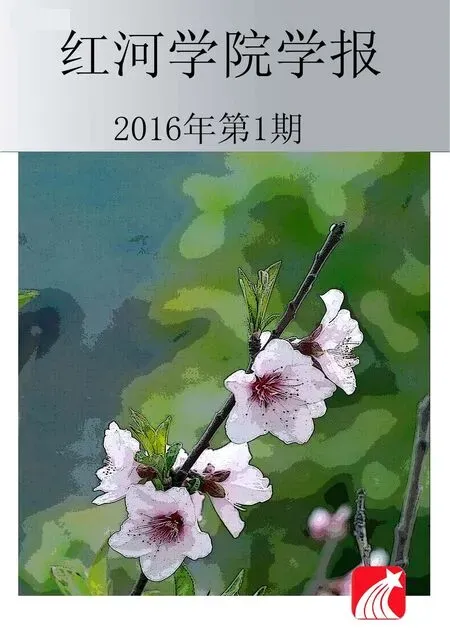《美国万花筒》中的人机互渗现象
刘 岩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昆明 650224)
《美国万花筒》中的人机互渗现象
刘岩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昆明 650224)
评论界对唐·德里罗第一部小说《美国万花筒》的主人公大卫·贝尔的主体身份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文章从贝尔身份问题的二重性切入,结合学界有关人机/技关系问题的讨论,通过分析主人公大卫·贝尔与小说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电视和摄影机等现代媒介机器的关系特征,认为贝尔的主体身份问题之所以引起两种对立的解读,是因为后现代文化环境下人机互动变得深刻复杂,并进而提出《美国万花筒》捕捉并呈现了人机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人机互渗,理解和把握后现代文化环境下人机互渗现象是理解德里罗小说另类主体重建的前提。
唐·德里罗;主体身份;人机互渗
无论就作品主题、叙事技巧还是文学意象与感性而言,《美国万花筒》都堪称德里罗后续小说作品的序言。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大卫·贝尔在当代饱受媒体影像浸淫的文化环境中探寻个体和民族身份的故事。身份探寻是美国文学经典母题之一,但是主人公大卫的身份探寻之旅却不同于传统的出逃——回归模式。围绕《美国万花筒》主人公大卫·贝尔的主体身份问题评论界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一些评论从后现代视角出发,认为置身美国后现代社会的贝尔丧失了主体性,犹如行尸走肉。如Robert Nadeau 认为该小说佐证了“正统独特的自我在当代已被排挤得不复存在”这一观念已成定律。[1]165与之类似,David Coward 认为该作品对于主人公“能否于无数个面具中确定那个是真正的自我语焉不详”。[2]133另一些评论从浪漫-超验主义视角出发认为贝尔是超验主义式的主人公。Michael Oriard 评论道:“《美国万花筒》一开始就是关于灵魂对意义的求索”,[3]6Benjamin Bird 认为主人公贝尔“具有自我指涉意味的叙事者身份让叙事成为可能”。[4] 188本文从贝尔身份问题的二重性切入,结合学界有关人机/技关系问题的讨论,通过分析主人公大卫·贝尔与小说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电视和摄影机等现代媒介机器的关系特征,认为贝尔的主体身份问题之所以引起了两种对立的解读,是因为后现代文化环境下人机互动变得深刻复杂,并进而提出《美国万花筒》捕捉并呈现了人机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人机互渗,理解和把握后现代文化环境下人机关系的互渗现象是理解德里罗小说另类主体的前提。
一 人与物之间(机器技术与人互为隐喻)
20世纪下半叶当代技术发展尤其是媒体影像技术悄然改变了当代人置身的文化环境,传统意义上的现在与过去、先天与后天、虚拟与实体、仿真与现实和主体与对象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作为人造物的技术机器越来越深刻地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乃至影响人们认知和心理。技术机器到底是什么?我们与机器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小说对机器本质和人机关系的反思往往采用了科幻题材这一形式。David Porush 在其科幻小说研究专著《温柔的机器:科幻小说》(1985)中指出作为人造物的机器具有双重语义:“机器反映出作为理性文明、会思考能表达的人的生存悖论。一方面,机器代表着宿命主义和先验性,就连我们从实证当中得到的用来描述世界与自身的模型也是先验可知的。另一方面,机器表现出人的创造力和自由。”[5]13技术宿命论认为人的意识心理是由外部技术环境决定的,这样一来人的主体地位被削弱。早在1964年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指出:“技术改变的不是人们的观点理念而是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不断地改变了人们的感官理性或理解的模式。”[6]33如果说机器的发明与使用削弱了主体的价值,那么同时机器作为人造物则代表着弗洛伊德所说的“满足了人们的原始的渴望”。[7]736《美国万花筒》中的主人公大卫·贝尔与其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机器—电视机和摄像机—之间恰恰体现了这种悖论:一方面他深深意识到自己深陷媒体技术无法自拔,媒体技术的浸淫促使他自省道:“电视广告改变了人的意识,让我变成了他。”[8]270另一方面媒体技术媒体技术机器寄托着人的超越心里,如贝尔认为摄影机代表着“发明原始”。[8]238-283
Donna Haraway 是较早注意到科幻小说中反映出来的人机互动的现象学意义。在《电子人宣言》一文中她指出:“到了这个神奇的20世纪下半叶我们都成了喀迈拉,一种机器与有机物的混合体,简单说我们成了电子人。电子人就是我们的本体……融合了想象与现实。”[9]150在此基础上Haraway进一步指出机器的本质,“机器并非没有生命,被人膜拜和主导。机器就是我们,是我们生命旅程的一部分,反映出我们人的某一方面。”[9]180如果说Donna Haraway 敏锐地洞察到现代人日常生活环境的变化,Lisa Yaszek (2002)则在分析埃里森、品钦和其他科幻小说作品中的人机关系后,指出20世纪新技术发展在两个意义上颠覆了启蒙时代以来的人文主体。“首先,在技术变革背景中人体成为外部环境与心理意识之间的介导不再是保护性躯壳,这样一来新技术挑战了传统人文主体的定义。其次,随着人体成为可渗透的界面人机互动仿佛取代了感官体验成为主体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源点。”[10]1
二 技术机器反客为主
后现代文化环境尤其是组成这个人造然环境的技术与机器在德里罗的小说中不仅是人物生活中的道具,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还是神秘的场域、时空的漩涡和人物身份的凸面镜。对于德里罗小说的人物来说,摄影机、电视、电话、电脑互联网和核武器不光是物质对象客体,还是意识现象,引发行动、影响感知、融入人物的记忆和欲望,参与主体重塑与建构。小说一开篇介绍主人公贝尔的生活和工作都已经高度“电视化”了。贝尔的父亲是广告界大亨,他常常让贝尔观看新出来的电视商业广告以观察贝尔的反应,把贝尔当成了测试观众。长大后贝尔觉得“自己一生都活在别人的生活里”,[8]58又或者“你用别人的生活思考自己的人生,你的想象没有原创性,它要么是别人的想象要么近似别人的想象。”[8]130作为纽约电视台高管贝尔和他的同事们来说电视内外、真实与虚幻仿佛已无从区分。贝尔和同事们制作的电视节目内容无关真实,他们只是负责兜售影像。有一次贝尔接到任务去拍摄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该任务要求最好拍摄到暴风雪中的印第安人影像,不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到底如何。对于摄影机取景框来说暴风雪中的印第安人比安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印第安人更有价值。
《美国万花筒》中照相机和摄影机不仅贯穿了整个叙述,而且这类技术机器往往是作者反思个体和民族身份的触媒和起点。在小说开篇不久,主人公大卫·贝尔站在位于纽约的广告公司大厅里注视着一张拍自越南战场上的巨幅照片:
照片中央是是一个怀抱死婴的妇女,身后两侧站着8个孩子。孩子有的看着这位妇女,有的显然是对着镜头微笑并挥手。大厅中央一个年轻人单膝跪地正在调整焦距拍摄这幅照片。我在他身后站了一会儿那一刻令人难忘。一瞬间时空仿佛都消失了,照片里的孩子仿佛是对着照片前面的年轻人微笑挥手。这就是照相机的好处,它具有近乎宗教般的权威,仿佛能把人催眠,让镜头里的人和镜头外的人肃然起敬。我站在那一动不动,直到年轻人拍完了照片,好像我的任何细小的动作会打扰到那些身上缠着绷带的孩子进而影响了画面。[8]86-7
在这个场景中,相机镜头捕捉到了种种矛盾,但同时相机又消解了矛盾对立的基础。这幅摄影作品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拉到一起,它成了一个画框,通过这个画框越战受害者注视着带给他们伤害的凶手或者他们的恩主。薄薄的一幅画区隔了纽约和越南,穷人、富人,现在与过去,惨烈、庸常。贝尔站在年轻摄影师身后,感受到相机可以消弭时空,让纽约与越南,过去与现在,主人与奴隶,受害者和施暴者汇聚成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存在。此刻的贝尔犹如置身于另一个时空,这个时空由相机掌控。贝尔觉得他应该一动不动让年轻人把照片拍完,照片上妇女抱着死去的孩子对着相机,既像是祭礼又像是裁判亦或诅咒。相机捕捉到的这个场景还没有完结,在某个意义上还在继续。照片上战火中孩子仿佛穿越了时空,此刻就凝望着面前大厅里的摄像机。摄像机和拍摄的对象构成了电磁并向矢量,构建出两个平行的时空,这个独特的存在超越了自然生物法则和所有传统的时空概念。除了造就平行的现实,摄像机和摄影活动还意味着实现救赎。贝尔这样表述摄像机拍摄到的景物:“苍鹰略过天际,我把它从空中取下将它置于新的时空,这里没有过去也无所谓死亡。”[8]33转瞬即逝的动作被捕捉后进入另一个影像时空,这里苍鹰还是苍鹰,依然矫健翱翔天际。因为脱离了肉身的生死,影像反而强化了苍鹰的存在。如果说由于摄影技术的发明让天空中偶尔略过的老鹰无意间进入了另一个时空获得了一种永恒,那么在有意识的人那里摄像机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和满足人类对永恒的渴望和追求。贝尔在超市停车场偶遇几个购物出来的妇女,看到贝尔带着摄像机,她们马上摆出被拍摄的姿态,小说中德里罗借着贝尔的视线注意到:
她们好像意识到自己正在对自己挥手,心里想着要是哪一天需要拿出此刻在此经过的证据以打消自己的疑虑,那么她们就会想起此刻一卷胶片把她们定格在炎炎烈日下的城市广场。30年后的某一天在举证的那一刻,她们就会被投射到一块屏幕上,他们出现了,在泛着灰尘的光影里在一个超市门前七只手臂抬起来朝着老年的自己挥手,就像对健忘的回敬。如果确实需要证明她们此生来过,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吗?[8]254
这几个女人好像模糊地意识到在空洞的时间长河里生命无比脆弱。她们渴望被影像记录下来,透漏出她们意识深处的恐惧。她们觉得自己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庭、什么样的审判,什么样的法官和以什么罪名被起诉呢?其实心底里的莫名恐惧是担心自己从未存在过就无声无息地遁入时间的黑暗。而影像会为她们作证,证明她们真实存在过或至少曾经存在过,又或者至少她们留下了蛛丝马迹,影像比目击证人的陈述更可靠更容易被采信。影像将她们嵌入了时空,让她们复活成为客观的存在。从大学时代开始贝尔就拿着摄影机四处拍些实验类的片子,摄影机成了参见派对的必备装备,如同贝尔参与社交场合的道具。摄像机本省具有一种图腾般的魔力。在西部旅行途中贝尔在Ft. Curtis 小镇停下来筹备拍一部自传影片,如果说一开始贝尔的西部之旅是地理意义上,决定在小镇停下来拍片子之后,这趟西部之旅就开始按照摄像机散发出的“宗教般的权威”重新进行了校正。贝尔在小镇上取景,摄像机好像自身散发着一种魔力,当地人纷纷围拢了来。贝尔注意到“很快一群人就跟着我到处转”。[8]210摄像机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知道它的力量并且亦步亦趋。摄像机笼罩着的光环似乎扩散到了贝尔身上,在围观者眼中他不再是“大众媒体的一员”,转而成为“独立制作人”。摄像机赋予了贝尔遗世独立的光辉,让他从随波逐流的庸常当中超脱了出来。“不用流血,不用鏖战,摄影机在手就够了。”[8]241相机在手就等于掌握了认识现实的角度。只要贝尔相机在手,最后取景框里的人的去留就任由他裁夺。
三 人机关系新特征 :人机互渗
在麦克卢汉看来“所有媒介都是活跃的隐喻”,[6]64人类主体与技术客体之间过去常常被认为是不连续的,而隐喻结构让我们认识到二者之间是连续的。在Raymond Gozzi, Jr. 看来,有关人类意识和电子媒介关系的隐喻影响了我们的认知系统,这个过程“既是人性在机器上的外化也是人性对机器的内化”。[11]152这类复杂隐喻成为一个中心点,技术的悖论围绕着这个中心在主客两级之间摆动。在访谈集《多像一片叶子》(How Like a Leaf)中,Haraway 提出“技术科学是实实在在的符号”。[9]133她认为人与物之间的隐喻关系“不仅仅是隐喻”。[9]81Joseph Tabbi 受此启发,将其著作《后现代升华》的引言部分命名为“机器作为隐喻和超越隐喻”。在该引言中作者解释说:“技术产品本身可能就是人类思维的过程,所以在思考技术为何物的时候甚至隐喻这个对抗令人沮丧的事实终极文学武器都变得可疑起来。”[12]19人机交互现象模糊了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隐喻”一词本身变得不再适切。Tabbi 认为:“机器自身就构成了隐喻,它是一个代表着人类心灵与想象无法掌握和理解的身影,但是不管怎样毕竟人类亲手造就了它。”[12]20
德里罗小说人物与周围技术环境之间的关系隐喻不再是喻体和本体特征之间的单向映射,而是一种喻体和本体特征之间的双向映射。一天傍晚,大卫·贝尔回到家里冲了个澡后开始看电视,小说中这样描写到:“我看了一会儿电视,我开始意识到我离电视机大约一英尺,此刻就窝在椅子里看得很专注。我不知道电视里演的是什么,这并不打紧。离电视这么近以至于影像淹没在一片茫茫的点阵当中,但是电视就这样控制住了,我变成了电视机的一部分。我身上的组织和液体与电视屏幕上的点阵混合在一起。我就这样在电视前坐了约莫一个小时。”[8]43在这段描述中贝尔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控于《白噪音》中电视机发挥的那种“麻醉镇静作用”[8]16,电视之于贝尔不是单向的掌控,相反读者感到贝尔与电视机之间呈现出一种交融。虽然贝尔用被动的语气来叙述这个场景,“电视控制了我”,但是贝尔的意识显然超越了电视放送的内容,他试图理解的是此刻这一奇特情境的本质。这一段叙述不禁让人想起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电视影像随时要我们用鲜活的触觉感官来填补网眼之间的空隙,触觉是各种感官之间的复杂互动并非单纯的身体与物体之间的接触。”[6]273麦克卢汉用比喻的方式说明了人与环境之间互动想现象学意义。但是在上述看电视的描述中,贝尔并不是被动地去填补构成电视影像的点阵之间的罅隙,相反无生命是机器(电视)和人之间是一种互渗的关系。对于生活和工作都高度浸淫在媒体影像的贝尔来说,看电视就如同照镜子,镜子里映射出的自己的意识和欲望。
麦克卢汉在论及人技关系时曾断言:“我们成了我们的注视物。”德里罗小说捕捉到的人机关系则引导我们去思索人机各自特征的交互隐喻式的减数分裂:过去我们常常认为作为客体的机器是质匀、机械、被动和无机的而作为主体的人是有意识、主动的、有机的和智慧的。因此,接着麦克卢汉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注视物也正成为我们。传统的人机关系隐喻会说人变得像机器或者机器越来越像人。德里罗的小说中的人机关系则表明这种单向的表述无法表现出人机互动现象的全部特点,我们需要一个新语域来描述二者之间的双向复杂互动——人机交互隐喻,人机关系隐喻特点不是喻体特征朝向本体的单向映射与输送,而是喻体与本体特征间的双向交互映射,人机之间互为喻体和本体,形成人机交互隐喻关系。德里罗和品钦小说都探讨人机、技关系,但是品钦小说显然没有德里罗小说中典型的人机之间交互隐喻关系。在《万有引力之虹》中,品钦运用了工具性条件反射作为主人公泰隆和军事战争工业技术之间关系的隐喻。二战中,伦敦频频受到德国导弹袭击。奇怪的是,在盟军情报交换站工作的美国中尉泰荣斯洛索普和女人发生性行为的地点,往往就是德国导弹袭击的下一个目标。他喜欢把自己寻欢作乐的对象及其方位用各种颜色的星形贴纸标在一张地图上,而这些星星的位置和德国导弹轰炸的位置完全吻合。泰隆后来得知自己小时候被父亲出卖给拉兹洛 雅夫做实验:用G型仿聚合物作为刺激,产生条件反射的勃起,难怪自己在火箭降落于某个地点之前会产生强烈的欲望。这样一来泰隆的身体的一部分(阳具)和技术力量之间形成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到底泰隆的身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又在多大程度上被技术主宰。但是泰隆与技术之间还是可以划清界限:如果泰隆摆脱了条件反射,他依然可以做自由自在的风流浪子,就像《黑客帝国》里的Neo一样,一旦摆脱了超级计算机的控制依然可以做回自己。在《美国万花筒》中主人公大卫·贝尔有着和泰隆类似的童年经历。贝尔的父亲是广告界大亨,他常常让贝尔观看新出来的电视商业广告以观察贝尔的反应,把贝尔当成了测试观众。长大后贝尔觉得“自己一生都活在别人的生活里”[8]58,又或者:“你用别人的生活思考自己的人生,你的想象没有原创性,它要么是别人的想象要么近似别人的想象。”[8]130鲍德里亚把这种从机械条件反射到虚拟的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变描述为:“社会关系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控制没有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式的循循善诱而是代之以威慑:你就是信息,你就是社会,你就是事件本身,有无法开脱,你无所不包,诸如此类。”[13]29
四 结语
当代技术发展尤其是媒体影像技术悄然改变了当代人置身的文化环境,传统意义上的现在与过去、先天与后天、虚拟与实体、仿真与现实和主体与对象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美国万花筒》之所以在主体身份问题上引起双重解读,是因为德里罗对当代环境中技术机器尤其是电视机和摄影机等电子媒介与人的意识心里之间关系问题的描摹和理解。在德里罗小说中,人技关系呈现出技术-心灵交互隐喻性,即事物属性和本体价值在人物心里和电子机械物之间的双向传输。德里罗小说体现的人机间复杂互动隐喻是德里罗小说后现代主体重建的前提。
[1]Nadeau, Robert. Readings from the New Book on Nature: Physics and Metaphysics in the Modern Novel[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1.
[2]Coward, David. Don DeLillo: The Physics of Language[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3]Oriard, Michael. “Don DeLillo’s Search for Walden Pond.”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Don DeLillo. Ed. Harold Bloom[M].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2003:5-12.
[4]Bird, Benjamin. Don DeLillo’s Americana: From Third-to-First-person Consciousness[J].Critique 47.2 (2006): 185-2000.
[5]Porush, David. The Soft Machine: Cybernetic Fiction[M]. NY: Methuen, 1985.
[6]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M]. NY: Signet, 1964.
[7]Freud, Sigmun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Freud Reader. Ed. Peter Gay[M]. NY: Norton, 1989.722.71.
[8]DeLillo, Don. Americana[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
[9]Haraway, Donna.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M]. NY: Routledge, 1991, How Like a Leaf. NY: Routledge, 2000.
[10]Yaszek, Lisa. The Self Wired: Technology and Subjectivity in Contemporary Narrative[M]. NY: Rouledge, 2002.
[11]Gozzi, Raymond Jr. The Power of Metaphor in the Age of Electric Media[M]. Creskill, NJ: Hampton Press, 1999.
[12]Tabbi, Joseph. Postmodern Sublime: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Writing from Mailer to Cyberpunk[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Baudrillard, Jean.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M]. Sheila Faria Glas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责任编辑 贺良林]
Human-machine Inter-permeability in Americana
LIU Ya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There are double-readings about the subjectivity of David Bell the hero of Don DeLillo’s first novel Americana. It is held in this article that the double-readings result from the profound and complicated interplay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machin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ostmodern cultur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the article makes an analysis of such media machine as television and camera which function as more than mere material objects and concludes that DeLillo captures in Americana a kind of phenomenal human-machine inter-permeability, a new development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The new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s the premise on which the postmodern subjectivity is to be reconstructed against the postmodern society.
Don DeLillo; Subjectivity; Human-machine inter-permeability
I106
A
1008-9128(2016)01-0047-004
10.13963/j.cnki.hhuxb.2016.01.012
2015-04-20
201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项目: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小说主题研究(XKJS201410);2014年云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唐·德里罗小说研究(2014Y339)
刘岩(1976- ),女,吉林农安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