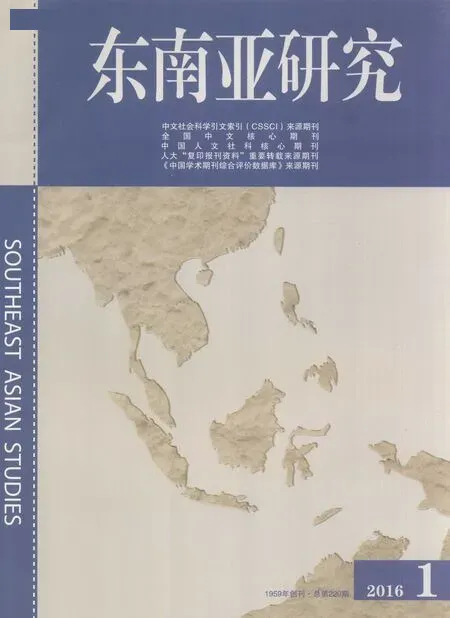缅甸包容性政治的建构:协和民主的适用性
项 皓 张 晨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缅甸包容性政治的建构:协和民主的适用性
项皓张晨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关键词]缅甸;协和民主;多民族国家;包容性制度;横跨性忠诚
[摘要]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当下正处在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因而如何建构一套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民主生根发芽,同时维护不同民族群体的利益是其面临的一大挑战。本文试图评估协和民主作为解决缅甸民族分裂问题方案的适用性。尽管协和民主在操作层面有一定局限,但其倡导的大联盟、精英和解以及提升民族间的交叉认同都能够促使多元分裂的异质性缅甸社会得到稳定。缅甸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成员,其国内政局的动荡和政治转型的进程值得我们持续地关注。
Abstract:As a multi-ethnic state, Myanmar/Burma is now undergoing a critical point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refore it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Myanmar to build a se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nation’s stability and democracy. This paper regards the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as an efficient solution to ethnic conflicts, the advocacy of grand coalition and overarching loyalty may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s. Myanmar is an essential member of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thus its domestic ethnic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worth our much attention.
自2011年文官政府掌权后,缅甸结束了长达49年的军政府统治,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但政治发展进程却饱受民族纷争的影响。截至2015年上半年,缅甸和平监察站的调查报告显示,缅甸政府军和民族武装组织仅在2015年1月到6月底就交火了231次。与缅甸政府军关系最紧张的是德昂民族解放军、克钦独立军和果敢同盟军[1]。频繁的战事严重影响到缅甸的政治转型进程。长期以来,研究第三波民主化和民族问题的学者都关注到民族问题和民主发展之间的关联,本文希望通过梳理民族与民主之间的逻辑和缅甸宪法中规定的制度设计来探讨在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协和民主条件下,缅甸的“民族—国家”和民主化是否能形成互补的逻辑,从而解决缅甸严峻的民族冲突问题。缅甸民主政治的建构涉及政府武装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停火,和平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具有包容性和妥协性、权力分享的政治制度,让民主得到社会各团体的理解和信任。
一多民族社会与协和民主的逻辑
对于多民族社会而言,建立和巩固民主制度是困难的,政治学家一般认为社会同质和政治共识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前提,也是民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多元民族社会中多样化的文化、宗教和地域等差异,往往会给民主政权带来不安定因素。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族群冲突和族群暴力的急剧增加又佐证了这样一种认识。于是,研究分裂社会和宪政制度设计的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严重的民族分裂对民主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这种社会里建立和稳固民主政府要比在同质的社会中困难很多。反过来,学者们也认为在民主尚未建立的国度中,民族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分裂要更加严重。第三个得到广泛认同的结论是,在分裂社会中建立一个成功的民主政府需要两大要素,即权力分享(power sharing)和群体自治(group autonomy)*参见A. Lijphart,“Constitutional design for divided societie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5,No.2,2004,pp.96-109.权力分享是指政府的一种制度模式,即保证各少数民族在参与政策制定时都有自己的代表和发言权;群体自治是指保证少数核心族群至少有本地区的区域自治权力(group regional autonomy ),见Lars-Erik Cederman, Simon Hug, Andreas Schadel & Julian Wucherpfennig,“Territorial Autonomy in the Shadow of Conflict: Too Little, Too L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9,No.2,2015,pp.354-370.。基于此,为了安抚各民族的利益纷争,宪政设计者尝试通过一些途径减少冲突,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聚合机制*参见Donald Horowitz,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以及霍诺维茨之后的著作和文章。,第二种是协和机制*参见A. Lijphart,“Consociational Democracy”,World Politics,Vol.21,No.2,1969,pp.207-225,以及利普哈特1969年之后的著作和文章。,第三种是隔离机制*参见Chapman, Thomas & Philip G. Roeder,“Partition as a Solution to Wars of Nationalism: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1,No.4,2007,pp.677-691等。。在细节的设计和认知上,三种模式各有利弊,但都特别关注到中央权力和地方自治的关联。缅甸的民族构成(如地理性集中)和历史传统都有实行利普哈特“协和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有利条件,因此这里考察的是协和民主在缅甸的适用性。利普哈特所提出的协和民主可以通过四个特征来进行界定:首先是由多元社会各重要区块的政治领导人组成大联盟(grand coalition)政府。其二是相互否决或协同多数原则(mutual veto),这种设计是为了额外保障关键少数的利益。第三,是在政治代表、公职任命和公共财政配置方面,坚持比例性原则(proportionality),也就是运用“多议员选区-政党公开名单-比例代表制”,即在政党名单上,选民有权选择候选人的当选顺序,选举结果最终根据选民投票的比例决定。第四,在每一区块上实现高度的自治(segmental autonomy),尤其是在文化和教育事务上,由民族地方自身决定。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则在于,国家的行政区域规划应当体现“同质性”原则,让一个行政区域内的民族构成尽量单一化[2]。
利普哈特的协和民主思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次提出,21世纪之后,通过对全世界各大洲民主政体的详尽考察,利普哈特又提出“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事实上,两者都是主张分享权力的“非多数民主”模式,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们主张的特征也有一些重合之处。但是,协和民主主要是以社会的种族、民族分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分野为前提的;而共识民主关注的焦点并不局限于民族与种族,还包括宗派、财富、阶级、地域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视野更加广阔,而且适用于更多国家。第二,协和民主是一剂猛药,它要求将所有重要的社会集团都纳入到分享权力的过程中来;共识民主则要温和一些,它提供了各种制度上的诱因,旨在通过这些诱因来促成广泛的权力分享。第三,反映在制度设计上,共识民主赞成比例代表制和巨型联合内阁,但不提倡少数派否决权和局部自治[3]。因此,这里选用协和民主作为缅甸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多看重的是协和民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策略性,能够适应缅甸这种人口区块之间存在深层分歧且社会对于民主统一性缺乏共识的国度。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根据缅甸官方的数据,缅甸的民族分布比较庞杂,其主体民族缅族主要生活在交通、文化相对发达的中部平原和南部沿海地区,而少数民族则各自聚居在山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农业生产力较低。缅甸各民族分布情况可见图1。

图1 缅甸族群分布情况一览
资料来源:The Data Team, “An unfinished peace”,the economist.com,Oct.15th,2015,http://www.economist.com/blogs/graphicdetail/2015/06/myanmar-graphics
同时由于历史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各种原因,缅甸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也与缅族存在较深隔阂,加上政府一直没有特殊倾斜的民族政策,导致单一政策平等的表相后隐藏的是发展结果巨大的不平等,最终引发20世纪60年代以后缅甸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力量的产生。缅甸的民族纷争以及国家认同不强,重塑了缅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同时也对缅甸的改革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在理论分析上,多民族并不必然意味着民族矛盾。如果民族构成过于分裂,每一个民族都无法占有绝对优势,反而会促进民族之间的民主合作[4]。因此,尽管在多民族国家中,人口越多,政治就越加复杂,就民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也越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多民族国家中民主就不可能实现,这只是意味着必须对民主的规范、行为和制度等进行认真的设计,从制度上为民族主义和民主化进程搭建起通畅的渠道,这样才能解决缅甸的族群纷争和民主内在不兼容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协和民主如何能在缅甸这类多民族国家中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我们的假设是,在多民族的背景之下,协和民主的政策更具开放性,能认可平等的公民权;在政治议程当中,比例代表制可以更好地代表在空间上分散的少数民族,通过协和民主建立起一整套匹配的政策和协商方式,最终建立一种包容性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强调各民族群众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不会因其民族出身而得到不公正的待遇。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golu)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民主的多元化和有力的中央集权[5]。首先,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分散在社会中,包括民族的区块。其次,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关键在于也拥有有力的中央集权,这样国家才可以顺利推行法令,保护产权,进行公共投资以鼓励经济活动。对于缅甸如今的经济状况而言,协和民主的特性可以促进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建立,而正是这一点将使缅甸民主转型的进程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二协和民主与缅甸的民族国家建设
缅甸少数民族在独立时作为自愿加入、政治平等的群体签署了《彬龙协议》,希望建立一个联邦并实现各邦自治。1947年的缅甸宪法甚至有保障“每个邦在独立后十年都有脱离联邦的权力”的条款,然而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缅甸陷入无休止的内乱和纷争当中,事实上演化成了半联邦制的国家,甚至具有单一制国家的内涵,被一个叫做缅族的单一民族控制了联邦所有的国家权力[6]。一方面,政府积极要求将国家建设成为“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单一民族国家,在推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采取的是相对保守的族群政策。另一方面,缅甸内部众多的小族群则一直顽强抵制中央政府的“国家建构”政策。
对于独立后的缅甸而言,“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的任务都亟待展开。“民族—国家”概念暗示了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常常是孪生的过程,但是它并不代表民族建构一定和国家建构相伴相生。世界上存在有民族而无国家的案例,如巴勒斯坦和库尔德人,也存在有国家缺乏民族的案例,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复杂的案例。缅甸刚好是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都进展缓慢的一个国度[7]。
缅甸的统治者(从吴努到丹瑞)都希望借由民族建构来建立一个同质化的国家,进而完成国家建构。比如1961年10月吴努将佛教定为国教,选择宗教同化的方案,而奈温则将缅甸语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以统一语言文字的政策来创制单一制国家。这样的“国家建构”事实上导致少数民族被强迫同化,除了接受这一点,各少数民族只能付诸武装斗争,不断强化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吴努到奈温时期的政策及其效果表明,缅甸作为多民族国家,其内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是国家建构的严重阻碍。对于缅甸的少数族群来说,他们首先将自己看作是族群的成员,其后才是作为缅甸国家的公民。而在新军人政府上台后,缅甸少数族群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仍然得不到实现,因此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抗争从来没有真正停歇过。
当我们系统地来观察缅甸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策略以及将协和民主运用到其间的可能性时,可采取林茨(Juan Linz)和斯泰潘(Alfred Stepan)的类型学分析框架来研究(如表1)。

表1 多民族政治体系中的国家、民族和民主建构战略的类型
资料来源:〈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8页。
根据国家建构战略和民族建构战略这两个维度,可以将一个国家的民主—民族策略划分成上述四个类型。这种划分不是固定和精确的,随着一个国家观念和政策上的变化,在这四个象限会呈现运动的趋势,如图2所示。
在类型I当中,政治精英对民族问题采取强烈的排斥态度,把非主导民族的少数族群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并且有可能通过一些歧视性的政策来隔离少数族群,通过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格逼迫其迁回原居住地。在类型II中,政治精英明确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区分,因此对公民资格采取排除性的战略,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中有立足之地,但国家政策只是给予非主导民族之外的人民以一定的公民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缅甸独立后实行的“一个民族”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种类型。民主转型前的军政府既没有在各民族之间培养出共同的国族认同感,也没有将少数民族同化和融合,这成为缅甸建立民主政府的一个巨大障碍。第III种类型是在公民资格问题中采取包容性的策略,结合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也就说,仍然存在少数民族与主导民族之间的区分,只有当少数民族融入到主流文化当中,才被允许进行政治性的参与。政治精英设计出很多同化的政策,但对于一些因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不能或者是不愿意被主导民族同化的人来说,在政治层面他们相当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这样造就了一个多样的社会,但并非是一个多元包容型的社会。在最后第IV种类型中,无论是对于国内主导民族还是少数民族而言,公民资格都是完全等同的。人民当中所有常住居民都被视为政治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政治精英给予少数族群以不同程度的政策照顾,这种政策倾斜体现在政党组建、宗教宽容和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这种社会可以被称为完全多元化的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也是协和民主期待建立的社会。

图2 民族—国家建构战略的类型变化
缅甸从军政府的独裁统治向民主政治缓慢过渡,目前我们从缅甸宪法中观察到的大约是从类型II向类型III的尝试,如宪法中规定少数族群也有表达、集会和组织的自由;少数民族可以组织政党(这一条其实在1990年大选中就得以体现);为少数族群在民族院中提供一定的席位;少数民族群众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来分享政治权利。因此,少数民族拥有进入政治体系的资格,文官政府也尝试通过同化来促成民族国家的构建。这种政策能否发挥理想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政治精英建设的目标,也取决于少数民族的成员是否准备好放弃对本民族认同的坚持。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由类型II退回到类型I的场景,即国家同化战略沦为失败,而少数民族在政治转型中成为被排斥的对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一是缅甸的少数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的利益需求及不满情绪能不能得到公开的表达。少数民族得到议席的保障并不必然促使少数群体中的个体得到特定的好处,因为在多数民主当中,少数群体获得的利益可能较小。而少数民族自身的愿望往往是要求实现类型IV中的模式,即得到直接分享权力的机会。其二,在国家层面,如果少数群体分成派系,拥有一定的代表资格,那么在选举和组建政府的过程中,多数群体就需要与少数群体结成明确的派系或是潜在的联盟,政治精英也需要得到少数群体及其代表的支持,在这种条件下,少数群体能够分享到利益最大化的政治权力。类型III的弊端在于由缅族主导的同化过程可能会导致其他民族产生挫败感,进而变得激进,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暴力冲突的恶性循环,从而威胁到民主的稳定和国内秩序的和平。而按类型IV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则能够孤立种族、文化和宗教少数群体中的极端分子(并不意味所有的极端民族冲突都可以完全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领导人大体上是依靠少数群体中的忠于国家的精英人士的支持,从而削弱极端分子对于整个政治社会的影响。如此一来,民主的理念也能得以巩固,因为民主政体将一切暴力活动都定义成不可宽恕的罪行,无论是在多数群体还是在少数群体当中。所以,民族暴力冲突将会得到妥当的处理并最终走向消亡。
由此看来,协和民主的基本主张在民族—国家建设层面可以部分促进缅甸的民族政策向稳定的类型IV转变,因为首先要建立的是一个包容各族人民的大联盟,让多元社会所有重要区块的政治领导人在大联盟中合作,进而治理国家。虽然大联盟达成共识的效率一直倍受怀疑,但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在关键性的过渡时期,都是通过大联盟平息党派之间的情绪并加强共识,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大联盟的实现需要很多前提,温和的态度和妥协的愿望是形成大联盟的先决条件,对于军政府非此即彼的同化性民族政策,缅甸上下必须形成妥协的愿望和精神。其次是赋予少数民族相互否决权,这也是保证大联盟的附带条件,只有这种否决权才能保证每个少数民族得到同等的政治保护。相互否决可以是一种非正式和不成文的彼此谅解,也可以是一种正式的宪法规则,连接了部分与整体的利益。一个民族过于频繁地运用否决权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为了提升自我和整体的利益,每个民族都会格外小心地使用这个权力。第三是在选举中充分保证各族人民的代表性。在缅甸各族力量分布不均的形势下,现行宪法中的比例代表制只是反映了各民族的力量对比,不能够消除决策中缅族与少数民族的对抗,比如尽管全国各民族兄弟大联盟(NBF)声称自己的成员要在选举中获得大约150个席位[8],但结果能否如意,充满变数。因此宪法可以考虑给予缅甸境内民族党派以超额的代表权,使得缅族不会在决策层面一家独大,因而起到制约的效果。最后就是民族自治,在少数民族专属的事务领域,由少数民族自己来统治,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财政按比例配置给各民族,少数民族地方的税收也要考虑到地方的特色。缅甸的自然资源集中在矿石和森林上,而这些又聚集于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政府的经济来源仰仗于此,因此必要的惠民措施也一定要施及此处。民族自治将强化一个多元社会的多元性质,为了保证国家不会四分五裂,缅甸的民主政府必须许诺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福利和更多的权力。
但是,针对缅甸的案例,实行协和民主也具有一定的困难。缅甸的人口构成中有68%是缅族,其后的两大民族是掸族和克伦族,分别只占总人口的9%和7%[9]。这导致缅族在缅甸的政治局面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又不完全拥有绝对支配的统治力量,从而阻碍了大联盟的形成。再者,缅甸的民族分野与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分层高度重合,这导致经济政治不平等和民族身份捆绑,社会其他方面的冲突都会轻易转化为民族冲突,从而动员大规模的群众参与进去。民族间的矛盾因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差异显得更为巨大。缅甸各民族在地理上趋于集中,并没有被水平的社会经济分化横切为“垂直”群聚,这样一个结构也被霍洛维茨称为“平行群体”[10]。因此少数民族彼此之间不愿意相互迁就,相互否决的机制可能会导致政治议程设定较为困难。最后一点就是缅甸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政治发展的阻碍(已有很多文献论述了经济水平与民主之间的关联,政治常在第三世界里呈现衰败和倒退的景象),“低度发展最大的讽刺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越低,其内在的不平等反而越大。”[11]但是缅甸特殊的国情也有适合实现协和民主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缅甸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都比较集中,例如克伦族在克钦邦占大多数,华人主要聚居在果敢,符合高度区块隔离的有利条件。如此一来,少数民族在地方具有一定权力优势,可以在每一个区划范围内实现高度的自治。
三缅甸实行协和民主应注意的问题
利普哈特的协和民主提出之后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同时也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政体转型和宪法设计,但是一些学者也“在借鉴国际学术界前沿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研究方法,从概念界定、研究设计、经验证据与因果机制四个方面入手,对共识民主理论进行系统的检讨和反思。”[12]因此对处于政治转型关键时期的缅甸,不加鉴别地将协和民主作为其宪政设计的模板可能会造成误导,但是协和民主所倡导的一些基本要素在缅甸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可取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转型与民主化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变革,作为一种精英统治制度,协和民主的成功实施,必须依靠执政精英们的表现。这些精英既要对自己所代表的族群有足够政治影响力,又要有善于妥协、积极合作的品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的选举制度要保证各民族地区之间代表性的平衡
赖利(Benjamin Reilly)在论文中提醒过,在民族冲突激烈的国家,选举制度的设计应当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13]。如果某一地区拥有明显的多数,其地方精英势力就可能试图支配敌对的少数,而不是选择与后者进行合作。比较权力的二元分化和极端的多元分裂可发现,适当的二元分化最能够适应政治的稳定和博弈,而二元化社会的问题在于它会导致霸权或者不稳定的平衡。高度分化的社会由于参与协商群体数量增加,它们之间的合作也变得更加困难。只有适中的多元结构才能避免政治决策被诠释为零和博弈。最合适的选举制度在于每一个民族都能关注自己的所得,但同时也能考虑到整个决策的代价。选举制度是复杂的宪政体系中的一个榫合,一旦出现差错,就会使整个体系趋于崩溃[14]。
2.建立区块化的多党体系
缅甸2015年大选中涌现了一批基于民族地方利益的政党,这种区块政党对于协和民主是有利因素,它们能够充分当好对应区块的政治代表,并具有与大联盟竞选领袖的可能性。关于政党体系和民主的质量,各方都有论述。多党制尽管有利于广泛地凝聚利益,但很可能也会加深内部的分裂,且多党制在决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方面也远不如两党制。从缅甸大选的结果来看,民盟和巩发党作为缅甸政坛深具历史渊源的两大政党,垄断了大部分选票;虽然给予少数民族平等自由的选举权,但少数民族势单力薄,没有联合起来,在政治上未能形成第三股抗衡的力量。这样纯粹性的“执政—反对”模式,有利于建立责任清晰的政府。民盟赢得了2015年大选的胜利,即将组建的受立法多数支持的内阁应当既要考虑到民盟和巩发党的利益,也要兼顾各少数民族政党的需求。
3.共建精英和解的传统
协和民主的本质是一种精英民主,如果政治领袖们致力于联合而不是对抗性决策,多元社会就可以享有稳定的民主政府。协和民主承认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且给予地方自治权,因此协和民主建立的前提就在于预先促成一个传统,让政治领袖采取温和与合作的态度,达成精英的和解。在军政府时期,由于政府对民族问题采取强硬的态度,导致民族间对立的情绪十分严重,但同时镇压的成本(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过于高昂,于是军政府开始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释放一系列妥协的信号,通过允许民主转型的制度和政策来缓和阶层及族群之间的矛盾,试图满足民众的自主需求。
4.促进交叉认同,建立横跨性忠诚
横跨性忠诚(overarching loyalty)是协和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统一政权的稳固有关键性的影响。在缅甸这样的多民族社会中,横跨性忠诚意味着各个民族都能认同和忠诚于一个更大的实体,国族认同是缅甸现代化和政治转型的一大目标。有学者早就关注到,在亚洲和欧洲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族群之间的深层分歧和统一性共识的缺乏,政治发展有两个维度的意向,其一是要实现国族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或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其二是要实现民主化[15],因而缅甸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是深刻依赖其国族整合的。在可能的范围内,缅甸的政治制度要能够激发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忠诚。单一的民族主义助长了民族地方武装的野心,并对整个国家的权威构成挑战,缅甸的分离倾向必须得到缓和与消除,否则中央政府将失去对领土和人心的控制。缅甸的少数民族分布在国家版图的边缘部分,这又容易引起外部争端,如果延续主体民族缅族带有挑衅性的民族建构政策,疏远少数民族,那么凭借地理位置的便利性,后者极易寻找邻国的支持,这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而“民族化国家—少数民族—境外祖国”三股势力相博弈的场域一旦形成,民主化进程必将受到极大的伤害。民主的一大内涵是强调公民而非国民,政治精英应当发挥自己的力量,促进包含多样和全面认同的国家观念向合法化方向发展,而不是加强公民资格的排他性。缅甸的民主转型要伴随更开放的国家政策,从宪法层面到实际操作层面,让平等的公民权利覆盖到更广阔的范围,使得各族人民的利益都能得到民主政府的保护,这样一来,民主巩固的机会将会大大增加。具体来说,在政治选举层面,缅族人民不能有过多代表(over-representation),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是平等的;在公民社会层面,学校和大众媒介允许民族语言的使用,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在法治层面,法律体系要考虑到地方的风俗和历史习惯;在经济社会层面,土地和资金分配在各民族之间也应该是公平的。综上所述,建立各族的交叉认同要求在民主化进程中充分避免大缅族主义,设计出更多具有共识性的政策,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
201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与相关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缅甸国内面临民主政权的稳固、民族冲突、宗教矛盾等多重不利因素,因此,对缅甸国家建构及其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应当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任务之一。目前,对于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其政治风险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主化改革带来国内政治稳定的问题。尽管现行的缅甸宪法对既有格局的稳定性做了一定的保护,但鉴于国内外民主势力的发展,改革引起的常规风险仍然可能对缅甸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二是缅甸的民族问题。缅甸的民族和宗教相互纠缠,一直是国家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与民族问题息息相关。协和民主有一套包容性政治制度的设计,缅甸政府可以参照协和民主的一些理念,从制度层面解决民族冲突,建立稳固而有效的民主政府,实现民主转型。
【注释】
[1] 林夕:《缅军和民族武装组织半年交火200余次》,缅甸在线,2015年6月28日,http://v2.myanmarol.com/News/Article/71343
[2] 〈美〉阿伦·利普哈特著,刘伟译《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一项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3] 同[2],译者前言。
[4] Reilly, B.,“Democracy, ethnic fragmentation, and internal conflict: Confused theories, faulty data, and the ‘Crucial Case’ of Papua New Guinea”,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5,No.3,2001,pp.162-185.
[5] 范世涛:《包容性制度、汲取性制度和繁荣的可持续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
[6] 〈缅〉连·H.沙空著,乔实译《缅甸民族武装冲突的动力根源》,《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4期。
[7] Monique Skidmore & Trevor Wilson, “Perspectives on a Transitional Situation”, Nick Cheesman, Monique Skidmore & Trevor Wilson eds.,RulingMyanmar:FromCycloneNargistoNationalElec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0,p.20.
[8] Moe Myint, “Ethnic bloc seeks powerbroker role in next parliament”,TheIrrawaddy, 22 July 2015.
[9] Network Myanmar, “The Union of Myanmar-Basic Data”, http://networkmyanmar.org/images/stories/PDF/stats
2009.pdf
[10] 关于这一说法可详见Donald L. Horowitz,“Constitutional Design:Proposals versus Processes”, in Andrew Reynolds ed.,TheArchitectureofDemocracy:ConstitutionalDesign,ConflictManagementand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9-24.
[11] Pierre L.Van den Berghe, “Ethnicity: The African Experience”,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Vol.23,No.4,1971,p.514.
[12] 包刚升:《共识民主理论有“共识”吗——对利普哈特研究方法的学术批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5期。
[13] Reilly, B.,“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ElectoralEngineeringforConflictManage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1,p.31.
[14] Reynolds, A.,“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in southern Africa”,JournalofDemocracy,Vol.6,No.2,1995,pp.86-99.
[15] Lucian W. Py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in Lenard Binder er al.,CrisesandSequencesinPolitical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117.
【责任编辑:吴宏娟】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Politics: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in Myanmar
Xiang Hao & Zhang Ch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Keywords:Myanmar;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Multi-Ethnic State; Inclusive Politics; Overarching Loyalty
[中图分类号]D733.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1-0023-07
[作者简介]项皓,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苏州大学老挝—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晨,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5-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