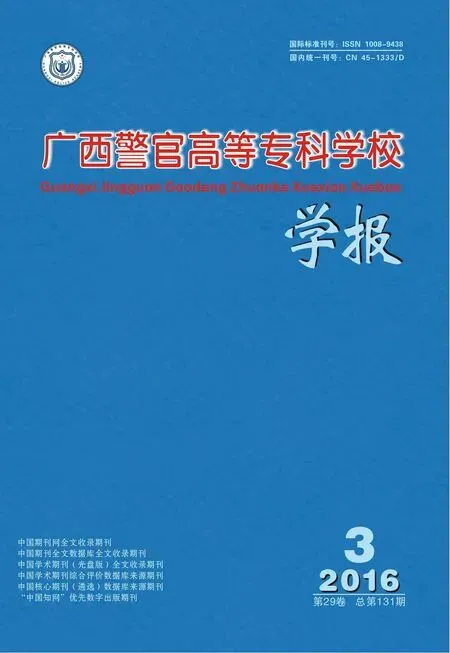暴行罪的立法审视与出路
陈文昊,郭自力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2206)
暴行罪的立法审视与出路
陈文昊,郭自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2206)
暴行罪缺位导致量刑畸轻畸重,故意伤害罪成为“口袋罪”,包容行为众多。寻衅滋事罪在实践中成为暴行罪的替代品。聚众斗殴罪地位尴尬,一部分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另一部分与寻衅滋事罪难以区分。暴行罪缺位使得暴行教唆行为认定困难,故意伤害中的“故意”内容言人人殊,虐待罪量刑畸轻,刑罚与行政处罚界限模糊。应当借鉴国外立法例,设立“暴行罪”,对以上各种问题颇有裨益。
实证研究;暴行罪;故意伤害
一、暴行罪缺位导致量刑畸轻畸重
案例1:被告人余某某与原告赵某系亲戚关系,2008年8月2日上午10时许,被告人因垫石灰坑问题与赵某某发生口角,在争抢铁锨过程中致使赵某某头部受轻伤。被告人辩解称:“我们争夺铁锨的时候无意中把铁锨甩她脸上了。”证人李某某证实:“两人开始争夺铁锨,因为余某某左腿装有假肢,争夺不过,就松手了。赵某某争夺铁锨时用力过猛,突然一松手,铁锨头就碰在她自己头上了”。法院认为,被告人余某某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①(2009)拓刑初字第116号。。然而,法院的判决有结果归责之嫌。被告人并无伤害故意,更无“暴行”行为,充其量仅有过失。而且,双方的亲戚关系也能佐证被告人不具伤害故意。
案例2:被告人王光宇自2008年起对其配偶董珊珊进行殴打、折磨、摧残,被害人多次逃脱无果。2009 年10月,被害人因医治无效死亡。诊断书上表明被害人“多发外伤;腹膜后巨大血肿;右肾萎缩性变形;头面部多发挫伤;多发肋骨骨折;胸腔积液;肺挫裂伤;腰椎1-4双侧横突骨折;四肢多发性挫伤。”主治医师张锋良称,收过这么多病人,从来没有见过打得这么惨的。“肚子里面都是血,快涨破了。最后在脖子这开了一个洞,放出的血一桶一桶地往外拎。”2010年11月28日,被告人王光宇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半[1]。一审判决后,北京大学郭自力、马忆南等专家出具专家论证意见书,认为本案被告行为已经明显超出虐待的范畴。但问题在于,一审法官李加表示,从现有证据来看,不能表明被告人的伤害故意,难以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暴行罪缺位使得以上问题的解决捉襟见肘,量刑畸轻畸重。笔者围绕该问题从实证与教义两方面切入,深度剖析暴行罪立法配置的必要性与妥适性问题。
二、我国无暴行罪,却有“暴行罪名”——之于实证视野
我国《刑法》并无暴行罪的设置,但单纯的暴力行为主要体现在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三个罪名之中。除此之外,转化犯中的暴力也可能构成犯罪,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事后抢劫。笔者通过对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三个罪名的实证分析窥探暴行罪设置的必要性。
(一)故意伤害罪量刑透析
一拳一脚,可能无罪,可能死刑。笔者以某省Z市①Z市为华东地区地级市,下辖4个区、3个县级市,人口约315万,全市面积3843平方公里。两级法院2012—2014年审理的故意伤害案件中选取201个样本,统计频数和频率(见表1)。

表1 故意伤害罪量刑幅度统计表
结合以上统计结果与其他现有文献来看,故意伤害罪的案件在我国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故意伤害罪定罪数量众多。以盗窃罪为参考系,2010年日本的故意伤害罪的判决数量是盗窃罪的21.26%,同年我国的故意伤害罪的判决数量是盗窃罪的67.7%。因此,以盗窃罪为参考系,我国故意伤害罪的有罪判决数是日本的3倍。第二,故意伤害罪量刑幅度广泛,呈正态分布之势。从刑种上看,故意伤害罪最轻可以定罪免刑,最重可判死刑立即执行。
这反映了故意伤害罪立法的弊端。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分为三档:基本情节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加重情节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再加重情节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质言之,犯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从管制到死刑立即执行之广泛,在分则中实属罕见。从比较法角度分析,故意伤害罪将大量国外刑法中的“暴行罪”纳入调整,使得故意伤害罪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兜底罪名”。
(二)越俎代庖的寻衅滋事罪
笔者以Z市两级法院2012—2014年审理的“随意殴打他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案件中选取100个样本,统计伤害后果(见表2)、犯罪原因(见表3)两项数据指标。

表2 寻衅滋事罪伤害后果统计表

表3 寻衅滋事罪犯罪原因统计表
②熟人纠纷包括婚姻、家庭、邻里等引发的纠纷。
从统计结果来看:第一,“随意殴打他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情形可能造成伤害,也可能未造成伤害;可能造成轻微伤,也可能造成轻伤。第二,“随意殴打他人”的入罪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以恪守。2013 年7月发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指出: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人需出于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无事生非的目的。但问题在于,从实证结果来看,该罪被作为故意伤害罪的兜底罪名加以适用。即在没有达到轻伤的情形下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案例3:被告人张某参与免费抽奖活动,感觉自己被骗。于2014年1月5日14时许,纠多人持香蕉棒前往活动现场,与员工薛某某等人发生纠纷,进而对薛某某等人实施暴力。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徐某某构成轻伤,薛某某构成轻微伤,法院认为行为人成立寻衅滋事罪③(2014)城法刑初字第26号。。问题在于,本案中的行为与出于“无事生非”和“流氓动机”的“随意殴打”本质上存在区别。
(三)聚众斗殴罪处境尴尬
笔者以Z市两级法院2012—2014年聚众斗殴罪中写明斗殴原因的137个样本,统计伤害后果(见表4)、犯罪原因(见表5)两项数据指标。

表4 聚众斗殴罪伤害后果统计表

表5 聚众斗殴罪犯罪起因统计表
由统计结果分析可得:从起因上看,基于琐事纠纷的聚众斗殴所占比例最高,达到46.72%;其次是基于积怨报复,比例为20.44%。问题在于,如上文所述,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原因在司法实践中不限于“无事生非”的情形,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陌生人间偶发的纠纷。如此一来,在实践中,多人寻衅滋事的情形不占少数,单凭人数多寡无法区分两罪。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聚众斗殴罪致人重伤、死亡的,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处死刑;而寻衅滋事罪最高只有5年有期徒刑。罪名的认定对刑罚轻重有重要影响。
因此,在犯罪原因上与寻衅滋事罪交互重叠,法定刑又远高于寻衅滋事罪。在此语境下,聚众斗殴罪的存废存在疑问:首先,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斗殴罪,一个从动机上、一个从行为样态上定界,难免有所交叉。其次,聚众斗殴罪第二款的转化犯规定是否妥当,在理论上也备受争议。
三、“暴行”缺位导致教义学内部不自洽
暴行罪的缺位不仅会造成罪名适用障碍,还会导致刑法教义体系的不相自洽。下文逐一进行分析。
(一)暴行的共犯问题怪圈
案例4:被告人宫某因为积怨准备好好“教训”被害人张某,其召集徐某等人,并请他们帮忙“教训”被害人。2011年12月22日,徐某等人在张某家楼下以棒球棍殴打张某、拿刀挥砍张某。张某被锐器砍击左膝部,导致左侧腘动脉、静动脉断裂而失血过多死亡[2]。
本案中,宫某成立故意伤害罪教唆犯的前提是其具有伤害故意,但仅凭“教训”一词认定宫某具有伤害故意难免草率。事实上,“收拾”“修理”“教训”“整治”“摆平”和“搞定”这些语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对于不同背景阅历、不同文化陶染的人而言,含义往往大相径庭。例如《红楼梦》第二十八回中黛玉对宝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3]。这里的“教训”绝对不可以理解为故意伤害。事实上,“教训”包含“教育”和“训诫”的双重含义,将“训诫”解释为“伤害”显然超出了语义的可能含义。但基于这种行为的应罚性,为了避免刑法对这种唆使行为威无所施,只得不当扩张语义解释。而在立法层面,暴行罪的设置完全可以妥善解决此类问题。
除此以外,在暴力作为转化犯必要情节的场合也存在体系不协调的问题。例如,甲盗窃财物之后,被害人A追逐甲时,知情的乙唆使甲对A实施暴力,未造成伤害结果。在此情况下,甲成立《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事后抢劫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乙的教唆行为应当如何定性。一种观点认为,乙也成立事后抢劫罪[4]。但是该观点同时认为,如果被害人A追逐甲时,知情的乙自己对A实施暴力,帮助甲逃跑的,成立窝藏罪。然而笔者不赞同这样的处理:乙唆使甲对A实施暴力的构成抢劫罪,最高可处死刑,乙自己对A实施暴力的仅成立窝藏罪,最高10年有期徒刑,这显然不妥。另一种观点认为乙不成立犯罪,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乙对甲成立事后抢劫的加担作用,按照该观点,如果被害人A追逐甲时,知情的乙用枪逼迫甲对A使用暴力的,也不成立犯罪,这并不妥当。事实上,在日本刑法理论中,乙成立暴行罪的教唆犯。但遗憾的是,我国刑法理论因为“暴行罪”的缺位在应对此类问题上捉襟见肘。
(二)故意伤害罪中“故意”之二难抉择
故意伤害罪中的故意是否包括暴行的故意?对此有两大阵营之对立。
1.两大进路之挫败
“结果加重犯说”认为,故意伤害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只要有暴行的故意。施加暴行未导致伤害的,构成暴行罪;施加暴行导致轻伤以上结果的,成立故意伤害罪。该观点存在问题,根据外国刑法理论,以无形方法不构成暴行罪,因而以无形方法伤害他人并造成伤害后果的不能构成暴行罪,只能成立故意伤害罪。在此情况下,便要求行为人对伤害有故意,这是该理论之不足。
“故意犯说”认为,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具备伤害之故意,仅具备暴行故意并不足矣。事实上,因为我国没有“暴行罪”的设置,在理论上要求故意伤害罪的成立必须具有伤害的故意。但是,该理论在设置暴行罪的国家导致罪刑不均:单纯实施暴行的,成立暴行罪;实施暴行导致重伤的,因为不具备伤害故意,不能成立故意伤害罪,只能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问题在于,在各国立法中暴行罪的法定刑一般高于过失致人重伤罪。结论便是,实施暴行造成伤害后果的比未造成后果的情形处罚更轻,这显然是不妥的。
由此可见,在暴行罪缺位的前提下,以上的两种学说在故意伤害罪的“故意”问题上扬汤止沸,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2.“伤害致人重伤未遂”系伪命题
我国理论对故意伤害罪中的“故意”可谓铢量寸度。一种观点认为,仅有轻伤的故意,而实际上未造成伤害后果的,不成立犯罪;而如果有重伤故意,未造成伤害结果的,适用故意重伤未遂的法定刑[5]。也有学者认为,未造成伤害结果的,适用故意伤害基本刑的未遂[6]。笔者对两种观点不以为然。
首先,除行为人具有明显伤害故意的情况以外,区分暴行的故意与伤害的故意既不可能,也不合理。例如,认为行为人想要切掉被害人的一根小手指就具有“轻伤故意”,行为人意图切掉被害人的一根大拇指就有“重伤故意”。但问题在于,其一,行为人不可能事前决定“切掉小手指”还是“切掉大拇指”。如上文所述,行为人通常仅仅具有“收拾”“修理”的故意。其二,行为人是具有“切掉小手指”的故意抑或“切掉大拇指”的故意不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证明。最后,切掉小手指成立轻伤,切掉大拇指成立重伤,由人体重伤、轻伤鉴定标准决定,一般人无法知晓洞悉。
“伤害故意”难以认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通过伤害结果“反推”行为人的故意。
案例5:2007年6月30日,被告人季某于公司锅炉房门口打开水时,与被害人汪某发生口角,相互推搡扭打。期间,被告人季某拎起身边一个盖有盖子的油漆桶甩向被害人汪某,泼洒在汪某身上,香蕉水起火燃烧,汪某和季某均被烧着。被害人汪某因高温热作用致休克而死亡。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季某有期徒刑10年[7]。从法定刑来看,法院显然认为行为人具有“重伤故意”,但这样的结论完全是根据结果“反推”故意得出的。事实上,种种证据表明,行为人不仅不具有伤害的故意,甚至不具有暴行的故意。
其次,认为成立故意重伤未遂的观点不符合刑法逻辑。《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质言之,造成重伤结果的,适用该加重情节。然而,“未遂”是指结果尚未发生,未达到既遂的犯罪状态。换言之,成立未遂意味着重伤结果并未发生。那么,“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未遂”一方面要求造成重伤结果,一方面否认造成重伤结果。这样的结论莫衷一是。笔者不否认结果加重犯未遂的成立,但问题在于,如上文所述,故意伤害罪中的“重伤”故意,无法认定。司法实践中只能根据伤害结果反推故意:造成重伤结果的成立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否则只能适用基本刑。
总结而言,故意伤害罪中的故意难以界定,导致实践中故意伤害罪的量刑畸轻畸重。而倘若设置“暴行罪”作为行为犯,故意伤害罪作为结果犯,则只需认定“暴行”故意,再根据伤害结果区分此罪彼罪,以克服上述问题。
(三)虐待罪孱弱、故意伤害罪威无所施
《刑法修正案(九)》在第二百六十条之一新增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但在笔者看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扩大了惩罚对象,却欠缺打击深度。因为该罪最高刑只有3年有期徒刑,即使在发生竞合的情况下法定刑也不及虐待罪。在我国,虐待罪量刑畸轻毫无疑问。在董珊珊一案(案例2)中,被告人仅被判处6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但诚如一审李法官所述,从现有证据来看,不能表明被告人的伤害故意,难以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斯言诚哉!在面对家庭成员的虐待行为时,《刑法》又显得弱不禁风。故意伤害罪的主观心态认定需要考察行为人与被害人有无仇怨等社会关系。因此,在家庭成员之间“伤害故意”的认定步履艰难。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中,虐待行为导致家庭成员遭受的身心损害很难达到轻伤以上程度。虐待罪入罪门槛高、“情节恶劣”语义暧昧、两年以下的基本刑畸轻,导致预防效果不佳。鉴于我国刑法立法缺位导致不能妥善应对虐童行为犯罪,有学者提出以日本的暴行罪补位伤害罪的不足,惩治故意伤害罪的未遂形态[8]。也有学者认为应引进暴行罪以严密我国刑事法网,使我国刑法实现由“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转变[9]。笔者认为,以上观点相当中肯。
(四)刑罚的阵地与底线被行政处罚鲸吞蚕食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的,予以相应行政处罚。这一标准使得故意伤害罪的立案追诉标准需要达到轻伤以上,否则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只能通过行政处罚来处理。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将伤情鉴定作为唯一的标准,仅仅根据伤害结果对行为性质加以论断。
从司法层面来看,仅凭司法鉴定结果认定罪与非罪存疑。一方面,如上文所述,虽然国外刑法一般将故意伤害罪视为结果加重犯,但在设置暴行罪的国家,行为人对暴行的故意是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必要条件。在此意义上,“唯结果论”存在缺陷。另一方面,我国对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分流尚不明确,在此前提下,一味依赖司法鉴定结果决定罪与非罪是不妥的。
刑罚和行政处罚是公法责任实现体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刑罚、行政处罚作为公法责任实现的两大支柱,在多元化的责任实现机制中易于发生交叉。在劳动教养已经被废除的背景下,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强制医疗和强制戒毒措施依然与刑罚并存,由此引发了刑罚与行政处罚如何衔接的关注。一般认为,刑罚以社会危害性作为责任实现的依据,而行政处罚以行为人的人格征表为关注核心,以行为人主观恶性作为责任实现的基础。如何实现刑罚和行政处罚的衔接与融合是刑事法律体系当下面临的重大挑战。显然,着重于行政处罚所带来的收益而过度使用,并不利于刑罚效果的实现。
从立法层面来看,暴行罪的设立实属必要。在我国,暴戾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难言不具可罚性,刑法中暴行罪的缺位壮了施暴者的胆。事实上,我国没有“暴行罪”,但存在诸多“暴行罪名”。如上文所述,基于“无事生非”“流氓动机”语义暧昧,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可罚的暴行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笔者认为,应该设置“暴行罪”,一方面可以对构成要件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寻衅滋事罪“兜底罪名”的诘难。就此看来,与其将暴行行为分流到行政处罚、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中加以解决,不如设置暴行罪为妥。
四、暴行罪的核心命题:秩序目的之达至
(一)国外立法中的一管之见
1.暴行罪的国外立法
《日本刑法典》中的所谓的暴行,只能是有形力行使,不包括无形力的施加。例如殴打、踢踹、搂抱等行为属于暴行,光线、电力、噪音等也属于暴行。暴行的本质特征在于物理力的施加。因此,恐吓行为、侮辱的言辞、催眠术等针对心理的影响力,即使使得对方身体出现了生理机能障碍,也不能成立暴行罪,而可能成立伤害罪。
对于暴行的定义,各国各地区存在不同,《瑞士刑法典》第126条将暴行定义为,“殴打他人未造成身体或者健康损害的行为”。《模范刑法典》第2111.1条规定,伤害他人身体未遂构成殴击罪,属于轻罪。除此以外,在德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均设有暴行罪的相关规定。国外刑法中暴行罪的规定体现了刑法对暴力行为“零容忍”的态度。
2.暴行罪与故意伤害罪的二元逻辑关系探讨
日本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暴行罪与故意伤害罪具有未遂犯与结果加重犯的二元逻辑关系。一方面,暴行罪是故意伤害罪的未遂形态。实施暴行导致伤害结果的情形下成立伤害罪,未造成伤害时成立暴行罪。出于明显伤害故意施以暴行,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成立伤害未遂,但由于刑法无处罚伤害未遂的规定,因此成立暴行罪。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故意伤害罪中至少有一部分系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
行为人仅有暴行故意,但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成立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例如,行为人以暴行故意,用石块扔被害人,石块并没有击中被害人,但被害人因为惊慌过度心脏病发作死亡,这种情形下也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死。
(二)“暴行罪”设置对教义学体系有所裨益
通过上文分析,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对故意伤害罪的认定模式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表述:
1.轻伤结果=故意伤害罪(轻伤)
2.重伤结果=故意伤害罪(重伤)
3.死亡结果=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在暴行罪的设计上,可以概括为:以殴打或其他非法暴力行为施加于他人身体,情节恶劣,但未造成明显伤害后果的行为。一方面暴行罪是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另一方面故意伤害罪是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表述各罪名之间的关系,对上述公式进行反思和重构:
1.至少具有暴行故意①如上文所述,暴行故意、轻伤故意、重伤故意无法区分,这里只需要证明至少具有暴行故意即可。+未造成结果=暴行罪
2.至少具有暴行故意+轻伤结果=故意伤害罪(轻伤)
3.至少具有暴行故意+重伤结果=故意伤害罪(重伤)
4.至少具有暴行故意+死亡结果=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5.明显的伤害故意②如上文所述轻伤故意、重伤故意无法区分,这里只需有明显的伤害故意即可,例如,行为人与被害人积怨颇深,难以化解的情况。+未造成结果=暴行罪
6.明显伤害故意+轻伤结果=故意伤害罪(轻伤)
7.明显伤害故意+重伤结果=故意伤害罪(重伤)
8.明显的伤害故意+重伤结果=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在暴行罪得以补位的情况下,上文列举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下面逐一加以剖析:
第一,使得故意伤害罪得以分流,克服“唯结果论”弊端,使得不具备暴行故意的行为脱逸故意伤害罪的范畴。在行为人并不具备暴行故意的前提下,以伤害结果定罪无疑不当扩大了处罚范围,量刑畸重,不利于人权保障。例如上文中抢夺铁锨时意外导致他人轻伤的情形(案例1),抑或将香蕉水泼洒在被害人身上导致其被烧死的情形(案例5),难以认定行为人具有暴行的故意,甚至存在成立意外事件的空间。
第二,将寻衅滋事罪中随意殴打他人的情形与聚众斗殴罪一并纳入暴行罪规制。如上所述,寻衅滋事罪与聚众斗殴罪面对诸多非难。一方面寻衅滋事罪作为兜底条款,处罚范围过宽。另一方面,寻衅滋事罪的“无事生非”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被曲解甚至规避(案例3)。更为重要的是,寻衅滋事罪最高只有5年有期徒刑;而聚众斗殴罪致人重伤、死亡的,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处死刑。实质上,两罪都是针对暴行行为的罪名,在处罚上如此大差别令人匪夷所思。
第三,暴行罪的设立使得暴行的教唆行为成立共犯。教唆他人对被害人施暴的,成立暴行罪的教唆犯。在实行者的行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教唆者也对伤害结果负责。例如,甲教唆乙“修理”A,乙导致A重伤的,乙成立故意伤害罪(重伤)的实行犯,甲成立故意伤害罪(重伤)的教唆犯。从表面上看,该处理与现行立法实践“殊途同归”,但实则大相径庭。在暴行罪缺位的情况下,“修理”一词只能一律被视为具有伤害故意,但并不妥当(案例4)。在暴行罪补位的情形下,“修理”被视为对暴行的教唆,但教唆者同时对暴行罪的加重结果负责。再如,甲盗窃财物之后,被害人A追逐甲时,知情的乙唆使甲对A实施暴力,未造成伤害结果。如上文所述,现有理论要么将乙认定为事后抢劫,要么不对乙定罪,导致量刑畸重畸轻。事实上,甲完全可以成立暴行罪的教唆犯,量刑在抢劫罪之下,这样的结论较为妥当。
第四,在暴行罪设立的前提下,不存在“故意伤害未遂”的逻辑悖论。因为故意伤害罪本质上是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倘若并未发生伤害结果,只能认定为暴行罪,而在暴行罪缺位的立法现状下,只能认为无罪,这显然不妥。也许有学者责难,认为将故意伤害罪视为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实际上还是结果归责,有悖责任原则。但要求行为人“至少具有暴行故意”本身从主观上对行为的入罪进行了限缩,并不违背一般人的预期。
第五,设置暴行罪,虐待罪量刑畸轻的困境迎刃而解。如上文所述,在现有司法实践中,往往因为无法证明行为人的“伤害故意”(案例2),难以认定故意伤害罪的成立。但事实上,只要行为人具有暴行的故意,且造成了伤害后果,就可以认定为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以故意伤害罪处罚。另一方面,在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情况下,由于涉及虐待罪与暴行罪的竞合,需要考察暴行罪的法定刑配置。笔者认为,就现有刑法文本而言,暴行罪的法定刑应当在虐待罪的基本刑之上。即暴行罪的最高刑应当在2年以上,才能克服虐待罪量刑畸轻的问题。
第六,暴行罪一方面将主观上不具暴行故意的行为出罪,另一方面将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情形从寻衅滋事等罪名中分离,纳入暴行罪调整。这无异于扩大了暴行罪的处罚范围,有利于避免将行政处罚奉为圭臬。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只要未造成轻伤,就一律纳入行政处罚的调整范畴的做法影响了刑罚的处罚效果。暴行罪的设置表现国家对暴戾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在刑事政策上具有重要意义。
五、刑法需要自我节制,更需要理性视野
刑法需要自我节制,但更需要以理性的视野自我调整。它的目光不可只停留在文本之上,刑法的视野应当包罗万象。之于解释者如此,之于立法者更是如此。
暴行罪设立的社会需求显而易见,但暴行罪缺位在我国的诸多缺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虽有增设“暴行罪”之呼吁,但可谓雷声大、雨点小,且在制度构建上往往立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缺乏整体观和体系观。在笔者看来,暴行罪的全面展开在我国是必要的,这一方面有利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避免畸轻畸重,一方面契合社会的实际需求。
当然,新罪名的设立应当结合我国的犯罪论体系,综合考量制度构建中可能出现的不协调以及如何规避的问题。将成文法的完善与落实相勾连,社会实效的衡量与法律宽严相济的考虑相结合,才能得到妥当的回答。笔者坚信,理性的思考只能通过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理性的法律应当引导人们理性地向前看。
[1]妻子遭家庭暴力致死丈夫行为如何定性[EB/OL].(2010-12-01)[2016-04-11].http://www.jcrb.com/pinglun/jrkd/201012/t20101201_473526.html.
[2]袁兴琴,李进“教训一下”一句话要了人命[EB/OL].(2012-11-02)[2015-03-12].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12/11/02/005294483.shtml.
[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94.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58.
[5]张明楷.故意伤害罪探疑[J].中国法学,2001(3):34.
[6]陈明华.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52.
[7]被告人季某过失致人死亡上诉案——兼论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与意外事件的区别[EB/OL].(2011-3-28)[2015-03-12].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210776.html.
[8]于改之.儿童虐待的法律规制——以日本法为视角的分析[J].法律科学,2013(3):174.
[9]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5.
责任编辑:蒋玉莲
[Abstract]The absence of crimes of violence breeds unbalanced sentence.Crimes of intentional injury turns to be a pocket crime,in which numerous acts are contained.The crime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s turns to be an alternative for crimes of violence in practice.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embarrassing crime of affray,part of which has converted to crime of intentional injury,and the other part claims to be hard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crime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s.The absence of crimes of violence makes it difficult to identify violence instigation and there are disputes as to the"intention"in crimes of intentional injury,giving birth to extremely light criminal sentencing as well as obscure punishment and administrative penalty.Accordingly,efforts need to be made to draw on legislation example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establiish the crimes of violence in the favor of the said problems.
[Key words]empirical study;the crimes of violence;crimes of intentional injury
On Legislation Review on Crimes of Violence and the Ways Out
CHEN Wen-hao,GUO Zi-li
(School of Law,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D918.92
A
1008-9438(2016)03-0025-07
2016-03-25
网络出版:http://www.cnki.net/kcms/detail/45.1333.D.20160519.1546.012.html
陈文昊(1992-),男,江苏镇江人,北京大学法学院2015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郭自力(1955-),男,河南焦作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