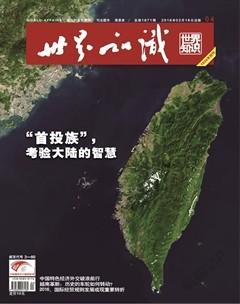利比亚政治过渡:五年后的从头再来?
唐恬波

在欧洲的利比亚难民。供图/东方IC
近期,利比亚的政治重建过程似乎有加速之势。2015年12月17日,在联合国和西方的强力斡旋下,利比亚东、西部议会代表和其他独立人士在摩洛哥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宣布将成立统一政府,以结束自2014年以来该国“两个议会、两个政府”的局面。根据协议,总统委员会于1月20日提名了由32人组成的内阁。可五天后,东部议会以压倒多数否决了该提名,理由是其成员过多,且资质不足、难以服众,要求总统委员会修改名单。新政府持续难产,折射了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过渡之艰难。而且即使新政府最后得以成立,似乎也只是让一切回到了卡扎菲倒台后的原点,只是2016年的利比亚已经没有了高油价的支持,却多了一群割据的军阀和一个残忍的“伊斯兰国”。
东西分裂和“二次内战”
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于2012年7月顺利举行了40多年来的首次大选,选出了作为临时议会的“国民大会”,也成立了临时政府。彼时,该国石油产量已基本恢复到2011年内战前水平,加之当时国际油价走高,令外界一度对利比亚的前景颇有期待。然而,由于临时政府的头面人物以亲西方的世俗派为主,但“国民大会”的多数议员是伊斯兰势力,世俗—伊斯兰阵营争权夺利,导致府会矛盾越来越大,严重干扰了国家政治的正常运行。更严重的是,利比亚一直没有建立统一的政府军,而是依靠雇佣不同的民兵或地方武装来维持秩序,结果各个武装借机壮大,逐渐控制了多地的治安甚至地方政权,并为了抢地盘、争资源而大打出手。
于是自2013年起,利比亚的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而且在2013年8月各地武装开始封锁石油外运港口后,利比亚的石油产量出现断崖式下降,拖累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13.6%。临时议会和临时政府对此无能为力,权威遭到极大削弱。2014年2月,世俗派将领哈夫塔尔声称应由自己接管国家,并武力进攻东部重要城市班加西的伊斯兰势力。同年6月,在一片混乱中,利比亚各方在联合国的推动下举行新议会选举,结果世俗派大胜,成立了名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新议会。然而,由伊斯兰势力控制的老议会拒不交权,自行成立“救国政府”。老议会和“救国政府”得到了米苏拉塔民兵的支持,被称为西部议会和西部政府。土耳其、卡塔尔与西部议会中的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等势力关系密切,因此尽管西部议会的合法性不受国际承认,但仍可获两国的支持。而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新议会则被赶出了首都的黎波里,被迫迁往靠近利比亚—埃及边境的东部城市图卜鲁格,原临时政府后来也迁往东部,在新议会支持下继续履职,两者被称为东部议会和东部政府。东部阵营在军事上主要依赖哈夫塔尔麾下的国民军和西部津坦民兵,哈夫塔尔更被东部政府任命为武装力量总指挥,并与埃及军方、阿联酋等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自2014年7月起,津坦民兵与米苏拉塔民兵为争夺的黎波里机场控制权开始进行鏖战,将利比亚拖入了“二次内战”。
和谈的主要动力始终是外力
2014年9月,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莱昂开始主持和谈,试图推动利比亚各方重新组成统一政府。但是,东部阵营坚持自己的“正统”地位,拒绝在未来的政治架构中给予西部任何实质权力,而西部阵营在为自己争取权力的同时,还坚持要求东部解除哈夫塔尔的武装职务。双方互不相让,谈判久拖不决。
而国际社会对利比亚乱局的容忍度则与日俱减。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和部分地方武装参与人口走私,使利比亚成为中东、非洲难民(以及经济移民)逃往欧洲的重要枢纽。随着难民危机深化,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急于稳定利比亚形势,使欧洲对利比亚的关注度明显上升。另一方面,自2014年10月以来,“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建立了稳定据点,势力不断壮大,使北非的整体恐情更趋严峻(比如,发动2015年突尼斯博物馆和海滩恐袭案的嫌犯都曾在利比亚受训),也对隔海相望的欧洲造成不小的威胁。受此刺激,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利比亚的外交投入,特别是欧盟努力推动联合国主持的和谈,甚至到了“威逼利诱”的程度:一边威胁制裁利比亚阻碍和谈的个人和实体,一边宣布一旦利比亚成立新政府,欧盟将马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然而利比亚各方恶斗依旧。到了2015年8月,人口只有600多万的利比亚,就有190万人急需紧急人道主义援助,120万人濒临食品短缺,43.5万人流离失所。2015年10月,莱昂推出联合政府组建方案,但遭利国内普遍反对,理由是分歧尚未解决,强行组建政府无济于事。而到了11月莱昂即将卸任之际,英国《卫报》曝光了莱昂与阿联酋外长的通信,显示莱昂涉嫌在和谈中偏袒与阿联酋关系密切的东部阵营。消息一出,利比亚舆论哗然,西部阵营尤为不满。但即便如此,由于另起炉灶的代价太大,接替莱昂出任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的德国人科布勒仍继续按照莱昂的方案推动和谈,一度也未取得进展。然而,2015年11月巴黎发生恐袭后,欧洲打击“伊斯兰国”的紧迫感进一步上升,急于在利比亚取得成果。12月13日,意大利外长真蒂洛尼和美国国务卿克里联袂主持高级别会议,17国外长、副外长与联合国、欧盟、阿盟、非盟代表出席了会议,要求利比亚各方尽快签署联合国拟定的协议。12月17日,利各方勉强在《利比亚政治协议》上签字。
可以说,利比亚和谈的主要动力始终是外力而非内因,利比亚国内就权力分配、哈夫塔尔去留等关键问题仍未达成共识,的黎波里等地安全形势极度败坏,实际上并不存在落实协议的条件。况且即便协议落实,无非也就是走制定宪法、全国大选、成立政府的老路,这其中的多数剧情,2011年以来利比亚其实都走过了一遍,但每步总是差强人意,最后终至不可收拾。五年的时间,利比亚跑了一个大圈,却似乎还没有回到原来的起点。
“伊斯兰国”的第三据点
自2014年春夏之交起,就陆续有利比亚籍的“圣战”分子从叙利亚、伊拉克回国,伺机在利比亚复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成功经验”。而且“伊斯兰国”也看好其在利比亚的发展前景,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特意派出高级助手协调、领导当地的武装分子。由于作战经验丰富、手段残忍,“伊斯兰国”势力在利比亚扩张迅速,在2014年10月攻占了东部海滨城市德尔纳(后被当地武装组织击败并撤出)。自2015年春起,“伊斯兰国”势力逐步占领了中部重要港口城市苏尔特,控制了附近200公里的海岸线,总兵员也增加到2000至3000人。而且与其他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本土极端组织不同,利比亚的这支武装从一开始就与“伊斯兰国”在伊叙的总部保持了密切的勾连。2015年下半年以来,“伊斯兰国”在伊叙战场受到的压力日益增大,流露出将利比亚作为退路的迹象——其领导层不仅向利比亚转移实力,还号召支持者赴利比亚“圣战”。
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了“伊斯兰国”在利比亚造成的威胁。根据外媒近日报道,美欧国家正在策划在利比亚开辟打击“伊斯兰国”的“第二战场”,这场预计由意大利领导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在未来数周内启动。据称,英国特种部队SAS已被派往利比亚,为即将到来的大约6000名美欧盟军士兵做准备。当前利比亚面临着与叙利亚类似的反恐困境,即明明知道空袭难以解决问题,但因为没有可靠的地面部队,目前也只能依靠空袭;希望尽快成立一个可以作为反恐伙伴的新政府,来提供这种可靠的地面部队,但联合国主持的和谈向来都不是以速度见长;考虑直接部署地面部队进行干涉,然而这不仅缺乏成功的先例,还恰恰符合“伊斯兰国”所渲染的“异教徒入侵”的戏码,从而有可能为该组织的宣传增添更多的煽动力。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