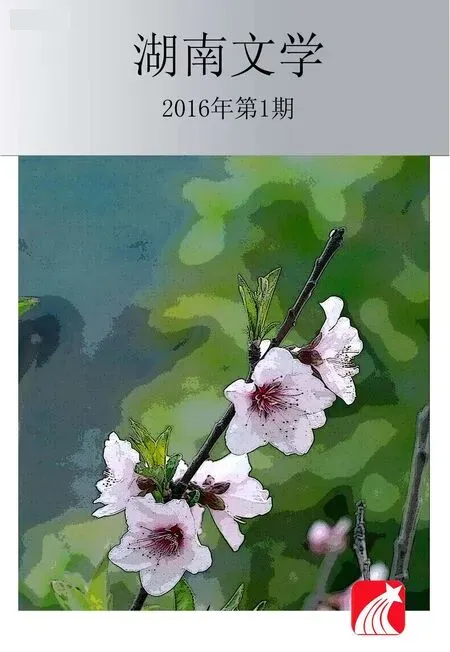菜孩子(外一篇)
→苏沧桑
菜孩子(外一篇)
→苏沧桑
冬至的曙光从窗帘透进来前,玉琴奶奶已经醒了。她本能地伸出左脚往另一个被窝伸过去,碰碰老头的脚,却什么也没碰到,只碰到了清晨五点半凉凉的空气。
老头在老家农村里。这是离老家一千多公里的儿子的家,城里的家。足尖的凉意让她缩回了脚,重新缩进被窝,感觉被窝霎时也冷了。
一千公里以外,老头会不会也像平时每天醒来一样,伸出脚碰碰她的脚,也碰了个空?
该起床了,带上小狗豆豆,给儿子、媳妇和宝贝孙子买早餐去,回来再叫他们起床。又会是一个忙碌的早晨。然后,他们出门,家里就剩她一个人,再过一会儿,连小区打扫卫生的阿姨们也离开了。楼道里,回响着电梯叮叮的回音,空调的嗡嗡声,像山谷回音,邻居们的门与门,像山与山,看似很近,走走却很远。
坐在阳台上,阳光暖暖地照上她眯缝的眼睛,脸慢慢热起来,但一种凄惶的感觉慢慢像水一样从脚底漫上来。此刻,老家村口的老槐树下,也会有这么好的太阳,老姐妹们坐在长板凳上,手里边做着事,边啃点南瓜子、红薯干,边扯着嗓子唠嗑,东家长西家短,舒坦。
她觉得自己像一棵树,一棵从老家地里挖过来的树,种到了城里阳台上的花盆里。她“漂”在城里,“根”却在老家。这里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弯腰风吹日晒,但就是不舒坦。
像她这样的“老漂族”,很多。离开老家,大多为了儿子、儿媳或女儿、女婿,为了与他们八分之一基因相同的小宝贝。报纸上说,在对三百名“老漂族”的调查中,大多老人认为子女对他们的重视不够,感觉很孤独,一半老人心里不高兴时选择憋着不说。
此刻,玉琴奶奶正在等待一个电话响起。今天太阳好,楼下的莲奶奶、楼上的牟爷爷,应该会叫她一起去买菜,或者一起去菜园。
菜园就在小区门口,是一大片待建的空地。听说原来是要建高楼的,被这个小区的人告了,造不成了,要重新规划,规划成什么还没定,所以就先空着。不知谁起的头,小区的老人一个一个偷偷地去圈地,渐渐地,一块空地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菜园子。种菜,仿佛成了“老漂族”们唯一的慰藉。
他们将废弃的泡沫箱、塑料桶、装修用的废旧铁皮桶都用上了,沤肥、储水,早上挑一点,晚上挑一点。玉琴奶奶第一次跟着莲奶奶和牟爷爷走进菜园时,仿佛看见自己重新走进了老家的春天里,那些花花绿绿呀,都是活的呀,老朋友呀,小孩子呀,蹦着跳着来认她。甚至,她隐约听到了母亲在跟她说话,看到地里的蒲瓜架下,闪过祖爷爷的身影。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一块菜地,她和素不相识的他们成了朋友,每天唠唠嗑,是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
玉琴奶奶最爱闻的气味,是从楼下菜地里飘来的大粪肥料的气味。自从她发现这一点,她心里有点慌——我怎么跟小区里那些保姆一样了?
小区的保姆阿莲说:“您不一样,您是东家。您看,天冷了,我们这些乡下来的保姆就懒得穿胸罩了,外套一套就出门了,你们虽然也从乡下来,但你们是东家,你们出门要面子,把胸罩穿在毛衣外面,再套上外套出门,回家一脱多方便。您瞧,连这一点事你们都这么聪明,怎么能跟我们做保姆的一样?”
电话一直没有响起。其实,儿子媳妇还没有去上班的话,玉琴奶奶特别害怕家里电话响起,尤其是周末,媳妇要睡懒觉,最讨厌有人打扰。她说:“你告诉他们别打了,你要是不说,下次要是再打过来,我自己跟他们说,让他们不要再打了!”
玉琴奶奶红着脸,跟他们说不要太早打电话给她。时间长了,电话就越来越少了。
一天,牟爷爷在菜园外的墙上,看到了一张可怕的布告。
“快来快来,要造房子了,让我们十天内把菜清理掉。”牟爷爷一口浓重的重庆腔,因着急,口音变得更难懂。他和老伴一起给女儿带孩子。老伴找了个小区食堂的活,他则无所事事,就去谋了一块菜地,花大力气平整完,播下了各式各样的种子,长势喜人,扁豆、青菜、丝瓜、青椒……地里种出来的蔬菜,成了每天餐桌上的绿色食品,吃不完,便楼上楼下地送,认识了不少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偶尔和儿子坐电梯,大家都牟爷爷、牟爷爷地叫他。
即使这样,牟爷爷也常觉得,这儿,终究不是自己的地盘,不接地气。两老早商量好了,等把孙子带大了,能住校了,就回老家,那里还有几分地,还有更老的老人,还有亲戚朋友。他也会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有时想得晚上睡不着。母亲八十多岁了,身体不太好,叔叔伯伯为方便照顾,把他们从老家接去了新疆。每每想起高龄的母亲,他总会沉默许久,眼眶里噙着泪水。
布告的大意是,这里按照政府规划,马上要打地基造房子了,所以,这片菜地过十天就要被处理掉了,你们赶紧该收的收,该拔的拔,不要再种了。
说良心话,这个布告还算有人情味的。
怎么办?怎么办?老人们急得团团转。肯定是那个坏女人又去告了。小区里有一个退休教师,老来跟他们抢地盘,一定要让他们分给她一块地。可是,这些地在老人们眼里,就像孙子那么宝贝,都是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呀,你要种,你自己去角落开垦呀,但她不,她打电话,去告状,说他们偷用小区地下车库的水,说他们施肥污染了小区的环境。老人们敢怒不敢言。怎么办呢?她到菜地里,这儿看看,那儿瞧瞧,终于,一位老人上前递给她一把青菜,说:“大妹子,你想要啥,自己拔吧。”她一点都不客气,说:“好!”就到每一块地里都拔了一些菜蔬,心满意足地走了。果然消停了一阵。然而,玉琴奶奶不会装,讨厌就是讨厌,对她从没好脸色。那天,玉琴奶奶在拔萝卜,她过来说:“这萝卜真是好啊。”玉琴奶奶就是不理她,当没听见,一直等她没耐心地自己走了。时间久了,她自然看得出人们的嫌恶,她一来,大家一声不响,她一出墙门,大家就说说笑笑起来。这回,是不是她又去告状了?
我们能不能去跟那个单位说说情?
谁去啊?都七老八十的,门都找不到。
儿子说了,叫我以后不要种了,本来就是人家的地。不对的。
唉,心疼啊,就像我的孩子啊。
胖婆婆抹起了眼泪。玉琴奶奶想:“那我就去当这个傻子吧!那我就去当这个出头鸟吧!我比他们年轻,有力气。”
那些天,大家都没看到玉琴奶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再过了些天,又一张布告贴了出来,意思是,再推迟三个月,请大家将庄稼收好。
玉琴奶奶什么也没说。其实,她也不知道,她每天去电话上那个单位那个管事人的办公室门口站着,到底有没有用。
夏去秋来,玉琴奶奶胃出血了。老家人告诉她,是在菜地里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叫她别去了。出院后,又腰痛。媳妇再三叮嘱她别去菜地了,说:“你都累出病了,有点空多操心操心家里的事好不好?要不你就吃吃睡睡,给我们省心,也是帮我们啊。”说这话时,她对玉琴奶奶一副嫌恶的表情,又一副心疼的表情。
整整一个月,她忍住不去菜园。一个月过了,身体好多了,她忍不住了。她想:“我去看看吧,如果看见一堆菜蔬的尸体,那我就死心了。”可是,当她一踏进墙门,阳光下所有的青椒、土豆、西红柿、毛豆,像一群孩子向她叽叽喳喳扑过来。她的眼泪刷地流下来了。
“你咋了?”邻居老太太正在帮她的地浇水施肥。“你这地里的菜好着呢,我们顺带都帮你弄一下的。”
另外一个成都来的大妈在帮她的地捡石头,抬头说:“你可瘦多了。你过来,我帮你做做腰部按摩,我学过的,以后,一周一次,我们约好,就一楼大厅里等哦!”
按摩手法果然有用。慢慢地,一周一次,她们像约会一样成了习惯。有天下大雨,玉琴奶奶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下楼,她不会过来吧?可是,等她一出电梯,就看见她坐在大厅里沙发边一把巨大的伞后面等她,一见她就叫:“妹妹你可来了?我顺便给你带了老家的红糖鸡蛋酒糟,胃出血,要补补的。”
她一时觉得心口有什么热热的东西堵上来,愣着没伸手接。成都大妈说:“别客气,咱们不分彼此。”
后来,大家都叫成都大妈“不分彼此奶奶”。
傍晚,媳妇回来,看到了冰箱里多出来的鸡蛋酒糟,还有各家送的一把把菜蔬。玉琴奶奶想好了,不管她说什么,就是对她刮暴风雨,她也不解释。为了这些珍贵的情谊,挨骂也值。
但媳妇叹了口气,什么也没有说。
吃饭时,媳妇问了些菜地的事,玉琴奶奶就说了,越说越起劲,越说越开心,什么都说了。“你知道吗?我们一点都没贪小便宜,水,都是我们从自己家里挑过去的。我们不能给儿子女儿丢脸!”
媳妇放下饭碗,沉吟半晌,说:“妈,以后家里的事,除了晚饭,其他都别做了,我会请钟点工来做的,你好好养,每天吃两个鸡蛋,自己弄点人参炖排骨、猪蹄或者鲫鱼。我们隔天晚上去饭店吃,点五个菜,打包回来第二天吃,你就省力一点。菜地么,想去就去,跟他们聊聊天、散散心,就是不要挑水什么的再累着了。我想,胃出血跟去菜地没关系吧。”
玉琴奶奶觉得奇怪,本来,媳妇是坚决反对她去菜地的。更奇怪的是,本来那天头很痛,媳妇说了这么多,她的头就不痛了。
她不知道,媳妇心里在想,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儿女,从来不知道父母身上发生的惊心动魄啊。
但终于有一天,媳妇还是爆发了。那天,媳妇到浴室接水泡脚,闻到了一股臭味。她以为马桶没冲干净,冲了一下,还是臭。便问玉琴奶奶,什么东西这么臭?玉琴奶奶过来,讪笑着不说话。媳妇便知道一定有什么秘密了。媳妇再问,脸色已经发沉了。
玉琴奶奶赶紧蹲下身子,拿起那个浇花的水壶,说:“是小便,我想拿去浇菜的。”
媳妇顿时大怒:“你你你,你怎么跟那些愚蠢的老太太一样!脏不脏啊!还存着?你你你!”
玉琴奶奶赶紧将壶拿到门口,媳妇大喊一声:“回来!你还想存哪儿?赶紧倒马桶里冲掉,壶扔掉!马上!”
十几年了,媳妇从来没有这么厉声过,可见,是生大气了。媳妇爱干净,她知道。
那些尿是脏,可是,对一个农村人来说,那可是菜宝贝们的牛奶啊。“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慈善的举动。”落户城里的儿女,农村来的父母,已是飞鸟与鱼的关系。
春节来临前,玉琴奶奶回家了。她找了个借口,说爷爷一定要她回去。她还说,她在这儿没医保,如果上医院,“伤不起”。上次的住院,她心里已经很内疚了,年纪越来越大,不想让儿子、媳妇增加负担了。
其实,最主要的是,她不愿意等到二十号那天,亲眼看着菜园被推土机推掉,她的菜孩子们被推掉,她在城市里唯一的梦被推掉。
阳台上的图书馆
太阳和灰尘的气味,以及纸的气味,弥漫在正被牙痛折磨着的阮艳红的错觉里。
牙痛像一个女鬼,跟了她整个白天了,现在跟着来到了夜里,并且更加狰狞了。痛的频率跟脉搏跳动一样,一秒钟抽一下,就像阴险恶毒冷酷的女鬼,一门心思全力以赴地用一把镐头挖着最痛的地方,往深里、黑里挖,像三百六十天里最严寒的日子,最黑最冷的最低点。这种痛,又是灼热的,像被烧红的烙铁尖,无休止地戳着她的灵魂。
家人说,上火了。好像是习惯成自然,单位里一有紧急任务,面对堆积成山的数据报表,阮艳红就觉得“头大了”,头一大,牙齿就痛,其实她也知道,这是着急上火。先是一跳一跳的隐痛,神经像一把扇子的扇骨一样,将隐痛辐射到整个腮帮子,直上太阳穴,再到整个头部。不是空洞洞的痛,是胀起来、溢出来的痛。如果牙齿不痛,那股虚火一定会从嘴唇突破,起泡,痒、痛,溃破,脸都没法洗,一擦,毛巾上就沾血。
但这次不同,是空洞的痛。
阮艳红迷迷糊糊中看到自己在爬楼梯。楼梯是灰色水泥砌成的,摸着墙皮,能感觉到水泥上细小气孔在手指尖的触感,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毛糙和滑腻!越往高爬,风越大,阮艳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到周围有一朵朵乌云的地方了,脚下的楼梯一直在变窄,然后阮艳红发现再也没有扶手和落脚的地方。云层形状狰狞,像一个人头马面的幻影。阮艳红回头看了一眼,被黑色云层覆盖的水泥楼梯忽然变成了她白天面对的种种财务报表。
“好累啊,快累死了。救救我吧!”
阮艳红从一身汗水里醒来,是牙痛把她从梦里救了出来。身边那个人鼾声正浓。
阮艳红强迫自己赶紧继续睡。明天上午一早又是会议,又是业绩!阮艳红仿佛看到那个外国老板寸头上的黄头发,像金子般闪亮。老外难道不会长白头发吗?我看这黄头发要看多久,要看一辈子吗?这,是我要的生活吗?
作为一名准文艺女中年,阮艳红从小的梦想是当图书管理员,而且,是学校里的图书管理员。记忆里有一缕特别亮的阳光,时时穿过时光隧道闪现。十三岁,她刚上初中,第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图书室,而不是图书馆。图书室只有一间教室那么大,立着一些黄色的木柜子,中间拼摆着四张桌子和几条长凳。很静,只有两个学生在翻找杂志或书,一个瘦小白皙的中年女人,想必是图书管理员,就坐在窗边的一张桌子前,静静看书,偶尔抬起眼睛,看看学生们。一个学生找到书了,来到她桌前。她拿起一支圆珠笔,把书翻到最后一页,在插在封底的一张卡片上写上一个日期。
窗外面,是南门湖。一片奇特的阳光,大概是从水面反射到窗玻璃上或天花板上,又反射到了她的双手上,使她的手看上去异常的白,衬着微微发黄的书,透出了一种奇特的气味,那是在姑姑看的《红楼梦》的插画里才有的一种气味。然后,她的眼前还浮现了一些画面,小镇外山脚跳跃流转着的溪水,水边草戏台上的长水袖,河埠头捣衣槌甩起的水珠的抛物线,夕阳下的炊烟,还有太婆黑白照片里的那朵头花……她突然想,如果一本书里有一些悲惨的人,被她那样抚摸着,是不是就不痛了?
后来,在小镇的街头,阮艳红听见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婆婆在跟旁人夸耀说:“我从不让我媳妇洗衣洗碗的,她管图书,手伸出去不能难看的,不然,对不住书的。”听的那个人也连连点头。阮艳红从那个人脸上看到了无限虔诚。
高中毕业,阮艳红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图书管理学专业,却阴差阳错被录取到经济系,而她最要好的姐妹却被北师大图书管理系录取了。
在三十三年的生命里,记忆里那缕阳光已经变得越加具体,与图书馆一起,成了一个梦。属于图书馆的阳光,必定是要透过窗子的,必定是有线条的,也必定是有细微的飞尘在游动,阮艳红必定是穿着棉布旗袍,或者棉布衬衣,戴着一副无边框眼镜,坐在一张木椅子上,登记,翻阅,看书。阳光与她,与纸张、油墨,与书里的人,与书里人的命运,发生着某种化学反应,它们合为一体,发酵,酝酿,芬芳,无声。一个图书馆,就是一缸酒。
多么幸福。
一次,阮艳红去北京出差,华灯初上时,她突然在马路对面看到了几个让她心跳加速的字:“国家图书馆”——阮艳红一想起来都要屏气凝神的地方。阮艳红屏气凝神地走进去——真大,真静,那么多人,都无声地坐着,或安静地走动。只是很奇怪,图书馆里并没有书香的气味,管理员都在电脑前坐着,各种电子设备都非常先进,但就是跟想象中的不一样。那么白天呢?阳光会从窗外照进来吗?会与文字、纸张、油墨发生化学反应,散发出香味吗?尽管有点失望,阮艳红仍然陶醉在里面不肯出来,在一排排书架前流连忘返。但是,当阮艳红想象自己也像那个图书管理员一样坐在那里重复着刷卡、点击鼠标的动作时,双脚不由自主往后退了退。
后来她又去过其他的图书馆。但是,都太高级,太先进了,人太多了,完全不是她印象里的图书馆。也许,学校里的图书室,会比较像“她的图书馆”吧?
丈夫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说:“如果觉得太累,就别求你的业绩了,既然那么想当图书管理员,你先去学校了解一下,我再帮你活动一下?”
阮艳红瞬间心动,又感动,并迅速投入了行动。
“怎么可能!”当阮艳红辗转打听到失散多年、眼下就在某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工作的同窗姐妹,如此这般描述她的梦想时,同学在电话那头大笑起来。
“你有多久没去图书馆了?现在的图书馆,已经不是你记忆里的图书馆了。忙啊,全自动的,人也像机器。借书只是最简单的工作,我们还要办展览、讲座、培训、交流等等,怎么可能让你有空静静看书?流水线!流水线你懂吗?你看,我忙得连女儿中考都顾不上,唉。”
“可是,总比我整天那么忙,却一辈子跟自己毫无兴趣的数字、表格、英文打交道要好吧?”
“只能说,差不多。还有,你没有学过这个专业,你能干什么呢?你不小了,现实点,亲。”
有一阵,她迷上了一档广播节目。一天夜里,她聚会回来,车开在南山路上,广播里传出来一个女声,是一位姓苏的女作家,在谈她年轻时读过的名著,她说了她读那部名著时的年龄、季节、心情。她还说,她永远记得那个借书的阿姨静静坐在图书馆里的样子。她觉得,最美的女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女作家的声音有点软,阮艳红的眼睛开始模糊,并产生了一个错觉,她听到这个声音像多年前图书馆里的阳光一样流淌在整个车里,和坐在图书馆里的女人合为一体。
她将车停在地下车库,整整坐了半小时,把节目听完。
元旦过后,那个声音却不见了,广播里传来的是她听一分钟就觉得脑袋要炸掉的摇滚音乐节目。她找到那家电台的微博询问,对方说那个节目比较小众,收听率不高,换到周末深夜播出了。
牙齿又痛了。早上六点起床,上班开车一小时,忙了一上午,连喝水都没空,匆匆吃了点外卖,在沙发上靠靠。可是没几分钟,又被一阵尖锐的剧痛惊醒。跑到洗手间,用冷水侧着脸漱口,稍好。又痛,像有什么在挖洞,一下比一下深。如此反复,纵有万般困意,也睡不着,索性不睡了,继续面对表格。这牙痛,熬熬会过去;这日子,熬熬也会过去?
牙痛,是没有指望的痛;生孩子,是有指望的痛。生活,有时就像牙痛,越痛越黑,越痛越深。
“牙髓炎。”口罩后的牙医说。三颗牙齿,分不清到底哪颗痛。打了麻药,给她觉得痛的那颗开了孔,先阻断神经,再根管治疗。可是,回到家,麻药过后,又痛。这回,用凉水漱口都没用了,更痛了。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说:“我本来就怀疑可能不是这颗,明天再来看。不要焦虑,小问题。对了,你的门牙短了一点,要做个牙套。”
“天哪,你先帮我把牙痛治好吧!门牙短不短,反正又不痛,也不影响吃喝,管它呢!”
阮艳红忽然想,她心心念念的图书馆,在她的生活里,就像短了的门牙,影响美观,但不影响她活着。
再上麻药,再打洞。麻药过后,并非医生说的不痛了,而是痛了一下午后终于不痛了,剩下了酸。医生说,另外一些牙也都磨损厉害,以后发展到神经裸露了,难免也会发作疼痛。
惨白的日光灯照在阮艳红惨白干燥的嘴唇上和鲜红的牙床上。躺在治疗床上的人,都显得异常的难看。阮艳红逐个看了看这些沉默得像一颗颗定时炸弹一样的牙,顿时觉得以后的日子就像这牙一样没有指望,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势必一颗颗败下去,如同生命里的生老病死,欢乐何其少,迎面而来的痛与累何其多啊。
牙痛好了,肩颈却开始痛。医生说,电脑前待久了,好多年轻人都这样。针灸吧,推拿吧,牵引吧,断不了根的,熬熬也会过去,会一阵一阵发作,“除非……”医生说。
“除非什么?”
“回到乡下当农民,再也不碰电脑。”
阮艳红虚弱地笑笑。医生也摇摇头,笑笑。
那天,阮艳红在微信的朋友圈里,看到了一幅照片。
那是一张荷兰老海牙图书馆的照片,名叫Handelingenkamer,被喻为世界上最美的图书馆,一年只开放一个月,八月底到九月底之间的周末,也就是欧洲遗产日时才开放。这座外观十足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内部却充满了中国古典味道——朱红色的雕花楼梯,繁复而精致,一圈一圈盘旋而上,一直从第一层盘旋到第四层,最终抵达全部是玻璃的穹顶,惊艳绝伦。这令人心醉的图书馆,于十九世纪末建造完成,因为当时还没有电灯,为了减少馆内蜡烛和煤气灯的使用以确保馆藏文献安全,大厦的天花板被修建成一个巨大的玻璃穹顶,好让光线能透过中庭及各层镂空雕刻的地板充分地照亮整座四层楼的图书馆。
与雕花栏杆和楼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厅正中那四张拼摆在一起的木头桌椅,朴实无华,就像,那些同样沉睡在繁华中的书籍们,像一群无邪的孩子。
阮艳红一下子泪流满面。
春天过后,趁丈夫出远门,阮艳红开始了预谋已久的大动干戈——将卧室外的露台包起来,三面都封上玻璃,再做两排书柜。她要在自己家做一个图书馆。
她去了从来没有去过的装饰材料市场,挑选一种木料,就是苏作家在节目里说的狐狸眼睛花纹的木头。木头运来了,她挑出那些看得顺眼的,也就是狐狸眼睛成对的,其他的就退回去。老板不干,说:“这怎么行?哪里有这样买木料的。”她说:“没什么不行的,我退给你,不要钱,你只要给我找好的来,我继续挑。”
换了三批木头,她不是在给书柜挑木头,她是给她的书孩子们挑摇篮。
木匠有点头疼,这些狐狸眼睛,怎么可能都拼成对称的呢?
“就得对称,工钱我加你,木料不够,我再去挑。这个歪了,不行!”
油漆未干的时候,阮艳红常常一个人站在露台正中间,闻着难闻的所谓环保油漆味,想象着所有的书籍沐浴在阳光下的情景,也想象着下雪天她坐在窗台上一边看书一边抬头看雪的样子。她发现,她的牙不痛了,手臂也不痛了。
她把储藏柜里尘封多年的藏书都搬了出来。
这是席慕容钢笔字帖,她大学时买的,她迷恋她的诗,也喜欢这些钢笔字,第三十九页上,有一大块墨汁,是她练字时,钢笔漏水了弄上去的。
这是她高中时初恋男孩送她的《呼啸山庄》,用牛皮纸包好的。她轻轻摸了摸,她知道,这个姜黄色的牛皮纸下面,封面已经破了一半,封底没了,是他俩吵架时她撕的而他抢了过去。当她用手掌轻轻抚过,她感觉掌心下面拂过了风声,拂过了遥远年代的爱恨情仇。
这是去年给女儿买的一套新书,全部是世界名著,却崭新依旧,女儿连一个字都没看,不喜欢。
“咔嚓”,当她翻开另一本旧书时,一页纸轻轻断裂了,从她的掌心落下去,落到了傍晚五点钟的夕阳的影子里。她俯身捡起,在夕阳下照见了淡淡的字迹,她的读后感。她找来一支胶水,将它重新粘回去,仿佛,重新粘合住一段往事。
丈夫进门时,她完全没有听到。丈夫一眼看到露台门框上方,用毛笔题写着三个大字“图书馆”,第一反应是阮艳红疯了,第二反应是对她的先斩后奏不满。平时,大事小事,阮艳红几乎什么都听他的,只一样——书,从来不扔,在储藏柜里越积越多,都是各种文学名著、杂志。找什么东西时,一翻出来,便飞尘漫天,但阮艳红不肯扔。现在,阮艳红居然为了那些破书自作主张把露台封起来,这么大事也不跟他商量,可不疯了?
他走进露台,看见那个有点傻气的女人正踮起脚尖,从“图书馆”高高的柜子上抽下一本书,一缕阳光照在她雪白的双手和发黄的书页上,一缕头发从她的耳朵后无意间垂下来,影子在书页上微微颤动。他忽然发现,他的妻子变成了另一个人,却又那么熟悉,如同他们年轻相遇时的样子,多么娴静温柔。
他嘴里嚷道,饭烧了好吗?饿死了……口气却像强弩之末,突然软了下来。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