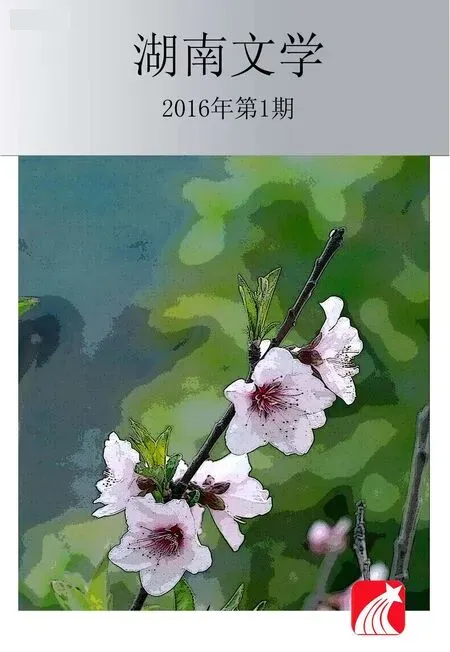荷叶塘
→袁送荣
荷叶塘
→袁送荣
那人,那宅,那荷
绵延环绕的峰峦之间,有一处钟灵毓秀的地方,它的伟大,缘自一个人、一座宅、一片荷。
人已作古,但辉名昭世。
宅露残破,却万人瞩目。
只有那片荷,永远鲜活艳丽。
宅在山之前荷之后,叫富厚堂。宅第主人取其名曰富厚,源自《汉书》“富厚如之”古意,用以祈祷子孙万代居住此宅能“清芬世守,盛德日新”。
这座宅第,说是中南乡间第一侯府,大概是因人而名,而我说,它蕴于乡野,立于田畴,十足的乡里人家。曾氏家族的宅子大大小小不下十座,但只有这座,传承的家风最为纯正与浓烈,曾国藩只是这座宅第的名誉主人,为其操心,却空有望云思乡的慨叹,他的儿子纪泽等后裔把国藩传承的家风淋漓尽致地效行下去。曾氏家族家风醇厚,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完整可师,历为典范,体现出主人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祭祖、睦邻的那种半耕半读的乡土本色,其子孙后代诚惶诚恐,均以肃雍和鸣之音,祭于先祖听。
宅内藏书楼三十九万册书典是主人淬取各派文化精华的象征,虽已散藏四方,人去楼空,但它哺育了一个人才辈出的超大家族,造就了这里传统而又创新卓进的文化。
曾国藩虽不曾在此宅居住过,这第一等屋场他无法消受,但这样环山抱水的处所,荷叶到处都是,从他的出生地白玉堂到黄金堂,以及他的兄弟们的宅第,都依山傍水,灵韵雅致,他被这里的山,这里的田园,这里的环境深深影响着,从襁褓到出仕。
履职数十年,他以文章、以辞赋、以行为继承发扬着他承秉的文化,像垒墙一样,不断地加固加高,坚实而不松弛,自然而不媚俗,并时常以书信、面瞩的方式谨告后人守法而行,革新鼎故,成为耕读文化乃至湖湘文化之集大成者和传播者。
当然,后人谨守其示,家风在宅内外绵延不绝。即使时势变幻,曾氏家法的精华还是同本土有机结合,风行这片古老的土地。
这里的乡民都像曾氏一样,耕作、读书,谨行着读书兴家之本、仁和守业之道的训则。于是,勤俭、憨厚、仁和、坚毅、谨慎,成为了荷叶人特有的内质。
就如这荷花,清纯自然,芬芳扑鼻。这花,在宅前数百亩水面上灿烂地笑着,展示着这片深厚土地上散发青春气息的笑靥。
荷在富厚堂前面的这片池塘里已生存了两百多年。她们总是在热烈的季节中红霞拂面,绿衣出水。她们总是花蕾邀客,莲蓬举杯,推开窗儿迎接四方来客。因为,每一次绽放,于她们而言,都是美丽的新生。
一起去看看吧:这座宅,这片荷……
最浓烈的芬芳
对我的老家荷叶塘而言,最浓烈的芬芳莫过于书香味。
荷叶塘的闻名遐迩是因为晚清大儒曾国藩。无论是曾国藩,还是“三担牛屎六箢箕”的荷叶农夫,都把读书当做第一要务,把耕作当做第一要事,把明理当做第一要义,把慎独当做第一要求。将书本比“大丘”,喻读书似犁田,视仁义为生命。
荷叶塘人都知晓这几句话:“荷叶两件宝:读书和考宝;荷叶两功利:耕读和仁义;荷叶有两出:读书和喂猪。”
长期以来,荷叶塘人无论富贵贫贱,家家户户必定都有读书郎,必须都有读书屋,必然都有藏书所。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就有“公记”“朴记”等规模宏大的藏书楼。一般平民家,就会有小书房,规模虽小却也容得下平静的读书心。一些必备的书籍总是不会少的,《论语》《千字文》《百家姓》《增广贤文》《资治通鉴》,另加一套族谱。当然,这些书里面很多是手抄本或民间铅印本。除了这些“高大上”,还会有一些草根书,比如《黄道吉日钞谈》《宅地平安略》《红白喜事俗录》等,这些书是老百姓生活工作必备的工具书。无论老少,耕作回来,洗净腿杆子上的泥巴,在昏暗灯光下,走进书的门户,拴在书的门栏,小的读幼学,做功课;大的念增广,算收益。
即使是生活都无法维系的贫穷人等,也会生出许多主意,找书读,为书忙。
我很敬重的一位老读书人,叫邹其霖,与我同出新耀冲。他的小时候,是在一种极度贫窘当中度过的,我不加渲染烘托,你用这个世界上最能体现穷困的情境去形容和考量,也一定不为过。读小学时他借来同学陈祖林的《新华字典》,读高中时借来老师吴春元的《中华汉语大辞典》,借来干嘛?全文抄写。几百万字抄下来,他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茧,甚至有点畸形了。两部字典,是字词的宝库,是知识的海子,别人仅仅在这个海子里游一游,就觉得满足了,可他却把这个海子里的水,一瓢一瓢舀进自己的心海,边抄边记,边记边用,直到把自己变成活字典。邹其霖“两部字典走天下”,在省作协机关待过,在《小溪流》里趟过,一路沧桑一路艰辛,而今又卷起铺盖回到荷叶塘当“耕夫”“樵夫”。他的活字典形象,早已成为荷叶塘的标识之一。
因为时代有所不同,我的生活境况肯定好过他,但总归还是穷孩子的范畴。而且,我俩拥有相同的基因:喜欢藏书读书。我还记得那次如今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藏书比赛。竞赛是我和玩伴朱正军发起的,主要是发动小伙伴们收集连环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除了课本和宣传册,就只有这种小小的花花绿绿的连环画了。一个组三十余户人家的孩子们全部都发动起来,大家变着法儿,拼足了劲,通过向父母索要、摘茶叶勤工俭学、偷家里辣椒卖等方式筹措资金,到代购代销店或城里的新华书店买回一本本连环画,有《小二黑结婚》《小英雄雨来》《战国传》,等等。又请来木匠做好长条形的木箱,把小人书小心翼翼地叠放好,然后开始吃“独食”,父母都不许去翻动。之后,会提着书箱到别人家去“斗书”,看谁的多,谁的新,谁的厚。再到后来,就统一集中放到朱正军家,成立图书室,因为他家书最多,有一千二百多本(套),大家便推他为馆长。我的略少,只有九百本,便担任副职。各人的箱子各人上锁保管,到了星期天,相约一起到朱家,打开箱锁,晒一晒,翻一翻,聊一聊。那种日子,真是安静而美好啊。
而今已是“互联网+”的时代,荷叶塘人的读书性情依然不改,虽然富厚堂藏书楼人去楼空,但周边的殷实人家,书房已越来越大,藏书也越来越多,书香自然越来越浓。更多的人除了拥有排兵布阵式的纸质书籍外,桌子上还多了一台电脑,在这个网络空间,人们似乎不必再在乎印制的书本,只要轻轻点触,便可一切在线,便可百科在心。但荷叶塘人不会拘泥于这个虚拟世界的知识碎片化、读书功利化、求知庸俗化的倾向,他们是主张读点纸质书的。他们要求孩子们读一些经典的大部头。孩子们左手翻书,右手点击电脑鼠标,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葛咯祠堂
原想,曾国藩曾氏一族在晚清时期应是除了爱新觉罗氏和叶赫那拉氏等皇族之外的中国第一等显赫家族。那么在其故里荷叶塘,也必然是名望最高人丁最旺的第一大族群。
其实不然。垄断荷叶塘姓氏的三大族第葛、曾、王,三者历经近百年的激烈PK,葛氏以现有人丁之量多,现存宗祠之奢华,现时人才之旺茂而略胜于曾氏,成为荷叶塘响当当的族氏“一哥”。
在宗氏文化的影响下,葛氏中兴,脉流成学,似乎有引领荷叶耕读文化前行不息之气概。
得说说那座古老的宅子。它是荷叶塘葛氏的血脉领地,是葛姓的精神家园,是荷叶耕读文化中宗祠文明的最权威展品,也是荷叶塘人文、建筑、民俗的综合体。
这座与当年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堡垒”,之所以能够留下来,缘于它的及时改头换面。在那个特殊年代,它被改造成一所学校,其“封建遗老”的不雅身份得以洗白,当时叫长塘学校,现在叫上达学校。
一个地方、一支宗脉不能没有文化。耕以裹食,读以楣庭,这是荷叶塘的基础“方言”,也是宗祠教化氏民的另一重要功课。因此,当地政府就地取材,将高大空阔的旧时宗祠清扫干净,用“思想杀虫剂”“改革除草剂”“政治空气清新剂”将祠堂里的阴暗、迷朦、老朽、颓废洗涤干净,用磅书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之后,这儿就不再是该宗族先人们神灵幽居的地方,而成为他们的后辈琅琅读书的场所了。嫩嫩的、稚稚的声音将沉重、阴森的宗祠吵闹得十分明快、清爽。
这里的老师、孩子只知道传授、学习实用的语、数、英等课程,除此之外,从未以历史的角度审视这栋古宅曾有的辉煌,从未以现实的角度了解自己为保护古宅及其透析的文化所作的功绩,也从未以未来的角度去思量这栋古宅人脉的力量和文化的升腾。
荷叶塘内一批批祠堂,就像这栋老宅子一样,都在服务大众、繁荣当地文化的一系列壮举中得以新生。
当年也许是经济上的无奈,没有更多的钱财去建设新学校,而让这些很可能倒在“破四旧”运动中的宗祠侥幸存活下来。
在荷叶塘后来的“教育明星乡”创建活动中,一部分祠堂未能留住落日的辉煌,被一片一片剥掉身上的鳞甲,化作历史的灰烬。
双江曾氏祠堂就是一例。解放后新砌的四合院式的土砖瓦房团团围住一息尚存的祠堂主楼大厅,青砖高耸,屋檐高悬,进深幽长,虽古旧怵人,但其史学价值毕现。高高的横梁上曾扎着一个锃亮的高音喇叭,成为这所学校的核心领地。上世纪九十年代那场学校改造运动中,它的身边矗立了一栋三层红砖楼房,俯瞰着灰头灰脸的它,那本已残破的躯体此时显得十分的不合时宜,就如在一身洋装的俊男头上带一个瓜皮小帽一般,不伦不类。新式学校就得处处簇新,这点残存的记忆实在因保存的意义太小,而被勒令退出历史舞台,不留半点痕迹。即便如此,当地人还是很习惯地称这所学校为曾咯祠堂,它的本名倒忘记了。攸永寒公祠也荡然无存,大夫第内的竹亭公祠更是与敦德堂、奖善堂一并淡出荷叶塘的风光。
至今保存最完好、最齐备的就只有葛氏祠堂了。
我曾在这葛咯祠堂从教两年,见证了它的存在与消逝。
我平生的第一个“官职”,就是在这座古宅里担任职小位卑的教导主任,古宅见证了我十九岁时初享成功的喜悦。校长葛增加老先生是葛氏后人,德高望重的他承担着育人与护祠的双重责任,我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我配合他用心管理着五六百号师生,古宅亦用心地荫护着我们。
铜梁山脉下的这位历史老人,历经百年而不老,在渺渺绿色中以白色作为它亮丽的外套,以灰色、黑色显现它厚重的年轮,那屋顶一丛又一丛山字高垛齐兵列阵般伫守着这精神家园,垛上的青草小树昭示它历史的深邃。大厅空寂,但“教风扑面”,偌大的石柱坚定地支撑起宗祠主体庞大的身躯,支撑着葛氏一脉盛德日新的宏大梦想,也支撑着这所学校人才日新的期冀。
戏台是宗祠不可或缺的部分,可谓之为宗祠的声音,是族人们除了巫祭先祖之外的又一集结号。
盛大的祭祀过后,族氏主事就会邀请当地有名的戏班登台表演,钟鼓齐鸣,笙笛和声,旦角同台,在盛彩中唱响族人的心灵,唱开族人心中那朵奔放热烈的映山红。
如今这个葛氏宗祠的戏台已没有往日的喧哗,至多也就是学校庆六一国庆时孩子们脸上抹点油彩、头发上扎个红绸子、在台上叮叮当当响闹一阵的舞台,除此,戏台便不再承接其他的打扰,清清静静地,收敛起它昔时的纵情。
宗祠的神主牌位新近得以恢复,原来教师的小办公室被清理整装后,摇身变成供台,葛氏各支各脉的领头先人和他们已逝后人的牌位有序排列在上,“各路人马”集中享受后裔们供奉的三牲果蔬,在缭绕青烟中乐观此状,怡享祭祀。这在三四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儿,但时至今日,我们有一种呼声,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文化不仅有高雅的,如京剧、国画,也有民俗的,如谱牒风水、宗族文化等等。我们说爱国爱家,爱国是至高的信念,爱家是基本的要求,家不仅是三口之家,也涵括同宗同族的大众之家,建祠以奠先人、以聚人心,只要剔除旧时封建纲常,修正族内陈规滥约,那么这种祭拜先祖、延续信念、报本返始、饮水思源式的宗族崇拜主流思想应是弥足珍贵和予以保护的。而宗祠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补充、细化与完善国家法制的作用,亦不可小觑,是大社会中难以或缺的小型教化体系。
葛氏宗祠代表着散落在荷叶塘民间的史料体系,它始终追求慎终追远、饮水思源、家国至上、独慎自省的宗族道德观念,承载着葛氏一族珍贵的创造革新和无限的人本情感,是葛氏先辈文化的符码与固态形式,是历史情境与时代意义融会的产物,研究它甚至比研究富厚堂更有现实意义。
这座矗立于涓水河畔、长塘甸中、铜梁山下、族人心灵的古宅,使倡学、尊亲、和合成为葛氏乃至荷叶塘人精神的盛宴。
这足以让它不古。
那甸金黄
那甸热烈的金黄,是荷叶塘人一生消受的瑰宝。
它叫长塘甸,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上行约一公里就到了。方圆十几里,纵横数千亩平整的良田,就任由这团金黄统领着那个叫秋的季节。
由不得半点杂色,来不得丝毫分心,那片片匝匝的金黄,熟透着、沉甸着,等风吹过那种成熟后,就笑着拨弄厚德的头脑,在荷叶塘人的敬畏与满足当中,一头钻进飞转的“扮桶”,躺入农家的箩筐,睡到庄户的谷仓。
生育这片金黄的田地,胸围大得不行,上依鸡笼山,下达落子山,左傍铜铃山,右靠贺家坳,山以绿色相衬,高低错落地为着这甸金黄遮蔽风雷。
用深沉的眼睛盯着这片躁动的金黄的,是略高于这稻秆的、红日山下的长塘葛氏宗祠和靠右依托的石林祠堂,远山拦着这片香,这片色,古宅监督着,警醒着,让它眉飞色舞之际,不因忘乎所以而过于肆意。
用悠永深情依偎着这片灿烂的金黄的,是略低于这田丘的那条涓水河,它发端于黄巢山,不出几里地,就开始履行自然赋予它的重要职责,潜心润物,无言成蹊。在沿途沙石的刻意设计中,它蜿蜒温顺,将这片金黄分成东西两块,独居其间,见证着两岸金黄的高兴、忧郁与奋斗。
河本自然生成,但七十年代治理水土,人民公社以“人定胜天”的勇气与“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浪漫憧憬,将盘折河道改造成全花岗岩结构的笔直的河干。
河的两岸用凿得又直又平的花岗石垒砌而成,高约一丈,宽约二十米,每隔二三里地儿,就会砌上一座或宽或窄的石桥,二拱而成,没有用一滴水泥,一寸钢筋,全靠物理力学的受力原理砌成,桥中的半圆碑上,用彩色绘成几个图案,并雕上一副时代感特强的对联:石山英雄移,林海人民造。再刻上修砌的时间,岸边种植无数的槐树。包括干流与支流,这种河道长达四十多公里。工程之浩大,修砌河道之实用与美感,让人咂舌,完全可列入文化遗产。可惜如今的河道有点离乱沧桑,但它当年的盛大与光彩,今天还是可以从它的躯体上凸显出来。
早春时的长塘甸,田丘如镜,田埂将水田刻画得妙不可言,大小结合,长短错落,就如一块巨镜被石头砸成七零八碎的,天空中漫散着淡淡的臭味,那是农民在水田中扬起的粪肥,这个季节,闻不到这种味道,就算不上春耕农事的开始。
不久后,丘丘田地都会站上几个十几个农友,他们娴熟地点着稚嫩的秧苗,织着绿意生动的图景,绣着希望的“湘绣”。不用几天,清淡无华的绿色就铺满整甸。
于是,在农人的山歌里,在古宅的琴声中,在高山的感染下,淡淡的那片绿,在时光中,渐进地默契成了草绿、浓绿。
长时间的绿,绿得禾苗有点不耐烦了,就开始色彩的蝶变,在初秋的催促下,绿秆在烈日的加工当中,变成了黄色,开始是绿中间黄,杂乱地洋溢着初秋的谨慎。随后,就全然弃绿了,让金灿的黄色裹了全身,秕谷也吮吸天地之气,不断地锤炼体质,让皮包骨的谷壳逐渐丰腴,竟变得饱满而壮实。
就这样,数千亩地齐刷刷地金黄了,秆儿根根高挺,谷粒线线下垂,团聚而居的村宅躺在这片金黄中品尝谷香,话道收获。
青山深受感染与鼓舞,便纷纷效仿,放纵地“变脸”,准备迎接下一个季节新贵,抖落满身的绿,开始山的七彩了。
这种纯粹的金黄,这份硕大的秋天礼赞,你在哪儿都难以看到。
十月左右,你来这里吧,品葛氏祠堂文化,觅人造河道胜迹,然后,立于高处,略略赏观金黄稻浪后,再兴奋地卷起裤脚,提鞋下田,走进金黄深处,或挥镰割禾,或握秸扮禾,或挑箩送谷,或一路捡穗,极尽农人之秋事,尔后,洗却劳作的疲倦,和纯朴的农友们吃新粮,喝米酒,嚼腊肉,唱山歌,醉梦乡。
你入梦的地点,依然还是这片田地。
你入梦的色彩,定然会是这种金黄。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