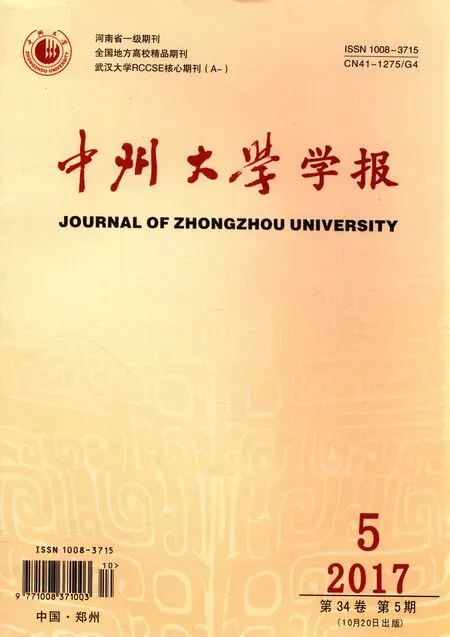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
——以毛姆《在中国屏风上》为例
尹 萍,祁国江
(黑河学院 a.通识教育学院;b.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
——以毛姆《在中国屏风上》为例
尹 萍a,祁国江b
(黑河学院 a.通识教育学院;b.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黑河 164300)
《在中国屏风上》是英国作家毛姆在中国旅行时的游记, 他对中国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的考察,对上至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的书写,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该该中既有文化“他者”中的中国形象,又有集体无意识下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体现了作家所属群体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范式。
毛姆;文化;中国形象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毛姆最初以戏剧家闻名,但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不少小说被搬上银幕,他的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其中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彰显了他对东方文化浓厚的兴趣。他的旅行札记《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2)和长篇小说《面纱》(The Painted Veil, 1922)都是以中国为背景创作的名篇。毛姆在1919—1921年间曾两次踏入中国土地,在《在中国屏风上》是由50多篇长短不一的作品构成了一幅中国之行的画卷。在近10万字的叙述中,刻画了上至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街头小巷的肮脏拥挤,瓷器、壁画的优美雅致,山峦、河水的压抑污浊,长城、天坛的静谧宏伟,构筑了一个别样的中国形象。
巴柔在《比较文学概念》中对形象下了这样的定义,“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它“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1]25。他认为,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亦即:形象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形象是他者的文化表述,无关真实或虚构。深受东方主义影响的毛姆,在他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的藐视和偏见。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之一:破败滞后的中国
该书中第一篇《幕启》,是这样一幅断壁颓垣,满目凄凉的画面:“在你的面前是一排茅草房,一直延伸到城门口,这些用土坯砌成的茅屋倾圮破落,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它们吹倒。古老并有着雉堞的城墙频于坍塌。”[2]1这就是毛姆刚刚拉开那层神秘的屏风所看到的。他看到的是一个衰败、凄凉的中国。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失利,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正处于饱受战争、割地、赔款之苦的千疮百孔之境地。而此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接近尾声,国家实力不断增强,通过海外扩张积累了大量财富,殖民体系得到保障。毛姆既有对中国现实状况的描写,又有意识形态的抒写。在描写鸦片馆时,他是这样形容的,“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2]35他把残害中国人身体和灵魂的鸦片,把人们吸食鸦片的地方,用尽了赞美之词,毫不掩饰地反应出作家的殖民主义心态。正如基亚所言:“形象总是某某事物的形象,总要与它或多或少忠实再现的现实保持某种关系,这是所有的折射、棱镜都改变不了的。”[3]87中国的道路不是狭窄曲折就是破损不堪。中国的客栈不是低矮拥挤就是油迹斑斑。“有一家既肮脏又不舒服的中国小客栈。在那儿,你会见到光秃秃的墙壁,滑腻腻的泥土地面。”[2]70在毛姆的笔下,中国的房屋阴沉、低矮、空荡,坐落在拥挤或冷僻的街道。客店邋遢、污秽不堪,但这幅粗糙简陋的画卷也别有一番景致。被列强恣意欺凌的中国,城市是阴郁的,河水是浑浊的,就连天然形成的山峦都在竭力地抖动着。
在《面纱》中,作者对中国的城市有过这样的描述:“街道狭窄曲折,街道上阴森森的一个人影也没有,俨然是一座死城。”[4]77陆路和水路交通闭塞,在不到一千公里的两座城市间穿梭少则五六天,多则数十天。这些贬义性的语言,可以窥探出毛姆对中国的反感与厌恶。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之二:庸俗无知的中国人
毛姆用他深邃的观察力和犀利的文笔,用两种方式来刻画中国人的形象:一是作为旁观者直观的观察,二是通过在华的英国传教士、商人和政客等转述。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的中国形象,一是普通百姓,二是达官显贵,三是儒雅学士。
他用较多的笔墨刻画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你可以观察那些中国人,顾客和店员,他们露出一种愉快的神秘表情,好像在进行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2]24“如果你脑子里没有装满东方人都是神秘莫测的这种观念的话,你会觉得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好人;可是如果你向常驻中国的那些老资格外交官提起你的这种钦佩,他们会认为你有些荒唐。他们把苦力视为不过是些牲畜。”[2]49毛姆对普通百姓的描写用尽了蔑视和挖苦之词。
在《面纱》中,男主人公瓦尔特用生命爱护自己的妻子,妻子却与另一位来自英国驻香港风流倜傥的副领事偷情,在一个午后,当他们两人在瓦尔特的家中密会时,突然发现门把手有人在拧动。两人神情极度紧张,他们在诚惶诚恐中这样彼此安慰:“除了中国人,没人上来就那样拧把手。”[4]3事实上,是丈夫瓦尔特昨晚听说妻子想看一本书,就顶着烈日给妻子送回来,他知道妻子一般都午睡,怕惊扰妻子,想着把书轻轻放下就走人。最终妻子在瓦尔特爱的感召下,“在善与恶的博弈中,回归了家庭。”[5]
无论是衣衫褴褛、身材枯瘦、干瘪的苦力,还是为生活而奔波的普通百姓,在毛姆的眼中都是窥视欲甚多、庸俗无知的人。中国有一个怪现象,人的地位可以为其行为辩护。大意就是不论你的人品如何,只要你有权有势,人们就会讨好你,想和你成为朋友。在《内阁部长》里,毛姆这样描写:“他是一个清瘦的人,中等身材,有一双瘦削、优雅的手;他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他把这位内阁部长形容为是奴颜婢膝、不择手段、凌弱暴寡、贪赃枉法、任人唯亲的政府官员。在领事和中国官员因为战俘而起争议时,领事完全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气急败坏地说:“他不允许一个可恶的中国官员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2]34有一位在中国工作的领事皮特先生,他不遗余力地查禁鸦片,但城里人只有他不知道他的雇员将鸦片藏在领事馆内,而且是在领事馆大院的后门公然进行大量的鸦片交易。这是全书唯一一位毛姆提到的英国官员,在中国禁止鸦片交易,实际情况又叫毛姆啼笑皆非。
不论是来中国30年的怡和洋行的老板,还是来中国十几年的大班;从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干事员,到现在住着气派的石砌大厦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连一句在街上问路的中国话都不会,甚至用异样怀疑的眼光打量任何学中文的人。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精神得到重生,带着某种目的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温格罗夫,在中国已经呆了17年,他表面上肯定赞扬中国人,听不得别人说中国人不好;然而从他妻子的口中,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她从无数传教士的言行中得知中国人肮脏、残忍、不可信任。夫妻两人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让毛姆迷惑不解。毛姆这位善于洞察人内心的作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他的感官所喜爱的,他的灵魂就厌恶。不管他想极力掩饰什么,他灵魂深处是憎恨中国人的,妻子的憎恨和他比起来真可谓相形见绌。温格罗夫先生是在英国生活得比较安逸的为数不多的来中国的其中一位,起初,他极为反感并加以拒斥,可是无休止的焦虑始终萦绕于心,他无法摆脱精神的枷锁——害怕永恒的惩罚,不得已来到中国。另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把工作当成了生意来做,他对自己的工作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热忱,他觉得中国人头脑简单、愚昧无知。这些所谓带着上帝使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认为自己在一个远离文明的世界里工作。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分子亨德森,刚来中国,他极不习惯用人力黄包车作为交通工具,时间久了,他认为坐人力黄包车是天经地义的,他用冷漠的口吻说:“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大部分来中国的外国人基本上都是他们国家里贫穷的下层人士,到了中国都成了富有的上等人,如沙利文本是爱尔兰的一个水手,在英国,他是一位食不果腹的贫苦人,到了中国,经过几番辗转竟成了一位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富人。毛姆此行一直想拜访中国著名哲学家辜鸿铭,对他有过这样的描写:人消瘦,吸食鸦片,寻花问柳,而他满腹经纶的儒家经典却少有人问津。毛姆对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哲人,毫不客气地把他形容为朝秦暮楚、嗜毒成瘾的人。然而,笔锋一转,又怀着体谅的情绪,把他的这种行为称之为“雅好”。辜鸿铭通过体验普通人所遭遇的人生浮沉,来使他的著作更有现实意义。这是毛姆赤裸裸地为西方殖民主义思想作辩护。
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之三:集体无意识下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
“一种文化一个时代中关于特定主题的典范之本,不是创造出一种形象,而是为那种文化和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生活中的原型找到了理想的表达式。”[6]45文人墨客塑造“他者”文化,无意再现他国的现实,按照当时所属文化的一般想象来描述他者,实际表现的是西方文化无意识的欲望。毛姆踏上中国国土时,正值西方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司法混乱,人口稀少却狂热的进行海外扩张。毛姆期待在这次异域的东方之旅中找到西方文化无意识中的缺憾。这正是异域文明化解在自身文明的期待视野中,变成自身文明自我评价自我定义的他者,西方的中国形象折射出西方自我意识、欲望的转移。
1250年前后问世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只提到了一个中国形象生成的起点,真正让中国形象鲜明地进入西方人的知识与想象视野的,是半个世纪以后陆续出现的三部著名游记”[7]127。他们分别是《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和《曼德维尔游记》。马可·波罗与鄂多立克本人都是亲历到访过中国的旅行家,马克·波罗更是在中国生活了17年,他们将大汗统治下的中国描述为地大物博,市井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却是从未踏入中国的曼德维尔撰写的《曼德维尔游记》。曼德维尔是一位英国绅士,游历最远的地方也不出法国。人称“座椅上的旅行家”。在这部游记中,他综合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关于东方的传说与事实,以骑士传奇的笔法进行杜撰,但符合西方文化期待视野下的伊甸园式的东方帝国想像。13—18世纪,西方近5个世纪不断美化中国形象。在社会文化中掀起了崇拜中国的思潮——中国潮,其中16—17世纪间的“中国潮”达到高峰。西方的中国热情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灿烂悠久的历史、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使中国成为西方社会期望中的理想楷模。从那时起,西方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就开始出现了东方帝国和中国文化的影子。在英国,从乔叟、莎士比亚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书写遥远神秘而又让他们心神驰往的东方帝国。“无法抵御社会的整个倾向——对他者的梦想,这倾向就构成了‘社会集体想像物’。”[3]197毋庸置疑,作为对中国深感好奇的毛姆,他笔下的异国形象显然带有英国社会集体想像物的神秘与辉煌。
尽管毛姆在中国游历期间,正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仍然看到并感受到了这个衰败的国家曾经拥有的辉煌。店铺里精雕细刻的木格,让人恍然间觉得在幽暗的格挡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东方奇珍异宝。雕梁画栋上的飞龙都已褪色,但仍不失优美。在内阁部长的收藏室里,他看到了价值连城的瓷器、青铜器和唐代的塑像。特别描写了从河南古墓中出土的造型优美、神韵精致的唐三彩马。中国的花鸟画令毛姆发出叹为观止的感慨,虽寥寥数笔,却表现出生命的搏动和颤栗。
在《天坛》中,“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象征着天球及四个基本方位。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2]17。毛姆描写了宏伟、壮观、精致的天坛,皇帝祭天,供奉神灵时恢弘的场面。更让人惊讶的是,在穷乡僻壤的乡村也能找到装饰华美的器物。在这里,毛姆似乎看到了《马可·罗波游记》中所展现的富丽堂皇的东方帝国。
结语
毛姆在中国的山川城郭间旅行,他看到的是落后贫穷、山河破碎的中国。他以“他者”的眼光,来揣摩中国人的性格和生存状态,一方面,难免有错位,甚至有贬低或丑化;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文化充满了好奇,不断挖掘东方文化的原始光彩,他似乎又看到了曾经地大物博、富庶无比、有着悠久灿烂文化的古老中国。在这片魅力无穷的东方乐土上,呈现出令人敬畏的长城、精雕细琢的飞龙、富丽堂皇的建筑、富有诗意的园林艺术以及满腹经纶的儒雅学士。这既是毛姆带有西方优越姿态的书写,又是不断找寻在文化记忆中保存下来的西方集体无意识的书写——最早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便是充满了异国情调和传奇色彩。
[1]转引自李正国.国家形象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2]〔英〕毛姆.在中国屏风上[M].唐建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3]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英〕毛姆.面纱[M].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5]尹萍.艾·巴·辛格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之犹太性解读[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6(4).
[6]王寅生.西方的中国形象[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
[7]周宁.龙的幻象[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刘海燕)
Culture“TheOther”intheImageofChina——A Case Study of Maugham’sOnaChineseScreen
YIN Pinga,QI Guo-jiangb
(a.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b.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ihe University, Heihe, Heilongjiang 164300,China)
The travel noteOnaChineseScreenwas written by English Writer Maugham when he travelled in China.It paints a bizarre image of China by visiting the landscape of mountains and rivers,as well as the cultural landscape.At the same time , he describ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from the high-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the ordinary people.It embraces the Utopian image of China in the culture “the other” and the image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Meanwhile, it embodies the social,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aradigm of the writer’s group.
Maugham; culture; image of China
2017-08-15
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文化诗学视阈下近代以来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及中国形象变迁研究”(2017D077);黑河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以来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及中国形象变迁研究”(RWY201709)
尹萍(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河学院通识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4
I206
A
1008-3715(2017)05-0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