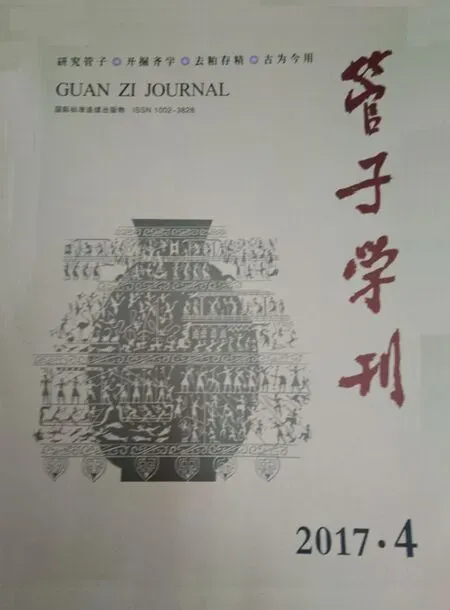从《郭店简·性自命出》对比印证荀子礼乐教化思想
王庆光
(中兴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台湾 台中)
新出土文献研究
从《郭店简·性自命出》对比印证荀子礼乐教化思想
王庆光
(中兴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台湾 台中)
儒家崇尚周文化。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在周文化中,“礼”“乐”相辅而成,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孔子称许“郁郁乎周文”,推动“文之以礼乐”的“成人”理想。荀子对“礼”作了深刻的分析,对“乐”同样做了认真的讨论。《郭店简·性自命出》被公认是论述心性教化的专篇,其言养性、心术与乐教有重大参考价值,拟将其与《荀子》对比,希望透过传世文献、出土竹简的对比印证,获得对先秦儒学礼治主义比较全面与深刻的理解。以下分为四小节进行论述:一,《性自命出》的节次划分、各节内涵、学派归属的衡定;二,《性自命出》的心性、礼乐之教、心性论;三,从殷周礼俗差异解读荀子礼乐教化思想;四,荀子礼乐教化思想与《性自命出》的深层比勘。并简单作一“结语”。
养性;心(志)与物;心术;礼乐教化;比勘
郭店竹简于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墓出土,墓的年代约当于公元前4世纪末,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竹简书写时间应早于墓葬,著作年代自然还要早些,均在《孟子》成书之前。竹简文献,主要是儒家与道家著作。儒家著作有《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缁衣》《穷达以时》《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语丛》(一、二、三、四)等共计十四篇。其中《缁衣》《性自命出》重复出现于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购回的竹简,被命名《性情论》者内容相当于郭店简的《性自命出》,是《性自命出》的又一版本[1]1。《性自命出》言心性论、乐论、情论,在14篇中字数最长,有1580字,共67枚简。学界分之为上、下两部分,称为上、下篇。
一、《性自命出》的节次划分、各节内涵、学派归属的衡定
(一)依李学勤先生的看法,“从简号1到36为一篇,中心在于论乐;简号37至67乃另一篇,中心在论性情。两者思想相关,可能共属一书。然而各为起讫,不是同一篇文字”①李学勤:《郭店简与〈乐记〉》,《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张岱年先生九十寿庆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引自李天虹著《〈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分为上篇、下篇的认定:《性自命出》应分为两部分,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李零先生、梁涛先生等即分上、下二篇。
(二)据谢耀亭先生,依文意,《性自命出》可分为四部分:总论(1-9节)、性论(9-14节)、礼乐之教化(14-35节)、求善心(36-67节)。他概括《性自命出》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总论(纲)整体阐释的是性、心(志)、物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展示了由外到内、由隐到定的过程,并由此引出相关论题:“性”源于命而溯于天,下启情而达于道。
2.性论,对于性的外显、外显后与物的关系、相互作用等进行详细的论说,并回答了人的性、情怎样向道德逼近的问题。
3.礼乐之教:“教”是一种由外向内转化的手段。教的内容是诗、书、礼、乐。简文作者认为(诗、书、礼、乐内容的)这些东西本来是人所具有的,只是经由圣人的适当处理再用以教人。所以“诗书礼乐”在本质上有一种向心灵层面转化的倾向。“教”是为了让心中产生“德”,此与郭店简《五行》之“德”相同,并非生而有之。这也说明,在此时代,德还没有完全深入到人的心灵层面。第23-35简虽整体为谈“乐”,然其重点直指人“心”……如此,对“心”的探讨,成为理论的深层要求。31-32节与《五行》篇中对“思”的重视是息息相通的。这也让我们认识到一时代的论述,离不开一时代的思想基准。
4.郭店简36-37节具体探讨“求善心”的问题。“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36简)因“心无定志”,是以求心为难①谢耀亭著《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86页。参阅丁原明:《郭店儒简“性”、“情”说探微》,《齐鲁学刊》,2002年第1期。。
(三)《性自命出》作者的学派衡定。《性自命出》专门探讨心性问题,学界根据文献对勘,或认为应与孔门中子游、公孙尼子有关(陈来倾向其属《公孙尼子》之一篇),或推测可能是世硕作之《养书》(陈战国),也有将其归属《漆雕子》或《宓子》或《世子》的一些篇章者。笔者则暂将《性自命出》归属七十子后学礼治主义一派,试述理据如次。
1.“好恶为性”。《性自命出》:“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这里的好恶是指人的内在的倾向和要求。在先秦思想中,《礼记·乐记》云:“好恶无节于内,物诱于外”也是一种以性——物相对而说的例子。《荀子》中也常常以好恶论情性。《正名》《天论》二篇以“好恶”为“六情”之首。《礼论》说:“好恶以节,喜怒以当”“礼岂不至矣哉”。《乐论》更清楚地宣称人民“好恶之情、喜怒之应”若恰当、政治才能平顺,云:“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好恶”既与“喜怒”并言,故一则说:“先王喜怒皆得其齐,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天下畏之。”二则又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以道制欲……乐行而民乡(向)方矣,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这与孟子宣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显然有着共识。
2.喜怒之气为性。“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这是认为“性”是人的喜怒哀悲之气。“气”在中国哲学史上意义有几种,其中之一是指“情”,《大戴礼·文王官人》:“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此也厘清了上述荀子“民有好恶之情”“喜怒之应”的旨意[2]296-297。另外,荀子更从“精气”言“性”。《正名》云:“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又云“欲者,情之应也”,均显示《性自命出》与《荀子》在“气性”上是一个路子。战国兴起“治气养生之术”,《管子·内业》提出人的精神由天之精细之气所构成,精气是人的生命之源。“气”,成了一种不仅可以构成天地万物,而且还是构成人的内在精神的原始物质。陈战国先生于是据此下一断案:“《性自命出》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显然是接着这个(‘精气’)传统讲的。喜怒哀悲是情感,属于心理层面。但《性自命出》认为,喜悦之情是从喜气中发生的,愤怒之情是从怒气中发生的,哀伤之情是从哀气中发生的,悲戚之情是从悲气中发生的。《性自命出》说:‘情生于性。’意思是说,情感并不是性,能够发生情感的喜怒哀悲之气才是性。这种人性论是讲‘气性’的……而此‘气性’则是指喜怒哀悲之气,亦即气即是性,气中并没有一个‘天理’。”②陈战国著《先秦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85页。战国先生也说到“好恶,性也”,不过他认为此表述“不严格、不完整”,其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好恶,情也;情生于性。”“性”指内在的喜怒哀悲之气,“情”指由内在之气生发出来的情感。(同书第85页)
张茂泽认为,《性自命出》不属于思孟学派,而更接近荀子,系统性格介于孔子、荀子之间,是荀子心性论的渊源之一。他表示:“荀子本着气性论,深化且系统化了《性自命出》篇的心性论,将它发展为一个系统。反过来说,《性自命出》心性论,或许正是‘荀子’心性论比较直接的学术思想渊源。”③张茂泽:《〈性自命出〉篇心性论大不同于‘中庸’说”》,《人文杂志》2000年第3期。光案,张茂泽(第一作者)、郑熊(第二作者)撰《孔孟学述》,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亦即是说,《性自命出》的“气”是自然之气,而“天”是否具有道德意涵则尚难确定,至少在心性论的部分的确与荀子相当接近。
不仅在心性论方面荀子比孟子更接近《性自命出》,在修养论方面,《性自命出》强调“习”“教”等后天的经验学习与礼乐的文化陶冶也和荀子一致。譬如《性自命出》认为“心无定志”,须“待习而后定”。荀子则在《劝学》篇中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在孔门七十子后学中,思孟仁学倾向“内圣”、礼治主义倾向“外王”,然而思孟同时开出“外王”、礼治论者亦自含“内圣”。《性自命出》既与《礼记》中的《檀弓》《乐记》互证,又提及“门内之治”“门外之治”有别,故就目前已出土资料来看,笔者较倾向归属七十子后学礼治主义一派①刘沧龙:《〈性自命出〉的情性论与礼乐观》(《鹅湖》月刊总429期,第32-43)说:笔者倾向认为,“性自命出”中的心性论与乐教思想不是子游或公孙尼子的特殊见解,而是代表了孔门弟子一般性的看法。将“性自命出”视为与思孟学派的思想源头有其根据,但必须同时考虑到它和告、荀思想的联系。陈丽桂便认为“性自命出”的思想倾向于告子、荀子一系,该篇对“性”内容的界定,及其对“教”功能与礼乐的肯定与强调,“在在和孟子背离”。但虽如此,她却也表示,“性自命出”的思想内容有统合的倾向,她说:“总结它的主题理论和荀子、告子、孟子,乃至《礼记》的《乐记》《中庸》等部分篇章都有相当类似处或关系,若以这些论著为基点来推测,‘性自命出’明显呈现出统合的情况。”(《郭店儒简〈性自命出〉所显现的思想倾向》,《中国学术年刊》,第20期[1999],第137-150页,此第137页。)。
二、《郭店简·性自命出》心性、礼乐之教、心术论
(一)《性自命出》言养性。首先,《性自命出》设定的一个人性论结构或程序是:天、命、性、情、道。《性自命出》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第 2-4 简)“生”“出”“降”三个字都是产生的意思。“天”是自然界。“命”指人的生命。“道”是从情感开始的,最后达到“义”。使人的情感逐渐地合于义的过程就是“道”,就是人应该走的道路。“义”即合于礼义,与《中庸》说的“发而皆中节”的意思相近。“道”可以是一条从内到外的路(让自己的情感向“义”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是一条从外到内的路(把外在的道德规范逐渐内化为内在的道德情感)。
接着,《性自命出》提出七个“养性”的步骤,其云:“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黜之,或养之,或长之。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黜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第6-7简)意思是说:“物”能够动摇性,“悦”能够使性感到喜悦,“故”能够与性沟通,“义”能够使性得到磨砺,“势”能够使性或出或黜,“习”能够使性得到养护,“道”能够使性得到成长。这些因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势”“物”和“悦”,这类因素是客观的。“势”就是外在的环境和形势。文武时期社会环境好,人性中善的因素容易得到发展。幽厉时期社会环境不好,人性中不善的因素容易泛滥(《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曰),“物”即与自己有关的事务(“凡见者之谓物”)。如孟子所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种能够引发欲望的东西就是“物”。“悦”即能使人的精神得到愉悦的东西,大概指音乐之类。“物”和“悦”也有好坏之分导致人性向善或不善的方向发展。另一类是“故”“义”“习”“道”,这类事物是人为的。“故”即人的创造,如《诗》《书》《礼》《乐》等。“义”即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习”即学习、习俗、习惯。“道”即引导和教化。这些因素对性的发展和形成具有正面作用,能够使人性向着善的方向发展、并最后形成良好而善良的本性[3]88。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在人性的发展和形成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心”。《性自命出》云:“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承前‘物、悦、习’)”(第 1-2简)“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志之不可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第6-7简)“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第9简)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即人的本性大体一样,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与孔子说的“性相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仅是一个意思,更是孔子思想与话语的继承。《性自命出》的新意所在是表述:要想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首先要通过教育使人心向善。“性”是人的本质,“心”是人的意识。通过教育让“心”专注于好“物”和好的“悦”上,引导“性”投向好的“物”和好的“悦”,使“性”得以向善的方向发展。即人性虽然大体一样,但是由于各人用心不同,这就造成了有人日趋于善,有人日趋于不善。而要想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首先要通过教育使人心向善。
荀子与其印证之部分:以上思想与语言跟荀子十分近似,《荀子·劝学》云:“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此外,二者还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点:《性自命出》强调心必须有“定志”才能向善,《荀子·修身》亦重视“志”“志意”,而云:“志意修则骄富贵”“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笃志而体,君子也”。儒家言“立志”,指的是人生在世必须坚持以仁义、诚信为人格理想,遇到颠沛流离的艰困环境,更须贞定生命的韧力表现奋发的意志力。因为道德事业永无退路!
(二)《性自命出》言礼乐之教化。儒家教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既然要做有道德的人,那就一定要注意养性,亦即培养人的道德本性。《性自命出》认为,养性的关键在于“教”即礼乐教化。它说:
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诗》《书》礼乐,其始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第14-18简,上七)
意思是说,《诗》《书》礼乐是为一定的实用目的而作的,后来经过圣人的梳理、分类、体察、节文,把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和义理揭示出来,用来对人进行教化,使人们能够“生德于中”。
礼作于情,或生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序则宜道也。又(或)序为之节,则文也。致容貌,所以文而节也。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拜,所以□□□其举节文也。币帛,所以为进与征也。其辞宜道也。(第18-22简,上八)此段大意是:《礼》是为了能使人的情感得以正确地表达,具有节制、文饰情感的作用。礼中有情、有序、有文、有义、有道,这些因素能够使人懂道理、守规矩、明尊卑长幼,能够培养对别人的尊敬之情。
《乐》不仅能抒发人的情感,而且还能对人的性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和陶冶作用。《性自命出》说:
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够(厚)。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敛。
意思是说,观看《赉》《武》之舞,便会恭敬而振作。观看《韶》《夏》之舞,便会勉励而庄重。对音乐反覆吟咏,会使心灵受到触动,得到熏陶。吟咏得久了,就会使人纯洁善良,使情感的出入合于道义。这是一个人培养道德的开端。而郑、卫的音乐属于邪淫之声,对人有毒化的作用,千万不可接近。《性自命出》所谓“养性”,主就是指以《礼》《乐》对人的性情进行熏陶,熏陶得久了,就会使人性中善的因素得到发展和巩固,从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3]92。
学习、教养、变化是《性自命出》的关键词,乐教对生命中感情的变化讲得格外活泼生动,云:“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哭之动心也,浸杀,其刺恋恋如也,慼然以终。乐之动心也。濬深郁陶,其烈流如也以悲,悠然以思。凡忧思而后悲(第29-31简,上十),凡乐思而后忻。凡思之用心为甚。难(叹,李零),思之方也,其声变则□□□,其心变则其声亦然。吟,游(‘流’,李零,下同)哀也,噪,游乐也,啾,游声也,呕,游心也。”(第32-33简,上十一)
意思是说,“人性相近,其心不远,哭泣、乐音都能动人之心弦,悲戚、欢乐随着体内之气变化、转折,移情之于心,引起人们的沉思……忧思、乐思,是思虑之心对情气之心的提升,反过来加深了悲欢的内涵,辅助了意志之心……这里着重讲声、音、情、气、心思、性格、身形、容色的连续性、整体性,犹如气流,由内而外,由外而内。”[4]7
荀子与之印证部分:1.《劝学》云:“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儒效》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2.《礼论》云:“钟鼓管罄,琴瑟竽笙,《韶》、《夏》、护、汋、桓、萷、象,是君子之所以愅诡其文也。”《乐论》云:“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可见荀子多出《春秋》一经,提出八种古代乐舞,唯独未提及《赉》舞,但已是传世文献最接近《性自命出》这段陈述的了。3.《乐论》云“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与《性自命出》“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够”“咏思而动心”包含的内涵全然一致。
(三)《性自命出》“心术”说、“修德”说
凡道,心术为主。(第14简,上七)
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得,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第36简,下一)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求其心有为(伪、诈伪)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为(伪,诈伪)也,可知也,不过十举,其心必在焉,察其见者,情安失哉?(第37-38简,下二)
恕,义之方也。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智类五,唯义道为近忠。恶类三,唯恶不仁为近义。所为道者四,唯人道为可道也。(第37-41简,下三)
郭齐勇先生诠解:“《性自命出》的身心观,是身心的一体观,也是修身养心的互动观。”(第37-38简,下二)“此章认为,学习圣贤人格的方法途径是乐教。通过音乐教化,人们不会停留在外在形式或现象上模仿,而可以从内心感悟圣贤内在的仁德,做到身心不二,我之心与圣贤之心相贯通。”[5]
(第37-41简,下三)这章为君子修养开示许多门径、方法,“围绕内心之仁的展开,是对孔子‘为仁之方’所做的脚注。孔子强调‘言忠信,行笃敬’,‘温柔敦厚’,‘仁者,其言也訒’,‘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论语·颜渊》)“本篇反对伪诈、虚情假意、文过饰非,认为谨慎是行仁之方,肯定真诚纯朴的可贵。”[5]
《性自命出》又提出《乐》能鼓舞人们勇于跨越死亡:
凡用心之躁者,思为甚。用智之疾者,患为甚。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用身之忭(弁)者,悦为甚。用力之尽者,利为甚。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郁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第42-44,下四)
粱涛先生论《性自命出》对上篇、下篇深度考索之后,断言二者存在着差异,笔者迆录长文,谨供学界参酌,他说:
竹简《性自命出》上篇“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气,“并非是物质性之气,而主要指人的精神力、生命力,具体讲也就是情”。“是人对外物产生的主观情感……是一种自然人性,是气性。这种性自身不具有善、不善的规定,但在后天的作用、影响下,却有成为善、不善的可能。‘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第4-5简)‘出性者,势也。’”(第11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竹简下篇在谈论性时,主要已不是喜怒哀悲、好恶等内容,而侧重于仁爱、忠、信,与此相应,对人性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恕,义之方也。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第 38-40简)
‘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智类五,唯义道为近忠。恶类三,唯恶不人为近义。’(第40-41简)
……
竹简把仁看做是‘性之方’,表明作者已试图将仁与性统一起来,在它看来,仁可能就是性,或者说是由性生出的,故说:‘性或生之。’不过由‘或’一字看,尚有一丝犹豫、不肯定[6]53。人的爱有七种,唯有发自性的爱为接近于仁。这里同样肯定仁来自于性,来自于性的爱,不过它只说‘性爱’近‘仁’,而没有说即是仁,在表达上同样有所保留。仁与前面的喜怒哀悲、好恶不同……而是道德情感,具有善恶的判断能力,表达、反应的是人主体的意志和欲求。人具有了仁、爱、忠、信之情或性……表现出主体的自觉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便是‘性善’者了。‘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第51-52简)
……
从竹简的内容来看,其上篇主要是指‘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而下篇则又提出‘性善’论。这样,由竹简的上篇到下篇,实际呈现出由自然人性论向道德人性论的过渡。……竹简下篇有一处讨论‘情’的文字,由于过份突出情的作用,显得引人注目。‘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第50-51简)
……
‘苟以其情’的‘情’主要是对仁而言,是道德情感,而不是自然情感,而强调道德实践应该从内在的仁出发,不必拘泥于外在的固定礼仪,乃是儒家一个基本主张,它在孟子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竹简乃是这一思想的较早反映。”以《中庸》为对照,可称之为“情感形上学”①梁涛著《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48页。简40-41,学者不详所指,李零以为:“这里的‘爱类七’可能只‘圣’‘智’‘仁’‘义’‘忠’‘信’‘孝悌’等好的道德,‘性’‘情’‘物’恐怕不在其中。作者认为只有出自于本性的‘爱’最重要,而这种‘爱’最接近于‘仁’(因为‘仁’是直接来自于‘性’)。‘智类五’可能指‘敬’‘义’‘训’‘忠’‘信’,这些概念都是君子必知,一定要遵守的道德要求,其中‘信’出于‘忠’,‘忠’出于‘情’,而‘义’是‘情’之所归。‘恶类三’可能只‘不仁’‘不义’‘不忠不信’。它们当中以‘不仁’为最坏,‘不仁’则‘不义’,所以说‘唯恶不仁为近义’。‘智类’可能属于道德规范,‘爱类’和‘恶类’则属于情欲,彼此正好相反。”《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台北:万卷楼公司,2002年版,第141页。)。
《性自命出》要求君子心胸宽广,出言必行,宾客来到,则以整肃的容颜对待,祭祀与居丧《礼》须表现庄敬思念的深情:
君子执志必有夫广广之心,出言必有夫柬柬之信,宾客之礼必有夫齐齐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齐齐之敬,居丧必有夫恋恋之哀。君子身以为主[于]心。(第66-67简,下十二)
荀子与其印证之部分:荀子专篇言修身功夫,《修身》云:“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节。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非十二子》云:“士君子之容,其冠进(‘峻’,高也),其衣逢(宽大),其容良。父兄之容:俨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子弟之容:其冠进,其衣逢,其容悫……缀缀(不背离)然,瞀瞀(不敢正视)然。”
荀子对圣人气象及其知、其行采用叠语作出精彩的形象描述:“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介介兮其有终始也。猒猒兮其能长久也。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统类之行也。绥绥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乐人之臧(善)也。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如是则可谓‘圣人’矣,此其道出乎一。”(《儒效》)这种精致的文学修辞,应与古代宗周贵族“君子听律习容而后出”(《大略》)的严格训练与文化积淀有关。
三、从殷、周礼俗差异解释荀子礼乐教化思想
以上一、二两小节若属礼乐教化的理论剖析,本小节拟落实到政教风俗之荦荦大者观察礼乐教化的实践。殷末周初,继军事行动之后,文王、武王、周公兢兢业业治理天下,《尚书》中的《召诰》:“天既终大邦殷之命……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意思是:老天既已结束了大殷国的命运……每个人民都背着抱着扶着他的妇女儿童,在悲哀地呼吁老天。(纣)却禁止民众逃亡,(要是逃亡的)就把他们逮捕起来。《大诰》:“天休于文王,兴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遂受兹命。”(老天造福于文王,振兴了我们小小的周国。当年文王都是遵从着占卜去做事,所以才能安然地接受了这国运。)《康诰》:“王曰:呜呼。小子封(康叔,武王幼弟)。……膺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说:唉!年轻的封呀。……接受而保护殷国人民的,也就是协助天子来度量老天的使命,使[殷国人民]成为新的民众[意谓革除旧时的恶习])[7]118,93,99。
周公以王命告诉卫国康叔(封):“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意思是:“不孝顺不友爱,是大的罪恶,虽然这对于官府不曾得罪,然而老天给予我们民众的法则就大大地混乱了,那么你就赶快用文王所定的刑罚,惩处这种人而不要赦免他们。”梁启超称为“伦理刑主义”,这是“殷彝”之外的新司法律则。殷周伦理的殊异更显示在婚配观上。
《性自命出》:“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第28简)这里正涉及作者对殷周婚配观巨大差异的理解。本小节陈述孔子、荀子改革东夷与殷遗民风俗习惯的志业。
(一)东夷与殷遗民的“婚配文化”受生殖信仰支配。殷、周二族婚配习俗有绝大差异,前者未脱母系社会,后者坚持父系社会。试阐其义如次。
《诗经》学者解郑、卫恋爱诗表现的母系社会高禖祭祀允许“私奔”之风俗:
风俗问题之严重者是东夷与殷商民族都以“鸟”为其始祖信仰,其婚配文化于《诗经·国风》的邶风、鄘风、卫风、郑风歌颂爱情的诗歌表露部分。孙作云先生说:“殷人的先妣曰‘简狄’,相传简狄无夫,吞玄鸟(燕)之卵而生子,后人便以简狄为禖神。《礼记·月令》说古代祭祀高禖,在燕子北来之候:‘仲春(二月)之月,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求子)。’”这传说最初应该属于殷人系统以简狄为禖神。而且其生子与祓褉(洗涤、行浴)有关。三月三日的临水祓褉,即是祭祀高禖的延长。《诗经》的许多恋歌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唱出的,有时用回忆的形式、追述这种风俗,《诗经·国风》十五首恋爱诗为其记录,《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徂)。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鄘风·桑中》:“期我于桑中,邀我于上宫,送我于淇水之上矣!”“上宫”,我以为即指“社”或“高禖”庙……此诗是在举行桑林之社祭时所唱[8]298-305。
“社或高禖庙”跟婚配怎有关连?宗教史家说:“社祭起源于原始宗教中的图腾生殖崇拜,在商代以后,图腾地域化,遂演变为土地之神。商代立有亳社(当即桑林之社)以祭土地之神。”[9]44谢谦说:“祭社之时,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热闹非凡。《老子》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春台’是春社的另一种说法。民众参加春社,除了祈祷和感恩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精神调剂功能。”①谢谦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1999年版,第100页。当西周封土建侯的制度建立后,社不但是土地生殖崇拜的象征,也具有了区分政治等级的意义(《礼记·祭法》),不同于商代以前的以土地生殖崇拜为中心的社祭仪式,正因为如此,西周的社祭革除了男女狂欢的原始习俗,变得严肃隆重起来。只有在某些教化未行的诸侯之国,还多少保留着原始社祭的“非礼”遗风。社稷之成为国家的象征,正是始于西周这种封建诸侯赐土立社的政治化的宗教仪式。光案,此出《老子》20章,易顺鼎曰:“魏晋至唐,古本皆作‘登春台(台)’,无作‘春登台’者矣。河上本亦作‘如登春台’。”不过,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之甲、乙本《帛书老子》均作“春登台”,而非“登春台”(高明著《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18-319页)。因而谢谦之说法缺乏文献学依据。然而,老、庄倡自然、无为、玄牝,含有殷商母系社会因子,与宗周礼乐社会之家庭观念、国家体制与审美精神显然有差距。西汉武帝采取董仲舒对策独尊儒术,经学时期长达二千年,东夷与殷文化逐渐被淡忘。
“桑林之社祭”为何?庄子以“桑林”祭祀之乐舞为极美,《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梁惠王)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成玄英《疏》:“桑林,殷汤乐名也。”
再从燕、齐、宋、楚之社稷祭祀“合男女而观之”,观察东夷与殷遗民“群婚式孑遗”。谢艳萍女士说:“野人与封建那套‘尊祖敬宗以收族’(《礼记·大传》)的礼法无涉。他们的婚配方式还是‘群婚式’孑遗。《墨子·明鬼》有其相关报导,说:‘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这是殷遗民及东夷祭祀‘高禖’,男女相会的风俗。”[10]
宗教史家亦言:“《周礼·地官》提到古代春社有一种高媒仪式,‘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此时也,奔者不禁。’《墨子·明鬼》中也说:‘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乐而观也。’古文献中只片言支语证明,春秋战国还处处存在着原始群婚的痕迹。不仅青年男女‘乐而观’,一些统治者也乐于前往。《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有‘庄公如齐观社’,观看‘尸女’放纵表演的记载,孔子在《春秋》上注了一笔,‘以其非礼也’,这也是古代祭社的一个侧面。”[9]44
(二)孔子与荀子对于殷民婚俗的导正。从儒家看来“合男女而观(欢)之”则为缺乏“羞恶之心”的表现。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荀子紧跟孔子,肯定“男女有别”,批判郑、卫的诗歌乐舞为“夷俗邪音”(《荀子·乐论》),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
佐藤将之先生揭示荀子“礼义之统”是一套完整的修身、齐家、治国的伦理文明的理念体系,认为伦理文明秩序是人类在宇宙中特有的,依赖礼义予以呈现,“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荀子·礼论》)。何谓伦理文明秩序?可分三层阐述之:1.通过各种礼仪实现“理”:“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荀子·乐论》)2.修身:“伪也者,文理隆盛也。”(《荀子·礼论》)“伪”就是崇高“文理”的修身功夫。辞例:“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荀子·性恶》)“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荀子·礼论》)②光案,孝,《仪礼·冠礼》规定少年之成年、命名与继承之家风。3.君子带头践履:“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子,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荀子·礼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文理”把群体的“人”提升,比埒天地之崇高存在位阶,开出人们日常生活之轨道、呈现伦理道德的文明秩序[11]232。
荀子认为情和欲是人性中最基本的要素,如果任其泛滥,就会导致争夺、嫉妒、淫乱的发生。先王作乐的目的就是引导它们向着有利于社会和谐安定的方向发展,好的艺术能使人和睦、团结,坏的艺术能使人淫乱、散漫,所以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荀子·乐论》)。雅、颂之声正是先王制作的“礼乐”。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贵礼乐而贱邪音”需要解释:(一)礼乐乃“德音”,郑、卫之声为“邪音”,二者本质殊异不能并存。“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出所以征诛,入所以揖让也。”“郑声,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起……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同上)又说:“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同上)
《荀子·乐论》又主张:《雅》和《颂》作为音乐,足以使人表达快乐之情而不淫乱。做为诗文,足以使人明辨是非而不邪恶,这样就可以使人的善心受到鼓舞感动、而不会受到邪污之气的侵扰。
(二)“礼”主分,“乐”主和,二者辩证统一。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没有“乐”社会就不和谐,没有秩序与和谐,社会就会瓦解。因此,荀子在“隆礼”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乐”。“乐”能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和亲和力,能够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男女长幼同心同德、和睦相处。“乐”以一音为主,众音和谐,节奏有度,万变不乱,充分体现了自然、社会、人生之理。“礼”与“乐”相互配合,就能使人们“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悌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荀子·乐论》),使整个社会和谐而有序[3]288。
四、荀子礼乐教化思想与《性自命出》的深层印证
(一)荀子的“情性”学说。荀子对上述“春秋战国还处处存在着原始群婚的痕迹”,绝不会无视,他一方面肯定“纯真爱情”,说:“《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纳于宗庙。”(《荀子·大略》)又说:“《易》之《咸》,见夫妇”(同上);并尊重民间习俗,“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同上)。更重要地是提出“以情说性”的“情性”学说。
荀子论“性”“情”的同一关系:
在《荀子·正名》中有一段明确的表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从文中看来,性、情、欲本是一物,以其天生而有则谓之性,就性之内容言即是情,而情本是一种感应,就此感应言则为欲,名虽多端,其实一也。又《荀子·正名》另云:“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性、情之同一关系更是明白。职此之故,荀子有时候就将性、情相结合成为一个同意复词来使用,只是他喜欢用“情性”而不是“性情”。“情性”也者,正是“以情说性”也。以下皆是《荀子》中所见者:
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非十二子》)
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矫饰其情性……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导不若己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儒效》)
纵情性而不知问学,则为小人矣。(同上)
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同上)
彼人之情性也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王制》)
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礼论》)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性恶》)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同上)
夫子之让于父,弟之让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者皆反于性而悖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而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同上)
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者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同上)
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从(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同上)
除了性、情合言以表示两者不可分之外,《荀子·天论》亦曾曰:“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天情”即是天生固有之情,可见“天情”仍不外是“情性”的同意词(synonym),至于“天情”所包含的内容,此地列举出好、恶、喜、怒、哀、乐等六种,后四种是情绪,好、恶是依于感官对色声香味触等“外物”的刺激、反应[12]17-19。
光案,依《性自命出》语汇,“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第1简),“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第 4简)。
在荀子的理解里,“情性”“天情”出自天生,如果任其发作而不约束,就必荡然无度、违礼失序,甚至“陶诞突盗,剔悍骄暴,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间”(《荣辱》)。所以“荀子总是苦口婆心地提醒人们,一定不能太过相信它或对它掉以轻心。荀子甚至为了逼显出它可能带出负面影响的严重性,还不断地重复地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荀子复尝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则可以豁然了悟,荀子其实没有否定或取消情性的意思,所谓‘性恶’其实只是激越之词。若‘性无善无不善’才是荀子真正的主张。”[12]21
由于老子以“道法自然”(《老子》25章)、“复归于朴”(《老子》28章)、“绝学无忧”(《老子》19章)才是生命的真实义谛,荀子竟以“不事而自然”“本始材朴”的天性为不可靠而主张“天生人成”,并认为唯有“化性起伪”才能营造出美好的人生和社会,这显然都是对老子所进行的反批判,从思想史、观念史角度说,别具提升、进步之意义而当为世人所保爱珍惜者。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荀子》中经常出现带有道德意义的“情”,譬如《修身》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殆乎道,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强国》亦说:“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礼论》更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凡此不一而足。只不过,跟孟子主张“理义之悦我心”、道德情感人人均有不同,荀子或是从后天的奋发努力经过经典的学习与实践或者师法礼义的熏陶之后所重新造就出来“情”“善情”。此“善情”已非“本始材朴”之旧,它毕竟是从“情性”“天情”加工得来的,所以当我们在承认“善情”可以出现的同时,即必须同时相信“情性”“天情”等存在的事实,换言之,人之有“善情”的说法,和“情性”“天情”是非道德(non-moral)或“无道德”(immoral)的主张,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牴触或不一致的问题存在[12]23。
陈德和先生以为依荀子,从本始材朴的“天情”涵化忠臣孝子之“善情”,一种“志意思慕之情”(《荀子·礼论》)。他说:此“善情”已非“‘本始材朴’之旧”,而属“文理隆盛”之“伪”,此已涉及“性伪之辨”“化性起伪”的准确意涵。在荀学思想的诠释中对“性”“伪”关系做如此的新解:(一)马积高先生主张“伪”是不离“性”的①马积高著《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荀子不是说人性中有善的素质,而是说人性中有可以知善的素质和行善的能力。这知与‘能’即《正名》中所说:‘所以知之在人者’之‘知’和‘所以能之在人者’之‘能’。由此可见,荀子所谓‘伪’,其实是不离性的。”,(二)路德斌先生认为“伪”是一种以“义”“辨”为基础的趋善的能力②路德斌:《荀子人性论之形上学义蕴:荀、孟人性论关系之我见》(《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指出:“我们切不可把‘伪’仅仅理解成为一个单纯的工具性的行为或过程,实际上,‘伪’同时也是一种能力,一种根于人自身且以‘义’‘辨’为基础并趋向于‘善’的能力。对荀子来说,‘伪’而成‘善’的过程,实是一个合‘外(仁义法正之理)内(义辨之能)’为一道的过程。’(又参路德斌著《荀子与儒家哲学》,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13-15页。),(三)冯耀明先生则说:“伪”甚至是一种生而有之“性”,显示荀子虽然强调后天学习(“伪”),但“‘伪’而成‘善’的过程,实是一个合‘外(仁义法正之理)内(义辨之能)’为一道的过程”③冯耀明:《荀子人性论新诠》(《台湾政治大学学报》第14期,2005年7月,第175页):“单就‘伪’一概念,不难依之以说明荀子学说中‘善如何可能’的问题。依我的看法,第一义的‘伪’不只是人的内在之能,而且也是一种人生而有之性。”。
《性自命出》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第2-4简)“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黜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第7简)其中的道、情、性是出自天生而然;“故”即人的创造,如《诗》《书》《礼》《乐》等。“义”即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习”即学习、习俗、习惯。“道”即引导和教化。对比之下,荀子以礼义、诗书变化“情性”的思想确实是对《性自命出》上述思想“接着说”的。
(二)荀子言“心术”。荀子重视“心”在道德教化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例如《荀子·解蔽》云:“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道?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记忆)。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己所藏害所将受为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这既是对《管子》道家四篇“静因之道”的补充和发展,也是对老子的“静观”说的深刻批判[13]405。认识论之外,荀子又以“心知”为行为善恶、价值选择的最高依据,“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荀子·解蔽》)。又说:“博学而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心也者,形体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所谓“形体”指的是耳目鼻口舌触等“天官”、好恶喜怒哀乐等“天情”。这异于黄老之学以“道”留处于其中,心中才有神明。“静乃自得”“静则不变”。如果心受到感官的干扰,神明就会流失,就会不清明了。
上述者与《性自命出》:“凡心有志也,亡与不可,志之不可独行,犹口不可独言也”(上三)、“君子身以为主心”(下十二,君子以身正心)的思想是一致的。郭齐勇先生说:“所谓‘身以为主心’是强调以端正身形来端正吾人之心,或者说:‘以身正心’。居恭色庄是用以涵养心性、端正内心的。修内与修外,正心与正身,于此达到完满的统一。”[4]9
陈战国亦言:“儒家《荀子·解蔽》篇讲‘心术’,《性自命出》也讲心术:‘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第14节)一是如何理解别人的用心,一是懂得自己如何用心。……总而言之,无论是事君,还是治民,还是修身,都需要有内在的真诚,都需要有美好而善良的心性。”[3]97
(三)《荀子》倡导“学礼乐”“化天性”“为圣人”。儒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程颐先生说:读《论语》,人格态度没改变者,不算读。荀子以为,人的天生“情性”与社会秩序(“正理平治”)有一个“磨合”过程。要维系社会秩序(外)和节度自然欲求(内),就必须“学”、必须“为”、必须“伪”,控制、节制、改变自己的内在自然性。陈战国先生阐释“学为圣人”的意涵,论述精当,迆录如次:
荀子所说的学习,主要是指学做圣人,而不是学习一般的知识。他说:“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荀子·礼论》)
荀子认为,学习需要专心致志,日积月累,“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今使途之人伏术为学,专心致志,加日悬久,积善成德,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荀子·性恶》)
对人的教化需要三个方面的配合:一是礼的约束,二是老师的教导,三是环境的影响。“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情安礼、智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学习要达到全面而纯粹的地步才算完美,所以要对“经”和“礼”反覆诵读,认真思考,以求达到融会贯通。要效法良师益友努力地去实践。要去掉不好的东西、培养有益的学识。直到眼睛除了这样的知识不想看,耳朵不想听,嘴巴不想讲,心除了这样的知识不想思考。久而久之,“经”和“礼”中所讲的道理和为人准则就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其人也就有了坚定的德操。
这是对《性自命出》云:“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第7简)更深层与全面的道德学习思想。
《性自命出》全然印证了礼乐之教,而云:“《诗》《书》《礼》《乐》,其始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也。”(第15-18节)
“凡古乐隆心,益乐隆指,皆教其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第23-28简,上九)
“乐之动心也,濬深郁陶,其□则流如也以悲,悠然以思。凡忧思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凡思之用心为甚。叹,思之方也。凡声变,则其心变。其心变,则其声亦然。吟游哀也,噪游乐也,啾游声也,呕游心也。”(第30-33节)①释文依李天虹著《〈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荀子重视后天学习、规范的制约和环境的影响,这是他的教化论的突出特征。就普遍状况说,道德的形成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依《性自命出》用语,由执礼到安礼。荀子认识到这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所以他重视对人的教化,重视化性起伪[3]283。
刘沧龙也得出类似的断言,他说:“圣人以诗书礼乐等人文活动施行教化,没有了礼乐的制作,心志也不会有所定向,对儒家来说,德性的培成必赖礼乐。作为文化传统的更新者,孔子认为礼的内在生命是仁,另一方面,也唯有经过礼的形塑,仁才得以具体呈现。《语丛二》言及仁、忠、信和礼、乐,简文说:‘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仁忠信,由中出;礼乐刑,由外入。”[14]
结语
本文针对《性自命出》与《荀子》对共同关切的养性、心术、礼乐之教等议题做一对比印证。兹略作结语:
(一)《性自命出》应系孔门七十子后学礼治主义的一部作品。“好恶,性也”“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是“气性”论,宜归礼治主义一支。《性自命出》设定的一个人性论结构或程序是:天、命、性、情、道。以人的生命生自自然界(天),“道”从情感开始,最后达于“义”(符合礼义),“道”可以从内发展到外,也可以把外在道德逐渐内化。《性自命出》云:“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诗、书、礼乐,其始皆生于人……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教,所以生德于中也。”《性自命出》云:“诗、书、礼、乐,其始皆生于人。”诗、书、礼、乐等教材经由圣人亲自体会并整理出一套学理用以教人,使人们积淀而内化,最终心灵层面转化。
(二)《性自命出》:“《赉》《武》乐取,《韶》《夏》乐情。郑、卫之声,则非其声也。”我们从殷、周二族的“注错习俗”做源头性的考索。说明《国风》恋爱诗反映殷礼虽然在许多方面被周族学习,却未脱母系社会与群婚(后者来自高禖祭祀),自孔子以来至孟子、荀子都提“人禽之辨”,其关键在于要社会民俗往“亲亲、尊尊、男女有别”(《礼记·丧服小记》)改变。荀子批判男扮女装之怪异(《荀子·非相》),但也肯定纯洁爱情的价值,以为“其诚可比于金石,其情可纳于宗庙”(《荀子·大略》)。荀子也与《性自命出》共推音乐教育的快速效果。后者说:“声,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前者云:“乐,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乐论》)
(三)《性自命出》与荀子教化思想有极大的印证契机。1.“性”来自命、天;“德”来自圣人有意识地教化。诵读《诗》《书》,熏陶于礼、乐之中,道德就在人的内心扎根(“生德于中”)。与“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义理相当。2.此种自外而内的德育礼论重视的是涵化(acculturation),主张品德来自学习与实践的累积。《性自命出》:“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与《荀子·荣辱》:“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君子安雅,越人安越,楚人安楚,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荀子·劝学》:“礼者,道德之极也。”可做对比。
(四)荀子惯常使用“情性”这个复词,以及同义词“天情”,荀子其实没有否定或取消情性的意思,所谓“性恶”其实只是激越之词。若“性无善无不善”才是荀子真正的主张。《荀子》中经常出现带有道德意义的“情”。《修身》:“士君子不为贫穷殆乎道,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强国》亦说:“夫义者……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礼论》更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这一方面与竹简《性自命出》下篇有一段讨论“情”的文字,由于过份突出情的作用“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第50-51简)显然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1]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M]//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2]陈来.荆门竹简《性自命出》篇初探[M]//中国哲学,第 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3]陈战国.先秦儒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郭齐勇.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五行》发微[C]//丁四新.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5]郭齐勇.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心术观[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6]廖名春.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校释[M]//清华简帛研究,第1辑,2000.
[7]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
[8]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6.
[9]张践,马洪路,李树琦,史仲文.中国春秋战国宗教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宋艳萍.从《谷梁传》、《公羊传》看鲁、齐文化的不同[J].管子学刊,1997,(2).
[11]佐藤将之.荀子礼治论渊源与先秦诸子思想研究[M].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
[12]陈德和.孟荀性情说的共法与不共法[C]//陈器文.第六届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
[13]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导论[M].台北:万卷楼公司,1993.
[14]刘沧龙.《性自命出》的情性论与礼乐观[J],鹅湖(月刊),总429期.
K877.5;B222.6
A
1002-3828(2017)04-0096-11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4.16
2017-10-13
王庆光(1945—),男,山东淄博人,中兴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哲学博士。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