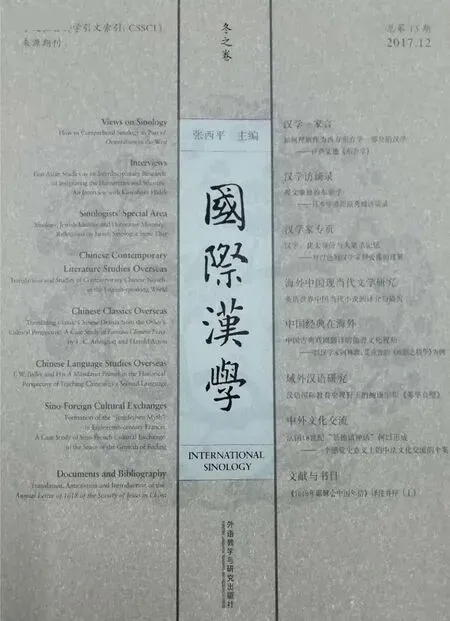韩少功《马桥词典》中的回环观与文化悲观主义
□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从形式上看,是一部关于湖南东北部马桥村的方言词典。词条内容包括趣闻逸事、叙述者的见闻、传说等,大多数的篇幅都足够长以拥有自己的叙事结构。它们被拿来同“志怪”“笔记”,以及在中国有一千多年发展历程、兴盛于清朝的“小品文”对比。韩少功在倒数第二个词条“白话”中指出:与目前普遍认同的观点相反,“白话的原脉”①韩少功:《马桥词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来自“从魏晋时代的《搜神记》到清初的《聊斋志异》”的汇编。韩所说的这些神怪故事里的“白话”意涵,必然是其形式和内容中的固有部分,即便蒲松龄的作品是文言文。
有些词条开始所说明的关键词后来仅在半途中突然出现,且与该则故事的联系也不紧密。中国学者对“关键词”的熟知,不只是因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那本《关键词》(Key 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刊物所载论文的开头就已经有“关键词”一栏,以便于主题检索。审查机构后来也以此方式找出具有“颠覆性”的言论。扎米亚金(Yevgeny Zamyatin)的反乌托邦作品《我们》(We)的每一章都由“关键词”开始。
《马桥词典》中的人物均称呼自我戏剧化的叙述者为“少功”,但我们知道,作者韩少功已经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马桥。读者由此可迅速推断出,这个村庄、方言、“少功”与真实生活并不完全对等,它们应该是作者丰富的讽刺性想象的最佳反映。
虽然有着独特的结构与内容,《马桥词典》(简称《词典》)也可以看作是由一系列故事串联而成的小说—相比较《红高粱》《九月寓言》《在细雨中呼喊》中的故事,或是魏晋及清代选集中彼此不太相关的故事,它们数量更多,更简练多样。《词典》中的词条一般都富有教益,由自我戏剧化的编者/叙述者说出,他偶尔离题,抒发其对人生、语言、民族志学上“差异”的哲理性思考。《词典》经过了精心布局—最好从前往后阅读。有时连续的几个词条构成了一个故事、人物速写片段或是一次冒险的推理想象。将《词典》当成一部小说阅读,可发现其中的人物在重复出现,有本地的情报员,也有同叙述者一起被下放的知青同志。结尾处的一组词条便描述了叙述者“少功”在约二十年后,到马桥再学习时与村民重遇的场景。
因此,《马桥词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但其情节总体上有着时间次序和大纲模式;比起本书提到的其他小说家,它的叙述者更自觉地扮演了业余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角色。小说中有三条散点式、相互穿插的情节线索分别联系着三个不同阶段的中国历史:叙述者作为“前红卫兵”的经历关联了毛时代晚期的马桥;马桥村民怪异地只记得20世纪之后的历史,对19世纪90年代狂热并具有创伤性的“莲匪之乱”竟一无所知,但叙述者/研究者却认为这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的重大地方历史事件;叙述者自己对马桥地方史进行研究,从公元前下溯至军阀割据、日军侵华、共产主义时期、到后毛时期收尾。马桥村民关心的大事,都是一些纠纷、劳动时的不幸、婚外情或其他怪异行为,而不是像《九月寓言》与《生死疲劳》中能引起领导者和历史学家关注的事件。
故事情节有时可用来解释历史“事件”,并不意味着这些事件都真实可信。马桥村民由联想进行推论(例如,蛇被认为是好色的,因此女性的画像可以用来抵御它)具有主观任意性,该特征同样存在于叙述者自己的词源学推测①这在第三个词条里已有明显表现:作者由古地名联系到现代某地,只因为它们在名称上有一个相同特征,并不去检验其间两千年的地名演变史。、将当地特有习俗与古籍记载相联系的做法中。读者甚至不敢确定,这些“奇怪的”当地信仰、习俗和语言使用是否真有关联?是否是在实际使用中产生的讽刺性变体?或者,像韩少功的著名“寻根”小说《爸爸爸》那样,将其他文化中的风俗移植到湖南以获取震惊效果。②韩少功将此告诉沈从文的研究者凌宇,凌宇在一次长沙研讨论会中提到,作者之前也有引用,可参见Jeffrey C.Kinkley,“Shen Congwen’s Legac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1980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Ed.Elle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Cambridge, M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第98、102页,第399页注释71。例如,女性身体带毒、忌讳与初恋结婚的说法让人联想到湘西的一些传说,那里是韩少功的祖籍地,是与湖南东北部全然不同的地方。③参见Jeffrey C.Kinkley,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尤其是第154—155、231页,第288页注释8。
叙述者从古典文献中引用的段落,及其参考的当代历史学家对古四川“巴”文化的观点均是可信的,但“莲匪之乱”以及作为其出处的地方志却都是虚构的。④这里指的是《平绥厅志》,应该是韩少功根据其湘西苗地知识虚构出来的,该地区确实经历过“平定”,也设有“厅”,但“平绥”也可能是一种双关,指代平绥或北平—绥远铁路。蔡元峰在其著作的第36页注释66中,将这一虚构的起义与真实的苗民起义相联系,但苗民起义是在湘西和贵州一带,而不是湖南东北部。这里的“莲匪之乱”可能是指江西省的莲花县,进而可联系到毛泽东1927年领导的秋收起义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国共战争。可参阅 Howard Y.F.Choy,Remapping the Past: Fictions of History in Deng’s China, 1979-1997.Leiden: Brill, 2008。我们知道,无论该作品中的人物对致使“前红卫兵”下放的“文革”以及其他事件多么漠不关心,他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经一场革命、土地改革和大跃进后的饥荒重塑的世界⑤叙述者在书的第37页列出了这些事件。,与《爸爸爸》中湘西部落乡民的生活环境不同。例如,马桥有一位不受欢迎的“前地主”,他过去拥有的田地被称为“台湾”,因为穷困的村民希望将其“解放”并占据!一些马桥的特性可纳入源于冲动而对中国“国民性”的讽刺性分析中,这项工作具有多方面寓意。正如马桥当地方言的意思与现代标准汉语里的意思相反,“莲匪之乱”让人想到“文化大革命”,后一时期的红灯表示“前进”,而不是“停”。探索对立事物的统一性,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滑稽模仿。反叛所表现的主题,语言的力量、禁忌、意义的颠倒有时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该书接近结尾处的一个词条是“民主仓”,这是牢犯们的特有用法,与“因提倡民主被捕”完全无关。而下一个词条所说的“天安门”,也与北京的同名建筑相距千里。
《马桥词典》将历史写成故事,讲述“文化–历史”的静止与循环,这与《爸爸爸》有相似之处。每一个词条或一组词条都以新的视角展开新的叙述,比如讲乞丐王“九袋”的故事的那个词条,便同本书第二章论述的那些小说的开头一样,让读者对年代问题感到困惑。乞讨本是旧社会的现象,却在近些年来重新出现;这耗费读者不少时间来读懂该词条是在写过去—是以回顾“文革”年代事件为总旋律外的一个倒叙。叙述者在无休的、哲理的思考中,质疑小说中的线性时间及因果关系说法的合法性:
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事物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①《马桥词典》,第64页。
这便是历史的回环往复的首要“意义”。“马疤子(以及1948年)”这一词条对此有很好的体现。1982年,叙述者“少功”了解到马文杰获得平反,从土匪变成了爱国功臣。叙述者思忖道:“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1948年并不是1948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这个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嵌入了我的1982。”②同上,第98页。即使是在集体化以后,一些田地还借用人名来命名,让人想起它们革命前的主人。③同上,第120—124页。再比如,叙述者有一次差点被加上“反动”的罪名。因为他在读马克思的书,而不是毛主席的。这时候,公社干部喊道:“什么思想?”④同上,第158页。这本“问题”书,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就像《长恨歌》里所说的,悲剧总在复现,第二次是喜剧。
叙述者发现,马桥人编造毛主席语录,就像古人经常假借孔子、老子之名编造圣言那样。⑤同上,第164页。在后毛时代,旧社会的风气重现的现象尤其惊人:“赌博出来了,娼妓出来了,拦路打劫出来了,好,鬼也出来了。”⑥同上,第220页。这些曾在马桥待了六年的下放知青,本应该有可能为当地人的生活打开一扇新窗,但后毛时期的马桥却没有他们留下的任何痕迹:“连土墙上一道眼熟的划痕都没有。”⑦同上,第264页。与此相反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些老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大用了,现在又纷纷出笼卷土重来,不了解实情的人,可能误以为是一些新词。”⑧同上,第299页。其实循环复现的现象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叙述者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指代“杀人”“行贿”“无赖”的词语;其中有两个词据说是源于解放前的秘密组织“红帮”的用语。
这些都给人性投上了一层阴影。或许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当书中所有逸事以多种模式发生后,叙述者在阐述历史的回环模式时将历史性复现直接与反乌托邦的观点相连。
在我看来,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无非是坚持完与元的两分。把历史看成是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他们所有的荣辱成效毁誉得失,会永远一清二楚地保存在那里,接受精确和公平的终审。他们的执着将最终得到报偿。而历史的悲观主义者,无非是坚持完与元的合一,把历史看成一个永远重复的圆环,他们是不断前进的倒退,不断得到的失去,一切都是徒劳。⑨同上,第341—342页。
《马桥词典》所认同的观点在此不言自明。上述引文源于倒数第三个词条,标题为“归元(归完)”。小说最后一部分回到叙述者作为知青刚到马桥的场景,他在第一次看到那个村庄时问道,为什么它叫作马桥?却没有得到答案。他以为只要掌握了马桥人的起源,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并在这样的误解中开始了他与村民的纠葛。可是,马桥人哪有起源!
叙述者认为历史是回环往复的,进而悲观地看待历史,这并不意味着马桥人持同样的观点。对于像叙述者这样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身处无尽的圆环中唤起了他们对“现代”的焦虑。在所有叙述者对文化差异进行辩护的哲理性话语中,他似乎必须将马桥人看成是可悲的、未启蒙的。
《〈论语〉与近代日本》(刘萍著,2015)
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刘萍教授著的《〈论语〉与近代日本》一书于201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主要探讨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古代典籍——《论语》,自19世纪后半叶“明治维新”(近代)以来在日本的研究史与接受问题。本书共有五章。第一章“近世日本《论语》流布概说”,讨论在近代之前《论语》在日本的传播史。《论语》在近代日本的传播呈现出空前未有的态势,对于《论语》的研究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中广泛而深入地展开。因此,本书的第二、三、四章分别以近代日本中国哲学思想领域、中国历史学领域以及中国文学领域的《论语》研究为主题,以服部宇之吉、武内义雄、山路爱山、津田左右吉、吉川幸次郎的相关研究与论著为个案进行研究。本书的第五章专门讨论日本近代文学家的《论语》情结。例如,下村湖人、中岛敦选择以《论语》为蓝本,以《论语》中的孔子、孔门弟子为人物原型,构造其文学创作《论语物语》《弟子》,以此寄托作家自己的人生理想,阐发其学术思考与追求。总之,作为一部传统文化典籍,《论语》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就东亚特别是日本文化发展而言,《论语》也是一部不能被遗忘的文献。近代日本的《论语》研究,折射出日本民族自身近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挑战与所做出的抉择。(秋叶)
——《革命后记》初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