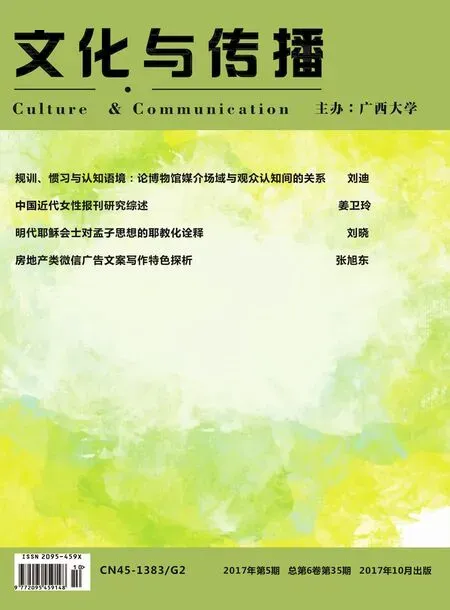数字时代下品牌资料库的文化叙事
秦 莹
《王者荣耀》的舆论在商业和文化领域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讨论。第三方数据机构App Annie近日发布的2017年5月全球手游指数榜单显示,《王者荣耀》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手游,也是全年在国内游戏产业引起热议的现象级新品游戏,根据5月腾讯公布的2017年最新一季度的财报显示,在收入上,《王者荣耀》今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就达到60亿。①转引自王梓辉:《王者荣耀:一款成功的游戏为什么变成舆论的公敌》,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7月7日。数据分析出《王者荣耀》的核心用户群体特征以及捕捉到这部分群体的消费习惯,如消费层次、常购品牌、消费频率等,预测哪些品牌的广告适合植入。通过布置《王者荣耀》线下城市赛以及玩家交流赛的文化展演,将更多包含口语的、文字的、图像的、视频的多模态呈现形式的多元信息输入到品牌资料库这个多媒体文本中。品牌资料库是品牌营销的有力保障和决策基础。资料库的集成一部分来源于品牌内部的生产、加工、营销、流通数据,一部分来源于品牌线上与线下的用户社群数据。前者多是以数据记录并保存,但后者带有明显的多模态属性。这些数据并非只是建立于能见度的基础,主要还是建立在解析度之上,其背后有一套深刻的算法和编码组织。不少学者提出一些观点,“我们所经历的当代数字媒体世界,本质上是借由0s和1s位元组成的世界”(Holtzman,1997:123),由此形成一种组织模式,资料库似乎已经开始渗透文化,并开启了文化叙事的开端,聚焦于数字系统与社会及文化效果(Steyerl,2009)。Lev Manovich以激进的方式思考了数字媒体的本质,并认为数字媒体是无数软件技术、演算法、资料结构以及界面惯例与隐喻的发展与累积的结果,这意味着数字媒体、新媒体、全媒体的新特征并非存在于其内部,而是存在其外部(邱志勇,2014)。由此看来,数字化过程正牵涉到一个知识典范,一个以各种新方法来中介真实以及人类经验的新典范(Manovich,2003)。每一次知识典范的转移都伴随着对本体、关系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对本体的认识又是基于对主体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而媒介、语义和叙事的数字表征和多模态属性正是突破这层关系的切入口,在数字时代可以被用来作为分析资料库的起点。
一、语义、媒介和叙事的数字化流变
“我们正进入一个历史时刻,一个影像胜过文字的时代”(Gombrich,1982:137)。环境的改变和三点有关:语义的表达模式逐渐转向图像;传播的媒介逐渐转向流媒;叙事的对象逐渐转向网众①有关“网众”的概念,请参阅杨伯溆(2002a)。,同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企业与用户的传受关系的改变:传受间意义的流动性开始明确指向传者的邀请、受者的参与以及二者的共构。
(一)语义:从图像流变
语义的表达逐渐转向图像(Kress,2006)。这意味着赋予视觉影像与语言相等的地位,两者皆是通过人为的建构与诠释而产生的。传统的口语与文字书写已不再是建构意义、产生知识的唯一途径,视觉影像亦是意义建构的重要机制(Mitchell,1992)。正因为视觉影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响着人类的文化与生活世界,W.J.T.Mitchell继Richard Rorty因对于语言是否能详细描述真实世界持有怀疑而提出“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后,提出“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数字图像是各种表达形式集于一体的产物,视觉的、文字的、口语的元素结合以及配合。作为当代视觉文化的多媒体文本,数字图像是一种观看和理解的方式。语义学传统一直维持着重口语文字、轻视觉图像的倾向,然而随着美国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高度仰赖视觉图像的传播诉求,以及日新月异的传媒科技和视觉化时代潮流驱使,视觉语义于20世纪末成为语义学中新颖且备受关注的思想脉络(Medhurst,1982;Olson,1991)。
(二)媒介:从物质流变
传播的媒介逐渐转向流媒。Marshall Mcluhan认为不同的媒介形式会影响甚至决定人类的感知与社会组织。人类历史步入印刷文明后,进入了以文字书写为主导的视觉感官时代;到了电子媒介时代,多重感官经验可以深化受众参与,将全球化受众的情感经验开始进行联系(Lull,2000:43-44)。“每个媒介域都是已有的工具和做法相互妥协的结果,并嵌入不同时代的技术网络”(德布雷,1991/陈卫星译,2014:261-262)。一方面我们开始关注当下互联网的流媒体属性,这让我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物质媒体思维,开始使用全媒体的思维特点:接触点多,形式多,平台多,全关系,多构面;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了媒介的行动逻辑,媒介作为技术/文化的复合体,本身是一种生产关系。人对媒介的掌控和驯化,赋予它特定的意义之后,作为一种技术/文化的复合体的传播媒介又反作用于传受双方。简言之,使用者赋予媒介的意义影响了媒介,反过来,当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媒介参与我们的文化建构和日常互动之后,它又影响了我们的感知、经验和行为(刘海龙,2017)。
(三)叙事:从用户流变
叙事的对象逐渐转向网众。随着语义与媒介的流变,单一空间与特定时间的叙事模式被“全媒体叙事”模式替代,这一过程伴随着用户从窄众到网众的扩展。讲故事(Storytelling)一直是人类经验的核心——我们如何解释和理解世界。但在数字时代的今天,自媒体受众有了渠道获取广告信息,同时寻找更加身临其境的娱乐体验,企业和用户的沟通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由畅销书作家Robert Rose与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合作提供的“战略叙事”(Strategic Storytelling)介绍了“叙事思维”(Narrative Storying)的概念,并展示了如何在数字世界中实现最大的影响,开创了对叙事及其在数字时代中的作用的新认识。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讲故事比理论论证更容易改变人们思想,这意味着人们需要以叙述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因为故事为现实提供了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是理解世界的关键。战略故事讲述建立在这些见解之上,以展示品牌展演的故事。很多跨国企业在使用战略故事模型,旨在管理受众在高度互联的数字环境中所期待的复杂的叙事生态系统。该模型的四种参与层次分别是:传播出版(Broadcast and Print)、互动(Interactive)、线上参与(Participatory [Online])和真实体验(Experiential [Real World])。这四个层次共同组成了一个加强网络,加强现有用户的联系。
由此可见,在媒介、语义、叙事相互渗透的数字时代,品牌资料库的集成正在逐渐由文本转向多模态,由物质体转向流动,由窄众转向网众,形成一种受众参与的多空间、多维度、全视角的动态体验,资料库美学在数字时代中已经变成一种重要的文化叙事,收集并创造文化细节的知识(Fuller,2006)。这一创造是品牌传者与消费者共同参与和完成的,消费者的参与已经成为文化产品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变成生产商和消费者共构的结果。在这种传播现象中,“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得到了以下三方面的阐释,其一是“我与你”的交流/传播,一种平等的、共享的、能动的、双向的互动(金元浦,2003:24);其二是多个主体的交流/传播,包括传者、受者、符号、文本、媒介等,特别是传者、受者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对于传播过程而言最为关键;其三是主体间多种方式的交流/传播(黄卫星&李彬,2012),例如移情的倾听(empathic listening)( John Stewart,2001) ,例如邀请语义(Invited Rhetorical)(Sonja K.Foss& Cindy L.Griffin,1995)。
二、品牌资料库的文化叙事
资料库美学的文化叙事是参照波普的实践实证主义、库恩的范式革命、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社会等等。每一次范式的转移都是一次文化叙事的转移,同时也是一次理性重建的过程。波普科学哲学的任务是为科学知识的增长建立一套方法论规则,以使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得以“理性重建”,这套方法论规则被波普称为科学发现的逻辑。我们遵循波普的逻辑,就会发现Manovich所说的“数字化过程牵涉的新的知识典范”也不例外。在此从巴贝塔的知识社会说起,考察品牌资料库文化叙事谱系,思考资料库作为一种实践理论,为数字时代提供了哪些可能性。
(一)巴贝塔的知识社会考察
今日社会的各种制度里,信息网络与资料库实力不容小觑,数字时代媒介、语义和叙事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以模拟再现为目标的原始符号和叙事传统,而是回到本体论角度转换人们对媒介、语义和叙事的知识典范。我们无法以过去的符号学或静态影像的概念来理解数字时代,软件背后都是多模态式的资料库文本,数据的操作与运算,数字音频、视频文本、背后的统计原理有着统计社会学的知识考量,又夹杂着数字时代的知识社会学因素,如媒介的变迁、资本的融通、人口的流散、地域的消解等等。“在人的社会里,任何的概念基本上都负载着特定的文化意涵与历史期待,因此,并非是超越特殊时空的绝对客观中立性的”(叶启政,2001:3)。从逻辑的观点看,如果两个理论都能解释同一套观测资料,比较简洁的理论应当较优。但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界面对两个能解释同一套资料的理论,不一定挑中较简约的那一个。科学史家不再想在旧科学中寻觅较具永恒性的要素,他们想要表现出,旧科学在它所盛行的时代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库恩,1962/王道还,傅大为,程树德译,2007)。品牌资料库在数字时代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也必然沿袭了口语文明与印刷文明的知识社会特征,尽管在书写与语言主宰的年代中,口语与视觉图像在人类社会扮演沟通传播的角色也从未消失。一开始,文字借由视觉图像得以展现,当无法透过文字表达时,符号被发明出来(邱志勇,2014)。当符号的发明累积到一定程度,才出现了媒介、语义和叙事的集大成者——资料库。借用“图像解释学”(iconology)①1955年,Erwin Panofsky将其独立成一研究取径,指向与图像意义解释相关的活动。的逻辑,如果我们将资料库进行知识考古,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图像、影像、语言、文字编制成一套完整的象征形式,并再现出每个时代的意志。如果我们可以挖掘出资料库所承载的媒介、语义和叙事形式的历史,进而人们可以就象征形式所传达出的内容加以掌握资料库的历史。
(二)品牌资料库的文化实践
“在所有的变化中,经济过程的改变是最显著的”(熊彼特,1996,转引自于海,2010:171)。商业、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结构,从而改变了它的精神。从事工商业活动的阶级,绝不会以经院学者的冷漠态度来看工商业方面的问题。随着这一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他的思想也会越来越多地灌输给了社会,这种工作造成的特殊思想习惯、价值图式以及对公众和私人生活所采取的态度,慢慢扩展到了所有阶级那里,扩散到了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所有领域。西方历史上的这一模式一直传承至今,被许多企业效仿。传受关系的改变让企业着眼于更具参与性和分享性的营销活动,开展“品牌共创投入”(brand cocreation engagement)(Vernette E &Hamdi L,2013)行动。消费者以活力充沛(vigor)、全心奉献(dedication)、乐在其中(absorption)的态度,在产品概念、产品功能、品牌形象、消费者体验等创新构面,投入品牌价值之共创,利用互联网将“品牌共创投入”的行动与逻辑扩散到更大范围,获得更多用户的共识和认可,最终目的是以新方法来中介现实,形成人类经验的新典范,展开新的叙事话语。媒体传播国际集团(Omni Media Group)旗下的Hoho Ad传播集团,专门以各类捷运车厢,打造故事空间,透过实体与虚拟的混合,呈现出能与受众体验勾连的品牌视觉叙事,强化消费者的品牌投入度,创造品牌的故事景观(storyscaping)。早在2014年,家居创意霸主IKEA就通过在列车内构造“移动的家居空间”,包裹整个车厢来营造情境的品牌创意。2017年年初,日本现美新干线(GenbiShinkanshen)以“会移动的现代美术馆”为设计理念,邀请名摄影师蜷川实花打造车身,并将新干线由内而外打造成现代艺术空间,各节列车分别拥有不同展览主题。这种体验式营销正是文化叙事的一种,配合品牌精神,在一定空间内创造气氛,鼓励或催眠消费者进入品牌营造的正向氛围。在台湾,已经有许多国际品牌喜欢用创意空间,比如Under Armour行动篮球列车、麦当劳捷运包厢、阿联酋航空安排的欧旅捷运专车等。②参考自《包场不如包捷运,移动体验行销成国际品牌新动力——全世界都在打造移动故事间》,hohoad.com.tw
(三)品牌资料库的实践理性
早在古希腊时期,传统语义学即被建立为一门关于认知与沟通之反思的独特学问,更标志和渗透到整个西方文化之中。语义的发展也出现几次重大转向,口语到书写再到印刷。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修辞学》(Rhetoric)中界定了三种语义类型——强调实用性并与未来有关的政治性论述(deliberative),强调正义与否且与过去有关的法律性论述(judicial),以及强调善恶并和现在有关的仪式性论述(evaluative)。Cicero催生了一门涵盖哲学、诗、戏剧、行动与批评等艺术形式的语义学,Quintilian更认为语义同时包含叙事与逻辑两种符号模式,虽然语义与逻辑两者相辅相成,但却是两种不同的资讯处理方式,直到印刷术发明以及现代科学发展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于理性、真理的命题,对于语义的兴趣逐渐减弱,同时语义也开始注重风格与辩才,语义也与哲学分道扬镳(Poggenpohl,1998)。尽管语义无法达到逻辑的理性,但道德、偶然性的问题也并非单凭逻辑就能解决。语义作为一种实践理性,还是提供了人们一种理解表象的方式,而语义的目的更是为了让受众看清情况,做出更明智的行动。(同上引:211-213)。但媒介空间不断呈现出如吉登斯所说的“失控的社会”特征,网络上出现了各种“乱象”和非理性(支运波,2011)。各类网络社区内话语伦理和语言暴力屡见不鲜,假新闻、标题党此消彼长,我们好奇知识的增长与科学发展的理性基础究竟何在?语义能否重回到古希腊时期与逻辑并行的角色。
三、结语
数字转向背后的悖论是,一方面媒介科技的蓬勃发展创造出各种模拟形式与前所未有的幻觉;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影像的恐惧以及对这种虚拟力量的焦虑(邱志勇,2014)。它绝不会回到天真的模仿或拷贝,它是对于媒介、语义和叙事的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重新认识,它是文字、语言、图像、影像之间的复杂互动。数字转向让我们认识到,数字如同人类的另一种感知,是一个极为深奥的问题,而且数字经验或数字素养无法以文本性的模式解释。Vilem Flusser认为,我们必须对数字化提出某种程度的批判,它的存在改变着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概念,数字化时代存在一个中介,即机器操作者,如果说传统媒介的魔力是一种“神话”,那数字媒介的魔力就是一种“程式”(Flusser,1983/李文吉译,1994:37-38)。如今数字影像以及其他已经成熟的文化形式,是否已经变成了电脑程式码?
虽然以下几个问题不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仍有一定讨论价值,有待后来者进一步讨论。首先是有关于品牌资料库中的数据真实性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势必会牵涉到消费用户的隐私问题。有关数字伦理的讨论倒不新鲜,但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跨国公司的长驱直入,国际品牌的消费用户遍布全球,如果发生品牌数据造假或消费者隐私泄露的事故,将对品牌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巨大挑战。其次是人们应当关注数字时代品牌资料库的本质如何成为叙事的神话。当人们参与到品牌的共构和消费的浪潮中时,如何解构数字时代资料库美学的规律与模式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后是全球消费文化的影响。由于跨国公司的介入,我们正经历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变迁(杨伯溆,2002b),品牌数据库的内容也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和整理。消费文化的全球性扩散不仅仅是爱好、兴趣、审美、习惯的改变,而且是对媒介、语义和叙事在认识和理解上的革命性转变。这种转变最主要体现在全球与地域的关系上。而这一关系又紧紧围绕着全球化的推进,这一事实正在改变着人们对空间、地域与全球的理解。
参考文献:
[1]Arns,I. (2008). On contemporaneity:The media arts in the age of their post-medium condition. In C. Hubler(Ed.),Media arts Zurich (pp. 41-46). Zurich,Switzerland:Scheidegger & Spiess.
[2]Barthes,R.(1977). Image, music, texts (S.Heath,Trans.). New York:Hill and Wang.
[3]Burnett,R.(1995).Cultures of Vision:Images, Media, and the imaginary.Bloomington, 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4]Chaudhuri,S. &Dayal,U. &Ganti,V. (2001).Database technology for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IEEE Computer,34,48-55.
[5]Chen,H. & Chiang,R.H.L. &Storey,V.C.(2012).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From big data to big impa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36,1165-1188.
[6]Debray,R. (1996). Media Manifestos: On the technological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forms. Verso.
[7]Fuller,M.(2003).Behind the blip: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software. London:Autonomedia.
[8]Foss,S.K.&Criffin,C.L. (1995). Beyond Persuasion.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9]Foss,S.K.(2004). Framing the study of visual rhetoric: Towards a translation of rhetorical theory.In C.A.Hill & M. Helmers(Eds.),Defining visual rhetoric(pp. 303-313). 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0]Gombrich,E.H. (1982).The image and the eye: Further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London:Phaidon.
[11]Holtzman,S. (1997).Digital mosaics: The aesthetics of cyberspace. New York:Touchstone.
[12]I.Lakatos,A.Musgrave(Eds.).(1970).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Gambrige Univ. Press.
[13]Kress,G. & van Leeuwen,T. (2006).Reading Images: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4]Kuhn,T. S.(1970).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Univ.Of Chicago Press.
[15]Lima, M. (2011). Visual complexity mapping patterns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6]Manovich,L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7]Manovich,L. (2003). Software takes command. 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
[18]Manovich,L. (2007). Database as symbolic form. In V. Vesna (Ed.),Database aesthetics: Art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flow(pp. 39-60). Minneapolis,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McLuhan,M. (1969).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Signet.
[20]Mitchell,W.J.T (1994). 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Paul,C. (2007). The database as system and cultural form:Anatomies of cultural narratives. In V.Vesna (Ed.),Database aesthetics: Art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flow (pp. 95-109). 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2]Poggenpohl,S.H. (1998).Doubly damned.Visible Language, 32, 200-233.
[23]Vernette,E. &Hamdi,L. (2013) . Cocreation with consumers: who has the competence and wants to cooperate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 55, 4, 539-561.
[24][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5]金元浦.范式与解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6]舒咏平.品牌传播策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7]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28]邱志勇.视觉性的超越与语义的互访:数位时代视觉语义的初探性研究[J].中华传播学刊,2014(12):107-135.
[29]叶启政.均值人与离散人的观念巴贝塔:统计社会学的两个概念基石[J].台湾社会学,2001(06):1-63.
[30]杨伯淑.关于“网众”的社会学理论探索[J].新闻传播论坛,2002(07).
[31]杨伯溆.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跨国公司的介人及其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09):29-38.
[32]黄卫星,李彬.传播: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南京社会科学,2012(12):90-97.
[33]刘海龙.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J].现代传播,2017(04):27-36.
[34]支运波.媒介空间与公共理性[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1(06):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