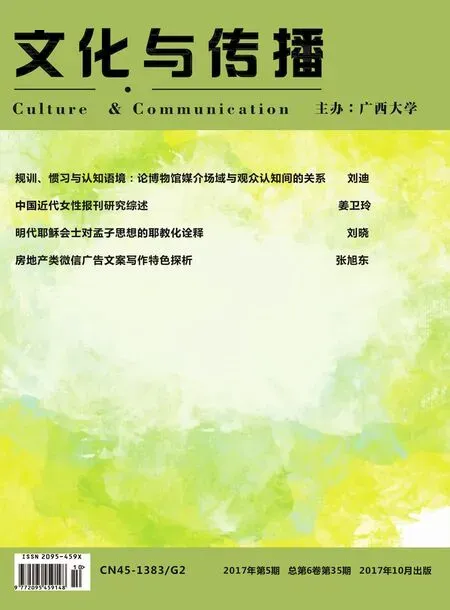明代耶稣会士对孟子思想的耶教化诠释
刘 晓
明代中后期,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掀起了历史上首个儒耶互动的高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当时,借着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契机,天主教各教派如耶稣会、方济会、多明我会等都纷纷向中国进发,企图叩开中国的大门,但是真正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与中国思想文化摩擦出实质性火花的,主要还是耶稣会。
在这次传教活动中,耶稣会派出的传教士大多是饱学之士,不仅对西方的政治、科技、文化有所掌握,而且,他们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为减少传教阻力,耶稣会士接受沙勿略教士提出的“适应当地文化”的传教方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积极研究,力图将耶教思想顺利“嫁接”到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中去。为此,他们努力研习中国古代典籍,找寻、阐述耶教与中国文化主体——儒学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对儒学进行耶教化的诠释,来减少儒、耶文化的差异,力争获得中国社会的认同。
但是纵观明代中后期,传教士对儒学的理解还不深入,具体到孟子研究上来看,表现为传教士对孟子思想的系统研究专著尚未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孟子》一书篇幅较长、内容丰富繁杂,翻译和理解都存在一定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孟子的一些观点、主张与耶教理论直接冲突,这是传教士们无法接受的。虽然如此,孟子依然是耶稣会士会通儒耶时不可避开的话题,在他们所写的各类传教著作之中,可以散见对孟子思想的会通与批判。这一点,以利玛窦最为突出。下面我们将以利玛窦为中心,兼采其他耶稣会士的思想主张,探寻当时耶稣会士是如何创造性诠释孟子思想的。
一、耶稣会士对孟子“天”、“上帝”观念的诠释
在儒家的信仰体系中,“天”无疑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在孟子来看,“天”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
首先,“天”是自然之天。孟子见梁襄王,曾说:“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引用《孟子》,仅注篇名)[1]10在这里,孟子把“天”看成了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久旱天必降下甘霖,这表明“天”是按照自然规律运转不息的。
其次,孟子认为,“天”是人类社会中各项事业兴衰的决定力量。孟子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梁惠王下》)[1]37有德的君子建功立业,并传之子孙,至于能否成功,还得看“天”的意思。在这里,孟子就明确认定“天”是包括礼乐文化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之兴衰的决定者。
再次,“天”还是人之责任及使命的赋予者。孟子在与弟子万章讨论“尧舜禅让”问题时指出,并不是尧将天下给予了舜,而是“天与之”(《万章上》)[1]168-169;谈到禹把帝位“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时,孟子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万章上》)[1]170。可见,孟子坚信,人的职责与使命都是上天赋予的。所以,他才会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样的说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子认为,“天”是“道”之行与废的决定者。“道”是儒家倡导和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提出君子不仅要修养仁、义、礼、智的个人之“道”,还要通过“修身”,由“内圣”而至“外王”,最终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1]94、“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1]13、“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梁惠王上》)[1]13的“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然而,“道”之实现与否,在孟子看来,却取决于“天”的意志:“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1]82这就决定了“天”在孟子思想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重,甚至是高于“道”的。
总而言之,对于“天”的推崇,对于主宰之“天”的认同,构成了包括孟子在内的整个先秦儒家信仰世界的核心[2]。
再来看耶教的天主信仰。耶教的天主信仰以“三位一体”论为其理论基础。“三位一体”论认为,天主是宇宙间唯一真神,但天主本身具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父”耶和华是天主的第一位格,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不仅创造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而且还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进行着监督和管理,担任着拯救世人和审判邪恶的职能,他高高在上但又无处不在,充满慈爱但又赏罚分明;“圣子”耶稣是天主的第二位格,因天主不忍看到世人犯罪沉沦,便获得肉身而降世为人,作为救世主来拯救世人,这便是天主“道成肉身”的存在形态;“圣灵”是天主(此处指圣父与圣子)发出并降临在其教徒身上,用以指引教徒感悟天主、重获新生的一个位格。这三个位格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关系,共同构成耶教之最高信仰——天主。
由对孟、耶最高信仰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孟子的“天”和耶教的“天主”有着相似之处,孟子的主宰之“天”能管理万物、赏善罚恶,且具有至高的德性,这与耶教的“天主”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构成了二者对话与会通的基础。传教士们正是利用了信仰上的这种相似性,才得以实现“合孟”、“化孟”(即耶教化解读孟子)这一工作的。
也正基于此,利玛窦一改之前传教士把天主教最高神的拉丁文名称“Deus”直接音译为“陡斯”的做法,在其著作《天主实义》中,他首次将“Deus”译成 “天主”。这样翻译,正体现了利玛窦对儒、耶在信仰上的相似之处的准确把握——儒家信天、敬天、事天,把“Deus”译为“天主”,减小了文化背景的差异,比较容易使中国人明白传教士所信奉的神到底是什么。
耶稣会士极力推崇原始儒学①原始儒学,指由孔子在春秋时代创立、并由孟子发展的儒家学说,区别于后世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以及现代新儒学。,指出,在《诗经》、《尚书》、《孟子》等原始儒家经典中,经常提到一位最高的神,他有时被称为“天”,有时被称为“上帝”,而“帝者,天之主宰”[4]99,二者其意一也。在《孟子》中,就曾通过直接言说或间接引用的方式,多次提到“天”、“上帝”等概念:
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1]150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梁惠王下》)[1]23
《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离娄上》)[1]126
这些在传教士看来,这些都能证明孟子是有神灵信仰的。传教士在确信了这一点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把孟子等先秦儒家所提到的“天”或“上帝”与耶教的“陡斯”进行会通,做出耶教化的诠释。他们肯定地说:
人谁不仰目观天?观天之际,谁不默自叹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即天主——吾西国所称“陡斯”是也。[4]9
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4]21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传教士对孟耶的会通是相当成功的。被称为“中国基督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对于传教士们的解释十分信服,他说:
孟氏存养事天之论,而义乃綦备。盖即知即事,事天事亲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天主之义,不自利先生创矣。(《天主实义重刻序》)[4]99
然而,在当时也有一些精明的儒士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差别。如士大夫黄贞就曾指出,“圣人知天事天夷不可混说”,他认为,儒家之“天”与耶教之“天主”是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儒家“知天事天”,只需“存心养性”、加强自身修养即可;而耶教“知天事天”,则是对天主的“恭敬奉侍”。如将两者混淆,实是“似道非道而害道,谄儒窃儒而害儒”(《尊儒亟镜》)[8]154。可谓一语道破真相。
二、耶稣会士对孟子“仁”学的诠释
“仁”是孟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是其所倡导的最高伦理道德规范。孟子“道性善”,认为人人皆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扩而充之则为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又以“仁”为“全德”之名,来统率其他诸德。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1]138孟子将“仁”的出发点和实质,归结为侍奉亲人、孝敬父母。孟子认为,亲人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连亲人都不能爱,何谈“仁民”、“爱物”?在侍奉亲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培养、扩充自己的仁心仁性,进而“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1]12,从爱父母兄弟到泛爱天下大众,以至爱宇宙间万事万物,正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1]252。同时,社会的管理者如果能以仁心行仁政,把这种美好品德应用在治国理政上,那么,“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59: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1]4
就这样,由亲人到陌生人、由自身修养到治国理政,孟子把“仁”按照由近及远的递进关系逐渐铺开,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爱”是耶教伦理最核心的原则之一。耶教“爱”的基本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天主对人类的爱,二是人类对天主的爱以及人类之间的互爱。天主是一切爱的总根源,他因爱而创造了人,甚至因爱而甘愿让其子耶稣来代替人类受难,这使人不得不去爱天主。但是由于天主是看不见的,所以爱天主就表现在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是“爱仇敌”的具体行动中。《圣经》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天主来的”(《约翰一书》)[3]。
传教士通过对耶教之“爱”与孟子之“仁”的对比分析,发现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于是他们声称,孟子所讲的“亲亲而仁民”,其实就是天主教所追求的关于“爱”的伦理。虽然孟子没有倡导要敬爱天主,但是爱天主是要通过爱人来实现的:
爱天主之效,莫诚乎爱人也,……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上帝欤?爱人非虚爱,必将渠饥则食之,渴则饮之,无衣则衣之,无屋则舍之,忧患则恤之、慰之;愚蒙则诲之,罪过则谏之,侮我则恕之,既死则葬之。[4]80
这不正是孟子仁政、民本思想的翻版吗?就这样,传教士把孟、耶各自关于仁爱的伦理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以孟、耶伦理思想会通为基础,耶稣会士们对孟子“行仁”的言论均表示赞同,尤其对孟子所讲的舜孝顺父亲的故事表示认可——舜的父亲瞽瞍几次欲加害于舜,用心险恶,然而舜依然尽守事亲之道,孟子对此大加赞扬。传教士们评论道,“恶者固不可爱,……仁者爱天主,故因为天主而爱己爱人,知为天主则知人人可爱,何特爱善者乎?”[4]81教士们从另一个角度,和孟子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其说理的落脚点,最终还是在天主那里。而且,耶稣曾教导人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3]4。由此观之,虽然表面上,耶稣会士和孟子思想是贯通的,实质上,他们已经迥然相异了。
三、耶稣会士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性诠释
耶稣会士在诠释孟子思想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味迎合,他们毕竟是站在耶教立场上来评判孟子的,所以,在会通孟、耶的过程中,对孟子的颂扬或者批判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天主教在华传播。在孟子人性论问题上,因其与耶教人性论的差别显著,耶稣会士就采取了批判性诠释策略。
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善是人先天所固有的本性,是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人只需要存心养性,去除内心的蒙蔽,就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而耶教主张人性善恶二重论[6]:一方面,从人性的先天性上看,由于人性是天主赋予的,而天主是纯善的,所以人性从先天本质上来说是善的,这是从源头上对人性善所不得不做的规定;而另一方面,从人性的现实性上看,由于人经不起诱惑而使自己的本性堕落,所以人性又是恶的。耶教更强调的是,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所犯的“原罪”而导致任何人生来便有罪、任何现实人性都有满满的罪恶这一事实。针对人性论上的这种差异,利玛窦对孟子进行了批评,他指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缺乏逻辑法则,又不懂得自然的善和道德的善的区别,他们就把人性中所固有的东西和人性所获得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以至“人性怎样在原罪之中堕落,上帝又怎样运用神恩,……他们就更是绝对毫无所知了”[5]367-368。
此外,孟子人性论不区分人性与物性,这也与耶教人性论产生了分歧。儒家认为,天道“一以贯之”,在人则为人之性,在草木鸟兽则为草木鸟兽之物性,只是“鸟兽性偏,而人得其正”[4]38,所以,孟子才说人“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1]147。这是耶教所不能容忍的。针对这一观点,传教士进行了批评和更正。他们借用“量变质变”理论,指出:“夫正偏大小,不足以别类,仅别同类之等耳。”[4]38人与禽兽属于不同的类,它们之间有质的差异,而“正偏大小”等只能在量变范围内论说才有意义,如果用它们来说明异质事物具有同“性”,是毫无根据的。最后,传教士们得出结论说,孟子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其实,“人所异于禽兽者,非几希”[4]38。
传教士之所以要对孟子不注重区分人性、物性的观点口诛笔伐,主要还是因为,西方思维特别强调主客分立的逻辑,对于中国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理论,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同时,在耶教理论中,对动植物是持贬低态度的,因为只有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只有人类才能得到救赎,才能进入天堂,所以利玛窦说“现世者,非人世也,禽兽之本处所也”[4]25。因此,传教士们坚决强调人性与物性之殊。
当传教士批判性地诠释了孟子的性善论后,引起了部分中国人的反感。一位文士曾批评传教士“自昧”,认为他们“妄计心外有天主可慕可修,可创业于彼,便是不循自己本分而向外驰求。……始不知人人所固有者曰本心、曰本性、曰大道,并形所由来者,今古圣贤莫不于此尽心性焉”(《原道辟邪说》)[8]。
四、耶稣会士对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孝观念的批判性诠释
孝观念,在儒家伦理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深入人心。孟子十分注重孝道,他多次强调“申之以孝悌之义”[1]13;在与人论辩中,孟子也常常对守孝、尽孝之事大加赞扬。对孝观念进行会通,有助于耶稣会士传教工作的开展。此外,由于先儒在论及孝道时,多与“天”、“上帝”等观念相提并论,如《礼记》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郊特牲》)[9]397这就更加引起了传教士的注意和兴趣。
孟子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上》)[1]138东汉赵岐解孟子“三不孝”云:
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祠,三不孝也。[1]138
这三条判定不孝的标准,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里。然而,来自西方的耶教传教士皆终身不娶,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大不孝”。一旦被中国人扣上“不孝”的帽子,其传教活动就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另一方面,虽然天主教允许教徒娶妻生子,但是要求坚守“一夫一妻制”戒律,不可奸淫、不可纳妾。但是,由于中国人有重视子嗣的传统,一旦娶妻不能生子,就会立即纳妾,而这又与天主教的戒律相冲突。于是,孟子的“无后为大”论,引起了教士们的高度警觉。
针对上述问题,耶稣会士们做出了常识和学理两个层面的解释。从常识上,针对传教士终身不娶,利玛窦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加以澄清,文中列举了八条理由来解释,理由主要围绕传教士为了弘扬天主教,需要专心侍奉天主,不想让家庭和财色名利来牵绊自己,等等。针对中国人纳妾生子的问题,教士们结合生活常识,说明以“有后为孝”是十分荒唐的。他们以舜为例,说如果以“无后”为不孝,舜也做不到至孝,因为舜三十才娶妻,而按照生理学,男子二十岁就可以生子,舜在这十年里就是不孝;另外,他们又说:
学道之士,平生远游异乡,辅君匡国,教化兆民,为忠信而不顾产子,此随前论乃大不孝也;然於国家兆民有大功焉,则舆论称为大贤。[4]91
学道之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危,无暇顾及生子,如果按照孟子的理论,那就是大不孝,但是社会舆论依然称他为圣贤,可见社会舆论也不以“有后”、 “无后”为孝之标准。
从常识上驳倒“无后为大”论之后,传教士们更关注的是在学理上将此论予以驳倒。
对此,利玛窦指出:
此非圣人之传语,乃孟氏也,或承误传,或以释舜不告而娶之义,而他有托焉。[4]90
利玛窦认为,孟子“三不孝”说值得商榷,或许是孟子承续了前人错误的言论,或许是孟子为了解释“舜不告而娶”临时提出的。进而,利玛窦又以圣人孔子为权威,声称孔子就从没有说过“无后为大”这样的话:“孔子论孝之语极详,何独其大不孝之戒,群弟子及其孙不传,而至孟氏始著乎?”由此推论,“以无后为不孝,断非中国先进之旨。”[4]91
在此基础上,利玛窦重新解释了“无后”的意思,他说:
以继后为急者,惟不知事上帝,不安于本命,不信有后世者,以为生世之后已尽灭,散无有存者,真可谓之无后。[4]92
“无后”被利玛窦解释为“不信有后世”,那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意思,就成了:不孝有三种表现,其中最大的不孝,就是不相信人死后有“后世”(即天堂、地狱)。这种大不孝,不是对自己父母的不孝,而是对天父上帝不孝。
在改变了孟子“无后为大”说的原意之后,利玛窦又结合孟子的孝理论,提出了新“三不孝”,认为这才是更为全面、且被全世界所认可的“三不孝”的本来面目:
陷亲於罪恶,其上;弑亲之身,其次;脱亲财物,又其次也。天下万国通以三者为不孝之极。[4]91
进而,利玛窦要为孟子乃至整个儒家重新定立“孝之说”:
凡人在宇内有三父:一谓天主,二谓国君,三谓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为不孝子矣。天下有道,三父之旨无相悖;盖下父者,命己子奉事上父者也,而为子者顺乎,一即兼孝三焉。天下无道,三父之令相反,则下父不顺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己,弗顾其上,其为之子者,听其上命,虽犯其下者,不害其为孝也;若从下者逆其上者,固大为不孝者也。国主於我相为君臣,家君於我相为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虽君臣父子,平为兄弟耳焉,此伦不可不明矣。[10]91
他首先把事奉天主作为世间最大的孝,孝天主而不孝父母仍不失其孝,若孝父母而不孝天主则为“大不孝”。甚至,在天主面前,君臣、父子、夫妇的上下尊卑等级关系荡然无存,他们都“平为兄弟”。利玛窦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孝观念。至此,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观念,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明代儒、耶两种思想的接触尚属首次,在理解上难免达不到一定的深度,耶稣会士甚至为了宣教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较为随意的牵强附会的解释。通过上文耶稣会士对孟子思想的耶教化诠释之分析便可见一斑。但是,这次互动却为后世儒耶交流开了先河,提供了范例。后来天主教的主流始终是在坚持会通儒耶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诠释,进而借助耶教化的儒学开展传教活动的。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们对孟子的理解和诠释工作,也在逐步深入:到清初,介绍、研究孟子思想的传教士及著作多了起来;至18世纪初,由耶稣会士卫方济编写的《孟子》全译本出现;进入19世纪,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理雅各、新教传教士安之花等人对孟子思想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与阐释,其著作至今仍不失为西方理解孟子的重要资源。但是,作为源头,明代耶稣会士耶教化诠释孟子思想的初步尝试,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赵法生.论孔子的信仰[J].世界宗教研究,2010,(04).
[3]圣经[M].上海:中国基督教会,1996.
[4]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5]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尚九玉.简析基督教的人性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
[7]许苏民.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J].学术研究,2010(08).
[8]徐昌治编,夏瑰琦点校.圣朝破邪集[M].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
[9][清]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