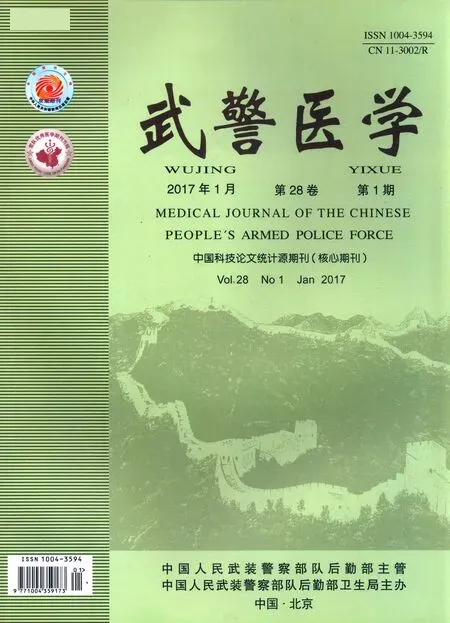关注最小意识状态
董月青
专家论坛
关注最小意识状态
董月青
最小意识状态;丘脑;电刺激;植物状态;促醒
最小意识状态(minimally consciousness state, MCS)是一种严重的意识障碍,却又有别于植物状态,主要表现为患者存在最小、但是清晰的认知自我和周围环境的能力。神经行为学和影像学的研究显示,MCS和植物状态在临床表现和神经病理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意识障碍患者觉醒的波动性,视觉、听觉、运动和语言功能受损,限制了患者与检查者进行沟通,因此在临床上存在很高的误诊率[1]。另外,MCS在预后方面较植物状态的患者具有更大的神经康复潜能,因此将两者进行准确的鉴别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2]。笔者重点介绍MCS定义的提出,MCS的诊断标准和临床评估,讨论对MCS进行准确诊断的评估技术,进而为有效地治疗提供重要的线索。
1 MCS 定义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至今,神经危重症监护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严重脑损伤患者得以存活。尽管这些患者能够睁闭眼,却不具有交流的能力。1972年,Jennet 和 Plum 把这种重症监护人为制造的“产品”称为“植物状态”。近些年,一些医师应用更具中性的词汇“无反应清醒综合征(unresponsive wakefulness syndrome, UWS)[3]”来替代“植物状态”这一名称。然而,一些学者认为,UWS缺乏机制的解释,并且可能在一些植物状态患者重新出现明确认知功能的情况下,很难再把他们定义为植物状态或昏迷。1995年,美国康复协会提出“最小反应状态(minimally response state,MRS)”来描述这种间断出现明确意识的行为,新诊断分类重点强调的是患者存在明确且有意义的认知行为。鉴于植物状态和昏迷患者同样也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反射性行为,所以Aspen工作组建议应用MCS替代MRS,通过保留的意识来强调与植物状态和昏迷的区别。2002年美国康复、神经和神经外科等相关领域专家一致通过了MCS的诊断标准。Aspen工作组的最初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可操作的MCS定义标准,更好地区别MCS与植物状态。
2 诊断标准和临床评估
2.1 诊断标准 要确立MCS的诊断,至少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行为上的证据,在检查中至少重复出现一次。由于MCS患者行为上的波动性,因此在做出诊断前需要一系列的检查。在意识状态稳定前,意识状态容易在植物状态和MCS之间摇摆,使诊断更加困难。MCS要在明确出现以下条件一项或更多项后方可明确诊断:(1)简单的指令行为;(2)手势或语言上做出“是/不是”的反应,无论正确与否;(3)理解语言表达;(4)对相关的环境刺激偶尔做出移动或有效的行为,而不是反射性的活动。
例如,偶发的运动或有效的反应:(1)出现喊叫、微笑、哭闹等,需要明确这些运动或反应是由带有感情内容的语言或视觉刺激引起,而不是由中性刺激引起;(2)直接由语言提示产生的发音或手势;(3)移动物体时,物体位置与方向存在直接的关系;(4)触摸或握持物体时带有明确的感受物体尺寸和形状的动作;(5)对移动或显著的物体视觉追逐和固定。因为诊断MCS的标准很大程度上依靠语言和运动的完整,而失语和失用可能使床旁评估变得困难,所以在做出最终诊断前须详加考虑。
以下两种复杂的行为出现之一,标志着患者从MCS恢复:(1)明确且连续出现的、相互之间的交流,交流可以通过语言、书写、是(否)的信号或通过增强的交流设备进行交流;(2)物体的功能应用,要求区别和准确的应用两个或更多的物体。
MCS的出现标志着患者恢复了与环境相互做出反应的能力。由于MCS临床表现复杂,而被进一步分为MCS+和MCS-。MCS+表现为更高水平的行为反应,如遵循命令做出动作或对语言内容做出特异反应;MCS-表现为低水平的非反射行为,如视觉追逐、疼痛定位或对情感刺激产生微笑等反应[4]。
2.2 临床评估 对意识障碍患者进行评估时,需要考虑可能影响诊断结果的相关因素。例如,对意识障碍人群行为上的波动性需要反复进行评估,而且这些评估手段对神经行为反应要足够地敏感。传统的格拉斯哥(GOS)预后评分,只能反映患者个体的意识行为变化,不能区分随机或反射性的行为与有目的的行为之间的区别,因此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克服此缺点,需要引入标准和个性化的评估手段。标准化的评分系统依赖固定的管理和评分程序,能够评估更加广泛的神经行为功能;而个体化的评估就是对每个研究个体给予个体化、特异的问题进行评估。
标准化的神经行为评估包括昏迷康复评分修订版(CRS-R)、近昏迷-昏迷评分(CNC)、西方神经感觉刺激简介、西方脑外伤量表、感觉模式和康复评分等。尽管各种评分的观测指标不尽相同,但是所有的评分标准都包括听觉、视觉、运动和交流的功能;所有评分系统都显示出充分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是在心理测量和临床应用上又各不相同。在所有评分标准中,CRS-R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把植物状态、MCS 和昏迷进行鉴别的评分系统。Giacino等[5]对80名意识障碍患者应用CRS-R和残疾评分(DRS)进行比较时发现,尽管两者做出同样诊断的病例占87%,但是CRS-R却在DRS诊断为植物状态的患者中发现了10例MCS患者,而DRS诊断的MCS患者,CRS-R都做出了正确诊断。Schnakers等[6]对在创伤中心的急性期和在康复中心的亚急性期共60例脑外伤患者进行了GCS评分、CRS-R和全面无反应性量表(FOUR)的评估。29例被GCS诊断为植物状态,而4例被FOUR发现至少有一项意识存在的指征,而CRS-R把7例FOUR诊断为VS的患者检测出了MCS 的证据,所有7例患者显示出视觉固定,这是一种从VS中进一步康复的预兆。
3 功能神经影像评估
功能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步改变人们对昏迷和慢性意识障碍认识。当我们认为一些植物状态患者将来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患者已经进入MCS。把植物状态和MCS区分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功能神经影像显示两者在残余大脑功能、意识认知和预后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7]。
3.1 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RI, fMRI) 对于慢性意识障碍的患者,fMRI不仅能够阐明神经恢复和塑性的机制,还可以挑战传统的意识障碍诊断概念。目前,临床上主要通过任务态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来研究意识障碍患者的大脑功能,两者有各自的优势,也存在各自的不足。
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1例23岁因创伤所致植物状态的女性患者在MRI扫描的时候,被要求从事运动和空间想象的任务,即打网球和在室内行走[8]。患者的fMRI激活模式与健康对照组相似,表现为在运动想象任务时运动辅助区的临时激活,而在空间想象任务时表现为海马旁回、后顶叶皮质、运动前区侧方皮质的激活。尽管多学科的团队对患者进行了详细的神经检查,患者在缺乏认知自我和周围环境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大脑的激活。这一令人兴奋的发现揭示出在植物状态和MCS患者中,尽管在床旁我们没有发现积极的认知能力,但是却可以通过运动想象、空间想象、语言和视觉模式的fMRI发现[9]。另外,1例创伤所致的MCS患者在采用上述两个想象任务进行MRI扫描的时候进行了“是”和“否”的回答[10]。
以上研究的共同点就是,任务态功能MRI为临床提供了在床旁检查发现不了的意识认知证据,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功能MRI作为一种检测手段,是否可以被整合到临床意识的诊断中去?在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患者具有认知的波动性,并且可能不是按照我们的指令进行精神想象,而使诊断出现错误。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rs-fMRI),是基于静息状态下大脑的自发波动与相关功能脑区在时间上相关的原则而产生的检查。确定大脑活动的静态相关产生了“静息态脑网络”的概念,包括默认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显著网络、丘脑-皮质网络和执行控制网络等。
目前,对昏迷康复的研究最引人瞩目的静息态网络是DMN。灰质的节点广泛分布在网络中,包括后扣带回皮质、楔前叶、前额叶皮质中部、顶叶的下部(角回和缘上回)、海马结构。研究显示,在创伤昏迷康复后出现了DMN连接的改变[11],纵向的DMN连接增加与功能康复相一致[12],且DMN网络功能失常的严重程度可以预测神经认知任务的表现[13]。此外,Rs-fMRI测量的DMN中皮质节点的功能连接与弥散张量成像测量所得的节点之间白质结构连接相一致。Rs-fMRI与弥散张量成像检查结果的一致性说明与健康受试对照者一样,神经解剖结构连接是功能连接的基础[14]。最值得注意的是DMN中功能连接的强度与创伤后昏迷的意识水平呈线性相关。
3.2 PTE-CT的研究 大脑能量代谢依赖不间断地葡萄糖消耗,并可以通过氟脱氧葡萄糖(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进行检查。在意识丧失后,脑葡萄糖代谢率(CMRglc)下降到正常的50%以下。植物状态急性期患者CMRglc下降到正常的40%~50%,而在亚急性和慢性阶段进一步下降到正常的30%~40%(图1)。逐步提高意识水平似乎与一个逐步倍增的能量代谢相关。

图1 植物状态和最小意识状态的PET-CT影像
A.植物状态,可见红色低代谢区域覆盖整个额颞顶枕部皮质,像头盔一样覆盖在大脑皮质上;B. 最小意识状态,可见抑制区域主要是点块状分布在大脑皮质
以往的研究表明,意识活动的相关区域包括脑干内的觉醒中心和额-顶皮质网络、前楔叶等相关的皮质区域,这些结构构成了整体意识的框架。随着平均皮质CMRglc值在正常的 40%和“突触”能量在正常的34%时,VS患者的大脑皮质可能处在一个低水平的能量周转状态。Maandag等[15]研究显示,这些患者的神经活动占主导地位的是低频活动,不能反映广泛的皮质连接。VS患者的脑电图显示较低频率活动(δ、θ)的增加,同时伴有高频率活动(β和γ)的减少。而MCS患者可以处于一个中间的能量状态,支持向正常神经元活动的过度[16],使大脑皮质能够远距离连接而增加认知。
MCS患者额-顶区内的平均代谢为60%,接近正常,较植物状态患者的代谢(42%)明显增加,并且额-顶区在所有大脑功能区中增加最为明显,从而支持额-顶叶皮质在意识障碍的发病中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楔前叶和相邻的后扣带皮质被认为在整合、输入额-顶叶认知网络信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楔前叶活动的出现与总体的额-顶叶CMRglc的增加密切相关。有人提出楔前叶代谢率的保留能够区分MCS 和植物状态,而楔前叶的轴索再生一直被视为患者从MCS中复苏的驱动机制[17]。
植物状态患者皮质活动的分布均匀,体素变异很小,由此可以推断大脑的各个区域存在均一的低代谢,不存在正常代谢的区域。而在感觉(输入),额-顶皮质(认知)和运动(输出)网络中存在功能完整的皮质群岛是MCS的主要病理特征。
基于对大脑代谢的研究,日本和欧美国家应用脊髓电刺激治疗意识障碍患者,并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我们在国内率先应用高颈段脊髓电刺激治疗意识障碍患者,把电极放置到C2-4的硬脊膜外,特别是对于MCS患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患者促醒的概率达到62.5%。我们观察到脊髓电刺激能够增加患者大脑皮质细胞的代谢,并且诱导神经递质发生改变[18,19]。
过去10年见证了我们对意识障碍研究的重大进步。我们定义了MCS,应用全新功能影像对MCS和植物状态的病理生理、残余脑功能和预后进行了评估。很多理论和经验都支持MCS较植物状态对治疗干预存在更好的前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惊喜。随着更多全新的模式和分析方法的出现,延伸了我们处理数据的能力,对那些接近正常认知却不能用言语或动作进行表达的患者,会有全新的认识,进而会改变有关意识障碍的传统观念。
[1] Schnakers C, Vanhaudenhuyse A, Giacino J,et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vegetative and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clinical consensus versus standardized neurobehavioral assessment[J]. BMC Neurology, 2009, 9: 35.
[2] Luaute J, Maucort-Boulch D, Tell L,etal. Long-term outcomes of chronic minimally conscious and vegetative states[J]. Neurology, 2010, 75(3): 246-252.
[3] Laureys, S, Celesia, G G, Cohadon F,etal. Unresponsive wakefulness syndrome: a new name for the vegetative state or apallic syndrome[J]. BMC Med, 2010, 8: 68.
[4] Bruno M A, Majerus S, Boly M,etal.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underlying the clinical subcategorization of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patients[J]. J Neurol, 2012, 259(6): 1087-198.
[5] Giacino J T, Kalmar K, Whyte J. The JFK Coma Recovery Scale-Revised: measur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iagnostic utility[J].Arch Phys Med Rehabil, 2004, 85(12) : 2020-2029.
[6] Wijdicks E F, Bamlet W R, Maramattom B V,etal. Validation of a new coma scale: the FOUR score[J]. A nn Neurol, 2005, 58(4) : 585-593.
[7] Rodriguez Moreno D, Schiff N D, Giacino J,etal. A network approach to assessing cognition in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J].Neurology,2010,75(21): 1871-1878.[8] Owen A M, Coleman M R, Boly M,etal. Detecting awareness in the vegetative state[J].Science, 2006, 313(5792): 1402.
[9] Monti M M, Pickard J D, Owen A M. Visual cognition in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from V1 to top-down attention[J].Hum Brain Mapp, 2013, 34(6): 1245-1253.
[10] Monti M M, Vanhaudenhuyse A, Coleman M R,etal. Willful modulation of brain activity in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J].N Engl J Med,2010,362(7): 579-589.
[11] Bonnelle V, Ham T E, Leech R,etal. Salience network integrity predicts default mode network func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2, 109(12): 4690-4695.
[12] Hillary F G, Slocomb J, Hills E C,etal. Changes in resting connectivity during recovery from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J]. Int J Psychophysiol, 2011, 82(1): 115-123.
[13] Sharp D J, Beckmann C F, Greenwood R,etal. Default mode network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J].Brain, 2011,134(Pt8): 2233-2247.
[14] Teipel S J, Bokde A L, Meindl T,etal.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e underlying default mode network connectivity in the human brain[J].Neuroimage,2010,49(3): 2021-2032.
[15] Maandag N J, Coman D, Sanganahalli B G,etal. Energetics of neuronal signaling and fMRI activity[J].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7,104(51):20546-20551.
[16] Lechinger J, Bothe K, Pichler G,etal. CRS-R score in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is strongly related to spectral EEG at rest[J]. J Neurol, 2013, 260(9): 2348-2356.
[18] 董月青, 李建国, 张 赛. 高颈段脊髓电刺激促醒颅脑创伤昏迷一例并文献复习[J].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2011, 27(6): 668-670.
[19] 董月青, 张 赛, 孙洪涛,等. 高颈段脊髓电刺激治疗重度意识障碍的疗效分析[J]. 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 2014, 19(6): 258-260.
(2016-09-10收稿 2016-10-10修回)
(责任编辑 武建虎)

医学期刊常用字词正误对照表
董月青,博士,副主任医师。
300162 天津,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六科
R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