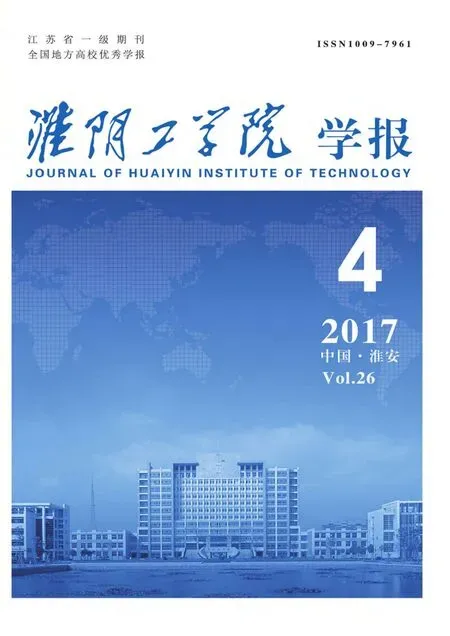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介模式再思考
——兼谈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
曾景婷
(1.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2.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介模式再思考
——兼谈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
曾景婷1,2
(1.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2.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当今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热点议题,如何走出去,翻译家的翻译活动是其关键。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从文本选择、读者中心和文化调适三个方面体现出译介模式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作用。谙熟中国文化的海外汉学家与优秀中国译者互为补充的译介模式是现阶段的理想选择;译者应根据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不同阶段以及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可接受程度合理调整译介模式。只有在译介模式和翻译策略之间找到“支点”才能承担起中国文学“走出的”的历史重任。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葛浩文
0 引言
2012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树立了信心,说明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瓶颈不仅在于原作质量,译本质量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美籍汉学家葛浩文既熟悉中国文学历史和现状,又了解海外读者需求和审美机制。本文通过分析葛氏翻译之道中的文本选择、读者中心和文化调适三大特点,探究海外汉学家译者模式如何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行之旅。
1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
译介效果是检验翻译活动的重要尺度。[1]就中国文学译介效果来说,全球化使得处于世界体系顶端或中心的文化加速向全球传播,而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文学则在“向心”传播中阻力重重。在2014年“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葛浩文指出,中国小说在西方不太受欢迎,中国文学在美国的地位还不如日本、印度甚至越南文学。[2]如何在西方的强势话语下将中国故事生动地传播出去,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而又需要知己知彼、稳打稳扎的现实问题。而影响译介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译介模式。
可以说,中国文学“走出去”,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学译介模式的理想性选择这一核心议题[3]。目前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译介模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中国译者译介模式。早的不提,从晚清时期,中国学者就开始尝试性翻译并对外输出富含中国特色的诗词和小说,如,陈季同将李白、杜甫等人的诗译成了法语;再如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在国内受到了专家、学者和读者们的一致认同和好评,但根据2007年江帆博士对百年来十余种《红楼梦》英译本的深入研究,并到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与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译本相比,不论在借阅数量还是在研究者引用次数方面都远逊于霍译本。[4]可以看出,本土译者即便英语文学创作功力深厚,由于对异域读者阅读习惯及文学出版市场缺乏深入了解,也很难得到国外行家和读者的认可。[5]
第二种是中国政府译介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政治因素,中国政府创办了《中国文学》杂志,主要由中国译者负责翻译、传播中国文学作品;继而,1981年,从事翻译工作的本国学者,模仿英国《企鹅丛书》,创办了《熊猫丛书》。毋庸置疑,这些都成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里程碑。那么传播效果怎么样呢?耿强(2014)从整体考察“熊猫丛书”在美国文化系统中的接受过程。通过分析其译介效果揭示出该丛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这套丛书在美国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大学图书馆,而在美国主流的连锁书店并未出现。这就说明丛书在市场上并未流通,阅读译本的只可能是对中国问题研究感兴趣的师生,普通的美国读者对这些译本未能产生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评论界在选材、文学价值和翻译质量三方面对丛书负面评价越来越尖锐。如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 对刘恒的《黑的雪》以及贾平凹的《天狗》的评论十分严厉。金介甫认为外文出版社及其推出的如熊猫丛书系列采取集体翻译方式,倾向于数量高于质量,英文译文的风格单调而毫无变化。因为如此枯燥无味、缺乏想象力,所有关于作品文学性的宣称都会在读者翻开书的第一页时烟消云散。
窥一斑而能见全豹。这两种译介模式可以看出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本国学者一厢情愿的“输出”热情,换来的是受语读者群和传播渠道的狭窄,受到很多国外尖锐的批评及冷遇。追根溯源,无外乎翻译质量和译作选材与受众的需求相悖。而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意识到译介学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译者所为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采用目标读者群所能接受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传播本族的文学与文化。正如译介学所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标语之间如何转换,而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的信息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因而,简单将文学作品的忠实翻译和中国文学 “走出去”完全等同起来,并且认为只要完成“一部合格的译本之后”就一定能够获得海外读者的阅读和欢迎,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6]
第三种是外国汉学家与中国译者合作的译介模式。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读者主要是非华语地区外国人士,而外国汉学家具有既精通中国文学史又了解海外读者阅读需求和习惯的双重优势。就现有译介模式而言,中国文学外译最为成功的模式是葛浩文、林丽君夫妇合作翻译,他们各自拥有母语优势,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在场,及时沟通,因而既能全面理解原文内涵和意境,又能使英译文的表达流畅地道,并且最大程度地传达原作的艺术特色,被誉为中西合璧的翻译“梦之队”。
2 葛氏译介模式的翻译之“道”
作为译者,葛浩文始终在原作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张力,在保持原文风格特点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照顾到读者的接受程度。目前,尽管学界诟病诸多,但基本认可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是成功的。笔者认为,葛氏主要成功之处在于文本选择、读者中心和文化调适三个方面。
2.1文本选择
在一部作品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边界之后,译者既是隐身的也是现身的。葛浩文说过:“文本选择错误是最大的错误,比翻译错误更为糟糕。”葛浩文也说过:“我常常选择我特别喜欢,也认为是老美非读不可的作品来翻译,可是他们未必那么喜欢……我就是照着自己的兴趣来,基本上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在一次访谈中,葛浩文又谈到:“有一些还没有找到出版社的作品,我一般会先译出一部分,三五十页,先请经纪人或出版社过目看看是否有出版的可能,如果有出版社感兴趣,我就继续翻译完然后出版)如果没人表示有兴趣,那就算夭折了”[7]。在西方世界,葛浩文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鉴赏家与发现者,他几乎是重新“发现”了萧红,并因此翻译了《呼兰河传》。他也是莫言的最早发现者之一。莫言获奖正说明了葛浩文在文本选择时的敏锐判断。当然,这种选择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学趣味,还与整个美国阅读市场的需求和出版商的关注不无关系。
2004 年9月,葛浩文在香港《翻译季刊》上发表了题为“Blue Pencil Translating: Translator as Editor”的论文,讨论自己作为译者在翻译新时期中国小说过程中所扮演的一半是译者、一半是编辑的角色。[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提到明显删减的莫言小说有两部(Goldblatt,2011)。[9]其实,《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等小说的翻译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删改现象。《红高粱家族》是由五个原本独立的中篇故事组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与故事之间结构较为松散、前后存在着一些重复或是有出入的地方。译者修正了原作中的粗心错误,另外还“大刀阔斧地省去了很多卫星事件和细节描述,去掉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枝丫。[10]《丰乳肥臀》1996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年又出版了一个缩减版。翻译时译者采用的是由莫言本人提供、在工人出版社的版本基础上进一步精缩的版本。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经莫言同意,译者、出版社也做了一些改动。结果,800多页的小说译成英文后,只剩下500 多页。[11]
很多学者认为葛浩文采用的是“连译带改”式的非忠实性翻译方法。在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译本中,葛浩文“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建议作者修订倒数第二章,重写最后一章,并提出修改想法供莫言参考。莫言接受了他的意见,对这两章进行了修改。[12]在一次访谈中,葛浩文对此进行了说明和解释:“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那是个充满愤怒的故事,结尾有些不了了之。我把编辑的看法告诉了莫言,十天后,他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结尾,我花了两天时间翻译出来,发给编辑,结果皆大欢喜。而且,此后再发行的中文版都改用了这个新的结尾。”可见,改动原作结尾的是莫言本人,只不过他是在葛浩文的建议下进行修改的,这似乎可以被理解为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的一次生动例证,甚至是翻译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葛浩文的单方面改动,更不能简单地由此得出译者采用的是“非忠实性翻译”这样过于武断的结论。
2.2读者中心
葛浩文明确主张“读者中心”,即译者应为目的语读者而译。而读者对译介主体的认同程度对译本的接受与传播效果也尤其重要。[13]读者对译介主体认同度、知名度与可信度越高,取得的译介效果越大。在相对“忠实”的前提下,葛浩文往往会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对译文进行调整。以《狼图腾》为例。原作者在每一章开篇所引诸如“ 周穆王伐田畎戎,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之类的典籍资料全部舍弃。因为英文读者无法读出历史厚重感,也无法获得文学情感体验。小说末尾的“理性探掘” 在英译本中也删除了, 因为学理探讨与小说的故事性难以兼容,英文读者无法接受。[14]且看一例:
把假事哭成了真事,把西门闹哭上了黄泉路。[15]
Thus turning a lie into the truth and sending Ximen Nao straight down to the Yellow Springs of Death.[16]
“黄泉路”指人死后到阴曹地府报到时走的路,背后富含典故,对于不懂中国文化历史的西方读者来说,不理解作者所云。葛氏作为一名汉学家,精通中国文学、历史,更是对西方读者在理解中国特色词汇方面的困难有着深刻认识和把握。因此,葛氏将“黄泉”英译成“Yellow Springs”, 看似平淡无奇,也是多番推敲辛苦得来;“yellow” 一词在西方文化中用来形容消极、负面的事件或形象,从而暗示译语读者此词在文中指向消极的一面,且在形式上基本达到了与原作对等。为了使目标语读者能够和原语读者以同样的方式理解、接受原文意义,葛氏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之上,站在译语读者角度,在“Yellow Springs” 后面增译了“of Death”,从而确保译语读者正确掌握这一文化意象,达到了原语与译语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对等,实现了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葛氏在透彻理解原文基础之上,不斤斤计较与字面上的对等,而是直达语言的深层含义,已经多少可以窥探出葛氏的翻译风格:忠实于原文且不被原文束缚,忠实原文且不缺乏创造。从而使莫言作品在西方世界同样受到读者欢迎,就连作家莫言也称赞道:“如果没有他的杰出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17]
通过上述例句分析得知,葛浩文将忠实原作作为译介的首要原则,同时考虑到译语读者的可接受性,所以译文中也不乏葛氏的创造。从译介学理论层面分析,实现译作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不是单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是要求译者在译语环境中能够找到激发目标语读者与原作读者产生同样效果的相同或相似的语言手段。葛氏作为汉学家,一方面可以很好把握原文的艺术效果,同时英语为母语,使其巧妙地运用语言将原作的艺术形式展现在译作中,就像原作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在说话一样。因此,文学作品的译介,译者的创造性并不可少。同时,实现一种文学作品在异域国度或民族的顺利传播,目标语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以及赞助人是至关重要的三个因素。葛氏美籍汉学家身份有利于其充分把握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以及赞助人的需求,从而进行有的放矢地创造性译介,实现中国文学作品真正走进译语读者的心中。
2.3文化调适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译”已经成了主要议题之一,这也是体现译者是否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对于“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策略的遴选存在较大分歧。“归化”主张最大化地淡化原语的“异国风情”,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接近读者。“译者要做的就是应该让他/她的译作“隐形”,以产生一种虚幻的透明效果,并同时为其虚幻的身份遮掩:译作看上去‘自然天成’,就像未翻译过一般”。 “异化”则主张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原语的陌生感和特有的民族风情,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接近作者。“主张通过干扰目标语盛行的文化常规的方法来彰显异域文本的差异性。”[18]任何国家、民族之间都存在差异,中国与政治、经济体制迥然不同的西方国家之间存在异质也势成必然。所以“异”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屏障。正如许钧教授所言:“正是因为语言之‘异’,造就了翻译的必要性,那么翻译的根本任务,便是克服语言之‘异’造成的障碍,以进行思想的沟通与交流。”[19]因此,在这“译”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两种文学之间的“异”,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2013年10月15日,在由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高峰论坛上,葛浩文直言:“虽然作为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不安、互惠互利且脆弱的,但正是这种关系让世界文学成为可能,让我可以不要做莫言。”
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一部章回体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了从人转世为驴、牛、猪、狗、猴,最后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该部作品主要围绕“土地改革”话题,阐述农民和土地之间的种种关系,因而原作中富含大量中国文化的负载词语,这些中国特色浓厚的词汇之于译者无疑是一项挑战。译者林少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感慨:“文学翻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既能成全一个作家,也能毁掉一个作家”[20]。然而这恰恰也是译者独创性的显著标志。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底蕴和翻译功底,抑或对译语读者的阅读机制和阅读习惯不甚了解,这都将导致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过程不是被完全“同化”就是被目标语读者所排斥。因此,翻译策略无疑是译介过程中需考虑的重中之重。且看葛氏如何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游刃有余地展现自己的独特翻译观。
例1:你没有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已经是万幸了。
Not labeling you a member of the landlord class and sending you out to be reformed through labor is better than you deserve.
例2:我们也熬出头了,摘了帽。
We’ve come through it and have been rehabilitated.
例3:“还有你,吴秋香,当初看你可怜,没有给你戴帽子……”
“And you,Wu Qiuxiang,I took pity on you and spared you from having to put on a dunce cap. ”
例4:他用一种十分古怪的腔调说:“听说你也摘了地主的‘帽子’了,我来祝贺你。”
“I heard you shed your landlord dunce cap,” he said in s strange voice,“and I’m here to congratulate you.”
如上四例中,“摘帽”和“戴帽”负载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意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给社会不良分子——地主所贴的一张无形的标签,带有嘲讽意味。因此翻译中,不能简单译成“cap”,即日常所戴的普通帽子;葛氏选用的“a dunce cap”在西方是指孩子犯错时所戴的一种由纸制成的,上面标有字母“D”或单词“Dunce” 的帽子,也带有强烈讽刺意味,这样在一定层面上与原作所说的“戴帽子”有曲径通幽之妙。例4中,葛氏在 “landlord”之后增译了“dunce cap”,从而给 “dunce cap”赋予了一层崭新的意义,即用译语读者熟悉的文学意象,向他们展现了中国特色的文学意象。上述例句中的“摘帽”和“戴帽”虽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但所含的蕴义都是一样的,而葛氏并未循规蹈矩地采用同一个词汇来表达,而是将“戴帽”分别译介成 “a member of the landlord class”,“put on a dunce cap”;“摘帽”译介成 “shed your landlord dunce cap”,和 “rehabilitated”,葛氏对语言进行了“归化”,使目标语读者能够对那些负载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有一个全面、透彻的认识,有效地实现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3 结语
毋庸赘言,葛氏不失为汉学家模式选择的标准——既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与习惯,又能够熟练地使用母语(英语)进行文学翻译,同时又熟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美籍汉学家葛浩文从文本选择到读者中心再到文化调适的翻译之道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外译中国文学作品过程中,要从民族文学成功转型为世界文学必须合理使用“归化”和“异化”策略,并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支点”,这才是真正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根本。葛氏为我们树立了使用此法的榜样,但葛浩文的译法并非无懈可击,如遇到原作中一些译语读者较难理解的词句,葛氏直接将其删译,英文中也有误译之处,此文不缀。因此,我们切忌盲目临摹,而是要辩证地学习、区别地看待。同时,我们还要让自我传播与他者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相结合,使小众话语文化与大众话语互渗,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21]
[1] 鲍晓英.从莫言英译作品译介效果看中国文学“走出去”[J].中国翻译,2015(1):13-17.
[2][7] 葛浩文,史国强.我行我素:葛浩文与浩文葛[J].中国比较文学,2014(1):44-45.
[3]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 2010(6):10-15.
[4] 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
[5][11] 吕敏宏.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 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学走出去:理论与实践[J].东吴学术,2013(2):44-54.
[8][11] Goldblatt,Howard. Blue Pencil Translating: Translator as Editor[J]. Translation Quarterly,2004.
[12] 孙会军. 葛译莫言小说研究[J]. 中国翻译,2014(5):82-86.
[13] 王志勤,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J]. 学术月刊,2013(2):21-27.
[14] 孟祥春. 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 中国翻译2014(3):72-77.
[15] 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16] Goldblatt,Howard.LifeAndDeathAreWearingMeOut[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Inc,2008.
[17] 姜智芹.他者的眼光:莫言及其作品在国外[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2):76-78.
[18] Venuti,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19] 许钧. 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0] 范武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语言硬伤依然存在—写在莫言获奖之后[J].当代外语研究,2013(4):38-41.
[21] 杨四平.“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文化战略[J].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2):31-34.
(责任编辑:郑孝芬)
The"Going-out"ofChineseLiteratureandItsTranslatingModels:WithAmericanSinologistHowardGoldblatt'sLifeandDeathareWearingMeOutasanExemplar
ZENG Jing-ting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ngjiang Jiangsu 212003,China)
At present,the"going-out"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hot-debated issue in promoting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How to go out and translators' translating activities are playing a key role. This paper takes Sinologist Howard Goldblatt's English version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as an exemplar to probe into how the translating model has influenced the"going-out"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the choice of texts,readers' centre and cultural adjustment. The translating model that Sinologists who know Chinese culture very well and excellent Chinese translators supplement each other is an ideal choice at the present stage. Translators should adjust the translating model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Chinese culture's "going-out" and Western readers' acceptability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Only by finding a fulcrum between translating models and translating strategies can translators take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going-ou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ng model; Howard Goldblatt
H315.9
:A
:1009-7961(2017)04-0031-05
2017-04-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WW025);第八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ZGWYJYJJ2016B22);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预研项目。
曾景婷(1979-),女,江西南城人,副教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与比较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