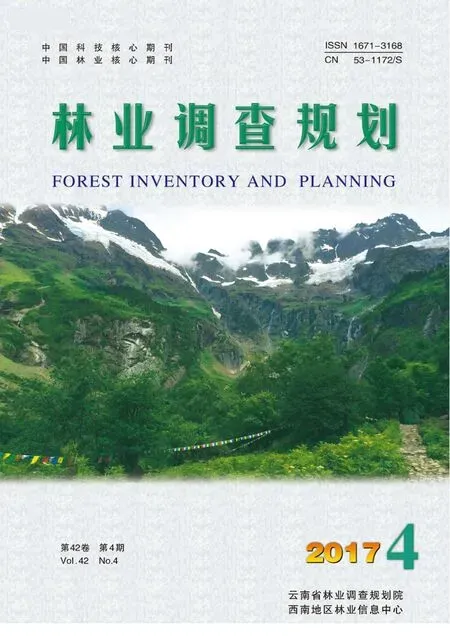三江源国家公园对当地牧区社区原住民的影响
张文兰,仙 珠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三江源国家公园对当地牧区社区原住民的影响
张文兰,仙 珠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国家公园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2015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经批准成立后,不仅增加了区内居民的收入来源,还改变了居民的思维方式,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等。公园内的居民多以放牧为生,为减轻对牧区社区原住民的影响,使其更好地融入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提出加大对移民的扶持力度,实现移民的顺利转产,重视社区居民参与公园管理,创新社区发展新路径,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建议。
牧区社区;原住民;公园管理;社区发展;三江源国家公园
1 国家公园和牧区社区的概念
1.1 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的概念最早源于1872年,由美国人乔治·卡特琳提出。其初衷是为了保护西部大开发中的印第安文明、野生动植物和荒野。根据IUCN和UNEP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世界符合IUCN标准的国家公园共有5 220处[1]。在我国还没有出台国家公园法律层面的定义,目前采用1994年IUCN对国家公园的定义:“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及游憩活动的天然陆地或海洋,制定用于为当代或后代保护一个或者多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排除与保护目的相抵触的开采和占有行为,为民众提供精神、科学、教育、娱乐、游览的基地,用于生态系统保护及娱乐活动的保护区”[2]。
1.2 牧区社区
社区是社会人类学中的概念,对于社区的定义很多,比较常见的定义为:人们共同生活的一定区域,德国学者滕尼斯称它为“结合社会”,美国学者麦其佛称之为“社区”[3]。根据这个定义,社区的基本要素包含如下:有以一定社会关系为基础生活的人群;地域间有界限;具有一定的社会规范或准则[4]。吴泽霖主编的《人类学词典》中,对社区这样界定:在特定社区内,若干相互依赖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在一起,而且经常有面对面的接触[5]。这里将家庭作为构成社区的基本单位。
社区分为城市社区、牧区社区和农村社区。农村社区是最早的社区形式,其次是城市社区,牧区社区是后起的。牧区社区是并列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一种新型社区。
2 研究区域概况
2.1 三江源国家公园基本情况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在 4 000 m以上。由于园区内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故起名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总面积12.31万 km2,涉及黄河源园区、长江源园区和澜沧江源园区3个园区,构成“一园三区”的格局。
该区域内平均海拔 4 000 m以上,年均温-5~6℃,主要植被类型为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草原、草甸等。园区内发育着大面积的原始生态系统,并且保存完好。
2.2 周边社区基本情况
社区是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参与是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三江源国家公园共12.31万 km2,占三江源地区面积的31.16%,涉及5个保护分区。园区包含12个乡镇52个行政村,1.68万牧户,6.16万人口,其中1.98万为贫困人口[4]。园区内居民目前主要以挖虫草、政策性补偿、放牧为生,很少有生产经营性收入。目前园区内居民人均年收入不到 5 000 元。
3 三江源国家公园对牧区社区的影响
3.1 增加居民就业机会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居民以藏族为主,主要以放牧为生。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成立已将原住民纳入到公园管理中来,如公园的管理中设置了生态管护员岗位,工资 1 800 元/月。每位管护员管护范围为200~333 hm2不等。主要职责为对草地、湿地监管和维护,发现、报告破坏草原、湿地的行为[6]。生态管护员的选聘中以贫困户优先。
3.2 异地搬迁对原住民造成的影响
三江源生态移民主要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根据《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三江源区在2004—2010年对18个核心保育区进行整体移民,计划涉及牧民 10 142 户、55 774 人,涉及4个藏族自治州的16个县,争取在5年内使三江源核心区变成“无人区”[7]。《计划》于2004年开始实施,截至2009年底,已搬迁移民约 50 000 人,基本完成了计划任务。但由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居民宗教、文化、生活方式有特殊性,使得三江源地区异地搬迁远比扶贫搬迁复杂,以至于产生了很多问题。
3.2.1 搬迁后出现返牧现象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原住民基本都是藏族牧民,祖祖辈辈以放牧为生。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不会说汉语,也听不懂汉语,只能使用藏语。据有关数据显示,玛多县15岁以上含15岁的人口中文盲占35.41%,称多县15岁以上含15岁的人口中文盲占66.75%,曲麻莱县15岁以上含15岁的人口中文盲占69.87%[8]。而异地搬迁无论到镇上或者县上,都需要使用汉语,经济生活由原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跨入商品经济,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牧民搬迁后不再拥有牧场和牛羊,传统的生存技能完全派不上用场,他们面临着一夜之间完成牧民向市民的转变,这意味着异地搬迁后牧民的生活习惯、生存方式等全方位的改变。即使同是藏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宗教信仰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使得跨区域的迁移比县内迁移的适应和融入更加艰巨。虽然当地政府积极想办法帮着他们找到就业渠道和尽快适应搬迁后的生活,但这些努力大多事倍功半,很多牧民由于无法适应搬迁后的生活,只能重返原地重新放牧。
3.2.2 增加了牧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部分牧民实现脱贫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牧民异地搬迁都是搬往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牧区子女原来接受教育的地方,这也增加了牧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在异地搬迁的过程中,自愿搬迁的多为家庭贫困户,即在园区内没有大量草场和牛羊,生活拮据,异地搬迁后政府的补偿对他们很有吸引力。这部分贫困牧民也希望通过搬迁赢得生活的一线希望。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牧民通过家庭分离,将原来的家庭分成几个家庭,以此让其中的几个家庭搬迁,几个家庭留在原来的草原上,这样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子女也有了上学的机会,也不会失去原来的牛羊和草场。所以奶奶带着孩子,妈妈带着孩子在城里居住的现象很多。这也说明了牧民已经注意到了教育的重要性,鼓励孩子上学,从思想上实现了脱贫。
3.2.3 原住民离婚率提高
从草原搬迁到县城后,由于原来的土著民大多没有文化,而县城的市民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加上城市生活对人们技能和文化、学历等的要求不同于牧区等原因,面对现实的变化,女性对另一半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离婚率高于搬迁之前。
3.3 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建立,吸引了很多游客。以往园区内的环保公益人士只做保护环境的事,但随着旅游人数越来越多,园区内一些保护环境的热心人士联合当地村民积极组织一些队伍迎接旅游。如:村民为了避免游客随意骑马而造成破坏草原、造成人身意外伤害,自愿组织马帮。马帮有专门的人员为游客牵马、骑马,讲解三江源,提供住宿等。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很好地缓解了旅游给三江源国家公园带来的压力,也为游客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4 提高了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成,必定在我国面临严峻生态环境挑战的当今产生巨大影响。若借此机会打造三江源国家公园专有品牌,将园区内原住民的牛羊等产品收购加工成产品进行销售,不仅方便了原住民将牛羊变现,还增加了收入。
3.5 改变了原住民生活方式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以藏族居民为主,而藏族长期以来以游牧为生,除了放牧,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以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文件,如《湿地保护管理规定》、《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等。这些文件的核心是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由于牧民原有牲口过多,草原承载力有限,于是从2004—2006年初,生态移民工程在青海省相关州县逐步展开[9]。而当地的牧民95%以上靠家畜生活,禁牧、移民以后要改变牧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学习新的技能或者靠其他生存方式继续生活,而三江源区内的牧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几乎不会说汉语并且主动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不高,多数人甚至没有上过小学。
4 减轻三江源国家公园对牧区社区原住民影响的建议
为有效利用三江源国家公园对当地牧区社区原住民的有利影响,规避不利影响,提出以下建议:
4.1 趋利避害
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甘达村村民有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主要得益于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入住甘达村10年时间对当地村民的影响。三江源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要靠政府,更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像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这样的环境保护类非政府组织长期扎根于三江源,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专业性和责任心。因此,环境保护工作中非政府组织是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
再次,生态管护员岗位的设置一方面提高了当地居民保护环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当地居民积极地投入到国家公园的保护和建设中来,另一方面增加了园区内居民的收入,实现了脱贫。这些都是对当地社区原住民有利的影响,要大力鼓励和实施。
4.2 加大对移民后期的扶持力度,实现移民的顺利转产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移民属于自愿移民与工程移民相结合的生态移民[10]。单纯的工程补偿职能解决温饱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移民后的贫困问题,必须要培育后续产业,加强对移民的培训,为他们找到一条生存之路,如发展特色畜牧业经济,开发新兴产业,以转换牧民生产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4.3 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调整补偿标准
2005—2009年,曲麻莱县计划安置 1 000 户牧民到格尔木市定居,但实际上只完成了240户、1 760 人的2期移民,原计划并未完成。2011年以后,青海省采取了新的补偿政策,按1.9~3.4万/户·a的标准发放[11]。考虑到异地搬迁后的牧民面临无法就业、生活方式、文化等多方面问题,这些补偿只能保证移民的基本生活。一些拥有大面积草场、牛羊的原住民本身很富有,这样力度的补偿对他们没有太大吸引力,他们会选择继续留在园区内。补偿机制是否完善是移民很关心的问题,补偿的力度关系到有多少原住民愿意移出三江源国家公园,移民后能够“稳得住、富得起”。
4.4 重视社区居民参与公园管理
国家公园的开发如果只有少部分社区居民受益,那么必然会引来其他居民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家公园的稳定。将全部原住民纳入国家公园的开发中,不仅能使原住民从公园经营、管理的主体从中受益,也调动了其保护公园、管理公园的积极性,有利于国家公园的发展。
4.5 创新社区发展路径
目前,园内社区经济来源主要为挖虫草,养殖牛、羊以及出售牛羊制品、从事生态管护等,食物、生活燃料、交通基本自给自足。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只会让原住民处于生活的底层,必然会限制社区发展。而原住民对自身特有的传统文化并没有适当发掘。公园应帮助原住民发掘自身民族文化价值,寻求适合社区发展的新途径。
4.6 建立和完善社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虽然园区内居民有着天然的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情怀,但介于原住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汉语能力有限,而到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的人群以外地人居多,为了规范行为,维护各方利益,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很有必要。
5 结语
国家公园的开发建设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贡献,尽管国家公园的建立会给原住民带来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但国家公园应高度重视社区参与对园区内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以及公园建设和监督的巨大作用。在规划初期就应将原住民充分纳入进来,并在公园的发展中予以贯之,协调好公园与原住民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殷培红,和夏冰.建立国家公园的实现路径与体制模式探讨[J].环境保护,2015(14):24-25.
[2] 张希武,唐芳林.中国国家公园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4:43-44.
[3] 覃光广,冯利,陈朴.文化学辞典[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8:541,452.
[4] 孙九霞.藏区城镇、农业、牧业社区文化比较研究—以甘南夏河县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06,17(3):33.
[5] 吴泽霖.人类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154.
[6] 青海省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EB/OL].http://xxgk.qh.gov.cn/html/1670/293034.html
[7] 陈桂琛.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143-147.
[8] 孟向京.三江源生态移民选择性及对三江源生态移民效果影响评析[J].人口与发展,2011,17(4):2-8.
[9] 周华坤,赵新全,张超远,等.三江源区生态移民的困境与可持续发展策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3):185-186.
[10] 刘英.生态移民:西部农村地区扶贫的可持续发展之路[J].区域经济,2006(6):37-38.
[11] 刘红.三江源生态移民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6):101-105.
The Effect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on Original Inhabitants of Pastoral Community
ZHANG Wenlan, XIAN Zhu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Xining 810007, China)
National Park is emerging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contributed to increase the income sources of the inhabitants, change their way of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ffect on inhabitants of pastoral community and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support more for immigrants, transfer the production of immigrants, value the participation of inhabitants in management for park, innovate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relevant laws.
pastoral community; original inhabitant; management for park; community development;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10.3969/j.issn.1671-3168.2017.04.033
S759.91;C912.8
A
1671-3168(2017)04-0152-04
2017-06-02.
青海民族大学博士点建设调研项目阶段性成果;青海省社科规划项目“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社区参与机制”(16023)阶段性成果.
张文兰(1990-),女,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Email:85177924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