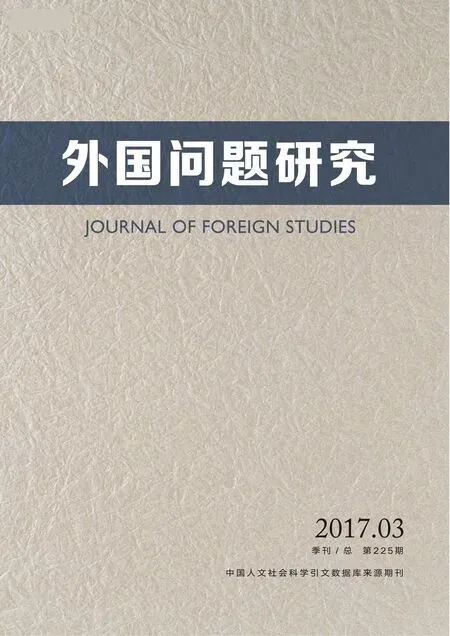“东亚协同体论”再考:“帝国话语”中的“近代”、“超近代”和“社会革命”
汪 力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东亚协同体论”再考:“帝国话语”中的“近代”、“超近代”和“社会革命”
汪 力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近代日本在其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建构帝国统治秩序的话语体系。而中日战争中日本使中国迅速屈服企图的失败不仅体现了日本军事上的局限,也表明日本帝国的话语秩序发生了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东亚协同体论”应运而生,三位代表性的“东亚协同体”论者分别从“近代”、“超近代”与“社会革命”的视角,尝试修复帝国的话语秩序。然而这一努力最终未能克服帝国话语的困境。
东亚协同体论;帝国话语;蜡山政道;三木清;尾崎秀实
从1938年到1940年,随着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日本政府的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口号的提出,“东亚协同体论”的话题席卷了日本的学界与论坛。这种理论主张,以中日战争为契机,在东亚建设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的国际秩序。热心鼓吹这种理论的,主要是属于首相近卫文麿智囊团体“昭和研究会”里的所谓“革新”的知识分子。在战后日本的思想史研究中,“东亚协同体论”起初被认为是企图利用近卫政权控制军部的中国侵略“危险的尝试”,结果堕落为侵略中国的意识形态。*宮川透:《三木清》,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8年,第105—135頁。然而,到了1980年代,“东亚协同体论”却因为其“理想主义的性格”受到肯定性的评价,被认为与近代日本外交思想中主流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相比,具有批判性的意义。*高橋久志:《「東亜協同体論」——蝋山政道、尾崎秀実、加田哲二の場合》,三輪公忠編:《日本の一九三 年代——国の内と外から》,東京:創流社,1980年,第50—79頁。伊藤のぞみ:《昭和研究会における東亜協同体論の形成》,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88年,第227—248頁。接着,随着后现代主义等各种“现代思想”在日本的流行,“东亚协同体论”又被积极评价为试图克服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同中国的民族主义“连带”,试图实现多元的地域秩序“后现代”、“后殖民”思想;*内田弘:《解説》,《三木清 東亜協同体論集》,東京:こぶし書房,2007年,第234—253頁。或者是在总体战的条件下企图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革新思想”。*米谷匡史:《戦時期日本の社会思想——現代化と戦時変革》,《思想》 1997年第12期。米谷匡史:《解説》,《尾崎秀実評論集——日中戦争期の東アジア》,東京:平凡社,2004年,第439—475頁。以及就蜡山政道而言,又反过来被认为是致力于实现东亚的“近代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类似于美国战后“近代化论”的开发不发达国家的思想。*酒井哲哉:《「東亜協同体」から:「近代化論」へ——蝋山政道における地域·開発·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位相》,日本政治学会編:《日本外交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第109—128頁。
或许就日本国内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而言,这种探寻过去思想“可能性”,从而加以继承的研究姿态,某种意义上无可厚非。然而,虽说思想与现实总是相互乖离,这些见解似乎不能很好的说明,为什么偏偏在日本推进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这些“可能性”被日本的知识分子们热心提倡。同时,在近年来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东亚协同体论”被批判为企图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提供理论依据的侵略思想。*史桂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历史研究》 2015年第5期。如果“东亚协同体论”真的是所谓重视“他者”的“主体性”的思想,那么恐怕不能简单地说这种批判仅仅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然而,本来近代日本的对外思想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多数都是主张侵略中国,或者维持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权益的思想,*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一卷 总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页。仅仅批判“东亚协同体论”是侵略思想,不能够很好的说明何以“东亚协同体论”会在这一时期出现。
与其追问“东亚协同体论”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理想主义”成分,不如思考为什么日本的知识人要在中日战争长期化的时刻谈论这样的“理想”。与其分析究竟“东亚协同体”能不能称之为“后现代”或者“后殖民”的思想,不如分析何以日本为了主张建设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必须批判“近代”,主张所谓“近代的超克”。本文拟从“帝国话语”的视角,*关于“帝国话语”这一视角,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杨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从“符号”论的角度揭示了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支配亚洲的“话语秩序”。并联系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动,探究这一问题。
一、“帝国话语”的结构与危机
入江昭指出,近代日本外交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它不是根据抽象的思想原理,而是依据对现实形势的认识,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与之相对,在民间,“理想主义”的亚细亚主义外交思想很有影响力。*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66年,第27—29頁。同时入江又指出,中日战争时期的“东亚新秩序”外交,意味着“明治以来仅仅以军事、经济面的具体政策为主轴的日本对外政策,在这里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入江昭:《日本の外交》,第133頁。
然而,中日战争以前的日本外交虽然常常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没有将自己的对外政策加以正当化的话语。例如,明治时期日本政府侵略朝鲜的外交行动,一贯打着所谓“实现朝鲜的独立与永久中立”和“维护东洋的和平”的旗号。如果主张“东亚新秩序”的侵华战争时期外交是“意识形态外交”的话,那么高唱“东洋和平”的明治政府侵略朝鲜的外交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外交”。何况,作为外交行动目标的所谓“真实意图”与将外交行为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之间,有时未必有那么清晰的界限。*最近出现了从“东洋的和平”的视角为明治政府的朝鲜侵略外交辩护的研究,例如大澤博明:《朝鮮永世中立化構想と日本外交——日清戦争前史》,井上寿一編:《日本の外交 第一巻 外交史 戦前編》,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第43—64頁。
从“帝国话语”的视角来看,如井上清所指出,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将其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也形成了。*井上清:《日本帝国主義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第149—169頁。然而,将日本的侵略扩张正当化的话语,不应只看作是在事后将外交策略和军事行动正当化的意识形态,其本身也是日本建立起其对东亚的帝国主义统治的思想要素。这些话语塑造了日本政治家与知识人关于日本统治东亚的秩序思想,并通过教育机关与媒体,控制本国与殖民地的民众,使得帝国的统治得以安定。在此基础上,这些话语才能够时刻为日本的军事与外交行为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离开这种话语秩序的背景讨论个别外交言论究竟是不是所谓“帝国的真意”,意义有限。
随着明治时代日本的扩张所形成的“帝国话语”,主要包含以下两个侧面:
一是所谓“脱亚论”话语。*如平山洋所指出(平山洋《福沢諭吉の真実》,文藝春秋、2004年),《脱亚论》在其发表时并未产生重大影响,战后才被重新“发现”。这里使用“脱亚论”一词并非指福泽谕吉的文章,而是指通过与西洋的同一化为侵略亚洲提供正当性的话语结构。这种话语声称日本通过“近代化”,已经成为“文明国”,在主张与西方列强的同一化的同时,用“前近代”、“野蛮”、“专制”等符号歧视其他东亚国家。关于这种歧视性话语的构造,韩东育指出,主要包括“以‘国民国家’取代‘华夷体系’的政治正义性”,“以‘近代文明’征服‘中世野蛮’的文明正当性”,“以‘资本经济’改造‘自足经济’的经贸优越性”三个方面。*韩东育:《东亚世界的“落差”与“权力”──从“华夷秩序”到“条约体系”》,《经济社会史评论》 2016年第2期。其外交策略始终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上,强调日本的“安全保障”的必要性,主张为此“不得不”侵略朝鲜与中国。同时通过参与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国际法秩序,与列强的亚洲侵略相协调,参与列强分割东亚的竞争。*例如通过“文明与野蛮”话语所进行的正当化甲午战争的工作,参见大谷正《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東京:研文出版,2006年,第119—126頁。
二是所谓“亚细亚主义”话语。这是强调日本是“亚洲”国家,将自身与西方列强相区别,主张与亚洲各国“连带”的话语。这种连带的根据,第一是“亚洲”这一地域概念;第二是日本与朝鲜、中国等“东亚”国家间地理以及经济上的“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同文同种”等有关日本与东亚各国间的历史、文化的共同性的主张;第四是强调面对即将到来的西方列强“侵略亚洲”的威胁,亚洲各国有共同防御的必要;第五是东亚各国为了成为“文明国”,有必要接受日本的“指导援助”,等等。*关于“亚细亚”这一区域认识的多义性,参见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 連鎖 投企》,第一部:《アジア認識の基軸》,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第31—142頁。其外交策略主要是支援朝鲜、中国等东亚国家内部的“亲日派”等势力,通过干涉内政维持和扩大帝国权益,并向西方各国主张日本在东亚的所谓“特殊地位”。*例如关于甲午战争后日本民间的诸种“兴亚”活动,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2004年;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细亚主义》,张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这两种话语乍看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两种话语都为正当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和维护帝国的权益服务。其次,两种话语在逻辑上相互补充。也就是说,当日本主张“脱亚论”,参加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竞争的时候,同时会主张日本与东亚的“特殊关系”,强调日本独自的利益。而当日本提倡“亚细亚主义”,要求与亚洲“连带”的时候,会同时主张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文明国”,主张日本的“指导的地位”。更进一步说,如坂野润治所指出,在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同一论者会根据形势变化交替主张“脱亚论”和“亚细亚主义”,在这两种话语间的转换不被同时代的人看作是所谓“思想转向”。*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明治 思想の実像》,東京:筑摩書房,2013年。
这样的话语秩序在日本的扩张和帝国统治的稳定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蛮横的“二十一条”外交引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昂扬,帝国的话语秩序开始出现破绽。大战后,随着国际秩序的变化和东亚地区所谓“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帝国日本的话语也进行了调整。如“币原外交”的理念所体现的,随着国际联盟等国际机构高唱“民族自决”与“国际正义”,日本也不得不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币原外交”在以与欧美各国的“协调”为基本理念的同时,比起日本在华的政治、军事利益,更重视经济利益,奉行所谓“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入江昭:《日本の外交》,第90—91頁。此外,币原的所谓“不干涉内政”的理念,企图通过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妥协,满足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部分要求,来继续维持帝国权益,特别是所谓“满蒙权益”。从通过与欧美协调来维持帝国权益这一点来看,也可以看作是“脱亚论”思想的延长。*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明治 思想の実像》,第173頁。
尽管采取了这样的转换,进入昭和期,帝国的话语秩序仍然变得不安定了,到1930年代中期以后终于走向崩溃。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所谓“协调外交”的崩溃。“币原外交”中的“不干涉中国内政”话语,只在中国仍处于分裂状态时有效,当中国的统一逐渐成为现实的时候就会陷入危机。为了镇压“满洲”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和准备世界大战,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了傀儡国家伪满洲国。中国就此向国联提出控诉,结果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由此,日本外交不得不进行重大的方向转换。此后,尽管日本采取种种手段试图恢复与英美的协调,*关于所谓“危机中的协调外交”,参见井上寿一:《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第三章:《「東亜モンロー主義」外交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東京:筑摩書房,2006年,第87—129頁。不过,针对此点,小林启治认为,“协调外交”这一概念不能仅仅认为是对英美协调,而是与否定侵略、国际正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协调理念有关,“满洲事变”后日本外交即使对个别国家采取“协调”政策,也不应理解为协调外交的继续。见小林啓治:《二大政党制の形成と協調外交の条件》,井上寿一編:《日本の外交 第一巻 外交史 戦前編》,第153—154頁。并成功维持了经济上的贸易往来,但整体仍未能取得成功。关东军为了正当化所谓“满洲国”的存在,采用了“王道”等富于“亚细亚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第108—118頁。这种意识形态转换又反过来影响到日本国内,帝国话语整体上亚细亚主义的色彩大大增强。本来,近代日本必须不停的向西方表明自己并非“黄祸”而是“文明国”。亚细亚主义话语的主流化使得日本与西洋的同一化变得非常困难。
第二是近代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国民革命后,尽管出现了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但政治上仍处于内战等不安定状态下。因此,日本仍然能将中国看作“前近代”的“野蛮”与“混乱”。然而,进入1930年代,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中国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从1935年起,中国共产党也转换了政策。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的举国一致态势,给日本以很大的冲击。以矢内原忠雄的《支那问题的所在》为首,一时间“支那统一化”成为日本言论界的流行话题。*关于“中国统一化论战”,参见西村成雄:《日中戦争前夜の中国分析——「再認識論」と「統一化論争」》、岸本美緒編《岩波講座 帝国日本の学知 第三巻 東洋学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294—332頁。有人甚至提出,与中国走向统一相反,日本的国策的统一性由于政府、军部、政党等多元行动主体的不统一走向崩溃。*山本実彦:《中国の近状を報告す》,《改造》,1937年2月号,223頁。虽然如坂野润治所指出,日本总是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较为有力的时期主张“脱亚论”,*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明治 思想の実像》,第155頁。这也必须以事实上中国近代国家尚未形成为前提。不管国民政府实现的统一多么不充分,既然统一的近代国家已经形成,无论日本如何渲染“前近代的野蛮”都只能是自说自话。此外,“亚细亚主义”话语总是强调在中国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日本的“指导”的必要性。这一点也随着在中国统一化的过程中,国家建设的样板从模仿日本到参考苏俄、德国等其他国家,走向多样化而瓦解。*关于1930年代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作为近代化的模范国的苏联形象,参见郑大华、张英:《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世界历史》 2009年第2期。关于德国的影响,参见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东亚的流行。在1930年代,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要远远超出实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虽然像大上末广那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强调中国社会的“亚细亚的专制性”,鼓吹日本殖民统治的“进步性”也是可能的,*石堂清倫、野間清、野々村一雄、小林庄一:《十五年戦争と満鉄調査部》,東京:原書房,1986年,第35—39頁。但是作为一种激进的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秩序意识非常的不稳定,“进步”与“反动”的关系不断的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终结这一时代认识的前提下,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曾经“进步”的日本资本主义,如今已经变得“反动”,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崩溃。此外,这一时期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间进行的“日本资本主义论战”中,以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为代表的“讲座派”占据了优势。《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一书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建立在“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以为军备扩张而强行建立的军事产业为中心,具有结构上的脆弱性,必然走向崩溃。*長岡新吉:《日本資本主義論争の群像》,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84年,第170—172頁。随着这样的日本认识的传播,“半封建”的日本要对中国主张自己“近代”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变得十分困难。
当话语的统治不安定的时候,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能”,暴力的统治范围就会扩大。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继而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如近卫文麿政权的声明所显示的,这场战争以保护“居留民的生命财产”,“膺惩支那军的暴戾”为口号。*《盧溝橋事件に関する政府の声明》(1937年8月15日),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史史料5現代》,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第78—79頁。这种围绕居留民的“人权”的话语,某种意义上也是“脱亚论”的延长。然而,尽管日军在战场上连续取得胜利,只要中国拒绝屈服,这种话语对于“收拾事变”就毫无意义。随着日本政府否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政府地位,一举取消宣战媾和问题,“事变”的“解决”变得更加遥遥无期。在这种尴尬处境之下,为了诱降国民政府,“收拾事变”,近卫政权转换方针,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将侵华战争的目的重新设定为在东亚建立所谓“新秩序”。*《東亜新秩序政府声明》(1938年11月3日)、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史史料5現代》,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第82—83頁。“东亚协同体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登场的。
二、蜡山政道:“近代”的再编
尽管“东亚协同体论”并不是蜡山政道提出的,但“东亚协同体论”忽然成为日本学术思想界的中心话题,很大程度是由于蜡山的《东亚协同体的理论》一文的影响。蜡山也不无得意地说,自己“起到了陈胜、吴广的作用”。*蝋山政道:《国民協同体の形成》,《改造》,1939年5月号,第9頁。通常认为,“东亚协同体论”的共通特征之一是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一定程度的积极评价。*橋川文三:《東亜共同体の中国理念》,《橋川文三著作集》,第七巻,東京:筑摩書房,1986年,第240頁。然而,蜡山却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犯了双重的错误”,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重错误是仅仅主张自己的民族主义,缺乏对东洋整体的认识;第二重错误是勾结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与日本对抗。*蝋山政道:《東亜協同体の理論》,《改造》,1938年11月号,第13頁。
那么,蜡山何以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采取如此严厉的批判立场?要理解这一点,不能仅仅只看中日全面战争时期蜡山的言论,需要从蜡山长期以来的国际政治思想来考察。
作为日本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蜡山政道终其一生都对国际秩序问题保持着高度的关心。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蜡山的许多论著都讨论了中日关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问题,但其视角大多并非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为中心,而是始终注目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机构的关系问题。
早在1928年,蜡山就已经指出,在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中,比起日美两国间的问题,围绕中国的矛盾要深刻得多。*蝋山政道:《国際政治と国際行政》,東京:厳松堂書店,1928年,第181頁。九·一八事变以后,蜡山在拥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谓“特殊权益”,为关东军的行动辩护的同时,又反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认为拥护“满洲国”与维护日本在国联的地位可以并行不悖。*蝋山政道:《満洲事変と国際連盟》,《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21—31頁。与他的主张相反,日本退出国联,舆论界开始煽动所谓“自主外交”。对此蜡山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势力期待国际联盟、英美和苏联的介入,然而这些势力之间互相对立,不可能统一对抗日本。日本只要与英美保持个别的协调,同时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就能同时实现帝国统治的安定和与国际秩序的协调。*蝋山政道:《連盟脱退と今後の国際外交》,《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37—45頁。此外,蜡山还指出,尽管苏联的外交非常“自主”,但绝非像日本的“自主外交”论者那样仅仅主张本国的利益,而是与国联积极交涉,将本国的利益包装成人类普遍的利益来主张。蜡山认为这是20世纪新的外交技术,日本应当学习。*蝋山政道:《破綻せる国際機構の再検討》,《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57—60頁。
1935年蜡山政道的访美,对于他的“东亚新秩序”构想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后来他在其“东亚新秩序”论集《东亚与世界》的序言中回想,自己的“东亚新秩序”思想是在访问美国的过程中为了对抗美国人对日本的东亚政策的种种批判而形成的。*蝋山政道:《東亜と世界──新秩序への論策》,東京:改造社,1941年,“序”第1頁。蜡山在访问的感想中,一方面批判美国人对自己所主张的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体制等普遍的秩序的执着,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的根本思想是所谓“实用主义”,美国人所信奉的普遍的理念可以因为实际的需要而修正。为了经济复兴等客观的需要,美国有与日本妥协的可能。由此蜡山关注罗斯福政权对东亚局势的所谓“静观”政策。*蝋山政道:《危機の視点より観たる日米関係》,《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108—113頁。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蜡山从近代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与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关系的角度,对战争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当近代日本想要超出英美所设定的国际秩序,进行独自的扩张时,必须要有扩张对象以外的“第三国”的威胁的存在。实际的战争对手,在以朝鲜为侵略对象的时候是清朝,而在以中国为侵略对象的时候是俄国。通过这种与第三国的战争,日本得以在扩大帝国版图的同时维持与英美的合作关系。然而,由于辛亥革命和俄国革命,俄国一时间退出了东亚的霸权争夺,而中国陷入分裂状态。从而使得日本无法再主张自己独自的要求,只好追随英美所设定的国际秩序。此后,苏联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通过国民革命展开了再统一运动,重新回到国际舞台,这样日本独自的权益开始动摇。同时,由于英美对于国民政府的统一运动采取乐见其成的态度,导致“满洲事变”的发生,“协调外交”崩溃。也就是说,近代日本的扩张总是需要与中国或者俄国等“第三国”的对抗和与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协调这“两重性”的条件。当这种“双重条件”不能维持的时候,帝国的统治秩序就会出现困难。蜡山认为,为了克服这种困境,日本需要建立由自己主导的“自律的轴心”。*蝋山政道:《支那事変の背景と東亜政局の安定点》,《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185—192頁。
至于蜡山这个时期具体构想了怎样的“自律的轴心”,有必要注意他提出了其独特的“开发”思想。蜡山在论及统治华北的原理的时候,一方面批评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理念“民族”不过是19世纪的旧观念,由于其“感情”的支配,国民政府才“堕落”到共产党的人民战线战略中;另一方面,蜡山又主张,为了防止华北出现“思想真空”导致共产主义乘虚而入,应当将三民主义以“民生”为核心进行重组,成为“民生、民权、民族”的顺序,再加以利用。*蝋山政道:《北支政治工作の文化的基礎》,《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211—214頁。蜡山又认为,围绕怎样开发中国,有三条相对立的路线,即英国所支持的国民政府的开发,日本主导的“满洲国”式开发,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联式开发。他断言,国民政府的开发不仅是从属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式开发,而且其范围仅仅局限于一部分的城市,广大农村仍处于完全未开发的状态;共产党所提倡的苏联式开发虽然不乏将来的可能性,但是既然中共已经选择与国民政府合流,就失去了其独自的意义。至于日本主导的“满洲国”式开发,蜡山声称,这种开发主要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目的,因此与从资本的逻辑出发的帝国主义的开发有着根本不同;然而,至于其具体的政策,蜡山批判说,由于过度依赖政府机关以及财阀等特权资本,日本总是推行自以为是的教条的开发政策,被中国人“误解”为帝国主义也是无可奈何。他主张有必要动员更多的民间资本和文化团体,给日本式开发增添活力。*蝋山政道:《支那開発の国際相克線》,《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224—235頁。
众所周知,1938年,恰好在武汉陷落和近卫政权的“东亚新秩序声明”之前不久,蜡山发表了著名的《东亚协同体的理论》一文,其中将中日战争的意义规定为“东洋的觉醒”,认为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等欧美主导的东亚秩序发生破绽,体现“东洋的统一”的东亚区域秩序成为现实。蜡山又认为,像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那样的感性的表达东洋意识是完全不够的,何况东亚其实并不存在统一的文化,比起文化的统一,在日本的指导下推进协同体式的经济开发更为重要。他主张,与这种开发相结合而建立的新的中国政治体制,应该是地方的自治政府与中央的联邦政府相统一的双重体制。*蝋山政道:《東亜協同体の理論》,《改造》,1938年11月号,第6—27頁。
这些主张对于世界秩序的意义,到欧洲大战爆发之后,蜡山才在《世界新秩序的展望》一文中进行了清晰的表述。这里,蜡山首先再次强调,中日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在东亚的特殊地位与英美所主导的普遍的国际秩序间的矛盾。继而他指出,这次欧洲大战的原因与此也有相似之处。本来东欧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民族主义很不发达。尽管德国和俄国在这个地区有着各自的特殊地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败北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两国都从东欧暂时撤退。于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将并不适用于该区域的民族主义的原理强行灌输到这一地区,建立起众多小国,从而无视了德国和俄国客观的生存需要。所以,蜡山主张,日本的“东亚新秩序”问题并不是日本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史规模的秩序变革的一环。*蝋山政道:《世界新秩序の展望──東亜協同体を序曲として》,《改造》,1939年11月号,第4—19頁。
然而,必须指出,这一宏伟的世界秩序变革的目的,不外乎寻求与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妥协。蜡山主张,尽管日本所提倡的“东亚新秩序”与《九国公约》矛盾,但事实上日本政府并不敌视美国,始终希望美国能够认清东亚的“现实”,邀请美国商讨《九国条约》的修改问题。修改的基准,首先当然是承认日本在东亚的“特殊地位”,其次是共同“援助”中国的近代化。*蝋山政道:《世界新秩序の展望──東亜協同体を序曲として》,《改造》,1939年11月号,第19—24頁。也就是说蜡山的开发论并不是封闭的,相反,可以说是对英美开放的,对其“门户开放”的要求采取妥协的态度。反过来也可以说,蜡山是为了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协调,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东亚的所谓“特殊地位”,才主张这样的开发论。
对美国,蜡山的“东亚协同体论”与其说是要超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建立“亚细亚主义”的东亚秩序,还不如说是为了与美国的世界秩序妥协,才需要制造日本独有的“世界秩序原理”。同时,在中国终于艰难的实现以军事动员体制为中心的民族国家这一曾经是日本所提倡的“近代”时,蜡山却将其批判为过时的十九世纪的残余,或者是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的似是而非的“近代”,而主张只有日本所主导的东亚的协同体式的开发才是真正应当追求的“近代”。也就是说,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话语构造来看,这不过是为了修复由于与西方同一化的困难和中国统一近代国家的形成而带来的帝国话语秩序破绽。在这个意义上,蜡山政道的“东亚协同体论”可以说是帝国话语中“近代”的再编。
三、三木清:“近代的超克”的形成
在与“东亚协同体论”有关的知识分子中,三木清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他作为当时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积极提倡“东亚协同体论”,并担任了昭和研究会关于“东亚协同体论”的报告书《新日本的思想原理》的起草工作。他的“东亚协同体论”,最后主张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开拓世界史的新阶段,可谓开创了太平洋战争下的“近代的超克论”的先河。*三木清在“近代的超克”思潮中的位置,参见廣松渉《〈近代の超克〉論》第六章:《三木清の「時務の論理」と隘路》,東京:講談社,1989年,第126—155頁。然而,本来三木清是“西洋”与“近代”的倾向很强的知识分子,对东亚的国际秩序问题并不关心。如果三木作为一位严肃的哲学家,并非只是随着时局任意的转换立场,那么他何以走向这样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有加以考察的必要。
尽管在20年代三木一度接近马克思主义,在中日全面战争前夜,他已经开始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对苏联的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等右翼的“改造”思想和民族主义,而是坚持进步立场,探索抵抗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三木清:《自由主義の将来性》,《三木清全集》第十五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16—18頁。作为哲学家,三木并非讨论具体的政治问题,而是通过讨论“文化”问题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他批判当时流行的将日本主义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的现象,指出这种排外主义的日本主义尽管大声主张所谓“日本的东西”,实际上却无法说清究竟什么是“日本”的;虽然激烈排斥西方文化,却利用德国的全体主义哲学为自己辩护。三木认为,这种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主张日本“全体主义”的特质,不过是由于日本社会还遗留有很多“封建残余”而已。真正的“日本精神”绝非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吸收中国、印度、西方的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现在被说成属于“西方”的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西方所特有,而是如近代科学等具有普遍性的近代文化。所以,现代的日本文化也不应该封闭自己,而应当在保持民族的主体性的同时,将西方文化“身体化”,使之真正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结果,将能够形成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三木清:《日本的性格とファシズム》,《三木清全集》第十三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241—267頁。这就是三木所构想的抵抗法西斯主义的逻辑。
从这种追寻普遍性的立场出发,三木开始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结构中帝国话语秩序的破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木认为,这种破绽正是他所指出的日本主义的局限性的表现。在1935年中日两国围绕华北事变的纷争中,三木提出了如下见解。日本在推动华北分离时打出了“共同防止赤化”的旗号,然而“赤化”也就是共产主义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思想问题。在日本,可以用“日本精神”来镇压共产主义,但在中国宣传“日本精神”毫无意义。如果不用思想而企图用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会得出日本必须用暴力征服全世界,以根绝“赤化”的荒谬结论。因此,为了“日支亲善”,日本不能在中国宣传“日本的东西”,而必须向西方传播近代文化那样,主张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三木清:《日支思想問題》,《三木清全集》第十五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28—35頁。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三木将其看作获得他所主张的普遍的思想的良机。三木认为,日本人虽然以“日支亲善”为战争目的,却没有有效的方法让中国人理解这一点。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激烈抵抗,证明了日本人在“思想战”中的失败。这种失败表明了“日本精神”的局限性。日本有“日本精神”,中国也有“支那精神”,主张“日本精神”是不可能说服中国人的。为了“日支亲善”,日本必须主张具有“世界的妥当性”的思想。*三木清:《日本の現実》,《三木清全集》第十三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438—443頁。
从这种“普遍”的视点出发,三木就必须将中国认识为“他者”。因为如果中国和日本是同质的,那么日本主张“日本精神”也能够统治中国,没有寻求“普遍性”的思想的必要。因此,三木对于传统的“同文同种”等亚细亚主义话语持批判的态度。他指出,实际上日中两国人种不同,虽然同样使用汉字,其含义却完全不同,以“同文同种”为根据主张“日支亲善”是没有说服力的。本来,专门研究“哲学”这一西方学术的三木对于中国思想等“东洋”的学术兴趣有限,这一时期却开始关心思想界流行的一些中国研究,特别是津田左右吉的中国思想论对他启发很大。津田认为,虽然古代中国向日本传播了许多文化,但这些基本上只影响了一部分贵族,对于一般民众几乎毫无影响。日本的历史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并未和中国形成一个“东洋”世界。三木在对津田这一区别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逻辑表示赞赏的同时,又认为不应完全否定“东洋一体”。也就是说,“东洋一体”的实现,不是依据“共同的传统文化”等文化史上的关系,而是只有通过创造新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才有可能。从这一观点出发,三木指出,津田对佛教的影响力评价过低,佛教之所以能对中国和日本以及整个亚洲发生巨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普遍性。*三木清:《日本の現実》,《三木清全集》第十三巻,第446—457頁。
从这种视角出发,三木认为,中国历史倒可以给现在的日本提供不少启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最具世界性文化影响力的是唐代。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唐的国力比明或者清要强,而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期代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对印度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吸收,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此外,日本能实现其独自的历史发展,也是因为文化上不仅不排外,还总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来发展自身的文化。这也是日本的近代化能够成功的原因。三木主张,今天的日本文化也不应采取自我封闭的态度,而应该努力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创造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来实现“东洋的统一”,从而为世界的统一作出贡献。*三木清:《文化の力》,《三木清全集》第十四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318—335頁。
出于这种对“他者”的认识的视角,三木对蜡山政道那种否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价值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三木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伴随着中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所必然出现的事物,具有客观的进步意义,而且并非与建构“东亚协同体”矛盾,相反正是它的前提。日本应该接受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如果要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加以限制,也不能从日本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而必须从世界的普遍性的立场出发,这时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应当受到同样的限制。*三木清:《東亜思想の根據》,《三木清全集》第十五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311—312頁。
由于三木把侵略中国的战争看作获得“普遍性”的契机,他就不得不站在肯定战时“日本的现实”的立场上。这里他提出了“历史的理性”的思想。三木引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指出历史并非通过道德的善或者主观的普遍的目的前进,相反通过私利私欲等“恶”来实现历史的普遍性。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然而,三木并不以黑格尔的逻辑为满足,因为这种逻辑把人看成了历史的道具,不符合三木的人道主义思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三木计划通过“技术”来统一主观与客观、历史与主体、情念(pathos)与理性(logos),这就是他所谓“构想力的逻辑”,最终成为三木晚年宏大的哲学冒险。*三木清:《歴史の理性》,《三木清全集》第十四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249—260頁。此外,三木号召,日本的知识分子应该更有自信,因为现在日本的问题离开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无法解决的;同时,知识分子也应该更加积极的关心现实。日本所面对的现实过于重大,不允许任何人置身事外。知识分子不应揣测怀疑日本的战争动机,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而应该从“历史的理性”的立场重视其历史意义。三木还声称,如果无法发现这样的历史意义,就只有自己“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三木清:《知識階級に與ふ》,《三木清全集》第十五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239—242頁。
从这种肯定现实的立场出发,三木终于进一步对他本来的抵抗对象法西斯主义,也采取了积极包摄的态度。三木认为,近代的自由主义的知性过于抽象,对于身体和历史等具体性缺乏理解,而另一方面民族的协同体的思想与之相反,在理性和开放的态度上有所欠缺。所以,新的知性应该建立在利益社会(Gesellschaft)和共同体(Gemeinschaft)的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这样产生的新的“全体主义”,才有可能成为指导“世界革新”的普遍性。*三木清:《知性の改造》,《三木清全集》第十四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191—216頁。三木主张,这种“世界史的”理念的目标是“确立超越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全体主义的新的思想原理”,*三木清:《世界の危機と日本の立場》,《三木清全集》第十五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387頁。从而解决资本主义问题这一二十世纪最大的世界史课题,“东亚协同体”正是实现这一世界史的普遍性的途径。*三木清:《現代日本に於ける世界史の意義》,《三木清全集》第十四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149頁。
中日战争前夜的三木虽然已经告别马克思主义,但仍在努力探索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性。他从而发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话语秩序的破绽,将其视为获得普遍性的契机。由此他发现了中国这一“他者”,并高度评价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然而,由此三木也给侵略战争赋予积极的意义,并呼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侵略战争。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修复帝国的话语秩序的努力。进一步,由于三木参与帝国话语秩序的建构,法西斯主义就从他抵抗的对象变成了“辩证法的扬弃”的对象。最终三木所构想的世界史的普遍性,是一种通过“东洋的统一”来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一种“近代的超克”的逻辑。如果“近代的超克”可以看作是日本主义的一个顶点,那么三木就从对抗日本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参与帝国的话语秩序的建构,最终为最为极端的日本主义的出现打开了道路。
四、尾崎秀实:“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
与蜡山政道和三木清不同,“东亚协同体论”的另一位参与者尾崎秀实从自己的在中国的体验出发,一贯关注中国问题,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发表了大量独特的评论。尾崎在他众多的评论文章中,最关注的始终是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尾崎有关“东亚协同体论”的评论中,他说:“与民族问题相比,‘东亚协同体论’应该认识到自己是怎样可怜和微不足道。”*尾崎秀実:《東亜協同体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観的基礎》,《中央公論》,1939年1日号,第13頁。然而。与此同时,尾崎又对当时推行统一和抗战的国民政府,始终采取十分批判的态度。
从尾崎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说,这种态度某种意义上理所当然。不过,为了从理论上理解尾崎的立场,我们有必要具体的分析尾崎所谓“民族问题”的意义。“民族问题”一词听起来十分模糊,可能会被理解为少数民族权益或者一般的民族独立问题。但就共产主义者尾崎而言,其“民族问题”的概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思想有关。列宁在20世纪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俄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的论战中,形成了其“民族自决”的思想。他坚决拥护俄国与东欧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利,但认为“民族主义”基本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课题,无产阶级没有积极加以主张的必要,并反对崩得等团体“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深入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结果,开始重视殖民地解放的问题,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民族”这一20世纪的根本课题。俄国革命后,随着欧洲革命的退潮,共产国际形成了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斗争的世界革命战略。这一战略在主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无产阶级应当参与的同时,又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的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解决民族解放问题,总是想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妥协。所以能够彻底完成民族解放任务的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政党,无产阶级应该在支援资产阶级左派的同时夺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参见太田仁樹:《レーニンにおける資本主義と民族問題》,《岡山大学経済学会雑誌》,第19卷3、4号。
从这一理论的前提出发尾崎的逻辑就变得十分清晰。在他看来,既然国民政府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权,就必然会向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妥协,不可能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尾崎在接到西安事变的新闻当天写下的,预言了蒋介石的存活的《张学良政变的意义》一文,向来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依据深刻的科学的分析对事情的发展作出了正确的预测,成为“尾崎秀实传说”的一部分,*米谷匡史:《解説》,《尾崎秀実時評集》,第453—454頁。然而事实上这篇文章的内在逻辑并不一贯,在指出国民政府的统一得到广泛的支持,作为统一的象征的蒋介石不会被杀害的同时,又认为这种统一不过是表面文章,并未根本改变社会结构,这种“统一”越进展中国社会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化越加深,西安事变不过是这种“统一”的矛盾的体现而已。*尾崎秀実:《張学良クーデターの意義——支那社会の内部的矛盾の爆発》,《中央公論》,1937年1月号,第406—414頁。此外在“中国统一化论战”中,尾崎激烈的批判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矢内原忠雄,分析了国民政府主导的产业开发如何与英美等“国际资本”相勾结,从而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对矢内原的论敌大上末广表示了支持。*尾崎秀実:《支那の産業開発と国際資本》,《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一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131—135頁。更进一步,在中日全面战争走向扩大化之际,尾崎又分析了国民政府的军阀本质及其与财阀、列强的关系,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激烈批判。*尾崎秀実:《南京政府論》,《中央公論》,1937年9月号,第23—36頁。
虽然尾崎如此激烈的批判国民政府,但这绝不意味着尾崎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评价不高。也就是说从尾崎的逻辑来看,中国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世界史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帝民族主义,其根本的力量源泉不在于国民政府,而在于人民大众。国民政府并非中国民族主义的真正的代表,不过是部分的利用这种巨大的能量,勉强维持外观上的“统一”而已。所以尾崎始终关注中国的“民族运动”,并将中国共产党看作领导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共产党虽然现在受到国民党的“围剿”,势力受到很大打击,但由于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换,又获得了集结民族运动的能量的良机。随着这一政策转换成为现实,国民党的本质的变化也就是再次左翼化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尾崎秀実:《南京政府と中国共産党》,《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一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213—214頁。随着战争的进行,尾崎还认为,国民政府如此激烈抵抗的原因不在于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为了集中在上海、南京一带的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国民政府由于其内在的脆弱性,有可能寻求与日本妥协,以便再次镇压共产党。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所期待的“和平”也不可能实现,中国人民必然会抛弃蒋介石,集结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抗日势力的旗帜之下。*尾崎秀実:《蒋介石よどこへ行く》,《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二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302—303頁。尾崎的“‘支那’赤化的趋势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尾崎秀実:《支那は果して赤化するか》,《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一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197頁。这一命运般的断言,应当从这样的逻辑来理解。
在尾崎看来,即便日本帝国主义能打倒国民政府,也不可能战胜这一巨大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力量。然而,如果说这是否意味着尾崎认为日本绝对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从而“收拾”“支那事变”的话,则又并非如此。尾崎参与近卫内阁和昭和研究会,并参与“东亚协同体论”的讨论,一方面固然出于党的情报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他所期待的中日战争“大乘的解决”的可能性。他比任何人都要强调“东亚协同体”中的“民族问题”,与其说是为了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的抗日运动,不如说是期待着日本的“革新”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变革。*尾崎秀実:《東亜協同体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観的基礎》,《中央公論》,1939年1月号,第17—18頁。如果日本能够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的“革新”,当然中国也能随之顺利挣脱殖民地、半殖民地位,以民族解放为中心的“民族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一点也可以从尾崎在所谓“和平运动”中为汪精卫伪政权提供的意识形态中也能看到。他主张,汪精卫政权在得到日本朝野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的基础上,应当谋求“民族问题”的根本的解决。*尾崎秀実:《汪精衛政権の基礎》,《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二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378頁。
由此,在尾崎看来,“东亚协同体论”论的最终指向是包含中日两国的整个东亚的“革新”。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自然十分重视这一“革新”的经济基础。就“东洋一体”的理念而言,尾崎向来对明治以来“亚细亚主义”的“同文同种”论述不以为然,认为依靠“邻邦”和“同文同种”之类的议论来达成中日两国间的理解,实乃“百年待河清”之举,这类“‘东洋的’支那论”,本质上都是为“大陆政策的本原的方法”即武力扩张服务的。*尾崎秀実:《支那論の貧困と事変の認識》,《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一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220—221頁。不过,这种严厉的批判不代表尾崎不构想某种中日间“连带”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在他看来正是东亚革新的社会基础。这一基础就是土地问题。尾崎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的中国认识,指出中国社会变革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的革命任务,并认为随着中日战争的展开,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需要带来了实现这一变革的契机。然而,土地问题并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同样是日本社会变革的核心问题。尾崎援引“讲座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出日本农业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小农土地不足,地租过高等问题。这样,“东亚一体”的共同性倒不在于“同文同种”,而在于共同的“革命任务”。“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一高远理想的现实条件,首先应该是东洋诸社会的内容即半封建的农业社会的解体,以及由此而来的农民解放。日本必须先自己革新,再为诸民族高度的结合创造条件。”*尾崎秀実:《東亜共栄圏の基底に横たわる重要問題》,《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三巻,勁草書房,1977年,第210—216頁。也就是说尾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恢复了在批判“亚细亚主义”的过程中失去的“东亚共同性”。
作为一种激进的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秩序意识是非常不安定的。然而正如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大多数这一时期都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即保卫苏联的逻辑所表明的,如果占据“社会主义”的位置,就能取得相当的优越地位。尾崎秀实的“东亚协同体论”及其“东亚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帝国主义”的话语。如果将尾崎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另当别论的话,*战后尾崎作为共产国际的谍报员为人们所熟知,但其实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诸多贡献,参见渡部富哉:《尾崎秀実を軸としたゾルゲ事件と中共諜報団事件——彼らは侵略戦争に反対し中国革命の勝利のために闘った》,白井久也編:《国際スパイ ゾルゲの世界戦争と革命》,東京:社会評論社,2003年,第27—51頁。他战争时期的言论活动,也可以看作一种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解决帝国话语秩序的危机的努力。
结语:“东亚协同体论”的归结
“东亚协同体论”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抗日民族主义。通过对以上三位“东亚协同体”论者的思想逻辑的整理,可以发现以下的力学结构。个别的“东亚协同体”论者越是批判中国的民族主义,他的思想就越重视“对英美协调”,越“近代”;反之越高度评价中国的民族主义,其思想逻辑就越倾向于挑战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并主张“近代的超克”。蜡山在探索与美国妥协的途径的同时,激烈批判中国的民族主义;三木虽然主张吸收西洋文化,但随着积极评价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主张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实现新的“世界统一”。尾崎秀实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民族主义,予以极高的评价,同时积极主张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并暗中期待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蜡山政道明确坦白了这一力学结构,他主张如果与英美的妥协顺利进行,那么日本扶持的中国新政治体制应该采取地方高度自治的分权的联邦制;而如果这种妥协不顺利,则不得不采取权力相对集中的集权的联邦制。*蝋山政道:《東亜協同体の理論》,《改造》,1938年11月号,第27頁。
当然,“东亚协同体论”内部“对英美协调”与积极评价中国民族主义的矛盾,并非意味着这一时期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事实上恰恰相反,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列强为了遏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得不开始摸索与中国的合作;同时中国也期待着战争的所谓“国际的解决”。*参见鹿锡俊:《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美关系的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一九三 年代的中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44—460页。“东亚协同体论”中两者的对立的奥秘就在于,日本为了继续侵略中国,必须将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相分离。这或许正是“东亚协同体论”背后的“帝国的真意”所在。
此外,此时“东亚协同体论”里的种种区域秩序构想,不可避免的与中国的国家构想与秩序观相对立。首先与蜡山所定义的日本主导的开发构想和国民党主导的依靠英美的开发构想这一对立相反,这一时期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本来国民政府重视轻工业、以输出为重的工业化构想,急速地向以重工业和军事产业为重心的自我中心化构想转变。*参见严鹏:《国家作用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一个李斯特主义的解读》,《当代经济研究》 2015年第12期。至于三木清所主张的以日本的“普遍性”来引领东亚新秩序,如冯友兰所指出,“在历史上,在地理上,或在文化上,无论就哪一方面说,中国本来是东亚的主人”,虽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以后,不得不以日本为模仿国来建设近代国家,但这不过是因为日本在近代化,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建设上取得了成功而已,如果中国也实现了近代化,那么“中国天然是东亚的主人”。*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尽管在工业和军事力量方面一时处于劣势,但中国并没有对自己根本的价值观失去信心。当日本无法用暴力征服中国时,开始主张自己价值观的普遍性,自然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
最后,尾崎秀实的“社会主义变革”构想并非是他一个人独自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近卫新体制运动有关的“左派”知识人的共通理念。然而,这一“革新幻想”在面对天皇制的壁垒时,也不得不中途挫折。*伊藤隆:《大政翼賛会への道——近衛新体制》,東京:講談社,2015年,第231—232頁。诚然,“革新左派”可以勉为其难的将天皇制、战时体制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然而这样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以天皇制为中心的,致力于战时动员的国家社会主义亦即“日本法西斯主义”。近卫新体制的结局也可以说是“东亚协同体”的“梦想”的一个归结。
2017-03-0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亚诸国当今纷争的历史渊源研究”(编号:15CSS028)。
汪力(1988-),男,安徽宣城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A
1674-6201(2017)03-0020-12
(责任编辑:冯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