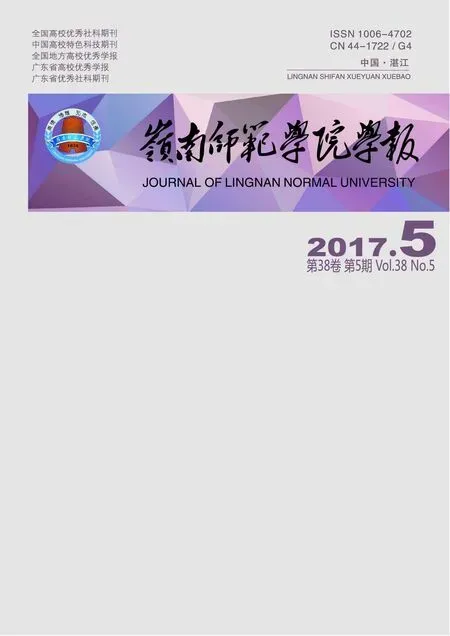追问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应然性
龙 翔
(岭南师范学院 哲学研究所,广东 湛江 524048)
追问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应然性
龙 翔
(岭南师范学院 哲学研究所,广东 湛江 524048)
技术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危害最大、影响最广的潜在源头。技术主体作为技术的建构者和技术风险的制造者,当然应该对其制造的技术风险承担伦理责任。同时,由于技术主体又具备独有的认知、评估和解决技术风险的能力,需要继续追问他们的伦理应然性。
技术风险;技术主体;伦理应然性
一、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
“风险”这个词最早在欧洲大陆使用,当时主要是指在空间存在的客观危险,如在某地或某处发生的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自然现象或者航海遇到礁石、风暴等事件危险。英语的“风险”一词,是英国在17世纪从欧陆引进的,并将其演变成了“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的意思。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技术、工业、商业、经济及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发展需要,风险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三维变化,即从空间转向到时间;从正在发生转向到可能会发生;从确定性转向到不确定性。正如以研究“风险社会”著称的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许多学者所说的:“‘风险’这个词的意思也已经不是最初的‘遇到危险’,而是指在将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1]21。“风险的本质并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会发生”[2]3。“风险是某件不期望的和危险的事物可能发生的潜力”[3]133。如果这种可能性已经实现,风险就成为了现实的破坏或伤害。
在20世纪之前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与人无关的“自然风险”。它是自然因素和物力现象所造成的风险,这种“外在风险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4]22。外在的自然风险的发生虽然存在着突发性、意外性、偶然性和非常态性,但它是自然发生的,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技术方法特别是工具理性的建立和完善,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实现了由附魅向祛魅的转变,人类利用已经掌握的自然规律和高度的理性化逻辑,基本上可以将大量同质发生的自然事件变成“确定的”、可以把握和控制的对象。自然风险的不确定性不断地过渡到确定性。绝大部分的自然风险都可以被准确地预测、评价和防范,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自然风险问题。因此,“风险”还没有成为当时社会需要担忧的一个主要问题。
与以前社会不同,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的风险中,虽然也有来自自然界的,但是更多的则是“人为的风险”,这种风险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比如人为的金融投资、商品买卖、企业决策、社会制度、乘坐飞机、工程建设等等都会带来风险,在所有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当中,人类自己发明、使用的技术引发的技术风险则是最难以预料、最令人不安、也是最可怕的。虽然古代技术也会引发技术风险,但其风险性根本无法与20世纪的现代技术相提并论。正如吉登斯说的:“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5]115。由于技术是直接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以,大力发展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追求的目标。但是,恰恰是不断发展的现代技术引发的各种技术风险成为现代社会最危险的源头。“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6]63
由于技术风险源于技术,而技术又是由技术主体发明与建构出来的,所以,从逻辑关系上讲,技术主体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技术主体在发明创造技术的同时,无意中也制造出了技术风险,因此,技术主体与技术风险之间是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
二、追问技术主体的伦理应然性
既然技术风险成为严重威胁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发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然迫切需要人类自己积极行动起来,采取谨慎的态度和科学的办法,尤其是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技术主体需要积极承担伦理责任,才能有效地化解这种“文明的危机”。“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能预见后果。”[8]90根据责任的这种因果力关系,技术主体当然应该对他自己制造的技术风险“负有因果关系的责任”[9]。这种因果关系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
法律责任是一种事后责任,是在已经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应受害人的请求或有权机关的强制下,由行为人被动、不得已承担的责任,是一种依靠“他律”、带有强制性、不管主观上愿意与否,都必须履行的责任。事后责任既然是在已经发生事故、导致了危害的结果之后,对行为主体责任的追究和惩处,造成的危害后果便是既成的事实,无法挽回。与法律责任不同,伦理责任(亦称责任伦理)是一种事前责任,事前责任也可以说是一种预防性责任、关爱的责任或积极、主动地承担的责任,它是一种“自律”行为,是行为主体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主动地采取积极行动来预防、阻止或避免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发生。“责任伦理学要求行动者要以后果为导向、为基础,这样行动者就不仅考虑到他想要达到的结果,而且考虑到可能发生却不希望发生的结果。”[10]110责任伦理的目标是追求善的结果,防止恶果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所以,“责任伦理被当今人们普遍视为风险社会的应对之策”[11]329。
众所周知,“应然性的核心概念是‘应该’,而‘应该’的本质是对某种事件发生原因或发展结果的带有肯定性的逻辑判断。这种确定性是针对因果关系的”[12]。按照应然性的这一规定性,由于技术主体与技术风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技术主体在发明创新技术的同时也制造出了技术风险,所以,技术主体就应该对其制造的技术风险承担伦理责任。这就是技术主体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应然性。
“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技术的力量使责任成为必需的新规则,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13]101的确,在当今的知识社会,如果一个人拥有专业知识和特殊能力,他理应承担更多以及特殊的伦理责任。追问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应然性,就是进一步从技术主体拥有特殊的认知、评估和解决技术风险的能力等方面来继续追问技术主体“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
(一)技术主体具有认知技术风险的能力
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不可感知性”,现代技术和技术产品,无论从外观形态还是基本属性,利用我们的感性根本无法发现和认识其风险性,完全超出了人的感知能力。像现代农业生产的农作物中基因突变,电脑辐射,核放射,食品中的有毒细菌,附着在日常用品上无色、无味的病毒等既无法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感知,也不能依靠我们的日常经验获得认识。“现代化自身产生的新的危险肉眼看不到并且也不能立即辨认出来;最重要的是,外行人不能发现它,更不用说应付它了。”[14]235二是“知识依赖性”,“文明的风险只在科学的思维中存在,不能直接被经验到”[15]59,现代技术是理论性、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统一体,它的风险性呈现出抽象的理性知识特征,需要通过科学理论计算和实证分析才能“感知”它的存在。由于当代技术风险的这两个固有的特性的客观存在,从而完全排除了外行人仅凭自己的感官来了解和认知技术风险的可能性,认知它的唯一途径只能利用专业知识,将通过实验、仪器测量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再与技术理论的参数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性以及不一致性的差距,从而确立技术风险的种类和大小,就像医生根据我们外行根本看不懂的血液化验数据来确定病情一样。所以,对技术风险的认知只有掌握了技术理论知识的技术主体才有可能。
由于技术主体具有认知技术风险的能力,也就获得了解释技术风险的“特权和专利”,而拥有这种能力和权力就是他对他自己制造的技术风险应该承担伦理责任的根据。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的:“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他人做出回答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道德主体。”[16]11“今天的科技工作者对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的成员,而科学家掌握着专业知识,因而他就承担着一种别人不可能具备的独特的通告与预防的责任。”[10]110这种独特的伦理责任要求技术主体有责任和义务保障社会公众对技术风险的知情同意权,维护技术利益和技术风险分配的公正性。
技术的历史表明,技术的功利性是技术发展的动力。每一种技术的成功应用,既实现了期望的利益,同时又蕴涵着危害的风险,而从技术中得利的往往是垄断技术的少数人,遭受技术风险威胁的大多数人不但没有享受到技术的好处,甚至还对技术衍生出来的风险一无所知。这种信息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显然是与昌明“每一位社会成员都享有以正义为基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甚至全社会的利益也不能践踏这一权利”[17]3的现代民主社会追求的平等、公正的普世价值相背的。为此,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责任感并拥有解释技术风险特权的技术主体首先应该“赋予外行和一般大众以准入资格和更突出的地位——开放决策过程,进而在伦理道德层面以还原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公民身份的方式,从而达到防患于未然的基本目的。”[18]其次,技术主体还应该向广大公众如实介绍技术的信息,解释和说明技术的缺陷和存在的风险。“工程师有责任做出个人牺牲,来唤醒公众对有缺陷的设计、有疑问的实验、危险的产品的注意,这使得工程师是一定意义上的道德英雄。”[19]60
手足口疾病属于病毒性疾病,致病的病毒有很多种,多见于夏季,7岁以下儿童高发。有很强的传染性,注意隔离。
(二)技术主体具有评估技术风险的能力
任何技术都有风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风险就不要技术。因为“人是一种技术存在、”[13]25“要成为人就必须拥有技术”[20]9。技术就像人体的器官一样,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有机整体。技术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存在。“工具技术、工业技术被视为人兽分离的重要标志,如果不是唯一标志的话。”[21]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发明还将是人类永无止境的事业。
虽然人类离不开技术,但并非所有的技术都具有同质性和有用性,只存在对人类的有利价值和好处。相反,有些技术不但对人类无利,甚至对人类会造成严重的灾难。即便是同一技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其价值和功效都可能会发生逆转。特别是随着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技术的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而外在性能却越来越难以把握,常常发生人们不希望的副作用。复杂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把我们带入了一个高风险的世界。所以,为了让技术造福人类,避免技术给人类造成危害,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进一步完善新技术,对现有的技术进行必要的取舍。美国学者巴萨拉在其著作《技术发展简史》中就明确指出:“慎重考虑或阻止技术发展的广泛影响对他们是有好处的。”[22]17
一个新技术是否需要进一步完善或一项现存技术是否选择淘汰,需要通过技术风险评估来做出决定。技术主体具有认知技术风险的能力为其对技术风险进行评估创造了可能性。“人为”的技术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意向性存在,从技术的构思、设计、发明、生产制造到符合市场需要的技术产品,每一个环节无不打上了技术主体的意志、知识、能力和价值观的印记。正因为如此,技术主体当然能够对技术及技术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客观的评价。技术主体一旦具有了评估技术风险的能力,他就有责任利用这种能力选择、采用恰当的评估方法对技术及其风险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对于任何一种新技术,工程师和科学家必须有若干方法来评估它给受其影响的人带来的风险。”[23]134
过去,通常采用的是成本—效益评估方法,该方法的最大特点是精确、量化、操作简单,只考虑技术的经济利益风险一个指标。只要技术创造出能够计算准确的经济效益,该技术就是好的,就是值得推广应用的。但是,成本—效益分析法作为评价技术风险的方法仅仅考察技术的利益风险,却把许多更加重要的东西忽略了,难以精确量化的技术其他风险,完全被排除在评估体系之外。像技术的生态风险、安全风险、社会公正风险等一旦发生,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多少金钱都是弥补不了的。所以,为了克服成本—效益评估方法的片面性及存在的缺陷,技术主体开发设计出综合风险评估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把技术从经济体系中剥离出来,再放入到社会总体关系中,是“对技术是否可能、可行的真理性评价,以及技术是否合意、正当的价值性评价”[24]353。采用综合风险评估方法对技术风险进行评估时,不仅考虑技术的经济风险,同时,还要考察技术风险对政治、教育、文化、福祉、心理、生态、社会安全等多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把多种因素都纳入到体系之中进行综合评估,既重视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又关注它可能造成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所以,综合风险评估方法已经成为当今评估技术风险非常有效的手段并被广泛地应用。
通过技术风险评估虽然为完善新技术和技术取舍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但是,技术风险评估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技术的善。“善”是西方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被定义为一切事物追求的终极目标。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25]2什么是“善”?在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里,“幸福就是善的代名词,因为幸福和善一样是我们独特功能的实现。我们之所以选择愉悦、财富和荣誉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以它们为手段可以获得幸福。”[26]81幸福——我们“把它理解为生活得好或做得好。”[25]9实现技术的善,就是技术达到让人快乐、幸福,生活得好。“与技术善对应的是技术恶,就是技术对人的需要、快乐和幸福的损害,导致人的痛苦和不幸等等。”[27]由于技术的发展既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性,又有其社会建构性,从而其“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28]132。因此,为了实现技术的为善目标,避免技术恶的出现,技术主体应该而且必须对技术及技术风险做出科学、正确的评估和选择,抛弃那些可能造成恶的技术,保留和进一步完善能够带来善的技术,实现技术的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和技术给社会带来风险的最小化。
(三)技术主体具有解决技术风险的能力
美国技术风险研究专家刘易斯在《技术与风险》一书中指出:“对风险的管理有两大基本战略:防止和减轻。前者是指降低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的发生概率;后者是指在事件发生时减少其不良后果。”[29]52的确,从技术、技术风险的特性及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来看,我们既然不能放弃技术,也不能消除技术风险,那么,降低技术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一旦发生了,尽量减少造成的破坏损失,应该是解决当前技术风险问题的现实途径与可行之道。
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表明,“技术的结构决定技术的功能”,技术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要素联系的复杂性和有机性以及结构组织的非线性和随机性,决定了技术功能(后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存在的客观性。由于技术风险的源头来自于技术,所以,解决技术风险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从解决引发该风险的技术本身的内部结构着手。解铃还需系铃人。通过技术创新(包括重新设计、调整、改进、或者寻找替代技术)来完善技术结构,进而达到控制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降低技术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减少技术风险造成的损失。“科学技术且只有科学技术才降低或消除了人类活动的风险,使人能轻易做一些先前须付出一定代价才能完成的事情”[30]。
风险社会的技术与主要依靠经验的古代技术和工匠技术完全不同,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依靠科学理论建立起来的具有高度的理论性、专业性、复杂性、系统性和抽象性等特点的完整的知识体系。现代技术主体与过去的工匠相比,已经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今天的工程师从日常生活中摆脱出来,即是说,他摆脱了偶然性问题,身边的物质以及工具。由于保持了距离,他按照科学的原则把个别性问题变成一般性、抽象性问题,并按照科学方法去解决它。一个工程师的意向构形建立在数学、物理学和技术科学基础上。工程师借助技术文献、量化技术以及理论结论的实际运用,得到具体实在的信息,这信息使他可以去改正科学的抽象。新构造或发明的可能性在设计的阶段展现出来。”[31]13
改造和完善如此抽象、复杂的现代技术结构,进而化解其产生的未知风险,这些问题对于没有专业技术知识的普通人来说,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难以逾越。相反,唯有建构现代技术的技术主体,他们既了解技术内部结构和原理,对技术蕴含的风险也具有认知和评估的能力,这就大大增强了他们解决技术风险的能力。所以,现代社会的技术主体是解决技术风险难题的真正的、唯一的主体和生力军。有了这种能力,他们就应该利用自己的特殊才能完善现代技术,化解其带来的各种风险,这既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面对当前复杂、恐惧而不断增长和扩散的技术风险,“工程师的责任是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这就要求他们通过技术革新来减少风险。”[23]178只要他从良心出发并付之行动,发挥自己的技术创新的能力,通过对技术本体的改造,当然能够降低技术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减少该技术风险的危害性。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杜邦公司的化学家成功研制出了氯氟烃(CFCs)制冷剂,50多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大量使用CFCs这种材料,但是后来科学研究发现,地球同温层臭氧空洞与大量使用它有直接的关系。在此情况下,1988年,杜邦公司技术专家通过技术创新,研制出了同样制冷,但对臭氧层无害的无氯替代物(HCFC—22T)和(HCFC—1426)。这种替换技术产品是无公害、无浪费技术,既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又确保“生态学上的健全”[32]42。
三、结束语
“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今天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项根本转变。两者都与科学和技术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有关,尽管它们并非完全为技术影响所决定。第一项转变可称为自然界的终结;第二项,传统的终结。”[33]191的确,在现代社会,毫无控制、盲目增强的科学技术产生的风险可怕性,不但严重地影响我们人类的生活,甚至还直接威胁到自然世界的彻底毁灭。所以,如何化解技术风险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成为当今人类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技术主体作为现代技术的建构者和技术风险的制造者,同时他又具有认知、评估和解决技术风险的能力,那么,他理所当然地应该肩负起相应的伦理责任。“你有能力的话,就必须承担与你能力相当的那种责任”[11]125。这种特殊的伦理责任促使他自觉、主动地采取积极行动,利用掌握的专业技术知识,充分发挥解决技术风险的能力,减少甚至消除技术风险的危害性。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有益、人道、正当、道德的善举,也体现了技术主体“公益服务”[34]96的伦理责任。而且,“这是一种必须履行的新责任——你应该做出这样的行为,必须使其后果与人类生活的真正永恒价值相匹配”[35]61。
[1] RISK UR.Society:Towards New Modernity[M].London: SagePublication, 1992.
[2] 亚当.风险社会及其超越[M].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马丁.工程伦理学[M].李世新,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6]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7]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 JONAS H.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9] 马丁.责任与控制——一种道德责任理论[M].杨韶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0] 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11] 肖峰.哲学视域中的技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 莫纪宏.审视应然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1(6):85-96.
[13] 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殷登祥,等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4] 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5] 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6] 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17]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18] 崔伟奇.科技伦理:在风险观念的语境中[J].江海学刊,2008(3):5-10.
[19] 艾尔尼. 工程、技术与环境[M].吴晓东,翁端,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0] 拉普.技术哲学导论[M].刘武,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21] 吴晓江.芒福德的技术观:破除机器的神话[J].世界科学,2004(1):44-46.
[22] 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M].周光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3] 哈里斯. 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M].丛杭青,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24] 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6] 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M].匡宏,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27] 肖峰.两种技术善之间的伦理选择[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7(3):1-6.
[28]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M].陈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9] 刘易斯.技术与风险[M].杨健,等译.北京:中国对外出版公司,1994.
[30] 赵万里.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6):50-55.
[31] 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李小兵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32] 星野芳郎.未来文明的原点[M].毕晓辉,等译.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5.
[33] 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34] 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5] 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郇建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QuestionCloselyontheEthicsNecessityoftheMakerofTechnicalRisk
LONG Xia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Guangdong 524048,China)
Technical risk has become the potential source in modern society which has the most harmful and the widest influence. Technical subject,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maker of technical risk, should bear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which has made the technical risk. Meanwhile, because of technical subject has the unique ability to cognition, evaluation and solve the technical risk, it of course needs to question closely on their ethics necessity.
technical risk; technical subject; ethics necessity
2017-09-13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2YZX02)。
龙翔,男,岭南师范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
B82-057
A
1006-4702(2017)05-0025-07
(责任编辑张建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