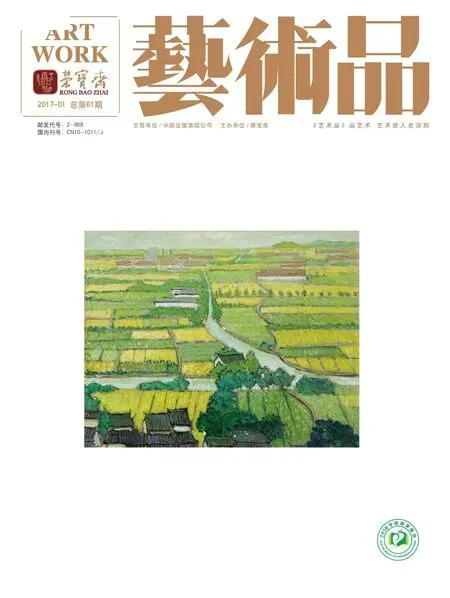螺钿妆成翡翠光
文/常亦扬
螺钿妆成翡翠光
文/常亦扬
清代诗人刘应宾有诗云“螺钿妆成翡翠光”。螺钿的光泽堪比翡翠,华美高贵,赏心悦目。其经过工匠的精心打磨、雕刻、抛光,成品往往视觉效果奇佳,光彩夺人。螺钿工艺以其光而不耀、内敛有节制的独特魅力占据我国工艺美术史上不可替代的一席。
一、螺钿的内涵及历史渊源
螺钿在中国工艺美术中的应用历史悠久,商周时即有漆器以螺钿作镶嵌花纹。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一件彩绘兽面凤鸟纹嵌螺钿漆罍(图1)就采用了螺钿工艺,雕琢精致典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在古代,螺钿亦有钿嵌、螺填、陷蚌或坎螺之称。宋方勺在《泊宅篇》中称之为“螺填”,元陶宗仪在《辍耕录》中称之为“螺钿”,明黄成在《髹饰录》中则称之为“陷蚌”“坎螺”。
“螺”与“钿”原各有不同词义。“螺”指江河湖海中的螺蚌壳,“钿”指将金银宝石等镶嵌在器物上作装饰。徐铉在《说文》新附中说,“钿,金华也”。《集韵》有记载,“钿,以宝饰物”。钮树玉《说文新附考》有言,“钿,宝钿,以宝饰器”。《髹饰录》以“钿螺”合用,《利用第一·霞锦》中说,“钿螺、老蚌、车螯、玉珧之类,有片,有沙。天机织贝,冰蚕失文”,描述了螺钿可裁切成片或研磨成粉饰于器物,其天然光泽好似锦绣,连传说中的冰蚕锦也失去了光彩。
螺钿在工艺美术中的大量应用,大致开始于晋南北朝之际,成熟、盛行于唐代,一直延续到晚清。沈从文先生在《螺钿史话》一书中认为,螺钿工艺在美术中重新占有一个位置的时间“照文献记载,则时代宜略早一些,或应在西汉武帝到成帝时,因为用杂玉石珠宝综合处理,汉代诗文中均经常提起过。宫廷用具中如屏风、床榻、帘帷、香炉、灯台和其他许多东西,出行用具如车辇、马鞍辔……无不有装备得异常奢侈华美价值极高的”“金银、珠玉、绿松石、红宝石、水晶、玛瑙,以及玳瑁,均有发现,惟蚌片实少见”。1
二、螺钿的种类及制作工艺
适用于制作螺钿器的螺蚌料有五六十种之多,加工后的螺钿可分为厚螺钿和薄螺钿两大类。两类的区分全在壳片的厚度,厚螺钿的螺片厚度一般在0.5毫米—2毫米之间,因厚螺钿壳片较厚,硬度大,又称之为“硬螺钿”;薄螺钿则一般在0.5毫米以下,因裁切精薄如纸,又谓之“软螺钿”。薄螺钿多精细秀美,厚螺钿华丽堂皇,各有不同艺术成就。
薄、厚螺钿二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材料上。
厚螺钿主要取自河湖中的蚌壳,一般多为白色,色彩单一,缺乏霞光,较薄螺钿精细密致的程度稍差一些。
而薄螺钿则主要选用珍珠贝、夜光螺、鲍鱼壳等优质海贝,属于彩螺,光泽绚丽。关于海贝,《南州异物志》记载,“交阯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色焕灿”。《相贝经》提到海贝有“状如赤电黑文,谓之紫贝;素质红黑,谓之朱贝;青地绿文,谓之绶贝;黑文黄书,谓之霞贝”。谓其光色蓝紫青黄绿红,灿烂如彩虹。而《髹饰录》中提到的“车螯”,即指鲍鱼贝壳,俗称“石决明”,《本草纲目》中言“其壳色紫……可饰器物”;“玉珧”即指小蚌壳。这些海贝经过处理后,即可用于制作精细的图案,并闪烁出绿、红、蓝光。
其次,厚螺钿与薄螺钿的制作工艺与装饰方法也不同。
厚螺钿一般是被镶嵌于器物之上的,嵌入之前,多采用研磨的加工方法。厚螺钿采用研磨的方法,目的是要磨去其几年乃至十几年间形成的成长层单位,虽能获得比较大的贝片素材,但表里面会出现成长线。另外,厚螺钿由于光的漫反射作用会呈现七彩色,而不是表现为某种特定颜色,并在表面会产生细微的研磨痕迹。厚螺钿一般还会在表面进行毛雕处理,《髹饰录》中所言“有片嵌者,界郭、理、皴皆以划文”的“划文”指的就是厚螺钿螺片上的毛雕。
而薄螺钿绝大多数使用的是粘贴于器物的方法,称为“点螺”。粘贴之前,一般采用煮泡的剥取加工方法,即把原材料放入特制溶液中浸煮,从贝的成长层单位剥出真珠层。浸煮后的贝壳会变软、变薄,在漆器未干的时候将软螺钿一点一点粘上去。这一方法是剥取与壳口平行层级的成长层单位,因此虽不能获取大块的贝片,但没有研磨的擦痕,贝片表里层能反射出蓝、红单色光。《髹饰录·填嵌》说的“又分截壳色,随彩而施缀者,光华可赏”,即指薄螺钿这一做法。经处理后的蚌壳一般多切磨成薄片、细丝,或切碎成大小不同颗粒,镶嵌于各种质地的器物上。
目前发现薄螺钿漆器的最早实例是元代的广寒宫图嵌螺钿黑漆盘残片(图2)。王世襄先生在《中国古代漆器》中说,“盘面用薄螺钿嵌出两层三间重檐歇山顶楼阁。因碎片中有‘广’字痕迹,与景物印证,遂定名为‘广寒宫图’。楼阁后植树,叶似梧桐丹桂,云气自下腾空而上。不同物象,采用‘分裁壳色,随采而施缀’的做法,相较元代以前的厚螺钿大大前进了一步,《髹饰录》杨明注谓‘壳片古者厚,而今者渐薄也’,过去曾以为‘今者’指明代,此残片证明元代已有薄螺钿漆工艺,且技法已相当成熟”。2其上面所有的图案就是将薄如蝉翼、长宽仅毫米的细小如点的螺片一一点植、拼接而成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除厚、薄两种螺钿外,还有一种“衬色螺钿”,主要应用在漆器镶嵌上。据《髹饰录·填嵌》门记载,“衬色甸嵌,即色底螺钿也。其文宜花鸟、草虫,各色莹彻,焕然如佛郎嵌。又加金银衬者,俨似嵌金银片子,琴徽用之亦好矣”(螺钿琴徽见图3)。“衬色”就是在透明的贝壳薄片下面再衬托上不同的色彩,后嵌到漆器上,即等于人工设色,所衬各种颜色是通过透明壳片的表面而显色,故呈现出色彩晶莹、温润的效果。“佛郎嵌”即“掐丝珐琅”,今人称为“景泰蓝”。一般螺钿漆器的分截壳色均系用壳片的天然光泽,而衬色螺钿的色彩是用笔施绘而成,因而色彩表现直观,没有贝壳天然光泽的变幻特色,因此,人工衬色可以随心所欲,达到天然螺片所无法达到的境地。
“衬色螺钿”的实物比较鲜见,有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晚期嵌衬色螺钿团花长方盒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黑漆嵌螺钿圆盘等。
上述各种螺钿器的钿片和漆面是平整的。倘取材厚贝壳,施加雕刻,嵌入漆器,花纹高出漆面,成为浮雕或高浮雕,那就是黄成所谓的“镌甸”了。不过镌甸只限于以螺钿花纹为主的漆器,如采用多种物料雕成嵌件,镶入漆器,那就成为“百宝嵌”了。
三、螺钿在古代工艺美术中的应用
从应用范围来说,螺钿工艺在漆器上的应用最为广泛。同时由于螺钿这一材料本身的易得性及装饰效果佳等原因,也常用于装饰家具、乐器、铜镜以及其他工艺美术品类。螺钿的应用、做法以及花纹图案,也常因材料、器物而异,艺术要求不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
(一)漆器
螺钿在工艺美术中的应用可能最早就滥觞于在漆器上的镶嵌。螺钿,与描漆、堆漆、填漆、雕填、犀皮、雕漆、款彩、戗金、百宝嵌等并列,是古代漆工艺具有代表性的修饰技法之一,其中的百宝嵌工艺亦会使用到螺钿进行装饰。
唐代是中国螺钿漆器工艺的成熟期。从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中遗存的螺钿漆盒、铜镜等文物中可见一斑。(图4)这一时期的螺钿兴盛与当时佞佛关系密切,而国内的实物材料保存不多,与会昌毁佛和五代毁佛有关。
螺钿也是宋元时漆器的重要品种之一。苏州瑞光寺塔发现的黑漆经函(图5),可看到五代、宋初时期的厚螺钿做法。
宋人笔记和其他文献中记漆事的文字甚多。如,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宋高宗幸张循王府,张俊3进奉大量珍宝,其中就包括均用织金锦绸缎承垫的“螺钿盒一十具”。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钱象祖批评卫泾“身为大臣,顾售韩侂胄螺钿髹器”,卫泾用“螺钿髹器”献媚权相韩侂胄,足以说明“螺钿髹器”的名贵。南宋临安市贾所编《百宝总珍集》名贵商品中有“螺钿匣”名。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则记载宋徽宗之时已有“螺钿砚匣”与“螺钿笔匣”。明曹昭《格古要论》后增《螺钿》条讲道,“螺甸器皿,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宋朝内府中物及旧做者,但是坚漆或有嵌铜线者甚佳。元朝时富家不限年月做,造漆坚而人物可爱”。从中都可见螺钿漆器在宋元时期之工艺成熟及价值珍贵。
明清时期,从数量、品种来说,官方和民间对螺钿漆器的需求都达到了空前水平。嵌螺钿漆器兼有厚、薄螺钿两种。厚螺钿如螺钿或百宝嵌家具,尚具宋制遗风,以粗犷朴质见胜。薄螺钿如《髹饰录·填嵌》中杨明所注“点、抹、钩、条,总五十有五等,无所不足也”,即言由于薄螺钿之精细,模凿切割出的基本形态非常之多,图案全部用窄螺钿条镶嵌拼贴而成,不用壳片,也无划纹。黄成还认为,因薄螺钿片和螺钿沙屑的天然霞光只有在黑漆地子上才能得到很好的衬托,所以二者“共不宜朱质”。
这一时期在螺钿漆器制作领域涌现出江千里、吴伯祥、吴越桢等一批名家巨匠,而以江千里声誉最高。江千里生活在晚明时期,以制作金银嵌薄螺钿漆器著名,尺寸精巧,题材多为《西厢记》故事。嘉庆时重修的《扬州府志》记载“杯盘处处江千里,卷轴家家查二瞻”就可见“千里式”漆器在当时的盛行。(图6—图9)
同样会使用螺钿进行装饰的“百宝嵌”品种,在此时也有周翥、方信川、王国琛、夏漆工、卢映之、卢葵生等名工留史。(图10—图12)
明代黄成《髹饰录》中涉及螺钿漆器装饰工艺的记载原文如下:
1. 《髹饰录·填嵌》4
黄文:“螺钿,一名蜔嵌,一名陷蚌,一名坎螺,即螺填也,百般文图,点、抹、钩、条,总以精细密致如画为妙。又分截壳色,随彩而施缀者,光华可赏。又有片嵌者,界郭、理、皴皆以划文。又近有加沙者,沙有细粗。”
杨注:“壳片古者厚而今者渐薄也。点、抹、钩、条,总五十有五等,无所不足也。壳色有青、黄、赤、白也。沙者,壳屑,分粗、中、细,或为树下苔藓,或为石面皴文,或为山头霞气,或为汀上细沙。头屑极粗者,以为冰裂纹文,或石皴亦用。凡沙与极薄片,宜磨显揩光,其色熠熠。共不宜朱质矣。”
黄文:“衬色蜔嵌,即色底螺钿也,其文宜花鸟、草虫,各色莹彻焕然如佛郎嵌(珐琅嵌)。又加金银衬者,俨似金银片子,琴徽用之,亦好矣。”
杨注:“此制多片嵌划理也。”(衬色蜔嵌的螺片正面,多刻画皴纹脉理。)
2. 《髹饰录·雕镂》5
黄文:“圆滑精细、沉重紧密为妙。”
杨注:“圆滑精细,乃刻法也;沉重紧密,乃嵌法也。”指雕刻要精细,打磨要圆滑,嵌件要沉重,嵌入漆地要紧密。
3. 《髹饰录·斒斓》6
《髹饰录》记载,螺钿工艺还与其他漆器装饰工艺结合。如“描金加蜔”“描金加钿错彩漆”“描金错洒金加钿”“描漆错钿”“金理钩描漆加钿”“金双钩螺钿”“填漆加钿”“填漆加钿金银片”“螺钿加金银片”“百宝嵌”等。错综复杂,极为绚丽,构成一派五彩斑斓的装饰风格。
(二)家具
螺钿不仅作为漆器日用器皿的装饰,而且可以用来镶嵌于体量更大的家具。
明清以前的家具实物留存不多,但各种史籍及图像资料中对螺钿家具的记载与描述是汗牛充栋,可资参考。
宋代苏汉臣的绘画作品《秋庭戏婴图》中,就有唐草纹样黑漆地螺钿圆形椅子的形象,精致写实,并且极有可能是前朝还未曾出现的薄螺钿。(图13)
其他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
西湖老人在《繁胜录》中记载在京城临安市场上“关扑螺钿交椅、螺钿投鼓、螺钿鼓架、螺钿翫物、时样漆器”,说明至少在南宋时用以螺钿装饰的各类器物用具种类繁多,并且在市场上已普遍存在。
南宋尹廷高有诗曰“蟠螭金凿五色毯,钿螺椅子象牙床”,不仅说明了螺钿家具的真实存在,而且表明了其贵重与奢侈的地位。
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临安人杨靖者,将满秩。造螺钿火柜三合,穷极精巧。买土人陈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赍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献老蔡(蔡京),一与贯(童贯),以营再任。子但以一进御,而货其二于相国寺,得钱数百千”,从中可见当时螺钿工艺的穷极精巧。
南宋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记载“王黼作相,穷极华侈,累奇石为山,高十余丈,便作二十余处,种种不同,如螺钿阁子,即梁柱、门窗、什器,皆螺钿也。琴光漆花、罗木雕花、碾玉之类,悉如此”,是说宋徽宗时奸相王黼家中所用梁柱、门窗及各种日常生活器具等皆用螺钿镶嵌工艺制造,以示其穷奢极欲。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钿屏十事》也记载,“王橚,字茂悦,号会溪。初知郴州,就除福建市舶。为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盛事十项,各系之以赞以献之,贾大喜,每宴客必设于堂焉”。王橚以上作政缋十事的螺钿屏风献媚贾似道,足以说明“螺钿器物”的名贵。
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马天骥为平江发运使,独献螺钿柳箱百支,理宗为之大喜”。这些记载都说明“螺钿器物”在南宋日益繁盛。
螺钿家具在当时的奢华及受追捧程度,甚至曾引起皇帝的不满。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为摒弃华糜之风,就曾多次下令焚毁螺钿器物。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镇江守钱伯言尝献宣和所留器用,其闲有螺钿椅卓。上(高宗)恶其靡,亟命于通衢毁之”。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命“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百姓观者,莫不悦服”。绍兴初年(1131),“徐康国为浙漕,进台州螺钿椅桌,陛下(高宗)即命焚之。至今四方吹诵圣德”。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也记载,“高宗践阼之初,躬行俭德,风动四方。又尝诏有司毁弃螺填倚桌等物,谓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宜乎去华崇实,还淳返朴,开中兴而济斯民也”。虽如此,胡铨《经筵玉音问答》还记载了宋高宗曾赐宋孝宗“通朱螺钿屏风”,皇帝“还淳返朴”之意未能抵挡住私人偏爱美好之心。
明清时期,即有大量螺钿家具实物存世。(图14—图17)
明曹昭《格古要论》讲到“洪武初,抄没苏人沈万三家条凳、椅、卓螺钿剔红最妙”。《天水冰山录》记权臣严嵩被抄家时,家具文物清单中也有许多螺钿家具,仅仅床榻大器即有螺钿雕漆彩漆大八步床、螺钿大理石床、堆漆螺钿描金床、嵌螺钿有架亭床,等等,其他可知。乾隆时,在两淮盐政李质颖进贡清廷的单子上,就有彩漆螺钿龙鸿福祥云宝座、彩漆螺钿龙福祥云屏风等十余件漆器螺钿家具。
至清末,如其他工艺一样,螺钿家具随着时风日益衰落,进入了低谷。
(三)乐器
《髹饰录·填嵌》中记载了“衬色甸嵌,即色底螺钿也……琴徽用之亦好矣”。螺钿镶嵌在乐器上的应用范围除了作为琴徽,满足实用功能之外,还大量用于各种乐器的装饰图案上。
现今遗存实物多见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唐代嵌螺钿乐器,包括琵琶(图18—图20)、阮咸(图21)等。这几件乐器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在镶嵌螺钿的同时,还会辅以琥珀、玳瑁等材质,颜色鲜艳而有变化,古朴大气,华贵大方,为唐代典型特征,以后即少见。
(四)铜镜
至少从周代起,螺钿就开始成为镶嵌艺术使用的材料。而蚌类和青铜器的结合,较早的实物可见于商周时期的斧钺,稍后的可见西汉时期的嵌贝鹿形青铜镇(图22)等。
直至唐代盛世,中国的螺钿工艺进入了成熟期,现今遗存的漆背螺钿铜镜可见二者结合之精轮美妙,堪称瑰宝。“唐代多用嵌螺钿作铜镜的装饰。镜背用漆灰铺地,上面再填嵌壳片花纹,故可以说是一种铜胎嵌螺钿的漆器”7,当时的螺钿铜镜主要使用的是厚螺钿,将其雕刻成各种图案,按照原先的设计要求黏贴于素镜背面,然后研磨,最后再在螺钿上毛雕花纹。漆地多为黑色,螺钿为白色,黑白分明,精巧细致,颇为华美。(图23—图28)
(五)其他工艺品
除了上述几大类外,螺钿也被用于其他工艺器物,如鼻烟壶(图29、图30)、扇子、梳篦(图31)等。在材料方面,与石器、象牙、金银器、瓷器等也有结合使用(图32)。
四、小结
清代诗人刘应宾有诗云“螺钿妆成翡翠光”,认为螺钿的光泽堪比翡翠,华美高贵,赏心悦目。螺钿因材料源自自然,且各贝类品种不同,所折射出来的光泽也各异。贝片本身天生丽质,反射出来绚烂的光芒,经过工匠的精心打磨、雕刻、抛光,成品往往视觉效果奇佳,光彩夺人。
王世襄先生喜用“千文万华”一词来形容我国历史久远绵长的漆工艺,笔者认为同样可以借用来形容螺钿工艺,以其光而不耀、内敛有节制的独特魅力占据我国工艺美术史上不可替代的一席。
注释:
1沈从文著,李之檀编《螺钿史话》,9页,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
2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器》,67页,三联书店,2013年。
3张循王为南宋武将张俊的王号。
4明·黄成著,明·杨明注,长北校勘、译注、解说《髹饰录图说》,11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
5同4,152页。
6同4,176页。
7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器》,10页,三联书店,2013年。
(本文作者任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责编/王可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