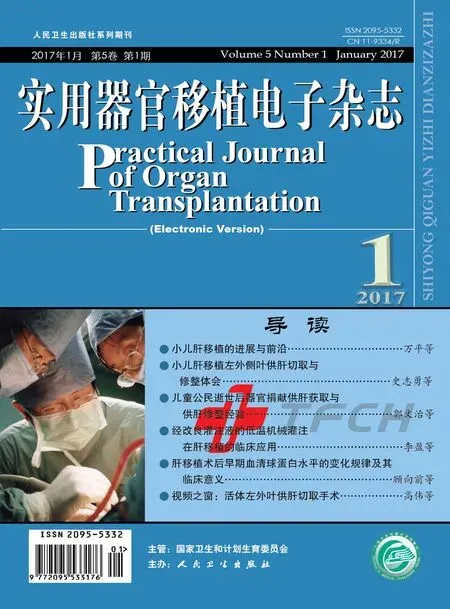儿童肝移植术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诊治进展
王凯,高伟(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天津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192)
近年来,肥胖人群数量增加,脂肪肝发病率逐年增高[1]。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已经成为儿童慢性肝病的主要原因[2-4]。美国国家健康营养普查数据显示,约17%的儿童存在超重问题,70%~80%的超重儿童患有NAFLD。而在肝移植术后患儿中,NAFLD的发生率为3%~10%[5]。也有研究发现,肝移植术后3年NAFLD的发生率高达27.1%[6],甚至有研究报道显示,肝移植术后约30天即出现移植肝脂肪变[7]。一项Meta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9例儿童肝移植患儿术后出现NAFLD,其中4例患儿在移植术前伴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这 4例受者在术前均存在超重问题及代谢综合征的其他表现[8]。而在另一项研究中,12例被诊断为移植术后NAFLD的儿童患者术前均不存在超重情况,其术前均为进展性家族性肝内胆汁郁积症1型(progressive intrahepatic familial cholestasis type 1,PFIC 1)[9]。由此可见,NAFLD已成为儿童肝移植术后主要的长期并发症之一。
在儿童肝移植受者中,移植术后NAFLD大多为个案报道。因此,我们对此类疾病的病因学、组织特征、诊断及治疗进行综述,以期在随访管理中加强对儿童肝移植术后NAFLD的认识。
1 NAFLD的形成机制
NAFLD是指在排除酒精摄入、病毒感染、自身免疫性肝病或药物性肝损害等情况下,经肝活组织检查,肝细胞脂肪浸润程度>5%,从肝内细胞脂肪堆积(脂肪肝)到不同程度的炎性坏死与纤维化NASH均包括在内[10]。
NAFLD的形成过程较复杂,许多肥胖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脂联素、瘦素、抵抗素等均可诱导产生胰岛素抵抗以及肝内轻度炎症反应[11-12]。此外,瘦素、TNF-a和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还可以通过激活肝星状细胞促进肝纤维化[13-15]。肝移植术后血浆中的促脂肪化因子,如瘦素的水平会升高[16]。同样,移植术后抗脂肪化细胞因子会减少,如脂联素[17]。这些变化会导致NAFLD复发或新发NAFLD,而且会引起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可对产生肝血糖的抑制功能受损,引起高糖血症、高胰岛素血症,这些变化可刺激TNF-α与IL-6的表达,导致脂肪合成增加及肝脂肪变性[18]。NAFLD的另一个特征是提高移植术后的氧化应激水平,如硫代巴比妥酸反应物,在移植术后的6个月内表达水平仍较高[19]。免疫抑制剂也被认为是导致NAFLD的一个重要因素。
2 NAFLD的相关危险因素
2.1 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在移植术后NAFLD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包括马铃薯糖蛋白样磷脂酶主要包含蛋白3(patatin-like phospholipase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3,PNPLA3)多态性I148M和IL-28B。
脂肪营养蛋白(adiponutrin,ADPN)是一种三酰甘油脂肪酶,可调节肝细胞内的甘油三酯水解。PNPLA3基因可编码ADPN,而且某些已知的基因多态性与NAFLD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PNPLA3基因148位点的多态性由异亮氨酸(rs738409-C)替换为蛋氨酸(rs738409-M),这种变化降低了甘油三酯水解酶活性[20-21]。以膜结合形式出现的ADPN编码蛋白可能参与脂肪细胞中能量的消耗与储存[22-23]。PNPLA3的基因位点rs738409-G也是NAFLD发展中发生脂肪肝、纤维化、肝硬化及肝细胞癌的独立危险因素[24]。肝移植术后5年脂肪肝的产生,与PNPLA3的高危位点有关[25],这提示受者的基因型决定了肝细胞内甘油三酯的蓄积而不是供肝ADPN的作用。研究发现,PNPLA3多态性与肝移植术后肥胖相关,尤其是与等位基因G密切相关[26-27]。对于IL-28B的作用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IL28-B多基因型通过促进代谢综合征的一些潜在危险因素而在移植术后脂肪肝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28]。但 Watt等[26]的研究并未发现IL28B基因型与移植术后糖尿病或肥胖的相关性。
2.2 术前原发病:最主要的问题是原发病复发。有研究报道显示,NASH患者在中位随访时间12.7个月后出现移植物持续脂肪浸润的患者高达17例(占32%),其中8例(占15%)患者经组织学证实为NASH复发[29]。甚至有研究报道显示,NASH/隐源性肝硬化患者肝移植术后5年脂肪肝的复发率高达100%[30]。
其他常见的与移植术后NAFLD相关的术前诊断还包括酒精性肝硬化〔(优势比(OR)=8.031,P=0.003〕[6],在术前诊断为酒精性肝硬化的患者中,术后有64.3%的患者发生NAFLD,非酒精性肝硬化的患者只占34.8%[6]。如果患者术后出现肥胖或术前存在移植物脂肪肝,那么术后NAFLD的发生率则高达100.0%,而在不伴有这两个因素的情况下,NAFLD的发生率仅为37.5%。隐源性肝硬化也是NAFLD的危险因素之一,一项对隐源性肝硬化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发现,肝移植术后约一半的患者出现脂肪肝,25%的患者出现NASH[31]。
日本学者通过对PFIC1患者的观察发现,活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LDLT)术后脂肪肝与ATP酶8B成员1(ATPase class I type 8B member 1,ATP8B1)基因功能异常有关[32]。这项研究共纳入11例患者,其中8例患者术后发生大泡性脂肪变,中位时间为60天(21~191天),7例患者由严重脂肪肝进展为脂肪性肝炎,中位时间为161天(116~932天)。所有出现脂肪肝的患者均存在严重的ATP8B1基因变异。也有研究认为,术前肥胖、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等均为肝移植术后发生NAFLD的高危因素[30]。
2.3 术后并发症:有研究认为肝移植术后某些并发症是移植术后NAFLD的高危因素。Zahmatkeshan等[7]报道了3例移植术后的NASH病例均与血管并发症相关,肝移植术后门静脉血栓可能是由于这些病例发生了肝脏早期脂肪浸润。
术后肥胖也是NAFLD的一个高危因素(OR=3.873,P= 0.001)[6]。而 18% ~ 67% 儿童患者肝移植术后出现超重或肥胖问题[33],这更容易诱发术后NAFLD。
2.4 免疫抑制剂:目前认为免疫抑制剂,尤其是激素的使用可导致移植术后代谢综合征,对肝移植术后发生NAFLD具有促进作用[30]。在儿童肝移植术后5~10年,血脂异常、肥胖、高血压、高血糖等情况高于普通人群。高甘油三酯血症的发生率为10%~56%,高胆固醇血症为7%~57%[34]。这些变化与免疫抑制剂的长期使用,尤其是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 CNI)类药物的使用有关。在1篇个案报道中,儿童受者的他克莫司药物浓度最高达30 ng/ml以上,且异常增高的状态持续2周,而后出现肝功能异常,病理显示存在肝细胞气球样变、小泡性与大泡性脂肪变性(15%~20%)[35]。他克莫司主要由细胞色素P-450代谢,在存在药物毒性的前提下,线粒体功能显著受损,导致小泡性脂肪变性。Becker等[36]的研究显示,激素剂量与肝移植术后血脂代谢异常有关,但CNI的种类对其没有影响。Dureja等[37]研究表明,NAFLD的复发率达39%(34/88),其与移植术前及术后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移植术后甘油三酯水平及术后6个月泼尼松的剂量有关。在包含53例原发病为NASH受者及95例原发病为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受者的研究中,接受激素治疗的NASH受者术后发生肝纤维化的危险明显高于未接受激素治疗的NASH与HCV受者(P<0.001)[29]。
对此,也有一些有争议的研究。Perito等[38]发现在撤除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儿中,与对照组相比,其肝移植术后代谢综合征的发生率并无差异。撤除免疫抑制治疗5年后,在12例受者中92%的受者至少患有1项代谢综合征,33%超重或肥胖、50%血脂代谢异常、33%存在血糖不耐受、42%出现收缩期高血压,说明肝移植术后代谢综合征不都是免疫抑制剂的作用。对于激素的使用,有研究认为小剂量激素的使用与小儿肝移植术后脂肪肝的发生无关,移植肝的纤维化与供肝的年龄有关[39]。这组研究共纳入了54例儿童肝移植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1年,其中23例患儿(43%)被证实存在小泡性脂肪肝(5%~80%)。
3 NAFLD的诊断
影像学检查是目前评估NAFLD的重要方法,但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40]。目前,组织学检查仍是诊断的金标准,尚无非侵入性手段可以作为可靠的诊断方法[41]。Patrick等[42]报道了1例肝移植术后类似肿瘤的移植物内局灶性脂肪聚集的罕见病例。该患者供肝为30%的大泡性脂肪肝,于肝移植术后2年进行超声及MR检查发现肝脏占位,伴有转氨酶及碱性磷酸酶明显升高,经肝穿活检病理证实为脂肪聚集。
NAFLD的病理诊断一般包括3个特征性表现:脂肪变性、气球样变和小叶炎性改变[43]。其中,气球样变是NAFLD组织学改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成人患者相比,儿童NAFLD患者的组织学具有不同的特征性表现[44]。两者脂肪变性的分布不同。在成人患者中,脂肪变性首先开始于小静脉周围区域(腺泡区3),而儿童患者则首先始于门脉周围区域(腺泡区1)或呈散在分布。而且儿童患者中炎性浸润可出现在小叶间或门脉中[9]。在儿童患者中,纤维化常出现在腺泡区1。
目前,有两个主要的评分系统能够评价NAFLD与NASH的组织学活性,均可应用于儿童和成人患者中。Brunt评分是一种半定量的方法,建立在小泡性脂肪变、气球样变、小叶与门脉炎症反应基础上,分为3级:1级为轻度、2级为中度、3级为重度[45]。另一个评分系统是NASH-CRN系统[46],利用量化评分为疾病分级,也就是所谓的NAFLD评分 (NAS)。NAS来自于各评价指标的总得分(0~8分),包括脂肪变性(0~3分)、小叶间炎症反应(0~3分)、气球样变(0~2分),NAS评分为1~2分表示不存在NASH,5分以上方可确定,3~4分为临界表现。
肝移植术后NAFLD复发与新发NAFLD患者,在组织学上没有明显差别,在临床表现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有研究对91例肝移植术后NAFLD的成人患者进行了详细分析,11例为NAFLD复发,80例为新发NAFLD[43]。在性别、年龄、高胆固醇血症、 肥胖、高血压等方面,两组间无差别。NAFLD复发组中糖尿病的发生率高于新发NAFLD组(100.0%比37.5%,P<0.01)。在肝移植术后1年,67%的新发NAFLD患者证实存在NAFLD,而在NAFLD复发组,这一比例为100%,NAFLD复发组5年后的严重纤维化(3期、4期)和脂肪性肝炎的比例明显高于新发NAFLD组(严重纤维化:71.4%比12.5%,P<0.01;脂肪性肝炎:71.4%比17.2%,P<0.01)。经治疗,有18例(占22.5%)新发NAFLD患者脂肪肝消失,而NAFLD复发组患者则均未出现此种好转。因此,该研究者认为NAFLD复发出现的更早一些,程度更为严重且不易逆转[43]。
4 NAFLD的治疗
目前尚缺少肝移植术后NAFLD治疗的针对性方案,主要是针对术前与术后的危险因素进行预防、减轻肥胖、避免高脂血症,药物治疗上维生素E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47]。
4.1 饮食控制、减肥及身体锻炼:应避免体重降低过快,此举可加重脂肪性肝炎和肝性脑病[48]。
4.2 免疫抑制剂的选择:对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主要是防止其引起的高血脂与代谢综合征等不良反应。减少或避免使用激素,减少CNI类药物的用量及浓度要求,避免使用雷帕霉素。至于他克莫司与环孢霉素的选择及酶酚酸酯类药物的使用,并不会促进移植术后NASH患者肝纤维化的进展[29]。
4.3 药物治疗:主要是减少脂类摄入[49]、刺激脂类代谢[50]。在既往文献中,维生素E对NAFLD的治疗作用得到肯定,成人患者常用的维生素E治疗剂量为每日800 U、比格列酮每日15 mg,并辅以必须脂肪酸每日2 000 mg(多为鱼油胶囊),其疗效已得到肯定[51]。有学者比较了噻唑烷二酮与生活方式改变对移植术后NAFLD患者的影响,其结果认为通过这两种方法均可减轻脂肪肝的程度,但考虑到危险性及收益性,建议采取良好的生活方式[52]。这项研究中共有22例患者移植术后9个月内发生大泡性脂肪变性,观察期内药物组和非药物组分别减重4.1 kg和3.5 kg,药物组大泡性脂肪变的比例由63%下降到31% (P=0.005),非药物组由47%下降到33% (P=0.17),在非药物组体重的变化与脂肪肝比例具有相关性,而药物组则不存在相关性[52]。另外,在动物实验中已证实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s)可降低肝移植术后新发NAFLD的发生风险[53],其主要作用机制是减少胰岛素抵抗、减少2型糖尿病的形成,还可以下调脂肪因子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