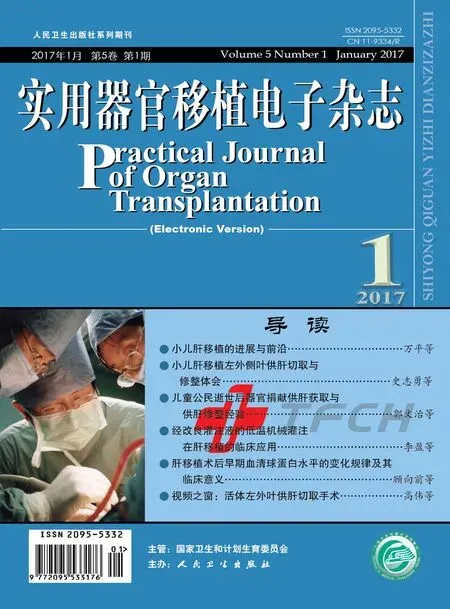肝移植术后感染并发症的研究现状及进展
谢秀华,孔心涓,饶伟(.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山东 青岛 66003;.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山东 青岛 66003)
自从1963年美国Starzl教授开展世界首例原位肝移植手术以来,临床开展肝移植手术已超过50年, 挽救了无数终末期肝病患者的生命。然而,肝移植术后的多种并发症也已成为影响其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其中术后感染尤为明显。因此,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免疫抑制剂预防肝移植术后感染非常重要。由于影响肝移植术后感染并发症的因素复杂,国内外医学中心对肝移植术后感染并发症病原体的构成、耐药分析及易感因素均有不少研究报道。本文将对以上3个方面的临床研究进行综述,从而为临床上更有效地防治肝移植术后感染并发症提供理论支持。
1 病原体构成
肝移植术后存活率的改善,得益于手术技术的进步、围术期管理水平的提高及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减少等[1]。早年国外研究表明,肝移植术后感染病死率高达50%[2]。近年来,随着高级别广谱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及围术期管理水平的提高,肝移植术后感染病死率有所下降。
Moon等[3]的研究表明,移植后感染作为术后早期并发症之一,机会性致病菌较为多见,这与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密不可分。当前有文献报道显示,肝移植术后感染并发症的发生率为30%~70%[4],其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真菌,以细菌感染较为多见[5]。Kim等[6]对144例样本的研究显示,术后1个月内菌血症的发生率可达21%~33%。Mukhtar等[7]对246例样本的研究表明,感染多发生在术后3个月内,其中革兰阴性菌感染率为74%,而革兰阳性菌感染率为24%,革兰阴性菌中75%为多重耐药菌。法国最大的肝移植中心进行了1项为期10年的包括710例肝移植患者的研究,Bert等[8]认为近几年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肠杆菌菌株呈增多趋势,这是造成肝移植术后感染的重要菌种。吴金道等[9]对1 380株病原体进行分析的结果同样显示,革兰阴性菌占优势(占69.57%),而革兰阳性菌和真菌分别占20.07%和10.36%。而Kawecki等[10]及刘建明等[11]的研究均表明,革兰阳性菌的感染率高于革兰阴性菌的感染率。
近几年革兰阴性菌的感染率呈上升趋势,甚至已逐步超越革兰阳性菌,成为感染的主要病原体,这种变化可能与人们对肠道细菌移位认识的不断加深有关[12]。但是不同研究中心的术后感染率及病原体分布呈现差异性,这可能与国家/地区间医疗水平、病原菌流行病学等差异有关。尽管各中心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但是感染并发症的发生的确不容忽视,仍是肝移植医师值得重视的领域。
2 耐药分析
当前大部分肝移植中心术后仍常规应用他克莫司(或环孢素A)+吗替麦考酚酯+泼尼松三联抗排斥治疗,而机会性致病菌感染已成为实体器官移植发病率和病死率的重要原因之一[13],因此,如何调节肝移植术后的抗排斥治疗力度与病原体感染防治之间的矛盾成为肝移植医师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目前临床上细菌耐药现象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
根据2012年国际耐药菌定义,肝移植术后感染多呈现多重耐药(multi-drug resistance,MDR)现象, 而泛耐药现象和极端耐药现象的报道比较少见[14]。MDR的出现可能与移植前后长期大量使用广谱抗菌药物、免疫抑制剂等因素有关,也与国内近年来病原体的高耐药趋势有关。除了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杆菌、耐甲氧西林的金葡萄球菌、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等耐药菌外,Fabian等[1]的研究结果表明,念珠菌属和曲霉菌属也是真菌感染中的“常客”,这无疑给抗感染治疗增加了难度。革兰阴性菌对美罗培南、阿米卡星、亚胺培南较为敏感,耐药率均低于30%,而对头孢曲松、氨曲南等的耐药率均较高;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较为敏感,耐药率均低于20%,而对氨苄西林、诺氟沙星等耐药率均较高[8]。这说明MDR已经成为全球范围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需严格掌握抗菌药物的使用,尽可能减少MDR的发生。
当前,各个器官移植中心均已认识到肝移植术后感染并发症的重要性,根据本中心的感染情况进行相关研究,然而,其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这充分说明感染并发症的研究仍存在进步空间,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研究。同时,也督促我们提高医疗技术和改进用药认知,从而降低耐药率的发生,提高肝移植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3 易感因素
肝移植患者术后感染并发症的发生可能与以下易感因素相关:患者术前营养状况、手术时长、 术中出血量及输血量、留置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时间及拔管时间[15]、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有无糖尿病、再次手术及再次移植等[16]。Chen等[17]对中国台湾地区68例肝移植患者的临床研究发现,胆道狭窄也是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另外,手术刺激、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均可激发受体内潜伏的病原菌,同时供体组织也极有可能携带相关潜伏病原菌进入受体[18],当出现诱因时上述病原菌均可爆发,进而造成术后感染并发症的发生。
肝移植术后感染并发症的诊断通常较为困难,如发热、白细胞计数增高等症状或检查可能会被掩盖或缺乏[19],因此,鉴别术后感染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预防措施更加值得重视。Juntermanns等[20]对201例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评分高与感染的高发生率并不相关,但在并发脓毒症的患者中,病死率更高,因此在MELD评分高的患者中,预防感染非常必要。而文强等[21]的研究表明,术前MELD评分是监测肝移植术后感染发生及判断预后的良好指标。Shi等[22]对475例肝移植患者进行的研究发现,Ⅱ~Ⅳ期肝性脑病、移植前经验性应用抗菌药物、术后泌尿道感染、腹腔感染等4项因素为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显示,移植前广谱抗菌药物的应用可使肝移植受体术后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风险显著增加[22-24]。Santoro-Lopes等[25]认为,术前即存在耐药菌定植的患者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而Vera等[4]研究显示,留置ICU时间的延长能够增加术后感染的发病率。研究表明,缩短ICU留置时间、住院时间和早期拔除导管是降低肝移植术后菌血症发生率的重要因素[6]。杨富等[26]通过Meta分析也印证了上述研究结果,留置ICU时间的延长及气管插管时间(≥72小时) 的延长使术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风险增加。Kim等[27]进行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对大部分肝移植术后患者来说,早期进行肠内营养可以降低细菌感染和胆管并发症的发生率。
因此,积极控制肝移植围术期相关影响因素有助于降低肝移植术后感染并发症的发生率,从而为提高移植物存活率及患者的生存质量打下良好的基础。
4 总 结
迄今为止,肝移植手术已在全世界得到推广,在广大终末期肝病患者寿命延长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Watt等[28]对多中心的肝移植研究发现,肝移植患者的1、5及10年存活率已分别达到85%、68%及50%。我国肝移植历经多年的发展,目前术后移植肝生存率和受者生存率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郑树森等[29]的研究显示,截止到2014年,国内较大移植中心肝移植围术期病死率已降至5%以下,受者的术后1、5及10年生存率已分别达到90%、80%及70%。然而,肝移植术后感染并发症仍是肝移植手术无法避免且亟待重视的并发症之一。
肝移植患者由于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等因素,感染的相关临床表现可能不典型,而非感染因素也可引起发热等感染类似的临床表现,使得肝移植患者感染并发症的早期诊治较为困难。而且,移植后患者感染的病原体范围广泛,病情发展迅速,因此,积极进行病原菌的分离培养、尽早发现病原体、了解药敏情况、对指导临床选择有效的抗菌药物十分必要。术后应及时拔除各种引流管,严格掌握侵入性操作的适应证,尽可能降低术后继发细菌感染的发生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肝移植患者术后的生存率及生活质量[30]。肝移植术后发生感染并发症的原因很多,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医务人员应严格规范抗菌药物的管理和使用,必要时可进行主动筛查监测是否存在耐药菌定植。
综上所述,肝移植患者术后感染并发症的发生率、病原体分布情况等因移植中心而异,但总体流行趋势及分布情况相似,而其危险因素则包含范围甚广,明确高关联度的危险因素将有助于临床医师在实际的临床工作中加以避免或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