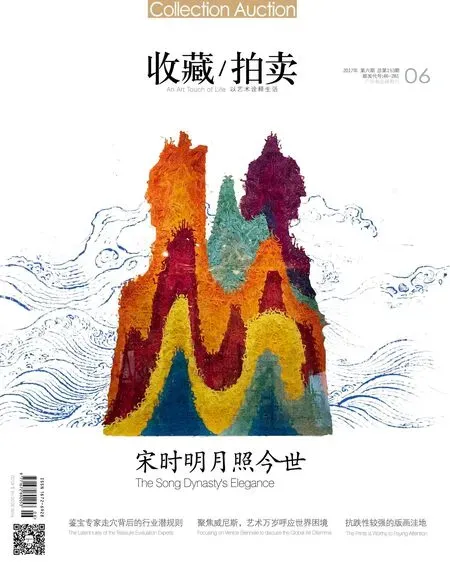林泉之心,北宋文士的山水情结
文/图:一光
林泉之心,北宋文士的山水情结
文/图:一光

北宋 郭熙《早春图》

北宋 李成《晴峦萧寺图》
北宋文人大抵是风流的,但这风流中总不免流露出一种孤冷、忧郁的哀伤。他们时常在热衷政治与规避仕途中辗转,在进取之心与退隐之意间逡巡,精神的困锁使得他们力图在人事羁縻与尘世纷扰间寻求解脱、暂避。如此,丘山野逸是北宋文士朝堂生活的一种补充和替换,山水乃是他们精神世界中的一方避居之地。
平生之游
清代孙琮在评点北宋士人风尚时如是说:“宋世士大夫类皆耽于玩山水,以为清高,亦一时风气。”之于北宋士人们而言,人生境遇无论如何颠沛、曲折,皆无法改变他们对于山水的眷恋。
欧阳修曾在洛阳度过了他官僚生涯的最初四年,其间他遍游洛阳城中的山水园庭、塔庙佳处。此时的欧阳修意气奋发,林泉胜景莫不回荡着他的朝气。此后,欧阳修仕途不顺,谪居滁州,然则贬谪生活却成了他饱览山水的绝佳契机,他造访了滁州名胜琅琊山,并记录道:“琅琊幽谷,山川绮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临听忘归。”欧阳修在《浮槎山水记》中将这种赏玩山水的乐趣称之为“山林者之乐”。每当走过长松丰草,每当静闻石泉潺湲,欧阳修总能感受他已经抛却下了世俗的欲心,超越了所谓的“天下之乐”。
北宋士人对于山水的赏玩几乎达到了魂牵梦萦的地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回忆,他三十岁左右时曾做过一场山水梦。梦中游历的是一处小山,山上花团锦簇,山下流水潺潺,水边有乔木树荫。这处山水美景让沈括在梦中喜乐不已,甚至想移居此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沈括的山水梦便是他日常山水休闲生活的折射,以致在这场梦后,他曾三番五次地梦到此处山水景致,“习之如平生之游”。
北宋山水游乐之盛,因应于理学背景下文士的自然审美旨趣。北宋的理学家深入自然、流连万物,研味物理之趣,从而形成了一种“观生意”的精神追求。“观生意”是一种由我及物,又由物及我的观照之法,其概有两层意义。其一为“爱物”,理学深化了中国哲学素有之泛爱生命的思想,旨在超越人与物的分隔,以一种亲近自然之平等态度,体察天地万物的内在生命;其二是“观我”,“爱物”之目的并非仅仅停留在对于自然万物的审视,而是将万物视为个体生命之对象化的存在物来看待,并在这样一种物我无间、物我合一的精神情境中达到自我生命与宇宙生命的融合境界。
饱游饫看
渊源于理学“观生意”的精神追求,北宋山水画学方发展出一套完备的自然山水观照之法,郭熙在《林泉高致》一书称其为“饱游饫看”。《林泉高致》一书是郭熙的艺术笔记,由其子郭思整理,于北宋后期问世。书中郭熙列举了山水画家观照自然山水之时的弊病,所谓“所养之不扩充”“所览之不淳熟”“所经之不众多”“所取之不精粹”四者是也。针对这四种审美观照的弊病,郭熙提出画家应以“饱游饫看”的方式体察自然山水。
所谓“饱游饫看”由两部分组成。一者是审美心胸的调整。郭熙认为观照自然山水之基础在于拥有一颗虚静的心灵——“林泉之心”,拥有“林泉之心”者方能真正喜爱、亲近自然山水,将自然山水视为“行、望、游、居”的心灵家园,方能真正发现自然山水的审美价值。此外,画家在观照自然山水之时理应“注精以一”——精神高度集中,此乃山水画创作之必要前提,亦将影响创作之全部过程。当内心虚静、精神专一,画家则获得了一种“胸中宽快,意思悦适”的审美心胸。
二者是审美观照的多变视角。面对自然山水现实形态的多样性,郭熙认为可以从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来进行观照。郭熙提出之“春夏看”“秋冬看”“朝看”“暮看”的观照方式旨在把握自然山水在时间流变中的不同情状,而“步步移”“面面观”的观照方式则力图把握自然山水在空间变换中的不同形态。自然山水现实形态的丰富性在为画家提供着丰富视觉资源的同时,也向画家提出着如何将这种丰富的视觉资源凝练为具有统一性的画面布局的难题。对此,郭熙认为应当以“远而望之”“临上瞰之”的方式将自然山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统摄。郭熙以“三远”对于这种整体统摄的观照之法加以总结:
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三远”之法既立足在对于自然山水时空形态多样性的观察之上,又超脱出多样细节的琐碎繁杂,以天地的整体性囊括万物的丰富性,实现着由自然现实向艺术意境的深化,将观者的视觉经验引向无尽的远方,品味一种“自失”于山水之中的审美体验,以郭熙之言来说,此是山水的“景外意”“意外妙”。
“景外意”“意外妙”是北宋山水的审美价值判断,其意味着山水画作不止于自然山水的图像呈现,更是在山水之象中寄托一种象外之意,那是北宋文士山水情结的指归。
院中名画
北宋的郭若虚认为当世的山水画远出古人之右,并有鼎立后世格法之功中,他在《图画见闻志·论三家山水》这样写道:
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神入妙,才出高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前古虽有传世可见者,如王维、李思训、荆浩之伦,岂能方驾?
北宋的山水画既有细节之真实描摹,又有宏观之全景概括,极尽全力地表达出山水的内在风神,传达着整个生活、人生的环境、理想、情趣与氛围。这种精微又广阔的笔墨图景展现着“行、望、游、居”的生活—人生—自然境界,它勾起着观者对于彼时彼地林泉游览的联想,让观者再次沉浸在山水行吟之中。这是中国山水画最为紧要的审美功用,魏晋画家宗炳称其为“卧游”。
翰林学士院既是北宋文士政治空间,亦是他们山水精神的“卧游”之所。宋王朝沿袭唐制设有翰林学士院,学士院的正厅称为“玉堂”,据南宋蔡启《蔡宽夫诗话》记载:
学士院旧与宣徽院相邻,今门下后省乃其故地。玉堂两壁,有巨然画山、董羽画水。宋宣献公为学士时,燕穆之复为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间……元丰末,既修两后省,遂移院于今枢密院之后,两壁既毁,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诏郭熙所作《春江晓景》。
宋仁宗天圣年间,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郎的燕肃为宋宣献绘制的一幅六扇山水屏风被放置在玉堂正中,与董羽之水与巨然之山交相辉映。王安石曾为玉堂中的这扇山水屏风题诗一首:
六福生绡四五峰,暮云楼阁有中无。
去年今日长千里,遥望钟山与此同。
王安石的这首题画诗作于熙宁元年(1068年),此前一年他曾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短暂任职。如今,当王安石在玉堂中与燕肃之画相对时,不禁怀念过往,唏嘘叹息。八年之后,王安石罢相回宁,过起了隐居生活,也许他在遥望南京钟山之时,也会吟诵到“遥想钟山与画同”。燕肃的山水之于王安石而言,既是那山水村居的感怀,也是那朝廷庙堂的留念。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在江宁,苏轼奉诏回朝,任职翰林学士知制诰,位极人臣。在朝期间,苏轼常在玉堂之中当值,政务缠身,而玉堂内郭熙的《春江晓景》(苏轼称之为《秋山平远》)则成为他精神的安适之境,他写有《郭熙画<秋山平远>》一首,苏门弟子黄庭坚依韵作有《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一首。苏轼与黄庭坚的唱和之作道出了北宋文士的山水情结,即使他们身居庙堂之内,但是依旧追慕着闲云野鹤一般的林泉生活。
闲居与当政既是北宋文士生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又彼此矛盾,相互掣肘,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消除两者的对立,给予身心一处暂时的避居之所,成为北宋文士所面对人生难题。正是山水画为解决北宋文士的内心困顿提供了一种绝佳的解决方案。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写道山水画作有着“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功能。矗立在玉堂之中的《春江晓景》,在严肃庄重的政治空间中,为文士的山水之思、隐逸之想开辟了一处精神之境。面对着《春江晓景》,玉堂之中的翰林学士可以摆脱世俗政务,享受短暂的山水之梦。一如郭熙所述:“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
北宋文士的山水情结内涵着一条基本的理路。他们首先为代表自然生命与环境特征的特殊对象的形色之美所吸引;其次即对自然环境作以宏观之欣赏,体味自然环境与现实社会所迥异的独特审美风格,一种幽静清纯之美;再次则强调这种具有幽静清纯之美的自然环境之于心灵的安置功能,所谓“适意”;最后便以自然为人生之道,突出天地自然与心灵在理性智慧层面的联系,所谓“理趣”。在这样一条理路之中,山水由自在之物转化成为我之物,客体之自然转化成主体之心灵。
(编辑/雷焕昂)

北宋 范宽《溪山行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