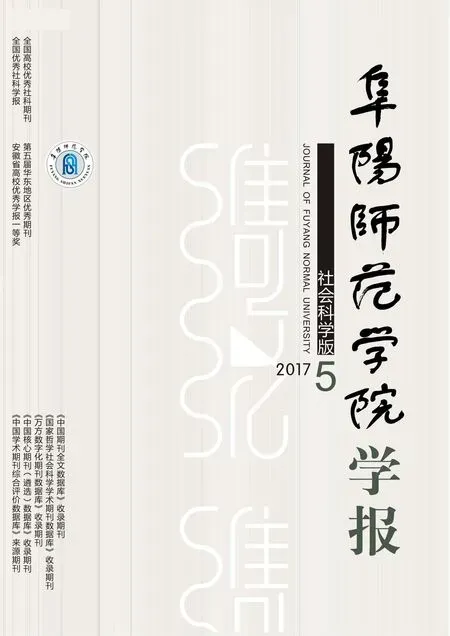皖江城市带与苏南城市群农村金融发展比较研究
张汗青,杨 呈
皖江城市带与苏南城市群农村金融发展比较研究
张汗青1,杨 呈2
(1.铜陵学院 经济学院;2.农业发展银行 铜陵分行,安徽 铜陵 244000)
通过对皖江城市带与苏南城市群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的对比,反映出皖江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较低、创新不足以及有效供给缺失等问题。基于两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提出在深耕传统业务前提下,通过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打造有为政府等措施,为欠发达农村地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农村金融;金融创新;普惠制;监管
引言
皖江城市带与苏南城市群(简称皖江、苏南地区,下同)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可视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案例,两区都处于本省境内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带,相比省内其他地区,农村开放程度最高、农业资本积累最早且居民都拥有艰苦奋斗的开拓精神,这就决定了两地区在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和特征上具有一些共性,而皖、苏两省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的较大差距,又使得发展的具体阶段存在差异。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都是发展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学界在经过数年研究后形成较为丰富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观点:一是林毅夫等人认为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农村金融能有效地动员农村闲置资源[1],一些学者也通过计量手段推导出农村金融与经济的正向关系,如冉光和杜兴端等学者分别运用ADF单位根检验[2]和格兰杰检验[3],验证了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然而,胡宗义等另一些学者通过对金融行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库兹涅茨效应的分析研究,发现了金融行业规模的扩大,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且农民增收的边际效应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4]。这既与金融行业“嫌贫爱富”的逐利性有关,也与政府关于农村发展政策的变化有关。温涛认为在过去,农村金融行业服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成为向工业部门和城市地区输送农村资源的管道[5],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并非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一种政府主导行为,因而发展路径也不可能沿着行业内在逻辑展开,这种由政府主导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不仅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可能因为资源配置的扭曲产生抑制效应[6],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应要求我们在对农村金融发展的阶段特点进行梳理时,要深刻剖析农村金融的微观基础,通过对发展背景和业务特点共性和特性的比较,取长补短,为欠发达农村地区如何促进经济与金融的联动发展探明道路。
一、皖江、苏南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共性分析
(一)农村商业金融资源整合起步早,发展迅速
农村商业金融的主要形式即为农村商业银行,是继政策性金融(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民间金融之后,涉农帮扶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市场化运行水平最高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村商业银行的出现,既是商业金融经营战略上的巨大突破,也是对传统制度经济学的成功践行。农信社的股权改革,从法律上明确了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扫除障碍。自2011年农信社股权改革之后,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由农信社改制形成)发展迅速,年新增约120家,截止2016末,全国总数突破1000家(见图1-1),其中皖、鄂、苏、鲁四省已全面完成农信社改制,农村商业银行总数占全国总数的1/4以上,其中皖江城市带辖内农商行52家,苏南城市群有16家,分别占安徽省与江苏省总数的2/3和1/4。我们将两个地区的经济数据列表如下(截止2016年末):
图1-1 我国农村商业银行数量变动示意图

数据来源:《2015-2020年中国农村商业银行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表1-1 皖江、苏南地区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现状

银行数量GDP总量(单位:亿元)占本省GDP比重人口总数(单位:万人)占本省总人口比重 皖江城市带(9市2区)5215 328.470.36%2 952.448.01% 苏南城市群(5市)1641 73759.53%3 324.145.04%
资料来源:安徽省、江苏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由作者计算所得
由图1-1可知,皖江、苏南地区作为本省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其人口、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与农村商业银行数量的分布,基本呈现出集聚关系;农信社的股权改革较早,也有利于吸收更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入股,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有助于提高农村闲散资金的使用效率,推动了农村小微产业的发展;而股权改革后行政管理制度的变革,则有效打破了地区间投融资活动的限制:省内所有农商行统一管理,加速了资源整合,实现了竞争与合作并存;又能以业务为载体,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可见,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源整合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二)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打造“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1)的概念,根据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已作出明确的界定,这种以“小微互助”为基本形态的普惠制,在微观层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活方式,在宏观上,普惠程度的高低也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同向变动关系,且与地区收入水平、社会平等程度以及城市化率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普惠金融对促进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完善尤为重要,自2013年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后,率先完成股权改革的农商银行成为了推动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目前,这种金融理念随着农商银行的服务在农村地区的推广,逐渐形成以下三大功能:1.便利交易。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技术,提供更加便捷的电子支付工具,提高了农户的交易频率,解决了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如皖江地区推行的“社区e银行”,一方面增加了农商行的开户数,提高了银行账户的使用率;另一方面使得银行可以吸收低成本的社会资金,同时为用户提供了充分的商户信息及市场咨询,实现“精准营销”。2.改善生活。服务“三农”,脱贫致富仍是农村发展最基本和重要的目标,普惠金融的推广,以现代技术为贫困地区人口克服交通、通信不畅以及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障碍,使其也拥有平等参与市场活动、获得融资来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从而改进生产和改善生活的权利。皖江及苏南地区的农商银行,利用大数据技术,精确掌握农户的生产情况和财务信息并根据农业生产不同阶段所对应的资金需求的变化,主动联系、上门服务,实现“精准扶贫”,保证了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为农户购买大额耐用消费品提供贷款(如家电、汽车等),扩大了农村的消费市场,促进农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3.创业支持。受经济周期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工返乡潮频现,如何帮助返乡农民和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式农民”就业、创业,也成为了近年来农村金融业务的新增长点,很多农商银行都相应推出了多种创业贷款计划,帮助农民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技能,因地制宜发展小微事业,再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创业,实现共同富裕,从官网的公开业务中,为实现以上三大功能,皖江、苏南两地农商行基本上都制定了具体的计划(见表1-2)。
表1-2 皖江、苏南地区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功能一览表

交易便利改善生活创业支持 皖江城市带社区e银行、基础服务村村通、金农便民宝(全体)5311同舟计划(马鞍山农商)、平安行(绩溪农商)、安居贷(肥西农商)等“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助农贷(南陵农商)、菁英.创业贷(九华农商)等 苏南城市群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全体)Freestar生意贷、有田贷(常熟农商)、家庭农场贷款(紫金农商)等创富贷系列(无锡农商)、工会创业贷(宜兴农商)等
资料来源:根据各农商行官网资料整理得出
注:苏南地区16家农商银行业务范围已全部覆盖以上三大功能
(三)民间金融运营风险加大了政府监管难度
民间金融,一般指非正规金融,是游离于正规金融监管之外,不受正规金融制度保护的金融形式。民间金融因资金获取便利,少抵押或者不抵押在农村地区盛行,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金融机构因覆盖范围不足、资质审核严格造成的资金缺口,但也由于利息率过高、违约风险大甚至发展成高利贷,给农村地区带来了较大的不稳定因素。皖江、苏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使两地民间金融呈现不同表现形式:前者主要以家庭互助、联保为主,资金分散规模较小;而后者由于民间资本发达,更多地表现为组织程度较高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和商会。无论何种形式,民间金融在发展中的先天不足使其面临一系列内外问题:经营不规范、内控薄弱、抗风险能力差;未得到有效监管,同时也未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自身健康发展,而且问题的累积所带来的风险,亦会扰乱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秩序,破坏农村地区现代化进程,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实施有力措施,履行相关政府职能,规范民间金融市场。
二、皖江、苏南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分析
皖江、苏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虽然因地理位置较近以及农村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具有一定共性,但是伴随发展水平的差异带来的特性则更加明显和值得重视,只有充分认识和借鉴发达地区在农村金融发展实践中的优胜之处,才能更好地取长补短,缩小地区的行业发展差异。
(一)相比皖江地区,苏南农村商业金融服务理念先进,配套更加完善
现代金融制度的起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休·T·帕特里克(Hugh.T.Patrick)在1966年发表的《不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Patrick认为,金融供给,包含了“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两种形态[7],“供给领先”是指金融制度的发展通常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深化,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是对金融服务有需求的市场参与者的被动反应;而“需求追随”则指金融机构的供给先于经济主体的需求而产生的,依据这种理论所进行的实践,很可能人为造成某种“熊彼特式”的创新,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同样,在农村金融领域,“需求追随”更符合发达农村地区的特征,而“供给领先”偏向于欠发达地区,表现在皖江、苏南地区,后者的农村金融业务拓展和细化程度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强劲和外贸的繁荣而更加深入,而皖江地区的业务结构仍然为金融管理部门僵化的规制所束缚,既不能依托地方特色对现有业务进行调整,又使得统一安排的业务体系在经济水平的制约下难以同步推行,各成员行强调步调一致既给农民生活带来不便,也增加了从业人员的工作难度,使得整个皖江地区农村商业银行的整合尚未显现出规模效应。另外,皖江地区业务开展的滞后性也较为明显,如很多农村地区提供旨在便利交易的“金农便民宝”(一种类似POS机的终端)仍然处于营销阶段;而苏南农村地区常规业务,如存取、查询、挂失、代缴代偿早已实现了电子银行系统全覆盖。皖江地区的农村商业银行因传统业务的破局之需,亦发展部分企业业务,但是服务形式简单,起步较晚,并且因为资金、管理和经验不足,尚不能与实力雄厚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竞争,开发优质客户较为困难;而反观苏南地区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早已从涉农为主转型为涉农、涉工、涉商三线统筹发展,这种转型正是由于苏南地区工商企业集聚、外贸发达,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所致。在业务上也表现为个人业务、公司业务和国际业务发展并重的局面。业务体系成熟度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也愈发明显。
(二)相比皖江地区,苏南农村金融创新程度高,金融市场更具活力
根据Patrick对于金融发展不同阶段特征的描述,可以认为,关于机制体制的创新是否能有效作用于实践,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因素,行业内创新的发生应该出现在该行业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并非中低级阶段,创新的成功不仅包括了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的变革,还在于这种变革是否带来预想的社会经济效应。相比皖江地区,苏南农村金融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其创新能力也明显优于前者,从公开资料显示,两地业务结构有明显差异:苏南地区16家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完全转型为具有全系列金融业务的现代金融机构,其中12家除拥有支农专项业务外,还为资产雄厚的个人和机构定制各类财富管理和增值方案;而皖江地区的主要任务仍是为符合资质的农户和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并无一家银行拥有独立的国际业务和资管业务,“扶贫脱贫”的功能定位使得商业金融带有某种公共产品的性质,虽然资源整合较早,网点多,规模大,但仍然呈现出“大而不强”的态势,业务体系的不完善虽然与主管部门的行政安排有关,但仍然反应出本地区经济规模偏小和开放度不足的缺陷,更是地区间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程度差异的反映。可以说,产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创新的活力就越大。
三、皖江城市带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具体分析了皖江、苏南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共性和差异后,文末就发展中的农村地区如何借鉴和吸收发达地区发展农村金融的经验提出建议。
(一)立足传统金融业务,寻找利润增长新机遇
至2016年,虽然我国中东部地区已全部完成对农信社、小贷互助协会和村镇银行的股权改制工作,但农村金融系统的资源整合在一些地区仍然显示出了政策意义大于经济效应的形势,以皖江地区为例,金融机构数量的上升并没有带来净资产规模、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的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落后社会经济条件造成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据银监会估计,城乡两极可支配金融资源分布很不均匀,农村地区仅为20%左右,优质客户群和业务量都较小,部分农村群体又由于无法提供符合资质的抵押品而丧失获得正规贷款的渠道,造成农村地区资金需求缺口较大。为了弥补缺口,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农村商业银行的主体地位即是未来发展的关键,首要措施就是在立足传统信贷业务的前提下,细分客户群,提高金融产品的种类和品质。皖江地区的农村商业银行可以借鉴苏南同行,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和对公业务,从服务乡村逐渐扩大到城市地区,从在农业生产中寻找业务增长点到服务城镇居民衣食住行,进而扩展到为城镇工商企业乃至地区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这种发达地区农商行的业务发展路径也是欠发达地区正在探索或经历的,事实证明这一路径不仅有助于扎根农村的金融机构扩大客户基础,提高资本充足率和信贷扩张的能力,还能促进农金系统经营机制的创新,使其进一步向市场化和国际化迈进。其次,农村商业银行在完善自身业务体系的同时,不仅要注重服务范围的广度,还要拓展其深度,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实践服务“三农”的基本目标,还应积极加强与地方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参与农村“民生工程”的建设,为农村居民在扶贫安居、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提供金融支持,真正将银行经济效益与地区发展相联系。这种更深层次的涉农服务,能够有效地延长信贷业务链,提高资金利用率和受众面,促进农村人口素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使更多农村居民有能力有精力开展生产,增强创富能力,反过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二)发展多种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农村生态金融闭环
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包括金融设施、服务和经营理念的相对落后,主要是农村地区的信息缺失造成经营成本高,风险大,虽然农金系统因政策调控等因素,有意扩大了在农村地区的经营范围,但同时众多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仍在逐步缩小业务量甚至完全退出农村地区,这就要求我们探索新的投融资渠道,来弥补农村资金缺口。比较值得皖江地区借鉴的做法,是政府允许和鼓励民营资本在金融政策与法律规范的框架内,依托互联网及现代物流技术参与农村金融活动,以更加灵活的资金投放方式,实现农村产销一体,提高资金流动性和借贷弹性。在此思维下,苏浙发达农村地区以及鲁、川等农业大省已较早地同阿里、京东等互联网企业农村金融事业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快速推进以“阿里模式”和“京东模式”为代表的“电商+供应链金融”:一方面为农户生产提供小额低息、无抵押贷款,通过自有电商资源解决农产品销售渠道问题;另一方面利用自有电子支付工具和自有物流,解决农户消费品“最后一公里”的运输问题,将农村地区打造成一个以“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为核心的农村金融生活闭环。这种全新的金融服务体验,加速了产品和资金在城乡间的流动,提高资金利用的边际收益,有利于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营销”双重目标,同时也具有普惠金融的性质。
(三)明确政府职能,加强监管,做“有为政府”
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村金融时应效仿苏南,明确政府定位,打造“有为政府”:首先,政府是“服务者”而非直接参与者。在发展农村金融前,政府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吸引外来投资,扩大经济容量为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各个行业提供物质基础,此外政府还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营和创新环境,以市场选择代替行政干涉。其次,政府是“监督者”。政府应履行义务,为农村金融的发展走上合规健康道路而努力,包括加快建立适应民间金融发展的准入机制和操作规范,加强金融风险的教育和宣传,在农村地区实施金融知识扫盲等。最后,政府是“联络人”,政府要重视与本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联系,实现信息共享,为农村发展加强合作;要牵线搭桥,鼓励本地农村金融机构走出去,参与跨区跨省竞争,提高经营能力和影响力,要发挥纽带作用,促进农村地区“四位一体”(民间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金融格局的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多层次、全方面的服务。
注释:
(1)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1]林毅夫.金融改革与农村金融发展[J].上海改革,2003(10):27-31.
[2]冉光和,温涛,李敬.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效应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07):27-31.
[3]杜兴端,杨少垒.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09):120-122.
[4]胡宗义,刘亦文.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县域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10(05):25-31.
[5]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09):30-43.
[6]温涛,冉光和,王煜宇,金融产业持续发展运行机制研究[J].金融温注与实践,2004(01):18-21.
[7]Hugh.T.Patrick,Finas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mder developed coimtries,1966.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between Wanjiang Urban Belt and South of Jiangsu Urban Agglomeration
ZHANG Han-qing,YANG Cheng
(Tongling college,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of China Tongling branch Tongling 244000)
By compar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between Wanjiang urban belt and the South of Jiangsu urban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low level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the lack of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 supply in the Wanjiang region. Based on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areas,this paper proposed the measures ,rooted in the deep traditional business, about how to optimize the rural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reate a promising government ,which are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rural areas .
rural finance; financial innovatio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supervision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5.23
F832.2
A
1004-4310(2017)05-0120-06
2017-08-10
安徽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机制研究:目标选择与政策效应分析”(SK2017A0530)。
张汗青(1988- ),女,安徽铜陵人,铜陵学院经济学院助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杨呈(1988- ),男,安徽马鞍山人,供职于农业发展银行铜陵分行,金融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