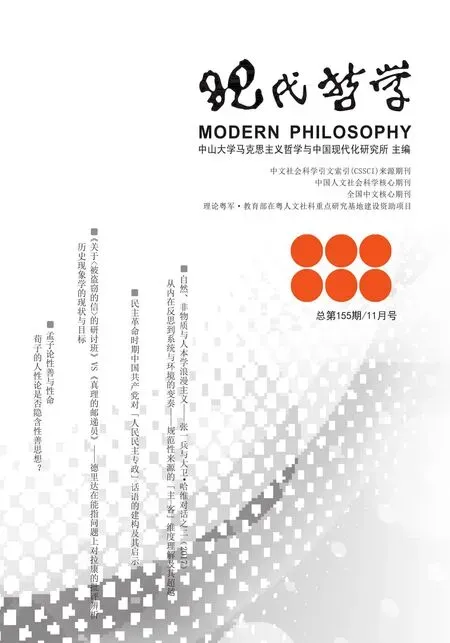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刘荣茂
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刘荣茂
探讨《荀子·礼论》是研究《荀子》专篇思想的重要尝试。《礼论》一篇可划分为三小节,分别讨论“礼养”“礼文”“丧礼”三个论题。礼养与性朴是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两个观点。荀子认为,礼的确立是为了养护人的欲望,欲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礼的意义和目的是“养”,养欲、养情、养德。篇中“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说法表明,人性原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质朴的。这与《性恶》的观点非常不同。《性恶》与《礼论》在人性的说法、性伪关系、礼与情欲关系上都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性朴的思想在《性恶》外的《荀子》其他重要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
荀子;《礼论》;礼养; 性朴论
对于荀子的礼论,前人有大量的研究,但是,鲜有人专门研究《礼论》这篇重要的文章。本文在对《礼论》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挖掘其中包含的一些被人忽视或未被人足够注意的荀子思想。显然,性朴(不是性恶)的思想被人忽视,而礼养的思想则未被人足够地注意。本文希望对此二者的讨论可以拓宽荀子研究的视野,以期更多的研究者深入研究《荀子》的其他篇章。
一
《礼论》为《荀子》第19篇,前为《正论》,后为《乐论》。有论者认为,它是荀子在约公元前279-255年居稷下学宫时所作*廖名春编:《荀子二十讲》编者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页。。今本《礼论》近五千言,论及礼的起源、目的、特性等方面,对丧礼的讨论尤其详细。它还对人性有重要的论说:“性者,本始材朴。”解读荀子这篇文章,既要立足其本身,也要联系《荀子》其他篇章。本文第三节将阐明,此种联想能让我们得出惊人的结论。
对全文进行小节划分是讨论《礼论》具体内容的前提。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把《礼论》全篇分为5段,而梁启雄的《荀子简释》则把它分为22段,两者仅是文意、语脉的分割,都未能很好地揭橥本篇的基本论题。综观全文,本篇讨论了三个主要论题,所以本文把全篇分为三节,详见下表:
第一节讨论礼的起源和根本目的,用“礼养”二字来概括是合适的。第二节涉及礼仪的制定、施行、特性等内容,但最重要的是凸显“礼义之文”的特性,所以用“礼文”来概括。第三节讨论丧礼和祭礼,对前者说得很详细,对后者则说得稍简略。荀子尤为注重君王的丧礼。表面上看,《礼论》前后文之间的联系有时严密、有时松散,全篇似乎不是荀子一气呵成的作品。根据以上的划分,三个主题环环相扣,文章结构非常严谨:第一节指出礼的根本目的是“礼养”;实现“礼养”的必要条件是礼的器物和威仪,故第二节讨论“礼文”;集中展现礼的基本精神、威仪、器物(礼之文与义)的具体礼仪的是儒家重视的丧礼,所以第三节顺理成章地讨论丧礼与祭礼。可以看出,全篇经过了荀子或本书编定者刘向的合理编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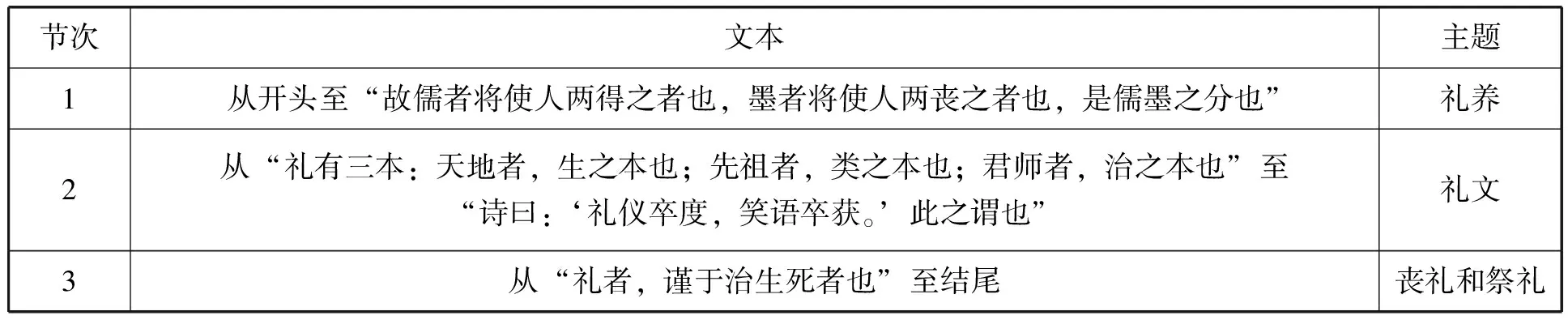
节次文本主题1从开头至“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礼养2从“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至“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礼文3从“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至结尾丧礼和祭礼
二
荀子在《礼论》开篇论礼之起源,得出“礼者,养也”的结论。这可以说是整篇中最核心的命题,也是荀子对礼义的功能和本质做出的最具概括性的判断。以往很多论者太强调荀子之礼的等级性。礼养论可以冲淡这种论调。荀子在说了“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之后,用排比句式详细阐述了礼之养义:“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本文所引《荀子》,均依照[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等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为了简便,下文所引《荀子》原文,仅注篇名。这无疑在说礼的目的是“养”,即养人之欲——满足人的各种欲望。在论述对普通人而言之礼养后,荀子接着描述了对天子而言的礼养:“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睪芷,所以养鼻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礼论》)这些冗长繁复的句式体现出荀子强烈的论辩和说服意图,以及其对所得之学的自信。荀子就天子之起居、坐行、视听等礼仪行为说明礼的养之功能。荀子以天子礼仪为例说明礼的效能,不仅因为天子至尊的地位,而且因为“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道》),君王对民众具有示范作用。
荀子认为,礼义的设立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礼论》开篇之言众所周知:“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很多引用者过分注意其中的“制礼义以分之”,而忽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的意思是:礼义虽然对人类的情欲有所限制,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它们。为使人类不至于因有限的生活资源而相互争斗,先王用礼义给人的不同情欲设定一个合理的范围。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含有今天常说的“可持续发展”之意。很多论者为这段话中的“争”“乱”等字眼所吸引,误以为荀子反对情欲。事实上,荀子对欲持的是肯定的态度。礼之养显然首先是指养欲。
在《礼论》中,“礼养”的含义更为宽广:除上面引文中的“养威”“养安”等,文中还有“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等说法。因此,礼之养具有很宽的内容,不仅包括满足物质欲望(养身),还包括德性的培养(养情、养心、养德)。礼之养义表明礼不只是通常认为的制度规范,起约束之用,更重要的是具有涵养、教化的积极作用。因此,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论》)礼是君子与凡民、文明与野蛮区分的标识。
实践礼仪可以使行礼者的情感、行为处于优雅的秩序和状态,或者说行礼者的教养是通过仪式实践提升的。所以,在“礼养”之后,荀子进而讨论礼的器物与威仪,即“礼文”。荀子指出,礼之制定是“称情而立文”(《礼论》),礼器、威仪等礼节仪式的设置是基于人情,礼文则是养欲、养情、养德的实现方式。礼器、威仪都喻示着特定的价值和意义,调教和完善行礼者的情感和品质。人行礼正是在与器物的关联中使身心仪式化,彰显人文价值与意义,使自然生命向德性生命转化。
儒家历来重视丧礼,荀子也不例外。在《礼论》中,丧礼更是“礼养”与“礼文”思想的突出表达。丧礼在儒家礼仪中就仪式之细密、应用之范围而言可能无出其右。儒家丧礼仪式的细密不仅在于时间悠长(三年之丧),也因其涵盖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丧礼的器具、仪式的设计既要求生者,又针对死者。恰恰因为死者已逝,丧礼礼仪象征的非功利的人文价值才鲜明体现出来。荀子一方面批评墨家薄殓节丧的功利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赞同道家的忘情废礼。亲人间的哀敬思慕之情并非有害,不需克除,不能减削,而是需要尊重、呵护和培养,这是人道的根源。人类间这种最珍贵情感的调节和培养是通过富有寓意的器物、严谨的威仪的陶冶而实现的。所以,《礼论》第三节说:“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这些耗费大量物资和精力、毫无实用的繁琐礼仪正是靠对善良情操的培养以及德行的促成而获得了实践的动力。
已有论者从积极意义来理解荀子礼养论中的欲,认为荀子所说的养人之欲是必要、可能的*陈中浙:《论荀子的“养人之欲”观》,《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第64页。。但是,如果仍然坚持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把《礼论》与《性恶》中的欲混为一谈,就难以客观地看待《礼论》中的欲。与《礼论》正面地评价欲相反,《性恶》负面地评价之。《性恶》明确地说,礼义“矫饰人之情性”“扰化人之情性”。这显然与《礼论》中的礼养论相悖。
三
《礼论》第三节提出一个特别的说法:“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这段话讨论的是人性,但并非来自《性恶》。荀子在提出“性者,本始材朴也”的命题之前,探讨了礼对情感的损益和调节作用。荀子说:“文饰、粗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礼论》)荀子不认为忧伤、悲戚的感情就是不当的,快乐、恬愉才是必须的,而是每种情感都要有合适的度。为了恬愉忧戚等情感平和恰当,需要礼的裁剪,故荀子说:“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继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足以为万世则。”(《礼论》)面对各种相反的情感,并不是肯定一方而否定其反面,而是“两情”需要“时举而代御”。前面说过,礼养包括了礼养情。礼对情感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取消情感。未经礼仪损益的情感有过不及之分,但是荀子并未称其为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前引这段话对人性的看法与《性恶》篇观点的差异。如果把《礼论》与《性恶》两相对照,便会发现两篇的诸多观点,尤其在人性论上截然不同。具体而言,有以下四点:
首先,性朴说与性恶说的不同。上文表明,《礼论》的人性论显然是一种性朴论。它与《性恶》篇的思想不可同日而语。性朴表明人性没有明确的价值趋向,“无伪则性不能自美”,为了达到美善,需要伪对它进行加工,而不是否定之,就如同把璞变成玉,仅需要对璞打磨修饰,而非把它全部抛弃。但是,如果人性为恶的话,就必须完全否定它,才有可能走向美善。《性恶》提到,恶之情性要达到中正、平和,需要“矫饰”“扰化”*《性恶》言:“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这是反其道而行。而性朴至于美善,却可顺势而为。对于人性,《性恶》还明确提出“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这显然与《礼论》的性朴说背道而驰。
其次,性伪合与性伪分的不同。对于性和伪的关系,《礼论》的说法是“性伪合”,“合”可以理解为结合或配合,说明人性与人为的相互依赖关系。与之截然相反,《性恶》却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是“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性恶》两次明确提到“性伪之分”*《性恶》言:“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很多地方也暗示性伪之分的观点,但没有与“性伪合”相同或相似的说法。“性伪之分”表明,性和伪是紧张对立的,尽管前者也是后者的前提。而在《礼论》中,性和伪却可以和洽地结为一体。可惜的是,论者们总是受到《性恶》中性伪分的鲜明观点的影响,忽略了《礼论》中完全不同的说法,没有意识到《荀子》不同篇章的分歧。显然,“性伪之分”与“性伪合”无论如何是不相容的。
第三,养欲与逆欲的不同。上文对《礼论》的概述已经指出,作为礼的本质的“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养欲。《荀子》其他篇也多含有礼养的思想,而极少《性恶》中“矫饰”“扰化”的说法。例如,《强国》说:“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富国》提到:“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礼者,养也”可以说是荀子一贯坚持的主张。与之不同,在《性恶》中,礼义是为了对治、矫治欲求而制定的。礼不是对欲的调养和顺遂,而是违逆和克制。对待欲求、情性的态度,《性恶》与《礼论》不仅没有共识,而且完全针锋相对。难以想象两篇文章会出自同一位作者。
第四,文饰与矫饰的不同。这一点与前三点紧密相关。荀子在讨论礼之文(仪节)时,提出礼具有饰的作用。然而,《礼论》中的“饰”是“文饰”,而非《性恶》的“矫饰”。“矫饰”“扰化”表明礼义与人性是势不两立的,《礼论》中的“饰”却是性情的完善和升华。“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礼论》)礼节威仪是对人性情的展示、调节和完善。究其实,礼的调节和修饰作用蕴含着性情的质朴无华,“文饰”与质朴之性情互为前提。荀子说:“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礼论》)理想的礼仪实践是文饰与人情的协调匹配,这与孔子赞赏“文质彬彬”的态度是一致的。《礼论》中礼文与性情是互为前提、相互实现、相互配合的关系,这在《性恶》中是看不到的。《性恶》中的礼义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礼论》所言“性者,本始材朴”以前没有被深入探讨。它不同于以前反复提到的性恶论。质朴的人性,可能会转变为恶,也可能向善发展,但本身不善亦不恶,而是中性的。朴之性虽然不是善的,但要竟称其为“恶”,这是名实不符。朴之性隐含着向善发展的潜质,在“礼养”的作用下能“性伪合”,达到美善,但如果像某些研究者以“善”名之*黄开国:《董仲舒的人性论是性朴论吗?》,《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35页。,那也言过其实。朴之性并非“文理隆盛”,原初之性与礼乐化成之情性有巨大的差别。所以,性朴论与性善论、性恶论都不相同。《论衡·本性》提到:“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性朴论尽管暗示人性最终可能成为美善的或邪恶的,但并不赞成人性原本就含有现成的善性或恶性。在先秦的人性论中,告子的性无善无恶的主张与性朴论似乎最相近,两者都认可原初的人性并没有明显善或恶的特征。但是,性朴论认为,对于一个社群的稳定,质朴的人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后天人为地调节和完善;而性无善无恶论没有提到如何去改变原初的人性,也没有对人性的整体规划。
性朴的思想并非仅见于本篇中。《荀子》的其他许多篇章都蕴含着“本始材朴”的观点。例如,《劝学》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蓬非生而直,沙也非生而黑,它们都是后天人为的结果。对此,王念孙言:“此言善恶无常,唯人所习。”*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页。这是说,荀子这句话表明人并没有现成固定的善恶之性,它可以被改变*王充有相同的说法:“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参见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页。。性朴论强调人的可塑性和未完成状态。而《劝学》的宗旨恰恰是通过学使人由不完善的状态达到完善。《劝学》的“学”可以说是《礼论》的“伪”。《荣辱》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儒效》有类似的看法:“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不同地区的人安适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不是由于人种不同,而是后天习成的;人在德性、职业上的不同也不是早已命定好的。不同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或学习程度导致人的贤愚、贵贱之差别,这恰好反衬出天性之质朴,善恶未定。
《性恶》篇对人性持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荀子》其他篇章的观点与之不同。《性恶》开篇认为人生而好利、疾恶、好声色,会导致争夺、残贼、淫乱。但是,在《劝学》《荣辱》《礼论》等其他篇中,我们看不到对人性如此负面地否定。如果人出现邪恶的行为或倾向,那是后天人为所致。《劝学》说:“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兰槐(即白芷)之根因为环境和人为的原因而发臭,但它原初的质地并非如此。《荀子》其他篇都没有提出或蕴含人生而为恶的思想,只有《性恶》篇有这样明确的主张。
《性恶》与其他篇章的显著差异表明,此篇并非荀子亲自撰写,其中的观点并非来自荀子本人。荀子应当是性朴论者,而不主张性恶*参见周炽成:《性朴论与儒家教化政治:以荀子与董仲舒为例》,《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5—17页。。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荀子是在晚年完成著作的。他的文章清晰而有条理,作为一位大思想家,他应该不会同时提出两种不同的人性论。否定《劝学》《儒效》《礼论》等篇,而以《性恶》为荀子的作品,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会否定掉今本《荀子》的大部分内容。合理的推断应当是:《性恶》篇不是荀子的作品,而是后世的伪托*另参见周炽成:《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34页;《荀子非性恶论者辩》,《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48—50页。。
《礼论》提供了荀子真实的人性论。然而,研究者们囿于传统看法,或者忽视《性恶》与《礼论》在人性论上的差异,或者误认为《性恶》与其他篇章是一致的。即使有人发现荀子对人欲的肯定和认可,但依然认为荀子主张性恶,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巨大差异。有论者提出,荀子的性恶指情欲的放纵会导致恶,但情性本身无所谓恶*路德斌:《荀子“性恶”论原义》,《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第135页。。这可能是察觉到《性恶》与其他篇的差别。不过,这并非《性恶》的观点。《性恶》鲜明地主张人性恶,并反对和驳斥孟子的性善论。王博说:“对学的强调,从逻辑上来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是非自足的或者有缺陷的存在,所以需要通过后天的工夫来塑造和弥补。至于这种缺陷是什么,以及到什么程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荀子那里,当然是其性恶的主张。”*王博:《论〈劝学〉在〈荀子〉及儒家中的意义》,《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60页。对学习重视的同时,一定要主张性恶吗?《劝学》有关于人性恶的或明或暗的说法吗?他显然是以《性恶》理解《劝学》,混淆了两篇的区别。论者们提出这些分歧的观点,归根究底是因为将《性恶》与其他篇章相混淆,并毫无批判地当作荀子本人的作品。
今本《荀子》是由西汉学者刘向编定而成。如同《庄子》的成书一样,他大概把所有托名荀子的论著都收入《荀子》一书,而没有对作者进行详细的考辨。刘向似乎没有注意到《性恶》篇与《荀子》其他篇章存在的众多分歧,所以把它们编为一书。众所周知,先秦的子书一般都不是由一人独自完成,而是包含不少后学的成果,比如《墨子》《庄子》等。像本文一样,把先秦子书的不同篇章分开研读,可能会发现许多不同和分歧,这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先秦诸子的思想。
仅从《礼论》看,礼养与性朴相合,而与性恶相悖。正因为本性质朴,自身尚未完善,才需要礼义修饰、调节、养护;礼养论肯定人的各种欲望,即是肯定人性,礼义对人性不是“矫饰”“扰化”,而是“养口”“养目”等的肌体之养,这说明人性也不是生而即恶,两者是相顺、相合的关系。如果人生而即恶,就需要压制、改变,而本篇的礼养说没有任何压制之意。以往许多论者受性恶论的影响屡屡强调礼的等级性和强制性,因为人性为恶,所以需要礼的强制和规范。但根据本文所论,我们看到荀子更注重礼的教化、修身作用。礼养是顺应质朴之性的完善,而不是违逆情欲的限制。由此可知,荀子的看法更符合儒家而不是法家,荀子的性朴论与孟子的主张也并非针锋相对。
B222.6
A
1000-7660(2017)06-0126-05
刘荣茂,山东莒县人,哲学博士,(贵阳 550025)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讲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性论通史”(15ZDB004)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