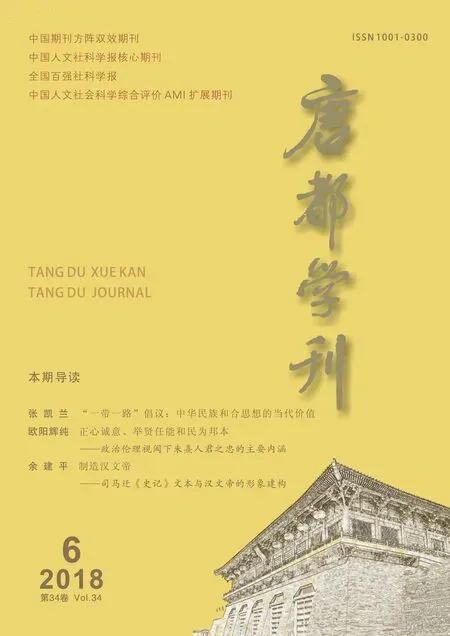制造汉文帝
——司马迁《史记》文本与汉文帝的形象建构
余建平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史家常称“文景之治”,文景并称,但景帝的历史地位相比文帝要低很多。文帝在有汉一代有崇高的地位,其去世后被群臣尊谥为“文帝”,在宗庙祭祀中被列为“太宗”,就是汉人对其一生德行仁政的概括。
关于文帝形象评说和研究的著作颇多,司马迁和班固称其为仁德之主,汉人又多有关于文帝节俭、爱民的美誉。现代研究者对文帝及其统治下的汉朝则带有更强烈的反思色彩,陈苏镇认为,史家对文景之治颇多誉美之辞,文景时期的繁荣主要是刘邦以来,特别是惠帝、吕后时期与民休息的结果,文、景二帝对诸侯王权力的收夺,使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再次出现[1]。高敏、邵金凯、薛小林分别从文帝的政治改革[2]、黄老刑名之术[3]和与军功集团的政治斗争[4]等角度深化了我们对文帝的认识,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理清,如文帝的形象是怎么形成的?与文帝有关的史料有什么特点?这些史料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样的?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文帝这一经典皇帝形象的发展演变过程有重要意义。
一、《史记·孝文本纪》中的汉文帝形象与其他文献记载的差异
司马迁作《史记·孝文本纪》,文末载: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5]437-438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纪传之主的评论,与纪传主体内容相比,带有更为直接、强烈的私人情感。“德”与“仁”是这段文字的关键字眼。在儒家的传统中,能同时具备仁与德的帝王,只有舜、尧、禹、汤、文王等人,而司马迁认为汉文帝完全可以与这些圣王相提并论。但是从诸多文献的细节记载可以看出,文帝形象远没有那么完美无缺。《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慎夫人衣不曳地以及文帝不愿以中民之金作台的故事[5]443,以此说明文帝的俭朴,但《史记·佞幸列传》载文帝因宠幸邓通,而赐其蜀郡严道县铜山,使其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5]443,这与《孝文本纪》的描述反差何其大!
《汉书·贾谊传》载贾谊向汉文帝上书:“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以疏举。”[6]2230从贾谊的奏疏可以体会到,文帝治下的汉朝仍有诸多流弊有待改革,如《上疏陈政事》[注]文中提到的贾谊奏疏名,均据严可均《全汉文》。提到的是以礼义还是以法令治国的问题,“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6]2244。贾谊认为,文帝治下的汉朝仍继承着秦重法令而轻礼义的传统,以致出现了“杀父兄”“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6]2244等非常恶劣的社会现象。可见,文帝之朝虽有除诽谤、去肉刑等简省刑法的措施,但当时承秦法制,严刑仍较繁多,并没有达到政清人和的地步。最为重要的是,法令并没有起到威慑罪犯的作用,反而导致了各种社会恶习,而在贾谊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不用礼义而引起的。又贾谊《说积贮》曰:“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6]1128司马迁所说的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是“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而贾谊笔下的汉之为汉四十年,却是“民且狼顾”,这显然有着较大的反差。
司马迁强调文帝之仁德宽厚,但从史书其他文献却可以看到文帝铁血冷酷之一面,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功勋旧臣周勃等人的打压;二是对淮南国、齐国等王国势力的削弱。文帝为高祖刘邦庶子,身处远离政治中心的代国,吕氏之乱平定后,因其母薄姬谨良而被除诸吕有功之臣陈平、周勃等人迎立为帝。“臣立君”的政治结构必然让身处帝位的文帝焦虑不安,他在“益明习国家事”及逐渐培养起自己的可靠势力之后,终于决定消除功勋旧臣的威胁。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令列侯之国[5]422,此令并没有取得效果。前元三年(前177),文帝再次下诏,免丞相周勃之位,令其率诸侯之国[5]424-425。周勃在自己的封邑常怀不安,“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5]2072。后周勃被人上书告发谋反,被捕狱中,得太后之助,才免于难。周勃为什么会“自畏恐诛”,他对文帝打压旧臣的心思应该是很明了的[7]。从周勃之事可以看出,文帝绝不是《史记·孝文本纪》描述的那般宽仁敦厚。文帝对淮南国和齐国的打压和削弱更可见其冷酷的一面。陈苏镇对此有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汉文帝为削弱淮南国、齐国等王国势力,相继推行“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使淮南王舅父赵兼远离淮南,并使齐哀王舅父驷均和齐悼惠王十子离开齐国,置于汉郡的严密监视之下,从而分散和瓦解了这两支威胁最大的王国势力[8]。历代论者多称赞文帝有长者之风,但在其巩固帝位过程中,其实是刑德并用,并不是只有宽厚这一面,冯唐就曾批评文帝“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
应劭《风俗通义》记载了汉成帝与刘向的一段对话,颇为有趣,可视为汉文帝形象建构的注脚。《风俗通义·正失》:
(孝成皇帝)常见中垒校尉刘向,以世俗多传道:……(孝文皇帝)躬自节俭,集上书囊以为前殿帷,常居明光宫听政,为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庐居枕块如礼,至以发大病,知后子不能行三年之丧,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断狱三百人,粟升一钱。“有此事不?”向对曰:“皆不然。”……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结,所谓治安之国也。……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蚀,地数震动,毁坏民庐舍,关东二十九山,同日崩溃,水出,河决酸枣,大风坏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推此事类,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为升平。[9]93-98
成帝听信民间关于文帝的传说,而刘向以实际例子逐一反驳,他认为文帝未央前殿过于豪奢淫丽;文帝好黄老之术而不用儒生。刘向又从灾异的角度,历数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相继出现了日食、地震、水患、冰雹、大风以及狗马人生角等灾异之象。按照汉人的理论,灾异的出现是由于阴阳不调,而阴阳不调则是因为主政者之不德,所以刘向说文帝之世,不可谓升平。
从《风俗通义》记载的汉成帝与刘向的对话及《史记》《汉书》相关篇章的记述中可看出似乎存在着两个反差较大的文帝形象:一位是《孝文本纪》叙述的俭朴、仁德之君,另一位是《孝文本纪》以外文献呈现的宠幸佞臣、不听忠言、好刑名法术的中庸君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形象反差?这种反差背后的历史动因是什么?
《风俗通义·正失》记载了刘向对此现象的分析:
(汉成帝)上曰:“后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语何从生?”向对曰:“生于言事。文帝礼言事者,不伤其意,群臣无小大,至即便从容言,上止辇听之,其言可者称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后人见遗文,则以为然。”[9]98
刘向认为,文帝谦虚平易的态度,特别容易获得群臣的认同和褒奖,而这些逐渐积累起来的声誉,正是文帝成为仁德之君的舆论基础。刘向的分析颇有见地,但从文帝如何善待言事者这个角度分析,视角过于狭隘。能够接触到文帝并且与之亲身交谈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到汉文帝或没有身经文帝之世的人来说,汉文帝向天下发布的诏令以及历史文献中关于文帝的记载才是他们想象和理解文帝的基础。
那么如何理解文献之间出现的反差呢?这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涉及文书的书写和历史的建构等问题。概括地说,造成汉文帝形象在各类文献中出现反差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汉文帝的身世背景及其诏令独特的书写方式;二是司马迁的政治背景与《史记》的创作。其中,文帝特殊风格的诏令是司马迁作《孝文本纪》的基本史料,也是汉文帝形象建构的基础;而司马迁的政治背景及其作《孝文本纪》的背后深意,则是建构汉文帝形象的历史动力。
二、汉文帝的身世背景及其诏令独特的书写方式
《史记·孝文本纪》对汉文帝的即位过程有详细的描述,这段文字对于我们理解汉文帝的身世背景及其即位前后的心态有重要的帮助。
正如上文所言,文帝对陈平、周勃等除诸吕之功臣是非常忌惮的,因此他对即位一事曾有很深的顾虑。《史记·孝文本纪》对此叙述详细,当陈平、周勃派人来迎接其入长安时,文帝犹豫未定,后通过占卜得天子之兆,他才下定决心前往长安。车至高陵时,仍要“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即天子之位后,他连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并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掌握长安城的军事大权。汉文帝在给将军陈武的一封书信中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5]1242从其书信之用词不难看出他即位初期之忧虑。
与秦始皇、汉高祖相比,汉文帝所处的政治环境已有很大不同[注]秦始皇统一六国,功高业大,其为人专断,对大臣有很强的威慑性。汉高祖戎马倥偬,一介布衣,建立起庞大的汉帝国,他善于驾驭群臣,所采取的一系列除灭异姓王的措施,令臣下不能不心存畏惮。。汉文帝在即位前只是偏居一隅的诸侯王,刘邦的功臣陈平、周勃等人虽主动迎立其即位,但在汉初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这一帝位的基础是不牢靠的。《日食求言诏》自称,其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如果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而身居高位,反而会有被疾风暴雨侵害的隐患。文帝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他在即位元年(前180)相继发布《封赐周勃等诏》《益封高帝从臣诏》,通过奖赏的方式安抚那些帮助他即位的高祖旧臣。这些压力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他在诏令中的姿态、语气和风格。
(一)文帝诏令表现出谦让宽容、关爱百姓的书写特征
诏令是皇帝向天下发布的命令性文书,是皇帝权威地位的体现。汉文帝之前的皇帝,如秦始皇发布的《除谥法制》《令丞相御史议帝号》等[注]秦始皇诏令名据严可均《全秦文》。,带有始皇帝浓重的威权意识,具有强制、命令的风格特征。汉文帝诏令的风格与此相反,文帝善于在诏令中淡化帝皇的威权,而以一种亲民的口吻表现出谦让宽容的性格特点。
文帝即位元年,有司请求早立太子,文帝曰: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5]419
秦汉时期,立太子的制度早已成熟。汉文帝在听到群臣请求早立太子的建议后,第一反应是“朕既不德”,强调自身德行的不足,并且推己及天下,认为天下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同时,汉文帝在这封诏书中提出,即使不能像尧、舜那样把天下禅让给贤人,但楚王、吴王、淮南王等同宗之人也可以继承帝位,何必让人“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5]420。我们能从诏书中体会到汉文帝的那分小心,对天下人看法的在意,以及对自身名声的维护,这在汉朝其他帝王身上是较少体现的。
汉文帝宽容的个性主要体现在他对刑法的省减,汉文帝即位二年(前179),发布了一道诏书,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朕闻法正则民慤,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5]418-419。秦时民众犯法,其父母妻子要相坐,至汉文帝时始废除。诏书开头就强调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认为只有法律合适正当,才能有效引导民众,使其安居乐业。诏令多次强调“民”,以民众的视角考虑法律问题,体现出文帝以民为本的品性。
其后,汉文帝又发布诏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即位十三年(前169),又废除肉刑。《史记·孝文本纪》载:“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5]427-428汉文帝在这道诏书中还是沿袭一贯的风格,谦虚恭让,用“德薄”“教不明”“自愧”这样一些词进行自我反思,又用“朕甚怜之”“何其楚痛”等词表明对百姓遭受肉刑的同情。
汉文帝对祠祝传统的否定,更能体现他对天下百姓的关爱和同情。文帝即位十四年(前168)发布诏书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绵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5]429这封诏书还是以自谦之辞“不敏不明”“甚自愧”开头,后以先王“先民后己”为借鉴,引出诏书的主题,即希望祠官祝釐要为天下百姓祈福而不是为皇帝一人,以表明自己对汉王朝百姓的关爱。
文帝的这些诏令不仅与秦始皇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与汉高祖、惠帝等皇帝的诏令也有巨大的区别,他在诏令中体现出的宽容谦让以及对群臣百姓的关爱和同情为他积累下了良好的政治声誉。
(二)罪己诏与罪己求贤政治传统的形成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日食而向天下发布罪己诏的皇帝,文帝之前的皇帝如秦始皇等人,诏令是他们向天下宣示威权、发布强制命令的手段,皇帝之权威不容置疑,皇帝也不可能罪己,至汉高祖、惠帝也没有在诏令中表现出罪己的意识。文帝则不一样,他用发布罪己诏的方式,越过始皇帝的威权,接续“禹汤罪己”的政治传统。罪己诏虽是在责备自己,降低了皇帝高高在上的权威,但却主动拉近了皇帝与臣民的心理距离。文帝即位二年,因连续日食,于是向天下发布《日食求言诏》:
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置传。[5]422
文帝强调,如果皇帝不行仁德,治理国家不均,上天就会降下灾异,进行惩戒,这两次日食就是上天在警告汉文帝,文帝在诏中用“天下治乱,在朕一人”,主动承担起治理天下的责任。“天下治乱,在朕一人”是化用商汤“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10]24之语。汉文帝主动接续商汤罪己的传统,将灾异的责任揽于一身。其后他再次强调自己的不德,下不能理群生,上不能承宗庙,“其不德大矣”。诏令以“令至”开头的部分,是针对灾异的具体应对措施,如令群臣思皇帝之过、举贤良方正、省繇费、罢边戍等,以破解灾异频发的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这不仅是汉朝第一封罪己诏,也是第一封征贤良方正极谏诏,汉文帝在这封诏书中不仅强调自己的不德,主动承担天下治乱的罪责,也用诏书的方式向天下士人发出征召贤良的声音。求贤纳言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一个重要传统。《国语·周语》有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0]7此是召公劝谏周厉王之语。召公认为,古代君王在统治过程中,设立了各种措施和制度来吸收众人之言,以求事行之不悖。即使在秦代这一传统也未曾断绝,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放弃了逐客之令,但是在帝王威权空前强化的秦朝,敷纳以言的政治传统必然会被弱化。汉高祖刘邦承秦朝之旧,这一传统仍未完全恢复,文帝以诏书的形式,接续并强化了这一政治传统,他的这一举动无疑为他积累下了深厚的政治声望和舆论基础。
(三)《与匈奴和亲诏》和汉文帝的偃武修文
自秦末以来,天下扰扰,兵事不息。刘邦在与项羽的争霸中胜出,天下局势逐渐平定,但北方强大的匈奴一直是汉朝边疆的主要威胁。刘邦在征讨匈奴时被困平城,幸得陈平秘计才得以逃脱。汉文帝即位后也对匈奴用过几次兵。如即位第三年(前178),匈奴入北地。汉文帝发兵八万五千,令灌婴率军攻打匈奴。十四年冬,匈奴入边为寇,文帝遣三将军,并想要亲自攻打匈奴,皇太后固谏才没有行动。这几次军事行动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风俗通义》载刘向对这几次军事行动的评价:“年岁谷不登,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9]99可见当时对匈奴用兵耗费了汉朝巨大的国家物资,以至于引起谷价的上扬。在经历了几场战争之后,汉文帝和匈奴签订了和亲协议,这一协议影响深远,被视为汉文帝的主要功绩之一。《史记·孝文本纪》: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5]431
这道诏书很能体现文帝诏令的特色,诏书起首即强调自身的不明不德,并将因兵事而引起的四荒不宁归罪到自己身上,这与上文的“天下治乱,在予一人”的表达方式是一致的。由此文帝指出,如果军事战争不停止,中外之国将不得安宁。书写至此,他又回到自身,强调自己对国家的忧心,对百姓的同情关爱,“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为了社稷的安宁,为了万民之利,才与匈奴结兄弟之义,定下和亲。
文帝特别擅长降低皇帝身份的权威,尝试以个体的感受去表达对百姓的关爱,这就使得诏令的情感抒发更为真切,打动人心。汉文帝开创了一种新的对外政策,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特别是与汉武帝时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相比,汉文帝与匈奴的和亲可谓一项仁德的功绩。
(四)汉文帝《遗诏》及其典范意义
汉文帝在去世前,立下一封遗诏。这封诏书最能体现文帝诏令的书写特色,他用一种细节性的展示,充满关爱同情的语气和质朴的语言,树立起遗诏书写的范式。《史记·孝文本纪》载:
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5]433-434
这段遗诏可分为三个层次:从“朕闻”到“谓天下何”是第一层。汉文帝认为天下万物,靡不有死,死亡是自然万物最平常之事,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是重死而恶生。汉文帝对这种传统多有批评,认为“厚葬以破业”和“重服以伤生”这两种嘉死恶生的传统,他都不能接受。由此,他又转到自身,以“朕既不德”这一谦虚之词开端,对皇帝崩丧天下人服丧过重的传统提出批评。文帝认为,如果他去世之后,天下人为其服丧三年,将会极大影响人的正常生活,造成诸多恶果,而这更反衬出他的“不德”。第二层从“朕获保宗庙”到“其奚哀悲之有”。汉文帝在这小段话中以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对自己统治的二十多年做了总结。文帝诏令经常使用的“不明”“不德”等词汇在这段话中频繁出现,偶然出现的“方内安宁”“靡有兵革”等肯定之词也将其托于上天之保佑。从“其令天下吏民”到“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是遗诏的最后一层。这是这一遗诏的核心内容。这段话展示了汉文帝去世后诸多细节性的规定,如天下人三日即可释服,不要禁止娶妇、嫁女、食肉等民众日常活动,衰绖之带不得超过三寸,宫殿哭临者旦夕各举声十五即可以及葬下之后,“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即释服。同时,在其死后,不可大兴土木,更改霸陵山川。这些规定如此琐碎,似乎与皇帝的诏令书写范式格格不入,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宽泛的、威权的诏令反而容易流于空疏,这种细致、具体甚至是琐碎的叙述方式反而更能展现其俭朴、谦虚的个性以及对黎民百姓的关爱,这是其他书写方式无法达到的。
从上文所述可知,汉文帝诏令的风格是非常独特的,他对自身不德的强调,对百姓的关爱同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以诏令的形式向天下传布。刘向认为世人关于文帝之治至于升平的流言,是源于文帝善礼言事者,过于片面。文帝发布的诏令以及由此形成的舆论基础和政治声誉才是汉人想象汉文帝的基础。这些藏于中央秘府的文书档案,成为司马迁作《史记·孝文本纪》的文献基础。
三、司马迁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与《史记》的书写
《史记·孝文本纪》有一段夹叙夹议的话,可看作是司马迁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总结和评价。《史记·孝文本纪》曰: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5]433
司马迁的这段话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汉文帝的俭朴。司马迁认为,文帝秉政二十三年,在宫室、苑囿、狗马、服御等人君所好之物上无所增益,曾经想要建一座高台,但听说要耗费中民之产,便作罢;其夫人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可谓节俭;文帝死后立遗诏令不得治坟,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可以说是俭朴至极。二是罢兵和亲。文帝以书报南越王尉佗,使其臣属于汉,又与匈奴定下和亲的政策,使整个国家免于战争和动乱,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三是以德化民,简练刑法。司马迁举了张武受贿,文帝反以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的故事。司马迁认为,文帝通过这一系列政策,使汉朝短时间内就达到了“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太平盛世,这与司马迁在“太史公曰”的评价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对司马迁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有所了解,就会明白他的这段文字似是另有所指。司马迁大约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担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与公孙卿、壶遂等人修订太初历,其后即开始编写《史记》,中间因为替李陵辩护,被处以腐刑。武帝征和二年(前91),在他给任安的信中提到《史记》全书的篇数,可见其时全书已基本完成。
司马迁撰述《史记》正处在崇尚奢华、频繁用兵、刑法日盛的武帝时代。武帝之崇尚奢华,从其筑建章宫可知。《汉书·郊祀志》载,武帝封禅泰山回来,因柏梁台起火,于是临时在甘泉宫受计,这时有人劝曰:“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6]1245太初元年,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幹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6]1245。以建造更大宫殿的方式来消除柏梁台火灾影响的提议,必然深得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的欣赏。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建有千门万户,旁边另仿海上仙山,凿太液池,并筑数十里的虎圈,这种奢华的作风与文帝不愿作中台的俭朴正形成鲜明的对比。
武帝之频繁对外用兵,更与汉文帝弭息兵革的努力显出对比。元光二年(前133),武帝始启边衅,伏兵马邑以诱单于,但无功而返。元光六年(前129),汉始出兵攻打匈奴,自此至征和三年(前90),凡四十余年,汉与匈奴屡次构兵,汉朝国力虚耗严重。武帝不仅征发匈奴,亦派张骞等人开拓西域,路博德等人平定闽越,西南诸夷也在武帝的武力下臣属于汉。武帝虽然大大开拓了汉朝疆土,但汉人对此却颇多讥评。宣帝欲褒武帝,诏群臣大议武帝庙乐,夏侯胜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6]3156夏侯胜等人在武帝朝之后,正是武帝大启兵祸,以致国家虚耗,百姓流离的见证者。司马迁正当武帝朝,对此体会应更为深切。
武帝朝之刑法与前代相比,更为严酷。《汉书·刑法志》曰:“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6]1101武帝朝刑法之酷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繁多。《刑法志》认为,武帝时律令就有三百五十九章之多,另有大辟四百多条,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多事,难怪掌管律令者都不能全部掌握。二是任用酷吏。司马迁专列《酷吏列传》,记酷吏之事迹。武帝朝酷吏之尤甚者,莫过于张汤、杜周,二人皆擅长舞文弄法,承上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5]3153,刑法只是他们操纵臣民、奉承皇帝的工具,毫无公平可言。
司马迁对武帝朝的各项政策应是极为不满的,东汉卫宏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注]裴骃《史记集解》引卫宏《汉旧仪注》,参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21页。《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载王肃对魏明帝说:“(武帝)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11]司马迁所作的《今上本纪》被删削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孝文本纪》中分俭朴、和亲、以德化民三个方面对汉文帝的评价,似是以汉武帝为对立面而做出的。司马迁虽是称赞汉文帝,实是以一种“春秋笔法”的方式对武帝时政进行刺讥。这是史家用心之处,也是我们不可不察之处。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作《汉书》有明显的不同,他作《史记》是以继承《春秋》为己任的。《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2]《史记·孔子世家》引孔子之言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5]1944司马迁对《史记》的寄托和期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太史公自序》记载了一段太史公与壶遂的对话,颇可见司马迁对《史记》的寄寓。《史记·太史公自序》: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5]3299-3300
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很高,认为《春秋》是王道之大者,能拨乱反正。当壶遂对其效仿《春秋》作《史记》的动机提出质疑时,司马迁用了“唯唯,否否,不然”几个模糊的字眼,并列举了汉武帝以来“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的盛况。从司马迁的闪烁其词可以看出,他对汉武帝的祥瑞太平是不以为然的,虽然他极力否认他作《史记》是继承《春秋》,但其话外之意能不难体会,他创作《史记》就是以孔子修《春秋》为榜样的。
《春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春秋笔法”,即以一种隐晦、委婉的方式对历史人物及事件微文刺讥。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孝文本纪》中,称赞汉文帝“德至盛也”“岂不仁哉”,固然有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肯定,但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何尝又不是对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政策的刺讥呢!
事实上,将汉文帝与汉武帝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称赞汉文帝的方式来反对汉武帝的大有人在,这种比较意识似已成为汉人的一种思维习惯。《汉书·东方朔传》载:
上从容问朔:“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瑇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6]2858
东方朔举汉文帝之事为武帝陈为君之道,他着重描写了汉文帝的俭朴,说他身衣弋绨、足履革舄,并以韦带剑,以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可谓俭朴至极。文风至“今陛下”开始一转,大肆批评汉武帝大兴土木、奢华侈靡、好大喜功。东方朔与汉武帝的这段对话并不一定真有其事,可能是汉人的伪托,但这段对话也可见出汉人对文帝和武帝的看法,文中描述文帝的俭朴以反衬武帝奢淫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同样的方式也可见《汉书·杜延年传》:“(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6]2664杜延年所处的昭帝朝正值武帝朝之后,杜延年认为对汉武政策导致的岁比不登、流民未还最好的反拨,是修文帝时政。此后召开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以文帝之政批评武帝朝盐铁专卖政策:“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13]汉元帝时,贾捐之亦言:“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6]2832贾捐之称赞文帝之偃武修文其实是要刺讥武帝之穷兵黩武。汉人议论往往有很强烈的功用色彩,善于在诏令中自我展现以形成良好政治声誉的汉文帝,无疑是汉人批评武帝的最好例子。
四、结语
历史人物形象的建构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而成的:一是直接史料,如有关人物的文章、被他人记载下的言论等。以汉文帝为例,他向天下发布的众多诏书是后人了解其人的直接史料。直接史料往往被看作是最为真实、最能反映人物个性特点和情感的文献,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直接史料并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的,文帝在诏令中多强调自身的不德,展示他宽容俭朴的品性,但从《史记·孝文本纪》以外的文献来看,汉文帝似不像其诏令所展现的那般俭朴、宽容。直接史料的辨别是一方面,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直接史料既然被看作是最为真实、与人物关系最为密切的基本文献,那么它们展现出来的风格特点往往会决定读者关于此人的想象,汉人对文帝的赞赏未尝没有受文帝特殊风格的诏令的影响。二是史书的书写。史书以直接史料为来源,结合其他基本文献,撰述传记。史家在书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以其对传记人物的理解,选择、删减、编排史料,并做出相关评价。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对汉文帝的描写,就可以看出司马迁强烈的史家意识,他对汉文帝极高的赞赏也必然会影响到汉人对文帝形象的想象。三是政治环境。史书的书写往往受史家所处时代政治环境的影响。司马迁身处武帝时代,他难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他的时代背景为视角而对文帝做出评价。东方朔、杜延年、贾捐之等人以对文帝的褒扬来反对武帝的政策,也是政治环境影响的结果。
通过对汉文帝形象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历史动因的探寻,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历史真实及历史书写这一命题。追求历史的真实曾是历代史学家一生的追求,但首先应该反思的是,历史是否存在绝对真实。以汉文帝为例,他的生活经历,他发布的众多政策命令毫无疑问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细致的史料考证或者出土文献的大量发掘,去还原一位真实的汉文帝,但我们所还原的其实还是我们所建构的汉文帝。相反,如果我们抛开对真实历史的追寻,转而去探究历史是如何书写的,这无疑要切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