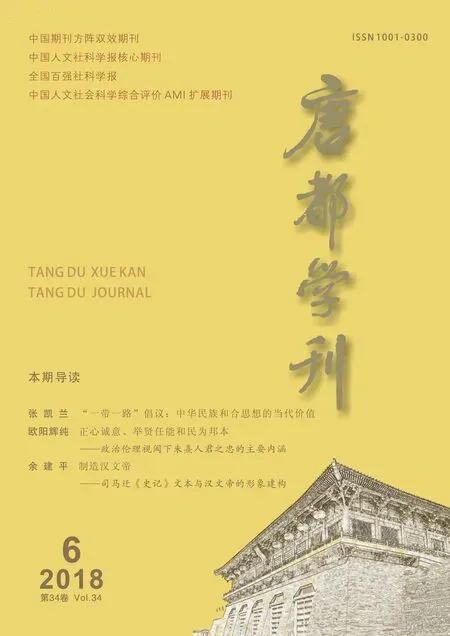二十世纪中美《史记》研究比较
许菁频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文学院,杭州 310012)
美国学界对中国《史记》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1938年和194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教授(Derk Bodde,1909—2003)相继出版了《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1]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年)的传记》[2]两部作品。前者以李斯为切入点,对秦代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3];后者以《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记以及《蒙恬列传》为中心分析秦代社会历史。
如果说卜德对《史记》的研究还只是着眼于几篇与秦代相关的传记,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华生教授(Burton Watson,1925—)则拉开了美国全面系统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的帷幕。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发行了华生教授的博士论文《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4],这部专著有《太史公自序》等的译文,很少有注释,可读性强,具有向普通英语读者普及《史记》的意义。华生教授在介绍了司马迁其人的基础上,概述了《史记》的形式和内容,分析了《史记》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史学理论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华生教授对《史记》的翻译事业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61年,华生教授翻译的《史记》[5]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选译了《史记》中的81篇传记,均是有关汉朝历史的。该译注以1934年泷川资言注解的《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同时参考百衲本《史记》和《汉书》中部分章节翻译而成。1969年,华生教授的第二个翻译版本《中国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选译》[6]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新翻译内容涉及周、先秦时期的人物列传,如《伍子胥列传》《刺客列传》等。在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华生教授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并增加了秦朝部分的翻译,于199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出版第三个版本《史记·秦朝》[7],该译本被列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译丛》。至今为止,华生教授已翻译了80卷《史记》,成为已经出版的最为完整的《史记》英译本。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史记》翻译家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1943—),他组织了大量人员准备对《史记》进行整体翻译,拟出版9卷,第1卷《史记·汉以前的本纪》(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和第7卷《史记·汉以前的列传》(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The Memoirs of Pre- Han of China)于1994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卷主要翻译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第7卷则是汉朝以前的列传1至28。2002年,该出版社又推出了第2卷《史记·汉本纪》(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The Basic Annals of Han China),翻译了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等。2006年和2008年,第5卷《史记·汉以前的世家》上册(Grand Scribe’s Records,The Hereditary Houses of Pre-Han China,Part I)与第8卷《史记·汉朝时期的列传》上册(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The Memoirs of Han China,Part I)亦由该出版社出版。该译注不同于华生教授的普及版《史记》,而是具有显著史学研究特质的英译本。
伴随《史记》英译本在美国的推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加入《史记》研究的行列。毋庸置疑,20世纪美国《史记》研究与翻译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将其与中国的《史记》研究相比,希图探析中美《史记》研究的异同,以此反观两国在文学史学方面的不同建树:
一、关于司马迁的研究
20世纪国内司马迁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于其身世、政治思想、史学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经学思想等均有涉猎,甚或考察其帝王观、命运观、妇女观、伦理观、法治观、天人观、地域审美观、文化学术史观等等,论著颇丰。这其中,既有上半世纪王国维对司马迁生平考证的文章《太史公系年考略》(1916)、《太史公行年考》(1924),李长之聚焦于司马迁的时代、思想和人格精神的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注]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自序中写道:“本书蓄意要写,是二十七年的秋天的事。”序言则完成于1936年,写作时间长达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侯外庐、任继愈等学术大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司马迁思想进行剖析的学术文章,以及王伯祥、郭沫若等人对《史记》的注释、考据工作。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司马迁的研究真正步入遍地开花的阶段。施丁、陈可青编著的《司马迁研究新论》[8]、韩兆琦的《司马迁的审美观》[9]、刘振东的《论司马迁之“爱奇”》[10]、李少雍的《司马迁与普鲁塔克》[11]、肖黎的《司马迁评传》[12]、刘乃和的《司马迁与史记》[13]、聂石樵的《司马迁论稿》[14],以及陕西司马迁研究会编撰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15],对司马迁进行了百科全书式地探究。
美国的司马迁研究始于1958年华生教授的博士论文《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在此之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于1840年在其创办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上载译了法国学者雷慕沙(Albe Remusat,1788—1832)所撰写的文章《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谈和他的儿子司马迁生平介绍》[16]。而华生教授的论文则对司马迁和《史记》均进行了一定的介绍、分析。论文共分五章,其中第二章“司马迁列传”(The Biography of Ssu-ma Ch’ien),翻译了包括《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等与司马迁生平有关的文章。与中国学者就司马迁研究司马迁不同,华生教授在论文中,还将司马迁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进行了对比,以方便西方人更直观地了解司马迁。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杜润德(Stephen W.Durrant,1944—)于1986年创作的《处于传统交叉点上的自我:司马迁的自传体著作》[17]一文,以《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作品为依据,深入剖析了司马迁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如何在过往的基础上建构“自我”。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候格睿(Grant Hardy,1961—)于1999年出版了专著《青铜与竹子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18],全书共由八章组成。其中,第六章和第七章将司马迁视为可以与儒家圣者孔子相媲美的史学家。此外,杜润德的《司马迁的救赎》[19]与华生教授的《司马迁的世界》[20],这两篇文章均对司马迁的生平与个性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毋庸置疑,美国对司马迁的研究远不及中国的详赡、系统与深刻,在一定程度上看,其研究还处于普及性层面,研究者往往希图向国人介绍司马迁其人其事。但值得肯定的是,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研究视角的不同,以及研究目的的迥异,美国学者的司马迁研究中也颇多亮点,尤其是对司马迁内心情感冲突的挖掘、对中西史学家创作心理异同的比较,为当今司马迁研究增色不少。
二、关于《史记》的史学研究
国内有关《史记》的史学研究主要热点集中在《史记》的实录性、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史记》的编撰传统、“太史公曰”的史学精神,以及史记人物的研究等方面,其余如将《史记》与《左传》《汉书》《资治通鉴》的比较亦不乏力作,成果的丰硕、分析论证的深刻均是有目共睹的。梁启超、李长之、任继愈、白寿彝、张大可、李文初、韩兆琦、赵生群、莫砺锋、俞樟华等人,均为《史记》的史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相比于国内学者,美国学者对《史记》的史学研究涉及面较为狭窄一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史记》是如何编撰的。美国学者往往从《史记》的具体篇目入手,分析《史记》编写的规律。例如,倪豪士1991年发表的《重新考察〈史记〉中的循吏列传》[21]一文,认为《循吏列传》在编撰中经历了从档案文献到成为书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倪豪士的另一篇论文,发表于2007年的《缺乏掌声:关于晋世家与司马迁的春秋之说明》[22],则以《晋世家》为例,分析司马迁在写作中如何选择、运用《春秋》中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司马迁对“春秋”一词的理解。1988年候格睿在其博士论文《〈史记〉中的客观性与阐释性问题》中,不仅考察了司马迁是如何运用史料进行编撰的,而且分析了司马迁在史料编辑时所显现的道德意义[23]。
第二,《史记》的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中美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学者对《史记》的实录精神赞誉有加,美国学者中不乏有对《史记》的真实性抱有怀疑态度之人。华生教授在《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中以《五帝本纪》为例,来论证《史记》的真实性。华生教授认为,司马迁力图去除五帝的神奇传说,从而保证历史的严肃性,这对中国历史的书写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华生教授对《五帝本纪》中内容的真实性表现出了极大的怀疑,认为“它完全可能把一系列传说中的人物或事件转化成严肃的历史事实”[4]。普利斯顿大学的柯马丁教授(Martin Kern,1962—)在《关于〈史记〉卷24乐书的真实性及意识形态的注释》一文中,则对《乐书》一章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2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梅可教授(Michael Nylan)明确质疑司马迁写作的客观真实性。她认为受命于皇权的史官怎么可能做到“实录”呢?[25]
与戴梅可教授的全盘否定不同,佛兰克·吉尔曼(Frank A.Kierman)于1953年获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史学态度》在1962年出版。该书在译注《史记》中战国后期四部传记,即《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的基础上,高度赞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26]。候格睿则透过司马迁自相矛盾的叙述,看到了《史记》叙事的准确性。1994年,候格睿在长篇论文《司马迁的多重叙述: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西方史学有现实贡献》[27]中指出,相比与西方史学的统一叙事,司马迁自相矛盾的叙述、多重解释的可能性,更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历史,且更关注道德层面的审视。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汪荣祖(1940—)在《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一书中,也肯定了司马迁的求真心理。汪荣祖认为:“司马迁以三代为世表,十二诸侯为年表,秦楚之际为月表,盖依史料之真伪多寡为详略,正见作者务实求真之意。英师濮冷布(J.H.Plumb)谓《史记》虽称‘巨制’(a remarkable book),未悉‘历史考证’(historical criticism)之事,故‘有异于吾人习知之历史’(is quite unlike what we regard as history)。历史考证者,即‘不盲目接受史证’(not to accept all evidence blindly)。司马迁果昧于史证之真伪乎?非也。其取材论证,诚有疏误;而其考求实证之心,固无异于今人。”[28]76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李惠仪(Wai-yee Li,1959—)在《〈史记〉中的权威观》一文中,结合司马迁的生平经历,认为司马迁本人是主张历史真实的,但《史记》中说蕴含的情感倾向也是不言而喻的[29]。
美国学者对有关《史记》史料的拥有不能与中国学者同日而语,因此,在进行《史记》的史学研究时,其视野的不开阔,甚或分析时往往陷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境地也是情有可原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在进行《史记》史学研究时,深刻关注到了《史记》作为史学巨著的解释功能和道德批判功能,并对其历史“解释”功能的不足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正如杜维运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所言:“中国史学未能到达西方‘综合’的境界,也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30]
三、关于《史记》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是20世纪国内《史记》研究的重头戏。1949年前,林纾、魏元旷、李景星、高步瀛、施闺章、李长之等人对《史记》的文学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之后《史记》的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虽受建国初政治气候影响,《史记》文学研究停滞不前近三十年,但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中依然取得不菲的成果,仅《史记》人物研究的论文,就有近八百篇左右[31]。诚如曹晋所论:“具体而全面的研究涵盖了《史记》的文学观、美学观、散文风格、传记文学特质、语言艺术、民间文学、《史记》与先秦文学的承继关系,以及《史记》对后世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的影响。”[32]专题论文、专题著作以及学位论文的大量涌现是这一时期《史记》文学研究的显著特点。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与整理”,更可见中国对《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视。当然,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不论是“论著的重复与欠专精”[32],还是本体论研究的薄弱,都是我们不能规避的问题。
相比于中国《史记》文学研究的轰轰烈烈,美国《史记》文学研究显得有些萧瑟冷清,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了一些突破:一是对《史记》文学技巧的分析。曹晋在《〈史记〉百年文学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完全可以借鉴来分析《史记》人物列传的叙事风格。”[32]在这方面,一批美国学者已做出了一定的成果。华生教授《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一书中,对《史记》的文学技巧和风格均做了一定的探讨。叙事技巧是美国学者研究《史记》文学技巧时最感兴趣的话题。杜润德教授的《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33]一文从《史记》文学性角度切入,考察《秦始皇本纪》的叙事结构,并分析司马迁在历史描述中所隐含的态度。候格睿教授在《司马迁〈史记〉的形式与纪传体叙事手法》[34]一文中,将《史记》的体例、叙述技巧与作品的创作目标相结合进行考察,从而探析《史记》作为道德解释性工具的作用。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约瑟夫·艾伦教授(Joseph R.Allen)在探析《史记》所运用的叙事技巧的基础上,对《伍子胥列传》和《李将军列传》的叙事技巧进行了细致分析[35]。
二是《史记》中人物形象及塑造手法的分析。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南微莉(Vivian-Lee Nyitray,1954—)1990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其博士论文《美德的写照:司马迁〈史记〉中四位君子的生平》,采用文学批评方法分析《史记》中“战国四公子”的人物组成,尤其是信陵君与守门人侯嬴之间的关系[36]。杜润德在《混乱与缺漏:司马迁对前贤刻画的几个方面》一文中,通过分析司马迁对董仲舒和孔安国的形象刻画,试图探究他们对青年司马迁所产生过的影响[37],而在《模糊的镜子: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38]一书中,则在描述《史记》诸多矛盾与冲突的基础上,分析其隐藏于文本之下的文学模式。该书“特别注重对《史记》文本文学性的研究,通过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和详尽的语义分析,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司马复杂的内心世界”[39]。此外,杜润德教授的《试评〈史记〉》一文中,将《史记》与中国古代小说相联系,认为《史记》“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类历史传奇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40]。
美国学者运用西方的叙事理论对《史记》的叙事技巧进行分析,以及通过解读《史记》中的人物形象试图触摸司马迁的“灵魂”,这显然是有益于中国的《史记》研究。但甚为可惜的是,鲜少有美国学者从文学角度将《史记》与西方史传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学者在此方面已做了初步的尝试,如钱钟书的《管锥编》、李少雍的《司马迁与普鲁塔克》、黄新亚的《司马迁评传》、刘清河的《从〈旧约〉与〈史记〉的比较试探东方文学的一点规律》等论著均是其中的佼佼者。但由于阅读的局限性,此类成果还不够丰硕。我们期待美国学者能在这方面做出一定的努力。
毋庸置疑,20世纪中美《史记》研究在数量、质量上均有不小的差距。20世纪初,中国《史记》研究在一批学术泰斗,如梁启超、李长之等人的带领下取得了绚丽的成果。80年代以后,一批年轻的学者勇于进取,对《史记》进行了全方位的开垦,成果的丰硕是有目共睹的。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史记》研究的步履艰难也是毋庸讳言的。如何从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研究领域切入进行《史记》研究以取得更大的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比较中美20世纪《史记》研究的异同,寻找各自研究的长处与不足,无疑有益于当下的《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