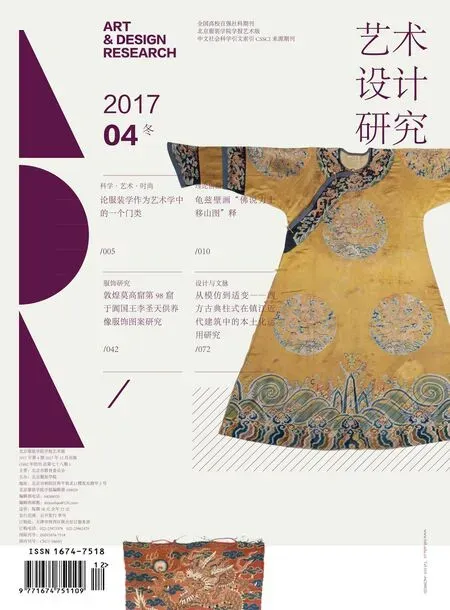中西方传统服饰礼仪文化比较研究
宋 炀
服饰礼仪中的“服饰”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但包括包裹与装饰人体物品的总称,还包括人类穿戴、装扮自己的行为。“服饰礼仪”是服饰的一种重要社会功能,它是人类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伦理道德、烘托场合气氛、实现人际交流等一系列社会功能而在着装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关于服饰及服饰着装行为的社会制度或道德规约。服饰礼仪包括由官方颁布的典章法制、由风俗习惯形成的礼仪风俗、由宗教信仰规定的仪式制度、由民间约定俗成的道德规约、由特殊阶层群体培养的格调范式。按类型划分,有用于特定场合的仪式服饰礼仪,也有普通生活中的日常服饰礼仪。服饰礼仪体现为由一定的色彩、纹饰、款式、质地等一系列服饰元素构成的着装标准。在社会生活中,不同层次的服饰礼仪规范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服饰规范系统。这个服饰规范系统受到社会环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以及时代潮流的影响与制约。服饰礼仪能够从阶级性、价值观、伦理性等角度反映出民族服饰文化的特征。因此,对中西方传统服饰礼仪文化的平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真正的把握服饰的民族气质与精神特征,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传统服饰文化。
本文对中西方传统服饰礼仪文化比较研究的范畴是针对中国文化圈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形成的两个服饰文化体系下的服饰礼仪研究。由于篇幅和精力有限,在此排除了另外两个重要的服饰文化圈,即伊斯兰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的服饰礼仪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中国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中上层社会的服饰文化为主。这是因为相对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服饰,社会上层的服饰不仅具有制作工艺精湛,存世概率高,考证相对容易,服饰文化构成更系统与完整等特点,而且社会上层的服饰和服饰礼仪在主流文化的影响和滋养下,被赋予了更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能传达更详实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民族服饰文化的精神特征。
在古代中国,“礼”深入社会的每个层面,因而礼仪的名目极为繁冗,《中庸》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在 《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按照礼仪的不同目的和施行的不同场合,礼仪被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利、嘉礼五种类别。每一种传统礼仪又包括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礼法、礼义、礼器、辞令、礼容、等差等。其中,礼容,即行礼者的体态、容貌和衣着。即如《礼记·杂记下》说:“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由此可见,作为礼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礼仪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礼仪文化源于基督教所提倡的骑士精神,发展至文艺复兴时期,礼仪是宫廷中的一系列行为规范与准则,成为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528年4月意大利外交家鲍达萨尔·卡斯蒂廖内(Baldesar Castiglione)撰写的《朝臣记》(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出版问世,书中详细地描述了15世纪欧洲宫廷朝臣的行为举止、社交技能和礼仪规约,探讨了实现“完美绅士”的理念,奠定了西方传统礼仪文化的基石。17世纪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建立了一整套关系衣食住行各生活方面的宫廷礼仪规范,培养土地贵族成为宫廷贵族以巩固自己的王权。19世纪,资产阶级精英传承宫廷礼仪并将其与资产阶级追求的格调品味结合,演绎为一系列近现代文明礼仪。高举个人主义旗帜的西方礼仪强调个人才智的凸显,形成包括称谓礼仪、交谈礼仪、拜访礼仪、餐桌礼仪、服饰礼仪、女士优先礼仪、服务礼仪、问候礼仪、社交礼节等一系列礼仪规范,并系统地形成有明文规定的典章法度。
总之,中西方皆具一套完备的服饰礼仪文化,形成民族文脉的基因编码,成为现当代研究和传承传统服饰文化重要的研究内容。
此外,在详细展开中西方服饰礼仪文化比较研究以先,我们不得不澄清研究中存在的重要难点,即两种服饰礼仪文化发展中存在时间上的剪刀差。中国传统服饰礼仪文化建立在宗教祭祀活动的基础上,其发展的繁盛期在封建社会,随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在向近现代服饰礼仪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断而未续的现象。西方传统服饰礼仪建立在骑士精神基础上,在宫廷文化中发展到繁盛阶段,经过资产阶级精英与市民阶层的文明化传承与沿革,形成现当代系统规范的服饰着装礼仪,并在国际上推而广之。因此,两种服饰礼仪的研究存在时间上难以平行比较、观点聚讼不已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抛开时间轴上的对应,而是以宏观的历史观纵览东西方礼仪文化的特征,以文化学与服饰学的角度,以点带面地进行文化属性上的比较研究。
一、中国传统礼仪与服饰礼仪的文化特征
1、中国传统礼仪的内涵与文化特征
荀子曾说: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仪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礼仪之邦”,声教播于海外。相传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乐,就提出了礼治的纲领。其后经过孔子和七十子后学,以及孟子、荀子等人的提倡和完善,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那么,何以为礼呢?礼仪的深层内涵又是什么?《说文解字》云:禮,从示从豊,字形采用“示、豊”会义。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禮字从示。豐者行禮之器。礼,履也,即以丰厚之物履行敬拜活动,向神明显示尊敬。①即从古文字的字面意思阐释:禮,即是古人举行敬神祈福的祭祀活动及祭祀活动中的礼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简体“礼”字给出了四种解释:祭神;理解、仪式;以礼相待,礼貌;礼物。②《说文解字》对仪的解释为:仪,从人,义声,用“人”形而从“义”声。仪,度也,法度法制也。今时所谓义、古书为谊。③从字面意思上阐释,仪,即是人的外表与举动的法度,有仪态、仪表之意。《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仪”字给出了七种解释:容貌、外表;礼节、仪式;准则、法度;仪器;匹配,配偶;通“宜”,适宜、合适;通“宜”,应该。据上述古文字分析,若将二字之古意熔铸于词,分析“礼仪”之意,即为古人举行敬神祈福的祭祀活动,及人在祭祀活动中的仪表、举止等礼节,及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礼器和法度等一系列规范的仪式。《现代汉语词典》对“礼仪”一词的解释即:礼节和仪式。④足见,古今一辙,礼仪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对人,对己,对鬼神,对大自然,表示尊重和祈福等思想意识的,各种惯用形式和行为规范。综上所述,从词源上分析,中文“礼仪”的内涵构成包括几大元素:第一,礼仪根源于宗教信仰。第二,礼仪实践为身体行为与仪式。第三,礼仪借助于礼器和法度,其是人神沟通的媒介。
1983年7月,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向美国学者邓尔麟谈及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中西文化的区别,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⑤同时,钱穆先生也提出礼仪文化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性问题。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礼是一个家庭,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正是遵守同样的礼仪,社会关系准则才能从家庭成员中延伸,从而形成一个家族,再扩大成为一个民族。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⑥因此,以宗法社会为基础而发展形成的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具有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目的性,其具有鲜明的社会等级性与阶级性。

图1: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直裾深衣结构图
2、中国传统服饰礼仪的文化特征
中国传统服饰礼仪文化是以儒家思想发挥核心作用的中国文化圈或汉文化圈中形成的服饰礼仪文化。在地域上包括中国古文化对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等在内的汉文化圈。在时间上包括从先秦至清末,以汉民族文化为主轴的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服饰礼仪。
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服饰作为中国礼治的重心成为经国治世的重要方略。先秦时期提出《周礼》《仪礼》《礼记》的“三礼”以及在《礼记》中提出的“五礼”奠定了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基础,以《周礼》为代表,中国即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的服饰礼仪规范。孔子云“君子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不貌无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因此必须“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服饰文化观念和着装礼仪是“三礼”“五礼”中最核心的内容,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对服饰文化思想的探索与总结,而是从宏观角度出发勾勒了中华服饰制度以及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整体格局,内容涉及服饰文化、容貌举止、礼仪行为和周旋揖让的艺术等,是最富有实践意义的行为指导与内蕴解析,为我国传统服饰礼仪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期,中国历代的《舆服志》即是通过服饰规范特定社会地位群体的行为举止和形态仪表的典范,体现了“唯礼是尚”的中国传统文化。纵观中国服饰发展史,这种“唯礼是尚”的思想融贯在传统服饰的造型、色彩、纹样、造物方式等多个方面。
(1)中国古代服饰造型的克己复礼
中国古代服饰往往以符号化的语言赋予人体以社会礼仪与等级属性,并逐渐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服饰礼乐观。中国传统服饰造型封闭、含蓄、飘逸,轻形重神,认为形而上的精神才是美的最高境界。如老子在《道德经》第70章所云“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意思是,真正有思想、有品行的人,即使衣衫褴褛,也不损伤其人品修为。⑦老子“被褐怀玉”的服饰观强调的正是轻貌重德克己复礼的思想。即如《白虎通》中所言:“衣者,隐也。裳者,彰也。所以隐形自障闭也”⑧中国传统服饰强调对身体的遮蔽覆盖,刻意以衣裳障碍替代人体的自然曲线。以最为典型的中国古代服饰深衣为例,深衣之“深”即取其“衣裳相连,被体深邃”之意,其长无曳地,短无露肤,极好地保护了身体的私密性,即为“克己”。此外,深衣作为礼服,以其色、形与意合于礼,须而使身体动作合于礼,使其容貌自然有威可畏、有仪可象,即为“复礼”。深衣的主要部件包括袷、袂、袼、缘、衽、要、带及下齐等(图1),各部件的裁剪无不蕴含礼教思想。其“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⑨可见,深衣的裁剪合中正之数,而有中正之形。这正是荀子所说的“以礼正身”。同时,中国传统服饰追求儒家倡导的“中和”、“中正”之美,服饰造型的中正裁剪呼应了传统服饰美学以对称为美,以中央为尊,强调“正衣立冠是为礼”的礼学思想。而正是由于礼,身体超越了其原始性而达成雅化的目的。此外,礼由外转入内在的身体需要,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人的整个性命安居于此,而呈现出一种中和的威仪气象。⑩因而,深衣的造型裁剪所呈现的正是礼乐文化下的社会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着装者的身心修养。

图2 :明代袍衫的十字型裁剪结构(图1、图2图片来源:刘瑞璞、陈静洁《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汉族篇,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8月,第87页)

图3:周代皇帝冕服
(2)中国古代服饰造物的敬天格物格物致知,知至意诚。此为儒家研究造物原理而至道理通达的理论,此理论同样适用于研究传统服饰造物方式与其中蕴含的礼学思想。在结构裁剪方面,中国传统服饰具有“十字型、整一化、平面化”的特点,服饰的装饰是为了完善结构形式而存在,结构形式又以不破坏面料的完整性和原生态而设计,由此形成了“布幅决定结构”的十字型平面结构(图2),并成为中华服饰结构的稳定基因。这种传统的裁剪方式根源于古人崇尚“节俭”的生存价值,经过“尚物”这种敬畏自然的道儒哲学的湆练,十字型平面结构中“格物致知”的造物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礼学层面的“敬天惜物”精神。[11]此外,中国传统服饰造型结构中蕴含着古人对“丝绸”应用的思考,充分体现了在面料使用上“格物”思想的探索。与西方服饰传统面料羊毛不同,丝绸流畅柔韧的特质在服饰裁剪中体现出动静之间的变化关系。传统丝绸服饰在摆放或悬挂时像画卷一样平整,展现了二维平面的大方气度和坦荡胸怀,在着装时,起伏连绵的衣褶和曲直缠绕的襟裾却营造了线条流畅、飘逸灵动的洛神之美。
(3)中国古代服饰色彩的纲常法礼
历代统治者把服饰当作“严内外,辨亲疏”的伦理工具,“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自古以来,服饰色彩就是反映着装者社会等级,维系社会秩序,体现纲常礼法的重要元素。自北朝末至隋代起,在受胡服影响而产生的常服系统中,逐渐形成了以服饰颜色排列等级的“品色服”制度,服饰色彩以纯色为正色,两色相杂为间色。《礼记·玉藻》载:“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12]即如孔颖达所述:“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駵黄是也。”古代服饰的色彩等级礼治森严,以正色贵,其中尤以玄黑与赤为贵,贵族的朝服与礼服皆用此二色,周代皇帝冕服上玄下曛的色彩即反映了天玄地黄,乾坤宇宙的运行之道(图3)。而间色由正色杂取而得,被视为不纯之色、邪淫之色而为贱。[13]《论语》便有“恶紫夺朱”[14]一说,古人认为以间色乱正色,是以邪胜正,以异端充正理之意。《论语·乡党》中也有大量关于服饰色彩使用与着装者等级地位和德行礼仪关系的记载。“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即是君子不用天青色和铁灰色作镶边,浅红色和紫色不用来作平常居家的衣服。在历代《舆服志》中也有大量关于特定社会等级专用色彩礼仪的案例记载,包括自唐以来,唯天子袍衫得用赤黄的限令。《新唐书》载“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元史·舆服志》也有“庶人不得服赭黄”之令。统治阶级对服饰色彩的使用限令说明中国的服饰色彩带有明显的等级性与礼仪性,彰显了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成为划分社会等级强有力的政治工具。
(4)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风俗伦理
中国传统服饰的二维平面造型特征使服饰的装饰变化较少地体现在造型与结构方面,而更加注重服装的图案铺陈与平面装饰点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中国服饰强调纹样装饰与君子德行关系的写照。因此,纹样最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中国衣冠礼乐的思想。服饰纹样体现的礼仪思想具有寓意丰富,内涵隐晦的特点,即所谓“衣不在衣而在意,纹不在纹而在文”。如古代天子冕服上绣绘的十二纹章就是从自然事物中取材,通过抽象概括的符号比拟天子所应具有的品德。明清时期服饰上大量应用的吉祥纹样也是将服饰赋予思想寓意与精神寄托的典型案例,其无论采用寓意、比喻、象征、谐音的手法,其装饰目的都是“齐以为礼”。除了纹样本身充满吉祥礼乐思想以外,纹样的构图也讲究礼数章法,强调和谐、对称、统一的造型样式,构图上两两相对,相互均衡,左日右月,上龙下凤,忌讳倾斜,讲究寓意。
(5)中国古代服装配饰的崇德尚礼
中国传统服饰追求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的统一,即“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在传统服饰中,有大量“以己度物,以衣比德”的例子。如自古中国男子就有佩玉的习惯,“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玉是高贵优雅,美好明洁的象征,以玉佐身,即要求君子时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规范人的道德,用鸣玉之声限制人的行为动作。因此,佩玉是中国服饰文化崇德尚礼的体现,它表现了配饰之人所追求的精神世界与自我修养。再如宋代官员上朝之时皆手持白玉板做成的圭臬,其具有标明官员身份的作用,同时还引申为提醒官员说话做事应时刻遵循的标尺、准则和法度。另外,冕冠上的充耳也是服饰崇德尚礼思想的另一案例。在西周王朝至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属臣的冠冕两侧皆以丝绳在耳旁垂坠两块美玉,称为“充耳”(图4)。玉制的充耳称为“瑱”“珥”或“充耳”,绵制的称为“纩”或“充纩”,属于男子冠帽上的装饰品,自先秦一直沿用至明代。作为一种礼服配饰,充耳缀与皇帝的冕冠均有时刻提醒皇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寓意。此外,朝臣大夫们“冠配充耳”也是一种礼制,诸侯王公站立堂下,要垂首恭听君王言论,不得顾左右而言其他,若头部左右晃动,“充耳”即会以惯性击打佩戴者的耳廓和面颊,以示“自惩”。足见,充耳的主要服用功能也是礼制胜于装饰的。
总之,中国服饰的样式审美建立在精神追求的基础上,以人伦秩序为核心,以文质彬彬、以衣比德、寓道于器为主导思想,形成了反映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的中国传统服饰礼仪思想。
二、西方传统礼仪与服饰礼仪的文化特征
1、西方传统礼仪的内涵与文化特征
英语“etiquette”有礼仪,礼节,礼貌,规矩之意。[15]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等级与社会群体范畴中,符合其群体传统习俗的一系列行为规则和典范。“etiquette”的同义词有good manners(礼貌), propriety(适当、得体), decorum(礼貌、礼仪), protocol(礼仪、礼节)等。英语“etiquette”一词于18世纪中叶从法语“étiquette”转化为英语,这一词汇源于18世纪的法国宫廷,最初是指法国宫廷贵族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行为礼仪规范,包括服饰着装的规则典范。这种由宫廷文化孕育的行为礼仪规范与贵族发展的历史休戚相关,西方宫廷礼仪可以上溯到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乃至古罗马时期的贵族文化。北方日耳曼等民族的大举入侵虽然使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但罗马贵族并没有消亡,而是通过战争与和谈等方式与后来的北方民族上层阶级融合在一起,形成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封建贵族,其具体分成两个阶层,一是拥有大量土地的领主,二是追随领主的骑士。到中世纪中期,领主和骑士之间的分界开始模糊,混合为统一的贵族阶层。在中世纪后期的12~13世纪,随采邑制的推行,原贵族与骑士阶层的紧密融合,可以说所有的贵族都是骑士,但骑士并不一定是贵族。因此,骑士不仅是军人的头衔,也是贵族的封号,其包括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等。中世纪后期,由于经济发展繁荣稳定,与贵族融合的骑士生活安逸稳定,也不再通过暴力扩张领地,攫取财富,基督教神职人员为了进一步促进这一阶层的稳定甚至赋予了其具有贵族气质的“骑士精神”(chivalry),骑士精神来源于职业的武装阶层,强调作战的公平与荣誉感,后被诠释为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勇敢、忠诚、慷慨、谦恭,渴望荣誉,以及对妇女的尊重和举止的温文尔雅等特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骑士阶层通过血统的延续、政治经济权力的世袭、文化的传承积淀形成了稳定的贵族阶层,使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前的欧洲形成典型的贵族社会,并逐渐培养出精致文雅的宫廷式礼仪文化,并形成了通过出身和品味区别于底层社会的一系列上层社会身份识别方式,包括服饰礼仪。秉承骑士精神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等级森严、典章严格的特点,宫廷礼仪同样强调个人中心,并具有严格的典章规范制度,特别是具有标明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服饰礼仪。20世纪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化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中介绍了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礼仪文化的历史进程,并指出文明主要表现为个人行为举止的文雅化,是基于保持自己地位的竞争所带来的羞耻感不断增强的结果。在经历了由宫廷礼仪(Courtoisie)到礼貌(Civilite)再到文明(Civilization)的西方礼仪文化转变的过程中,人的文明化是其核心。[16]

图4:周天子十二冕旒冠上的充耳

图5:紧身胸衣的基布和鲸须插片裁剪结构图
总之,西方的礼仪文化源自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成形于文艺复兴以来近世纪的欧洲宫廷,在资产阶级精英阶层与市民阶层中得到系统性发展,其精神本质建立在西方皇权统治与人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具有注重个人品格和特质的特点,以平等、自由、开放为精神内核,即通过服饰着装礼仪、就餐礼仪、商务交往礼仪等一系列社交礼仪维护社会秩序,规范道德行为,体现人的素质修养,最终实现人的价值。
2、西方传统服饰礼仪的文化特征
西方传统服饰礼仪文化是以地中海文明为基础,包括北非的尼罗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以及南欧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及经过来自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而形成的,从欧洲中世纪以来发展形成的基督教文化圈的服饰礼仪文化。
西方服饰礼仪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上,强调通过服饰的造型塑造人体的比例关系及人的行为举止,以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形体差异、品德差异与阶级等级差异。
(1)西方传统服饰礼仪的人体中心
西方服饰礼仪彰显对人体美与人性美的探索与思考,注重人体自我表现,强调通过服饰强化和炫耀身体。恰如人类史专家乔治·斯瓦伊格雷洛在分析“从骑士时代到宫廷时代的美体训练”时指出:宫廷权贵阶层从14世纪就开始注重训练并保持身姿挺拔优美,随着宫廷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自身行为的要求越来越苛刻。[17]因此,西方传统服饰造型立体、开放、多变,与中国传统服饰封闭、包裹、稳定的服饰造型特点不同。在崇尚人体美的思想指导下,西方服饰最富有魅力的表现形式就是服饰与身体间“遮与露”关系的辩证,通过对人体曲线的表现与身体某些部位的裸露,最大限度地发挥服饰与身体的吸引力是西方服饰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在服装的结构裁剪方面,西方传统服饰具有“复杂型、分析性、立体化”的特点。因为高寒地带的欧洲人选择以羊毛为主要服饰面料,羊毛的可塑性使西方人创造了“分析的立体结构”,并以人体的比例结构与运动姿态为研究对象,服饰呈现如同建筑与雕塑般的空间感与体积感。以文艺复兴时期服饰为代表,上装衣身衣袖分离裁剪、紧身胸衣分片拼合(图5)、衣片外轮廓呈曲弧线等皆体现了西方服饰造型裁剪的特征。
(2)西方传统服饰礼仪的行为重塑
服饰具有重新塑造身体的作用,并通过对身体行为的限制作用,服饰能够赋予身体不同的身份地位。西方服饰即经常通过服饰对身体行为的重塑与限制达成服饰礼仪化的功能。西方贵族视身体动作与行为模式为高贵出身的标志,并内化为贵族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能够走路的婴孩开始,贵族们就在舞蹈教练的指导下学习行走、舞蹈、骑马、行礼等,在镜子前练习身体的动静礼仪,使着装的身体呈现出最优雅的仪态是他们每天的功课之一。在《优雅的艺术:18世纪的时尚与幻想》一书中,爱德华·梅德将宫廷贵族的服饰礼仪划分为两个范畴:第一,呈静态的着装仪态,例如站姿、坐姿等。第二,呈动态的着装行为,如行走坐卧,舞蹈等。在崇尚思想决定情感的西方宫廷,上层社会追求将快速积极的思维与身体的冷静安宁并置的理想状态,礼仪要求精英阶层将澎湃翻涌的思绪和情感隐藏在平静安宁的身体中,对身体提出着装后的“静态美”。以18世纪欧洲宫廷贵族女性为例,女性在站立时头部微微上扬,向一侧稍稍倾斜,和躯干形成“S”形曲线,下颌收敛,眼睑低垂,肩背下倾,躯干向上挺直,整个上半身呈现出纤细挺拔但自然轻盈的感觉,这一时期女性穿着的紧身胸衣恰恰帮助女性塑造了这一礼仪形象。此外,向左右横向延伸的驼蓝式帕尼埃裙撑夸张了女性下半身的体量,掩盖了腿部的动感线条,进一步强调了女性身体的静态美。因此,无论是在西方服装史上流行了数个世纪的紧身胸衣还是裙撑,都于限制女性身体快速灵活的行动而塑造端庄优雅的礼仪姿态有关,而为了优雅端庄的礼仪,女性的身体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从当时德文郡公爵夫人(Duchess of Devonshire)给朋友的信中就可见一斑:“我的新法式紧身胸衣紧紧勒住胸部,以致我在站立的时候几乎无法呼吸,我的腰和胳膊同时被它勒得酸痛,我觉得我随时都要窒息晕倒,只有通过不停煽动扇子带来新鲜空气来维持呼吸,但穿着这件紧身胸衣时带给我的骄傲、挺拔、尊贵感、仪式感和十足的女人味,使所有为此付出的一切都变得值得。”[18]足见,服饰具有重塑身体行为并传达礼仪精神的作用。除了对静态身体的约束,服饰同样对动态的着装身体进行约束管理。在近世纪西方服装史上,曾主要流行过三种裙撑造型:圆钟型裙撑(Round hoop)、帕尼埃裙撑(Pannier)和巴瑟尔裙撑(Bustle),三者都以夸张女性的臀部及下肢为造型特点。其中,将女性臀部向左右平均各扩展4英尺的帕尼埃裙撑(图6)最具有代表性。在这种裙撑风靡一时的18世纪欧洲,穿着帕尼埃裙撑的女性常常导致街道交通堵塞,剧场和舞厅骚乱,甚至教堂礼拜秩序混乱。但这并不影响贵族女性对这种导致行动不便的服饰的喜爱,因为这种裙撑不但为女性增添了庄重优雅的气质,而且使着装者的身体远离人群而彰显出身体如艺术品般的尊贵性与礼仪性。为了合理地掌控宽大的裙撑,女性必须在行动前做一番合理地规划,而身体能够极好地驾驭这种服饰并作出优雅的动作是衡量着装者身份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在宫廷舞会中表演当时流行的阿里曼达舞时 (图7),灵活自如地控制帕尼埃裙撑并能够保持轻松的状态,做出优雅的动作成为宫廷女性的礼仪必修课。同时,男性舞伴也要时刻注意裙撑为二人共舞制造的障碍,当众碰撞女性的裙摆对于绅士来说相当粗俗无礼。也正是由于裙撑的不便,西方贵族男女之间的问候礼仪由贴面礼转变为吻手礼(Kissing of the hand)(图8)。由此,服饰塑造了公共交往中两性之间温文尔雅的交往礼仪。

图6:1765年 向左右进行造型拓展的帕尼埃裙撑与法国式罗布
(3)西方传统服饰礼仪的女士优先原则
女士优先(Ladies First)的礼仪原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源于有骑士风度的男士对力量柔弱、行动不便的女性的礼节性帮助。女士优先礼仪原则发展至今具体表现在多个社交细节中,包括行走时女士先行,女士靠内侧行走;乘车时男士替女士打开车门;上下楼梯电梯时女士先行;见面时先向女性致礼;用餐时为女性推拉椅子等。礼让女性最初是基督教思想指导下富有力量的男性对体力相对弱小的女性的保护和礼让,“骑士风度正说明两性关系中较强一方对较弱一方的服务,并以此成为男性自己的荣誉”[19]至文艺复兴时期,男性服饰塑造的雄大的上半身与紧贴肉体的下半身使男性形体呈现颇具动感与力量的倒三角形形体轮廓,女性紧窄的上半身与膨大的裙子使女性形体呈现相对稳定含蓄的正三角形形体轮廓。在体现和塑造两性身体差异的同时,服饰配套衍生出一系列女士优先的行为礼仪,强化了男性社会性与女性家庭性的社会属性。在17~18世纪欧洲宫廷文化发展的高峰阶段,崇尚女性成为风流世纪君主专制体制之下男性享乐的重要途径,大量诗歌与绘画等艺术作品表达了对女性从身体到精神的崇尚与赞美之情,此时期女装在塑造和表达女性的身体美上也达到了人工装饰的巅峰,重装之下女性的诸多行动不便为男性彰显绅士风度、实践礼仪风范提供了更多机会,男士能够对女性屈膝相迎,脱帽致礼,推门帮臂,这些留存至今的礼仪相当一部分皆源于服饰着装。18世纪末期,随着沙龙文化的博兴,以及19世纪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和获取知识的机会逐渐增多,女士优先成为资产阶级精英对女性表达尊重的一种社交礼仪。沿革至今,女士优先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第一礼仪,并已经内化为很多西方国家人民的道德自觉,成为西方礼仪文化的重要特征。

图7:18世纪法国宫廷舞会中流行的双人阿里曼达舞

图8:18世纪贵族男女之间的吻手礼
(4)西方现代服饰礼仪的理性精神
自19世纪初,西方精英阶层已逐步放弃出于物质炫耀与身体炫耀的服饰礼仪文化,而更加注重展示自己服饰着装的良好品味与礼貌教养,从而培养出代表资产阶级精英阶层文化与理性精神的服饰礼仪。现当代西方服饰着装规则如军服番制般具有严谨的系统性与理性精神。“番制”是军队的番号制度,军服番制由军衔标识体现,西方现当代礼服的着装“番制”也具有这些特点。着装系统是由所有构成服装的元素,即形制、饰件、色彩、材质和搭配规则诠释,表现出较强的隐秘性与专属性。在西方主流社会中,已经形成一套系统的服饰着装礼仪规则,就是文化对服饰提出组合规则的着装密码(The Dress Code)。它类似于社会集团的潜规则,这个着装规则类似“军衔番号规制系统”,只有遵循这种着装规则,才能符合社交礼仪的秩序。如系白领结(In White Tie)是指燕尾服,是晚间隆重和公式化正式场合的第一礼服,白领结、双侧章裤子是构成燕尾服最具有标识的服装元素。[20]西方现当代服饰着装礼仪的严谨典章规范性与原则性是一脉相承的西方理性精神的写照。恰如埃利亚斯在《文明化的进程》中所述,“从“宫廷礼仪”(courtoisie)、“礼貌”(civilite)到“文明”(civilization)”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清楚地表明西方礼仪这样一种趋势:即一种“文明的特质”的逐渐形成—深思,算计长远,自制,精确调节自己的情绪,识人之明,深知内幕,用理性来抑制人的情感和行为方式。”[21]
三、中西方传统服饰礼仪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中西方服饰礼仪文化有许多共通性。首先,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中西方服饰礼仪都具有鲜明的阶级等级性。其次,中西方服饰礼仪皆通过一系列服装密码组成符号系统,传达服饰礼仪。如中国君子以玉比德,西方女子以扇子传情。最后,中西方服饰礼仪文化皆体现为一系列的礼仪行为,并形成一套系统的行为准则与制度规范,即法度规训。
然而,服饰礼仪是文化与历史积淀的结果,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家庭观念和民族习俗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礼仪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为:
1、中西方礼仪观念的差异
第一,文化差异是中西方服饰礼仪文化差异形成的根源。儒释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特别是在儒家中庸、仁爱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服饰礼仪文化呈现出谦卑、内敛、仁慈的特点。基督教信仰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宣扬的自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成为西方服饰礼仪文化的基础。第二,价值观念差异是中西方服饰礼仪文化差异形成的内因。服饰礼仪反映了其所代表的文化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服饰礼仪文化在宗法社会的基础上形成起以“仁”“义”“礼”“智”“信”为中华伦理和个人道德体系的最核心因素,提倡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中国服饰礼仪文化强调贬己尊人,如《礼记》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体现自谦礼让、尊卑清晰、长幼有序的纲常观念,形成与西方迥异的服饰礼仪文化。西方的服饰礼仪文化源自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成形于文艺复兴以来近世纪的欧洲宫廷,其精神本质建立在西方皇权统治与人本主义的思想上,强调理性精神,注重个人品格与特质,尊重个人利益和价值,提倡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第三,社会族群观念的差异是中西方服饰礼仪文化差异形成的外因。稳定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传统的礼法社会强调“家”与“族”的集体观念,中国文化中有一个西方文化中没有的概念,那就是“族”。[22]在中国,礼首先是一个家庭的准则,再延伸到有血缘关系并遵守共同礼法的族群,从而形成家族和民族,“礼”是由家庭、家族和民族构成的人类社会关系准则。因此,中国服饰礼仪文化较侧重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天人之礼”与道德伦理的“纲常之礼”。相对而言,开放的海洋文明孕育的西方服饰礼仪对族群的观念较为单薄,而强调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个人发展的基础上。在基督教文化中,也格外强调个人与神关系的建立,也正因如此,尊重个人隐私成为西方礼仪文化中公允的价值观。因此,西方礼仪文化较侧重表现人与人关系的“社交之礼”与体现自我修养的“行为之礼”。因此,可以说,不同的文化差异、价值观差异和族群观念差异是中西方服饰礼仪差异的根源。
2、中西方身体观念的差异
如前所述,依据《说文解字》中对礼的考据,礼仪的构成包括几大元素:第一,礼仪根源于宗教信仰。第二,礼仪实践为身体行为与仪式。第三,礼仪借助于礼器和法度,其是神人沟通的媒介。这就是说,礼本身就是建立于人的身体之上,是人的身体凭借礼器将“事神致福”之事表演出来。故而,荀子亦有言:“礼者,体也”,“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23]意思是,礼是一种身体行为,只有礼成为身体相应的习惯时,礼才能安居与身,达到内外交融、身心交摄,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制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24]身体是礼仪的载体,而身体对于礼的完满呈现还要借助其它物质性的东西,如身上之饰与上手之器等。而对于身体来说,这些物质性东西中最具本己性的自然是人的衣饰。[25]服饰以其色、形、意合于礼,继而使着装者的身体动作合于礼。从而实现了服饰由“美”走向“真”与“善”的更高境界。由此可见,身体观是研究中西方服饰礼仪差异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身体观受儒家和老庄思想影响深远。老庄崇尚以自然为美,反对人为装饰,如同老子排斥人为之乐、有声之乐,倡导自然、无为,体现道之精神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道家的这种美学思想解释身体之美的观点,即身体发肤之美应超脱出物质本身的形貌之美,而将美升华为对天地万物“神格”的感悟上。此外,儒家思想也追求轻形重神,认为形而上的精神才是美的最高境界,即将身体之美建立在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追求一种超越人的形体之上的人格精神与道德境界之美。受老庄与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所倡导的身体之美都不是西方人那种可观的外在美,而是内在的心性美、品格美。也正是在这样的身体观影响下,古代中国服饰造型总是倾向遮蔽身体,续而的礼仪功能是装饰规诫身体,使身体的进退俯仰、徐慢缓急呈现神韵之美与德行之美。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大量着重描摹着装者风度气质的诗句,如东汉傅毅 《神女赋》中对郑女的描写:“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礼记》也将服饰礼仪与修身之道密切联系,以为“齐明盛服,非礼不动,以为修身也”。
与中国的身体观不同,西方身体观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上,强调人体的比例关系及人体的空间占有意识,这种身体观根源于孕育海洋文化的自然环境,并系统性地受到西方哲学物我分离的二元对立思想影响。在理性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古希腊艺术家实际上以科学的测量、分析与实验的方式来塑造数学模型化的人体。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数理和谐”观念,到波利克里托斯的《规范》,再到罗马学者维特鲁斯的《建筑十书》中都能看到西方早期的理性化人体美理论。“黄金分割”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依据数理和谐原则提出的美的定律,这一学派把数理和谐原则与“黄金分割”应用于对理想的人体比例的认识上,崇尚人体美,并对欧洲的人体审美形成深远的影响。进而,西方人将这种观念和认识应用于服饰美学,逐渐形成以强调人体外形与比例为目的的服饰造型观,并形成以行为举止来衡量人的礼仪修养的服饰礼仪观。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遮蔽和否定身体,追求以精神代替身体,服饰的造型、色彩、纹样等各个方面都在彰显着装者超脱于身体之上的精神礼仪追求。西方传统文化强调和肯定身体,强调本我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服饰造型结构、着装行为、符号语言、优先原则都是围绕人而展开的,服饰礼仪在体现人的道德品质的基础上也强调服务于人。
存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作为传承千年的礼仪之邦,华夏民族的服饰礼仪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礼乐文化最光辉灿烂的篇章。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华服饰礼仪的文脉曾经历较大冲击,民族服饰文化的自信心曾一度低迷。但优秀文化的因子往往是历久弥新的,其作为一种民族文脉持续地影响着民族的精神与面貌。在文化兴国的时代呼唤下,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与设计创新工作正在夜以继日地推进,服饰礼仪文化作为传统服饰文化重要的支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正是研究传统服饰文化工作不可回避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中西方服饰礼仪文化的比较为切入点,以期更清晰地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服饰礼仪的文化特征,传承华夏服饰礼仪之文明。
注释:
①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4页。
② 王力、岑麒祥、林焘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版,第231页。
③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21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793页。
⑤ 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页。
⑥ 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页。
⑦ 李艺:《老子的服饰观及其当代意义》,艺术设计研究,2016年06月。
⑧ 陈立撰:《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33页。
⑨ [汉]郑玄 注,[唐]孔颖达 正义:《礼记正义》,第961-961页。
⑩ 刘乐乐:《从“深衣”到“深制”礼仪观的革变》,文化遗产 2014年,第5期,第115页。
[11]刘瑞璞、陈静洁:《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汉族编),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8月,第319页。
[12]《礼记·玉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第550-551页。
[14]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选自《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

expectations for social behavior according to contemporary conventional norms within a society, social class, or group.The French word étiquette, literally signifying a tag or label, was used in a modern sense in English around 1750. From the 1500s through the early 1900s, children learned etiquette at school. Etiquette has changed and evolved over the years. https:// en.wikipedia.org/wiki/Etiquette. 2017年12月10日。
[15](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化的进程》卷一,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16](美)Valerie Steele. The Corset: A Cultural Histor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P72.
[17]Edward Maeder. An Elegant Art: Fashion and Fantas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1983:37.
[18](德)爱德华·博克斯,侯焕闳 译:《欧洲风化史》2版,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9]刘瑞璞、马立金、周长华:《礼服》,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第1页。
[20](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化的进程》卷一,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478页。
[21]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页。
[22][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3页。
[23][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6页。
[24]刘乐乐:《从“深衣”到“深制”礼仪观的革变》,文化遗产,2014年,第5期,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