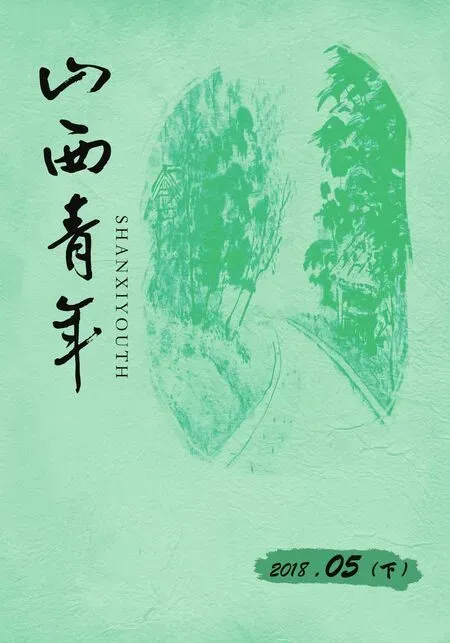论传统法制建设中的“忠孝”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张豪爽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一、“忠孝”的起源
“忠孝”源于我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家长为中心,由家族组织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的政治制度。在古代国人的思想中,家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最直接、稳固的纽带。“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家族来维系的,而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通过忠孝而得以实现”[1]。
以自耕农生产方式为主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使中国古代的社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的特权,即父权。“百道之行孝为先”,“孝”被视为最根本的道德,子对父的顺从以及对其命令的绝对服从被视为父子之间关系的根本准则。而偌大一个“国”,实为一个“家”,皇帝即是享有父权特权的大家长,而其臣民即为其子孙,对皇帝的“孝”,就叫做“忠”。在当时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中,“孝”即是“忠”,“忠”即是“孝”,“忠”、“孝”没有实质的区别。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如果人人都能像孝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自己,那么天下便再无难事可言。统治者们明白:“孝”是维系自己统治的工具,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根本法宝。于是,“为子为臣,唯忠唯孝”、“亲亲尊尊”等“忠孝”观念便融入了我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中,成为我国传统法制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忠孝”的传统法制建设
(一)先秦时期
神权法思想是夏商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观念和法制指导思想,习惯法是其主要的法律形式。《吕氏春秋·孝行》引《商书》:“刑三百,而罪莫大于不孝。”可以看出,夏商时期把“不孝”看作是最严重的犯罪,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同时,商朝时还规定了“不吉不迪,颠越不公,暂遇奸宄”罪、“乱政”罪和“疑众”罪,对于不正不善的人、违抗命令对统治者不敬的人、奸诈和内外作乱的人以及反抗国家统治的人,视为“不忠”,将其作为重罪,以野蛮、残酷、粗暴的刑罚进行严厉的镇压,以维护商代的统治。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在西周时期达到成熟,宗法制度构成了西周社会的基本结构。“亲亲”和“尊尊”是西周重要的法制指导思想。“亲亲”要求人们在宗族范围之内亲爱自己的家人,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妇听”[2]。“尊尊”则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等级秩序,依自己的身份行事,恪守自己的名分。“‘亲亲’的核心是孝,‘尊尊’的核心是忠。‘亲亲’原则所维护的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尊尊’所维护的是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3]。要求“亲亲”是为了达到“尊尊”,教化人们孝父是为了忠君。“亲亲”是“尊尊”的前提和基础,“尊尊”是“亲亲”的延伸。
西周时“不孝”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因为“不孝”不仅会影响家庭中人与人的亲情关系,甚至会危害到西周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的统治。所以“不孝”的行为在西周被视为“元恶大憝”,要“刑兹无赦”。此外,王命在西周时期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全体臣民绝对服从和遵行。所以违抗王命、触犯王命也被视为严重的犯罪,正所谓“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服也”[4]。而且,“在宗法体制之下,君、父一体。对于处于君父位置的‘尊长’来说,其优越地位有政治的和血缘、家族的双重保障,而对于处于臣、子位置的卑幼、下属来说,他们对尊长有政治的和伦理的双重义务”[3]。所以,臣、子如果流放或者杀害其君、父,将会受到严厉的刑罚,如将罪犯千刀万剐、肢解,而且多数情况下还会株连其家属。
(二)秦汉时期
秦代主要采用了法家“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等的法治主张,规定了“子不孝”、“卑幼殴尊长”、“谋反”、“操国事不道”、“泄露皇帝行踪、住所、言语机密”、“不行君令”等罪名。“谋反”是指意图推翻皇帝专制政权的犯罪;“操国事不道”是指操纵国家政务大权,改动政令及其他倒行逆施的犯罪行为;“不行君令”是指违抗、拒不履行皇帝命令的行为。此外,秦代法律赋予父亲送惩权,如《封诊式·告子》“爰书: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
汉初的法制指导思想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之以法家思想;汉武帝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之以法家思想。在立法上,“亲亲得相首匿”的刑事法律原则是“孝”在汉代法制建设中的主要体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法律允许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了犯谋反、大逆等严重的罪行外,可以互相藏匿犯罪,不予告发或作证,而不负刑事责任。此原则源于孔子的“亲亲相隐”思想,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5]。此外,“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汉王朝非常重视家庭立法和关系调整。汉律强调“父为子纲”,为维护父权的统治,规定有“不孝”罪,且列为重罪。如子女控告父母或者在父母丧期间发生性关系就构成“不孝”罪处死刑。两汉刑法中规定“不忠”的犯罪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侵犯皇帝权威的犯罪,包括对皇帝不忠、欺骗、轻慢、侮辱皇帝的行为、“非议诏书毁先帝”、“左道”、官吏阻止、拒不执行皇帝诏令的行为等。二是危害中央集权制度的犯罪,如“阿党”和“附益”、“僭越”、“出界”、“泄露省中语”等。三是镇压敌对阶级反抗的各类犯罪,如“大逆不道”罪等。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法律由纷繁复杂向简明规范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实现法典化的转变自此开始。北魏时加重对“不孝”罪的处罚。太和元年(447年)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政”[6]。此外,还规定了直系卑亲属依法为尊亲隐罪、“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7]。晋律中也有“不孝罪弃市”的规定。为了镇压危害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违反纲常伦理的行为,在北齐时,“重罪十条”,即“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8]正式入律。在这十条之中,“恶逆”、“不孝”等是违反“孝”的犯罪行为,“反逆”、“大逆”、“叛”、“降”等是违反“忠”的犯罪行为。
存留养亲制度也是“孝”的一种体现,其始于北魏。这一制度是为了解决被判处死刑或者徒刑、流刑罪犯的父母老疾无人侍养的问题而设置的,是指直系尊亲属年老应侍而家无成丁、死罪非十恶的犯人,通过上请而可以获得特殊的处置,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将犯人留下来照料老人,待老人去世后再实际执行的制度。《魏书·刑罚志》载北魏孝文帝曾诏曰:“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且据《魏书·刑罚志》记载:“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9]”
(四)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制建设的成熟、完备阶段。在唐代,封建家长是君主在家庭中的代表,家国相通,忠孝相维。唐律中最著名的当属“十恶”的规定,其是危及封建皇权和国家统治的十种重罪的总称,其具体内容是:一是谋反,二是谋大逆,三是谋叛,四是恶逆,五是不道,六是大不敬,七是不孝,八是不睦,九是不义,十是内乱。在“十恶”中,“孝”体现在第四条“恶逆”:“(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10]。“恶逆”项下所列出的罪名,绝大多数要处以绞刑甚至是斩刑;第七条“不孝”:“(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丧,诈称祖父母父母死”[10]。犯“不孝”项下所列出的罪名,都要处以徒以上刑罚,且遇赦不原。“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罪名是违反了“忠”的要求。“《疏议》说:‘谋反’是‘谋危社稷’,即图谋推翻皇帝的统治;‘谋大逆’是‘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即图谋毁坏皇帝祖庙、皇陵和宫殿;‘谋叛’是‘背国从伪’,即背叛封建国家,投降伪政权;‘大不敬’是指盗取皇帝服用物,盗取或伪造皇帝印玺,给皇帝配药不按本方,做饭犯食禁,指责皇帝、诽谤朝政,对皇帝、使臣无礼等,即侵犯皇帝人身及其尊严的各类行为”[3]。
除此之外,“无违”原则也是我国传统“忠孝”文化的一种体现,其主要体现在子孙必须服从祖父母、父母的教令上。《斗讼》篇规定:子孙违反教令者,徒二年。如果“可从而违”,即予以严惩。子孙对于父母的责教,必须服从,即使责教无理,也不得有不满的表示。且为了进一步落实子孙不得违反教令的规定,《斗讼》篇规定祖父母、父母因责教子孙而殴杀子孙者,只处徒一年半,较一般人殴杀罪要轻得多。而且,对于不孝和违反教令的子孙可以向官府告发,而不受“同居有罪相为隐”的限制。
(五)宋元明清时期
魏晋以来,随着门阀等级制度被革除、土地买卖和租佃制的普遍推行,地主阶级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利,地位已与之前有了明显的不同。为了迎合这一变化,新的理论——宋学产生了,而在宋学中居于首位的理学在宋代的法制建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宋代统治者为了提倡孝道、家庭和睦、贞节烈妇等,大量运用旌表。“自汉以来,历代王朝提倡封建礼教对‘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常由官府立牌坊,赐匾额,称为旌表”[11]。而宋代旌表的孝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割肉疗亲,另一类是毁身葬亲。宋代加强了对破坏中央集权、对“十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不忠的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宗室、外戚、宦官等六种人专政。
元代十分重视孝行,将孝行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在法令中规定了大量提倡孝的内容,如《通制条格》中规定:“随处诸色人等,往往父母在堂,子孙别籍异财,实伤风俗,送户部讲究得旧例,祖父母、父母不得令子孙别籍,其支析财产者听。今照得土民之家,往往祖父母、父母在日,明有支析文字,或未曾支析者,其父母疾笃或亡殁之后,不以求医侍疾丧葬为事,止以相争财产为物、以此参详,拟合酌古准今,如祖父母、父母在,许令支析者听,违者治罪”[12]。
明代统治者吸取元代因“宽纵”而亡国的历史教训,且深谙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重典治国”和“明礼导民”成为了指导明代法制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朱元璋十分重视忠孝节义,他说:“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也”[13]。元代对于“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的不孝行为处杖刑一百,对于“闻父母丧而匿不举哀”的行为处杖刑六十。对于“谋反”、“谋大逆”等不忠的犯罪行为,本人处凌迟之刑,其祖父母、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性,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16岁以上者,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残疾,一律处斩刑。
清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后一个朝代,清代的法制建设,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了两个不同的阶段。清代前期的法制建设以“参汉酌金”、“详译明律,参以国制”、“渐就中国之制”为主旨;清代末期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威胁以及国内日渐盛行的革命思潮,进行了以移植西方法制为特征的大规模修法活动。清律中,规定了“谋杀祖父母父母”、“尊长为人杀私和”、“殴祖父母父母”等不孝的罪名,还规定了“子孙违反教令”罪,对违反父母、尊长命令的子孙卑幼处以杖刑。而且还赋予尊长“送惩权”,即对于多次违反父母、尊长的人,可以将其直接送至官府,要求将其发遣。此外,清代“刑律”中还规定了“谋反大逆”、“谋叛”、“盗制书印信”等不忠的罪名。
三、“忠孝”的当代价值
(一)亲亲原则对现代立法和司法的借鉴意义
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政权下,对待“孝”的态度是不同的,而对待“孝”也是其对待道德态度的体现。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倾向性的意见认为,道德是法律的指针,是法律实施的基础,是法律条文不可或缺的补充。适当的道德水准是法治文明的先导,这也是我国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目前,我国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如何妥善安排老人实现老有所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独生子女的数量大大增加,而如何使子女主动关心照顾父母、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自觉形成一种对于父母的责任感,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家庭入手,从“孝”入手。因此,可以加强宣传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强化人们对于父母的责任感,并可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的法律惩戒,向社会强行立标,匡正人们的相关行为。
(二)尊尊原则对现代立法和司法的借鉴意义
“尊尊”原则在古代,表现为对最高统治者个人、家族权力和地位的忠诚与维护,其优点在于能使中央的决策及命令顺利、彻底地执行。当今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阶段,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社会处于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作用。而保证这些决策不打折扣地贯彻实施,就需要有系统且具体的司法制度作为保障。
此外,“人,尤其是作为统治者的人,一直是法律适用和法律发展的推动者。说法律昌明,也是统治者昌明;说法制成就,也是说统治者成就。任何时代、政权下的立法、守法、执法,无不体现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和自身的利益追求,体现他们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体现他们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和信心。法律适用原则的生成与坚守,也同样难出这样的藩篱。[14]”
(三)存留养亲制度对现代立法和司法的借鉴意义
当今中国社会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负担全家生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是这一人犯罪被判了刑,那么这一家人的生活由谁来保障呢?仅仅依靠政府吗?政府的负担能力又有多大呢?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家中上有七十岁的父母卧病在床,下有还正在上小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妻子又与之离婚远走,老人无人照顾赡养,孩子无人教养,若政府无法负担其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失去了生活唯一来源的这一家人该如何生活?因此,存留养亲制度在现今生活中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对于出现类似情况的罪犯,可以考虑适度予以优容。例如:对刑罚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可以考虑设立特殊情形的缓刑等。
(四)亲亲相隐原则对现代立法和司法的借鉴意义
法不外乎人情,对于人们来说,法律不仅仅应该是打击、惩治犯罪的冷冰冰的工具,也应该有顺应人情的一面。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不顾人情,只顾打击犯罪,那么这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甚至是一个畸形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会使人人都秉持着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变得冷漠,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疏远淡漠,甚至会使人性扭曲。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民众,对于中国这个人情社会来说,是不利于其未来发展的。因此,对于一些非典型的案件,在特定亲属范围之内,可以适当地对近亲之间的相隐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例如可以明确规定近亲属的范围内,相互之间实施的包庇行为或者毁灭证据、作伪证的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可以减轻处罚。但是,对于亲亲相隐也要有一定的限制,否则会造成法律的滥用。如特定亲属范围应当排除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司法人员,以免造成权利的滥用和司法腐败。
参考文献:
[1]贺晓荣,郝春莉.论中国传统法文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5):72-79.
[2]左传·昭公二十六年[M].
[3]曾宪义.中国法制史(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9,38,157.
[4]国语·周语[M].
[5]论语·子路[M].
[6]魏书·高祖记[M].
[7]魏书·窦瑗传[M].
[8]隋书·刑法志[M].
[9]魏书·刑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85.
[10]唐律疏议·名例[M].
[11]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53.
[12]通制条格[M].
[13]明通鉴[M].
[14]曾宪义,夏锦文.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