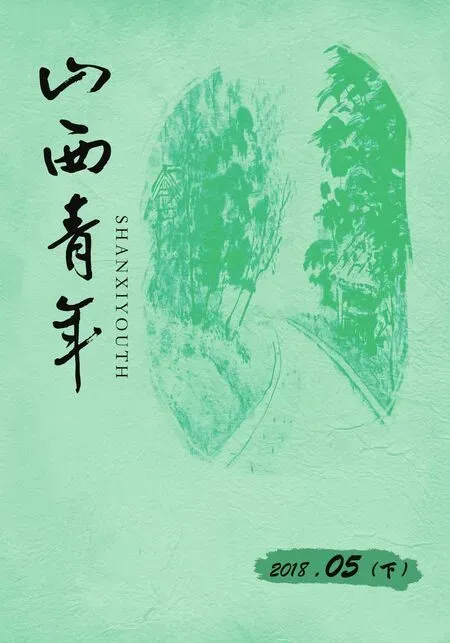对完善少年司法处遇机制的思考*
程一鸣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201620)
自1984年我国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创设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发展到今天,虽然还没一套成熟的体系能够为之所用,但是在实务中,在借鉴国外少年司法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我国一直以来都在进行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处遇机制的探索与发展。
一、国内对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处遇机制
就如今国内刑法体系来讲,对于未成年人的处遇机制主要表现在刑罚体系上,以及对于未成年人刑罚的特殊规定。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17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就是说,即使是上述犯罪,对未成年人的惩罚,相比成年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另外,对于实施不构罪的行为的未成年人,也即针对“虞犯“,现在的司法体系采取“分级保护”的措施。虽然他们的行为没有达到刑罚处罚性,但是已经对社会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具有一定的违法性。所以,对此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必将有应对措施,不能听之任之。特别对于反社会心理形成到一定程度的未成年人,性质恶劣的情况下,更加不能轻描淡写的处理。首先社会效果不好,会导致与其有类似心态的孩子会放任成型,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其次未成年人的矫正不可能一蹴而就,时间漫长,需要长时间的矫正和强制。
实际上,由于独身子女从小受到长辈的溺爱,缺乏必要的教育引导,形成了较为自我,追求享受的人格,大部分的未成年人是非观念和法制意识非常淡泊。所以在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置问题上,更要提倡“以教代刑”,以期在萌芽阶段将孩子的思想观念端正起来,为其今后立足社会独立生活做准备。例如,安排有针对性的关护帮教和亲子教育。首先由司法人员,在接受公安机关的移送之后,了解其家庭教育和是非观念上的主观恶性程度,对其行为有一个研判。如果是偶发的或者事出有因,就对其关护教育,毕竟人总会犯错,应该帮助孩子及时把问题解决。如果是成长环境过程中,形成的心理或者行为习惯上的由家庭教育带来的问题,那么不仅要进行关护帮教,还要进行亲子教育和亲亲教育,也就是对其父母的教育和对家庭环境的改善。这类工作就要委托相关部门进行,例如妇联、社工组织。现如今,由于每一个人主观恶性形成的时间长短和形成原因的不同,成效也是良莠不齐,很难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模式来进行。一些孩子往往在先行的较为宽松的帮教之时,未能起到明显的效果,因为毕竟贪玩和从小形成的行为习惯,身边的朋友圈子,往往要受到更大的挫折和教训,才能够恍然大悟,对于有所悔悟的未成年人乃至其父母,司法机关都会通过协作组织,让孩子受到正确的引导,例如上海市妇联的大树长成计划,对行为人乃至其家庭进行一对一的帮助,并进行跟踪帮教,争取树立起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念。
二、国外对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处遇机制
日本在司法领域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同样,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处遇问题上,也经历过重重探索和重大变革。1984年,日本从实体层面将“刑事处分优先主义”彻底修正为“保护处分优先主义”,同时从程序层面将“检察官先议主义”修正为“家庭法院先议主义”。在保护处分优先的前提下,日本实际上是以家庭法院为中心。家庭法院为中心的一大亮点在于其能够以家庭法院为主导,实行调查官制度,进行科学调查。家庭法院配置了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调查官对少年的犯罪事实,成长环境,性格、再犯危险性,矫正可能性等展开全面调查,从而可以协助法官作出适合教育和矫正少年的处分决定。此外,调查官在调查过程中还会对少年采取多种保护措施,以此调整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避免未成年人转变为受害人。
三、对未成年人案件处遇的合理期待
日本处理少年案件的科学调查和各项对应的保护措施,恰恰是我国现在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处理体系中的一大弊病。在我国,没有专业化的团队来对未成年实施社会调查。曾经在公检法系统中倡导过专门成立针对未成年人的专案部门,但是因为收案数量少,团队不专业化,而开始走向下坡路,渐渐形成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在刑罚处罚上的特殊规定,依旧未走出刑罚中心主义的圈子。而日本能够让家事法庭大行其道的根基就在于有这样配套的团队做好前期的科学调查,做到后期在对未成年人教育和引导的时候能够对症下药,在未成年人的案子上能够将矫治前置,只有真正达到一定的恶劣程度,才将其列入原始的司法程序。所以,笔者认为就日本家事法院中对犯罪人的调查官制度是可以适当引进的。
在多方向了解政策之下,结合成熟案例,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方式:
(一)加强开展预防工作
从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调研基础来看,大多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目的并不在于故意触犯法律,只是一种宣泄,一种暴力,是对于法律的一种无知,法制意识的薄弱,所以相对于后期的矫正引导,前期的预防工作的完善可以避免更多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学校法制教育课程对问题未成年人缺乏前期预防和教育矫治措施,对未成年人缺乏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学校在“育人”这一点还没有发挥主要功效。可以加强司法机关和学校的合作,设置一个更为专业的未成年人普法宣传课程,深入课堂,深入社区。专门人员对办理的案件进行总结,提取经典案例,以案释法,学校配合将此类课程加入到学校的基础课程,以期引起学生和家长的重视,在潜移默化之中,降低犯案率。专门人员进行的每一次预防工作,要接受教育单位的反馈,做好沟通工作。
(二)设立“一条龙”式的专门机构
针对未成年人,从其前期违法行为到后期犯罪行为,由机构中不同的部门进行参与干预和处置,将部门整合的好处在于可以便于案件的移交和对对象的重点关注。眼下的工读学校,强调以“教代罚”,禁止对未成年人施以强制措施,往往对于其行为的矫正收效甚微。那么这一机构的存在结合了司法强制力和引导教育的功能,在教育的基础上授予司法强制力,往往会事半功倍。但是对于该部门的监督力度也应跟上,从立法到监督,其职权范围都应该明确,针对什么程度的违法行为有哪些相应的措施都要作为公开信息公告给社会。
(三)提高办案人员的专业性
就办案人员而言,无论内陆或者沿海,犯罪率高还是低,其专业程度相较于其他专案人才应该更为全面。除了专业的知识技能的培训之外,还应该加强对于心理学、社会学等社科学科的培训,以确保在办案人员面对受引导对象是专业的,全面的。这有利于涉罪少年的教育矫治,与少年无障碍沟通交流,有利于开展犯罪预防工作。
我国未成年人的工作一直在发展,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它的脚步肯定是一直往前的,不可能后退,也不会中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部门都在改革中努力寻求一条适合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案件的道路。笔者也将以此作为研究起点,对我国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体系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不断的学习和研究,希望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日]河村博,编著.少年法(第2版)[M].东京法令出版,2015.
[2]玛格丽特·K.森海姆,等编,高维简,译.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M].商务印书馆,2008.
[3]姚建龙,著.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4]岳慧青.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未成年人检察体制改革[N].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1).
[5]李鹏,龙潭,黄亚烨.低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的预防与矫治[N].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1).
[6]路琦,牛凯,刘慧娟,王志超.2014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基于行为规范量化表的分析[N].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