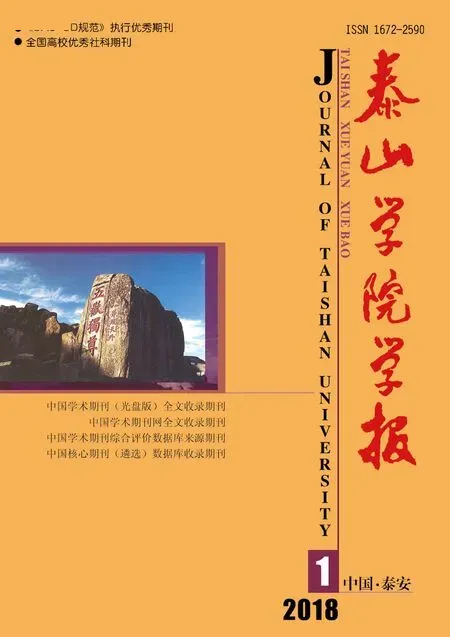穿越时间的荒野
——独孤食肉兽词的一种文本细读
莫 真 宝
(中华诗词研究院 学术部,北京 100101)
传统词在叙述事件或讲述故事时,往往营造相对清晰的时空结构,事件在比较容易把握的时空中展开,读者循此即可领会词人所述之事、所写之景,以及所抒之情。即便叙述梦境,梦里梦外,亦自然分明,毫不相犯。然时至今日,词之议论沸反盈天、叙事渐趋式微之际,独孤食肉兽却多填长调,不仅注重叙事,而且长期浸淫于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以及电影艺术,不厌其烦地将西方小说与影视叙事之法横向移植到词之创作中,他的词亦往往大炫其叙事之技,极大地拓展了词文体的时空表现能力。本文尝试从其颠覆传统词叙事时空的角度,就其叙事结构姑妄言之,以期为我们了解当代词文体新变之一助。
一
独孤食肉兽在2001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中,即自称所作为“后现代格律诗词”,后来又在网络结集的《食蟹集:开启现代城市诗词创作的筚路蓝缕之什》的序言等文章中,力主“现代城市诗词”,并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姑且把此类与传统词叙事迥异的词作命名为“后现代叙事词”。《念奴娇·你的故乡》的时空结构,便是这类“后现代叙事词”的一个典型。词曰:
常于梦里,行走在、无数陌生城市。某夜秋风深似水,来坐火车看你。绿月分衢,紫藤流壁,灯蘸帘波碎。镜花一侧,女婴睡靥恬美。同住春伞江南,婷婷出落,烟雨人间世。只待那年萤夏末,伴我蓝桥听水。此岸游踪,殊方归侣,邂逅真无悔。荒原遗轨,不知前客归未。
这是一首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爱情题材词作。开篇“常于梦里,行走在、无数陌生城市”两句,破空而来,没有具体时间坐标,套用英语语法的时态而言,是过去时、过去进行时,还是过去完成时?均不得而知。“某夜秋风深似水,来坐火车看你”两句所叙情事,和“行走在、陌生城市”一样,仍在梦里发生,从中可知,“看你”的人应当是“我”——整首词的叙事者。其叙述的时间点,为理解全词脉络之关键。然而,“某夜”,既非“今夜”,亦非“昨夜”,甚至亦非“明夜”,也可能是“今夜”,或“昨夜”,甚至“明夜”,时间点甚不分明。
好在作品随后借助空间转换,对时间作了“交待”,“绿月分衢,紫藤流壁,灯蘸帘波碎。镜花一侧,女婴睡靥恬美”数句,写“我”乘坐一列没有时间起点的火车,在某个秋风萧瑟的夜晚,走过“无生陌生城市”,终于到达某座城市。到达之后,便穿过铺满绿色月光的街道,逾越爬满紫藤的墙垣,熟门熟路地潜入一间婴儿房,默立“镜花一侧”,凝视一个“睡靥甜美”的“女婴”——“你”。“女婴”二字,对于理解此词叙事脉络至为重要,原来,就时间而言,“我”乘坐的是一辆逆向行驶的火车,火车从开篇即已完成时空穿越,载着“我”来到“某夜”之前很多年的“你的故乡”,并找到婴孩时代的“你”。由此可知,“某夜”,可为“今夜”,“昨夜”,甚至“明夜”,它实际上只是作者叙述事件的一个时间参照,具体指的何时并不重要。因此,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流动的时间,只是为了写足“常于梦里”这样一个反复发生着的事实。
一般而言,梦中的时间颠三倒四,难以确指,但古人词中写梦,往往一笔带过,梦与现实的时间界限交待清晰。晏几道《鹧鸪天》所谓“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其实他的“梦魂”有一个确定的指向,那就是指向过去。独孤食肉兽词中的时间,往往在过去与现在,甚至将来之间自由地切换,频繁地跳动,因而具有强烈的玄幻色彩。如《念奴娇·红毹纪梦:7月24日的天河机场》开篇写道:“透明街道,白飞机、方挽彩霞齐步。我以旧瞳镶子睑,回眺平窗云浦。天漆蓝屏,地趱金线,纸折千宫竖。”恋人“方挽彩霞”,我的“旧瞳”便在多年以后潜入她的眼睑之中,与她“一道”观赏舱外的茫茫云海、昊昊蓝天,以及金色地平线和飞机下降过程中所见次第竖起的城市建筑。此词甫一开篇,便抽掉了讲述者的时间坐标。又如《齐天乐·过期时刻表里那些经过武汉的火车》开篇“长烟又挟飙轮去,他年梦程携侣”、《洞仙歌·默片》过片“过期航线里,目选千城,经纬奔流熠心脉。探迷宫万镜,共未来人,浸蓝宇、梦驿轻于宝石”等,无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打成一片。
回过头来看这首《念奴娇》,“绿月分衢”三句,摹状“我”进入房间之前路上所见,以及此婴儿房外房内之布景,营造的“梦境”颇为迷离恍惚。“镜花”二句,为“我”穿越到过去时所见“你”婴儿时代酣睡的样子。“镜花”既可视为婴儿房中的布景,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月镜花”的成语,从而传递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空幻之感。
过片“同住春伞江南,婷婷出落,烟雨人间世”三句,承前,写“我”在梦中回到“你”的过去,眼看着你慢慢长大。这里叙述的是摇篮中的“你”在过去完成进行时态中,在这烟雨人间婷婷成长,唯此期间,与同住江南的“我”尚素昧平生,未曾在现实中相逢。而“同住春伞江南”的表述,又似乎从梦境回到了现实之中的情形。至于这是“我”在“现在”梦境中的陈述,还是在梦外所作的时间推衍,在类似博尔赫斯所营造的小径交叉的时空花园中,固无可解释,亦不必解释。
接下来,“只待那年萤夏末,伴我蓝桥听水”两句,其中的“待”字,则大抵相当于英文would,而不是will。盖“你”、“我”于萤火飞舞的夏末之夜,同倚蓝桥之事,在此词的大语境中,已然成为过去时。如果彼此不曾一同凭椅蓝桥,静听流水淙淙,则“我”无从“穿越无数城市”,同时穿越时间隧道去凝视幼小时的“你”。倘作更加马尔克斯式的解读,则以之为纯虚拟语态亦未尝不可——在多元不居的时空维度中,“伴我蓝桥听水”,未必是过去将来时中铁定发生过的事件。故而“只待那年”四字,同样没有时间坐标,它近乎马尔克斯名著《百年孤独》开卷破空而来的那句“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只待”二字所指,系梦中见到女婴尚在恬睡,尚在襁褓之中,“那年”,亦即多年以后,她出落成的婷婷玉立的少女,与“我”相恋,则“蓝桥听水”固然为将来时;而在梦外,因“你”共“我”蓝桥听水以后,已经远走殊方,“那年”亦即多年以前,又似为过去时。
接下来,“此岸游踪,殊方归侣,邂逅真无悔”三句,直接跳过“本应”即将到来的“伴我蓝桥听水”的场景与感受,却突然说到对往昔邂逅的无怨无悔,这是梦中的誓语,还是“梦外音”?也难以确指。“殊方”与“此岸”相对,指远方或异域。此三句若置诸开篇,而续以“常于梦里,行走在、无数陌生城市”的回忆,奠定全篇叙事与抒情的基调,或与传统线性叙事手法略相仿佛。词中却跳过了本应铺排的往事,接以如此斩钉截铁般的誓语。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期待“你”的回归,对“你”已离开的现实仍不接受,对“你”可能的回归仍心存幻想。煞拍“荒原遗轨,不知前客归未”,即表达出这种心态。此二句貌似遥应开篇——梦的火车应该返程了吧?则前句“邂逅真无悔”,差可算破梦之言。然荒原遗轨,复暗示此梦似无尽时,“我”一直在乘火车追寻“你”,直至车轨芜废、地老天荒。“荒原遗轨”,究竟是虚拟语态中不确定的未来场景,抑或“我”于此时此地所亲见的场景,文本未能做出交待。但在字面上,茫无边际的荒原之上,遗留下长长的铁轨,正如其《采桑子·雨站》所云:“十年汽笛声何处,终点灯昏。起点灯昏。双轨长长如泪痕。”如此凄凉之景,显然触目可及。而词中却据此兴问——不知梦中旅客归来没有——又产生一对矛盾:若“荒原遗轨”为实境,则此前“来坐火车看你”,乘坐火车訇隆前行,必为另一时空维度或前一时空维度中所发生之事,而于此维度中纯属子虚乌有;然其事既可问,则前客或可归,其梦或将醒,又似为此维度中之事。是耶非耶?全词至此,似跳脱于梦外,又复归于梦中。此前交叠嵌套而隐然可见的时空架构,至此轰然坍塌,复归于混沌。
二
古往今来,人在一定的时空里生活,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农耕时代,甚至早期工业时代,空间曾经是阻隔人们来往的鸿沟,“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古诗中的空间感具有难以抗拒的感染力量,但时至今日地球村的时代,空间已经不再是阻隔人们进行沟通的无可逾越的障碍了。从时间而言,虽然人类的平均寿命,较之古代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嵇康诗中“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的感慨,仍然困扰着现实中的每个人,尤其是比一般人更加多愁善感的诗人。任何人无法超越时间的限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说,独孤食肉兽的词有一个关注的焦点的话,那便是时间和空间。他的整个作品,集中表现了时间的错乱和空间的荒芜。与《念奴娇·你的故乡》相仿,独孤食肉兽在《贺新郎·平行时空中的火车》写道:
烟雨溶川陆。对浩荡、人间春暝,天涯同读。曾向季风通道里,镶嵌花光万幅。尽酬以、江南醇绿。遥夜远方诸城市,望梦程、原点齐围簇。中有我,旧瞳浴。秋晴极野樱云赎。约他生、春阑往驻,栈荒人独。满载蔚蓝原夏色,河外一星方烛。背深宇、其旋何速。锈火车头嘘谜霭,熠时门、叠启驱金轴。将执手,擘霞麓。
此词有个生造词“时门”,自注曰“时间之门”,词的时间意识于此可见一斑。全词仍以梦呓、隐喻为主,上阕显然是关于某段发生在“蔚蓝原夏”的恋情记忆,至过片,“秋晴极野樱云赎。约他生、春阑往驻,栈荒人独。”《百年孤独》的“多年以后”魔杖再度挥舞起来,只是此阕情境更为凄凉,纵然或有“他生”,亦难免依旧“栈荒人独”的荒凉之感。聊可慰者,“熠时门”以下,在另一影子星球或影子维度,“蔚蓝”的情感之旅已经再度重启、或正在进行,或在过去时态中复原并循环播映。开篇言“烟雨溶川陆。对浩荡、人间春暝,天涯同读”,隐喻此情不再、人间别久,末云“将执手,擘霞麓”,却又将前述“现在时态”中的情境轻轻推翻,一个“将”字,把想像中的“将来时”并入现实,如果还原成影像,是真是幻,孰真孰幻,不得而知。
独孤食肉兽词中的时空结构,复杂而无端,初看似乎几无脉络可循,若持传统词的叙事标准视之,则简直混乱不堪。细察之,则痕迹宛然。梦回过去,梦回童年,是其词的惯技。《木兰花慢·蝴蝶梦》小序云:“丁丑秋日梦回大堤口小学有作。”词曰:
石楼归旧梦,玉蝴蝶,熠阶除。瞰桃李芳园,领巾红飐,紫姹青初。回盱,拱弧叠嵌,割斜晖、相对稚龄予。多少幽廊过客,光阴异代同疏。窗隅,秉烛曳凉裾,修女又宵徂。正月苑萤流,儿时听此,门叟苍癯。荣枯,岂唯示我,觑遥灯、秋老汉阳鱼。一例华胥寓梦,觉来槐梦谁舒?
此词开篇“石楼归旧梦”,即揭示其梦回石楼——大堤口小学。上片云:“石楼归旧梦,玉蝴蝶,熠阶除。瞰桃李芳园,领巾红飐,紫姹青初。回盱,拱弧叠嵌,割斜晖、相对稚龄予。”“我”在“旧梦”中回到“石楼”,即作者当年就读的大堤口小学,闪光的“玉蝴蝶”照亮了校园的台阶。旧梦中的“我”踞于高楼一隅俯视“紫姹青初”的菁菁校园,校园里孩子们胸前的红领巾迎风飘展。“回盱,拱弧叠嵌,割斜晖、相对稚龄予”,回头不禁睁大了眼睛,因为目光越过大堤口小学(校舍曾为天主教堂)层层叠叠嵌套着的拱形屋顶,穿透投射到校舍墙面上的夕阳的馀辉,竟然意外地与就读小学时的“我”相遇了。梦中的“我”和读小学时的“我”四目相对的刹那,镜头在两个“我”之间来回闪动,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场面。“多少幽廊过客,光阴异代同疏”,不同时间段的人或不同时间段的“同一人”在幽暗的走廊上来来往往,彼此陌生,伤感之情溢于言表。而过片夜间秉烛摄衣巡夜的修女,到底是梦中所见,还是梦中听看门的老头讲述的故事?或竟是梦中见到儿时的自己,在漫长暑假的某一萤飞星流的夏夜,双手托腮,正凝神倾听看门老头讲述前朝的修女故事呢。
像这样将不同时间的人与物置于相同或相邻的空间里,表现了独孤食肉兽的独特嗜好,有多篇作品可证。早在1997年,其《西平乐·丁丑中秋前二日微雨夜酌悲情城市(SAD CITY)酒吧》过片即云:“百年红墅,酒调鸡尾,碟印狮徽,爵士谁听。挂暗壁、雕框旧影,细辫长衫,应是前朝人物,注目吧台,摄此靡靡诲往生。”此词有小序曰:“吧在黄兴路,壁上多挂清人照片,下阕因及之。”在这里,还只是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挂在墙上的清朝人照片以生命力,他们仿佛注视酒吧里呼酒买醉的人们,把酒客们的醉态“摄”入眼中,以作为过去的人的反面教材。
当作者发现了这样一种写法的妙处,就不断地强化它,自觉并自如地运用到创作之中。如《宝鼎·航行在1967年的一封家信》曰:“诸字携我归函,都未觉,卧而隐几。对少年(诗人大学时代的父亲)、如我清癯,透廊尘五纪。”一封作者的父亲在作者出生以前写就的家书,也成了魔法的演示者。作者读着这样一封家信,不知不觉中,“诸字携我归函”,“我”回到信函之中,“卧而隐几”(用《庄子·齐物论》“南郭子棊隐几而坐”典故),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我”居然穿越到50年前(五纪,50年,取其成数),在出生之前就和少年时代的父亲相遇了。再如《定风波·罗盘仪上透明的初见日》曰:“双罥钟楼南北月,互交灯语古今船。我亦透明无所觉。迎获。故人贻影叠凭栏。”月亮往还,照耀着高悬于钟楼之上的江关的钟,表达的是时间流逝的沧桑,而“互交灯语古今船”就有点穿越的嫌疑:今天的船怎么能和古代的船“互交灯语”呢?这些,只能存在于作者的意念之中。在古今船只“互交灯语”的同时,“我亦透明无所觉”,因为“我”是“透明”的,古今船只上的人对我无所察觉,“故人”自然也察觉不到“我”的存在,而我迎面所见到的,自然也不是真实的“故人”,而是故人往昔遗留在栏干上的一个接一个身影。此句的表现手法,仿佛电视《天龙八部》中表现段誉“凌波微步”的系列镜头。
这种“穿越”的写法,独孤食肉兽在诗作中也偶有运用。如古风《诸客》中的“维我凭轩听雨时,是渠(她)剪纸收灯处。”“昔人时人满黉廊,各若茕行无所睹。顾我而笑岂非子,唇花湿靥穿身去。”亦如上述词作一样,皆刻画不同时间的人穿越到同一空间,融融共处。这与传统词或白描、或铺叙、或勾勒的叙事方式迥异其趣,可以称之为“渲染”。
三
倘若想透过文字理解独孤食肉兽词中的这种“穿越”手法构造的时空迷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阅读古代词作,没有提供这样一种经验。这种“渲染”的手法虽然在传统词作甚至当今其他人的词作中未曾有意运用,或者说绝少运用,但在小说和电影等其他艺术门中,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小说无论,电影语言是独孤食肉兽最常使用的手法,以便体现其词叙事产生的“超现实”艺术效果。独孤食肉兽词中的电影语言运用非止一端,此处仅举数例,略作说明。如《莺啼序·武汉会战》曰:
行军地图展处,竞川峦骤立。共江面、舰飏丸旗,蜂訇云腹如席。捋汉上、塔楼攒动,霓虹世界钟涟画。漫昭和宫榻香凝,奏折幽觌。行辕所在,街垒相望,更高关雄扼。奥斯汀、尾曳蓝烟,遄驰梧下坊陌。发报机、键音坎坎,汇深宇、电波汩汩。拭伤员、有女如花,镜头堪饰。绀纱飘袅,眉染岚光,瓷牙谁与摘。注瞳井、延河迤逦,巨手挥斥,金粟江南,红窑陕北。抽刀兑雪,抡枪织焰,八千子弟方鏖战,蹈敌群、荷弹人如漆。蓝星遽转,街传《时代周刊》,女神擎炬而泣。机枰敬礼,裘氅牵风,向天涯望极。念此别、雨遮深峡,灯糁悬城,万里河山,百年家国。老斋舍外,笼萤秋语,粉题准拟春事早,赋新俳、月到樱花驿。陆沉争忍相仍,大夜惊湍,四鸣汽笛。
这首《莺啼序》写武汉会战,地点却分别涉及武汉外围沦陷区、汉口租界、东京倭皇皇宫、汉口滨江、武昌珞珈山、延安-南泥湾、武汉江防某处战场、纽约华尔街-哈德逊河口、汉口机场、峡江-重庆、武汉大学樱花大道。时间跨度从“行辕所在”的1938年夏延及“月到樱花驿”的1939年春。人物包括展观地图的日军军曹、幽觌奏折的倭皇裕仁、国军伤员、国军护士、蒋介石(第二、三片两度出场)、毛泽东、拼刺刀及互相射击的双方士兵、荷弹冲向敌军的国军烈士、日本艺伎等多人。人物繁复多变,叙事错综复杂,透过文字联想,殊难理解,如果把词中人事场景,视作一个个电影镜头,则不难发现,这些复杂的人事,却被电影镜头有序地组织在一起了。
其叙述手法深受电影转场效果的影响,所谓转场效果,一般是指两个场景(即两段素材)之间,采用一定的技巧如划像、叠变、卷页等,实现场景或情节之间的平滑过渡,或达到丰富画面吸引观众的效果。此词数处运用典型的3D暨蒙太奇及相关手法,打破了传统词的叙事常规,突显了文字表达影像的魔力。如“行军地图展处,竞川峦骤立”,以动态3D镜象开篇:随着行军地图的缓缓展开,氤氲出一片奇丽的图景,雄矗的山岳与奔腾的长江竞相从地图上立起。使读者仿佛从中看到无数川峦,从行军地图的二维平面上经3D摄影技术进行立体转换,而成为三维实景。其后,陆空远景全面展开:“共江面、舰飏丸旗,蜂訇云腹如席。”日本军舰斜挂“膏药旗”趾高气扬溯长江西上,与之偕行的蜂群喻象,则生动再现了日军机群在“如席”的云空之下来势汹汹的场景。上述描写,由近景拉开,复由高远处逼近,纯用镜头语言呈现出敌军从水路和空中同时夹击武汉的紧迫形势。“捋汉上、塔楼攒动”,再一次运用超现实3D摄影技术特写,强化日本侵略者对武汉的武装进犯:展玩地图的侵略者用笔尖、手指楔入并捋弄武汉的楼台、街道,令模型般的城市建筑悸动不已。至此,会战争夺地武汉,以全景形式初步呈现于读者面前。叙事至此,“按理”便应描写正面战场了,然而出乎读者意料的是,随后的画面却由喧而静,直接切换至万里之外的东京:“漫昭和宫榻香凝,奏折幽觌。”倭皇身形佝偻猥琐,在幽暗的宫中,窸窸窣窣地翻阅报道武汉战况的奏折。首阕即运用多种蒙太奇手法,通过镜头的拼接与转换,在广阔的时空之维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波澜起伏,动静相生。
此词还运用了长镜头等其他的电影手法。如“奥斯汀、尾曳蓝烟,遄驰梧下坊陌”。此二句写一辆不知其来何自、其往何处、所载何人、所藏何物的小轿车在汉口租界浓密的法国梧桐下穿坊走巷,颠簸疾驰,如被一台隐藏在沿街商铺或民房高处的移动摄影机连续追拍,这是此词中甚为突出的“长镜头”手法。这辆被刻意点明品牌并“尾曳蓝烟”的小轿车特写,也成为广角镜头景深中颇为惹眼的一个细部构件,展现了作者体物之细。又如“绀纱飘袅,眉染岚光,瓷牙谁与摘”,是半山庐内的蒋介石面部特写。“注瞳井、延河迤逦”,延河倒映着宝塔山等娴美意象注入蒋介石黯然如井的眼瞳,镜头亦由此切换至有“陕北的好江南”之称的南泥湾,和灯火浓暖的红窑洞。“金粟江南,红窑陕北。抽刀兑雪,抡枪织焰”,前两句写延安敌后根据地,后两句续写武汉正面战场,镜头陡切,不作任何交待与铺垫,是电影叙事常法。再如“蓝星遽转”,是太空摄影的视角,蓝色星球遽然旋至另一面,镜头亦由悲壮的武汉战场切换至繁华的美国都市纽约。从镜头叙事来看,细节聚焦与广角摄影层见错出,令人目不暇给,将电影叙事手法运用到了极致。
独孤食肉兽也许是担心读者读不懂他词中的电影手法,甚至有时不惜花费笔墨,直接告诉他的读者。如《莺啼序·武汉会战》中即有“拭伤员、有女如花,镜头堪饰”的交待,说这里需要有一个特写镜头,表现女护士们为伤兵擦拭和包扎伤口的细节。又如《水调歌头·湖南的原野》上片云:“烟月三湘境,每过客心溶。车窗旋作屏幕,暖绿小城浓。谁坐空厅凝盼,你在广场旋转,成长趁春风。划靥远灯白,初雪待铺绒。”词作讲述自己每一次坐火车经过湖南,想起曾经的恋人,情绪难以自持。“车窗旋作屏幕”云云,告诉读者,下文“暖绿小城浓”的环境以及“空厅凝盼”“广场旋转”的那个“谁”,不过是自己的幻觉投射于车窗上的影像画面。而“划靥”二句,因车窗外的灯光掠过旅客们的面庞,把我从幻觉中拉了回来,令“我”看清窗外是寒冷的雪夜的现实。“暖绿”“春风”“初雪”组成的真幻交织的世界,强烈的冷暖色调的“粗暴”组合,体现出内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实际上,这里有两层影像,一层影像,是“我”在车窗上“看到”的影像,一层是读者从词中“看到”的一位孤单旅人乘车远行、倚窗凝视的影像。旅人所见是影视中人物的幻觉,读者所见才是电影中的“真实”场景。
早期西蜀和南唐词人叙事,多运用简单的白描手法,往往将词中的时空局限于一个特写的场景,如韦庄、李煜常常如此。柳永大量填写与创制长调,发展了词中铺叙手法,其《雨霖铃》《八声甘州》所呈现的时空转换,常常由领字领起,层次清晰。周邦彦的“赋化之词”(叶嘉莹语),因多将叙述具体事件与抽象抒情融为一体,甚至有时以典故代替叙事,惟恐读者不明白,故多用“勾勒”之法,以示其叙事脉络。前此皆为传统词的惯技。独孤食肉兽早年的词,也多作花间南唐派头,不烦赘述。及至本世纪初以来,不仅多作宜于叙事的长调,从叙事手法而言,却与柳永擅长的“铺叙”、周邦彦擅长的“勾勒”不同,如前所述,他的运用电影语言的词,可称之为“渲染”,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其实,即使小令和中调,独孤食肉兽往往也能写出电影大片的效果。如《河满子·梦后》云:
谁在无星之夜,独留未阖之睛。荒墅间呈雷雨里,古帘带落青瓶。一片键光明灭,钢琴自响空厅。昨日长廊幽邃,重门随过随扃。若有素衣人秉烛,肃然导我前行。最是百年伤感,觉来无物关情。
这首词于醒后叙写梦境,梦中情景,并不局限于某人某事,而是大开大阖。上片像极电影大片的序幕,首先是广角镜:在移动着的广袤而又黑暗的夜空之中,一双眼睛不时地放射出如炬的光芒。接下来是由外而内的特写:抛荒的别墅在雨夜中随着一次次闪电逐渐呈现于荧幕之上,在闪电营造的转场效果中隐含了时间回溯,荒墅离观众越来越近,逐渐呈现生机。镜头拉近,开始“拍摄”室内镜头:一片眩人眼目的光影与撼人心魄的音响互相交织,“古帘”与前文的“荒墅”相匹配,“古帘带落青瓶”,强化雷电风雨之夜的外部环境之于室内的影响。“键光明灭,钢琴自响”的场景,这种“超现实”的词境,则非摄像机难以实现。过片“昨日”两句,镜头扫过幽邃长廊并聚集于次第开合的重门,重门合上的音响效果,必然不断变化,或重或轻,或“吱吱”或“咣当”,或许同时还伴了细碎的脚步声。梦中情景,当然有童年的影子,“若有素衣人秉烛”两句,“素衣人”,身穿白色教服的修女,其中即隐含了作者童年的生活环境——设立在天主教堂的大堤口小学——以及所受宗教情怀的影响。然而,这两句并非童年往事的重现,而是运用“写意”手法,若隐若现的白衣修女,引导童年的“我”渐至少年、青年的“我”肃然前行,二者既是在有形的长廊与重门之间穿行,也是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穿行。“重门随过随扃”,走过一扇门,随即关上一扇门,寄寓了难以言说的人生感慨。直到歇拍“最是”两句,“讲述人”——“我”才开始直接抒情,却令人疑窦丛生:他为什么往事梦中萦怀,如此伤感,醒来却“无物关情”呢?“百年伤感”,是伤感时间流逝还是世事无常?词人故意卖了个关子,就戛然而止了。电影镜头,最多也只能表现主人公伤心欲绝的表情,除非借助画外音,不能表现更多的细节。
独孤食肉兽不仅熟谙诗歌传统,而且醉心于西方哲学与艺术。他在《念奴娇·千禧前最后的意象》中写道:“达利、庄周,恍然皆我,午梦三微秒。石榴血溅,花间蝴蝶尖叫。”又有《水调歌头·自2015年4月送别1979年3月的Tomas Transtrmer》等词,直接“招供”了这种渊源。此词小序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他“最敬慕的诗人(不分古今中外,没有之一)”,并自注道:
“岸浸波罗的,瑞典味储咸”曰:“特翁作品两大译者之一李笠(另一为北岛):‘瑞典的味道是咸的,因为它全身浸泡在波罗的海里。’在神交特翁后,我才真正认识到瑞典学院一位前委员的卓识,诗歌是超越翻译的。不唯如此,它复如特翁如下诗作所言(引者按,指特翁诗《自1979年3月》),超越其文本、语言本体,它并非如前人言之凿凿是翻译中损失的那部分。”
在独孤食肉兽看来,他正是领会了特翁诗歌“翻译中损失的那部分”,而彻底接受了特翁的影响。他的词小到化用西方诗歌、小说的成句,以之为语典,大到借鉴其写法,向西方艺术的取法可谓无处不在。综观前文所举《故乡的你》及相关作品,他的词所呈现出的貌似时间错乱与空间荒凉之感,实则并非不可厘清,即使终究未能全部厘清,实则并非不可理解。持此以为钥匙,解读独孤食肉兽诸多此类万花筒般的长调,如《澡兰香·你的城市》《念奴娇·红毹纪梦:7月24日的天河机场》《念奴娇·校庆百廿年的W大学》,等等,对于一窥其词叙事时所构造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时空,或许不无助益。
[参考文献]
[1]曾峥.格律摇滚Y2K[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