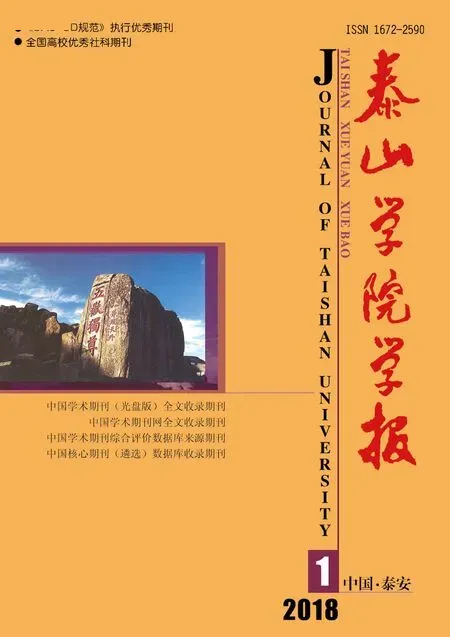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二题
闵定庆,张 洲
(1.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产业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5)
2000年2月,章士钊女章含之主编的十卷本《章士钊全集》由文汇出版社正式出版,收录了《甲寅杂志存稿》《中等国文法》《长沙章氏丛稿》《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等专著及散篇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书信、电文、启事、题词等,多达460万字,可谓洋洋大观。但是,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阙而未收,实为憾事。2009年,岳麓书社将陈书良编校的《章士钊诗词集》与胡如虹编校的《程潜诗集》,合为一册刊行,也未收章氏《论近代诗家绝句》,细味整理前言所云当是“未见”之故。[1](P5)众所周知,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曾以三种文献形态流行于世,或是短暂连载于《京沪周刊》,或是全文刊登在《江海学刊》上,或是部分诗篇附丽于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无论以何种文献形式出现,都与汪辟疆《点将录》存着一定的关系。这也有助于考证章诗的创作时间,探讨其所咏对象与汪录范围的内在关联性。
一、《论近代诗家绝句》的写作时间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跋》云:
章士钊在渝时,从余索缮本去,又就其师友所知者,各为绝句若干首。惟旨在论人,不在论诗。其原诗附以小注,尤多诗人故实,正与余诗相发,遂亦附入。[2](P784)
此跋署“甲申十一月记于重庆西里覃家小湾”,即1944年。汪跋明言将章诗附入定本的过程。据此可以肯定,章诗写作时间应略早于这个时间。1945年6月,汪辟疆在日寇将降的喜悦中,重新修订了一个“合校本”,署名“铁棒栾廷玉”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赞语有这样一段话:
及避寇居渝州,行严、旭初偶谈及此,乃取藏箧原稿覆按之,觉有原稿合而刊本不合者,亦有刊本漏略而进本宜补入者。寇锋日挫,受降匪远,心境恬适。一夕,被酒初醒,乃援笔逐一厘定,并各系赞语,或论人,或论诗,遇感辄书,难以例范。[2](P61)
文末署“乙酉六月”,即1945年。对此,程千帆《〈汪辟疆文集〉后记》也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交待:
《光宣诗坛点将录》初稿是汪老师1919年在南昌写的,今天已不可见。1925年,作了一些修改,连载在《甲寅》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1934年到1935年,《青鹤》第三卷第2期到第7期,又刊登了一次。除序文中删去章行严先生曾索此稿刊之《甲寅》这一记载外,两本全同。1944、1945年,老师在重庆,对《甲寅》本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写成定本,另外还写了一篇定本跋。十年浩劫中,定本被毁,跋文以有副本,幸得保存。所以在我整理老师的这部遗作时,它便成了工作条例。按照老师的设想,这部点将录在每位诗人名下有如下几个组成部分:赞、诗、评、杂记、小传,然后附录章行严先生的《论近代诗家绝句》。各项不求全备,可以缺少;每项不定一条,可以增减。(如或有赞无诗,或有诗无赞,或赞后又有赞,或二人合一赞。)其他各项也是如此。有一作,有附见。[3](1061)
这里谈到了汪辟疆先生《点将录》定本的几个有机组成部分,章诗虽是最后一道工序,但凡有则必录,同时补写注释若干,因此,章诗附入的时间应在作跋之前,而收到章诗则至少应在定本写定工作启动之时。照此推算,章诗完成的时间应在1944年10月。
程千帆《〈论近代诗家绝句〉跋》亦云:
先师汪辟疆先生早岁所为《光宣诗坛点将录》,虽一时兴到诙谐之作,然其辩之博而论之精,阐述近世诗学流派者,未能或之先也。长沙章行严先生读而善之,为刊诸《甲寅》,遂以流布。抗日战争中,先师与章先生违难入蜀,同客渝州。虽时际艰虞,而不废讲艺。先师既取《点将录》重加厘定,章先生亦别撰《论近代诗家绝句》百余首,间加小注,明其故实,以为桴鼓之应,而先师复增注焉。[4]
显然,汪辟疆对《点将录》重加厘定的工作与章士钊的吟咏有着一定的关联性。章诗的创作,看似亦如汪录一般,为一时兴到之作,实则蕴涵了一个漫长的心灵互动过程。1925年,汪录首次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五至九号上连载,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后又于1935年连载于《青鹤》第三卷第二至七期。抗战时期,汪辟疆随中央大学迁重庆,时与章士钊、汪东从容论学,激发了继续修改、写定的决心。①章士钊索阅《光宣诗坛点将录》缮本,“就其师友所知者,各为绝句若干首”,以为“桴鼓之应”。由此可见,章诗应作于1944年7月以前的一段日子。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章诗文本内发掘出有关记述,对其具体写作时间作更深入一步的探究。
例如,“谢无量二首”其二“麟凤郊游四十年”句,自注言赵启霖督蜀学,于南门外立祠,内设存古学堂,以谢无量任其事,时年不过二十五、六而已。章诗所谓“四十年”,非指谢无量任建祠堂事,而应从1901年谢、章二人订交算起,至今已过四十年。这应该是一个约指之数,但至少可以划定一个较为明确的写作时间,即在1941年以后。
又如,“于右任三首”自注:“君初出峡,沿途题《一剪梅》词,哀感顽艳,时流敛手。吾与汪旭初曾在重庆见其九稿,闻为西安故人所存,浸忘之矣,屋被炸后始发见。”此诗是于右任1941年底巡视西北之后带回重庆的,可知此诗所忆欣赏词稿之事至少是发生在1942年春天。
又如,章诗“赵尧生三首”其二自注:“四年前,君到渝,对称诗者以高格、正宗、古韵、雅言相标榜。曾履川请示有清诗家谁为第一,君曰:‘袁枚。’”按王仲镛《赵熙年谱》“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条:“(赵熙)应江庸、曹经沅之请,前往重庆北碚修禊。上巳,到北泉,下榻数帆楼。来者十余人,以《兰亭序》分韵赋诗,独不与。值陈铭枢请见合影。程潜偕章士钊方叔章后至,会已散,仍分韵有作。上巳后,移居上清寺,程、章及于右任、周钟岳等俱来访,邀请宴集。”数日后,赵熙见过蒋介石、孔祥熙即行返乡。[5](P1322)以“四年前”云云算来,当是1944年。
又如,章诗“程伯翰子大三首”其三自注:“沈祖棻为程氏妇,其门人已刊《风雨同声集》词稿。”此《风雨同声集》系沈祖棻门人词集,1944年7月初版刊于四川成都,沈祖棻序则作于六月天中节(25日日)。程千帆笺曰:“杨国权,四川綦江人,金陵大学国文专修科毕业,词笔清丽。尝与同学池锡胤、崔致学、卢兆显合刊《风雨同声集》,内收杨生《苾馨词》三十六首、池生《镂香词》二十五首、崔生《寻梦词》三十一首,卢生《风雨楼词》三十六首,祖棻为之序”,“章行严见而赏之,其《论近代诗家绝句》有云:‘大邦盈数合氤氲,门下门生尽有文。新得芙蓉开别派,同声风雨已堪闻。’自注云:‘沈祖棻为程氏妇,其门人已刊《风雨同声集》词稿。’”[6](P124)则知此“程伯翰子大三首”定作于《风雨同声集》刊行之后,也就是1944年7月之后。这至少可从内证的层面证明这个时间节点是在《论近代诗家绝句》创作的过程之内的。
上述四诗所涉及的史实,呈现了一个逐步缩小时间范围的推进过程,虽无法考知其开始写作的切确时间,但至少可以据此将定稿的时间确定在《风雨同声集》出版的1944年7月之后、汪辟疆撰写定本跋的1944年11月之前。由此可见,程千帆《〈汪辟疆文集〉后记》所言1944、1945年间,应是指写作《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的时间,不可与《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及章诗的写作时间混淆。
二、章诗所咏对象与汪录范围之间的关系
有论者认为章诗完全附丽于汪录,其所吟咏的人物全在汪录范围之内。但是,细品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跋》,似无此意。汪跋云:“章士钊在渝时,从余索缮本去,又就其师友所知者,各为绝句若干首。惟旨在论人,不在论诗。其原诗附以小注,尤多诗人故实。正与余诗相发,遂亦附入。”[2](P784)强调的是“就其师友所知者”,亦即章士钊自己所熟悉的近世诗家,也许有的在汪录内,也许有的会逸出汪录。
程千帆《〈汪辟疆文集〉后记》也进一步说明,按照汪辟疆的设想,在每位诗人名下有如下几个组成部分:赞、诗、评、杂记、小传,最后附录章诗。各项不求全备,可以缺少,每项不定一条,则可以增减。这一考虑,完全是基于史料多寡而定的。但从程千帆先生的行文上看,章诗之于汪录的依附性关系似乎不明显。程千帆在《江海学刊》本《论近代诗家绝句》跋语也说:
抗日战争中,先师与章先生违难入蜀,同客渝州,虽时际艰难,而不废讲艺。先师既取《点将录》重加厘定,章先生亦别撰《论近代诗家绝句》百余篇,间加小注,明其故实,以为桴鼓之应,而先师复增注焉。客岁,余为先师编定遗集,超伯大兄出章先生手稿见示,因悉取其所咏诸家见于《点将录》者附入之,俾相发明;然亦偶有章先生论及,而先师书中不之载者。[4]
所谓“别撰”显示出来的与汪录的关系,即为“明其故实,以为桴鼓之应”,但也“偶有”汪录所不曾论及的诗家,程跋对此现象未作进一步的说明。
通过对比《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三个不同点:
第一,从《江海学刊》所刊全文来看,章氏吟评的对象有自己的先后次序,并未遵循《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的次序,故未与汪录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第二,章诗与汪氏《点将录》大致一致而有所增补。章氏吟咏了一些汪录“一作”、“附见”的诗家,也吟咏了一些汪录未录的诗家,如蒯光典、汪辟疆等26人,同样是光绪、宣统至民国年间的代表性诗人,最后延伸到《点将录》的撰作者——汪辟疆先生,弥补汪录的不足。程千帆先生的增注主要是揭示某诗属谁,凸显“一作”、“附见”的延展性功能。
第三,章诗所咏对象及自注并未遵循汪录的论诗方向,而是基于阅读汪录时所激发的对于自己亲友的回忆进行的“激情写作”,故多侧重记事,同时也旁及词事,相对而言,论诗成分极少。因此,汪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激活回忆的感兴作用。这也直接导致汪辟疆对章诗做的注同样偏重于追忆往事,又使得《点将录》原有的诗学批评轨道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
总之,汪录、章诗、汪注、程案四者的延展与叠加,呈现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文本形态,整体的写作姿态随着每一个创作环节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论诗,发展到最后的记人,显然是由其内在的必然性所决定的。
章士钊吟咏的对象突出了师承、交游两个层面。首先,勾画了一幅“分布诗史”轮廓。“分布诗史”又曰“横向诗史”,即同一个历史阶段中各诗人的地位、分布和交游情况。如“周少朴中丞”条“七世将家三楚少”句再现了周树模、樊增祥、左绍佐“楚中三老”的往来唱和情景。三老均为退宦诗人,入民国后又均寓都下,文酒过从,一时称盛。这与陈衍所记“左笏卿兵备、周少朴抚部,皆常与仁先唱和者”非常符合。[7](P157)又“赵尧生”条“陈、杨都到西川去,善颂西川第一人”句,即言陈衍、杨增荦、赵熙同科及第,平生相契,暮年之时在赵的陪同下作峨眉之游。其次,近代诗人的师承渊源,突出了“横向诗史”应具的“纵向诗史”特点,能将同一诗派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流变情况彰显出来。如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未录夏寿田,《点将录》将其列入王闓运的“附见”,章诗“夏午诒”条“善爇王翁一瓣香,五言高浑跨潇湘”句,点明夏寿田为王湘绮徒弟,学行炳然,夙抱经世之才,但壮志难酬,晚年沦于深沉。由章诗可知,夏寿田亦属湖湘派,诗学六朝,五言尤善,晚年诗作禅意飘渺,是为湖湘派之变,但渊源仍是非常清晰的。
章诗吟咏的诗家,更与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相表里。章诗吟咏了近代诗人70人,计湖南籍12人、江苏籍9人、广东籍8人、浙江籍7人、江西籍7人、福建籍7人、安徽籍6人、湖北籍4人、四川籍4人、陕西籍3人,河北、河南、蒙古族各1人,可入《近代诗派与地域》所言近代六大诗派者,共计44人:
湖湘派。领袖:王闿运(诗坛旧头领)。羽翼:曾广钧、程颂万(入天罡,为诗坛中坚),陈锐(入地煞)。别子:樊增祥、易顺鼎(入天罡,为诗坛中坚)。桴鼓之应:文廷式(入天罡,为诗坛领袖及诗坛中坚),章炳麟、刘师培(入地煞)。此为光宣诗坛之旧派。
闽赣派。领袖:陈宝琛、郑孝胥、陈衍、陈三立(俱诗坛头领,为光宣诗坛领袖)。羽翼:沈瑜庆、林旭(入天罡,为诗坛中坚),李宣龚、夏敬观、桂念祖、胡朝梁(入地煞,为诗坛名家)。桴鼓之应:范当世、沈曾植、陈曾寿(俱入天罡,为诗坛中坚)。又鄂派:周树模(入天罡)。皖派:姚永概、吴保初、周达(入地煞,为诗坛名家)。此为光宣诗坛之正宗。
河北派。领袖:张之洞(入天罡,为诗坛中坚)。受熏化:吴观礼。(入地煞)。旗籍:三多(入地煞)。此为光宣诗坛之别派。
江左派。领袖:金和(入天罡,步军头领),李慈铭(入天罡,诗坛头领)。羽翼:朱铭盘、张謇、汪荣宝(入地煞,多马部军将校)。逸出:李详、俞明震、诸宗元(入地煞)。此为光宣诗坛之别派。
岭南派。领袖:康有为、黄遵宪(入天罡,为诗坛中坚)。羽翼:丁惠康、梁启超(入地煞)。同风会:谭嗣同(入地煞)。此亦光宣诗坛之别派。
西蜀派:赵熙(入天罡)。羽翼:林思进(入地煞)。此亦同光诗坛之别派。
由此可见,章诗虽为游戏兴到之作,但在体现近代地域性诗派方面,确实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说服力。
综上所述,章诗与汪录确实存在着很密切的关联性,但绝非一一对应关系,更不是一个依附性的关系。在章士钊的笔下,汪录庞大的结构所绘就的一幅巨大的诗史画卷,形成一个激发其人生回忆、刺激创作灵感的机制。章诗进而从亲历者的角度出发,侧重描述了自己所知晓、相交的诗家,通过诗意化的记忆,再现其生平事迹与诗词创作,为汪录所描画的近代诗坛画卷补上一幅幅“亲历者”眼中的“个体影像”,具有较高的诗史价值和史料价值。
[注释]
①汪辟疆《复徐中玉书》:“世局扰攘,吾辈尚得以从容讲习,又当何可谓非天厚?”见张亚权编《汪辟疆诗学论集》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3页。
②按:赵启霖督蜀学,在宣统元年(1909)八月上任,次年三月辞职。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报告书》1910年4月15日“时报”部分“赵启霖辞职”条:“四川提学使赵启霖提请辞职。3月26日获准。据传其辞职原因是与总督意见不合。赵启霖乃直谏之臣,与江春霖、赵炳麟并称‘都察院三霖’。四年前因参与参劾段芝贵、抨击庆亲王而被罢免御史,但去年摄政王爱其人物,擢用为四川提学使。”见李少军编译《武昌起义前后在华日本人见闻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3页。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六“赵启霖赠诗”条:“湘潭赵芷生提学启霖,官御史,性刚直,以言事得罪去。余电趣还湘,请监督高等学堂。比过武昌,张文襄留主存古学堂讲席。文襄内召,芷生谢归,余坚请主高等学堂。未几,诏复原官,录简四川提学使。先后有赠余诗数章。芷生学行,在湘中士大夫当首屈一指,余所最心折者。一别十年,世变澒洞,乃至于此。录其诗,益不胜今昔之感云。诗凡五章。”又,谢无量《送赵芷荪侍御南归》,见赵启霖著、施明、刘志盛整理《赵瀞园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399页。
③刘长荣、何兴明《谢无量年谱》,《文教资料》2001年第3期。另,彭华《一代名流谢无量——生平志业、学术成就与蜀学因缘》:“1901年,谢无量与章太炎(1869-1936)、邹容(1885-1905)、章士钊(1881-1973)等交游,为名重一时的《苏报》《国民日日报》等撰稿。1903年7月(闰五月),《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章士钊被捕,谢无量积极撰文并想方设法营救。在章士钊出狱后,谢无量与之逃亡日本,在东京补习日文、英文、德文。”见《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陈书良,胡如虹.章士钊诗词集程潜诗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9.
[2]汪辟疆著,王培军笺.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汪辟疆著,程千帆整理.汪辟疆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程千帆.《论近代诗家绝句》跋[J].江海学刊,1985,(3)
[5]王仲镛.赵熙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1995.
[6]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陈衍.石遗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