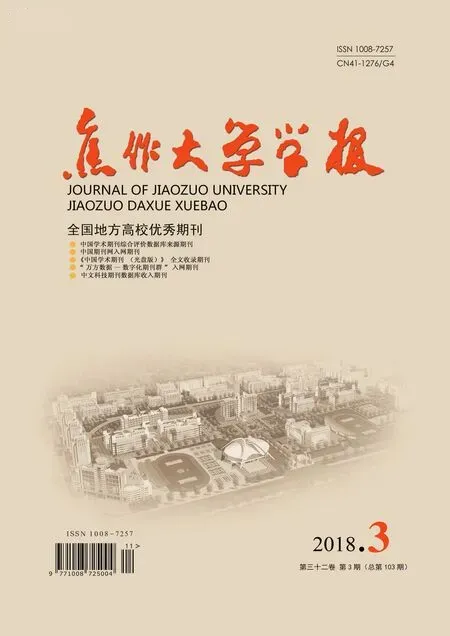陈子昂诗学理论对唐代诗人之影响
姜 楠
(焦作大学人文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初唐四杰”后,陈子昂鲜明而又坚决地反对齐梁诗风,他在诗学理论中标举 “风骨”“兴寄”“风雅”,对初唐的不良文风起到了“横制颓波”的作用,产生了“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效果,对盛唐气象的到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从宏观上为唐代文学定下了宏大高远的基调,盛唐、中唐、晚唐三代的诗人都可以从他的诗论中汲取营养。陈子昂的出现,在文学的发展中起了开关闯道的作用,力挽狂澜,倡导恢复“音情顿挫”“有金石声”的汉魏古音,他的五言古诗对五言律体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诗学理论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李白的清新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讽喻现实,都是对陈子昂诗学理论继承与发展的结果。陈子昂的诗学理论还影响了盛唐诗论家殷璠,他对陈子昂的诗学理论进行了补充与拓展,把“声律”“风骨”“兴象”作为品评诗歌优劣的新标准。
唐朝初年的统治者励精图治,聚贤纳士,激起士人奋发进取之心。伴随社会风貌的改变,文学创作也在孕育着强劲的力量。而此时陈子昂的创作风气顺应时代发展,也是后人心理期待的结果。对陈子昂的接受在他去世不久就开始了,杜甫经过陈子昂的故乡射洪时,亲自去凭吊陈子昂的故居,写下了《陈拾遗故宅》“有才继骚雅,哲将不比肩。……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1],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为后代诗人树立了标杆,对唐诗具有开创之功。“陈拾遗子昂,唐诗之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唐诗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2]。他的《感遇》诗开创了唐代五言古诗的风貌,确立唐代五言古诗质朴平实、真切自然特点。陈子昂一生创作的律诗很少,但他的《白帝城怀古》却是五言律诗的典范,该诗把白帝城附近的景色与个人的怀古之情结合起来,章法井然,对仗工整,“此一篇置之老杜集中,亦恐难别,乃唐人律诗之祖”[2]。《晚次乐乡县》在与故乡景色的对比中写出了异乡边城荒凉,思乡之情自然地从诗中流出。《度荆门望楚》描写了自蜀至楚沿途的风光,蜀山之清秀,巫山之雄俊,荆楚之壮阔,被他简括地勾勒出来。胡应麟说:“子昂‘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平淡简远,为王、孟二家之祖。”[3]这些诗歌明快的节奏,和谐的色彩,淡远的风格,工整的对仗都成为山水田园诗派汲取的精华,豪迈的气势,壮丽的景色使人似乎看到了李白的风采。陈子昂有着两次投笔从戎的经历,亲身体验了边塞军旅生活,写下了很多风格沉雄、语言质朴的边塞诗。陈子昂的边塞诗超出了前人边塞诗思妇闺怨、戍边乡愁的范围,拓展了边塞诗的题材,进一步涤荡了初唐诗坛的纤弱之风,为唐边塞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盛唐初期的张九龄受陈子昂的启发,直接承袭其《感遇》诗之名,也写下了以“兴寄”为主、委婉蕴藉的《感遇》组诗,“张曲江五言以兴寄为主,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磐含风,晶盘盛露”[4],“首创清淡之派”[3],深受后人的好评。
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诗学理论,使之成为盛唐的一种审美思潮。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指出:“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间多有全用他句处。李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如此。”[5]李白对陈子昂的尊慕和模仿,正体现出了他对陈子昂诗学理论的继承。李白在《赠僧行融》中也一再表示出对陈子昂的仰慕:“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6]孟棨《本事诗·高逸》:“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7]在这里不仅揭橥了陈、李二人的关系,还体现出了李白的另一美学思想:“寄兴深微”,这是他对陈子昂“兴寄”说的发展,要求诗歌创作从深入细微处体现兴寄,婉曲见意,余味无穷,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开启了殷璠“兴象”说的先声。李白在《古风》中高呼“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和“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6],他像陈子昂一样,批评了建安以来的绮丽之风,要求恢复风雅传统。陈子昂的“风骨”理论在李白手中更是得到了发扬,他倡导诗歌创作应努力追求“风骨”,体现刚健有力的气势,“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6],把这做为审美标准来评价诗人诗作。李白较为全面地继承了陈子昂的诗学理论,并形成了自己豪放俊逸的诗风,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陈子昂用“汉魏风骨”来纠正六朝的“采丽竞繁”,并身体力行创作了《感遇》诗,开创了唐代五言古诗的风貌,初步确立了唐代五言古诗的质朴平实、真切自然、言志缘情的特点。杜甫在“别裁伪体亲风雅”与“转益多师是吾师”的思想观念支配下,他的五言古诗更是气象万千,博大宏深,无施不可。杜甫不仅用这种诗歌体裁形式写下了前后《出塞》、“三吏”“三别”等带有汉乐府痕迹的佳作,而且还写有融记事、抒情为一体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沉郁顿挫的鸿篇巨制。唐人的古体诗在杜甫手中最终得以完备,并形成高峰。陈子昂的兴寄主张也为杜甫所继承和发展。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中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辞。”[8]他不仅把“比兴”看作诗歌的一种“体制”,还把“微婉顿挫”的艺术风格连在一起,杜甫更注重比兴的政治内容和诗人的艺术风格。
经过安史之乱,大唐帝国极盛而衰。中唐时期,社会冲突激烈,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统治者面临着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众多问题,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敝。这样的社会现实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时期的诗歌理论来看,最明显的是把“风骨”与 “兴寄”并重转变到只重“兴寄”上来。白居易是陈子昂“兴寄”“风雅”说的忠实践行者,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8]这里的“比兴”与陈子昂《修竹篇序》里的“兴寄”在比兴寄托这个意义上是相同的。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再次提到风雅比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8]他把“风雅比兴”作为诗歌的本质,认为诗歌如果缺少这一特性,就只能是“空文”。所以白居易会对屈原以下,甚至李白、杜甫等人都有所批判。他同陈子昂一样,对齐梁间的诗作给予否定,认为齐梁间的诗作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他所看重的是诗歌的 “美刺比兴”,干预时政的作用,特别是反映社会人生,体察民病、宣泄民情方面的作用。晚唐的杜荀鹤也创作了大批关注现实的诗歌,顾云为杜荀鹤《唐风集》作序时称他的诗作“有陈体,可以润国风,广王泽”,希望他继承陈子昂,成为“中兴诗宗”[9]。
从此以后,诗论家们多以“比兴”代替“兴寄”。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指出:“至于论诗,从唐以来,比兴一直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论诗的人所重的不是比兴本身,而是诗的作用。”[10]人们之所以重视“比兴”,就是因为它具有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揭露时弊这样重大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社会动荡、国危时艰、民不聊生的时刻,诗歌的这种功能就愈加凸显得重要。诗歌在上千年的社会中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与它讲求“兴寄”“比兴”是分不开的。“兴寄”“比兴”包含着对诗的重大社会功用的肯定,也表明了诗歌绝不是纯粹的文字技巧游戏。陈子昂的“兴寄”理论能贯穿于上千年诗学理论中而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肯定了诗歌的重大社会功用,这正是它深远的意义之所在。
陈子昂的诗学理论不仅影响了唐代最杰出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还对盛唐时期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殷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陈子昂诗学理论的引导下,殷璠完善并拓展了陈子昂的诗学理论。他完全认同陈子昂对六朝的绮靡之风所作的批评,在《河岳英灵集》的《集论》及《序》里再次对这种文风进行了批评:“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8]“然挈瓶肤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夫异端,妄为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8]可见陈子昂对六朝诗歌的批评深入人心,殷璠又一次指出了南朝以来诗歌内容不够充实、追求华美形式的缺点。他在继承陈子昂“风骨”说的基础上对“风骨”理论进行了拓展和重新的界定:“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8]所谓“风骨”必须继承建安时代明朗健康、刚劲有力的风骨和精神,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既有健康的思想内容,又须注意声律协调,便于吟咏,兼有音乐美的效果。他认为,盛唐诗歌应该是继承了建安风骨而又具有太康时代诗歌所不及的音韵之美,所以在《序》里指出:“开元十五年,声律风骨始备焉。”[8]尽管陈子昂在《修竹篇序》里对诗歌提出了“骨气端翔,音节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等新的要求,但他对当时被诗人们日益重视的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殷璠对“风骨”的重新界定是对陈子昂“风骨”理论的补充与发展。殷璠在“风骨”“兴寄”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兴象”说,并将“风骨”与“兴象”作为品评诗人高下的审美标准,开拓了诗歌的审美意境,为晚唐司空图诗论的提出做了准备。
陈子昂的革新理论不仅为唐诗的繁荣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同时也为后世文学革新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使打着复古的旗帜进行文学革新成了一个惯例。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打着反对六朝骈文、恢复先秦两汉古文传统的旗帜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北宋初期,以杨亿等人为代表的“西昆体”大行其道,到了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借鉴陈子昂文学革新的经验,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并最终取得了成功。明代的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来反对“台阁体”和“八股文”。以复古为革新的模式甚至被应用到政治变革领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抬出孔子进行“戊戌变法”。这种以复古为旗帜进行革新的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但从整个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其积极意义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在肯定陈子昂诗论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存在的一些问题。陈子昂的革新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修竹篇序》后面所附的《修竹诗》虽然体现了“兴寄”,但“兴寄”的内涵并不怎样崇高。该诗前半部分描写了孤竹在南岳保持着孤高坚贞的品质,到了后半部分,被“伶伦子”制成乐器之后,就“常愿事仙灵”,寄托的是渴望荣身于朝廷的功利思想,大大降低了陈子昂的人格追求,与他提倡的“骨气端翔”相去较远,并没有很好地体现他的文学主张。陈子昂的散文有不少骈体之作,并没跳出六朝的窠臼。马瑞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陈拾遗诗语高妙,绝出齐、梁,诚如先儒之论。至其他文,则不脱偶俪卑弱之体,未见其有以异于王、杨、沈、宋也。”[11]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也提到这一问题:“如唐之陈射洪,于诗有起衰之功,昌黎《荐士》所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也。而伯玉集中文,皆沿六朝俪偶之制,非萧、梁、独孤辈学作古文者比。”[12]此外,陈子昂的诗歌中存在议论过多、缺少鲜明的形象等不足之处。
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进而复杂的过程,诗歌的革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它要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够取得成功。六朝以来重形式的文风浸染已久,因袭过重,积弊太深,不可能一朝一夕完全革除,所以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其创作有部分脱节,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陈子昂。尽管陈子昂的创作存在一些问题,但同他对唐代文学的贡献相比瑕不掩玉,他仍是唐诗改革杰出的先驱,他的理论和创作影响了整个唐代甚至以后的若干个朝代,正如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的评价“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8]。他的诗学理论改变了初唐文坛纤弱无力的局面,为盛唐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