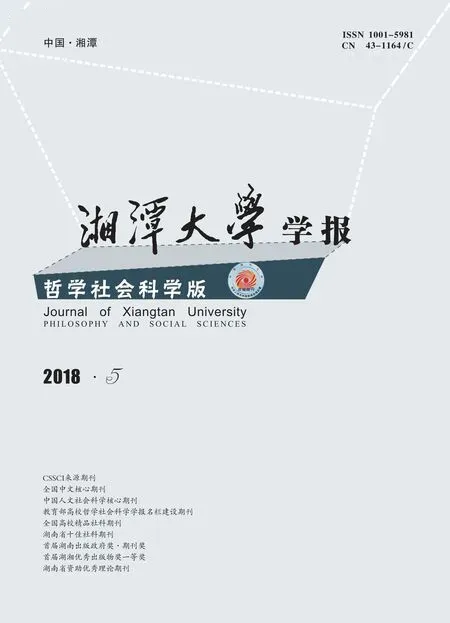韩少功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
晏杰雄,杨玉双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整体经历了一个从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历史转向,宏大叙事书写民族国家命运、承担历史使命、张扬时代精神的启蒙属性,曾经适用于高举“现代性”旗帜的20世纪中国,但已经不足以表达日益丰富和复杂的当代经验。随着19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进,与市场相生相伴的世俗社会来临,社会生活的主题从民族国家建设拉回日常生活的茶米油盐。在这一全新的文学语境下,“小叙事”之于文学的意义再次被推至幕前,“文学承担的使命不仅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认识历史。对于文学来说,压迫与解放的主题考察必须延续到个人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具体、感性的经验。”[1]从某种意义上,也只有文学(而不是其他理论和社会科学)可以更加广阔、深入地覆盖日常生活领域。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文学力量从不同角度进入日常生活的内核。新世纪以来,当代经验和历史记忆也从日常生活中被重新提取和书写,日常生活叙事逐渐摆脱了由宏大叙事注解的“工具论”桎梏,上升至独立的本体地位。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在场者,韩少功也是这一历史转向的实践者。“坚持在平民传奇的意义上展开小说叙述,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对于小说文体及其审美文化功能的一种理解与领悟。”[2]寻根作家群越过社会表层进入文化深层,从文化寻根走向生命寻根,从日常生活中观照人的生命形态,从早期作品《月兰》《西望茅草地》等短篇小说的政治批判意味,到《爸爸爸》《女女女》时期对民族历史的深层文化剖析,已经可以看到短篇小说中回归日常生活叙事的尝试,韩少功试图穿透民族文化的深层根络,将人和生活的本来面目从被遮蔽的隐秘之中解放出来,“寻根的积极意义是回到人的基本生存面,回到日常的经验世界……穿透由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构成的文化堆积,回到生活的本来状态中……真实的人生,人的本来面目,往往覆盖在厚厚的文化堆积层下。”[3]韩少功的长篇小说则显现更为纯粹的日常生活叙事,将生活拆解为不同的编码符号,将日常生活还原于丰富的片段之中。
一、日常生活的多维呈现昆德拉认为,小说存在的意义在于还原世界的丰富与复杂,避免成为确定性世界的说明[4],这种创作自觉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了本土化的多维呈现。《马桥词典》《暗示》《日夜书》复兴了中国的笔记体、纪传体叙事传统,其体例上的“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在本质上是一种“片段化”叙述方式,这一形式恰能契合日常生活叙事对于“还原世界的丰富与复杂”的需要。中国当代传统作家通常将日常生活看作一个结构整体,以穿透结构中的某一个关节点来牵动整体,这种 “全景式”叙事可以涵盖广阔宏大的社会历史图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地观照对象的整体和内部关系,但对于生活的观察限制在一个焦点之上,观察距离和角度很难自由变动,也就难以深入任意一处细节之中。韩少功长篇小说以“片段化”叙事覆盖日常生活,将个体生活经验进行编码和重组,对生活进行多维全息地文本重现,将整体拆解为不同的结构位置,将生活还原为无数的片段,从不同位置观测变化中的显象,观察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任意一个细节之中。崔卫平谈到韩少功的长篇小说给人以“全息式”的印象,也就是基于这种“片段化”叙事对于日常生活的多维呈现,“‘全景’是人为地把全部事物连成一片,放到一个所谓的‘统一整体’之中去。而‘全息’是允许事物与事物之间有裂缝,允许有些事物消失,从此断了线索,但这并不排除它继续对全文产生一种隐蔽和潜在的影响。”[5]韩少功的“片段化”叙事对于日常生活进行拆解,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生活描摹进行解构,但也没有完全消解小说的结构意义,仍然保留了小说的内在冲突和张力。
《马桥词典》以语言为观测点,理解被汉民族标准语制约与遮蔽的马桥方言,进入被政治话语包裹的外部世界所遗忘的民间世界。“言语”作为小说的切入口,是观察和理解马桥世界内在裂变与冲突的关键,也即小说序里所说“非公众化或逆公众化的语言总结。”[6]这种言语活动是个体在心理和生理机制作用下的私人表达,同时也有社会意义的趋向性,小说里一个个的词条并非纯粹的个体创作性活动,而是马桥人祖祖辈辈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烙印和精神写照,比如“小哥”一词表达的女性无名化、男名化,“渠”与他暗示的心理距离,“下”字道出的中国自古以来对性的道德偏见,“夷边”一词流动的“天朝上国”华夏血脉。马桥人在长期的共同的言语使用中生成了自己的语言结构,它既是马桥社会系统和价值系统的印证,也规定了马桥人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和伦理道德,比如马桥人对于成分和敌我的划分不同于知青理解的阶级划分,盐早继承了死去老爹的“汉奸”头衔,铁香沾了丈夫的“书记”光,这些思维定式表现出小农思维与现代思维的断裂;比如马鸣这个韩少功笔下典型的非正常、病态、丑态的角色,他在我们一般人眼里是疯子,但马桥人觉得他并不疯,之所以瞧不上他竟是因为他打着“科学”的名义学懒,破坏了马桥人的生活常态,这里马桥世界的常态和外部世界认为的荒谬形成了认知冲突;比如马桥人推崇鬼神,对于“火焰”“梦婆”“走鬼亲”等神秘现象和事物相当迷信,相反对于宣传无神论的科学思维表现出内在的抗拒。语言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小说借助语言这个钥匙,对马桥语言结构的生成和作用机制抽丝剥茧,解剖马桥世界的内在肌理,从而打开马桥日常生活的入口,在这些传统与现代、常态与荒谬、神鬼与科学的对照中,呈现老百姓眼中的世界,同时将掌故、轶事和传说融入其中,比如规劝会暴乱的荆界发生大火,比如台湾里的磨子与石臼打架,以及走鬼亲等等,还原一种原始的、强大的、可以自洽的民间逻辑,建构了一个神神鬼鬼、亦真亦幻的民间世界。
《马桥词典》问世后,韩少功越来越体会到,语言无法无死角地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处缝隙,更广阔的不为人知的社会现实往往隐藏在语言的背后,包含于纷繁的具象符号之中,于是在《暗示》中将叙事焦点对准日常生活最普遍最基本的存在——具象,作家以具象事物或现象作为进入日常生活的入口,首先指出了具象在当代生活中的构成和意义,具象映射的是人的意识领域没能被语言表达的部分,它揭示的是冰川未露出海面的庞大躯体。具象的一部分是“事物自然的原象”,可以理解为具象在历史和当代经验中恒定不变的那一部分,它产生于历史生活,也适用于当代经验,比如“场景”对人的影响,“家”和“办公室”必然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人的心理和行为,家给我们的温馨舒适感往往会让人们放下戒备,营造亲切友善的交往氛围,而办公室的严肃气氛则更适合工作上的交往、谈判,同一个话题在不同的场景之中达到的效果完全不同,类似的具象还有“家乡”“母亲”“爱情”,对这些具象的理解既适用于过去、现在、未来,也适用于不同族群。另一部分“传媒文化的造象”则是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渗透于当代生活的产物,可以从中看到消费文化对于当代人观念的重塑,作家将其放置于历史经验中思考与解读,同时结合个体生活经验,对当代文化进行了想象性的理解与表达,比如对于“摇滚”这个新兴的音乐概念,作家发现,听众已经从过去对于音乐本身的关注,转变为对“听”这个过程的重视,比起歌手和音乐作品,听众自身的个性释放和情感宣泄似乎更为重要,类似的具象还有“无厘头”“卡拉OK”“包装”“行为艺术”等发源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概念。一些文艺作品对于内容深度、语言逻辑的抛弃和视听快感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人情感和思想的真空。从“原象”到“造象”,韩少功通过具象连接人与人的关系,考量具象如何介入人生和社会,进而考察个体在不变与变之中的存在位置,揭示当代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形态,通过考察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去揭示状态之下的心理和生理机制。“《暗示》中有一种重构人的日常生活的欲望……以揭穿为己任,揭穿由某种知识构成的假象、陷阱和谎言,在叙事的再现努力中,不断地向一个真实的世界逼近。”[7]他抱着怀疑与警惕的目光,审视当代人潜移默化中所背负的某种现代文明的介入以及遮蔽,而这种怀疑与警惕最终指向的是揭开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日夜书》尝试以片段化的生活情境书写历史日常生活,描摹知青命运。韩少功之所以在距离知青生活几十年后才有了这部写知青一代的长篇小说,是为了有足够长久的时间来审视已经成为历史的知青生活,也可以从一个长远的时空跨度来观察知青一代的命运轨迹。首先,通过片段化情境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小说在“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公众性”历史语境中,讲述不同人“日常的”“个体性”事件,在“个人/历史”两种话语的互动模式下,呈现人与其存在语境的某种联系与互动,一方面是时代语境加诸个体的某种影响,一方面是个体在时代语境下的主体性。小说的开头一节“远方”中,以一系列片段的排列组合,将知青下乡的宏大历史背景浓缩于校园生活的日常情境中,以人物只身于校园之中的个体情绪映射“文革”背景下的时代空气。陶小布只身在“旅客散尽的站台”般的校园里闲逛,在“回声四起的走廊”里,目睹贴着红卫兵标语的墙壁,目睹武斗之中破碎的玻璃窗,目睹在红卫兵运动之中楼梯上被炸出的窟窿,目睹一个个空荡而狼藉的“红卫兵司令部”——教室,这里一系列片段情境共同还原了一个被革命运动肢解下的校园,还原了知识青年离开校园参与下乡运动的真实历史面貌。而陶小布的一句“亲爱的,我被你们抛弃了”是个人面对历史的深切痛感,也映射了一代知识青年共同的心理镜像。其次,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下,重新审视知青命运。小说中马涛这个角色令人印象深刻,他在“文革”之中被冠以“反革命、反党、反政府”的罪名,锒铛入狱,后来因为“错判”被平反出狱。马涛的形象到这里似乎就已经同某些典型形象重叠了,但马涛的形象显然包含了人性的复杂与悖论:一方面,他有高昂的革命热情和不畏牺牲的勇气,令人佩服,他在狱中受尽折磨,不得不令人同情,这一面确实契合我们对于时代语境中一代人形象的某种幻想;另一方面,马涛对亲人不管不顾,反而横加指责,将身边人陷于不义境地,对于妹妹马楠的牺牲毫无感激之情,出狱后愈加自我膨胀,自诩为时代的“英雄”,该获得所有人的尊重和敬仰。我们在马涛身上很容易看到矛盾和分裂的形象,但其实这种悖论是统一于同一个人格之中的,革命的激情不是出于革命理想的信仰——而是激进沸腾的时代情绪在自我意识中的高度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非评价《日夜书》“像是畸人录,又像是英雄传”是甚为恰当的。“错判”在当时时代语境中的意义指向了正面高大的人格形象,这一属性在其语境中显然以压倒性的日常生活从政治生活的概念图解中释放出来,这显然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青叙述。韩少功不掩盖人性的其他属性,最终将马涛这个人格病态的人物包裹成时代的“英雄”。作家在这里并不企图书写“一代人”的集体命运,《日夜书》也并不是一部知青的精神传记,“历史发展不是切换式的,是无缝的转换,是要素的重组,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生活巨流。”[8]在这里,个体不再主动或被动地框定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知青的命运不是交由“历史生活”的宏大话语逻辑来理解,而是通过历史夹缝中的日常片段来自我呈现。
二、抒情对日常叙事的介入福斯特曾谈及一个法国批评家对小说下的定义:“用一定篇幅的散文写成的一部虚构作品。”[9]9这里可以看到小说和散文的文体渊源。西方的文体融合可以追溯到象征主义诗歌运动,以及意识流对于小说形式的开拓,诗化小说最终敞开了小说的艺术形式。小说常常和叙事联系在一起,而散文常常和抒情联系在一起,这是单纯地从文体风格上将抒情和叙事予以区分。当然,“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体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种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10]5从小说文本的编码形式入手,抒情和叙事并非是以完全对立的姿态存在,而是以某种此消彼长、互相渗透的方式共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始于叙事诗的源头《诗经》,陈世骧称其“弥漫着个人弦音,含有人类日常的挂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11]2所谓“日常的挂虑”和“切身的哀求”可以理解为我们常说的“缘事而发”,这里的“事”说的不是国家大事,而是百姓劳作、丰收、出游、祭祀、求爱、庆祝等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日常生活刺激了人们的创作灵感与表达需求。作为有别于叙事传统的另一条隐线,抒情传统渗透于中国文学“‘有情’的历史”[10]7之中,即便是在中国叙事源头——史传文学之中,也可将这种美学品格窥见一二,比如将项羽纳入本纪,本身就指向了司马迁主观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倾向,王德威引述沈从文的观点,称“史传叙事的核心,无非‘有情’,而‘有情’的结晶,是艺术的创造、抽象的抒情”。[10]11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史铁生等作家汲取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对西方诗化小说进行本土化移植,最终发展为中国现当代小说文体形态散文化、审美形态诗化的一支。韩少功小说在审美品格上承袭了废名以来的抒情传统,在极致诗意的古典情境中映衬抒情主体的情感倾吐:“无边无际的星空压下来,压下来,再压下来,深埋我的全身。一层银色的星光湿漉漉和沉甸甸地打手,在林子里到处流淌。最早闪烁的一颗星,比往常体积倍增,是挂在草盖一角的大钻石,甚至闪烁在我的蚊帐里,垂落我的睫毛上。在这样一个遭到群星摩擦乃至重压的地方,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12]134“我”被“星空”“深埋”,被“星光”“打手”,被“群星”“摩擦”甚至“重压”,“一颗星”甚至“垂落我的睫毛上”,韩少功在这里将空间固态化,压缩成人与物平行共处的当下世界,抽象的无限的空间变得可触、可探、可感,人不再是虚无缥缈之中渺小的存在,想象力可以向四周伸展,将个体的“我”融于无尽的万物之中,最终营造了一个“物我合一”的化境,而这一意境最终指向的是个体情怀的抒发、倾吐,这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意境”说,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情感表达,以及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种种,都可以产生关联。
小说呈现散文化生活情境,解构严密的叙事框架,冲淡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文本的自由游走间构成叙事张力,“借助那一幅幅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图画……重建二元对立的感觉世界。”[3]在这里看不到扣人心弦、高潮迭起的情节,可能给不了读者畅快淋漓的阅读快感,然而作家并没有取消小说的矛盾冲突,而是将情节层面的戏剧冲突内化为心理层面的冲突,在人物的交互之间构建了价值、伦理、情感、道德等层面的对立关系,甚至是人物内在的自我分裂。《日夜书》没有一个牵引情节的人物主心骨,可以说每一个人物都有自我演绎的情景剧舞台。小说大量闪回、插叙、跳接的情境化碎片将这些人物以不规则形态串联起来。前一节的陶小布还在痛彻心扉地思念马楠,后一节就写到他和马楠的初夜;前一节还在写郭大军的女儿丹丹,后一节马楠就出场了。还有突然交代马涛的出狱,以及马楠母亲的去世。与其说小说不给读者时间来消化和整理,不如说这就是为了避免预设立场和期待的出现,让人物任意游走于文本的时空之中,从而在一个长远的时空跨度中形成叙事张力,以人生的各个阶段作为不同的叙事参照,孵化知青一代人生的多样化形态和其复杂的命运意味。如果说《日夜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近距离的人物细节,在《马桥词典》中视点和焦距则完全扩散了,从对点的关注转移为对面的观察,因此在初读此书之时容易形成一个大致印象——这里的故事不是为了塑造人物而存在,相反人物因为在故事中有一个位置而获得了存在意义,似乎很容易且不由自主地跳脱故事表层而直接进入文化深层。然而,如果将人物作为小说的核心因素来考察,近乎一种在显微镜下观察清明上河图的印象,也许更容易理解《马桥词典》作为小说的文体依据。在当代传统小说中,“以人物为中心”是显著文体特征,中心人物不止是小说的基本元素,而且对于小说的影响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马桥词典》之所以在体例上偏离传统小说,恰恰在于将中心人物分解为多位平行人物,人物群像以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状分布,共同构成了一幅马桥的民间画卷。然而,如果仔细地放大这幅画卷,其实每个人物背后的故事也有其丰富性,一个个生动饱满的人物随之跃然纸上,从而赋予作品小说的基本属性。比如盐早,他在“台湾”一节中以茂公儿子的身份第一次登场,埋下其悲剧命运的种子;“汉奸”里交代了他汉奸和哑巴身份的由来,以及和姐姐难以启齿的往事,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冤头”里描述了盐早、祖娘、盐午三人不对等的家庭关系,这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红娘子”里盐早已经活得比毒蛇还要毒,“渠”和“道学”里则言及盐早和他的妻、子多年后的生活现状。小说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几个跳跃性的时间跨度中,铺展人物复杂而沉重的人生轨迹,从和父亲、母亲、姐姐、弟弟、村里人的互动关系中,解释其悲剧性命运的隐喻构成,姐姐那一句“我们反正已经不是人”则是对其悲剧命运的现实注解。值得注意的是“我”与盐早的隐性互动,盐早曾经帮“我”担柴,曾经被“我们”戏耍,但言尽于此并没有更多的情感互动,“我”最初是作为词典的编纂者记录和描述盐早的故事,而在故事最后,因为一滴眼泪,“我”从盐早故事的旁观者进入了故事的核心,将巨大的情感容量一股脑倾泻出来,不动声色地渗入细枝末节的生活情境之中,既汹涌澎湃又细腻动人,“我没法在看着电视里的武打片时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打来一盆热水洗脚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挤上长途汽车并且对前面一个大胖子大叫大喊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13]145这种由客观叙事者到情感亲历者的叙事立场转变,也发生在《日夜书》中,陶小布在寂静山谷之中梦到马楠变成了一只松鼠,梦醒后不自觉轻声唤了一句她的名字,“这一喊我就明白了。马楠,原谅我,我的小辫子,我的黑眼睛,我怎么能让你走?怎么能让你成为一只松鼠?你得做我的老婆,老婆,老婆……”[12]135叙事者和主人公的身份在这里悄悄地转化,从冷静旁观的叙事主体过渡为一个人格立体、情感饱满的抒情主体。
对于小说和散文的审美融合,并不是作家突发奇想的文体实验,而是作家基于生活经验和思维习惯自然生发的一种审美感知,“社会生活自身的形式,人类思维自身的形式,往往是散漫的、游走的、缺损的、拼贴的、甚至混乱的,其中不乏局部的‘戏剧’,但更多时候倒是接近‘散文’。这构成了另一种小说审美的自然根据。”[8]传统小说围绕中心人物、中心事件展开的完整逻辑叙述,将生活框制于起承转合、悬念高潮的“戏剧”舞台之中,对于生活和人的观察限制于特定距离、特定角度的“单焦模式”,韩少功十分警觉这一模式对于“生活和思维”的“遮蔽”,将无逻辑和非必然因素在生活和思维中扮演的角色移植于文本中演绎,“之所以如此重视日常生活的价值关系,也正是因为他们从人的生存活动中发现了命运的虚拟性。”[3]正如《马桥词典》“枫鬼”中的那一句,“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13]65《马桥词典》中,盐早一直在身边伺候他疯疯癫癫的母亲,而母亲一直到去世之前,心心念念的都是另一个儿子盐午。无独有偶,《日夜书》中的马楠一直服侍病榻前的母亲,而母亲最后的遗言却也都是留给那个不在身边的儿子马涛。这里将命运的不可知论呈现到人生的层面,命运不是一个因果循环的完整的圆,而有其不可预知的神秘面,人物无法在取消起承转合的生活逻辑中回避自己的命运,这正是人生的无奈和唏嘘所在。
三、理论对日常叙事的介入前面谈到抒情对于韩少功长篇小说的介入,主要是考察小说散文化的文体特征和审美形态,这一介入将完整的叙事切断、甚至打碎,留下了巨大的叙事空白,交由抒情和理论来填补,尤其在《暗示》之中,叙事几乎完全被理论所取代,理论在文本中完全是喧宾夺主的部分,也就是韩少功所说的:“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昆德拉式的“伪哲学”[8]理论抒发。所谓“伪哲学”,大概意味着对于生命、死亡、人性、宗教等原点问题的思考上升到了形而上的意义,但也不是系统的“哲学”,姑且可以理解为一种由日常生活中生发的“哲思”。《日夜书》“国际歌”中将人对于宗教的热情、革命的热情甚至商业的热情并置,思考人性在社会文明不同阶段的普遍性。“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一旦有了候任铜像或石像的劲头,再苦的日子都会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还能放射出熠熠光辉……宗教不就是这样吗?在缺少宗教的地方,革命不常常就是这样吗?在革命退场的地方,商业消费不常常也是这样吗?……人类激情一次次失控性地自燃,拦也拦不住。”[12]86最后一章以“天堂”里一个初生婴儿的视角理解生命,作家将人的生命回到初初抵达的时候,面对一代人年华的末年、生命的最后阶段,相较于生命周而复始的喜悦,这里更多的是日夜更迭、岁月流逝的悲怆意味。《马桥词典》中多处表明作家的时间观,最典型的是“一九四八年(续)”中,光复和儿子的冲突,展现了不同的人对于时间的感知力不尽相同,所以历史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也不同,“时间这种透明的液体从来就不是均量地和匀速地流淌着,它随着不同的感知力悄悄变形……就是一个人的感知,也会随着情景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在一大堆感知的破碎片中,我们还有时间可靠的恒定守一的形象吗?还有时间的统一性吗?”[13]116《暗示》里甚至用整章的篇幅来论述“爱情”“生命”“记忆”“真理”这些问题。除了这些形而上的“伪哲学”理论,三部作品尤其是《暗示》中还有一些基于现实层面的文化评述,深入思考现代文明的衍生物——消费主义主导的文化众生相,包括时尚文化、现代主义文化、精英文化等,比如将“重金属摇滚”看做“新一代的劳动号子,是发烧友们心身全面跟上新时代的号子”[14]110,“时髦不过是社会中层心理焦灼之下急切而慌乱的文化站队和文化抱团。”[14]106同时,在左右阵营分庭抗礼、思想流行“站队”的今天,韩少功表现出对于新兴思想浪潮和派别更为理性、成熟的态度。从对“忏悔”的浪潮和“欧洲知识界抗议极右派和法西斯的示威壮景”中,作家欣慰于对于“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深仇大恨”的“拒绝和抵抗”,然而也警惕地察觉“新的思想专制和新的思想极权”正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积重难返”[14]97-98。无论是哪一种理论介入,都可以看出其中庞大的思想容量。
通常,更为简单有效的方式是用随笔或者杂文来承载这些理论,韩少功却选取了小说这一种“曲线救国”的文体形式。作家在《暗示》的序言里表示,这实际上是要突破文艺题材的文体限制,将大家认为严肃艰深的理论文章引入轻松的小说中,让理论沾染小说的轻松自如,小说也沾染理论的认真严肃,“思想理论是为了感觉服务,感觉和感动是落脚点。思想僵化的时候,需要用感觉来激活,感觉毒化的时候,需要思想来疗救。”[15]这种“思想”和“感觉”的互补正是要突破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式,实际上也是对现行知识谱系的一种革新,如果完全取消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写成纯粹的随笔或者杂文,那么也就陷入他所表达的某种“逻辑霸权”的“遮蔽”之中了。从这些理论介入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少功长篇小说总是在努力尝试打破意识形态、知识符码对日常生活的驯化,还原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马桥词典》揭示了“文革”背景下话语霸权对于地域语言的影响甚至侵蚀,展示了意识形态话语是怎样介入马桥人的生活,比如向毛主席“征圣”,杜撰毛泽东语录来增加自己说话的分量:“毛主席说,今年的油茶长得很好”,“毛主席说,要节约粮食但也不能天天吃浆”,“毛主席说,地主分子不老实,就把他们吊起来”。[13]165《暗示》里,韩少功将“知识危机”列为现代社会“基础性危机”之一,现代人越来越依赖于语言和文字符号,而现代文明编制下的信息知识网络,几乎已经成为现代人思维认知的重要构成之一,然而具象作为一种符号早在语言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以不同形态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从人类诞生伊始就贯穿于人类进化史,作为人类实践生活的知识性产物,具象符号为思维提供了认知来源,其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介入则是润物细无声的,比如“仪式”“场景”“真实”,在潜移默化之间渗透于现代人的思维血脉里了,无处不在却又不为人察觉。
韩少功长篇小说关注的是全人类的文化问题,如果说寻根文学是对地域的、民族的、原始的文化根络的纵深挖掘,不妨将韩少功长篇小说中的理论介入看做一种文化思维的横向发散,将寻根的脉络扩展到人类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范畴。在《暗示》中,韩少功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思路比如儒家、道学、墨家中,来解读当代社会具象符号,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具象怎样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另一方面从商业、娱乐、消费、信息等当代文化现象中,观察具象如何覆盖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种种成果之中。我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民族和世界之中必然有某种共性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之中,比如宗教、革命、生命、自然、人生的普遍意义,那么,如果从世界意义的大文化概念中抽丝剥茧,是不是也可以寻得传统民族文化的某种补给。抽象和具象符号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相同的是,这些符号都以某种方式或显或隐地介入思维、文化和社会生活,最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塑造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形态。我们谈到某一种语言或具象符号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包含了数代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思维,比如“家乡”之于人精神和灵魂的意义,比如“仪式”的象征意义以及其中包含的政治、伦理意味。作为一种发散形态的文化寻根,韩少功长篇小说中蕴含的人类性思想不仅是对普遍价值的弘扬,同时这一文化视野的扩张也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思维路径。
从《马桥词典》《暗示》到《日夜书》,韩少功以不同的切入点进入日常生活的内核,无论是语言、具象符号,还是历史片段,都是将人放置于存在语境中考察,将生活本身的丰富与复杂在文本中重现。韩少功长篇小说显示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汲取,和废名、沈从文等人一脉相承,他的小说不仅在叙事中掺杂了丰富的情感内涵,还包含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小说的抒情意识和理论意识也融入了小说的文体形式中,所以读起来并不像一本小说,反而更像散文、随笔,甚至理论专著。然而如果只停留和纠结于文体形式的新与变,也就很难去探究形式变革背后的思想轨迹和情感流变,也许跳脱出小说“形式的特别”,去更多地开掘其“内容的深切”是题中之义。如果梳理韩少功小说的发展脉络,联系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可以将他的长篇小说看做是文化寻根的横向移植,其中蕴含了作家的人类性思想,表现出对于全人类价值的弘扬。从这一意义上看待韩少功的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很有启示。
——《革命后记》初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