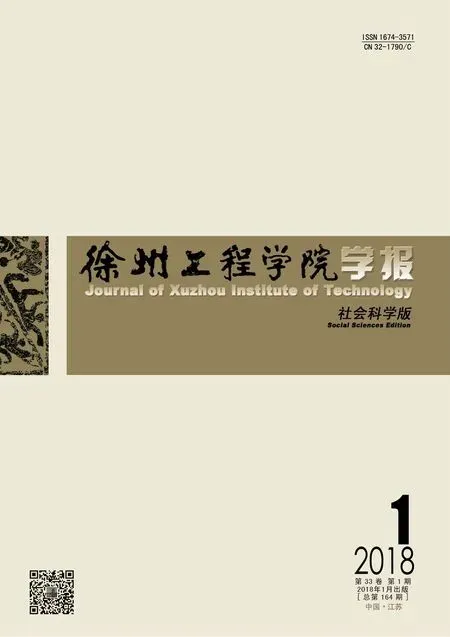旅游人类学视域下的创意型古村旅游探讨
——基于“海外学子走进金华古村落”项目的田野作业
林敏霞,谢周宏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在旅游发展的历史上,旅游按照不同的角度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比如在瓦伦·斯密斯主编的《东道主与旅游——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中,她按照不同游客的休闲流动性,把旅游分为五种形式:民族旅游、文化旅游、历史旅游、环境旅游、娱乐旅游等。这其中,“民族旅游”指以地方的“奇异”和异域的民族风俗习惯为特色的旅游,“文化旅游”指包括参观“如诗如画”、“古老”、“有地方特色”的旅游[1]。“古老的、如诗如画的地方”通常又与怀旧的乡村旅游联系在一起。如果“古老的、如诗如画的乡村”是位于异域的民族或者国度,不妨综合地称之为“民族乡村旅游”或者“民族古村旅游”。
“民族古村旅游”应该是全球化和城市化双重趋势下的旅游潮流和类型。人们之所以把古村或者乡村作为怀旧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古村和乡村自带有与城市和现代化“对立”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是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东道主为了迎合都市人现代性怀旧情感而创建出来的旅游之地,是东道主为了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乡村衰败而主动采取策略,开发国内甚至国际的“古村游”或“乡村游”。
中国经历近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后,也面临着和很多现代社会相似之处境:一方面是城市的膨胀、富足、拥堵和污染,另一方面是乡村的衰败、衰亡、萎缩和凋零。故而,近几年来,“守望家园”“乡愁”“美丽乡村”,不仅是文人笔下怀旧的笔调,也成为政治话语和政策决策的方向。它和遗产运动,非遗保护一起,促进了中国乡村的复兴、重建和新的自我定位。在现代技术媒介(包括官方媒体和自媒体)下,乡村以各种活动(包括项目、会议等)形式,用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出现在公众(乃至全球公众)的视野之中,努力自化为一个值得“一看”“一游”“一吃”“一住”的休闲旅游光观之地,是一个可以在地图上被标示和认可的景点和去处。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中部地区,辖2个市辖区、4个县级市和3个县,至今已有2 200多年的历史,在田野乡间散布着195个古村落,数量列居浙江省第二,其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7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8个,中国传统村落24个,省、市级历史文化村落122个。在这些古村镇中,共有历史文化遗存5 159处,其中古民宅3 100幢,古祠堂240幢,古寺庙83处,在古村落中还分布着大量的古戏台、牌坊、古桥、街巷等等①。这些古村落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留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璀璨的传统文化。
这一庞大的珍贵“古村落遗产”仅部分得到关注、保护和开发而显得有生机,还有相当一部分古村落还没有遗产认知和保护意识,其建筑面临进一步被破坏的境遇。同时伴随人口城市化迁徙和老龄化,许多古村落陷入破败荒废的边缘,成为无人的“空壳村”。因此,基于对古村落的保护需要、基于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考虑、也基于提高金华在国内和国际知名度的设想(这其中包括了力图争取“世界古村落保护大会”会址永久落户金华这一目标),以金华市外侨办牵首的一项名为“海外学子走进金华古村落”的项目在2014年末开始筹备并实施,目前已经完成了琐园村、寺平村、俞源村三期活动,并开始筹备第四期的活动。
项目引发了以“Jinhua homestay”“金华古村落旅游”为关键词的高频率的搜索以及相关报道和讨论。其中一篇名为《金华以“五+” 打造“中”色旅游新形象》的报道(该文被中国国家旅游局网站转载),把该项目概括为:旅游+外事,延伸“中”色旅游的文化传播新功能;土气+洋气,激发“中”色旅游的多元融合新内涵;生活+生产,探索“中”色旅游的富农惠农新手段;传承+创新,开辟“中”色旅游的保护利用新路径;线上+线下,拓展“中”色旅游的宣传营销新方式*参见浙江省旅游局网站http://tourzj.gov.cn/Default.aspx;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网站http://www.cnta.gov.cn/xxfb/xxfb_dfxw/201511/t20151113_751425.shtml。
该项目从概念(2014年11月份)到策划筹备再到实施开展(2015年7月第一期开展),前后时间只有半年多,但所引发的关注和讨论足以证明,在现代技术媒介(包括官媒和自媒)下,一个不知名的古老的地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在地图上被标示和认识。就这一点而言,项目是成功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笔者作为这个项目的间接参与者,曾介绍和带队自己工作单位的部分民俗学研究生,在项目中做志愿者和观察者,他们分别在一期和二期中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笔者感觉到在日益发展的多样性的旅游世界中,这个项目除了自身所要追求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目的与意义之外,实际上也为旅游的探讨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案例,其中有许多关于旅游人类学的经典讨论,在这个案例中或多或少都遇到了新的经验和问题。在此,笔者一方面希望以此项目资料和经验的讨论,进一步引领自己有关旅游人类学的学习和思考,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一学术层面的思考能反思和能促进该项目的良性开展。
一、东道主:民族/国家抑或地方/住家?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大致可以从东道主社会、游客、客源地三个角度进入研究,其中对东道主社会的研究,把旅游看成是涵化和发展的形式,探讨旅游业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者或者以批判的视角,质疑旅游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当地文化的商品化,或者认为旅游是良性有益的发展,或好坏兼而有之,凡此总总[2],这些或多或少皆以“旅游”作为一件客观存在的事实来讨论它对东道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旅游目的地或者东道主社会自身旅游业发展动机、组成成分往往被“均质化”对待,消除了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但事实上,东道主社会内部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生态旅游或者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等研究领域就表现十分明显。发展生态旅游需要建设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可能成为保护区旅游业经济利益的最大所有者,保护区内的民众可能无法直接享受旅游业带来的基本利益,又或者受到外来的旅游掮客的“压榨”[3]。这里,国家、旅游掮客和当地民众是对立的或者至少不是那么和谐的。
在金华“海外学子走进金华古村落”这一国际旅游营销的项目中,是国家/民族、地方、政府和民众在某种层面上被“古村落旅游”捆绑成了一体。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重振乡村” 是一场国家自上而下的一场政治、经济和思想运动。金华作为一个非工业城市,拥有众多古村落,在当前这场“重振乡村”的运动中,如何把握契机,变“废”为宝,让古村落重现生机,是市级地方政府层面积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具体到项目而言,2014年有着较为丰富的外事经验的金华市外侨办以“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为理念,想做一个“请海外的学生来金华旅游,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来讲述我们金华的故事”*资料来源:访谈资料XSF,2015年10月份。的活动,以此推动旅游发展和文化保护与交流。
至于村落层面,项目一期的琐园村,村干部近几年来一直谋划着村落宗族文化的复兴、古建筑的修复和知名度的提升;二期的寺平村,早在2003年地方文物系统的干部就开始挖掘和保护古村落,并已经自主探索和开发了古村落旅游。因此,当外侨办项目负责人联系到琐园村和寺平村的村领导时,村领导层面几乎很快就能领悟到这个项目活动是宣传、建造和发展本村的时机,是“我们可以走出金华,走出浙江,跨越世界”*资料来源:访谈资料LSM,2015年10月份。的机会。
由于项目借鉴homestay的形式来运作,外国学子需要入住到村民家中,由村民来接待饮食起居,因此,需要动员和落实“住家”,即负责接待项目活动期间外国学子的家户。通常,这些家户要有基本的接待能力:有空余的房间、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会做饭,当然热情好客也是其考虑的因素之一。项目组会给予接待家户相应的补助。
根据我们团队的田调经验显示:并非所有的家户在一开始面对这一项目的时候都是反应积极的。一则,无论是寺平村还是琐园村,在总体经济上都不错,有能力接待外国学子的,家里一般都是有三四层高楼房的家户,家中或者有务工的,或者自己有种植产业,因此,在发家致富层面上的动机和需求尚未十分迫切*尽管两个村落在经济上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并不意味它们能逃避“乡村人口流失”这一现代性灾难。比如寺平村“有1600多人,年轻一点的都是上班,在家里种田的很少。都是上班,或者做生意,不会待在家里。”(访谈资料)。琐园村的情况也相似。;二则,“老外”在文化、语言和地域上都十分遥远和陌生,不少家户因而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不过,中国基层干部在软性行政动员能力上的效率是惊人的,很快就把这些障碍打通,确定了住家户数*一期琐园村一共接待了来自14个国家的42位外国学子,有 15户住家接待他们;二期寺平村一共接待了来自12个国家的37名外国学子,有18户住家接待他们。。
根据住家一开始对待项目的态度上的不同,大致可以把住家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把这次接待当成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自己要起带头作用,要好好传播中国文化、自己家乡的文化,并不看重经济收益,他们通常是党员,在地方拥有一定的名望,这一类住家相对较少。第二类是被行政干部软性动员(通常诸如村委主任、妇女主任和这家的关系很不错),自己虽然担心做不好,但是也当成是任务完成,对经济收益并没有什么概念,也没有十分强烈的经营意识,多数住家属于这一类。第三类则多少看重参与这次项目能得到补贴,这一类住家占少数。最后项目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住家都对这次参与表示认同。部分未能参与活动的家户,或遗憾或嫉妒,都希望下次如果有机会,也申请成为“住家”。
因此,这个项目展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相比前述自然生态保护区旅游业开发中国家或者旅游掮客会占据大量的旅游业利润,而导致真正的原住民无法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这次项目活动中则是自上而下地把国家、地方、政府和民众联系在一起,去营造旅游活动,启发民众开展旅游接待业。
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而言,金华是中国在应对全球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许多乡村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面临人口老龄化以及流失等问题;另一方面,面临人们地方认同感减弱,乡土社会萎缩、地方文化消失等问题的困扰。因此,这个项目如同台湾社会“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强调地方社区或者族群的自我能动性”[4]一样,它要积极传达一种国家、地方、政府和民众共为一体的“东道主”面貌,彰显的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积极的地方社会建设家园的姿态。尤其当项目本身把“村落”直接推向“国际”的时候,村落(住家)、地方与国家已经三位一体为一个“东道主”,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展现的是一种国际间的民族旅游。
二、好客:礼物抑或商品?
“好客”(hospitality)曾作为旅游高级论坛第二届的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Nelson Graburn先生所发表的《好客,一种人类的共通精神:礼物还是商品?》一文指出好客是人类学社会中连接主客关系的一种共同性表达,它的核心观念就是“互惠”(Reciprocity),并运用萨林斯关于互惠的三种类型(即一般性互惠,平衡性互惠和负性互惠)来分析现代“好客产业”的变迁与挑战:现代商业性的好客要融入非商业性交换成分来培育顾客的忠诚度,而原先非商业性的好客招待形式也在试图融入商业性因素以谋求利益[5]。
从好客性角度而言,这项国际研学旅游项目的营造中,在财力安排上是倾其所能,善待来者。比如项目的接待方式,除了来回车票之外,所有申请成功的学子在落地中国境内之后21天的行程中,吃住行游的全部费用都由政府出资的项目资金来承担,此外还为每个人发750元人民币作为日用补助。接受这样款待的外国游学学子需要对东道主进行回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作业,把他们的作业(图片、文字、视频等关于金华的印象和介绍)发到 www.jinhua-homestay.com这个网站以及自己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中,内容除了感想之外,还包括做村落的中英文小册子,比如说关于菜单、住宿条件等。通过他们的宣传和推广,来把金华古村落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对东道主好客的最大回报。
在住家层面,虽然一开始很多住家把它当成一个接待任务来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中国的好客方式来对待游客:丰富的“好客食物”、提供卫生打扫等等,尽可能地让对方满意。“家+”概念*所谓“家+”,就是让古村落里家家都能是酒店、餐馆和便利店。古村的村民不用改变日常的生活习惯,当有游客来时,只要家里有空余房间就可以提供住宿;家里有游客必需品就可以变成便利店;家里能提供餐饮的又可以成为餐馆。“关上家门是星级酒店,打开家门是温馨家庭,走出家门是乡野生活”。第一点要求就是主人要非常热情。伴随项目的深入,参与者与住家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文化交流和情感互动,“他们(住家)都是回答说这些人(海外学子)就像我们的儿子女儿一样的。他们(住家)每个人都很热情,也正是因为这种热情感染了这些学子”*资料来源:访谈资料,XSF,2015年10月。。
政府所努力推行的“家+”模式的好客形式,显然是在努力避免纯粹普通的商业性好客所潜在的“负性互惠”可能会带来的问题。这种模式可谓是众多新兴非商业好客模式(诸如换屋旅游(Home Exchange)和沙发漫游(couch Surfing)的一种,它追求“不仅使顾客省钱,而且能够更多地满足顾客所要寻求的亲密感、真实感和后台进入感”[5]27-28,它展示了非商业性好客与商业性好客之间的竞争,即在现有颇为成熟多样的好客形式的大环境中,古村落应该以怎么样的一种好客形式来吸引游客。基本上,“家+”模式在最大可能上体现传统好客精神和社会商业经济文化效益的结合。此外,从项目整体层面而言,由于项目涉及“外事”的层面,它必须以“民族国家”的身份把“好客”的纯粹性做得尽可能尽善尽美。换而言之,“民族”的身份,要求该旅游项目的营造要在最大可能性上避免纯商业性的负性互惠,要用传统的“好客精神”来包装商业性的或者产业性。
如格拉本在文章所说的:“新的好客形式不断发明,或者说旧的好客形式在重新启用,通常是带着一种强烈‘怀旧(Nostalgia)意味。”[5]27-28因此,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从民众角度而言,该项目是以礼物性的好客方式来接待外国游学学子。这个项目接待上的好客性,尽管是为了未来商业性旅游开发推广的目的,却潜在地运用了人类学互惠性好客的手段来促进项目的推进,因此,在好客形式上,礼物和商品并非对立,而是可能彼此互融和可转换的,尤其是当好客与“民族国家”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时,好客的礼物性和传统性一面要有意地得到提高,而商业性一面要则隐退在礼物的背后。
三、景观:现实抑或超现实?
景观与旅游关系密切,旅游行为基本上是一种游客对东道主社会或者说相异于自我生活经验的社会的物和景观的“凝视”[6]。一方面,旅游地的景观是游客目光凝视的对象;另一方面,通过游客目光“凝视”,东道主也在重新建构自己的“景观”。因此,景观总是在游客和东道主的互视中发生变化。在乡村旅游或者民族旅游中,东道主社会总是要对自身进行“美学化”处理,去除污垢,或呈现高雅的自然,或呈现古朴的整洁,尽量提供“旅游点的社交性、干净整洁、通达性等标志”[7]155,来提高游客凝视的满意度。
“推广和开发金华的古村落”是本项目开展的目的之一。为了使得项目成功开展,对景观的“美学化”处理是必然途径。
1.村落整体景观的整洁和美化
在项目开始前两个月,项目组和村落花了60天进行环境整治和设置。全村的党员、生产队里的队长、会计等干部都义务参加村落垃圾清理工作。另外村上还花钱雇人打扫街道卫生。领导每天挨家挨户走访、指导村民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处理。连村民自己都说“村里卫生方面变化很大,现在都自觉多了,以前都是乱扔”*资料来源:访谈资料,ZXJ,2015年10月。。参与者则惊讶于如此宁静美丽的中国乡村,喜欢在村落里一圈一圈地走了又走。
此外,为了迎接项目的开展,村落中许多废置的古建筑得以有机会修葺,一些被火烧毁的古建筑也在原地重新“复原”。寺平村项目沙龙活动点就设置在一个在十几年前被火烧过的重新修建的“古建筑”中。项目组和村落用了两个月时间,使用一些传统榫卯结构技法把这个房子进行修建和改造,既保持了其古香古色的传统建筑特质,又使得它能容纳六七十人在这里开展沙龙活动。同样,项目一期琐园村的务本堂原本也是一个基本上废置的、破损的古建筑,因迎接项目开展而被改造为沙龙活动基地,成为了“活的空间”*据调查,活动结束后这个地方基本就成为村落常用的会议场,也是项目活动的历史展览区,里头呈现项目活动照片以及各个地方学生带来的文化交流物品和学生的作品,这个地方本身也成为一种“景观”,在今后的旅游开发中成为新的凝视对象。。项目使得“废旧品”在“正确的人”手上重新获得了价值,显示了 “垃圾理论” 在此次国际游学项目中的作用[8]。
2.住家景观的美化和现代化
在本次活动中,为了接待学子,每一户住家都对自家进行了“硬件”和“软件”上的更新:包括空调、电视、消毒柜、热水器等硬件设备的更新或者安装,甚至在家中安装了WIFI。所有的床垫都按照星级标准配置,卫生间进行了改造,以方便外国人的使用习惯。每日打扫卫生、对所招待的食物进行“卫生监测”。有意思的是,寺平村还在村落里头“招标”建了一个咖啡馆。此外,村里的旅游指示牌重新进行了更新和布置,新立的指示牌,不仅路线更完备,还在中文之外配上了英文和韩文。面对如此具备“旅游点的社交性、干净整洁、通达性等标志”的村落条件,参与者表示令人惊喜,完全打破了原先关于中国村落的想象*比如:有一位参与者这样子描述:“这么一个古老的村落,但是我们还是享受到了很棒的设施。我们的住家很棒,还有洗衣机。村子里到处都有WiFi,还有咖啡吧。即使是西方人过来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很理想的去处。我特别享受这里很安静的氛围,没有拥堵的交通和嘈杂。”另外一位参与者描述到:“对村庄的感受(我原来想)就是肯定很脏,地上有垃圾,污染情况等等。来了这边之后,发现完全不一样。也可能是因为这是一个旅游目的地,人们都很关注卫生情况。村子里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可以让村庄保持得很干净。整个村落的建筑太精湛太漂亮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的古建筑能保留得这么好。”。
3.村落文化景观的选择、安排和复兴
除了整个项目要展示什么给这些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学子看之外,村落里头也要考虑选择什么文化给他们看。什么是他们感兴趣的,值得我们展示给他们看的。项目组首先对村落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进行了一定的普查,然后挑选出他们认为最有特色的文化进行展示*尽管关于什么是最有特色的,项目负责人和镇一级、村一级的领导干部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既有许多组织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仪式”,又有许多被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民俗文化”重新被挖掘和展演。在寺平村的迎接仪式上,村民穿上统一的服装,排列20个方队,有大鼓、小鼓、腰鼓等4种类型队伍,迎接37位海外学子的到来。观看的人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在仪式活动期间,还特意为学子们组织和展示本来应该在春节期间开展的“迎龙灯”等活动。
总之,此次项目所营造的村落景观,不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物质形态上还是文化形态上,都是人们在对传统之物的崇信当中,控制性地将其进行整合,“以确信它自己的映像是一种完美的形式”[9]。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比“原物更好的超现实”[10]。
在“通过各种现场和非现场的处理,仔细去污除垢后的‘历史’,以及精挑细选的高雅的‘自然’”[7]153中,人们将自己日常生活打造成令人向往的“更加美丽如画”的现代性乡村怀旧旅游目的地。在复兴的诸如“迎龙灯”的民俗文化中,来表达一个地方(金华)和民族(中国)的认同。在此尽可能“完美的形式”和“超现实”的旅游景观的建构中,“当地人正据此从事自身民族的创造与再构建”[11]。
四、旅游地:乡村抑或城市?
根据整个项目的设计,一方面是以金华的古村落为基础,向国内外推广“金华古村落”,为金华村落营造“家+”的旅游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力图借助于金华的“古村落”, 把金华推出去,让世界知道“金华”。
按照上述的项目目标,整个项目的重心似乎应该落在“古村落”,精心地“美化”村落,充分地挖掘乡村文化,把乡村的怀旧旅游做到充分,似乎应该是工作的重点。但是根据整个项目的安排和节奏来看,项目活动中涉及内容非常多,不仅只是乡村体验,还有各种城市文化和工业产业的体验和参观。
项目一大半以上的时间和内容都是超越村落的。除了在住家体验乡村饮食,安排参看茶园稻田大致属于乡村内容之外,剩下的项目基本上超越了村落文化,其中有:参观展示金华历史的金华博物馆,参观代表金华“名片”的金字火腿博物馆(金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乐小镇IT产业、康迪车业新能源汽车(两者是金华主要的现代产业),参观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金华市区的现代商场、知名的双龙洞黄大仙景点、看金华的地方戏剧婺剧等等。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在面对“国际游客”的时候,地方的身份不仅只是“地方自身”,它还代表着“国家/民族身份”。因此,主办方不仅要让对方体验到“乡村”,让人在古朴中怀旧,在乡村中看到古老的文明,体会到漫长的历史在乡村中的延续,还要让学子们看到“中国这个民族”现代化、城市化等发达先进的一面。否则,只是片面展示古村落,容易把“中国的民族形象”单纯地与“落后”欠发达联系在一起。因为通常古村隐喻着历史和怀旧,城市和各种现代产业则代表先进和未来。从国际游子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他们在金华所看到的一切等同于中国的文化,然后也把他们通过书籍和媒体所了解的中国形象投射到金华。
由此可以推论,在一个以地方的“古村落”游为营造主体的旅游项目中,由于其面对的是“国际游客”,无形中就会把“国家”作为“民族”身份背负到项目身上,因而,项目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让国际学子看到“地方”乡村和城市的全方位景观,在乡村及其遗产中体会民族的历史脉络,在城市及其现代产业中了解民族的活力。项目在旅游地上是乡村的,又是超越乡村的;在项目内容上是乡土民俗的,又是超越乡土民俗的。它把城市、工业、商业、都市消费景观等象征民族国家发达的一面,都浓浓地塞入“古村落旅游”这一张地图中。因此,项目虽然没有标榜“民族旅游”,但“民族旅游”却自然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存在着。
五、文化媒介:国人抑或“老外”?
在这一项以国际学子为游客的项目中,“文化媒介”变得非常重要。文化媒介包括人和物,相比物而言,人是更为重要的文化媒介。许多文化需要通过“人”这一文化媒介进行传达。在本项目中,文化媒介大致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作为项目顾问的外籍专家;第二类是以浙师大外语学院翻译专业学生为主的充当日常生活翻译的志愿者;第三类是项目所邀请的中国学者;第四类是网站和自媒体等。
整个项目从创意到策划,都是在三位来自德国和英国的专家参与下进行的,他们有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验,较为清楚地知道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外国人习惯于以何种方式理解中国文化,用什么方式来讲授中国文化是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的。整个项目过程中,有几个事件和细节充分体现了项目组外籍专家在这一项目中所起到的作用。
项目组外籍专家中的J先生,不仅参与策划和指导了项目的开展,而且还在第二期活动中负责为学子们讲解村落古建筑的结构以及所蕴藏的文化涵义。在第二期活动中,另外还请了一位学中医十几年并在中国行医的外籍中医为学子讲授“中医文化”。且不论他们对中国的古建筑或者中医的理解和造诣是否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当他们用熟练的英文把他们所学习并消化过的中国古建筑和中医的知识清晰地讲解出来的时候,他们比中国本土的专家和学者更好地扮演了文化媒介的角色。因为后者即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自己深入的研究和体会,但其内容和表达却未必是对方所能接受的。正如项目主要负责人X女士所说:“我们也考虑过请一个建筑专家来讲,但里面蕴含的东西就算是专家还是‘讲不好’,因为这是一个接受度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项目是把人家请进来,由他们来感知来写,其实是一样的。J相当于我们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他感知了,然后由他来讲述,这种传播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访谈资料,XSF,2015年10月。
以浙师大外语学院学生为主的志愿者充当了日常生活中翻译的角色,他们会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地和参与者一起,同吃、同住、同行。虽然他们的外语交流有一定的水平,但是普遍地却对中国或者金华地方文化了解不深,也导致了文化交流和传达的受阻。国画、书法、传统建筑、婺剧、中医、生活的食物制作,几乎他们涉及的所有传统的内容,都变得难以翻译。“越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越难翻译……越地方专业的东西越难翻译。甚至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偏陌生的。……我们感觉很愧疚又感到很自豪。自豪的是我们拥有这么绚烂的文化,愧疚的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可能只是我们一部分年轻人,没有办法了解得比外国的人更多,不能够用流畅的语言娓娓地向外国友人来介绍或者说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是非常愧疚的、很惭愧的一件事。”*访谈资料:JHQ,2015年10月。
即便如此,如果今后真的要针对外国人来开展“家+”的活动,翻译志愿者似乎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媒介。正如一位南非的参与者所说:“对于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来说,这里可以跟学校合作让志愿者继续来这里合作,也许可以是一天的时间。家里可能有英文的菜单,外国人可以点,但是如果在平时出现了问题没有办法沟通。或许还是可以有志愿者参与到这里。因为住家这么好,完全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项目英文网站媒体是物的层面的文化媒介,它是由外籍专家参与设计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以外籍专家的思维方式在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影像和资料。同时网站又会伴随着项目地开展,不断地把参与者的“作业”——也就是他们对金华/中国的认知、感想以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的方式向全世界传递。因此,网站所展示的金华/中国是“文本的文本”。至于这个文本制作的“认真度”“形象度”“深度”“真实度”如何,项目组和其他人都无法完全把控,通过网站了解中国和项目的人的观点也无法完全把控。
因此,民族旅游是一个文化解读和翻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深度、信度和文化媒介密不可分。
六、多样性:旅游抑或非旅游?
在整个项目的各类相关资料中,有这样几个关键词: “海外学子走进金华古村落”、“研学活动”、 “家+”、“金华homestay项目”。这几个关键词既是旅游的又是非旅游的。 “海外学子走进金华古村落”是一个外事项目宣传的标题,但是外事活动的目的却是为了发展地方的古村落旅游。“研学活动”有很多类型,可以是教育的、学术的,但通常与远距离的空间转换有关系,要在“旅行”中进行。“家+”是一个创新的旅游接待概念,是国际上homestay和中国“农家乐”的综合体。“金华homestay”与国际通行的homestay在名称上虽然一样,但是实际上金华的homestay就是“家+”,与国际上流行的那种完全融入到当地社会家庭生活的homestay有着不一样的地方。该项目的homestay有许多因为民族、政治、行政安排以及本土文化习惯的因素,其“游客”融入感和进入感还处于在表层和前台,尽管这并不影响“好客”程度。因此,从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角度,究竟如何界定这个项目的性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果说它是旅游,那么它多少颠覆了西方旅游人类学当中已经形成的关于旅游的定义,比如有“自由支配的收入”,因为在这个项目中,参与者除了来回路费,21天中所有的费用都不用承担;如果说它不是旅游,这些人又确确实实好好地在“他时他地”游玩了一把,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反结构-再结构”、“阈限前-阈限-阈限后”的游客体验。但无论如何,该项目拟在提升金华以及古村落的知名度,以吸引本土和世界的目光和游客,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它与旅游的联系显然的。但是它性质上究竟如何定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或许正如格拉本所指出“必须诚实地面对我所看到的世界各地千姿百态的旅游模式,而且还试图通过可自由支配收入、文化自信,以及所谓‘世俗倒换’形式的多样性……”[7]17,也或许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如同格拉本先生所说的,要回到“阶级、时代与文化”等问题上的探讨。
于是我们多少会同意,“海外学子走进金华古村落”项目是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时代,作为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的地方,运用创新和创意的方式在创造现代民族古村旅游。它为全世界旅游形式增添了多样性,也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文化的创造、传承、发展和交流的新景观。尽管项目还隐含一些问题,但它在创意性地应对全球化进程过程中,为增进地方社会和文化独特性、多样性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个案。
致谢:
本文的完成首先感谢项目负责人徐淑芳女士,她的邀请使得笔者有机会参与该项目的交流体验和调查。此外,感谢笔者所在工作单位的2014级民俗学研究生阴卫和陈晓芳,他们参加了寺平村项目的参与观察与访谈,并整理了部分访谈资料。最后,本学院2015级民俗学研究生陈逾辉、官茹瑶、赵孟岩以及学院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工作室的本科生成员丁雅琴、张钰、刘晓莉也参加了访谈录音的整理,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1]斯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M].张晓萍,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3-4.
[2]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01(3).
[3]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55-356.
[4]林敏霞.“家园遗产”:情境、主体、实践——基于台湾原住民及“社区营造”经验的探讨[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85-90.
[5]格拉本.好客,一种人类的共通精神:礼物还是商品?[C]//葛荣玲,译.好客中国:旅游高峰论坛2102年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21-28.
[6]URRY J.游客凝视[M].杨慧,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GRABURN 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M].赵红梅,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THOMPSON M.Rubbish theory: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Oxford UP, Design Studies.1980(5):312.Vol.1.
[9]MACCANNELL D.Empty Meeting Grounds[M].Routledge,1992.
[10]ECO U.Travels in Hyper Reality[M]. Harcourt Trade Publishers,1986.
[11]WOOD ROBERT E.1984.Ethnic Tourism,the State,and Cultur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1(3):35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