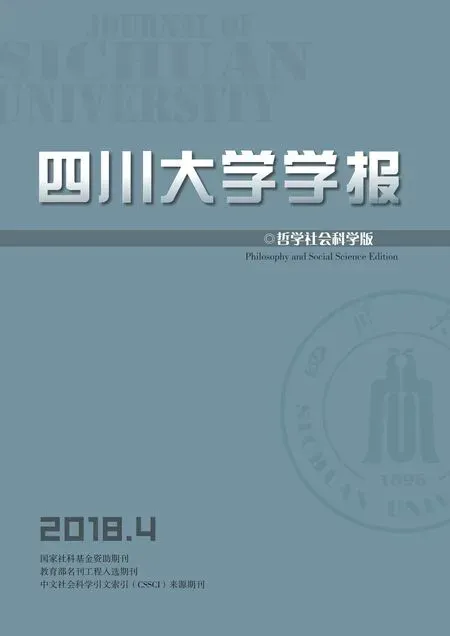边界:美国(文学)研究的范式确立与转换及问题
开始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研究把研究美国以及美国的特征作为目标,文学是其重要的研究内容。检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美国(文学)研究*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美国文学研究,早先的美国研究者很多是美国文学研究者。本文以“美国(文学)研究”这种表述方式指称这两者的关系,在提及美国研究时,重点也放在美国研究角度的美国文学研究。中国学者有关“美国研究”或“美国学”的代表性论述有张涛:《美国学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孙哲:《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1979—200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李青、杨小红:《略论“美国学”和美国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马敏:《美国研究主要学派思想评析》,《集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蔡翠红、倪世雄:《“美国研究”或“对美国的研究”——试析中外美国研究的不对称性》,《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孙有中:《美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赵可金:《“美国学”学科成长与中国意义》,《美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叶英:《中美两国的美国研究及美国学在中国的建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可以发现,其核心内容经历了范式的确立与转换的过程,从起初的挖掘与阐释“美国心灵”(American mind)的意义到后来的“神话-象征”模式的建立,之后伴随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开拓出阶级、性别、种族等方面的美国文学之表征研究,近年来裹挟着全球化的风尚,跨民族视野话题又频频出现。这个范式的转换过程,一方面与美国社会和文化的风向转变相关,如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政治权利运动带来的以多元性为主的文化价值判断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与美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对于“美国性”的探究相连,其中的发生机制对了解美国(文学)研究的过往、当下及未来的思想潮流不无帮助,值得总结。
一、民族与国家意识层面的意义:美国(文学)研究诞生的历史侧影
1945年,年轻的美国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旨在促进国际教育交流的议案,得到国会的积极响应。第二年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份议案,以法定形式确保它的实施,翌年冠以“富布莱特”名称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开始在世界各地出现。*Fulbright Progra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ulbright_Program,2017-9-1.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以向外宣传“美国”的理念,而此前此种行为基本上是由私人渠道来完成,美国政府并不插手。*Lawrence Buell, “Commentary on Henry Nash Smith's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in Lucy Maddox, ed., Locating American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pp.408-409.富布莱特本人之所以提出这个国际教育交流计划,是基于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应“保障盎格鲁-美国文明免于被摧毁”*J. William Fulbright, “Thoughts and Words,”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o.1, 1998, p.129.这个目标的思虑,这自然也符合战后美国总体对外战略。与1947年开始的马歇尔计划一样,富布莱特项目的实施显示了冷战初期美国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是美国政府向外宣传美国民主思想的一种文化策略。
与政府向外行为相关的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美国的人文学界出现了一个“向内转”的现象,一批以美国思想、文化、历史、文学和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专著陆续出版,这些著作的内容各不相同,但研究方式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都试图从总体上探究美国社会在上述这些方面的特征,之后被称为“美国研究”的学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Richard Hofstader,TheAmericanPoliticalTraditionandtheMenWhoMadeIt, 1948)、《美利坚文学史》(Robert Spiller et al,Liter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948)、《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Henry Nash Smith,VirginLand:TheAmericanWestasSymbolandMyth, 1950)、《自由主义的想象》(Lionel Trilling,LiberalImagination,1950)、《美国小说的起源》(Alexander Cowie,TheRiseofAmericanNovel, 1951)、《美国政治的天才》(Daniel Boostin,TheGeniusofAmericanPolitics, 1953)、《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美国革命以来的政治思想的阐释》(Louis Hartz,TheLiberalTraditioninAmerica:AnInterpretationofAmericanPoliticalThoughtsincetheRevolution, 1955)、《美国文学的周期:历史批评论章》(Robert Spiller,TheCycleofAmericanLiterature:AnEssayinHistoricalCriticism, 1955)、《美国的亚当:十九世纪中的天真、悲剧与传统》(R. W. B. Lewis,TheAmericanAdam:Innocence,TragedyandTraditionintheNineteenthCentury, 1955)、《安德鲁·杰克逊:一个时代的象征》(John William Wards,AndrewJackson:SymbolforanAge, 1955)、《美国小说及其传统》(Richard Chase,TheAmericanNovelandItsTradition, 1957)。此后,这种以总体——日后被称为“神话-象征”*1950年出版的《处女地:作为神话和象征的美国西部》用“象征和神话”作为一种修辞方式研究美国西部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后成为一种研究派别,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见Bruce Kuklick, “Myth and Symbol in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No.4, Oct. 1972, pp.435-450. 中国学者对此学派的评述可参见张涛:《神话-象征与美国学》,《美国学运动研究》第五章;胡亚敏:《神话与象征研究》,《外国文学》2014年第1期。为切入方式的研究还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诸如《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Leslie A. Fiedler,LoveandDeathintheAmericanNovel, 1960)、《花园中的机器:技术与田园理想在美国》(Leo Marx,TheMachineintheGarden:TechnologyandPastoralIdealinAmerica, 1964)、《布鲁克林大桥:事实与象征》(Alan Trachtenberg,BrooklynBridge:FactandSymbol, 1965)、《边疆:美国文学和美国西部》(Edwin Fussell,Frontier,AmericanLiteratureandtheAmericanWest, 1965)、《永恒的亚当和新世界花园》(David W. Nobel,TheEternalAdamandtheNewWorldGarden,1968)等代表性著作。*可参阅 Philip F. Gura, “Puritan Origins,” in John Carlos Rowe,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American Studies,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10; Buell, “Commentary on Henry Nash Smith's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金衡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冷战思维下知识分子与美国的认同》,《国外文学》2015年第2期。
与此同时,美国研究的学术刊物和学术研究机构也开始设置和建立。1949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创办的《美国研究季刊》(AmericanQuarterly)出版发行,此后经过1951年岁尾和1952年早春期间的酝酿,“美国研究学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Christopher Moss, “American Studi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pril 2, 2012,https:∥www.reed/am_studies, September 14, 2017.被认为是美国研究进入“成熟期的标志”。*Philip Gleason, “World War I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No.3,1984, p.343.从历史背景而言,这个时期的美国研究与冷战初期的形势错综相连:东西两个世界的对峙在意识形态上尤其凸显其锋芒,显示了文化宣传战略的需要,美国研究也因此无论如何脱离不了与政治需要的联姻。无论是学术团体还是学术研究本身,在冷战后的一些论者看来,都与美国的冷战大局和冷战思维不无关联。*Djelal Kadir, “Introduction and Its Studies,” PMLA, No.1 Jan.2003, p.12; Gura, “Puritan Origins,” in Rowe,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American Studies, p.19但也是在回顾美国研究的发展进程时,有论者发现,美国研究的出现一方面与冷战初期美国的地位需要以及用文化阐释作为支撑依据的努力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历史进程中“对于文化民族主义的自我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觉醒”有关。*Robert E. Spiller, “American Stud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Joseph J. Kawit and Mary C. Turpie, eds., American Culture: Dominant Ideas and Imag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0,p.611.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实际上可以往前延伸到20世纪初期的维农·帕灵顿。帕灵顿著有三卷本《美国思想主流》(MainCurrentsinAmericanThought, 1927),被誉为“美国研究知识领域的开创者”,*Gene 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 A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American Quarterly, No.3, 1979, p.298.他以一己之力并以非学院派研究者的身份梳理、总结、凸显了美国自殖民时代以来的人文思想潮流,确定了在此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人物,为美国的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美国文学可谓帕灵顿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美国文学在美国大学中的教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甚至更前,但直到1918年,美国文学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出现在课程中,此后的很长时间也没有被给予特别的关注。*Spiller, “American Stud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Kawit and Turpie, eds., American Culture,p.207.帕灵顿笔下描述的广义的“美国文学”(American letters)的出现改变了美国文学被遗忘的状况,爱德华兹、富兰克林、杰弗逊、林肯、库珀、爱默生、梭罗、富勒、艾伦·坡等后来被列入经典的美国思想家和作家,都在帕灵顿生花妙笔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详见Vernon L.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Harvest Books, 1954.从而为美国文学的演化基调奠定了基础。在此前后,美国的一些大学也开始了美国思想课程的开设,如耶鲁大学在1926年开设了美国思想和文明课程,*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p.304.十年后哈佛大学开办了“美国文明”项目,招收攻读这个方向的学位生,《美国文学》刊物也在1929年创办。*Spiller, “American Stud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Kawit and Turpie, eds., American Culture,pp.210,207.按照美国研究学者怀斯的说法,这个时候的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躁动,要向传统的学科分界——即美国文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状况发起挑战,其中的一个诉求便是对于“美国心灵”的探寻。*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p.304.这种探寻在随后的美国文学研究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个标志是《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与表达》(AmericanRenaissance:ArtandExpressionintheAgeofEmersonandWhitman)在1941年的出版,该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马西森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帕灵顿开创的文化史的描述,同时确立了“美国的文学身份”。*Myra Jehlen, “Introduction: Beyond Transcendence,” in Sacavn Bercovitch and Myra Jehlen, eds., 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London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2.所谓“美国的文艺复兴”,马西森解释说,“并不是对此前在美国存在的价值的复兴,而是展现美国式的繁荣,展现其第一次成熟期,确定其在艺术和文化进程中的遗产”。*F. 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 Londo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vii.至1947年,超过60所美国高等院校给本科生开设了美国文学课程,*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 p.306.美国文学身份的确立对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自然功不可没,而这与差不多同时期开始的美国(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展开有了近乎完美的衔接。
二、边界与跨越边界:美国(文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与演变
按照提出范式概念的美国科学史学者、哲学家库恩的看法,“范式”的作用是对发展中的学科提供一套指导原则、模式和解决的方法。*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viii.从这个角度而言,帕灵顿的思想史研究具有范式的特点,因为他确立了把美国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从民族意识的高度提出了美国思想的发展脉络,从而为后人探究美国的文化特征打下了基础,而这本身也提供了认识美国社会的指导性原则。就美国研究发展历史的角度而言,怀斯指出,从帕灵顿撰写《美国思想主流》到1965年埃兰·查腾伯格(Alan Trachtenberg)发表《布鲁克林大桥》一书,在这个漫长的时间段里,一直存在着一种“共识”,一种可以泛称为“范式”的东西,指导着人们研究“美国的经历”以及如何进行这种研究。也是在这篇被认为是“引述最多的”*Donald E.Pease & Robym Wiegman, 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p.1.美国研究综论性的文章里,怀斯总结了美国研究从帕灵顿到查腾伯格经历的共识和留下的遗产,主要有五个方面。首先,美国研究确定了“美国心灵”的存在,同时确认这是一种具有统一指向、可以归为一个共同体的思想;其次,研究美国是要区分新世界与旧世界(欧洲大陆)的区别,这一点其实就是没有明言的美国例外论的翻版;再者,美国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一些能够代表美国的人物身上,如从殖民时期的罗杰·威廉姆斯到文化自觉时期的爱默生等;然后,研究的中心集中于与美国相关的一些主题如清教主义、个体主义、进步概念、实用主义、超验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最后,美国研究的对象应该放在“高尚文化”(high culture)上。*以上对怀斯观点的引述,参见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pp.300, 306.
怀斯的总结高屋建瓴,凸显了美国研究的目的和要旨。与此同时,需要总结的另一方面是具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这一方面,著名的美国文学研究学者斯皮勒通过对帕灵顿研究方式的阐释,指出了美国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他在一部论述美国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著作中,将帕灵顿的研究方法对比于此前的文学研究方式,指出以往的文学研究建立在语文学的传统上,即从文学继承的角度阐释作品的意义,而在帕灵顿这里,这种方法让位给了“一种把文学看成是环境的直接成果的理论,既来自于作者经历本身也来自作者经历之外,它让作者的艺术表达臻至完整”。*Robert E. Spiller,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63, p.208.斯皮勒的阐释也是建立在他自己的实践基础上,即把美国文学活动看成是“事实上的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并由此可以深入到“美国的经历”(American experience),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在他于1947年主编的《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以及1955年出版的专著《美国文学的周期》中。
怀斯和斯皮勒从不同的角度总结的美国研究和美国文学研究的指向、目的和方法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了一种中心范式。帕灵顿之后的诸多美国研究和美国文学研究著作都多少表现了各自特有的内容和方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又都可以回溯到上述总结的中心范式上来。因此,我们有必要选择一些代表著作——以美国文学研究或者是包含了文学研究在内的美国研究作品为主,做一番探索,以勘明此种范式所经历的过程。
帕灵顿在《美国思想的主流》一书的导言里,一开始就阐述了他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要阐释美国思想是如何产生、如何遭遇反对、又是如何产生影响以至形成当下的特征的,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他“选择了一条宽阔的道路,融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于一体,而不是狭窄的基于‘美文’的纯文学作品(belletristic),主要研究内容放置于构成文学流派和运动发展的各种势力之中,它们形成了思想的体系,而文学的潮流最终是从中发展出来的”。*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p.ix.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帕灵顿的道路是一条跨学科之路。但是,帕灵顿时期的学科概念与现在的情况应有所不同,不能用现在的跨学科概念去做简单理解。所以,一个更加合理的理解方式是斯皮勒所说的,把文学作为“环境”影响的直接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帕灵顿所言的“宽阔”之路实际上是强调背景的作用,但是这种背景本身是由各种思想组成的,对这些思想的分析应以思想家和文本为基础,也就是直接进入历史的具体语境,同时又从中归纳出代表性的思想潮流,而文学则是放置在这些潮流中加以阐释。这样,怀斯提到的自由主义、超验主义、清教主义等自然成为帕灵顿笔下的主要分析对象。因此,可以说帕灵顿的方法是以历史语境为导向,以核心思想归纳为目的,纵横交错地勾勒出美国思想的发展脉络。与此同时,可以说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从帕灵顿这里一开始就遭遇了跨越,这种范式对日后的美国研究以及美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1年出版的《美国的文艺复兴》对美国文学的研究延续了帕灵顿开创的历史背景说,作者马西森特别强调他要阐释的是作家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一个“铁路、铁船、工厂和全国范围内的工会开始在那些年里成为主要势力”的时代,一个“十八世纪的自由精神与正在冉冉上升的剥削发生冲突”的年代。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直言不讳地对他所理解的帕灵顿的方式提出了批评,认为其研究方法在突破了人为的文学与历史的界线的同时,也有为了讨论思想潮流而把艺术当成表达的工具之虞。在马西森看来,“文学反映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照亮了这个时代”,而所谓“照亮”则是指文学本身的作用,文学不仅仅反映了历史大潮流,它也有“自己的生命”。*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pp.ix, x.批评家甑林(Jehlen)在评述马西森的研究方法时指出,马西森所坚持的历史观针对的是从30年代开始的新批评,后者的态度是反意识形态的,但同时马西森又采纳了新批评对主要作品的重视态度以突出其经典性,他所谓的“美国的文艺复兴”本身含有经典塑造之意。在很大程度上,马西森的这种试图与帕灵顿式的历史研究有所区别的美国文学研究方式开创了另一类研究范式,发展成了“一种新的形式”,即以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为主,以对主要作家的阐释为手段,梳理美国文学表现的特征,在此之后,也出现了一批与其相似的美国文学研究著作。*Jehlen, “Introduction: Beyond Transcendence,” in Bercovitch and Jehlen, eds., 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pp.2, 3.而另一方面,帕灵顿的方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继而发展成为了著名的“神话-象征”研究模式。需要说明的是,两者的研究模式并不是一种截然相对的关系,而是互相借鉴,历史背景与文学阐释的关联无论在哪种方式中都始终是一以贯之的,所不同的是,马西森式把中心放在文学上面,而帕灵顿式则是把文学纳入整个思想或者是文化的大潮之中,因而也更加靠拢一般意义上的“美国研究”,但不可忽视的是两者的目标指向皆是对“美国心灵”的阐释和揭示。
沿着这个线索,对一些代表性研究作品进行一番剖析,便可看出其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与渊源关系。例如,1942出版的《扎根本土》是一部阐释现代美国文学和文学思潮的著作,“被公认为是美国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常耀信主编:《美国文学研究评论选》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6页。该书也是“第一部关于现代美国文学思潮的长篇专论”,而且从方法论上而言,其作者卡津——年轻的非学院派文学批评家、纽约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与马西森的文学研究思想有类似之处,他在此书的序言里开门见山地对30年代以来占据美国文学批评界的两种风潮展开了批判,即专注于所谓“美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的批评思潮,前者指新批评,后者指30年代盛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详见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7-120页。卡津指出,文学研究不能忽视文学本身,也不能忽视文学赖以产生的社会土壤,这两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换言之,“文学并不是由‘社会’生产出来,而是产生于一批批的个人,产生于个人的情感、知识和才能”。这一点与马西森所说的文学有“其自己的生命”,文学能够“照亮”一个时代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评述帕灵顿的文学批评方法时,卡津也对其过分强调历史决定因素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认为帕灵顿评述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格兰特将军非常出色,而评论霍桑则颇为蹩脚,原因在于,在帕灵顿看来,“格兰特是创造了‘历史’,而霍桑则仅仅是‘反映’传统”。卡津的批评或许更多地是缘于他对其时泛滥的简单反映论的反感,但他把这种反对的情绪投射到了帕灵顿身上,难免失之偏颇。事实上,帕灵顿对霍桑以及其他文学家赋予了足够的重视,与评述别的思想家们一视同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卡津在著作中如同马西森一样,把现代时期的一些美国作家作为重点一一加以评述,为这些作家进入经典行列做出了贡献。他评述的作家包括豪尔威斯、华顿、德莱赛、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福克纳等,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卡津并不是孤立地评论这些作家,而是将其放置于社会和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中,如20世纪初的民粹主义,之后的进步主义以及来自欧洲的自然主义等思潮都成为了卡津笔下纵论的对象。不仅如此,除了作家以外,卡津论述的对象也包括产生思想影响的非文学家,如经济学家、《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勃伦。他从这位经济学家看待现代世界的批判态度入手,分析其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从中发现了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经历的“机器过程”。这种从文学角度切入的分析,既有历史的维度,又有文学与思想的深度,把历史观与文学渗透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其实是延续了帕灵顿与马西森开创的研究方向。卡津这部作品结尾部分以“美国,美国!”为标题,他总结说他所论述的是“美国意识”,追寻的是“美国的传统”,而这来自于“美国人民的故事”,也是基于一个“民族的自我发现”。*以上对卡津观点的引述,参见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An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American Prose Literature, Sa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 A Harvest Book, 1995, pp.xxv, 163, 140, 485.这自然也是怀斯所说的对于“美国心灵”的探索,与帕灵顿与马西森的传统是一致的。
卡津所说的“美国传统”是一个广而言之的概念,在另一个研究者的论说里则被压缩成了美国小说的专有“传统”,由此也可以进入对美国文化之特征的理解。1957年出版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一书从阐述美国小说传统的角度出发,强调了美国文化中固有的思想渊源和表现形式。作者蔡斯阐明了美国文学一个固有的特征或传统,他用传奇小说(Romance)一词来界定这个特征以区别于一般的小说(Novel),分析了从早期的布朗到霍桑、麦尔维尔、詹姆斯再到20世纪的菲兹杰拉德和福克纳等一些具有这个特征的作家的作品,从中勾勒出了美国文学的传统脉络。蔡斯区别了传奇小说与英国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小说,认为传奇特征赋予了美国小说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情节夸张和牧歌情调”,更多的“朝向意识的底层,一种摒弃道德问题或者是忽视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意愿”。而这与美国本土具有的“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之精密的深邃,源于启蒙时代的怀疑与理性思想以及富有想象自由的超验主义”紧密相关。显然,这些思想在蔡斯看来是构成美国文化的要旨,也是形成美国小说之固有特征的渊源。从这个角度出发,蔡斯在具体作品分析时,充分利用了这些思想资源,把作品与美国的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考虑,如他把霍桑的《红字》看成是源于清教主义的寓言,认为霍桑的清教虔诚思想与理性精神间的矛盾,让小说的人物也沾染上了浓厚的性格冲突色彩,主要人物海斯特既有“女王般的傲慢”,也有常人的“脆弱”,这让该人物形象具有一种“吸引力”,产生一种“经久不衰”的力量,致使其成为一个“永恒的女人”,一个“永恒的人”。*以上关于蔡斯观点的引述,参见Richard Chase,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7, pp.viii-ix, x, 77.在用传统的文学手段分析作品的同时,蔡斯也凸显了美国思想的塑形作用,尤其是在文学的表现上,美国思想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种局限于文学内部的分析,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与卡津将作家作品置于历史大背景下的阐述不尽相同,*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第123页。但在指向美国文化特征的表现方面,依然可与之相提并论。
这种基于美国传统思想的对美国小说特征的探究,在1960年出版的《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中再次得到确认和强调。作者费德勒认为,美国小说从本质论是非现实主义的,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而且“早在象征主义在法国发明以及进入美国以前,(在美国)就有了完备的象征主义的本土传统。它诞生于我们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深刻的矛盾与冲突,并由来自于清教思想的遗产得到延续,清教主义的一种‘典型’(也是寓言式)的表达方式是把感觉世界看成一个可以解码的符号系统,而非最终的现实世界”。当然,费德勒这里所说的“符号系统”不是后来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由语言构建的符号系统,而是指无处不渗透的美国思想传统——如清教思想,在人们生活中的表现。这使得美国小说从布朗到福克纳和威尔蒂,形成“一种哥特式的小说,非现实的和否定的,自虐的和夸张的,一种在阳光和肯定的大地里充满了黑暗和怪诞的文学”。*以上引述参见Leslie A. Fiedler, 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69, p.9.从费德勒的探寻核心象征手段的研究方法里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受到了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费德勒也延续了从整体的角度探讨美国文学中的美国性的努力。
如果说马西森开创的方法经由卡津和蔡斯再到费德勒,文学研究中美国的特征一步一步得到确证,同时原有的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方式逐渐向着纯文学研究的方向靠近,那么,帕灵顿式的融历史、思想、文学和政治于一体的“宽阔”研究法则在其身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在50年代及其后的神话-象征研究体系中达到了高潮,被认为是美国研究的典型方式,而其中也蕴含了诸多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1950年出版的《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是神话-象征研究学派的开山之作,作者史密斯是第一个获得美国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的学者,他在这部作品中从历史、神话人物、政治辩论、经典文学和通俗小说等多个方面入手,探究美国西部如何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和文化典型,也即富有道德内涵的农业和“花园神话”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所谓象征与神话是指在话语层面上的信仰及其发生的影响力,也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史密斯在该书的序言中对此进行了解释:“我所使用的神话和象征含有一种广泛的特征,表现为一种集体的表征,而不是某个单一思想著作的表现。我并不是要证明这种想象的产物可以准确地反映与经验相关的事实。但是正如我试图努力表现的那样,这种想象的产物确实有时候会对实际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xi. “花园神话”之说,参见该书第203页。显然,史密斯所谓“想象的产物”与意识形态相近,只是后者含有太强的政治意味以及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多年后史密斯对自己为什么不用这个词也做了解释。*Henry Nash Smith, “Symbol and Idea in Virgin Land,” in Bercovitch and Jehlen, eds., 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p.22.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史密斯所提倡的“神话-象征”手段,亦即从不同的话语表述中发现共同的内容指向,通过具体文本和语境的分析找出共有内容的形成轨迹,用帕灵顿的话来说,这就是“主流”思想的表述。就研究方法论而言,史密斯突出了跨越学科边界的努力,用一种综合的方式寻觅美国文化中的核心思想及其象征形式。其中文学也自然成为了表述方式之一,史密斯专门用一个章节的内容论述惠特曼与美国历史中的“天启命定”的关系,并从诗人的一些诗作中读出其对这种“引导美国走向太平洋的帝国路线的命定过程”*Smith, Virgin Land,p.45.的兴趣,尽管篇幅不多,但文学在“神话”形成中的作用还是得到了强调。
神话-象征学派的研究方式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回应,1955年出版的《美国的亚当:十九世纪的天真、悲剧和传统》即是一例,作者路易斯在书的开篇就直截了当地说,写作此书与勾勒“本土的美国神话”有关。如同史密斯,路易斯也指出美国的“神话”是一种“集体的行为”,必须从“文章、演说、诗歌、故事、历史和布道这些不同类型的作品中串联成篇”,而之所以把《圣经》中的亚当作为一个象征,是为展现“新的美国场景”,“新的个性”,“新的英雄冒险行为”,因为亚当是“一个脱离了历史、乐与先祖分离的个人,未被家庭和种族的遗产羁绊和玷污,一个独自站立、自力更生、自我奋进的个人”。*以上关于路易斯观点的引述,参见R. W. B. Lewis, The American Adam: Innocence, Tragedy 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p.1, 4, 5.显然,路易斯是借用这种纯洁而天真的形象来勾勒19世纪美国文化演变的过程,他讨论的人物包括哲学家、神学家、通俗小说作者、诗人以及作家等,其中库珀、霍桑和麦尔维尔是其讨论的主要对象。路易斯的研究方式既有神话-象征方式的特征,也吸取了卡津思想潮流纵论的手段、帕灵顿学科跨界的路径,以及马西森对作家作品细读式的探究,文学、文化与历史的融合指向的是对美国思想背景的烘托。这种纵论式的研究十年后在《花园里的机器: 技术与田园理想在美国》一书中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展现,作者马科斯以田园意象为中心,上溯古罗马维吉尔笔下的牧歌传统和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田园象征,下及美国作家霍桑、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等在作品中对田园意境的表述和由此产生的情感的纠结,并以美国历史和文化中各个方面的人物对田园意象的阐释为背景,深刻剖析了田园意象在美国人生活中构成的文化情结,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对于在荒蛮与人工自然间的“中间地带”生活状态的渴望和面对以机器为象征的工业化时代到来的既欢迎又抵制的矛盾心理。马科斯在史密斯的基础上,通过对田园理想的梳理和阐释,揭示了美国人对于自然的热爱、利用与神化、挪用的态度,并从这个角度解读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以及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隐藏的象征含义。例如,前者描述哈克与吉姆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竹筏遭遇蒸汽船的撞击,可以看作是机器对于田园的侵入,不过,马克·吐温并没有扩大这种遭遇带来的冲突,而是让哈克和吉姆继续有机会在大河上自在活动,说明了自然对于机器危害的克服,因为在马克·吐温的时代,自然依然可以起着调和机器的影响的作用;后者从东西部的对峙以及金钱与理想、当下与过去间矛盾的角度,预示了田园意象在工业化时代将不可避免地逝去。*以上关于马科斯观点的引述,参见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88, 155, 335, 364.马科斯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美国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欣慰与苦痛体验的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花园里的机器”也成为了一种神话与象征的话语。
综合以上对美国研究代表作的探索和分析,不难看出,这些研究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目的和宗旨非常一致。斯皮勒在上世纪70年代初曾总结说,在文化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对于一种真正的美国文化的承认并不容易,但却是必要的”。可以说这些研究体现了这个“必要”。斯皮勒同时也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了这些研究,他用了两个关键词:“综合”(synthetic)和“整体”(holistic),前者指跨越学科界线以指向一个核心,后者指在文学研究中利用其他学科如深层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方式,这本身也是一种边界跨越的方式。*以上对斯皮勒观点的引述,参见Robert E. Spiller,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Culture: 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in Perspectives,” American Quarterly, No.5,1973, pp.613, 614.这两个关键词其实反映了一种认识,即美国文学研究要放在美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同时需要找寻如何体现美国特征的路径,要达到这个目的,对学科“边界”的跨越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三、统一共识的瓦解:美国(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无论是怀斯所说的对“美国心灵”的探索,还是斯皮勒所言的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探究,以此为目标的美国(文学)研究都是建立在一种共识的基础上。但这种情况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变化,受其时正在纷纷兴起的各种新型研究类型的影响,如黑人研究、妇女研究、少数裔研究、通俗文化研究、民间文化研究、青年研究、电影研究、第三世界研究、本土美国人研究等,美国(文学)研究再也无法保持统一的取向,故怀斯感叹于美国研究曾赖以生存的共识的“分崩离析”,指出“类似以往神话-象征模式那样的发挥很大影响并能够统领文化理解的研究很少见了”。*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pp.312, 314.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文学)研究开始呈现新的研究方向,一些论者甚至考虑起未来的美国研究模式。在2002年出版的《美国研究的未来》一书的序言中,身为新美国研究代表人物的该书主编皮斯和韦格曼开宗明义地指出,“此书的作者们并不认为美国研究这个领域可以归纳为一种单一的、广为有效的范式,他们同时也不认为这个领域的历史过程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一种在不同的范式中占据一个统一的位置的努力”。*Donald E. Pease & Robym Wiegman, eds., 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言外之意,一方面是要反思过往单一模式占据主要位置所导致的思想过于统一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在开拓新模式中,要避免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些模式占有压倒性位置,再次一统天下。在同年出版的《新美国研究》一书中,另一位代表人物罗厄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新美国研究需要借鉴比较文学领域正在开展的对原有的世界文学范式的挑战,“重新组织其学术研究和课程设置”。*John Carlos Rowe, The New American Studies, Minnes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xiv.这几位新美国研究学者针对的靶子是以往研究的共识,即美国文化的独特性,他们将其视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John Carlos Rowe,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American Studies,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10, p.2.目的是“研究和理解美国的地缘政治界线”。在诸如斯皮勒等以往美国研究代表人物看来,这种研究本无可厚非,且恰是美国研究的要旨所在,但在新美国研究者眼中,这正表明了美国研究与“例外主义国家机制的共谋认同”,*Pease & Wiegman, eds., 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 pp.6,24.而这则是需要被抛弃的,因为例外主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政治中,都为美国形象的统一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其实这背后体现的只是以白人种族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在这个大一统价值体系的笼罩下,很多时候,美国固有的矛盾,如种族、阶级和性别矛盾等都被掩盖了起来,甚至被抹去了踪影。而这些正是6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强劲的多元文化观所批判的对象。这种批判的行为适应了其时正在发生的社会氛围的变化,而新型研究方式的出现也为美国(文学)研究的转向提供了学术资源和理论基础。如果说从50年代起走向繁荣的美国(文学)研究范式,缘于对美国文化特征的整体探索的动力,这是一种“向内看”的努力的结果,那么60年代中期后所谓新美国研究则是要打碎整体的概念,而这也是一种“向内看”的结果,不同的是,前者是基于一种抽象的、凝缩的角度看待美国,也因此总结为几种可以作为依据的主流思想脉络,如清教主义、超验主义、自由主义、田园理想等,而后者则是要打破这种主流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被忽视的美国现实出发,如种族问题、性别问题、阶级问题、生态问题、政治区域问题等等,探讨范围更加广泛的美国特征。所以,前者的“向内看”是要凝聚起统一的态度和思想,以深入探析在其看来是可以代表美国的一些“例外性”特征;后者的“向内看”则是从美国的现实出发,在很大程度上否定统一的倾向,由内向外推翻所谓“美国心灵”之普遍存在的理念,并进而对其进行解构与颠覆,以揭示其虚幻的存在和意识形态的作用。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在新美国研究的旗帜下出现了诸如美国的帝国主义研究、后民族与后殖民研究、白人性研究、性别与小说研究、劳工文化研究、种族建构研究、全球化研究等,*本世纪初,美国国务院下属教育和文化事务局邀请著名美国文学研究学者埃默里·艾利奥特及其学生编写了一个介绍新近美国文学研究新方向的小册子,内容包涵对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发表的各个方面、应用各种手段和方式的美国文学研究著作介绍。见Emory Elliott and Craig Svonkin,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Literary Scholarship: 1980-2002,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4.这些方面的研究很多未被以往的美国(文学)研究涉及过。这种旨在开掘曾被压抑的领域的研究在思想指导上其实是受到了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以至于美国研究本身在一些论者看来应该改成为“美国文化研究”。*Jay Mechling, Robert Merideth & David Wilson, “American Culture Studies: The Discipline and the Curriculum,” American Quarterly, No.4, 1973, p.372.以文化为切入手段,实施政治讨论与讨伐之目的成为了新美国研究的普遍规律,但在方法论上,新美国研究则也是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论证,从这个方面而言,与以往的美国(文学)研究走的路子是相通的。换言之,就方法论而言,其实以往的美国研究早已经具有了文化研究的雏形,不同的是,新美国研究的跨学科式的文化研究手段得出的结果往往是对以往美国研究中通行的认识的修正、批判和颠覆。从这个意义来说,新美国研究继承了6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的衣钵,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依兰·鲍德温等所言,文化研究的理论核心是“关于权力与表征的问题”。*Elaine Baldwin, et al.,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所谓“权利”(power),是指福柯所阐释的在文化领域内的压迫与反抗的关系,而所谓表征(representation),则是指文本的字里行间隐藏的、因此也可以被挖掘和发现的权力斗争的表述,这是新美国研究极力耕耘之处。如,罗厄通过探讨霍桑和亨利·詹姆斯与19世纪一些美国雕塑家尤其是女性雕塑家的关系和对他们作品的评价,分析这两位男性作家相关作品中的男性焦虑情绪,由此认识19世纪性别、性关系、性表现和女性性意识的变化轨迹,以及两位男性作家代表的白人中产阶级对此所持的反对态度。*Rowe, The New American Studies, pp.83-112.罗厄的分析旁征博引,将文学文本的解读放置于文化与政治氛围的大背景下,显示出一种明显的文化研究的手法,而最终目的是对传统的价值观,即白人中产阶级的性观念的犀利批判,这自然超越并颠覆了以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但其研究的基本路径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方法。换言之,无论是传统的美国研究还是新美国研究,其实都是通过历史、文化、政治、文学等方面的综合,找出一条通向问题的核心之路,斯皮勒所说的“综合”与“整体”至少在方法论上还是有适用的价值。只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综合”并不意味着内容的“整体为一”,不再同一的“美国”在以批判为主的研究的鞭挞下,其合理与合法性甚至也遭遇了危机。即便是“美国研究”之“美国”(America/American)的含义也引来了质疑,认为“美国”(America)不能只是指美利坚,而是指整个美洲。*Jan Radway, “What's in a Name?” in Pease & Wiegman,eds., 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pp.56, 63-64.看似只是名字上的变化,其实也暗含了诸多颠覆性的力量,与此相关的跨民族视野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因其对历史上“美国”观念的文学表征的梳理、进而展现其意识形态作用下的霸权含义,并进一步揭示以“美国”替代整个美洲以及世界的意图,因此也成为了撼动传统美国(文学)研究的又一根致命稻草,*金衡山:《美国文学研究中的跨民族视野》,《国外文学》2009年第3期,第12页。构成了“跨越边界”的另一种范式。
但是,在另一方面,颠覆性力量无论如何强大,分崩离析的音调无论如何高昂,新美国研究无论如何激进,其“民主话语”*Pease & Wiegman, eds., 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 p.32.的姿态不会改变,绵绵延续的自由主义传统不会改变,反而更加凸显,也就是说在本质上与以往的美国研究的共同之处并没有改变。马西森把他论述的浪漫时期的五位美国作家的作品定义为“为民主而作的文学”,而民主的含义表现为“朝向还是反对人民”。*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p.xv-xvi.这种简单但影响深远、带有古典式意味的“自由主义”传统,*参见张涛:《美国学运动》,第162、228页。更是帕灵顿阐释的主要内容,也一直在其后的美国研究中闪烁光芒,甚至在新美国研究中被发扬光大,区别在于,在后者的论述中“民主话语”更加多元,也更加激进。在这个方面,著名美国研究学者迈克尔·丹宁的劳工文化研究可以为例。1997年出版的《文化阵线:二十世纪美国文化的劳工化》是丹宁美国研究的力作,被誉为是打破了以往神话-象征体系占据天下的局面,挖掘了被“文化霸权”压抑的领域。*Pease & Wiegman, eds., The Futures of American Studies, p.29.此作关注的是30年代开始到4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经历的“红色”时期,期间以“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为领导路线的左翼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劳工运动与左翼知识分子携手奋进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书中丹宁提出了所谓“文化阵线”,即以劳工的角度透视文化的影响,从劳工层面分析文化的作用,这是以往的“红色”文学研究未曾涉及到的。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人民阵线”运动是一场“激进的社会-民主运动”,推翻了以往认为的是以美国共产党为主的左翼领导运动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而言,丹宁不仅仅是提供了不同的观点,更是从这场运动的民主性质中寻觅出了其时被遮掩的“美国性”。在论述“人民阵线”如何团结社会各类人的过程时,丹宁指出:“在‘人民’的名义下,这种人民阵线文化力图打造少数裔和种族的联盟,在盎格鲁美国文化、少数裔工人文化以及非裔美国人文化之间协调磨合,部分方式是通过重新唤起‘美国’这个表述的意义,想象存在着一种‘美国主义’,能够给那些少数裔工人提供一个有用的过去历史,那些人因为各种少数裔背景都被视为是外国人。”*以上关于丹宁的观点引述,参见Michael Denning, The Cultural Front: The Labou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7, pp.xviii, 9.换言之,丹宁一方面发现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发现阐述了“美国”以及“美国性”的作用,即便是在“红色时代”,“美国性”依然是统领美国人的思想武器,与人所皆知的“大熔炉”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这与传统美国研究的宗旨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发掘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机制。
上文已提及怀斯感慨自60年代中后期始,建立在一种共识基础上的美国研究影响不再,他甚至指出,“从学术角度而言,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寄生虫’——靠着别人创造生活,而不是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过同时,他也激情昂扬地说,“但事实上,(美国研究)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和健康”。这是因为它已经越过了以往的预设,即认为只存在着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美国文化”、并通过“美国心灵”得以表达的预设,现在的美国研究承认并不统一的共识,即美国文化在不同的层面表示出不同的内容,这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总结,即,“复数的而不是单一的,对于特殊者的重新发现,在文化体验方面对于阶段而不是本质的重视,以及美国研究的跨文化的、比较的维度”。*以上关于怀斯观点的引述,参见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pp.315, 317, 332.怀斯的文章写于1979年,正是多元文化思潮在美国起兴之时,他对其时美国研究学术方式的批评可谓醍醐灌顶,至今这种借用各种文化理论的套路依然大行其道,但同时他似乎也从打破“共识”的各种努力中看到了美国研究继续前行的希望,因为这种“民主话语”正是美国研究原本要挖掘的资源。
从文学研究本身来看,这也是一个边界跨越的过程,从早先的对“美国心灵”的探究到新近的跨民族视野的探索,文学研究的边界时时遭遇跨越的洗礼,文化研究的渗透打破了纯文学研究的界限,而泛政治化的敏感则使美国文学价值判断的共识不再具有统一性。这个变化的过程似乎也呼应了当下美国文学创作的趋势,*2016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分别给予了两部少数裔作者的作品:Viet Thanh Nguyen,The Sympathizer和Colson Whitehead,The Underground Railroad。前者是越南裔美国人,后者是黑人。同一年的曼布克奖授予了一位非裔作家的作品: Paul Beauty, The Sellout。多元与边缘的声音成为了传统主流缺场的代名词。但另一面,无论研究范式如何转换,无论美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如何走向多元,美国文学本身与美国文学的研究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与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当代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沃尔泽指出, 美国文化可以呈现多面化(manyness),以与移民来源相关的文化而言,美国流行诸如非裔美国文化、亚裔美国文化、华裔美国文化、墨西哥裔美国文化等等,美国人的自我称呼在很多程度也与这种文化身份相关,如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等等,这种身份文化现象是多元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础,但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社会则是一元化的(oneness),*Michael Walzer,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American,” in金衡山主编:《美国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2页。而所谓一元化的政治指的是美国式的价值观,即民主、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等观念。新美国研究在研究内容大大拓展的同时,在对美国的历史和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刷新了“美国”的形象,但背后依赖的价值观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一如既往地加以深化,就这个方面而言,新美国研究是另类的“美国心灵”的挖掘与展示。因此,可以说,无论边界遭遇多少次的跨越,划定美国社会与美国人的边界其实一直在被跨越的过程中保持不变,哪怕只是隐秘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