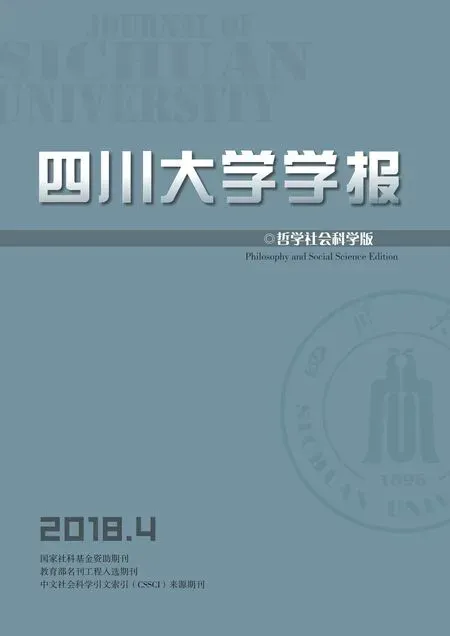19世纪后期新奥尔良的种族重构
——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中的种族主义思想分析
叶 英
19世纪后期,美国南部最突出的种族问题是奴隶制废除以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南部重镇新奥尔良的种族问题因其格外复杂而尤为突出,因为它不仅涉及白人和黑人,还涉及非黑非白却且黑且白的人,尤其涉及对黑人的重新定义。历史上,新奥尔良曾是法属和西班牙属殖民地,其种族观念独特,种族成分复杂,种族关系盘根错节,由此产生的社会分层与美国大部分地方都有所不同。南北战争之后,随着奴隶制的消失、南部重建的深入以及“北佬”的大量涌进,旧的种族观念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在种族观念上如何与美国主流种族观念相融,以及如何在新的种族观念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如何在种族上归类那些非黑非白却且黑且白的人?这些都是新奥尔良当时所面临的难题。以这一时期的新奥尔良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觉醒》(1899),就隐含着新奥尔良上流社会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觉醒》是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代表作,也是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因此,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女性主义视角,或分析女主人公埃德娜的自我意识、自由意识、主体意识乃至性意识的觉醒,或探讨上述意识的建构与解构。尽管有学者注意到该书具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发现其“故事背景充满姓名不详、相貌不明、被精心划分为布莱克、摩拉托、夸德隆、格力伏的黑人妇女”,*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4.认为它“既反复捕捉到埃德娜那些熟人的性别歧视也捕捉到他们的种族偏见”。*Anna Shannon Elfenbe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An Assault on American Racial and Sexual Mythology,” Southern Studies,Vol.26, No.4, 1987, p.306.但遗憾的是,囿于女性研究的视野,*如认为肖邦以黑人为客观关联物来表达女性所感受的压迫,将中产阶级白人的婚姻类比黑奴制,以说明女性的不自由,参见Helen Taylor, “Gender, Race, and Region,” in Kate Chopin, The Awakening, ed. by Margo Culley, New York: Norton, 1994, p.307. 或认为肖邦含蓄地将埃德娜与有色人种妇女相提并论,从而在刻画这个与传统女性形象相悖的人物时得以颠覆文学的刻板印象和盛行的偏见,对埃德娜与此类妇女互动的现实主义处理,则暴露出她生活于其中的克里奥尔社会之性偏见和等级偏见,参见Elfenbe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p.306. 或认为小说中的有色人种妇女使埃德娜的“解放”成为可能——作为家仆,她们将她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见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p.74. 或认为尽管那些异族女人将埃德娜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但由于她们象征着她所处的阶级地位以及与该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性约束,故颇为矛盾的是,她们“既是她获取解放的条件也是她通往自由的障碍”,参见Michele A. Birnbaum, “‘Alien Hands': Kate Chopin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Race,” American Literature, Vol.66. No.2, 1994, p.307.上述关注并没有引发对种族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托妮·莫里森指出,黑人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它贯穿美国历史,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和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故思考黑人的存在对了解美国文学至关重要。*参见Toni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pp.4-5.莫里森此番话对于重新审视《觉醒》一书不无启发,思考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存在是解读该小说种族主义一面的关键所在,但对于小说的这一面,女性主义解读是比较苍白无力的,而单凭传统的文学分析手段,如对人物、情节、叙事、语言等方面的分析,也是不够的,故本文尝试聚焦黑人在小说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存在及存在方式,在细读小说文本和研究其历史文化语境的基础上,依据种族建构理论来剖析小说主叙事之外的文本细节,以此揭示该作如何回应了新奥尔良当时所面临的种族难题,如何参与了对种族观念和种族身份的建构。
一、从“生物决定论”到“社会建构论”
沃纳·索罗斯曾建议将新的种族理论用于美国文学批评。他说:“文学批评家很少在新的种族理论的语境下去充分赏析手中的作品。”*Werner Sollors, 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1.种族理论有新、旧之分,足见人类对种族的认识绝非今日才有。实际上,早在达尔文提出其进化论以前,西方国家就出现过诸多关于种族的学说和理论,如人类同源论、人种多元发生说以及颅型学等。继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又涌现了重演论、幼态成熟学说、刑事人类学、智商遗传理论等林林总总的相关理论或学说。*参见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pp.20-27.这些理论或学说虽然观点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认为种族乃生物类别,种族差异(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皆由生物性遗传差异所决定,即所谓生物决定论。
非裔美国学者W·E·B·杜波伊斯在1897年对此观念提出了质疑:
在探讨种族的本质差异时,我们发现很难立即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过去人们提出了许多判断种族差异的标准,如肤色、头发、颅骨测量,……在这些方面,人类确有很大不同,……这些身体特征都显而易见,倘若它们能彼此吻合,那么人类的分门别类则将轻而易举。不幸的是,对科学家来说,此类划分种族的标准是那么令人恼怒地交织在一起:肤色与头发并不匹配,因为许多深肤色人种长着直发;肤色与颅骨也不匹配,因为黄皮肤的鞑靼人有着比日耳曼人还宽大的头颅。
杜波伊斯认为人类的身体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其历史差异,在身体差异之外存在着另一些差异,它们或许微妙、细腻、难以捉摸,但却悄然无声且毋庸置疑地将人划分成了不同种族。而所谓“种族”,他认为“就是人类的一个大家族,是一个有共同血缘和语言,有共同历史、传统和激情的大家族,其成员往往会自觉或非自觉地一同努力,去实现某些明确或不甚明确的生活目标”。*以上对杜波伊斯观点的引述,参见Philips S. Foner, ed., W. E. B. DuBois Speaks: Speeches and Addresses, 1890-1919,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pp.74-75, 75-76.显然,杜波伊斯对种族的定义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而这在当时并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
不过,继杜波伊斯之后,尤其是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否定了生物决定论,相信种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如弗雷德里克·巴斯指出“族群是个社会组织形式”。*Fredric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p.13.沃纳·索罗斯将“发明”一词引入对种族、族性、民族主义的讨论,取其“虚构并不真实存在的事物”之意,说该词可以“促进人们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构建性之认识”,他赞同并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国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它在国民并不存在的地方发明了国民”这一观点,有助于解释族性和种族。*Werner Sollors, ed., Invention of Ethni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x, xi.伊恩·哈尼·洛佩斯提出“种族捏造”这一概念,宣称生物意义上的种族是个幻象,肤色本身并不能成为划分种族的手段。他认为,种族是“由其形态和(或)祖先的一些在历史上偶然、在社会上意义重大的元素松散地捆绑在一起的一大群人。……种族应被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在此现象中,竞争激烈的意义体系将身体特征、相貌和个人特点联系在一起。换言之,社会意义将我们的相貌与灵魂连接起来。种族既非一种实质也非一种幻象,而是一种受制于社会性和政治性斗争之宏观影响以及日常决策之微观作用的持续、矛盾和自我增强的塑性加工过程”,也即是说“种族是可塑和易变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任意选择”,所以,“种族必须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种族分类的源头和始终不变的基础只能是人类的互动,而非人类的自然差异”。*参见Ian F. Haney López,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ce,” in Richard Delgado & Jean Stefanic, eds.,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Cutting Ed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42-246, 240, 241, 243.
简言之,人类对种族的认识是从过去的生物决定论发展为今天的社会建构论的。肖邦创作和出版《觉醒》的年代恰值前者盛行之时,而她在小说中对19世纪后期新奥尔良市多样化族裔进行的种族建构,又正好与后者相吻合,甚至可以说是对该理论生动而现实的演绎。鉴于此,从种族的角度对该小说进行一番审视,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被高调显示的黑人血统
从种族的角度来审视《觉醒》,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书中那些几乎无处不在的“黑人”*为行文方便,泛指有黑人血统的人。下文将谈及在不同历史语境下该词词义的变化。身影——那些白人家里的黑人保姆、厨娘、女佣、男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黑人,几乎没有一个称得上是人物,他们大多姓名不详,相貌不明,个性模糊,沉默无语,像影子一般飘浮、出没于故事的背景之中。E·M·福斯特把小说人物分为浑圆和扁形两类,说前者是个多面体,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化,后者是围绕着某单一观念或素质而塑造的单面体,用一句话即可形容且不会被环境所改变。*参见E. M. Fo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pp.73-74.以此来看,《觉醒》中的黑人显然算不上浑圆人物,因为他们既无多面亦无变化,但也算不上扁形人物,因为单面体也该有其代表着某种观念或素质的个性,可他们基本是同一类型,即便代表了某种观念或素质,那也是作为群体而不是个人来代表的。
作为个体,黑人们个性模糊,但作为群体其存在却异常醒目。《觉醒》讲述的是新奥尔良一位白人女子埃德娜自我觉醒的故事,即她由浑浑噩噩、习惯性地服从传统到日渐觉醒乃至以死抗争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这一转变过程。在此故事主线之外,小说敷设了拉蒂诺太太、赖茨小姐、勒布伦太太三位白人女子的故事,分别代表传统观念中白人女性在已婚、未婚和守寡这三种情况下社会默认的生存模式,以此突显埃德娜对传统的叛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纯”白人社会的故事;但从深层上说,它又绝非一个单纯的白人故事。小说共106页,*本文所用版本为Kate Chopin, The Awakening, ed. by Margo Culley, New York: Norton, 1994.就有60页涉及他种族和他民族,尤其是书中处处闪动着黑人的身影,让人绝对无法忽视其存在。当然,这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新奥尔良历来不乏黑人,早在18世纪初黑人就与奴隶制一道被引入路易斯安那。*参见Alice Dunbar-Nelson, “People of Color in Louisiana: Part I,”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1, No.4, 1916, pp.361-362.自内战以来,新奥尔良的黑人人口日益攀升,而白人人口却逐渐下降。“在19世纪70年代,白人人口从144601下降到140923;黑人人口从24074上升到50456,几乎翻了一倍,……到了19世纪末,黑人人口跃至287104,占该市总人口的27.1%”。*Dale A. Somers, “Black and White in New Orleans: A Study in Urban Race Relations, 1865-1900,”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40, No.1, 1974, p.21.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觉醒》这么一个关乎白人女性的故事,却充斥着黑人身影的历史原因。
除了比比皆是的黑人身影外,另一惹人注目的现象是对黑人的称谓。小说中的新奥尔良民族混杂,种族多样:埃德娜是来自肯塔基州的英裔美国人,庞特里耶和拉蒂诺夫妇的祖先为早期法国移民的克里奥尔人,玛丽奎塔为西班牙后裔,安托万太太是阿卡迪亚人,塞莱斯婷是阿卡迪亚人与印第安人和黑人混血的人,还有肤色深浅不同的黑人,以及多血统混杂、种族身份不明的人。在如此繁多的民族和种族中,肖邦唯独对黑人另眼相待。在她看来,其他民族或种族最为突出的差异是其文化,如小说不止一次地提到深受新教浸染的埃德娜不太适应克里奥尔人的不拘礼节和直抒胸臆,西班牙姑娘玛丽奎特性感迷人但举止粗俗、缺乏道德观念,墨西哥人奸诈无耻且充满报复心,墨西哥女人充满诱惑力。*参见Chopin, The Awakening, pp.10, 19, 33, 47, 107, 41, 97.然而在提及黑人时,肖邦突显的却是其血统。在其小说中,黑人大多无名无姓,取而代之的称谓是其身上血统的比例,如夸德隆(意为25%黑人血统,75%白人血统)、摩拉托(黑、白血统各占50%)、格力伏(75%黑人血统,25%白人血统)或布莱克(100%黑人血统)。在美国文学中,如此普遍地以血统比例来称呼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做法实不多见。在现实中,白人也极少如此称呼黑人,惟有那些黑白混血儿——非黑非白却且黑且白、被称为“有色人”的人,才这么刻意强调各自身上黑白血统的比例:“纯非洲血统的人从来不被称为有色人,而是被称为黑人。有色人是一个独立于并且优越于黑人的阶层,哪怕其血管中只有一滴白人的血,也因此而高贵一些。这种等级制好像从奴隶制被引入之际就存在了。对白人而言,所有血统不纯的非洲裔都是有色人。然而,在有色人内部却存在着被精心守护、高度戒备的差异。‘格力伏、布莱克、摩拉托、夸德隆、奥克托隆,这每个用语都意味着向白人那完美的身体标准更进一步的变形’。”*Dunbar-Nelson, “People of Color in Louisiana,” p.361.“奥克托隆”意为八分之七白人血统,八分之一黑人血统。换言之,在白人优越论泛滥的19世纪,有色人使用上述用语来强调各自的白人血统,而白人并不太关注有色人之间的这些差别。因此,身为白人的肖邦对这些差别的格外敏感,就更加别有深意。
然而,相比其对血统的敏感,肖邦对黑人相貌的观察似乎又过于迟钝。小说除了在一处提到一名黑人女仆“明显是个畸形人”而外,没有对黑人外貌更为具体的描写,甚至当埃德娜以其女佣为模特来绘画时也只字不提其相貌,仅抽象地说“该年轻女子的背部和肩部线条经典,其头发从帽子中释放出来时化为灵感”。*参见 Chopin, The Awakening, pp.57, 55.简言之,小说没有提供任何可借以判断这些人种族身份的外貌特征。而小说之所以模糊其外貌特征,细究起来,不外乎是因为他们不见得都皮肤黑,也不见得都长着典型的黑种人头发和五官,从外貌上看,有些甚至跟白人没有两样。如书中那位自始至终都无名无姓、被称为“夸德隆”的保姆,其身上只流淌着1/4的黑人血液,余下的3/4皆属白人血统。尽管小说没有对她进行任何相貌上的描写,但从遗传基因的角度推测,她看起来像白人的几率远远大于像黑人的几率,从外貌上应当很难将其归类为黑种人。不过,从血缘入手却可追溯到其黑人祖先。
由于历史的缘故,新奥尔良有不少貌似白人的黑白混血儿。在法属和西班牙属殖民时期,路易斯安那曾流行一种名为Plaçage的姘居制。早期的法国和西班牙移民男多女少,故社会允许白人男子与黑人女子进入一种姘居关系。这些女人并不能成为其法律意义上的妻子,待条件许可,白人男子仍可与白人女子结为夫妻,并同时保留原有的姘居家庭。这一风俗在新奥尔良尤为盛行,由此产生了许多黑白混血儿,在奴隶制时期甚至还形成了一个有别于黑人的“自由有色人”阶层,当然,这一阶层的形成也是历经无数次斗争的结果。有研究表明,路易斯安那的历史曾“充满试图定义黑人这一词语的努力,这些努力有时是通过刀剑,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民事或刑事法庭。经过约定俗成,在路易斯安那,黑人一词在1865年以前意味着奴隶,之后则指那些皮肤明显深色的人”。*Dunbar-Nelson, “People of Color in Louisiana,” p.361.换言之,在19世纪的新奥尔良,并不是所有有着黑人血统的人都被视为黑人,也不是所有黑白混血儿都可称为有色人。在内战结束之前,所有奴隶,无论是具有100%的黑人血统或只有一丁点黑人血统,均是黑人;唯有那些享有自由的黑白混血儿才是有色人。*据说,“自由有色人”也不全是黑白混血儿,也包括少数因在战场上表现勇猛而被主人赋予自由或自己赎回自由的奴隶,以及因个人魅力而被主人给予自由的女奴。参见Dunbar-Nelson, “People of Color in Louisiana,” p.371.在内战之后,肤色明显偏深的人是黑人,肤色偏浅的黑白混血儿则属于有色人——这大抵是因为随着奴隶制的消失,原来把奴隶和有色人隔开的那道分界线也随之消失,唯有从肤色的深浅来予以划分。而有色人则极力从血统上拉开与黑人的距离,以维持自己在社会中较之后者优越的地位。根据玛丽亚·赫伯特-赖特的研究,19世纪路易斯安那的种族分类别具一格:美国其他地方都是黑白二分的种族体制,而路易斯安那州是三分或四分的种族体制。*参见Maria Hebert-Leiter, Becoming Cajun, Becoming American: The Acadia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Longfellow to James Lee Burk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这三分或四分的种族体制就包括有色人这一成分。即是说,有色人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而是两者之外的另一种类。
对此,美国其他地方的白人却不以为然。在种族理论层见叠出的19世纪,美国主流社会不仅相信种族身份通过血液遗传,而且深信“即便白人血液中掺杂微小比例的原始非洲血液,其污染也无可救药;虽然凭肉眼看去,其黑色人种的表征并不显著,但黑色污染物仍然败坏血统,更有甚者,其本质上的黑人身份最终会以一个在身体特征上有返祖现象的孩子这样一个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当黑白混血时,通过血液遗传的是黑人的种族身份而不是白人的。不管一个人身上白人血统的比例有多高,一滴黑人的血就足以将其“染”黑,而且永远无法“洗”白,其黑人身份迟早会原形毕露。据说,这一种族返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白人中深入人心。*以上引述,参见J. Michael Duvall and Julie Cary Nerad, “‘Suddenly and Shockingly Black’: The Atavistic Child in Turn-into-the-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Vol.41, No.1, 2007, p.53.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部分地方都排斥黑白混血并实行黑白二分种族体制的原因。
按照上述理论,虽然有些黑白混血儿在外貌上更接近白人,虽然无论是在奴隶制时期还是在奴隶制废除之后有色人都觉得自己有别于且优越于黑人,但在绝大多数美国白人的眼里他们依然是黑人,并不比后者优越。这一种族观念的影响可以从小说中窥见:埃德娜曾遇到一家“体面的”摩拉托人,其女主人特别显摆自家的社会地位,津津乐道其房客都是“最富名望的人”。但埃德娜对其话题却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没有留下来与之“谈论阶级差别”。*参见Chopin, The Awakening, p.56.显然,身为白人的她并不关心黑人内部的差异。其实,同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小说作者对此也不关心。肖邦出生并成长于密苏里州,像小说中出生并成长于肯塔基州的埃德娜一样,出嫁之后才随其“克里奥尔”丈夫到了新奥尔良,其种族观念的形成无疑深受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所以从表面上看,她对黑人身上血统比例的差别极为敏感,但实质上,让她敏感的不是差别,而是雷同,即无论是貌似黑人还是貌似白人,他们身上皆有黑人的血统。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小说避而不谈那些“黑人”的外貌特征,而别出心裁地以血统比例来替代其姓名,并刻意淡化他们每个人之个性、强调其共性。可以说,与那些以“夸德隆”“摩拉托”“格力伏”之类的用语来强调自己拥有部分白人血统的有色人不同,肖邦在同样使用这些用语时,高调显示的却是他们身上的那部分黑人血统。而按照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观念,有黑人血统就是黑人,即便只混杂了一滴黑人的血液。如此一来,小说巧妙地从血统的角度建构了这些人的种族身份,使新奥尔良原来的黑人和有色人合二为一,一并归入黑种人的行列。
三、被白色化的克里奥尔人
19世纪路易斯安那的种族是多元的,而不是黑白二元的;其三分或四分的种族体制“是将卡津人、白种克里奥尔人和有色克里奥尔人考虑在内的”。*Hebert-Leiter, Becoming Cajun, Becoming American, p.3.具体而言,三分是指黑人、卡津人和克里奥尔人;而四分则是指黑人、卡津人、白种克里奥尔人和有色克里奥尔人。亦即:三分制将白种克里奥尔人和有色克里奥尔人统称为克里奥尔人,而四分制则把克里奥尔人细分为白种和有色两类。由此可见,无论哪一种划分方式,克里奥尔人中都既有白种人也有有色人。
那么,何谓克里奥尔?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克里奥尔这个名称在16至18世纪原本指生于美洲而双亲是西班牙人的白种人,以区别于生于西班牙而迁往美洲的移民。后被用于各种意义,因地域不同而有所不同甚或相互矛盾,……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某些地方,它指早期法国和西班牙移民之讲法语的白人后裔;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指讲法语与西班牙语混合语的黑白混血儿。”*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III,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79, p.233.据《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该名称指美国南部尤其是海湾各州早期法国或西班牙移民之白种后裔,……以及讲一种法语或西班牙语方言的、法国或西班牙移民与黑人混血的后代。”*Philip Rabocock Gove et al., eds.,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 G. & C. Merriam Company, 1976, p.534.据《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该词原指西印度群岛本地出生的西班牙裔征服者。后被用于指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的法裔、葡萄牙裔和西班牙裔移民的后代,……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早就采用该名称,至今仍被用于区别早期法国移民的后代和卡津人的后代。”*Willilam H. Harris and Judith S. Levey, eds., The New Columbia Encyclope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79.上述三个定义或释义都把路易斯安那州的黑白混血儿列在了克里奥尔人之中,只是较之前两个定义之明确,第三个定义对这一点的表述较为含蓄罢了。
其实,“克里奥尔”本是“土生土长”之意,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历史时期被出于不同立场或动机者用来排除或囊括某些社会群体: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出生于西班牙的殖民地统治阶层用该词将本地出生的人排斥于教会和国家的高级机构之外,以此加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参见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III, p.233.在法印战争(1758—1763)期间,一些曾在加拿大原法属殖民地阿卡迪亚生活多年的法国移民被驱逐或流亡至路易斯安那时,当地早期法国和西班牙移民的后裔用此称呼来拉开自己与这些阿卡迪亚人(即“卡津人”*“卡津(Cajun)”是英文单词Acadian(即阿卡迪亚人)在口语中被吞音后的发音。)的距离;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1803)之后,大量富有且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裔美国人涌入原法属殖民地路易斯安那,本地人又以此称呼在新来者面前强调自己对土地享有优先权。邦尼·詹姆斯·谢克尔指出:
在路易斯安那州,克里奥尔这个名称原指任何在本地出生的路易斯安那人,……所有当地出生的路易斯安那人均可自称“克里奥尔”,它曾被用来描绘各种肤色的人。“克里奥尔”并不表示任何特殊的社会或经济阶层。它也用于非洲裔奴隶的子女,既包括那些内战后依然贫困的黑人也包括少数成为种植园主的成功富裕的黑人;它被用来指卡津人的后代,……也指土著美国人以及多种族混血的人。*以上引述,参见Bonnie James Shaker, Coloring Locals: Racial Formation in Kate Chopin's Youth's Companion Storie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3, pp.48-49, 28-29, 29.
一言以蔽之,所谓克里奥尔人就是土生土长的路易斯安那人,它既非一个种族也非一个民族,该名称亦不过是建构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
考虑到路易斯安那独特的种族体制以及内战前后对“黑人”的不同定义,可以这么说,克里奥尔这一用语在内战之前把奴隶和卡津人排除在外,在内战之后把卡津人和肤色明显偏深的人排除在外,但无论内战前后,都包括了早期法裔和西班牙裔移民与黑人混血的后代,即所谓有色人。只不过有色人在战前指那些享有自由特权的黑白混血儿,在战后指那些肤色甚至相貌更接近白人的黑白混血儿。根据加里·米尔斯所言,内战以前,在自由有色人的名义下,拥有部分白人血统的克里奥尔人被赋予了在美国其他州不可能被赋予的一些特惠、机遇和公民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身上的白人血统多于黑人血统,往往与其白人亲戚关系不错且在公开场合得到后者的认可,因而绝大多数有色克里奥尔人从小就相信他们与黑人分属不同的种族。*参见Gary B. Mills, The Forgotten People: Cane River's Creoles of Colo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xiv.卡津人之所以被排除在外,一是由于历史的缘故,即其祖先是这块土地的后来者;二是出于阶级的原因,即大多数卡津人都沿袭其祖辈的生活方式在乡下务农,其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远低于拥有贵族血统的早期法国和西班牙移民的后代;三则可能是因为血统过于混杂——“处于不同经济水平的阿卡迪亚人都曾与非裔美国人、土著美洲人、欧裔美国人、英裔美国人以及那些经新奥尔良港口进入该州的移民繁衍过后代”。*Shaker, Coloring Locals,p.49.总之,在路易斯安那的社会层级中,白种克里奥尔人居上,有色克里奥尔人次之,卡津人再次之,黑人则位于社会底层。
随着奴隶制的消失、南部重建的深入以及联邦政府对第十四、十五宪法修正案的推行,上述社会格局被打破。法裔和西班牙裔白人早先在社会中享有的某些特权不复存在,自由亦不再是区分有色人与黑人的标准,原本是乡下农民的卡津人中出现了富裕的种植园主。换言之,过去那些存在于白种克里奥尔人与有色克里奥尔人之间、有色人与黑人之间、克里奥尔人与卡津人之间的种种界墙正渐次坍塌,路易斯安那原来的社会秩序濒临崩溃的边缘,一个新的、与美国其他地方接轨的黑白二分的种族体制初见端倪。值此社会格局大洗牌之际,为了确保各自的社会升迁和政治权利,“当时各种肤色的人都疯狂地忙于宣称自己是‘白人’”,路易斯安那的法裔和西班牙裔白人发起了将“克里奥尔”这一称呼专属于己的运动,以确保自己在新秩序中仍占尽优势,而“部分法裔和西班牙裔稍深的肤色以及该地区种族混杂这一隐藏的事实,更是促进了将克里奥尔人塑造成与黑人不一样的白色种族的运动”。*Shaker, Coloring Locals,p.29.
从《觉醒》可以看出,肖邦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运动。与现实不同,书中的新奥尔良市既无“有色人”也无“有色克里奥尔人”——这两个在该地区历史悠久的用语在小说中一次也没有出现。小说里只有克里奥尔人、阿卡迪亚人、西班牙裔美国人、英裔美国人、多种族混血的人以及有着各种百分比黑人血统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克里奥尔人”一词从不加“白种”或“有色”之类的限定词,就那么理所当然、毋庸置疑地专指早期法国移民之白种后裔,好似它从来不曾有过其他的含义。
小说赋予该词的这一排他性词义首先确立了克里奥尔人是白种人这一概念,由此将有色人排除在外,而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有色人,其实就是被冠以“夸德隆”“摩拉托”“格力伏”之类称呼的人。其次,该词义也将其他新奥尔良人排除在外,就连最早采用这一称呼的西班牙裔也不例外。譬如,在描写玛丽奎塔时,肖邦特别强调她是一位西班牙裔姑娘,以此将她与周围的克里奥尔人区别开来。埃德娜上下打量玛丽奎塔的目光停留在其“圆圆的、狡猾而迷人的脸庞和漂亮的黑眼睛”上,停留在其“丑陋的棕色脚趾头”上,停留在其“对着罗伯特‘挤眉弄眼’,对着博德勒‘撇嘴吐舌’”这些轻浮的举止之上。不难看出,该目光充满对“异己”的挑剔甚至厌恶。事实上,小说将玛丽奎塔这位书中唯一的西班牙裔姑娘刻画成了一名招蜂引蝶、挑起男人争风吃醋、甚至扬言要与已婚男子私奔的女子,一名脑子里除了男女间的风流韵事啥也不装的风骚女子。*参见Chopin, The Awakening, pp.33, 106-107.而“丑陋的棕色脚趾头”这一描述更是将其置于种族他者的位置,令人不禁怀疑西班牙后裔的血统是否纯正。
小说中的阿卡迪亚人虽然没有被明确地刻画成种族他者,但也充满了异族风情。只会英语而不会法语的英裔美国人埃德娜在与克里奥尔人交流时没有语言障碍,但与阿卡迪亚人安托万太太的交谈却需要翻译。这一细节一方面暗示克里奥尔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无障碍,另一方面则表现出阿卡迪亚人“非美国”的一面。安托万太太家“奇奇怪怪、古香古色的床”和“床单和床垫上挥之不去的一股充满月桂味的乡村气息”,以及安托万太太讲的那些天方夜谭、其子托尼一口“慢吞吞的阿卡迪亚方言”、村里阿卡迪亚小伙子汲水的方式,都让埃德娜仿若身处异国他乡。后来埃德娜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把自己编造的一个私奔故事硬说成是从安托万太太嘴里听来的,似乎这样一个有伤风化的故事唯有出自阿卡迪亚人之口才合乎情理,这一行为使得阿卡迪亚人更显异族化。此外,埃德娜的仆人塞莱斯婷讲的那一口patiois话——一种由古法语与英语、西班牙语、德语和美洲印第安语混合而成的当地土话,则表明她是阿卡迪亚人与多种族混血的后代,揭示出卡津人极为复杂的血缘。而阿卡迪亚人或卡津人不纯正的血统恐怕正是小说异族化他们的原因所在。
总之,小说不着痕迹地将克里奥尔这一称呼专属于早期法国移民的白种后裔,由此排除了一切“玷污”其白度的可能,建构出克里奥尔人白色的种族身份。如果仅凭此书来了解19世纪的新奥尔良社会,读者必定会以为克里奥尔人就是“纯”白种的有着贵族血统的法裔美国人,而惘然不知有色克里奥尔人的存在,更不知原来所有土生土长的路易斯安那人皆可称为克里奥尔人。这样的建构无疑有利于早期法国移民的白种后裔——即肖邦因婚姻关系而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群体。
四、“黑人性”与白人居上、黑人居下的社会秩序
《觉醒》不仅重新定义了黑人,建构了克里奥尔人,还在此基础之上勾勒出一个白人居上、黑人居下的社会秩序。而这样的社会秩序则是以黑人“低劣”的族性为基础的。
小说中黑人比比皆是,他们在白人的庭院、客厅、厨房、饭厅、卧室甚至产房里,在白人度假的沙滩上、小憩的公园中和漫步的街道上,为白人洗衣做饭,端茶递水,照顾孩子,整理房间,收拾庭院,演奏音乐。一句话,他们存在于白人活动的一切场所,其存在的主要方式就是为白人服务。不仅富有的白人享有其服务,就连贫寒的赖茨小姐也有黑人姑娘为之浆洗衣裳。而小说也常以服务类型来命名黑人,如女佣、保姆、厨子、院丁、餐厅仆人等,这是他们除血统比例而外的另一高频率的称谓。
然而,在内战之后的新奥尔良,黑人并非如小说描绘的那样几乎全居于社会底层,他们中亦有“商人、律师、医生、记者、音乐家、艺术家以及熟练工人”;白人也并非全居于黑人之上,他们中也有工人阶层,而且这两个种族的工人阶层在工作中既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此外,自1862年新奥尔良被联邦军队占领之时起,该城的黑人就开始了要求平等的斗争,战后更是一步一步争取平等的权利,首先是法律上的权利,然后是政治权利和平等获取公职的权利。*参见Somers, “Black and White in New Orleans,” pp.22, 30-31,22-23.
《觉醒》中的描绘之所以与现实不符,是因其主观的叙事角度。小说采用内聚焦叙事模式,以埃德娜的丈夫庞特里耶先生的意识活动开始,渐变为以埃德娜的意识活动为中心,最终以埃德娜心理意识的终结而结束。不言而喻,此叙事模式有利于表现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有利于展示女主人公的主观感受和觉醒过程。但如此一来,小说的叙事也就受限于埃德娜及其周边几位白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换言之,小说所展现的世界是白人意识中的世界,因而在这一世界中,黑人时而被物化,时而被隐形。如在缝纫机上忙碌着的勒布伦太太,“不允许任何危及自己健康的可能性存在”而让一个黑人女孩坐在地上,用手摇动缝纫机踏板。在其子罗伯特进来后,随着手摇踏板发出的咔哒、咔哒的声响,母子俩旁若无人地聊起了天。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黑人女孩既无言语也无目光更无思想和反应,就像缝纫机上的一个零件,唯有不时穿插于母子二人谈话中的咔哒、咔哒声显示出其物化的存在。同样,在埃德娜的宴席上,“不时有音乐之声,那是曼陀林的声音,声音的远近恰到好处,刚好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伴奏,而非对谈话的打扰”。在音乐声中,宾客们欢声笑语,推杯换盏,直到宴会结束,小说才提及“那些演奏曼陀林的人早已悄然离开”,“仆人都走了。他们在乐师离开时走的”。*参见Chopin, The Awakening,pp.21, 84, 87.乐师和仆人们何时到场?何时在场?无人知晓,也无人关心,他们的存在是隐形的。
事实上,当小说中的白人意识到黑人的在场时,往往是其不在场之时,确切地说,是在白人惊觉其服务缺失之时。如埃德娜与罗伯特从卡米纳达岛归来,拉蒂诺太太一边将埃德娜的小儿子递给她一边告诉她:大的那个已睡着了,小的这个顽皮,还不肯上床。埃德娜接过孩子,哄其入睡。拉蒂诺太太接着又告诉她庞特里耶先生如何担心她,然后告辞。埃德娜将睡着了的小儿子抱到里屋,罗伯特帮她撩起蚊帐,她将孩子舒舒服服地放到了床上。小说在拉拉杂杂地叙述了这么一连串的事情之后,才突然冒出一句“那个夸德隆早已消失不见”。*参见Chopin, The Awakening,p.39.这句貌似不经意的话让我们知晓,原来在此之前那个夸德隆一直在场,是她在埃德娜外出之时代替其充当母亲的角色,照顾孩子,可小说对此只字不提,因而她又是隐形的、不在场的,当埃德娜对其服务的消失颇多不满时,实际的不在场,反而使白人意识到她之前的在场。
当然,白人也不是完全无视黑人的在场,但入眼的往往都是黑人的不足:在庞特里耶先生眼里,“夸德隆是个巨大的累赘,除了能给孩子穿衣服和梳头发而外,一无是处”;在埃德娜眼里,女仆扫地“慢慢吞吞、心不在焉”,夸德隆做事“疏忽大意”,“不够当心”;在维克多眼里,那位身材畸形的女仆既愚蠢又固执,需要好好管教。此外,在白人眼里,黑人偶有所成,那是白人指导有方,如两名女仆“在维克多的指导下”做出了可口的冰激凌;即便偶有所长,他们也无进取之心,如公园里那位摩拉托女人做得一手好咖啡和烤鸡,却成天趴在桌上呼呼大睡,就像其身旁那只懒洋洋的猫。*参见Chopin, The Awakening,pp.39, 9, 32, 42, 45, 67, 24,99.
总之,小说通过几位白人的意识展现出的是一个黑人全都在为白人服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如果黑人服务到位,那他们在白人的意识中就是隐性的;如果黑人服务不到位,那他们在白人的意识中就是显性的。这说明白人下意识地视黑人为之服务为正常,不为之服务为反常。肖邦显然亦持此观念,因而她在叙事中不仅没有予以批判或讽刺,反而煞费苦心地为之提供依据:刻意渲染黑人之共性,模糊其个性,把他们都描绘成天生低劣的类型——既愚昧无知又消极懒散,做任何事情都缺乏主动性和责任感,倘若没有白人的管教和指点,啥事儿都干不好。这样的描绘无疑为白人居上、黑人居下这一社会等级秩序找到了理由,使之显得顺理成章,天经地义。
结 语
无论内战前还是内战后,新奥尔良的种族分类都不全然取决于生物性遗传差异,而更多地受制于各种社会意义、政治意义或经济意义上的激烈竞争。小说《觉醒》集中体现了19世纪后期围绕种族问题所展开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斗争。针对新奥尔良当时的种族难题,小说站在早期法国移民之白种后裔的立场上,重新定义了黑人,将原来与克里奥尔人关系难解的有色人并入了黑种人之列,以此“纯洁”克里奥尔人的血统,白色化克里奥尔人的种族身份,保障早期法国移民之白种后裔在新的社会秩序中依然能够高高在上。小说对黑人血统的凸显,对黑人“低劣”族性的构建,表现出种族主义强调血统、宣扬白人优越的一面,符合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种族的普遍认识,符合作者所代表的社会群体之利益。可以说,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参与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它不仅如某些学者所言,反复捕捉到了埃德娜那些熟人的种族偏见,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建构种族和加固种族偏见的工具。了解这一点,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该小说的认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人种族观念之复杂性、种族身份之可塑性以及种族偏见之顽固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直到21世纪的今天,种族问题依然是困扰美国社会的一大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