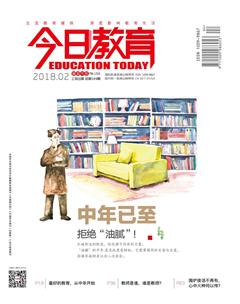我看见了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曾志新
近些年,芬兰的创新力一直排在全球前列,其学生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表现突出,因此,该国教育引起世人瞩目。而丹麦,据说其国民幸福感高,其教育水平几乎也与芬兰比肩。芬兰、丹麦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热土。2017年11月6日至13日,我们赴北欧进行教育考察关注的就是这两个国家。
教育可以更平静
芬兰图尔库市的教育局与市政府在同一栋小楼里上班,入口有咨询台但无门岗,有老式的狭窄电梯,过道中悬挂着一些画作和装置,没有张贴一条标语口号,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
在图尔库,我们了解到,芬兰各校师资力量相当,发展程度较为均衡,没有“择校”现象,中小学生都是就近入学,如果孩子的家距离学校超过5公里,政府就要补贴出租车费或提供专门的校车接送。
尽管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负担(私立教育除外),但是,芬兰的学校依然享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的干预很少,没有自上而下的各种精细化考核,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培训。教育部每四年制定一次核心课程纲要,只定一个框架,不做具体细节规定。芬兰的教师在课程教学的时间、内容、教科书、途径、学业测评等方面的决定权非常大。
芬兰在教育领域不崇尚竞争,校长们不愿与其他学校竞争,也不鼓励教师之间竞争。校长对教师基本没有过多过细的考核指标(除了课时量),他们不以学生考试成绩高低、升学率高低来评价老师,而是采取学生、家长评价老师,这些评价自动进入系统,校长会结合这些评价,与老师本人会商,提出教师成长规划。
芬兰教师的入行门槛高,所有教师(不包括幼儿园)都必须是硕士毕业,职业教师还必须有三年以上职业工作经验(我的理解可以是实习)。据说当地的教师是因心中有一定的使命感驱动向前的,并非被外在的“鞭子”或“票子”驱动。教师的职业素养很高,深得人们信任。据说,当地没有“补课教师”这个行业,更没有什么“课外补习专家”,因为没市场,人们相信学校就能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问题了,没必要在校外再“进补”。
在芬兰,政府相信校长,校长相信教师,家长相信学校,学校相信社会。教育因信任而平静、从容,因信任而和谐、美丽。
教育可以更生活
芬兰也在进行教育改革,我们所参观的每一所学校都在讲新课程变革。他们越来越重视教育要面向生活。他们发现生活中,很多学科之间并无森严的壁垒,大多是交融在一起的,因此,芬兰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越来越重视跨学科的融合,每个学校都有相应的项目式学习课程。
我们参观图尔库的Turun Lyseon Lukio高中时,正逢他们的高一学生正在进行Teamwork活动。4~6人组成一个team(项目组),一个教师负责5~6组,将五、六科知识融合起来,这是专门的课程,时长大约七周。2017年是芬兰独立一百周年,这一年各组的项目研究主题就是“一百周年国庆”,学生有的负责查阅历史,有的负责绘制地图,有的负责美编,有的负责资料搜集,忙得不亦乐乎。在这所学校针对4~9年级的孩子开设的生活实用性选修课上,学科融合也是贯彻得很到位。例如,在“攀岩课程”上,他们借助一个小小的“望远镜的使用技巧”就实现了数学、物理与运动等学科的结合。
在丹麦奥登塞市的SCT. HANS SKOLE,我们在学生们的木工房里,发现了他们制作的风筝,还有“爱”“真”“梦”“和睦”“长寿”若干美好的汉字在上头。这不既练就了木工技能,又学习了中国书法,且增进了跨文化理解。这所学校室内室外的若干地块上喷绘着这样的数学游戏区,孩子们就在这样的区块中跳来跳去,演算数学。该校校长告诉我们,这个小设施可以在运动中提高孩子们的数学能力,既巩固了知识,又锻炼了身体。
芬兰的国家新课程规定了七种横贯能力的培养目标,分别为:(1)思考与学习的能力;(2)文化识读、互动与表达能力;(3)自我照顾、日常生活技能与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4)多元识读(Multi-literacy)能力;(5)数位(Digital competence)能力(他们很注重培养适应未来高科技发展需要的下一代);(6)工作生活能力与创业精神;(7)参与、影响并为可持续性未来负责的能力(他们很注重孩子适应力和社群能力的培养)。在我看来,他们之所以称这七种能力为“横贯能力”,大概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贯穿人生的始终,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之间是相互贯通、难以区隔的吧。
在北欧,教育因融合而更接地气,因融合而充满意义。SCT. HANS SKOLE的校长说他还在读硕士学位,好像是工商管理方面的,当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想,好的教育应该有一个外显的指标——看学生还有无持续学习的愿望。我们教了很多学生,用各种有趣或枯燥的方式教给了他们很多割裂的、抽象的、远离生活的知识,最终让他们终生远离学习。也许,我们要痛下决心,跨出去,去融合别的学科,去拥抱多彩的生活。
教育可以更好玩
芬兰、丹麦在数字化学习环境建设方面也已取得长足进步,他们的“数字化”是让学生“玩”的,是真正服务于教育和学生成长的。
芬兰中小学的很多课程都已经实现了教科书电子化,不再提供纸质教科书。在图尔库的Turun Lyseon Lukio高中,我们看到孩子们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做“teamwork”,人手一台台式电脑在上地理课,孩子們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讲台进行生理健康课的汇报。在赫尔辛基的Sakarinmaki小学,使用电子产品甚至电子游戏辅助教学越来越成为师生教与学的常态。我们随堂听了一节八年级的瑞典语课,这节课后段,老师为了检测孩子们瑞典语学习的效果,要学生当场用平板或手机登录网络,现场点击一款简单的类似于“连连看”的游戏,要将瑞典语单词和相应的注释准确连接。学生如果一开始完成得好,游戏就会跳出这样的赞语:“Pefect starting. Keep it up.”如果完成情况不够理想,就会跳出“Play again”字样。我很欣赏这里的Play这个词,学习就是Play,就是“玩、游戏、扮演、演奏”,这应该是学习和教育的常态呀!大概是因为玩得多,无案牍劳形,芬兰、丹麦的孩子中少有眼睛近视的,这让我们很感慨。
在丹麦奥登塞市的SCT. HANS SKOLE,我们走进这间教室的时候,发现孩子们三三两两在一起做些什么,教室里很乱,桌子上、地上尽是纸屑,还有好几个凳子放在桌上了。后来,我才搞明白:孩子们是在做动画作品,自己手绘一条鲨鱼,剪下来,再在绘制的海水背景上一步步推着鲨鱼往前走,让其与另一条鲸相遇,凳子上的ipad录下这一动态,然后孩子们再利用视频软件把若干摄影片段拼接起来,不断调整,再拼接,最后就可以制作出一部动画片。我看得目瞪口呆,这些三、四年级的小学生真酷!这样的教育真酷!
走进北欧,我们看到了一种心中有“人”的教育的现代化模样。当我看到那边的孩子熟练地玩着电脑,畅享网络,而我们这边,老师和家长们因为“我们的孩子自制力很弱”而收其手机,封其网络,困其于题山题海,我不禁要问:这是面向现代化的教育吗?也许,像北欧国家那样,把步子放慢一点,多给孩子一些“play”的时间,静待孩子们身体、思维和心灵逐渐发育,岂不美哉?
教育可以更有想象力
在丹麦,我们参观了奥登塞的安徒生博物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中学老师,就把我们当作小孩,向我们演示她们是怎么面对儿童的:她们拖着藏有“宝藏”的小车,带领孩子们走特定的路线,在特定的景点停留,给孩子们讲安徒生的故事。
讲到一半,她会停下来提出问题。比如,她们向孩子们讲述了安徒生童年的故事,讲到女巫占卜安徒生的未来,告诉安徒生的妈妈“你的孩子会有大出息”时,会问孩子们:“小朋友,如果你遇到了童年时期的安徒生,你会对他说些什么?”
又比如,她们向孩子展示安徒生用过的物件(复制品),然后问孩子们:“孩子们,你手中的这个小物件现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再比如,她们会告诉孩子们,妈妈给安徒生做了一双靴子,这是他的第一双新靴子,以前他一直是赤着脚,在冬天就穿一双大木拖鞋。小安徒生就穿着这双平生最好的靴子去教堂礼拜。他高兴到了极点,唯恐别人看不见他的新靴子,就提着裤脚,故意露出新鞋子,嘎吱嘎吱地走过教堂。“所有人都知道我的靴子是新的,”小安徒生这样想。“哎呀,我只顾着新鞋子,竟然忘记了要在心里想着上帝,请上帝饶恕我吧。”可是,下一秒,他就看到自己新靴子上沾了一些灰,连忙蹲下身来擦拭。说到这里,解说员就顺势给孩子们讲《红舞鞋》这则童话,讲到小姑娘伴随着红舞鞋跳出城堡,跳出城市……“哎呀,我不记得结尾了,你们记得吗?”等孩子们续完,解说员会对他们表示感谢:“谢谢你,孩子,你讲得真好。”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环节结束后,解说员总是提醒我们:“无论孩子们怎么说,都没有错。”她们大概是认为,只要大人有对错的分别心,就会扼杀孩子的想象力和表达欲望。她们如此呵护孩子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表达力,也许,这就是这个国度不缺故事、充满童趣的原因吧。
走进北欧,我们隐约看到通往幸福的教育之路的模样。近年来,我国教育领域也在积极改革,笔者所在的学校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和丹麦、芬兰學校的理念也有了许多的相通之处:提倡“个性发展”“自主学习”“未来课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地方。尽管眼下我们还不能做太大的动作,但我想,我们心里还是要有光,要坚持寻找教育的无限可能。我深信,寻找终会寻见!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芬兰的蒋俊鸣、李彩老师以及我的同事张万国、贺晓丽、卓忠越、刘扬、严丽的悉心指点,特此感谢。)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