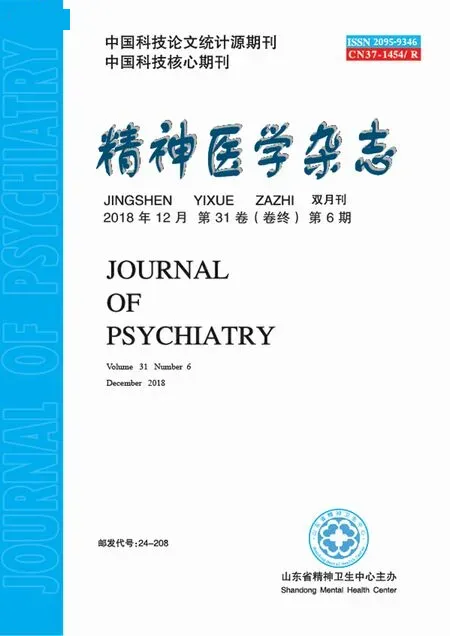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对强迫症患者病耻感的影响研究*
强迫症作为焦虑障碍的类型之一,是一组以强迫行为和强迫思维为主的精神障碍。该病特点为患者有意识的自我强迫和反强迫并存,二者强烈冲突使其感到焦虑和痛苦,且患者无法通过自身力量摆脱,随着病情的不断进展,患者的社会功能受到严重影响[1,2]。以往临床对于强迫症主要采取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以缓解强迫症状。然而调查发现,强迫症患者的治愈率和社会功能恢复并不理想,未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患者病耻感严重和社会歧视[3,4]。病耻感是患者因疾病而产生的一种内心羞耻体验,而精神障碍患者因疾病特征会被标签化,存在病耻感。这会加重患者心理负担,出现逆反、消极心理,因怕歧视和被贬低而拒绝治疗,治疗依从性差,且错失治疗的最佳时间,不利于疾病治疗和康复[5]。近年来,据多个对照研究证实,药物结合心理治疗是强迫症的有效治疗方案,且研究的重点是团体心理治疗[6]。但是,国内关于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对强迫症患者病耻感水平影响的研究较为罕见[7]。因此,本研究探讨了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强迫症患者病耻感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5年7月~2017年6月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治疗的强迫症患者76例,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各38例。纳入标准:符合《中国强迫症防治指南2016(精编版)》[8]中关于强迫症诊断标准,经病史、临床表现(强迫症状)和精神检查等确诊;耶鲁-布朗强迫症状量表(Yale-Brown Obsessive-Compulsive Scale,Y-BOCS)[9]总分≥16分,病程>3个月。排除标准:由其他精神障碍引起的继发性强迫症,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合并脑器质性疾病及严重躯体疾病者;精神发育迟缓者;有物质和药物滥用及依赖史者;无法配合研究者。脱落标准:患者中途退出研究或失访者。研究组男23例,女15例;年龄18~33岁,平均(26.27±3.09)岁;病程5个月~9年,平均(4.88±2.12)年。对照组男26例,女12例;年龄20~34岁,平均(26.33±3.16)岁;病程7个月~10年,平均(4.94±2.17)年。两组患者均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完成12周随访的患者共62例,研究组33例,脱落5例;对照组29例,脱落9例。脱落原因分析:因药物不良反应而脱落,研究组无,对照组3例;因不能坚持心理治疗而脱落,研究组3例,对照组无;因电话号码改变而随访不到,研究组1例,对照组4例;因其他不明原因而脱落,研究组1例,对照组2例。两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院内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药物治疗,即(1)采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治疗,包括舍曲林(左洛复,国药准字H10980141)、帕罗西汀(国药准字H10950043)、氟西汀(国药准字J20080016)、氟伏沙明(国药准字H20058921)。舍曲林起始剂量为50 mg/d,第3天加至100 mg/d,第6天加至150 mg/d,2周内加至200 mg/d;帕罗西汀起始剂量为20 mg/d,1周内加至60 mg/d;氟西汀:起始剂量为20 mg/d,2周内加至40 mg/d;氟伏沙明起始剂量为50 mg/d,第4天加至100 mg/d,第7天加至150 mg/d,2周内加至300 mg/d;(2)药物治疗前向患者及其家属详细讲解药物用法、效果及不良反应,嘱其遵医嘱服药,但不提供心理治疗。观察组在使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合并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具体方法如下。(1)团体构成:每个团体(小组)包括6~10例患者和两名治疗师,将38例患者分为4个团体。(2)治疗形式:采取会谈的方式进行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每次会谈2 h,每周1次,共12周。(3)治疗环境: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门诊部的团体治疗室进行。(4)准备阶段:干预前两名治疗师应单独与每一位患者分别交谈2 h,与其建立良好的同盟关系;交谈中着重评估患者病情及相关信息,并介绍团体治疗的方法、流程及注意事项,解答患者疑问;交谈结束后应确定患者是否愿意加入团体,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提供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指南。(5)治疗内容:①第1次会谈。采用接力的形式由成员进行自我介绍,包括描述自身的强迫症状及其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说明出现强迫症状的诱因,分享自己对于强迫症的了解和说出参加团体治疗后希望得到的预期效果;之后,由治疗师进行心理教育,详细讲解强迫症,即各种概念、临床症状及主要临床表现、特征和团体治疗中所运用的技术等,并分发自助阅读书刊,告知团体规则;会谈结束时布置家庭作业,即完善强迫症状监控表(每天记录自己的强迫行为或观念),阅读发放的自助书刊;讨论执行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担忧的问题,及解决办法。②第2次会谈。检查家庭作业有无认真完成,对于完成作业的患者给予表扬和鼓励,让其讲述完成作业的感受,而对于没有完成作业的患者应了解原因,采取改进的措施;通过患者自身不合理信念为例,说明认知歪曲具体的内容,帮助患者正确认识这些信念的不合理;会谈结束时布置家庭作业,即继续完善强迫症状监控表,并对照改表进行自我监控。③第3次会谈。检查家庭作业,回顾认知歪曲列表,由患者讲述自身的认知歪曲,团体讨论、分析其类型;介绍挑战认知歪曲的技术和方法,包括垂直下降技术、成本-效益分析等,并布置家庭作业,继续监控强迫症状和认知歪曲,驳斥不合理信念。④第4次会谈。回顾家庭作业,对于积极完成作业的患者予以鼓励,对于消极对待作业的患者施以团体压力,询问原因,消除患者在作业上存在的不合理观念;阐述暴露疗法与反应阻止疗法的原理和操作过程,并嘱咐患者在监控强迫症状和认知歪曲与驳斥不合理信念的基础上进行暴露练习和仪式行为的阻止。⑤第5~11次会谈。检查家庭作业完成情况,并采取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的方式检查患者有无进行暴露练习和仪式行为的阻止;成员互相协助完成会谈内暴露练习和仪式行为的阻止,讨论人际交往中存在的不合理信念,并对其进行驳斥,形成另一种适应性想法;布置家庭作业,完善强迫症状监控表、认知重建、暴露练习和仪式行为的阻止。⑥第12次会谈。回顾家庭作业,巩固之前学习的认知-行为心理治疗理论,掌握如何识别和驳斥不合理信念及认知重建;患者讲述退步和复发的原因,并讨论、总结防止复发的措施。两组患者均观察12周。
1.2.2 观察指标 (1)病耻感。于治疗前及治疗后第12周末采用精神疾病内在病耻感调查表(Internalized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Inventory,ISMI)[10]评估两组患者病耻感,量表共29个条目,分为疏远、刻板认同、歧视经历、社会退缩和病耻感抵抗5个因子,各条目均含4个等级选项,依次计为1~4分,1分表示强烈反对,4分表示强烈认同,其中病耻感抵抗因子中条目为反向评分,分数越高,说明病耻感水平越高。(2)服药依从性。根据患者是否遵医嘱服药评价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分为完全依从(完全按照医嘱服药)、部分依从(一半以上的时间患者不按医嘱服药,或停药)、不依从(拒绝服药),完全依从率与部分依从率之和为总依从率。(3)强迫症状。于治疗前及治疗后第12周末采用Y-BOCS量表评估两组患者强迫症状严重程度,共10个项目,各项目均采用0~4级评分,最高分40分,分数越高,强迫症状越严重。(4)生活质量。于治疗前及治疗后第12周末采用生活质量调查量表(the MOS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11]评估两组患者生活质量,量表包含36个条目,共8个维度,即生理功能(Physical Function,PF)、躯体角色(Role Physical,RP)、躯体疼痛(Bodily Pain,BP)、总体健康(General Health ,GH)、活力(Vitality,VT)、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SF)、情绪角色(Role Emotional,RE)、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MH),各条目均采用等级计分法,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2 结果
2.1 两组ISMI评分比较 治疗后第12周末两组ISMI各因子评分较治疗前均降低,且研究组ISMI各因子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两组ISMI评分比较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服药依从性比较 研究组完成研究的33例中,总体服药依从的患者为31例(93.94%),其中完全依从的21例(63.64%),部分依从的10例(30.30%),服药不依从的2例(6.06%)。对照组完成研究的29例中,总体服药依从的为20例(68.97%),其中完全依从的13例(44.83%),部分依从的7例(24.14%),服药不依从的9例(31.03%)。研究组服药总依从性高于对照组(χ2=6.597,P=0.01)。
2.3 两组Y-BOCS评分比较 治疗后第12周末两组Y-BOC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且研究组患者Y-BOCS评分低于对照组(t=4.203,P<0.001)。见表2。

表2 两组Y-BOCS评分比较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
2.4 两组SF-36评分比较 治疗后第12周末两组SF-36各维度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且对照组SF-36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3。

表3 两组SF-36评分比较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论
近年来,精神疾病逐渐受到社会和心理学者的关注,不仅对其病因学和药物治疗进行多方面研究,还开始重视患者的心理健康。徐广明等[12]研究中,采用自编的社会人口学调查表、贬低-歧视感知量表及心理健康知识问卷对1 609名居民进行调查,发现与健康人相比,患有精神疾病的居民病耻感水平较高,且在工作、社交和婚恋等方面更受到他人的歧视。同时病耻感还会对患者本身的治疗态度造成负面影响,使患者不能正视疾病,拖延治疗,导致病情加重,给治疗工作增加难度,降低治疗效果[13]。而强迫症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具有起病早、病程长、病情迁延不愈等特点,常常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尤其是近年来,强迫症的发病率呈现明显升高趋势,且健康人群中强迫症的终身患病率约为2%,已成为中青年人群中造成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14,15]。为此,如何降低强迫症患者病耻感是目前临床研究的热点课题。
团体心理治疗最先由美国内科医生提出,之后随着各种团体治疗试验的不断开展,使其广泛、迅速地用于心理问题的诊断和治疗。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是在团体情境下将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有效融合,引导患者纠正不合理的认知、信念、态度和行为,从而提高患者心理健康水平[16,17]。孙霞等[18]研究指出,采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能降低双相障碍患者病耻感,提高服药依从性。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者ISMI各因子评分均较低,服药依从性较高,说明通过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可改善病耻感水平,提高了服药依从性。分析其原因在于通过成员之间互动和交流,可明显减轻患者孤独感,促使其能平和面对疾病,有利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同时通过批判及矫正不合理信念、认知重建等措施,能促使患者充分认识不遵医嘱服药这一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而建立良好的健康行为,提高患者依从性。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者SF-36中各维度评分均较高,Y-BOCS评分较低,说明通过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可减轻强迫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这与宋晓红等[19]研究结果相似。分析其原因在于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借助团体的形式创造微型社会系统,加之通过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情感反映,不仅帮助患者逐渐展现自我和分享自身问题,引导其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不合理认知、信念、行为以及带来的负性影响,还便于治疗师了解患者思维和行为模式,有利于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强化认知重建、心理教育、暴露疗法、仪式行为阻止疗法、角色扮演等措施,可有效矫正患者错误认知,建立合理、积极的思维观念,有助于改变患者强迫行为,进一步促进生活质量的提升。此外,Braga DT等[20]研究也指出,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强迫症疗效确切,且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对强迫症患者采用团体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可有效降低其病耻感,增强服药依从性,有助于缓解强迫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较短,如能增加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其结果将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