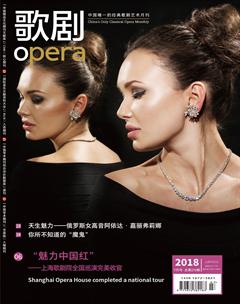歌剧音乐之根
韩万斋,在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期间是全校出名的《崇洋媚外》学生。他的附中、本科的三位作曲主课老师(杜勃兴、屠)台九、石夫)最早都是学西洋音乐的,杜勃兴更是一位非常熟悉现代派作曲技法的老师。他的几位忘年交师友——民乐指挥家、琵琶演奏家秦鹏章,最早是学单簧管的:民乐指挥家、作曲家叶语是中国交响乐史奠基人:非常热爱民族歌剧的刘诗嵘、荆蓝,一直都在专门排演西洋歌剧的中央歌剧院工作
他梦醒于一位录音师的话:《何必呢:你们写得累,人家演奏的人也累。》
不以《民族》为根的歌剧难以在世界上立足
現在音乐院校常提的一个词,是《中西方音乐比较》。这门课,我带了将近20年。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西方音乐史时,单就西方本身,也有很多需要《比较》之处。从西方音乐的野史、自传、书信、日记、采访……互相呼应或自相矛盾的字缝中,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很多真相。
譬如,古希腊调式和教会调式名称透露出的真相——基督教胜利了……窃取了民间调式:古希腊民间音乐的调式于是就《变》成了《教会(基督教)八大调式》:《格里高利圣咏》透露出的真相——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把民歌的歌词换成基督教的词,于是这些民歌就《变》成《圣咏》了。
又如,海顿特别爱在交响乐中用民歌主题,如他的《第104号交响曲《伦敦》,其中第四乐章的主部主题就是地地道道的《原生态》克罗地亚民歌:再往前推:巴赫、亨德尔……尽管音乐史书上都说的是《宗教音乐风格》,但实际上,如前所说:《宗教音乐风格》不就是来源于民间音乐吗?
那么,每个国家的音乐之根究竟在哪里?
俄罗斯作曲家,如格林卡,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曲调,都糅合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表达爱国主义思想,歌颂人民的功绩和美德。作品一经问世,立刻使他跻身于世界著名作曲家之林,至今声誉犹存。格林卡之后的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达尔戈梅斯基,他创作了许多声乐作品,最好的作品是歌剧《石客》和《水仙女》。《水仙女》的旋律脱胎于俄罗斯民歌,后来成为俄国民间最流行的歌剧之一。
德国作曲家,除了受意大利歌剧的影响外,还结合了本国的地方戏剧《歌唱剧》的特点。此外,音乐中常采用德国民间音乐素材。
再来看看法国。法国歌剧开始的时间比意大利歌剧晚了很多,当时的法国人希望能像意大利那样发展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歌剧,以此满足大众口味。比才的歌剧《卡门》中的音乐,就是地地道道的法国民间音乐风格。
还有捷克。尽管斯美塔那创作了《一个勃兰登堡人在波希米亚》,但被世人承认为真正的《捷克歌剧》的,还是音乐风格建立在真正捷克民间音乐基础上的《被出卖的新嫁娘》。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欣赏歌剧的习惯正在改变
西方国家似乎没有《民族歌剧》这一称谓。欧美发达国家的歌剧,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宫廷、教会、贵族控制在《歌剧院》里,专为被称为《上流社会》的宫廷、教会、贵族服务。而民间音乐则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前都被视为《俗乐》。其后,尽管在形式上给予了民间音乐名义上的《合法化》,但在宫廷、教会、贵族和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仍然难登《大雅之堂》。回顾一下当年《乞丐歌剧…‘真实主义歌剧》的遭遇,被宫廷、教会、贵族《包养》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音乐家》们,也必然地要尽量使自己远离《下流社会》——民间,并转而依赖和靠紧《上流》了。
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2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官方音乐机构——汉《乐府》,就将管理《俗乐》的部门与管理宫廷礼仪、祭祀音乐的部门平等对待了(汉高祖刘邦本人就是一位民族民间音乐的《粉丝》)。其后产生的各种半综合性、准综合性或综合性表演艺术,或在《雍门》,或在郊衢,或在勾栏瓦舍,即使建起了《万年台》,那也多是在村镇、县城的广场旷野。尽管也有过歧义,有过偏见,有过《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靡靡之音》《雅乐》《俗乐》之论,但它们从未完全离开过人民大众。因此,艺术欣赏,特别是音乐欣赏的《不平等》观念,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更不是我们固有的观念!
中华民族的歌剧史上,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情况。在西方的歌剧传入中国之前,已经有了比西方更早的综合性舞台艺术——戏曲。这一形式,不算参军戏、院本、南戏,仅从元杂剧开始,最少比西方的歌剧(1597年的《达芙妮》)早300多年。而在西方舞台上,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则一直以《科学化分工》明确的《话剧》《舞剧》《歌剧》等为主。
由于上述原因,无论你褒也好、贬也罢,中华民族的艺术欣赏习惯中,进剧场的心理预期,倾向于对《戏》和《剧情》的总是比《话》《舞》《歌》多一些。而西方人的艺术欣赏习惯中,对《话》《舞》《歌》的欣赏则更多一些。不过,有趣的是,近百年来,西方人欣赏歌剧的习惯也在渐变,向着《对‘戏和‘剧情的欣赏多一些》转变。这样,中外对舞台综合性表演艺术的审美要求,就渐趋一致、殊途同归了。
歌剧姓《歌》,为《歌》服务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标题为《音乐剧不是歌剧》。由于我从音乐学院附中到本科,再到工作、教书,无论看到、听到、读到、讲到歌剧时,都是把轻歌剧、喜歌剧、歌舞剧、乐剧和清唱剧、康塔塔等等打包、捆绑在一起,总是把它们归到《歌剧》的大范畴中的。也就是说,它们都属于歌剧这个大类之中。而芭蕾舞剧《白毛女》没有因为加了几个唱段就改名为《歌剧》,话剧《培尔·金特》也没有因为加了几段器乐就改名为《音乐剧》。那么,音乐剧从何而来?这篇文章论证来论证去,最后还是没把音乐剧论证到《歌舞剧》外面去,也就是说,它还是属于《歌剧》大类中的一支。不能因为在《歌》之外加了点什么东西,就把它逐出歌剧之外。
当然,正如歌剧大类中的清唱剧、康塔塔,话剧中的悲剧、喜剧,舞剧中的芭蕾舞剧、民族舞剧等等,在大类之外,另立个小类也不妨。大可不必在此问题上绕来绕去、争来争去。
有一位朋友问我,怎样用最简捷的语言表明歌剧与其他综合性舞台艺术之间的区别?我回答说:《戏曲姓《戏》,话剧姓‘话,舞剧姓‘舞,歌剧姓‘歌。》
什么意思呢?我的看法就是:戏曲的丰满——《曲》,靠《戏》来完成:话剧的高潮——《剧》,靠《话》来形成:舞剧的高潮——《剧》,靠《舞》来形成:歌剧的高潮——《剧》,靠《歌》来形成。
反之:戏曲的《曲》,是为《戏》服务的——是为了在它的完成过程中不断地推出一些精彩曲折或者发人深省的故事情节:话剧的《剧》,是为《话》服务的——是为了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地推出一些幽默诙谐或者哲理深蕴的名言警句:舞剧的《剧》,是为《舞》服务的——是为了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地推出一些技艺精湛或者美轮美奂的舞蹈段落:歌剧的《剧》,是为《歌》服务的——是为了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地推出一些优美深情或者脍炙人口的歌唱段落。
如此,好的歌剧,要善于找机会抒情(尽量充分地表达感情):好的乐剧,要善于找机会煽情(与器乐交响化地细绘心情、场景或掀起高潮):好的音乐剧,要善于找机会《发泄》(尽量充分地释放激情)。
歌剧与戏曲的关系
《学习》,并非照搬。中国的戏曲音乐是在中国民歌、中国曲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戏曲无论是在剧本创作、音乐创作、导演表演、舞美道具等各方面,都积累了中国独特的、丰富的经验。黄奇石同志提出《歌剧要向戏曲学习》,措辞非常精准!他并没有限定音乐素材与结构的选用,并没有限定完全按照戏曲模式……
《学习》,并非排它。我的研究生们问我:《写民族歌剧只能用戏曲音乐素材、只能用板腔体,不能用民歌、曲艺音乐吗?》我回答:《白毛女》不就用了民歌吗?少数民族的歌剧也非得用戏曲音乐、板腔体吗?你若当真完全套用某个戏曲的板腔,那和戏曲还有什么区别?——在恰当的地方、适当地应用是它的原则!》我的研究生们问我:《如何看现代主义音乐与后现代主义音乐?》我回答:《现代主义音乐——才情不够手艺凑:后现代主义音乐——灵感枯竭就忽悠。》当然,这是贬义的。
但是,我也鼓励我的学生们尽量多地学习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技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创作歌剧时,根本无法预料到会有什么情节、什么情绪,必须用什么技法。无论是古是今、是中是外,无论什么题材、什么体裁、什么风格、什么流派,手中掌握的技法越多,提起笔写作时越顺畅,越丰富。
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不管《洋》的、《土》的,都必须消化!生硬地复制粘贴,不是艺术!写得不好,无论你披羊皮、拉《洋》旗也好,穿马褂、抄戏曲也罢,都救不了你的《命》!
一《白》一《黑》、一《江》三《红》,都是我们民族歌剧、中国歌剧的经典。它们所体现出的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学原则和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实际上已经告诉了我们,在创作、演出歌剧时如何把握我们的分寸——中国的、歌剧的,不是唱歌:民族的、时代的,不是戏曲。
70多年了,歌剧《白毛女》之所以如艳阳般地照亮着中国民族歌剧的道路,使中国民族歌剧理直气壮地克难前进,就在于它所遵循的是人类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明的方向,是习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注入的正能量!
方向明确、正能量已足!我们牢牢扎根在民族沃土之中的民族歌剧,一定能够在世界剧坛上,烙上《中国歌剧》四个闪闪发光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