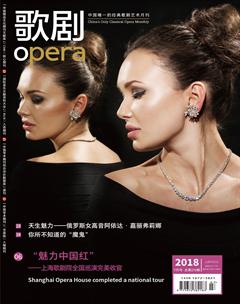终于等到不一样的音乐剧《贝隆夫人》
周凡夫
如果从1978年6月21日在伦敦爱德华王子剧院首演算起,音乐剧《贝隆夫人》到今年已经面世40年,竟然比这位原名伊娃·贝隆,曾贵为阿根廷第一夫人,还当过副总统的南美女强人在世的岁月还长(1952年贝隆夫人病逝时才33岁)。香港观众也是等待了40年,才得以在今年5月于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观赏了这部作品。
少见的《严肃题材》音乐剧
安德鲁·洛伊德·韦伯与蒂姆·赖斯(Tim Rice)是一对黄金搭档,继《约瑟的神奇彩衣》,和《万世巨星》后,《贝隆夫人》是两人再度携手作曲作词的第三部音乐剧。两人合作的这前两部音乐剧,以及韦伯后来创作的《猫》(Cats,1981)和《剧院魅影》等著名音乐剧在香港多次公演后,港、澳音乐剧迷才等到《贝隆夫人》的到来,这多少和该剧的内容及手法有关。
和韦伯其他著名音乐剧相比,《贝隆夫人》是以现代政坛人物的真人真事为蓝本写成的音乐剧制作。故事发生于1934年至1952年间,讲述了15岁的伊娃(Eva Duarte),从一个受尽社会歧视的乡间私生女成为阿根廷政治人物胡安·贝隆(Juan Peron)的第二任妻子,并进而成为第一夫人并权倾阿根廷的传奇一生。这样的女性人物,确如蒂姆·赖斯所言,应是普契尼笔下意大利歌剧的女主角。至于将之写成音乐剧,首要考虑的却是《市场价值》。
传统上音乐剧的《市场价值》建立在为观众制造一个能离开现实的开心世界基础上,但看完《贝隆夫人》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后,观众能感受到其与韦伯的作品,甚至是和其他作曲家的音乐剧很不一样。故事欠缺了浪漫的爱情情节,更多的是具有争议性的政治色彩。贝隆夫人的政治权力人生固然传奇,她的早逝也令人同情,但更令人反思的很可能是人对权力的追求,人与国家、人民的关系,这确实是音乐剧中少见的《严肃题材》。
奇特男主角切·格瓦拉
这个音乐剧女主角当然是贝隆夫人,奇特的却是男主角并非政治家贝隆——充其量他只能算是大配角。男主角是从序幕《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影院》中群众合唱《贝隆夫人安魂曲》(Requiem for Evita)后便出场的切·格瓦拉,古巴共产革命的核心人物。这位人物之所以成为这部音乐剧男主角的原因,和其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阿根廷历史为背景的特别之处很有关系。
很多人不知道,切·格瓦拉这位曾被《时代》杂志选为20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他是在阿根廷出生、成长的共产主义者,其家族在阿根廷已生活了十二代,声誉卓著,他的姨父姨母皆为阿根廷的共产党党员。切·格瓦拉1948年入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科,1950年游历了阿根廷北部12个省,走过4000多公里后,休学一年,与友人开着摩托车环游整个南美洲,开始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成型。格瓦拉于1952年9月回到阿根廷,彼時贝隆夫人已病逝。他回大学补念完医科,1953年3月完成学业,却未当医生,离开阿根廷在南美洲多个国家搞革命。1959年古巴共产革命成功后,被授予古巴公民身份,才成为古巴人。
切·格瓦拉在古巴共产政权中可谓权重一时,但1965年他却离开古巴,到非洲去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后来回到玻利维亚,1967年10月9日被逮捕并遭处决。死后他的肖像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标志,并被推崇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成为世界左翼运动的象征。
贝隆夫人变得更立体化
剧中的这位《男主角》,自始至终大部分时间都以切·格瓦拉这一鲜明的肖像形象出现。奇特的是,这位人物在剧中很多时候都像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批评者,以他的价值观来评说贝隆夫人的故事情节,有时则又扮演剧中的记者等不同人物,这种时而抽离、时而在剧中的手法,贯穿全剧,这在为观众制造脱离现实的音乐剧中很少用上。这位男主角的存在,呈现出了社会对当时独裁的军政府和阿根廷国母的反面声音,却能将贝隆夫人更立体化、人性化,而不仅仅是歌功颂德地塑造《圣贝隆夫人》(Santa Evita)。很明显地,这种处理手法,会为观众带来更多反思。
不仅如此,全剧以贝隆夫人最后一次全国性广播,她的病逝葬礼、追思,以及切·格瓦拉的旁白《民众为她筑墓纪念,但她的遗体失踪了17年》作为最后的高潮,暗灯落幕结束,留下一段让人遐想的悬念——这显然也与一般音乐剧经过重重艰难险阻、一一解决问题,最终大团圆结局的处理手法很不一样。
然而,即使在政治成熟的西方社会,这样严肃的《政治题材》和间离手法,也不一定能在娱乐至上的音乐剧市场中赢得票房。幸好《贝隆夫人》1978年在伦敦首演,1979年登上美国百老汇后,已赢得超过20个业界大奖,包括奥利弗奖与托尼奖。加上1996年被改编成电影,由乐坛天后麦当娜(Modonna)担任主演,又为之打上一剂推向国际舞台的强心针。
剧场元素丰富,可观性强
其实作为剧场制作来看,《贝隆夫人》堪称是一部可观性很强、剧场元素丰富且组合得很有效果的制作。这其中还包括多媒体投影的运用,从序幕的1952年7月26日于电影院放映电影时突然终止,宣布贝隆夫人的死讯:到伊娃初抵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用作投放首都城市的风光介绍:当然还有第二幕著名的阳台演说场景,荧幕投影则转为阳台大楼背景,阳台上各人转身,荧幕画面投影的则是成千上万的群众场面。随后几场还通过投影展现了阿根廷当年社会动荡下的各种街头场面的纪录片,大大加强了音乐剧的真实性。
简约的布景虽然无大的可观性,但灯光的丰富变化,将第一幕的十三场,和第二幕在间奏曲后的十五场等不同场景的变换做了很好的交代。伊娃与贝隆邂逅的场景,配合一对华美礼服的男女(身着如烈火般触目的舞衣),在旁翩翩起舞,到第二幕贝隆夫人走到人生最后阶段时,这对华美舞服的男女再现舞台,前后呼应,寓意呼之欲出。
此外,有趣的场面亦不少,包括第一幕伊娃结识歌手阿古斯丁·马加尔蒂(Agustin Magaldi),高唱《在干星之夜》(On This Night of a Thousand Stars)时,伊娃却诱逼对方将她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后来到了首都,伊娃用身体交换利益,先后和七位男朋友分手高唱《谢谢你,晚安》(Goodnight and Thank You)的设计(切·格瓦拉在这场戏中仿如《皮条客》一般):更有趣的是交代阿根廷军政府的混乱政坛的场景,五位军人各据摇椅,在有如《大风吹》的游戏下,摇椅逐次减少,离场者不断增加,最后只剩下贝隆一人。
同时,全剧的转接处理也很有心思。贝隆夫人与切·格瓦拉对唱《伊娃和切的华尔兹》(The Waltz for Eva And Che),两人以相互进进退退的快速独特舞步进行《对决》,让这两位历史人物进行交锋。大家都关心国家,关心贫苦大众,但政见不同,角度不同,如何去定义对错?这一对决的结果是贝隆夫人病发了,在权力争逐,肩负国民重大期望的重担之下,伊娃这位被人民视为救星的国母倒下了,剧情由此急转直下……
拉丁摇滚古典共冶一炉
不过,作为音乐剧,至为重要的仍是音乐。可以说,全剧至为感人的仍是早已成为流行曲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这首主题曲的音调,在全剧中不仅成为好几段歌曲的素材,且多次填上其他歌词唱出。在第二幕(下半场)间奏曲完结,出现历史性的场面《阳台演说》(On The Balcony of the Casa Rosada),贝隆夫人在阳台上首次唱出,以之来号召国民支持:到最后病重对全国国民广播时,再度唱出,而且唱到一半时,贝隆夫人已泣不成声,要由民众轻声和唱才能振奋起来续唱下去,成为至为感人的一场戏。而这首主题曲亦成为这部音乐剧的《招牌名曲》,除了旋律动听,更在于歌词道出了伊娃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深厚真挚感情,让在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上有很大分歧的人士也会为之动容。这可是每一个国民与自己祖国难以割裂的情感啊!
此外,伊娃入主贝隆家,将其情妇赶走,情妇所唱的一曲《换个衣箱换间房》也很动听,这位一曲角色,也因此曲得以名列于主要角色表上。
其实,这份演员角色表只有五位。按出场顺序,首先是南非男高音乔纳森·洛斯莫夫(Jonathan Roxmonth)扮演的《百变人》切·格瓦拉:毕业于伦敦的名校山景戏剧艺术学院(Mountview Academy of Theatre Arts)的女中音爱玛·琼斯顿(Emma Kingston)扮演贝隆夫人;男高音安东·卢廷吉(Anton Luitingh)扮演歌手马加尔蒂:出身于南非开普敦大学戏剧学院的男中音罗伯特·芬利森扮演胡安·貝隆,女中音伊莎贝拉·简(Isabella Jane)扮演情妇。尽管他们都非名气响亮的著名歌唱演员,但表现都很称职,乔纳森的唱段变化最多,且是几乎演足全场的高分量角色,奈何无一首能成名的曲目。爱玛的声线可塑性很强,乡村少女时的尖脆,到病倒后的沉厚,极具感染力。较可惜的是罗伯特的贝隆,与伊娃邂逅时,及在其弥留时的二重唱,都未能流行。
不过,尽管这部音乐剧的流行名曲不多,但带有拉丁韵味的节奏明快的乐曲却很有特点,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财富不断流进流出》和《在干星之夜》,拉丁节奏很有动感:其中亦有摇滚乐节奏的歌曲,如《马戏团》(Oh What a Circus)和《贝隆最后的火花》,亦有抒情的歌谣,如《高飞,崇拜》(High Flying,Adomd)和《换个衣箱换间房》:此外,序曲后的第一首合唱曲《贝隆夫人安魂曲》,和剧中很多器乐过门则明显是《古典音乐》的风格形式和手法。可以说,整部音乐剧的音乐,包罗了拉丁、摇滚、歌谣和古典等多种风格,共冶一炉,拼贴融合得几乎天衣无缝,因而全剧节奏明快,绝无丝毫冷场。
另一方面,当代音乐剧巡演的乐队人数大多缩减,这次列于场刊的乐队名单,连同指挥音乐总监合计10人,半场休息细看乐池中,可见有三台键盘,还有小号、长号、木吉他及电子吉他、低音吉他、低音提琴、鼓及打击乐器。也就是说三台键盘取代了很多乐器,但音效难免打了折扣,最明显的是第一幕结束前的《新阿根廷》(A New Argentina)的大场面,气势上打了折扣。
历史人物加工又爱又恨
话说回来,尽管这是一部直接标榜是真人真事的音乐剧,但《艺术加工》是难免的。切·格瓦拉和贝隆夫人虽然都是历史名人,但就两人的人生历史轨迹而言,相互交叠的机会并不多,像剧中直接交锋对决的场面,只是舞台上的设计,追求戏剧性的效果而已。同样,最后由格瓦拉说出的那句名言《民众为她筑墓纪念,但她的遗体失踪了17年》,现实确实是贝隆夫人的遗体失踪了17年,直到1971年才自米兰回归故土。
同时,从全剧的剧本歌词撰写,能看出蒂姆·赖斯借着切·格瓦拉的口,道出了他对贝隆夫人这个人物的看法。表面看来负面的多,处处对之做出不留情的鞭挞,但现实中却很可能是又爱又恨,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女儿以贝隆夫人的名字来命名呢!
《贝隆夫人》此次亚洲巡演,香港站于5月11日开演到6月10日结束,共计演出了37场,演期不算长,下一站是日本。香港站的纪念特刊,只有封面加有《贝隆夫人》的中文,内文全是英文,这好像已经是香港的外来音乐剧制作的《常态》。其实2006年和2014年《剧院魅影》两次在香港的演出的纪念特刊,都附译有不少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