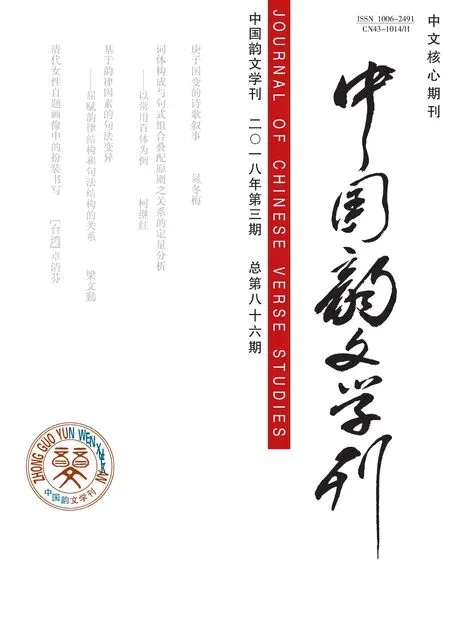扬雄五官箴非原作考辨
王允亮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关于扬雄官箴的流传情况,《后汉书·胡广传》载:
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
这段记载成为后人考察官箴流传的基本信息,也是我们进一步探讨其真伪的重要依据。严可均《全汉文》辑录扬雄官箴作品之后说:
谨案:后汉《胡广传》:“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駰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乃悉撰次首目,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如传此言,则子云仅存二十八箴。今遍索群书,除《初学记》之《润州箴》,《御览》之《河南尹箴》显误不录外,得州箴十二,官箴二十一,凡三十三箴。视东汉时多出五箴。纵使《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可属崔骃、崔瑗,仍多出一箴,与《胡广传》未合。猝求其故而不得,覆审乃明。所谓亡阙者,谓有亡有阙,《侍中》《太史令》《国三老》《太乐令》《太官令》五箴多阙文,其四箴亡,故云九箴亡阙也。《百官箴》收整篇不收残篇,故子云仅二十八箴。群书征本集,本集整篇残篇兼载,故有三十三篇。其《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艺文类聚》作扬雄,必可据信也。
按:严氏注意到扬雄传世官箴篇目数与《胡广传》所言不合,断定扬雄流传下来的官箴篇目不止二十八篇,认为亡阙九篇并非九篇尽失,乃所谓九篇内有亡有阙也,以为这样就解决了扬雄传世官箴篇目与《胡广传》所言不符的难题。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今人对扬雄官箴作品的判定多从其说,但实际上却未必准确。如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中就说:“汉成帝时扬雄爱《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后亡失九篇。”可见亡阙与亡失并无区别,皆指亡佚而言,并不是严氏所言的有亡有阙共为九篇。
既然如此,那么亡失的九篇又是哪些呢?严氏说:“今遍索群书,除《初学记》之《润州箴》,《御览》之《河南尹箴》显误不录外,得州箴十二,官箴二十一,凡三十三箴。视东汉时多出五箴。纵使《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可属崔骃、崔瑗,仍多出一箴,与《胡广传》未合。”扬雄官箴作品共三十七篇,严氏辑得三十三篇,其中《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署名有争议,即使除去此四篇仍得二十九篇,按《胡广传》所言三十七篇亡失九篇当为二十八篇,两者仍有一篇的出入。因数目上无法契合,所以严氏干脆认为这五篇都是扬雄的原作。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在严氏认为没问题的二十九箴中,仍旧有一篇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交州牧箴》。我们来看看《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爰自开辟,不羁不绊。周公摄祚,白雉是献。昭王陵迟,周室是乱。越裳绝贡,荆楚逆叛。四国内侵,蚕食周京。臻于季赧,遂以灭亡。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羁,遂臻黄支。杭海三万,来牵其犀。盛不可不忧,隆不可不惧。顾瞻陵迟,而忘其规摹。亡国多逸豫,而存国多难。泉竭中虚,池竭濑干。牧臣司交,敢告执宪。
据《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又《汉书·地理志》:“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交州牧箴》中“稍稍受羁,遂臻黄支。杭海三万,来牵其犀”写的就是这件事。对于扬雄官箴的写作年代,大致有初始元年(公元8年)和元始四年(公元4年)至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之间两种观点,均以王莽元始四年将十三州改成十二州为扬雄官箴创作的时间上限。但官箴中有《廷尉箴》一篇,而廷尉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已经改名为大理。如果官箴创作于此时,就不应该再称为《廷尉箴》,而应名为《大理箴》。其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但这一点往往被学者忽视了。其实,成帝末年也曾有州制改革,并以《尚书·尧典》之义,将十三州改为十二州。因此,扬雄的官箴创作应该在成帝绥和元年末至二年初(前8年左右),早于黄支国献犀牛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约十年。扬雄不大可能用到十年后的典故,这说明《交州牧箴》并非其原创之作,应出自后人的补苴。
如果将剩余二十九篇官箴中的《交州牧箴》再减去,正好符合《胡广传》所言三十七篇,亡失九篇,存二十八篇的情况。因此,胡广所言的亡阙九篇应指《交州牧箴》《司空箴》《尚书箴》《太常箴》《博士箴》与其他失传的四篇而言,严氏所辑的残缺之作,胡广时可能保存仍较完整,或者虽有残失,但他显然没有将它们列入亡阙之列。
除《交州牧箴》之外的四篇:《司空箴》,《艺文类聚》四十七作扬雄,《初学记》卷十一作崔骃;《尚书箴》,《艺文类聚》四十八作扬雄,《古文苑》卷十五作崔瑗;《太常箴》,《艺文类聚》四十九作扬雄,《初学记》卷十二作崔骃,《古文苑》卷十五作崔骃;《博士箴》,《艺文类聚》四十六作扬雄,《古文苑》卷十五作崔瑗,作者归属均有争议。对于归属有争议的这四篇作品的判定,严氏仅言:“其《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艺文类聚》作扬雄,必可据信也。”至于为什么可以据信却没有给出理由。严氏仅依据《艺文类聚》单文孤证,不顾《初学记》和《古文苑》中的不同记载,遽断定《司空箴》等四篇为扬雄所作实嫌武断。其实,如果仔细考察这四篇作品,就会发现将它们归于扬雄名下均存在问题。
我们先来看《司空箴》:
普彼坤灵,侔天作则。分制五服,画为万国。乃立地官,空惟是职。茫茫九州,都鄙盈区。纲以群牧,缀以方侯。列列隽乂,翼翼王臣。臣当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赋以均。昔在季叶,班禄遗贤。掊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力斯人,匪政斯敕。流货市宠,而苞苴是鬻。王路斯荒,孰不倾覆。空臣斯土,敢告在侧。
此作无论名称还是内容,都和扬雄创作官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四月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三月改大司空为御史大夫,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御史大夫复为大司空。可见在成帝末期,御史大夫名为大司空,据《后汉书志·百官志》注:
应劭《汉官仪》曰:“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狱司空,故复加‘大’,为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
可见御史大夫名为大司空,是为了和县道官的狱司空相区别,所以此处的“大”字是不能省略的。《后汉书志·百官志》又载:
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大丧则掌将校复土。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足知汉代的司空官一直到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以后才出现,之前则一直名为大司空。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
足知御史大夫虽然在成帝末年改称大司空,但其职能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负责图籍秘书,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等事务,这些职能与《司空箴》所言明显不是一回事。因此,无论从作品的标题还是内容来看,《司空箴》都不会是扬雄的作品,其作者应另有其人。
接下来再看《尚书箴》:
皇皇圣哲,允敕百工,命作斋栗。龙惟纳言,是机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献善宣美,而谗说是折。我视云明,我听云聪。载夙载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风,动于民人。涣其大号,而万国平信。《春秋》讥漏言,《易》称不密则失臣。兑吉其和,巽吝其频。《书》称其明,申申其邻。昔秦尚权诈,官非其人。符玺窃发,而扶苏陨身。一奸愆命,七庙为墟。威福同门,床上为辜。书臣司命,敢告侍隅。
“龙惟纳言,是机是密。出入王命”一句,《古文苑》“出入王命”作“出入朕命”,此处明显用了《尚书》“帝曰:‘龙,朕即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的典故。但除此之外,其中“是机是密”一语,则另有出处,东汉应劭《汉官仪》引用汉明帝的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尚书,盖古之纳言,出纳朕命,机事不密则害成,可不慎欤!”此处“是机是密”明显出自于此。另外,“出入王命,王之喉舌”一句亦有出处,东汉李固在对策中说:“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海。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李固将尚书出纳王命,喻为王之喉舌,为《尚书箴》所袭用。这就表明它的创作年代至少要在李固以后。再考虑到扬雄时期尚书一职仅止于在皇帝身边收发文书,于朝廷政令并未发生重要影响,而东汉光武帝为了贬抑三公之权,大幅度提高尚书的权力,使位卑秩微的尚书,一跃而成为帝国官僚中枢机构运转中的重要环节,与本箴所言情况较为相符。所以现存《尚书箴》也不可能是扬雄的原作,应是后人的补苴之作。
我们接着来看《太常箴》:
翼翼太常,实为宗伯。穆穆灵祗,寝庙奕奕。称秩元祀,班于群神。我祀既祗,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报。不矫不诬,庶无罪悔。昔在成汤,葛为不吊,弃礼慢祖。夔子不祀,楚师是虏。鲁人跻僖,臧文不悟。文隳太室,桓纳郜赂。灾降二宫,用诰不祧。故圣人在位,无曰我贵,慢行繁祭。无曰我材,轻身恃巫。东邻之牺牛,不如西邻之麦鱼。秦殒望夷,隐毙钟巫。常臣司宗,敢告执书。
其文末云:“常臣司宗,敢告执书。”因为春秋时鲁有宗伯掌宗庙祭祀,太常职责同乎此,所以文中言“翼翼太常,实为宗伯”,这里说“司宗”看似照应旧典,没什么问题。可是,在同为扬雄名下的另一篇《宗正箴》末也说:“伯臣司宗,敢告执主。”因为周室曾有宗伯掌管宗室之事,彤伯曾为周成王宗伯,箴文亦言“经哲宗伯,礼有攸训”,这样说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它们因旧称宗伯,两篇官箴中单独说“司宗”都可以,但是如果同时提出来,则面临不能回避的问题:两篇官箴都言“司宗”,这里的“宗”有没有意义上的区别?我们知道太常和宗正在西汉时都属于九卿系统,二者所司不同,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太常负责宗庙祭祀,宗正负责统领皇室宗亲,二者各司其职,互不混淆。这样的话,两者虽同言“司宗”,势必有所区别。但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扬雄同时创作这两篇官箴,他会用同样的字眼来指代两种官职吗?尤其是可能给皇帝看的作品更应谨慎细致,在需要表明身份的关键字眼上,他却用毫无区分度的同一词语来提示,且文中均出现易滋混淆的“宗伯”字样,这一切不免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其中缘由何在?其实,《太常箴》作者《艺文类聚》四十九署作扬雄,《初学记》卷十二和《古文苑》卷十五却均署作崔骃,其作者的疑莫能名已经透露出其中端倪。这两篇作品可能本来就不是一人创作的,只是后人将它们归并于一处了。我们知道扬雄的官箴创作于成帝末年,其时太常和宗正的官职名称均未改变,因宗正官名中“宗”字的凸显及其管理皇室宗亲的权责,《宗正箴》出于和官职呼应的修辞考虑,用到“司宗”一语的可能性更大。但就因已经于《宗正箴》中使用此语,扬氏也更不可能在《太常箴》中再原样袭用。再根据《初学记》和《古文苑》透露出来的蛛丝马迹,我们大致可以判定,现存的《太常箴》应是后人的拟补之作,只是在流传过程中不慎被并入扬雄名下而已。
最后来看《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礼是修,画为辟雍。国有学校,侯有泮宫。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经启其轨,勖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桢,惟周以宁。国人兴让,虞芮质成。《公刘》挹行潦,而洒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昔圣人之绥俗,莫美于施化。故孔子观夫人大学,而知为王之易易。大舜南面无为,而衽席平还师。阶级之间,三苗以怀。秦作无道,斩决天纪。漫彼王迹,而坑夫术士。诗书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陈,而颠其社稷。故仲尼不对问陈,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学,而闵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宾。
文末云“儒臣司典,敢告在宾”,此处之“在宾”何解?有学者解释为师居宾位,因为居于宾位的一般是身份尊贵的师者,所以此处“在宾”指代师者;又因汉时博士具有师者之尊,于礼居于宾位,所以也有学者将“在宾”释为指代博士。这两种解释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师居宾位,《后汉书·桓荣传》:“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汉明帝为了尊崇桓荣,特命他东面居于师位,自己则以学生的身份讲经讨论。这里的东面是什么位置呢?《仪礼·士冠礼》:“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阶下,直东序西面。”郑玄注:“阼,犹酢也。东阶,所以答酢宾客也。堂东西墙谓之序。”又云:“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宾西序,东面。”可见在庄重的礼仪活动中,主人位东面西,宾客位西面东,东面即是宾位。因此,说师者身份尊贵居于宾位没有问题。扬雄此处不言“敢告于宾”而言“敢告在宾”,可见在宾位的应是非宾客的他人,常居宾位的师者自然可能性最大。再看第二个问题,博士是不是该居于宾位?《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公孙弘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此奏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后博士即具有传经授业的职责,是当之无愧的师者。因博士有师者之尊,于礼居宾位,“在宾”可指代博士自然也没有问题。
但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博士成了此箴“敢告”的承受者,《博士箴》的箴谏对象也变成了博士,而非大家通常认识中的皇帝。由于“敢告在宾”的上句是“儒臣司典”,其中言有“臣”字,似乎只有针对皇帝时才能这么说,其实不然,我们看东汉崔琦《外戚箴》中的一段:
故曰: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迟;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杖势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据《后汉书》所载:“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则此箴为讽谏外戚梁冀之作,但最后却也以“微臣”自称,可见其时在对皇帝以外的人箴谏时称臣亦未尝不可。
由于博士一职的师者色彩,以及师者于礼居宾位的礼仪传统,《博士箴》中“敢告在宾”一语,便将箴谏对象指向了博士官,而这和扬雄官箴文的做法有着显著不同。我们知道,扬雄的官箴秉持的是官箴王阙的理念,其箴文的箴谏对象是皇帝,《博士箴》在这方面的特点说明,它显然不是扬雄的作品。由于以官箴箴官阙的风气起自东汉,如崔琦的《外戚箴》和高彪的《督军御史箴》均为此类,而扬雄创作官箴时尚无这种情况,所以此箴也应该是误入扬雄名下的后人之作。
通过以上分析来看,这四篇在《初学记》或《古文苑》中标为他人的作品,都被证实非扬雄所作。根据这个规律,再结合《胡广传》所言扬雄官箴亡佚九篇,崔骃及子瑗与刘騊駼等曾予增补的记载,则此四箴应均为后人之作,只是由于作品风格和名称上的相似,在流传中和扬雄的作品相混淆了。胡广生活年代大致与崔瑗同时,尚能分清其中的不同,可以将后人之作与扬雄原作区别开来,指出包括这四篇作品在内的九篇扬雄原作均已亡佚。只是不知是因为后人没有对其他几篇进行拟写,还是它们再度亡佚的原因,只有包括《交州牧箴》在内的五篇流传下来,其他四篇仍然付之阙如。
由于崔瑗在《叙箴》中说:“昔扬子云读《春秋传》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为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规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体国之宗也。”所以有一种意见认为扬雄只作了九篇州箴,十二州箴的后面三篇是后人的伪作。其实“九州”一词在汉代的含义相当含糊,既可以指确实的九个州,也可以指整个国家,前汉如桓宽《盐铁论·忧边》:“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咏《雅》《颂》,外鸣和銮,纯德粲然,并于唐、虞,功烈流于子孙。”后汉如王符《潜夫论·遏利》:“守志于一庐之內,而义溢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载之上,而名传乎百世之际。”这都是在全国已经分为十三州或十二州的情况下,仍以九州代指国家的例子。因此,崔瑗《叙箴》中的九州箴当指国家全境之箴,而不能限定为九篇州箴。最重要的是,胡广(公元91—172年)和崔瑗(公元77—142年)生活年代相当,据《后汉书·崔瑗传》记载,汉安帝初年胡广还曾经和窦章共同举荐过崔瑗,这说明胡、崔二人间是有所交往的。胡广对崔骃、崔瑗父子为扬雄官箴做的增补工作十分清楚,如果崔瑗能知道扬雄只做了九篇州箴,胡广岂容不知?而且后世也很少有人对十二州箴的说法提出过异议,这足以说明扬雄所作的州箴是十二篇而非九篇,所谓后面三篇皆系伪作的说法是有问题的。